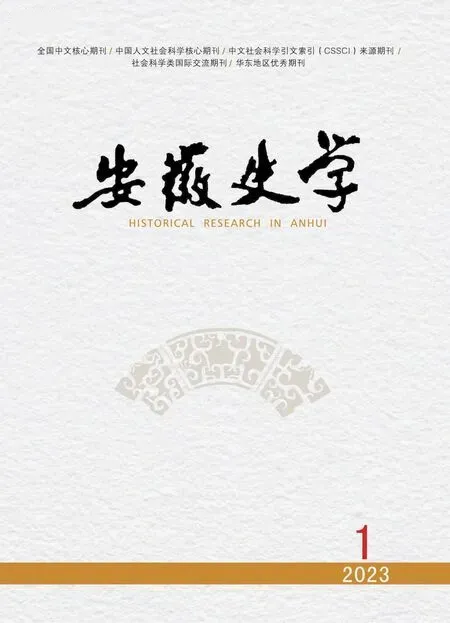惟老孔墨三宗:夏曾佑与先秦诸子叙事体系的建构
2023-10-07李长银李佳煌
李长银 李佳煌
(山东大学 儒学高等研究院,山东 济南 250100)
一般认为,夏曾佑是清末“新史学”思潮的主要推动者,实则其还是清末诸子学复兴的重要参与者。1903年,夏曾佑在《新民丛报》连载《中国社会之原》,集中探讨了先秦学术的变迁,以期揭示中国社会发展之原。1904年,夏曾佑出版《最新中学教科书中国历史》第一册,进一步发挥其“总以发明今日社会之原”的旨趣,于周秦之际,详于论述“诸家之学派”。(1)夏曾佑:《最新中学教科书中国历史》,杨琥编:《夏曾佑集》下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版,第824—839、911—912、947页。进而言之,夏曾佑在这些论著中率先提出了老子为“九流之初祖”、孔子为“政教之原”、墨子与孔子成“相反之教”以及老孔墨三家流为诸子百家等一系列学术观点,建构了一个较为完整的先秦诸子叙事体系,从而推动了中国诸子学的近代转型。
关于夏曾佑的先秦诸子学论述,民国学界曾予以高度好评。1923年,蔡元培在《五十年来中国之哲学》中将夏曾佑视为这一时期整理古代哲学的代表性学者,并大段摘录其关于先秦诸子的论述。(2)蔡元培:《五十年来中国之哲学》,高平叔编:《蔡元培全集》第4卷,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370—375页。至1941年,周予同在《五十年来中国之新史学》中则强调,夏曾佑在《最新中学教科书中国历史》中“着眼宗教与哲学相嬗之故,于老、孔、墨三家之‘道’,周、秦之际的学派”,“都另立专题”,其“识力”是非常“敏锐”的。(3)周予同:《五十年来中国之新史学》,朱维铮编校:《周予同经学史论》,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第371页。然而,当代学术界不仅未能予以充分关注,而且所论还存在显著的分歧。(4)如李洪岩认为夏曾佑 “试图从政治、宗教、风俗三方面,探寻中国社会与历史的最终奥妙所在,却未得出任何有价值的结论”(李洪岩:《夏曾佑及其史学思想》,《历史研究》1993年第5期)。也有学者认为,夏曾佑对老子的评价“时至今日犹没有过时”(陈其泰:《夏曾佑对通史撰著的贡献》,《史学史研究》1990年第4期)。于今来看,前者无疑是站在事后的立场对当时人进行批评,且过于绝对;而后者的看法颇能成立。因此,本文拟从学术史的角度对夏曾佑的先秦诸子叙事体系进行一次较为系统的探讨,进而评估其在中国近代诸子学史上的思想价值与学术意义。
一、老子为“九流之初祖”
先秦诸子有“百家”之说。其中最先出者,有老子、孔子。根据《庄子》《礼记》《史记》等典籍的相关记载,孔子曾问学于老子。但最迟在宋代,即有学者对老子年代提出质疑,认为老子在孔子之后。(5)罗根泽:《〈古史辨〉自序》第6册,海南出版社2005年版,第10—11页。至晚清时期,这一分歧还仍然存在。康有为认定,老子是孔子后学。(6)康有为:《万木草堂口说》,《康有为全集》第2集,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142—143页。但其弟子梁启超则坚持认为,老子在孔子之先。(7)梁启超:《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梁启超全集》第2册,北京出版社1999年版,第565页。直到1922年,梁启超提出“《老子》作于战国之末”说,引发了一场关于老子其人其书年代的学术论争。李长银:《梁启超“〈老子〉作于战国之末”说的建立及其意义》,《安徽史学》2021年第5期。因此,究竟以老子还是孔子为诸子的开端,无疑就成为了夏曾佑治先秦诸子必须正视的问题。
夏曾佑虽然推崇孔子,但仍然取信于《史记》,认为“孔子者,老子之弟子”;而且强调说:“欲考孔子之道术,必先明孔子道术之渊源”;“孔子之道,虽与老子殊异,然源流则出于老”;“老子之宗旨见,而后孔子之教育亦可推”。因此,“欲知孔子者,不可不知老子”。总之,夏曾佑认为,老子“其生最先”,为“九流之初祖”。(8)⑤⑧⑩夏曾佑:《最新中学教科书中国历史》,《夏曾佑集》下册,第824、829,824,825—828,828,828,828—829页。
但问题在于,老子虽然“其生最先”,他是如何成为“九流之初祖”的呢?夏曾佑指出,“老子生于春秋之季,欲知老子,又必知老子以前天下之学术”;“老子以前之学术明,而后老子之作用乃可识”。(9)⑤⑧⑩夏曾佑:《最新中学教科书中国历史》,《夏曾佑集》下册,第824、829,824,825—828,828,828,828—829页。因此,分析“老子以前之学术”就有了必要性。受汪中的影响(10)时人钱穆指出,夏曾佑在《最新中学教科书中国历史》中关于“孔子以前之宗教”的两节内容“多抄汪中氏《述学》”。钱穆:《评夏曾佑〈中国古代史〉》,《中国学术思想史论丛(六)》,《钱宾四先生全集》第23册,台湾联经事业出版公司1998年版,第284页。,夏曾佑提出,“老子以前之学术”为“鬼神术数”。自古以来,即有鬼神之说。“鬼神派者,起于人类思想最简单之时,凡根尘所接举,以为无因之果,必有一神物以司之”。而所谓鬼神,有天神、地祇、人鬼、物鬽。(11)夏曾佑:《中国社会之原》,《夏曾佑集》上册,第62、63、63页。“术数”因“鬼神”而后起。“世间之事,无一不若有鬼神主宰乎其间,于是立术数之法,以探鬼神之意,以察祸福之机”。而所谓术数,可分为天文、历谱、五行、蓍龟、杂占、形法。(12)⑤⑧⑩夏曾佑:《最新中学教科书中国历史》,《夏曾佑集》下册,第824、829,824,825—828,828,828,828—829页。要而言之,夏曾佑认为,春秋以前,“鬼神术数之外无他学”。(13)夏曾佑:《最新中学教科书中国历史》,《夏曾佑集》下册,第828页。其实,除了“鬼神”与“术数”之外,春秋以前的学术思想尚有“天”和“祖”。杨东莼:《中国学术史讲话》,北新书局1932年版,第11—18页。
至于“春秋以后,鬼神术数之外,尚有他种学说”。那么,春秋以后为什么会出现其他学说呢?夏曾佑提出,“人事进化”是主要原因。“春秋之时,人事进化,骎骎有一日千里之势,鬼神术数之学,遂不足以牢笼一切。”(14)⑤⑧⑩夏曾佑:《最新中学教科书中国历史》,《夏曾佑集》下册,第824、829,824,825—828,828,828,828—829页。进言之,“春秋之季,天下亦稍稍异矣。生殖日繁,竞争日烈,交通日便,知见日新,腐败日深,衅漏日见,五帝三王之道,渐不足以约束人群”。(15)夏曾佑:《中国社会之原》,《夏曾佑集》上册,第62、63、63页。因此,“春秋之末,明哲之士,渐多不信鬼神术数者”。(16)⑤⑧⑩夏曾佑:《最新中学教科书中国历史》,《夏曾佑集》下册,第824、829,824,825—828,828,828,828—829页。
而“一洗古人之面目”,开“九流百家”的是老子。那么,老子为什么能够“一洗古人之面目”呢?夏曾佑指出,主要在于其是“周守藏室之史”。具体而言,“周制,学术、艺文、朝章、国故,凡寄于语言文字之物,无不掌之于史”;“世人之咨异闻,质疑事者,莫不于史”;“史之学识,于通国为独高”。(17)⑤⑧⑩夏曾佑:《最新中学教科书中国历史》,《夏曾佑集》下册,第824、829,824,825—828,828,828,828—829页。换言之,“史之外无载籍焉,史之外无学问焉,故蜕化之机,其象虽现于全群,而其端必开之于史”。“盖当天下之学皆归于史之时,天下固愚,而史不必皆愚”。“史之中,必有知鬼神术数之不足以尽造化之原者”。(18)夏曾佑:《中国社会之原》,《夏曾佑集》上册,第62、63、63页。而老子正是“周守藏室之史”,有“犹龙之资,读藏室之富”。因此,当“蜕化之时”,老子著书上下篇。(19)⑤⑥⑧夏曾佑:《最新中学教科书中国历史》,《夏曾佑集》下册,第828—829、829、839、829页。
其实,早在夏曾佑之前,即有学者重视“史”的作用。清代学者汪中在《述学》中认为,春秋以前,“天道、鬼神、灾祥、卜筮、梦之备书于策者”,此“史之职”。(20)汪中:《述学》,辽宁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第25页。龚自珍则在《古史钩沉论二》中指出:“周之世官大者史。史之外无有语言焉;史之外无有文字焉;史之外无人伦品目焉”。五经是“周史之大宗”,而诸子是“周史之小宗”。(21)龚自珍:《古史钩沉论二》,《龚自珍全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75年版,第21页。而夏曾佑曾研读过汪中的《述学》与龚自珍的《定盦集》。(22)夏曾佑:《生平所学》,《夏曾佑集》下册,第1119页;夏曾佑:《日记》,《夏曾佑集》下册,第672、691页。由此而言,正是受到了汪中、龚自珍的启发,夏曾佑遂将“史”与“鬼神术数之学”联系在了一起。
接下来的问题是,老子是如何突破“鬼神术数之学”,而“一洗古人之面目”的呢?夏曾佑指出,老子之书,“讨其义蕴,大约以反复申明鬼神、术数之误为宗旨”。其证如下:其一,《老子》载:“万物芸芸,各归其根,归根则净,是为复命”。可知,“鬼神之情状,不可以人理推,而一切祷祀之说破”。其二,《老子》载:“有物浑成,先天地生”。可知,“天地、山川、五行、百物之非原质,不足以明天人之故,而占验之说废”。其三,《老子》载“祸兮福所倚,福兮祸所伏”。可知,“祸福纯乎人事,非能有前定之者,而天命之说破”。进而言之,“鬼神、五行、前定既破,而后知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圣人不仁,以百姓为刍狗。閟宫、清庙、明堂、辟雍之制,衣裳、钟鼓、揖让、升降之文之更不足言”。(23)⑤⑥⑧夏曾佑:《最新中学教科书中国历史》,《夏曾佑集》下册,第828—829、829、839、829页。
然而,老子之学不乏“矫枉过正”的问题。夏曾佑指出,“老子于鬼神、术数,一切不取”,“其宗旨过高,非神州多数之人所解”。(24)⑤⑥⑧夏曾佑:《最新中学教科书中国历史》,《夏曾佑集》下册,第828—829、829、839、829页。而且,其学“知旧术之所以腐败,而不言新理之何以推行,凡所设施,以长生久视而止,故有破坏,而无建立”。(25)夏曾佑:《中国社会之原》,《夏曾佑集》上册,第64页。因此,老子之书,“可以备一家之哲学,而不可以为千古之国教,此其所以有待于孔子欤”。(26)⑤⑥⑧夏曾佑:《最新中学教科书中国历史》,《夏曾佑集》下册,第828—829、829、839、829页。
由上可知,夏曾佑认为,春秋以前,为“鬼神术数之学”,但至春秋之末,“鬼神术数之学”弊端丛生,老子作为“周守藏室之史”,著书上下篇,“反复申明鬼神、术数之误”,突破了“鬼神术数之学”,遂成为“九流之初祖”。但是,其学仅“有破坏,而无建立”。
夏曾佑的上述观点提出之后,在晚清民国学术界产生了不小的影响。晚清时期,邓实于1905年发表《国学微论》,率先接受此说,认定老子是“九流之初祖”;(27)邓实:《国学微论》,《国粹学报》第1年第2号,1905年3月。1907年,来裕恂撰《中国文学史》,亦接受此说。(28)来裕恂:《萧山来氏中国文学史稿》,岳麓书社2008年版,第31—32页。民国之后,部分学者则进一步引申其说。1917年,江瑔出版《读子卮言》,“论道家为百家之所从出”,认为“古今学术之分合,以老子为一大关键。老子以前,学传于官,故只有道家而无它家,其学定于一尊。老子始官而终隐,学始传于弟子,故由道家散为诸家,而成为九流之派别。”(29)江瑔著、张京华点校:《读子卮言》,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72—73页。1919年,胡适则在《中国哲学史大纲》中将老子视为一个“革命”者,其“天地不仁”说“打破古代的天人同类的谬说,立下后来自然哲学的基础”。(30)胡适:《中国古代哲学史》,《胡适全集》第5卷,安徽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第240—242页。可以作为佐证的是,截止到1930年,胡适至少读过两遍夏曾佑的《最新中学教科书中国历史》。胡适:《胡适日记(1928—1930)》,《胡适全集》第31卷,第696页。这些观点显然与夏曾佑的观点有相通之处。总而言之,在晚清民国学术界,夏曾佑的老子为“九流之初祖”之说产生了较为广泛的影响。
二、孔子为“政教之原”
在先秦时期,孔子本是诸子之一。自汉武帝“罢黜百家,表彰六经”之后,孔子的地位发生本质性的变化,由诸子之一升为圣人。此后,孔子备受世人尊崇。但是,在学术界内部,今文学家与古文学家对孔子与六经的认识却存在较大的分歧。至晚清时期,这一分歧愈演愈烈。1898年,今文学家康有为撰《孔子改制考》,尊孔子为改制教主,认为“六经皆孔子所作”。(31)康有为:《孔子改制考》,《康有为全集》第3集,第85—140页。1902年,古文学家章太炎则撰《订孔》,与其针锋相对,认为孔子只是“古之良史”,“六艺者,道、墨所周闻”。(32)章太炎:《訄书(重订本)》,《章太炎全集(三)》,上海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第132—133页。关于章太炎的孔子观,可参看陈壁生:《“孔子”形象的现代转折——章太炎的孔子观》,《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15年第3期;贾泉林:《章太炎:学术与政治互动形成的孔子观》,《孔子研究》2016年第4期。因此,如何定位孔子,同样是夏曾佑治诸子学需要面对的问题。
受康有为等今文学家的影响(33)周予同指出,夏曾佑在和梁启超、谭嗣同结交之前,即治今文经学。而《最新中学教科书中国历史》的相关论述无疑受到了康有为《新学伪经考》与《孔子改制考》的影响。周予同:《五十年来中国之新史学》,《周予同经学史论》,第370—372页。,夏曾佑亦认为孔子是教主。不过,其具体议论则与康有为不同。或受清高宗“《五经》乃政教之原”(34)乾隆元年(1736),清高宗“命纂《三礼义疏》”,“谕总理事务王大臣”,“《五经》乃政教之原”。《清实录》第9册《高宗纯皇帝实录》卷21,中华书局2008年影印版,第8459页。的启发,夏曾佑进一步提出“孔子一身,直为中国政教之原”。(35)⑦⑨夏曾佑:《最新中学教科书中国历史》,《夏曾佑集》下册,第824、832、832—833页。那么,孔子为什么能够“直为中国政教之原”呢?夏曾佑首先指出,“孔子者,老子之弟子”。但是,孔子“既学于老子而会微妙通之旨,知其可以为哲学,而不可以为教宗”。(36)⑧⑩夏曾佑:《中国社会之原》,《夏曾佑集》上册,第64页。换言之,“孔子虽学于老子,而知教理太高,必与民智不相适而废,于是去其太甚,留其次者,故去鬼神而留术数”。(37)⑦⑨夏曾佑:《最新中学教科书中国历史》,《夏曾佑集》下册,第824、832、832—833页。由此可知,孔子能够“直为中国政教之原”,在于其“学于老子”,但因老子之教理“与民智不相适”,于是“去鬼神而留术数”。
问题在于,什么可以为“教宗”呢?夏曾佑指出,孔子“更博观夫古代之遗传,同群之程度,笔削弥缝,旁皇周浃,而后身自行之。于是反对古人之哲学,一变而为运用古人之教宗”。(38)⑧⑩夏曾佑:《中国社会之原》,《夏曾佑集》上册,第64页。由此可知,“古代之遗传”是“教宗”的基本凭借。而所谓“古代之遗传”,最主要的无疑就是“六艺”,即《诗》《书》《礼》《乐》《易》《春秋》。
那么,孔子是如何对“六艺”进行“笔削”的呢?与康有为有所不同,夏曾佑基本接受了刘歆《六艺略》的观点,认为“六艺”“其本原皆出于古之圣王”,孔子“博观”之后,“删定之,笔削去取,皆有深义”。其一,关于《易》,“包牺始画八卦,因而重之为六十四卦。文王作卦辞。周公作爻辞。”孔子作“十翼”。其二,关于《书》,“《书》本王之号令,右史所记。孔子删订,断自唐虞,下讫秦穆”,“凡百篇,而为之序”。其三,关于《诗》,“古有采诗之官,王者巡守,则陈诗,以观民风,知得失,自考正”;“孔子最先删录,既取周诗,上兼商颂”,“凡三百一十一篇”。其四,关于《礼》,“帝王质文,世有损益。至于周公,代时转浮,周公居摄,曲为之制,故曰经礼三百,威仪三千”;至周则衰,“孔子反鲁,乃始删定”。其五,关于《乐》,“自黄帝下至三代,乐各有名”,至周则坏,“孔子自卫反鲁,然后乐正”。其六,关于《春秋》,“古之王者,必有史官,君举必书,所以慎言行,昭法式”,“《春秋》即鲁之史记”,“孔子应聘不遇,自卫而归”,“乃因鲁旧史,而作《春秋》,上述周公遗制,下明将来之法”,凡十二篇。(39)⑦⑨夏曾佑:《最新中学教科书中国历史》,《夏曾佑集》下册,第824、832、832—833页。总之,夏曾佑认为,孔子在“博观”“古之圣王”的“遗传”之后,进行了“删定”,然后将其变为“古人之教宗”。
其中,“忠孝”是孔子之教的根据。夏曾佑指出:“其为教也,君子之道,造端乎夫妇,夫妇有别,有夫妇然后有父子”。而“父子者,宗法之始基”;“宗法者,凡百政事之始基”。具体而言,“从人之肉体之万无可解免者,制为五伦。五伦配五德,各亲其亲,各长其长。族制既明,则族各有务,而世禄定。世禄之法,通乎上下,其在下者有井田之法,以养其身,有腊宾乡饮之世,以和其气;其在上者,有冠昏丧治之礼以靡之,有诗书乐之文以驯之。民死徙无出乡,守望相助,疾病相扶持。士大夫物有其官,官修其方,日夕思之,官不失职,是谓太平世”。要而言之,“天下之治,起于宗法,而孝为其本原;天下之的,归于富贵,而忠为其断限”。总之一句话,“忠孝者,孔教之根据”。(40)⑧⑩夏曾佑:《中国社会之原》,《夏曾佑集》上册,第64页。
但问题是,孔教遂即与“鬼神之说”发生了冲突。夏曾佑指出:“孔子既立父君为全体之纲维,而与鬼神之说遂不得不大不便”。详言之,“鬼神之说,流别虽繁,大类只二”,其一是“暂设之鬼神”,其二是“永建之鬼神”。“用暂设鬼神”,则“必有轮回”。“今之君父,乌知非过去之臣子”;“今之臣子,乌知非过去之君父”,“则必有涅槃去来”。“今之君臣父子,识浪所转变”,“无明所熏染”,“而忠孝之说穷”。与此相类似,“用永建鬼神”,则“必有上帝”。“上帝之尊,非君父所能拟”,则“必有灵魂”;“灵魂之永,非君父所能司”,“而忠孝之说又穷”。因此,孔子“两害取其轻,与其受用鬼神之害,毋宁受不用鬼神之害”。此后,“积久而著焉”,有“畏死”“重子孙”“无信”。而“有此三根,而展转而生之习俗,又不知凡几,所以成今日之社会”。(41)夏曾佑:《中国社会之原》,《夏曾佑集》上册,第64页。总之,孔子主张“留术数而去鬼神”。
夏曾佑的上述观点提出之后,在晚清民国学术界引起了一定反响。尤其值得关注的是,其强调的“孔子一身,直为中国政教之原”的观点,被反复引用。1905年,邓实在《国学微论》中率先接受其说。(42)邓实:《国学微论》,《国粹学报》第1年第2号,1905年3月。1932年,杨东莼在《中国学术史讲话》中认为,这一观点“颇具卓识”。(43)杨东莼:《中国学术史讲话》,第401页。1933年,陈序经在《中国文化的出路》中强调说,这一观点“说得好”。(44)陈序经:《中国文化的出路》,商务印书馆1934年版,第133页。1949年,梁漱溟在《中国文化要义》中强调说,夏曾佑的这一观点“好像言之太过,却亦不是随便乱道”。(45)梁漱溟:《中国文化要义》,路明书店1949年版,第236页。由此可见,夏曾佑关于孔子的判断堪称是晚清民国学术界较有代表性的看法之一。
三、墨子与孔子成“相反之教”
先秦时期,“显学如林,而孔墨为上首”。(46)夏曾佑:《〈社会通诠〉序》,《夏曾佑集》上册,第127页。但与孔子及其学说的命运相反,自从汉武帝“罢黜百家,表彰六经”以后,墨家逐渐退出历史舞台。直到清代,墨子重新被重视。毕沅、孙星衍、汪中、孙诒让等一大批学者对《墨子》进行了整理与研究。(47)刘仲华:《清代诸子学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209—222页。晚清以来,墨学进一步呈现复兴之势。
孔、墨异同是夏曾佑最为关注的问题。而在夏曾佑之前,康有为即对孔、墨争教进行了阐述。康有为在《孔子改制考》中指出,周末诸子并起创教,其中孔子最先创教,“道无不包”,墨子则是孔子后学,“乃自创新教,锐夺孔席以自立,所以攻难者无不至”。具体而言,“孔子大义微言,条理万千,皆口授弟子。若传之于外,导引世人,大率以三年丧、亲迎、立命三者。其士大夫则以礼乐辅之。”而“孔子立义本父子,故制三年丧,教人敦厚,故久丧为传教第一义”。因此,“墨子力翻孔案,有意攻难,必先此数义。而《非乐》《非命》,著有专篇,短丧、薄葬,且有特制,此其义最相反者。”进言之,“墨子爱无差等,故薄父子;重生贵用,故短丧”。总之,康有为已指出,“墨子在孔子之后,有意争教,故攻孔子者无所不至”。(48)康有为:《孔子改制考》,《康有为全集》第3集,第185—194页。
受康有为的直接影响,夏曾佑进一步对这一问题做出了探索。夏曾佑指出,墨子,孔子之弟子,或史角之弟子,“其学与老子、孔子,同出于周之史官,而其说与孔子相反”。当然,就修身、亲士来说,这是“宗教所不可无”,故“不能不与孔子同”。除此之外,其他皆“与孔子相反”。“孔子亲亲,墨子尚贤;孔子差等,墨子兼爱;孔子繁礼,墨子节用;孔子重丧,墨子节葬;孔子统天,墨子天志;孔子远鬼,墨子明鬼;孔子正乐,墨子非乐;孔子知命,墨子非命;孔子尊仁,墨子贵义”。总之,“殆无一不与孔子相反”。(49)夏曾佑:《最新中学教科书中国历史》,《夏曾佑集》下册,第839页。
那么,墨子为什么要如此针对孔子呢?夏曾佑认为,“丧礼”是其中的关键。具体而言,墨子非故意与孔子“相戾”,只因其中一端不同,“诸端遂不能不尽异”。此一端即是“丧礼”。“儒家丧礼之繁重,为各宗教所无,然儒家则有精理存焉”。简而言之,“儒家以君父为至尊无上之人,以人死为一往不返之事,以至尊无上之人,当一往不返之事,而孝又为政教全体之主纲”,故儒家重“丧礼”。但是,“丧礼”并非没有流弊。学于孔子的墨子即“以为其礼烦扰而不悦,厚葬糜财而贫民,服伤生而害事”。因此,墨子欲“杀”丧礼。而欲“杀”丧礼,“必先明鬼”。因为,“有鬼神,则身死犹有其不死者存,故丧礼可从杀”。而“既设鬼神,则宗教为之大异”。(50)③夏曾佑:《最新中学教科书中国历史》,《夏曾佑集》下册,第839、839、911页。具体而言,“既设鬼神,则天为鬼神之大者,自不可以不言天,此墨子所以屡言天鬼”;而“天鬼立”,一切遂发生变化。其一,“天鬼立,则生死轻”,于是“可以重然诺,犯威严,以尚贤而贵义”;其二,“天鬼立,则五伦废”,于是“可以人皆平等而兼爱”;其三,“天鬼立,则督责严”,于是“不得不节用非乐,蹈大觳以备世之急”。(51)⑤夏曾佑:《中国社会之原》,《夏曾佑集》上册,第65页。总之,“丧礼”是墨子与孔子“不同之大原”,“丧礼”不同,导致“其他种种异议”,“孔、墨遂成相反之教”。(52)③夏曾佑:《最新中学教科书中国历史》,《夏曾佑集》下册,第839、839、911页。
接下来的问题是,该如何看待墨子之教呢?早在1895年,夏曾佑在答复宋恕的信中便提到:“战国之时,列国相争,人始开化,于是经世之教分为二途,孔、墨是矣。”而“墨子之教,因言苦行而不言报境,不合人心,不能行世。”(53)夏曾佑:《致宋恕函》,《夏曾佑集》上册,第445页。1903年,夏曾佑在《中国社会之原》中进一步说:“凡孔教之流弊,皆举而空之,墨子亦人杰”。“虽然,有天志而无天堂之福,有明鬼而无地狱之苦,是人之从墨子者,劳心焦思而无赏;非墨子者,放辟邪侈而无罚。仅仅乎持巨子之虚名,以易汤火之实祸,墨子虽能独任”,但天下人不能。因此,“墨教之亡,不亡于汉武之绌游侠,而亡于墨子之言鬼神”,假设“墨子当日有天堂地狱之说,则华夏之为共和也久矣”。(54)⑤夏曾佑:《中国社会之原》,《夏曾佑集》上册,第65页。
夏曾佑的上述观点问世之后,在晚清民国学术界产生了一定反响。晚清时期,邓实于1905年发表《国学微论》,率先接受此说,指出“墨子之学,与老子孔子同出于周之史官。顾官同而学不同,其与孔学尤相反”,然后转述了夏曾佑关于孔、墨异同的归纳。(55)邓实:《国学微论》,《国粹学报》第1年第2号,1905年3月。1907年,来裕恂在《中国文学史》中则基本照搬了夏曾佑的观点。(56)来裕恂:《萧山来氏中国文学史稿》,第33—34页。至民国时期,钱玄同于1917年发表《论世界语与文学》,有本于夏曾佑的儒、墨异同说,扬墨抑儒。(57)钱玄同:《论世界语与文学》,《钱玄同文集》第1卷,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23—24页。1937年,方授楚出版《墨学源流》,在讨论“墨子之根本精神”时即指出:“墨子之时,与其学说相敌者,仅一儒家”,“墨子与孔子年代相接,学术之基础相同,而其主张则相反”,然后即直接转述了夏曾佑关于儒墨异同的归纳,并提出:“至其所以然之故”,“殆在平等与否而异”。总之,墨子之根本精神在“平等”。(58)方授楚:《墨学源流》,中华书局1937年版,第111页。准此而言,有相当一部分学者或接受了夏曾佑关于儒墨异同的观点,或在其观点的基础上探讨了相关问题。
四、老孔墨三家流为诸子百家
除老孔墨之外,先秦时期还有其他诸子百家。但是,“诸子并兴,群言淆乱,欲讨其源流,寻其得失,甚不易言”。其中,“著录百家之书,始于《汉书·艺文志》”。《汉书·艺文志》是“刘向、刘歆之成说”。刘向、刘歆将诸子分为儒家、道家、阴阳家、法家、名家、墨家、纵横家、杂家、农家、小说家等“十家”,但小说家出于“稗官”,故可观者“九家”;而且,一一溯十家所自出,认为各家皆出于一个官守。此外,刘向、刘歆还指出,“九家之术,蜂出并作,各引一端”,但“合其要归,亦《六经》之支与流裔”。此说问世之后,“通儒皆宗之”。(59)③夏曾佑:《最新中学教科书中国历史》,《夏曾佑集》下册,第839、839、911页。
然而,晚清以来,即有学者对这一叙事提出了质疑,并提出了新的观点。康有为在《新学伪经考》中指出,刘歆编《七略》既独尊“六艺”为一略,“统冠群书以崇孔子”,即应将名、法、道、墨者列为“异学略”,附于“七略”之末,而不应以儒与名、法、道、墨并列,目为“诸子”,外于“六艺”,号为“九流”;而儒家即孔子,七十子后学者即是孔子之学,不应抑儒家于九流。(60)康有为:《新学伪经考》,《康有为全集》第1集,第415页。此后,康有为在《孔子改制考》中强调,“诸子之学”悉受“孔子之道”的范围;与孔子争教者,老、墨二家。(61)康有为:《孔子改制考》,《康有为全集》第3集,第204、164页。受康有为的影响,梁启超在《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中首先指出,《艺文志》“非能知学派之真相”。比如,“既列儒家于九流,则不应别著‘六艺略’”;“既崇儒于六艺”,则不应“复夷其子孙以侪十家”。而“庄子所论,推重儒、墨、老三家,颇能絜当时学派之大纲”。然后,梁启超重点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将诸子分为南、北两派。(62)梁启超:《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梁启超全集》第2册,第569—570页;宁腾飞:《梁启超“孔北老南”说的建立及其意义》,《史学月刊》2019年第2期。
继康有为、梁启超之后,夏曾佑进一步探讨这一问题,并提出了自己的一家之言。夏曾佑首先对《汉书·艺文志》的诸子叙事提出了质疑,“六艺皆儒家所传,授受渊源,明文具在,既为一家之言,必不足以概九流之说”。刘向、刘歆之“大弊”,在于“以经为史”。“古人以六艺为教书,故其排列之次,自浅及深”;刘向、刘歆“以六艺为史记,故其排列之次,自古及今”;“此宗教之一大变”。而“既已视之为史,自以为九流之所共”。但问题是,此不能“自解于附《论语》《孝经》于其后”。总之,刘向、刘歆之说“不通”,“与古人不合”。(63)④⑤夏曾佑:《最新中学教科书中国历史》,《夏曾佑集》下册,第911、911—912、912页。
然后,夏曾佑对《庄子·天下篇》《荀子·非十二子》《论六家要旨》中的诸子叙事进行了分析,并进而提出了新的解释。其中,《庄子·天下篇》所列的墨翟、禽滑厘为墨家,宋钘、尹文亦墨家,彭蒙、田骈、慎到“道而近于法家”,关尹、老聃为道家,庄周亦为道家,惠施为名家。《荀子·非十二子》所列的它嚣、魏牟为道家,陈仲、史为“墨家之一派”,墨翟、宋钘为墨家,田骈、慎到为道家,惠施、邓析为名法家,子思、孟轲为儒家。但其实,“名法出于道家、儒家之间”。至司马谈,将诸子分为六家,则于《庄》《荀》所举之外,增入一阴阳家,但其“不举其人,无从证其同异”。因此,“诸子虽号十家,其真能成宗教者,老、孔、墨三家而已”。(64)④⑤夏曾佑:《最新中学教科书中国历史》,《夏曾佑集》下册,第911、911—912、912页。
最后,夏曾佑还进一步提出“诸子十家之说,同出一源”的观点。承前所述,夏曾佑已指出,老子为“周守藏室之史”,孔子受学于老子,墨子或是史角之弟子,“名法出于道家、儒家之间”。因此,道、儒、墨、法、名五家“同源”而“同导源于史官”。其他诸家亦如此。其一,阴阳家实际上是“老子未改教以前之旧派”,“此即周史之本质”。其二,纵横家虽“出于时势之不得不然,初无待于师说;然鬼谷子、苏秦、张仪并周人,而《鬼谷子》书,义兼道德”。其三,“杂家号为调停,实皆以道家为主”。其四,“农家传书最少,然据许行之遗说以推之,亦近道家”。其五,“小说家即史之别体”。总之,诸子“同出一源”。(65)④⑤夏曾佑:《最新中学教科书中国历史》,《夏曾佑集》下册,第911、911—912、912页。
夏曾佑的上述观点提出之后,在晚清民国学术界引起了一定注意。1905年,邓实发表《国学微论》,指出“神州学术自老、孔、墨三宗而外,则有诸子百家之学,并起于周秦之际”。而“诸子九流之学,溯其所自,皆出于周官之典守,其与老、孔、墨之同出于史官”;“周道衰微,官司失职,散在四方,流而为诸子”。(66)邓实:《国学微论》,《国粹学报》第1年第2号,1905年3月。1907年,来裕恂撰《中国文学史》,指出:“先秦之学,既称极盛,而其派千条万绪”。刘歆、班固所定,“亦有未安”,“惟《庄子》所论,推重儒墨老三家,颇能挈当时学派之大纲”。(67)来裕恂:《萧山来氏中国文学史稿》,第39—41页。由此可知,夏曾佑的观点在晚清学术界即有一定反响。
至民国时期,部分学者进一步引申或发挥其说。1917年,钱玄同在《中国学术论著集要序录》中指出,“阴阳即东周中叶以前之旧学,纵横乃一时致用之术,小说为历史之支流”,杂家“盖集合百氏之说,初无宗旨可言”,“农家实道家之一派”,“法家出于道家”,“名家出于墨家”。总之,“十家之中,其能卓然自立者,厥惟‘道’‘儒’‘墨’三家而已”。(68)钱玄同:《中国学术论著集要序录》,蒋伯潜编:《蒋氏高中新国文》第6册,世界书局1946年版,第405—406页。钱玄同的这一观点虽与夏曾佑的观点略有不同,但无疑是引申了夏曾佑的看法。(69)早在1904年,钱玄同即阅读了夏曾佑的《中国历史教科书》,最迟在1909年得读夏曾佑的《中国社会之原》,而且,他非常推崇《中国历史教科书》,认为该书是当时“历史教科佳者”,并一度将该书作为编讲义的“蓝本”。参见杨天石主编:《钱玄同日记》上册,第5、157、199页。由此而言,钱玄同的观点应该是受到了夏曾佑的影响。1919年,胡适发表《诸子不出于王官论》,指出“《艺文志》所分九流,乃汉儒陋说,未得诸家派别之实”,“先秦显学,本只有儒墨道三家”,“古无名家之名”,“惠施、公孙龙,皆墨者”,“其他如《吕览》之类,皆杂糅不成一家之言”。因此,九流出于王官之说不能成立。(70)胡适:《诸子不出于王官论》,《胡适全集》第1卷,第247页。这一看法进一步发挥了夏曾佑之说。由此而言,夏曾佑的观点在民国学术界仍然有着一定的影响。
余 论
综上所述,先秦诸子学是夏曾佑学术的重要组成部分。早在20世纪初,夏曾佑在《中国社会之原》《最新中学教科书中国历史》等论著中率先提出,春秋之前,“鬼神术数之外无他学”,而老子突破了这一“鬼神术数之学”,遂成为“九流之初祖”;此后,孔子“去鬼神而留术数”,删定六经,成为中国二千年来社会的“政教之原”;墨子则“去术数而留鬼神”,与孔子“成相反之教”;然后,老孔墨三家流为诸子百家。可以说,这一系列观点建构了一个以老孔墨为主的先秦诸子叙事体系。
实际上,夏曾佑的诸子学研究早已超越本身,而在中国近代诸子学史上有着不容忽视的思想价值与学术意义。
首先,夏曾佑将诸子视为“社会进化之原”,进一步彰显了先秦诸子的现实价值。春秋战国之际,诸子百家忧世之乱,应时而起,立说授徒,各成派别。孔子与儒家本是诸子百家之一。但汉武帝“罢黜百家,表彰六经”之后,孔子与儒学成为主流意识形态,诸子渐成“异端”。“清代右文,硕学辈出,于数千年残缺之子书,为之考订掇辑,蔚然可观”。(71)江瑔著、张京华点校:《读子卮言》,第6页。至晚清,外国列强入侵,西学传入,这一趋势遂愈演愈烈。学者主张“通子致用”,但所论多限于学术领域。直到康有为撰《孔子改制考》,认为孔子创教,托古改制,诸子的思想价值才再一次被发现。受康有为的影响,夏曾佑著《最新中学教科书中国历史》,旨在“发明今日社会之原”。“其纲只三端”,其中之一即“关乎社会”,“每于有大变化时详述之”。最能体现这一主旨的无疑是先秦诸子。“周秦之际,至要之事,莫如诸家之学派”。而老、孔、墨三大宗尤为“社会进化之起原”。(72)⑩夏曾佑:《最新中学教科书中国历史》,《夏曾佑集》下册,第911、915、947,839页。其中,“孔子一身,直为中国政教之原”。因此,“言改政者,自不能不波及于改教”。(73)夏曾佑:《〈社会通诠〉序》,《夏曾佑集》上册,第128页。至民国时期,胡适著《先秦名学史》,则希望通过恢复“非儒学派”,“找到移植西方哲学和科学的最佳成果的合适土壤”。(74)胡适:《先秦名学史》,《胡适全集》第5卷,第12页。此后,民国学者探讨诸子学,其背后都有着“关心中国民族文化之前途”的现实关怀。(75)钱穆:《古史辨第四册序》,《中国学术思想史论丛(二)》,《钱宾四先生全集》第18册,第298页。以此来看,夏曾佑的先秦诸子论述,无疑顺应了晚清以来“通子致用”的思潮,进一步彰显了先秦诸子的现实价值。
其次,夏曾佑虽然在主观上推尊孔子,但客观上却进一步促进了“夷孔子于诸子之列”。前已指出,先秦时期,孔子与儒家本是诸子百家之一。至汉武帝“罢黜百家,表彰六经”之后,孔子与儒学成为主流意识形态,诸子渐成“异端”。直到清代,诸子渐有复兴之势。这里要指出的是,清代还出现了平等看待诸子与孔子的言论。“如汪中明确认为,孔墨平等,无分轩轾”。(76)罗检秋:《近代诸子学与文化思潮》,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203页。至康有为倡言变法,著《孔子改制考》,虽然“极力推挹孔子”,但孔子与诸子都是托古改制,则已“夷孔子于诸子之列”。(77)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梁启超全集》第5册,第3098页。受康有为的影响,夏曾佑著《最新中学教科书中国历史》,虽然认定孔子为“政教之原”,但同时指出,在诸子百家之中,“真能成宗教者,老、孔、墨三家而已”。而且,还对三家之优劣进行了评价。(78)⑩夏曾佑:《最新中学教科书中国历史》,《夏曾佑集》下册,第911、915、947,839页。如此一来,“夏书虽欲极力推尊孔子,而所得影响适得其反”。(79)钱穆:《评夏曾佑〈中国古代史〉,《中国学术思想史论丛(六)》,《钱宾四先生全集》第23册,第285页。“夷孔子于诸子之列”的观念得到强化。至民国时期,胡适出版《中国哲学史大纲》,建立了“平等的眼光”,对诸子各家一视同仁。(80)蔡元培:《〈中国古代哲学史大纲〉序》,《蔡元培全集》第3卷,第189页。此后,主流学者基本接受了这一“平等的眼光”。由此而言,夏曾佑的先秦诸子论述,虽然在主观上推尊孔子,但客观上顺应了“夷孔子于诸子之列”的趋势,进而推动了诸子学的近代转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