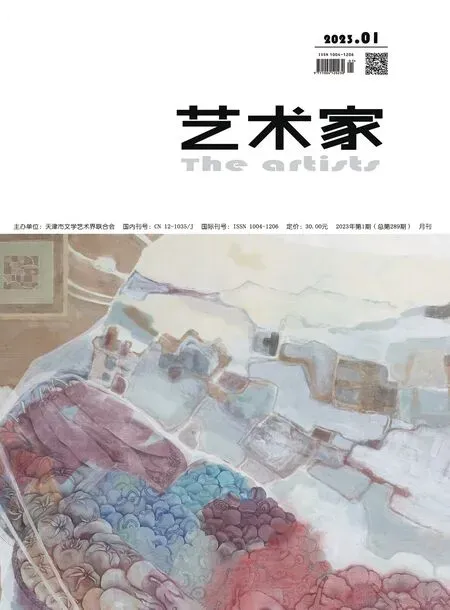从王褒《洞箫赋》窥探两汉“尚悲”音乐审美风尚
2023-10-07张一帆
□张一帆
两汉时期,随着器乐制作技艺日趋精湛,器乐的表现力与可知性问题、器乐审美感受的特殊性等问题日益引起人们的思考。作为“一代之文学”,即最早的文字形式之一的“赋”,几乎是一开始就把音乐视为应当着重关注的对象。这一方面直接表现为《韩诗外传》《说苑·善说》《淮南子·齐俗训》等的理论探讨,另一方面则表现为西汉枚乘《七发》、王褒《洞箫赋》、东汉刘玄《簧赋》、马融《长笛赋》与《琴赋》、傅毅《舞赋》与《雅琴赋》、张衡《舞赋》、侯瑾《筝赋》、蔡琶《琴赋》、阮瑀《筝赋》、繁钦《三胡赋》等音乐赋的批量出现。由于枚乘《七发》中对音乐的描述服务于文章的整体需要,并未独立成篇,因此,王褒的《洞箫赋》可以说是现存最早的音乐赋。
王褒的《洞箫赋》从器乐制作材料、演奏的乐师、音乐演奏效果三方面着手,词采铺陈多变,句式整饬流畅,篇幅不惜笔墨。对于瞽师奏乐的描写,王褒从发声学的角度提出了“发愤乎音声”的观点,肯定了音乐的不平之美,并直言“知音者乐而悲之”,表明其以“悲”为美的音乐审美观念。由于《洞箫赋》在体制体式及思想内涵等方面的诸多创新,文章试从该赋的程式与意蕴、“尚悲”音乐审美观的社会成因以及“尚悲”观念的哲学突破三方面入手,探析两汉时期崇尚悲音这一审美风尚的形成。
一、《洞箫赋》的程式与意蕴
《洞箫赋》在写作模式上可追溯至枚乘《七发》,但相比之下,王褒的描摹更加细腻、繁复,极尽铺陈夸张之能事,该赋使两汉时期音乐赋的写作模式趋于成熟,并以此启发蔡邕《琴赋》、嵇康《琴赋》等作品的创作。马融更是在其《长笛赋》序中云:“追慕王子渊、枚乘、刘伯康、傅武仲等,箫、琴、笙赋,唯笛独无,故聊复备数,作《长笛赋》。”可见,王褒其文在两汉音乐赋中有开导先风的作用。
《洞箫赋》开篇即写制箫之材——竹子。王褒认为乐器的材质、生长环境与音乐感染力有内在的联系,因此以大量笔墨突出生长环境之艰险,如“岖嵚岿崎,倚巇迤㠧”等,以至于作者发出“诚可悲乎其不安也”的感慨,也正因为其“处幽隐而奥庰兮,密漠泊以䡳猭”的生长特点,所以具有清冷温润、静而不喧的自然天性。三国曹魏时期的如淳在《汉书音义》中给洞箫做了如下定义:“箫,肃也,言其声肃肃然清也”,由此可见,其对于洞箫气质的审美定位与王褒如出一辙。在首段末尾处写洞箫制作之法,即“般匠施巧,夔妃准法”,此后音乐赋中的器乐制作者莫不是能工巧匠,器乐配饰物件莫不是奇珍异宝。
其次写奏乐之人,由于他“性昧之宕冥”,即生来未见过天地的形状,无法辨别白天黑夜,所以心灵处于较封闭的状态。也正因为瞽师不受外物所扰,所以能专注于自我的内心世界,悲愤郁结于心而发于声音,有了深厚的感情积累便能将各种繁杂急促、从容不迫的声音表现得淋漓尽致。
最后是对音乐效果的描写。王褒以细腻的笔触将音乐带给人的听觉感受以比喻、拟人的方式描绘出来。乐声或如潺潺流动的溪水,或发出折断枯枝的脆响,或如沉寂安静的潭水,音乐行而后止、止而后生。当器乐与人声相和时,王褒将无形的音乐落笔于具体可感的事物,“故听其巨音则周流汜滥,并包吐含,若慈父之畜子也……故其武声则若雷霆輘輷,佚豫以沸㥜;其仁声则若颽风纷披,容与而施惠。”他把洪水包裹大地般的巨音类比宽容博大的慈父之情;把平和流畅的乐声与人们侍奉长辈时恭谨顺和的心境相联系;汹涌澎湃的音乐令人想起慷慨壮士一去不复返的豪情,优柔温润的乐声又有如彬彬有礼的君子。“慈父”“孝子”“壮士”“君子”的拟况可谓纤毫不漏、细密无间,刘勰《文心雕龙·比兴》中“优柔温润,如慈父之畜子也,此以声比心者也”即出自此赋。《才略》中又云:“王褒构采,以密巧为致,附声测貌,泠然可观。”从具体写作手法来看,王褒重视押韵和声调的语言特色,两句一韵,偶有变换,句式上四、七式,七、四式,四、四式长短相济、变化多端,读起来朗朗上口,婉转悠扬。《汉书·王褒传》记载:“其后太子体不安,若忽忽善忘,不乐。诏使褒等皆之太子宫虞侍太子,朝夕诵读奇文及所自造作。疾平复,乃归。太子喜褒所为《甘泉》及《洞箫颂》,令后宫贵人左右皆诵读之。”诵读王褒赋为太子治病或许有夸张之处,但这也说明其赋骈偶整齐、音韵谐美所别具的艺术感染力。
王褒的《洞箫赋》在写作方式与行文构思上不落前人窠臼,对事物内部深度开掘,着力铺绘,力求鞭辟入里,与其前赋家力求“苞括宇宙”的横向铺陈相异。《洞箫赋》仅着墨于一支竹箫,先写制箫之竹的生长环境悲苦,再写奏箫之人因失明而悲愤,最后写令人怅然的音乐效果。因此,嵇康在《琴赋》序言中总结了其前历代音乐赋的创作特点:“称其才干,则以危苦为上;赋其声音,则以悲哀为主;美其感化,则以垂涕为贵”,一方面可见《洞箫赋》影响之深,另一方面也表明两汉魏晋时期尚悲的音乐审美观已十分盛行。
二、“尚悲”音乐审美观的社会成因
史书中关于王褒生平的记载非常简略。他在作品《圣主得贤臣颂》中云“今臣僻在西蜀,生于穷巷之中,长于蓬茨之下”,可见其出身寒微。据今人考证,王褒生于汉武帝太始年间,卒于汉宣帝甘露元年以后。也就是说,王褒儿时经历过汉武帝晚年穷奢极欲、与民争利导致的仓廪空虚、民怨鼎沸;昭帝时期“铁盐会议”召集贤良文学讨论,对武帝政治进行了反思批判,形成昭帝时期与民休息的政策;汉宣帝时期励精图治,四夷宾服,史称“汉宣中兴”。处于偃武兴文社会转型期的王褒,其创作自然表现出了丰富的思想内涵。武帝时期作为社会下层民众的王褒属于被盘剥的对象,目睹百姓流离失所和社会价值失序或许给少年王褒留下了难以忘怀的伤痛记忆,以至于在其后的文学创作中经常发出怆然伤怀的感慨。汉宣帝时期吏治改良,给予王褒等文士君臣遇合的希望,也使王褒能在一个相对宽松自由的环境中进行创作,所以能尽情抒发其崇尚“悲音”、甚至以“悲”为美的审美观念。
王褒尚悲的观念不仅属于个人,也属于他生活的时代。着眼于整个汉代,下至下层民众,上至帝王将相,尤其是作为创作主体的文人儒士,他们的作品中都充满了哀愁的情绪取向。汉代乐府民歌中有如《蘸露》《篙里》等悲歌大量涌现;汉高祖刘邦所作《大风歌》慷慨伤怀;枚乘《七发》、王褒《洞箫赋》、马融《长笛赋》等均言明以“悲”为美的审美意识。以至于钱钟书在《管锥编》中总结道:“奏乐以生悲为善音,听乐以能悲为知音,汉魏六朝,风尚如斯”。纵观两汉,虽然国势强盛,但有其百业昌荣则必有暗心颓愁。官僚体制下社会矛盾始终无法解决,尤其是权力高度垄断下的明争暗夺,财富的剥削掠夺,社会各阶层等级森严,造成诸多社会矛盾。险恶的政治环境导致人们彼此猜忌,如履薄冰的文士们只能将自我压抑的悲哀倾诉于音乐和文学。
此外,两汉王朝初长期的战乱导致自然环境受到了一定的破坏,灾害频发。据《汉书·文帝纪》记载,汉文帝前元九年“间者数年比不登,又有水旱疾疫之灾”。《汉书·天文志》中记载后元元年因地震,人们生活困苦。汉平帝时期各地农民起义、战争等导致“天下户口减半矣”。东汉时期,统治阶级内部矛盾斗争导致其无暇顾及人民,民不聊生、死者相望。在这样的背景下,音乐文学作品中出现了大量对生命短暂、世事无常的咏叹,如《古诗十九首》中的“生年不满百,常怀千岁忧”(《生年不满百》),“人生天地间,忽如远行客”(《青青陵上柏》)等。在死亡阴影的胁迫之下,人们用旷达之思表现了寻求人生出路的痛苦。社会政治、自然灾害导致了人生悲剧,所谓“悲事生悲情”,不幸和缺憾、悲苦、哀伤等负面情绪遂广泛滋生。由此,音乐中崇尚“悲音”便成为社会审美的主流。
三、“尚悲”音乐审美观的哲学突破
自先秦以来,关于音乐美学思想的探讨就离不开“哀”与“乐”、“悲”与“美”等范畴。《国语·周语下》中单穆公和伶州鸠在劝谏周景王铸钟时提出“乐从和,和从平”的观点,认为不平和的音乐对于国家人民有害无利,其中也暗含否定悲伤忧愁之乐的倾向。《史记·卫康叔世家》中记载季札听卫国音乐后评论“不乐、音大悲,使卫乱乃此矣”,认为悲伤的音乐是祸国原因之一;《礼记》中明确提出“乐者,乐也”,认为音乐是快乐之情的表达。由此可见,传统乐论的根本思想还是肯定和乐之乐,否定悲愁之乐,也否定以悲为美。然而,《洞箫赋》在描绘音乐感人功效时说道:“故知音者乐而悲之,不知音者怪而伟之。”蔡仲德在其《中国音乐美学史》中提出,此处“悲”字是“美”的代词,人们在欣赏洞箫演奏时,既能得到“乐”——快感,又能得到“悲”——美感。以悲代替美,蕴涵了只有能欣赏悲乐之美者才真正懂得音乐,才配成为知音这样的思想,此处的以“悲”为“美”,从两汉时期的论著中搜求关于音乐的记述,更能抉其幽微。例如,《论衡·书虚篇》中“夔为大夫,性知音乐,调声悲善”、《论衡·感虚篇》中“鸟兽好悲声,耳与人耳同也”、《韩非子·十过》中“曲无不悲”等字句都可以得到佐证。这表明,这一思想已经不是不自觉的意识流露,而是一种较明确的观念。
先秦时期儒家音乐美学思想否定以悲为美,从社会学的角度看是因为悲乐表现的大多是不平之鸣、不满之情,表达了人们反抗暴政的心声,不利于统治者治理国家。但音乐以抒情为本位,而人的情感自然有哀有乐,只要生活中有悲剧的存在,人们就必然需要悲乐来抒发情感。由此看来,并非音乐决定政治,而是政治决定音乐。因此,这种“前代兴亡实由乐”之说,其实是以凌驾于人的“礼”和外在于人的“天”来束缚人和音乐的发展。两汉时期儒家思想仍占据主导地位,汉武帝、汉宣帝均致力于复兴礼乐建设,但此时在音乐上却摒弃了“悲乐亡国论”,崇尚“越名教而任自然”,使情感超越了伦理纲常的束缚而得到自由的伸展,实际上是对人的一次重新发现和塑造,表明人们开始自觉地探索悲乐、死生等精神问题。此外,这种以悲为美的观念,已经超出了简单的情绪发泄,而是把“情”提到了本体的地位并对其进行探询。汉代的人们能够直面悲剧,并肯定以悲为美,反映了汉代人对自己本性情感的再发掘、再认识,也是对当时谶纬神学、天人感应等理论架构的一种突破。
悲作为一种更深层次的审美体验,能够指导人们认识生活、憧憬光明、憎恶黑暗,因此,汉代崇尚以悲为美。但这并不等同于“悲观主义”,其效果往往不是消极的,而是积极的。崇尚以悲为美、欣赏悲乐,从痛感中得到快感、美感,人们不仅能体会到感官的快适,还能拥有理性上的满足。两汉时期悲美意识的觉醒,表明此时的音乐不再作为“礼”的附属品和伦理教化的工具。它作为人们的审美对象,极大地拓展了表现的形式和范围,能够引导人们获得精神上的自由。当然,王褒的《洞箫赋》尽管有突破之处,但赋中“吹参差而入道德”“化风俗之伦”等颇具伦理道德色彩的字句表明他仍重视音乐的教化作用,由此可见,他并未完全脱离儒家的立场。但此赋中对“不平之美”的肯定,对人情感世界的拓展和发掘,对之后魏晋南北朝时期“情本体”的文艺美学思想仍有重要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