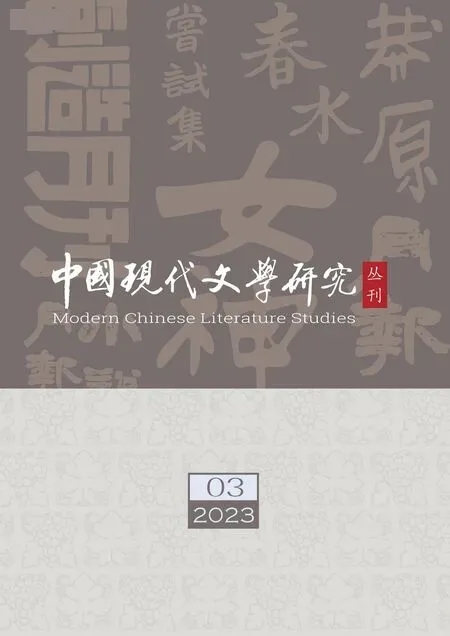从误读说起:《孔乙己》叙事艺术解析
2023-10-06高恒文
高恒文
内容提要:《孔乙己》是鲁迅最满意的作品。分析这篇小说的叙述者、叙述反讽、叙述结构和话语暴力、失语症等问题,可以重新认识作品的主题思想和艺术特征,从而对作品的“散文化”叙述结构以及几个主要细节,做出新的解释。
《孔乙己》是鲁迅最满意的作品。1孙伏园:《鲁迅先生二三事·〈孔乙己〉》,《鲁迅回忆录》(上册),北京出版社1997年版,第83页。小说看似简单,仿佛一幅人物漫画,实则就小说的叙述艺术而言,颇为复杂,因此读者往往掉以轻心,不免误读。误读本属正常的“诠释”或“阅读行为”,有其合理性;甚至任何阅读、诠释都是在“先见”“前理解”制约的前提之下的一偏之见。2参阅伽达默尔《真理与方法》,洪汉鼎译,商务印书馆2007年版;沃尔夫冈·伊瑟尔《阅读活动——审美反应理论》,金元浦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1年版。本文对以往关于《孔乙己》的误读有所商榷,进而尝试对这篇杰作的叙事艺术作出新的解读。
一 叙述反讽:“我”是否小伙计
叙述对象被叙述者的叙述所塑造。《孔乙己》的中心人物当然是孔乙己,叙述孔乙己故事的是“我”,即第一人称的叙述者。欲知孔乙己为何人,当先知叙述者“我”为何人、叙述孔乙己故事为何。对《孔乙己》的误解,首先从这里开始的。
将叙述者看作“咸亨酒店的小伙计”的研究者,比比皆是,恕不举例。实则小说开篇即云:“四文铜钱,买一碗酒,——这是二十多年前的事,现在每碗要涨到十文。”1鲁迅:《孔乙己》,《鲁迅全集》第1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434页。本文以下引用、论述《孔乙己》,均以此版本,不一一出注。虽然说的是酒价,其实也是孔乙己故事发生的时间。所以下文说:“只有孔乙己到店,才可以笑几声,所以至今还记得。”“至今”,呼应上文所谓“二十多年前”。小说最后一句:“我到现在终于没有见——大约孔乙己的确死了。”“到现在”,即“至今”,均为叙述孔乙己故事的时间。很显然,“我”所叙述的孔乙己的故事是“二十多年前”的事。又,小说开始,第二自然段的第一句称:“我从十二岁起,便在镇口的咸亨酒店里当伙计。”据此,可知叙述者已然中年,而非当年在咸亨酒店当小伙计的年龄。
李欧梵《铁屋中的呐喊》论《孔乙己》的说法,大体正确:“《孔乙己》技巧之妙不仅在写出了主人公这一难忘的形象,还在设计了一个不可信赖的叙述者。故事是由咸亨酒店一个小伙计用讽刺口气叙述的。这个人在叙述当时的情况时已经是一个成人了。”2李欧梵:《铁屋中的呐喊》,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第57、69页。这是精于小说叙述学理论的评论者的眼光。只是此说稍有含混:叙述者在叙述当时的情况时,不仅“已经是一个成年人了”,而且未必仍然还是咸亨酒店的伙计。李欧梵同时又说:“在小说结束时叙述者说到酒店掌柜已好久不提孔乙己欠账时,这个小伙计可能已经长大了,但他只说了一句:‘我到现在终于没有见——大约孔乙己的确死了。’语气是那么平淡麻木,毫无同情。”3李欧梵:《铁屋中的呐喊》,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第57、69页。这里也有含混:“这个小伙计可能已经长大了”,此说不确,说这句话的时间是叙述故事的时间,而非故事发生的时间,所以说这一句话的是叙述故事的成年人。
确定叙述者的年龄是很重要的。叙述者当年在咸亨酒店当小伙计时,他和“短衣帮”“掌柜”一样鄙视孔乙己,固然因为孔乙己的“可笑”,也由于他受到“短衣帮”“掌柜”鄙视孔乙己态度的影响。对于这样一个少年来说,情有可原,无可厚非,然而“二十多年”之后,他津津乐道孔乙己的“可笑”,却是一个严重的问题了,正如李欧梵所说:“作为正在回忆一个受害者的成年人,他仍然只是庸众中之一员。”1李欧梵:《铁屋中的呐喊》,第69页。
也许问题比这更要严重得多。这个叙述者为什么要叙述孔乙己的故事?叙述动机何在?其实并不仅仅是因为孔乙己的“可笑”。叙述者自云:
我从此便整天的站在柜台里,专管我的职务。虽然没有什么失职,但总觉得有些单调,有些无聊。掌柜是一副凶脸孔,主顾也没有好声气,教人活泼不得;只有孔乙己到店,才可以笑几声,所以至今还记得。
也就是说,“我”之所以至今记得孔乙己的故事,原因在于“我”在咸亨酒店的工作“有些单调,有些无聊”,十分失意,“只有孔乙己到店,才可以笑几声”。“有些单调,有些无聊”的真正原因,是因为:
掌柜说,样子太傻,怕侍候不了长衫主顾,就在外面做点事罢。外面的短衣主顾,虽然容易说话,但唠唠叨叨缠夹不清的也很不少。他们往往要亲眼看着黄酒从坛子里舀出,看过壶子底里有水没有,又亲看将壶子放在热水里,然后放心:在这严重监督下,羼水也很为难。所以过了几天,掌柜又说我干不了这事。幸亏荐头的情面大,辞退不得,便改为专管温酒的一种无聊职务了。
述者似乎对掌柜有些怨恨,对自己没有能够在“店面隔壁的房子里”侍候长衫主顾有些失落。这个对自己“二十多年前”的一丁点得失如此斤斤计较的人,却对孔乙己受到的无端的伤害无动于衷,甚至“至今”还要津津乐道,其冷漠、自私,实在可怕。因此,我以为,就小说的艺术技巧而言,这种叙述反讽,是《孔乙己》杰出的叙述技巧。韩南认为《孔乙己》是“鲁迅最优秀的小说之一”;他在称赞“反语是鲁迅小说的第一个、也许是最显著的特点”时说:“反语的对象是那个被社会抛弃的读书人,反语要素则是在酒店里当伙计那个十二岁的孩子。这种反语是我们称为描述性的一类,是通过一个戏剧化的叙述者之口讲出来的。”1韩南:《鲁迅小说的技巧》,张隆溪译,《韩南中国小说论集》,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366页。“反语”,即反讽;“反语要素”,是指这篇小说的反讽,关键在于叙述者及其叙述。
叙述反讽还表现在话语方式上。孔乙己其人,孔乙己的故事,是“我”的叙述对象,然而这个叙述行为却并非直接从孔乙己开始的:
鲁镇的酒店的格局,是和别处不同的:都是当街一个曲尺形的大柜台,柜里面预备着热水,可以随时温酒。
这是小说的开始。叙述鲁镇酒店的“格局”,是为了叙述这个“柜台”,而“我”当年正是站在“柜台”工作的“伙计”;同时由这个“格局”,紧接着叙述酒店的两类客人,即“短衣帮”和“长衫主顾”,而“我”却是只能站在“柜台”服务“短衣帮”的酒店下级“伙计”。直到叙述了“我”当年在咸亨酒店的工作如何“有些单调,有些无聊”,才讲到孔乙己。
这是一种类似于自我中心主义者的话语方式:处处以自我为中心,事事由自我而开始。也正因为如此,“我”津津乐道的是孔乙己如何“可笑”、如何让人“快活”,只是叙述孔乙己的外在的表现,一次也没有言及孔乙己受到嘲笑、侮辱时的心理。由于限制叙述视角的原因,叙述者无法叙述对象的内心世界,这个叙述成规,并不足以作为“我”毫不关心孔乙己内心世界的充足理由。推己及人,任何一个正常的成年人都有此能力。何况“我”是一个对自己在咸亨酒店的遭遇十分敏感并且至今耿耿于怀的人?
鲁迅自述,《孔乙己》的命意,“是在描写一般社会对于苦人的凉薄”2孙伏园:《鲁迅先生二三事·〈孔乙己〉》,《鲁迅回忆录》(上册),第83页。。掌柜、“短衣帮”等“庸众”,对于孔乙己的“凉薄”,就是作者所要表现的“吃人”。而“我”,正是“庸众”的一员。
小说叙述学理论,毕竟是后见之明,小说家也并非完全按照叙述学理论而写作;完全依据叙述学理论分析小说,其失也固。严家炎先生论《孔乙己》,对叙述者“我”及其叙述,有一个十分独到的看法:《孔乙己》的叙述者是一个成年人,而叙述当年孔乙己的故事,则回到少年。1严家炎:《复调小说:鲁迅的突出贡献》,《严家炎全集·第6卷·论鲁迅的复调小说》,新星出版社2021年版,第81~82页。韩南《鲁迅小说的技巧》论及《孔乙己》时,亦云:“虽然这故事是事隔近三十年之后的回忆,却没有让成年人的判断来控制孩子的天真。”2韩南:《鲁迅小说的技巧》,张隆溪译,《韩南中国小说论集》,第366页。二者的说法,十分相近。从小说叙述学理论来说,“我”的这种叙述,颇不合常规,然而验之于作品,这个说法确实符合作品的实际。尤其是孔乙己最后一次来咸亨酒店喝酒,众人依然“取笑”他,并且是异常刻毒地“取笑”,这时——
我温了酒,端出去,放在门槛上。他从破衣袋里摸出四文大钱,放在我手里,见他满手是泥,原来他便用这手走来的。不一会,他喝完酒,便又在旁人的说笑声中,坐着用这手慢慢走去了。
不仅是叙述内容,而且叙述语调,似乎隐约流露出对孔乙己的怜悯,这是一个少年良心未泯的不自觉的表现。这显然是当年那个小伙计的叙述视角,而不是那个津津乐道的成年人的叙述视角。韩南所谓“却没有让成年人的判断来控制孩子的天真”,此说十分深刻,只是不尽准确:主导小说叙述的明显是“二十多年”后的成年人,只是在叙述孔乙己“最后一次到店”时,偶尔不自觉地回到“二十多年”前的少年的视角。矛盾乎?这种叙述的不统一,或许正是文学作品丰富性和复杂性之所在。
严家炎先生由此论述鲁迅小说的“复调”的叙述特征,确属慧眼卓识。正如钱锺书《管锥编》论述《史记》称“马迁奋笔,乃以哲人析理之真通于史家求事之实,特书大号,言:前载之必须不可尽信,传闻之必须裁择,似史而非之‘轶事’俗说应沟而外之于史,‘野人’虽为常‘语’,而‘缙绅’未许易‘言’”,然而“《史记》于‘怪事’‘轶闻’,固未能芟除净尽”3钱锺书:《管锥编》第一册,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251~253、271,303、306~308页。;“勿信‘天道’,却又主张‘阴德’,说理固难自圆,而触事感怀,乍彼乍此,亦彼亦此,浑置矛盾于不顾,又人之常情恒态耳”4钱锺书:《管锥编》第一册,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251~253、271,303、306~308页。。名著《复义七型》的作者威廉·燕卜荪则视这种矛盾、含混、歧义,为文学作品的思想和艺术的重要特征。《复义七型》虽然是集中论述由词义、语义和句法的多义性所显示出的作品思想的内在之“矛盾”,但随后出版的《田园诗的几种变体》则是“将研究的层次由句与词上升到叙述”1约翰·康斯特布尔:《燕卜荪评论集》,引自约翰·哈芬登《威廉·燕卜荪传》,张剑、王伟滨译,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16年版,第一卷第十三章之注释33(第466页)。按,威廉·燕卜荪此著书名Seven Types of Ambiguity,或译为“朦胧的七种类型”(威廉·燕卜荪:《朦胧的七种类型》,周邦宪、王作虹、邓鹏译,中国美术学院出版社1996年版);“复义”似较“朦胧”确切。根据全书的论述,“Ambiguity”有含混、歧义、矛盾的意思。所以约翰·哈芬登说:“矛盾(conflict)才是《复义七型》中的关键词。”。燕卜荪研究专家约翰·哈芬登说:“‘矛盾’(conflict)才是《复义七型》中的关键词……‘冲突’(clash)可以说是《田园诗的几种变体》的主题词。”2约翰·哈芬登:《威廉·燕卜荪传》第一卷,张剑、王伟滨译,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16年版,第442~443页。上文所分析的“大约孔乙己的确死了”一句,类似《复义七型》中论述的类型;而此处分析的孔乙己“最后一次到店”的叙述,似近乎《田园诗的几种变体》中论述的叙述之“冲突”。
“二十多年”前的那个小伙计,目送着孔乙己“在旁人的说笑声中,坐着用这手慢慢走去了”,其恻隐之心的不自觉的流露,正是人性之良心未泯的表现;而“二十多年”后的“我”津津乐道地回忆孔乙己的“可笑”,殊不自知这是他在“庸众”世界中耳濡目染以致良心泯灭的体现。“我”回忆当年的见闻时,曾说:“在这些时候,我可以附和着笑,掌柜是决不责备的。”这正是“我”在“庸众”世界中耳濡目染的从众的变化过程。
因此,“二十多年”前的小伙计与“二十多年”后的“我”之于孔乙己的态度的细微差异,隐含着作者设计小说的反讽叙述的深刻命意。严家炎先生论《孔乙己》的叙述,不囿于小说叙述学理论教条,忠实于作品的文本的具体实际,见识之圆通,令人印象深刻。此例,当为文学研究之生搬硬套理论教条者三思,尤以“鲁迅研究”之理论化、玄学化者为然。
二 语言:话语暴力与失语症
鲁迅有著名的“骂杀”“捧杀”之说。3鲁迅:《骂杀与捧杀》,《鲁迅全集》第5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585~586页。借言之,《孔乙己》中“掌柜”“短衣帮”之“取笑”孔乙己,“笑杀”乎?理论化、玄学化之表述,当曰“话语暴力”乎?又,孔乙己应对“取笑”,说出“之乎者也”之类“教人半懂不懂的”的话来,可谓“失语症”乎?据此,《孔乙己》叙述孔乙己的故事,或可说叙述的是“话语”的故事。
《孔乙己》“描写一般社会对于苦人的凉薄”,这个命意是通过描写“掌柜”“短衣帮”对孔乙己的“取笑”来实现的。这种“取笑”,有三个明显的特征。第一,这是十分恶毒、残酷的“取笑”:
孔乙己一到店,所有喝酒的人便都看着他笑,有的叫道,“孔乙己,你脸上又添上新伤疤了!”他不回答,对柜里说,“温两碗酒,要一碟茴香豆。”便排出九文大钱。他们又故意的高声嚷道,“你一定又偷了人家的东西了!”孔乙己睁大眼睛说,“你怎么这样凭空污人清白……”“什么清白?我前天亲眼见你偷了何家的书,吊着打。”
“伤疤”“吊着打”,事实真相究竟如何,不得而知;可以肯定的是,这是孔乙己受到的极端的打击和侮辱,“短衣帮”们显然是乐见强者的残酷施暴,丝毫也没有对弱者的出于人之常情的同情。这种对弱者被强者残酷施暴的“取笑”,是缺失同情心、丧失人性的最鲜明的体现。
第二,这是恶意设计的“取笑”:
孔乙己喝过半碗酒,涨红的脸色渐渐复了原,旁人便又问道,“孔乙己,你当真认识字么?”孔乙己看着问他的人,显出不屑置辩的神气。他们便接着说道,“你怎的连半个秀才也捞不到呢?”
刚刚被“取笑”的孔乙己竟然木讷到这种地步,浑然不知人们故意设计圈套来“取笑”他,竟然还以“显出不屑置辩的神气”搭理将要再次“取笑”他的人们。欺辱一个老实人的愚蠢,尚在其次,更重要的是,科举失意,是孔乙己最大的人生失败,也是最严重的心理创伤,“短衣帮”们残酷地撕开孔乙己的这个心理创伤,以“取笑”他作为酒足饭饱时的乐趣。
第三,这种“取笑”,是不可理喻的。“认识字”与否与能否考上秀才,二者之间并没有必然性的因果关系:“认识字”并不等于一定能考上秀才;没有考上秀才,并不等于不“认识字”。孔乙己不善应对,所以不能据理力争。或许是因为“短衣帮”的这一“取笑”,直击其内心创伤,因而无力回应。
“鲁镇”,这个乡镇世界,是一个传统的“乡村”“共同体”(Gemeinschaft)1参阅斐迪南·滕尼斯《共同体与社会》,张巍卓译,商务印书馆2019年版;雷蒙·威廉斯《乡村与城市》,韩子满、刘戈、徐珊珊译,商务印书馆2013年版;彼埃尔·V·齐马《社会学批评概论》,吴岳添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任何“乡村”之“共同体”,自有其等级秩序。小说开篇介绍咸亨酒店“格局”和顾客——“长衫主顾”与“短衣帮”——时,就暗示了这种等级秩序。这样的“乡村”之“共同体”中,普通民众对于知识和“读书人”,既尊崇、敬畏,又嘲笑、菲薄,《儒林外史》中胡屠户对女婿范进中举前后截然不同的态度,就是十分典型的生动例子。戏曲如《牡丹亭》中的私塾教书先生,作为“腐儒”“学究”“村塾”的形象,更为常见。
对“腐儒”“学究”“村塾”的嘲笑,其中固然有嘲笑具体个人之迂腐、穷酸的原因,然而更重要的则是权力、地位方面的原因。所以在《儒林外史》中,同一个范进,中举之前被斥责为“窝囊废”,中举之后却被视为“文曲星”下凡。《孔乙己》中“短衣帮”们“取笑”孔乙己“你怎的连半个秀才也捞不到呢”,及其所谓“这一回,是自己发昏,竟偷到丁举人家里去了。他家的东西,偷得的么”,对科举失败者孔乙己的“取笑”,对科举成功者丁举人的敬畏,就是这种思想、观念的体现。因此,《孔乙己》中的“掌柜”“短衣帮”对孔乙己的“取笑”,其实质就是对一个科举失败者的嘲笑、鄙视。鲁迅自云《孔乙己》“描写一般社会对于苦人的凉薄”。“苦人”,指孔乙己这个科举失败者。“凉薄”,指“掌柜”“短衣帮”的“取笑”,对于孔乙己造成的心理伤害。
“共同体”的有序性,不仅体现在等级秩序,也体现在其成员对这种等级秩序的默认和维护。正如彼埃尔·V·齐马《社会学批评概论》在论述迪尔凯姆社会学理论时所说:
首先涉及的是被一个社会集团所接受的、并决定该集团每个成员的仪式的一整套价值和规范……当一种禁忌或法律被违反时,集体便执行具有示范和象征作用的惩罚。集体通过以它的名义进行的惩罚,来向不尊重它的规范的个人显示它的存在……惩罚往往具有一种加强集团内部团结一致的仪式功能。1彼埃尔·V·齐马:《社会学批评概论》,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10页。
这是彼埃尔·V·齐马在建构文学社会学理论时,所引述的社会学理论之一。这个理论所谓的“惩罚”,与鲁迅《呐喊》《彷徨》所表现的乡土社会的“吃人”,其思想实质似无大异。比如《祝福》中描写的“鲁镇”对祥林嫂再嫁的态度、看法,实为一种严厉、残酷的精神虐待,即“惩罚”之谓也,亦“吃人”之谓也。
《孔乙己》中“掌柜”“短衣帮”对孔乙己的“取笑”,也是如此。“长衫主顾”与“短衣帮”的衣着的不同,也是身份、地位、权力的区别。默认和维护这种区别,各安其位,各行其是,才能延续“鲁镇”这样的“乡村”之“共同体”的稳定。稍有例外,有违这种“乡村”之“共同体”的风俗、礼仪,则会扰乱甚至危及其井然有序的秩序。
然而,孔乙己恰恰是这样的一个例外。“孔乙己是站着喝酒而穿长衫的唯一的人。”此乃小说极其生动而深刻的警策之辞。“唯一的人”,例外也:既不属于“长衫主顾”的阶层,亦不属于“短衣帮”的等级。孔乙己虽然穿着一件长衫,却不能像“长衫主顾”那样“踱进店面隔壁的房子里,要酒要菜,慢慢地坐喝”,而是和“短衣帮”一样“靠柜外站着”喝酒。换言之,孔乙己“连半个秀才也捞不到”,却竟然像丁举人那样穿着一件长衫,出现在“短衣帮”面前。对“短衣帮”来说,孔乙己作为一个“站着喝酒而穿长衫的唯一的人”,似乎有意嘲笑、挑衅了他们对知识、“读书人”及其身份、地位、权力的尊崇与敬畏。于是,他们不约而同地以“取笑”的方式实施对孔乙己的“惩罚”。“取笑”,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其实质就是“吃人”,其形式就是话语暴力。
反之,仅仅因为“偷书”,孔乙己被“何家”“丁举人”等“吊着打”,看似匪夷所思,实则不仅仅是因为“偷书”,而是同样因为“孔乙己是站着喝酒而穿长衫的唯一的人”:他“穿长衫”,却与“短衣帮”一起“站着喝酒”,这样将“读书人”混同于“劳力者”,有辱斯文,有损“读书人”的颜面。因此,“何家”“丁举人”将孔乙己“吊着打”,就是为了维护“共同体”社会秩序而实施的“惩罚”。
因此,“短衣帮”对孔乙己的“取笑”,“何家”“丁举人”对孔乙己“吊着打”,都是“共同体”之阶级权力的体现;虽然“惩罚”的形式不同,但其实质完全同一。这样,孔乙己在“鲁镇”的命运,最终焉得不“死”?不是“大约”,只能是“的确”!
与“短衣帮”以“取笑”实施话语暴力相反,孔乙己则丧失话语能力,即所谓“失语症”。彼埃尔·V·齐马《社会学批评概论》云,“在词汇、语义和句法方面确定一些特定的集体利益的是一种意识形态的语言”,每一共同体中不同等级的成员都“求助于”属于他们等级的语言,即“社会方言”,“来解释和捍卫他们各自的观点”。1彼埃尔·V·齐马:《社会学批评概论》,第157~161、158页。斐迪南·滕尼斯《共同体与社会》亦云:在“共同体”中,“因为每一个自为存在着的结合,都建立在内部共同领会的基础上,就此而言,结合存在于共同的记忆与语言之中,共同的记忆与语言对大多数人来说就是客观的、心理的现实,所以,在一定程度上,或者说,在某些确定条件里,默认一致承当起的人们之间的原始的有机关联,将发展成一种公认的观念与本质”2斐迪南·滕尼斯:《共同体与社会》,商务印书馆2019年,第416页。。
据此,孔乙己和“短衣帮”的话语,属于不同等级的语言,即所谓“社会方言”。然而,问题在于,“孔乙己是站着喝酒而穿长衫的唯一的人”,既不属于“长衫主顾”等级,又不属于“短衣帮”群体。虽然他自以为是“读书人”,能说出“之乎者也”之类的话来,但这种话语却不属于“短衣帮”的语言,如叙述者所说:“他对人说话,总是满口之乎者也,教人半懂不懂的。”面对“短衣帮”的“取笑”,他的这种“之乎者也”话语,理所当然地不足以自辩。此亦正如彼埃尔·V·齐马《社会学批评概论》所云:个人属于共同体的不同等级、群体,有时候,“一种个人的话语之所以不连贯,往往是由于他使用了互不相容的词汇(即社会方言)”3彼埃尔·V·齐马:《社会学批评概论》,第157~161、158页。。
孔乙己便涨红了脸,额上的青筋条条绽出,争辩道,“窃书不能算偷……窃书!……读书人的事,能算偷么?”接连便是难懂的话,什么“君子固穷”,什么“者乎”之类,引得众人都哄笑起来:店内外充满了快活的空气。
“窃书不能算偷”,“君子固穷”,当然不属于“短衣帮”的语言。以“君子固穷”这句孔子名言应对“你怎的连半个秀才也捞不到呢”这句“取笑”,当属理所当然。
“物以类聚,人以群分”,一袭长衫,岂可与“短衣帮”为伍而“站着喝酒”?“君子固穷”,是也,然则岂不闻下句“小人穷斯滥矣”?“滥矣”,岂可与言?“不可与言而言之,失言。”孔乙己的错误在于,他应对“短衣帮”的“取笑”,说的是“读书人”的话语。“见人说人话,见鬼说鬼话”,孔乙己不明此理,被“短衣帮”等“庸众”视为迂腐、穷酸,正所谓“事有必至,理有固然”。
孔乙己的“失语症”,不仅体现在他应对“短衣帮”的“取笑”时所使用的话语。他和小孩子们的交往中,也时有“失语”:
有几回,邻居孩子听得笑声,也赶热闹,围住了孔乙己。他便给他们茴香豆吃,一人一颗。孩子吃完豆,仍然不散,眼睛都望着碟子。孔乙己着了慌,伸开五指将碟子罩住,弯腰下去说道,“不多了,我已经不多了。”直起身又看一看豆,自己摇头说,“不多不多!多乎哉?不多也。”于是这一群孩子都在笑声里走散了。
“多乎哉?不多也”,借用孔子之言,既近乎自嘲,亦为“着了慌”之际不自觉地说出小孩子们“难懂”的话来。又如孔乙己唯一的一次与“我”说话,考“我”:“回字有四样写法,你知道么?”虽然是讨好、搭讪,却适得其反:“我愈不耐烦了,努着嘴走远”;孔乙己却是“刚用指甲蘸了酒,想在柜上写字,见我毫不热心,便又叹一口气,显出极惋惜的样子”。在“我”看来,孔乙己无疑是迂腐、穷酸。
“鲁镇”这样世界,如此不能允许其成员以例外、独异的形象存在,如《祝福》中祥林嫂受到歧视,《孔乙己》中孔乙己受到“取笑”,大而言之,既是对异己的、非我属类的存在的无情扼杀,也是对个人的存在、对独立个性的存在的全然否定。在这样一个传统的风俗社会,秩序井然,对任何一个难以归类的独立存在个体的全然否定和无情扼杀,十分清楚地表明了这个社会的“吃人”的专制主义特征。任何专制主义社会,都是绝无自由、独立可言的。《孔乙己》的深刻的象征意义,或在于此。孔乙己是一个失意、沦落的“读书人”,他没有被专制体制收编,“连半个秀才也捞不到”,因而被“庸众”所“取笑”,因此同为“读书人”的读者,或更加心有戚戚焉?即使作者,既云“描写一般社会对于苦人的凉薄”,其心有戚戚焉,则是肯定的。
三 叙述结构:“散文化”文体特征
小说叙述故事,一般是以故事的时间先后顺序而依次叙述的,即使叙述有所安排、组织,间以倒叙、插叙、补叙,故事的时间性则是肯定的。中国古代史传,历史事件或个人经历之外的偶然事例的叙述,也以“初”之类的时间词,表明事情发生的时间。然而,《孔乙己》的叙述,孔乙己的故事,却不是在这个意义上进行叙述的。小说叙述的第一个故事,是这样开始的:
孔乙己一到店,所有喝酒的人便都看着他笑……
没有故事发生的明确时间。接下来叙述的几件孔乙己的故事,同样如此,或曰“有一回”、或曰“有几回”。也就是说,这些故事的发生时间,都是不确定的,甚至未必是以叙述的时间先后而发生的。改变这些故事的叙述先后顺序,对于表现人物,其实并没有什么影响。统观小说全篇,只是到了最后,孔乙己的故事才有较为明确的时间:一是人们议论孔乙己长久没有到店喝酒,时间是“有一天,大约是中秋前的两三天”;二是孔乙己最后一次到店喝酒:
中秋之后,秋风是一天凉比一天,看看将近初冬;我整天的靠着火,也须穿上棉袄了。一天的下半天……
“中秋之后”“将近初冬”,季节的强调,暗示“一天凉比一天”的言外之意。进一步观察,第二个叙述单元,叙述“短衣帮”如何“取笑”孔乙己而带来“快活”的,以“孔乙己一到店,所有喝酒的人便都看着他笑”一句开始叙述,似乎“短衣帮”不止一次这样“取笑”孔乙己,仿佛孔乙己每次到店喝酒,“短衣帮”都是这样“取笑”他的;第三个叙述单元,叙述孔乙己与“我”、与小孩子们的两个小故事,这两个小故事发生的时间,也是未必这样先后发生的。
与此同时,小说以另外一种叙述形式组织故事的叙述。如本文第一节所说,小说是由“我”在咸亨酒店的遭遇开始叙述的,然后以“只有孔乙己到店,才可以笑几声,所以至今还记得”而说到孔乙己,这是小说的第一个叙述单元。第二个叙述单元,叙述“短衣帮”如何“取笑”孔乙己而带来“快活”的;第三个叙述单元,叙述孔乙己与“我”、与小孩子们的故事。在这第二、第三叙述单元之间,以这样的话语组织过渡、衔接:
在这些时候,我可以附和着笑,掌柜是决不责备的。而且掌柜见了孔乙己,也每每这样问他,引人发笑。孔乙己自己知道不能和他们谈天,便只好向孩子说话。
第四个叙述单元,叙述人们议论为什么“孔乙己长久没有来了”和孔乙己最后一次到店喝酒,而在第三、第四叙述单元之间,是以这样的过渡话语进行衔接的:
孔乙己是这样的使人快活,可是没有他,别人也便这么过。
第五个叙述单元,也是最后一个叙述单元,简述“自此以后,又长久没有看见孔乙己”,结束孔乙己的故事。很显然,第二和第三叙述单元,如果改变叙述次序,先叙述孔乙己与“我”、与小孩子们的两个小故事,再叙述“短衣帮”如何“取笑”孔乙己,似乎也不是不可以的,只要将过渡语略作变化即可:将“孔乙己自己知道不能和他们谈天,便只好向孩子说话”,改成“孔乙己不仅不能和孩子说话,而且也不能和大人说话”。
由以上两个方面的分析来看,《孔乙己》的叙述结构,十分独特。这种叙述结构,体现了叙述者对叙述内容的干预、控制和解释。这就是一种“散文化”的叙述结构,即以散文文体的叙述方式组织小说的故事的叙述。韩南《鲁迅小说的技巧》一文的一条注释中,提出了这样一个论断:
鲁迅终身都是一位小品文家,他关于文学目的的强调的观念使他的全部作品统一为一个整体,而使杂文、随笔和小说之间体裁的界限不那么分明。1韩南:《鲁迅小说的技巧》,张隆溪译,《韩南中国小说论集》,第359页注释2。
这个判断很有见地,也符合鲁迅的创作实际。《孔乙己》的“散文化”叙述结构,正是这篇小说与杂文、随笔之间“体裁的界限不那么分明”的一个重要的文体特征。
《孔乙己》的“散文化”叙述结构,绝不是孤例。比如《阿Q正传》,第一章题目是“序”,依次叙述“我要给阿Q做正传”的四个“困难”,实际上就是以此特殊的方式叙述阿Q的故事;从第一到第四个“困难”,这当然不是阿Q故事发生的时间和顺序。此后的第二、第三章,只是大体上按照时间的顺序,进行叙述;或者更准确一点地说,所叙述的故事,只有先后的时间顺序,却没有准确的时间,多用“……之后”“从此以后”提示故事发生的时间顺序,其中间以“这是未庄赛神的晚上”“有一年的春天”,提示不很具体、确切的时间。只是从第四章开始,故事发生的时间越来越具体,并且故事之间的时间联系也愈加紧密。
与此同时,叙述者对故事和叙述的安排、控制和选择、解释,十分明显。全篇共九章,每一章都是以标题提示叙述内容,这实际上是如标题所示,以九个叙述单元,从九个方面,叙述阿Q的故事,解释阿Q其人。这与《孔乙己》的叙述形式和叙述结构,几乎是一样的。再如《狂人日记》,十三则日记,除了第一则,其余十二则,只是以大体的时间顺序而依次编辑的,其中各则日记的次序,未必就是日记所记事情发生的时间顺序,比如第三、六、九则日记,似乎完全可以以另外的次序进行安排。
上述叙述结构的特征,显然与这些小说的“非情节化”故事特征有密切的关系,这也是鲁迅小说的现代性之体现。1参阅严家炎论中国现代小说的“现代化”特点,其中第二、三点,对此有简洁的论述,见《中国现代小说流派史》,人民文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21~24页。然而,从文体特征而论,似更为确切。我在上文之所以将这种叙述结构称为散文化叙述结构,指的是以散文文体的叙述方式组织、安排小说的叙述,意在于此。
散文化叙述结构,未必仅仅只是以故事的时间顺序、以故事的非因果逻辑关系进行叙述。1980年代以来,以此而论中国现代小说的散文化叙述结构者,多依据西方现代小说叙事学理论,论述颇有真知灼见,解志熙《新的审美感知与艺术表现方式——中国现代散文化抒情小说综论》、陈平原《中国小说叙事模式的转变》等,先后发表、出版,均为有代表性的学术成果。2参阅解志熙《新的审美感知与艺术表现方式——中国现代散文化抒情小说综论》,《河南大学学报》1986年第5期;陈平原《中国小说叙事模式的转变》,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上文指出《孔乙己》的故事时间诸问题,属于这种分析方式。我在此试图依据中国传统的文章理论,着眼于散文的文体特征,讨论鲁迅小说的散文化叙述结构。上文指出的《孔乙己》叙述结构的第二方面的诸问题,则是依据中国传统的文章理论作出的分析。下文对此略作总结、概括。
第一,根据某种叙述意图以事情的分类、性质和意义组织、安排叙述,其表征之一,就是例如上文分析《孔乙己》所揭示的那样,叙述单元之间,以过渡语衔接上下叙述单元,诸如“孔乙己自己知道不能和他们谈天,便只好向孩子说话”“孔乙己是这样的使人快活,可是没有他,别人也便这么过”这样的过渡语。这种叙述单元之间的过渡语的使用,是散文的典型的文体特征。中国古代文章的理论和实践,十分注意这一点,所谓“起承转合”是也。众所周知,兹不赘述。
第二,中国古代文论有著名的“警策”之说。陆机《文赋》云:“立片言而居要,乃一篇之警策。虽众辞之有条,必待兹而效绩。”《孔乙己》中的“孔乙己是站着喝酒而穿长衫的唯一的人”一句,即为“警策”之言。孔乙己故事的全部秘密,尽在此一句,可谓“乃一篇之警策”。不仅如此,这一句既由上文叙述“长衫主顾”“短衣帮”之别而来,也是下文叙述孔乙己故事的主旨,可谓“虽众辞之有条,必待兹而效缋”。
第三,小说理论有“草蛇灰线”“伏线千里”之说,主要指故事或人物言行、心理等方面的前后呼应,属于“故事”范畴,如小说开始叙述墙上挂着一把猎枪,则读者意会此后这把猎枪必然打响;文论有“照应”“呼应”之说,则是指语义、字面的上下文的照应,属于“措词”范畴:桐城文论,颇有细则;而八股作法,殆若公式。二者的区别,是很明显的。《孔乙己》中散文的呼应写法,十分明显。比如第一个叙述单元的最后一个自然段中的话:“只有孔乙己到店,才可以笑几声,所以至今还记得。”这既是承上启下的话,也可以将下文反复出现的“哄笑”“笑声”,看作对这一“笑”字的呼应。
其实,《呐喊》中的《一件小事》《鸭的喜剧》等篇,散文化的叙述特征更为明显。有的研究者甚至干脆将这些小说视为散文。竹内好称《一件小事》是“小作品”,认为《鸭的喜剧》是“描写身边琐事的小品文”1竹内好:《从“绝望”开始》,靳丛林编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106~107、109页。,绝非误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