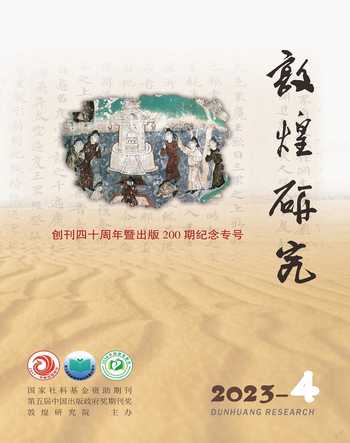莫高窟的贤劫千佛诞生变
2023-09-28梁尉英梁旭澍
梁尉英 梁旭澍



内容摘要:莫高窟第197窟主室西壁佛龛帐门南北两侧中唐绘制的壁画非多子塔,今经研究判定为贤劫千佛从莲花中出生的贤劫千佛诞生变;由此推及第169窟与第197、351窟同样位置、同样内容、不同布局结构的三铺壁画亦应为贤劫千佛诞生变。且第197、351窟南、北、东三壁绘制的壁画可以称作简约式的贤劫千佛诞生变。贤劫千佛诞生变是由五通曼荼罗演变派生而来的。贤劫千佛诞生变的窟数、铺数虽少,但对敦煌佛教史乃至中国佛教史、佛教美术史等具有史料价值和研究价值。
关键词:莫高窟;壁画;非多子塔;贤劫千佛;从莲花中诞生;贤劫千佛诞生变
中图分类号:K879.2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4106(2023)04-0170-17
On the Illustration of the Birth of the Thousand Buddhas of
Bhadrakalpa in Mogao Caves
—Beginning with the Image of Bahuputraka-caitya in Cave 197
LIANG Weiying1 LIANG Xushu2
(1. Editorial Department, Dunhuang Academy, Lanzhou 730030, Gansu; 2. Exhibition Center, Dunhuang Academy, Dunhuang 736200, Gansu)
Abstract:Research on the murals on either side of the niche in the west wall in Mogao cave 157, which was painted in the Middle Tang dynasty, has revealed that the painting is not an image of Bahuputraka-caitya, as previously believed, but an illustration to the birth of the Thousand Buddhas of Bhadrakalpa(the“auspicious age” in Buddhist theology) from a lotus flower. Furthermore, three other murals painted in the same location, and containing the same thematic contents and composition, have been identified in caves 169, 197 and 351. Meanwhile, an analysis of the murals on the south, north and east walls of caves 197 and 351 has concluded that these paintings can best be regarded as simplified illustrations of the same theological event. This illustration derives from a mandala depicting Amitabha and the Fifty Bodhisattvas. Although this illustration is small in number and appears in only a few caves, it is still very significant for the study of Buddhist history in Dunhuang, and in the history of Chinese Buddhist fine art.
Keywords:Mogao Grottoes; mural; Bahuputraka-caitya; Thousand Buddhas of Bhadrakalpa; birth from a lotus flower; illustration of the birth of the Thousand Buddhas of Bhadrakalpa
(Translated by WANG Pingxian)
序 说
莫高窟第197窟位于南區九层楼南段由下而上的第二层,坐西向东,始建于中唐(吐蕃占领统治敦煌地区时期),后经五代、宋(曹氏归义军时期)多次修缮,重绘大部分壁画。
第197窟主室西壁中唐凿镌盝顶形佛龛。龛外帐门南北两侧壁面,中唐绘制屏风式的内容、结构完全相同的壁画各一铺(图1、2)。每铺画面皆为白地,各绘土红色干、枝和绿叶的莲花树,分枝顶端各有一朵盛开的大莲花。本文为行文方便计,姑且将其称之为“莲花树”,现实中并不存在,是画师艺术联想、巧妙构思而虚拟的宗教性神树。此种莲花树是有其历史渊源的。今见画面颜色,大多为年久颜料褪变之色,并非原始本色。
北侧莲花树顶端盛开一朵赤褐色的单层覆瓣大莲花,枝端每朵大莲花上都有一身结跏趺坐、双手结定印、头面侧向中央佛龛的禅定佛,皆具圆形头光、身光。头光或红色或黑色,身光或绿色或浅灰色。禅定佛皆内着绿色络腋、外着褐色袈裟。13身禅定佛由上而下呈3、2、3、3、2身大体平行排列的布局。
南侧枝端每朵大莲花亦有一身结跏趺坐、双手结定印、头面侧向中央佛龛的禅定佛,头光、身光、手印、着装皆与北侧者大同小异。13身禅定佛由上而下呈3、3、3、2、2身大体平行排列的布局。
这两铺壁画艺术风格迥然不同。北侧者,莲干、莲枝粗壮,花与叶肥大,显得茁壮茂盛、生机勃勃;禅定佛壮硕有生气;画技成熟老到,精气神颇佳。南侧者,莲干、莲枝柔细,花与叶细小;禅定佛细瘦乏生气;画技稚嫩,精气神欠佳。显而易见,这两铺对称的壁画非一人所绘,甚或师徒二人同时分别作画,为师者于北侧先行示范,为徒者南侧后步学笔。
关于这两铺壁画的定名,笔者所见有二说:
其一,敦煌文物研究所整理《敦煌莫高窟内容总录》称多子塔[1],敦煌研究院以前者为基础修订增补的《敦煌石窟内容总录》承袭此说[2]。
其二,张大千《漠高窟记》称:“第二百八十窟……贤劫千佛左右帐门”{1}[3],谢稚柳亦持此说[4]。
笔者自2006年以来,因工作之需阅读佛教典籍时,常看到关于多子塔的记述,屡屡觉得第197窟佛龛两侧壁画所谓“多子塔”的画面内容与经论所述多子塔的意涵大相径庭、名不符实。今此陈述管见,认为这两铺壁画应是贤劫千佛从莲花中诞生的本生变,不当之处,敬请斧正。
一 佛教经论关于多子塔的叙说
多子塔又名多子支提、多子窣堵婆(波)、千子塔、千子窣堵婆、千子制底、放弓仗塔等。失译者名二卷本《辟支佛因缘论》卷下《王舍城大长者悟辟支佛因缘论》载:
从天寿尽,王舍城大长者家……斫一小树,无诸枝柯,一人独挽,都无滞礙,即挽出林。见斯事己,即思惟而体是言:“我于今者得见因缘。”即说偈言:
我见伐大树 枝叶极繁多
稠林相钩挂 无由可得出
世间亦如是——
男女诸眷属 爱憎系缚心
于生死稠林 不可得解脱
小树无枝柯 稠林不能碍
观彼觉悟我 断绝于亲爱
于生死稠林 自然得解脱
即于彼处得辟支佛……时人因名多子塔。[5]
此说世人多子是牢牢系缚人心的人生累赘,多子使世人不能求得解脱。大长者悟透此理而觉悟,求解脱得道而为辟支佛。大长者“现通入灭”后,其亲人眷属为纪念此等非凡之事而建造了塔庙,时人将这座塔庙称为多子塔。此多子塔是贬意,寓意多子是人生的累赘,并不是专为多子而造的塔庙。大长者所在的王舍城,是古印度摩揭陀国的都城,其址在今印度恒河中游巴特那市比哈尔处的拉查基尔{2}。此多子塔庙今已不存。
另有多种经论之说,认为多子塔是为纪念贤劫千佛从莲花中诞生而建造,后人观瞻礼拜,成为地标性的实体建筑物。后秦佛陀耶舍、竺佛念译《长阿含经》卷11《阿?夷经》载:“毗舍离有四石塔,东名忧园塔,南名象塔,西名多子塔,北名七聚塔。”[6]又载:“(尼乾子)不越四塔:东忧塔,南象塔,西多子塔,北七聚塔。”[6]此座多子塔既称为“四石塔”之一,可知其是用石头砌筑的,位于毗舍离城,约当今之恒河北岸、干克河东岸的毗萨尔之地。
唐玄奘、辩机《大唐西域记》卷7《吠舍厘国·五·千佛本生故事》载:“(释迦牟尼佛)告涅槃期侧不远有窣堵波,千子见父母处也。”[7]又载:“千子归宗侧不远有窣堵波,是如来经行旧迹,指告众曰:‘昔吾于此归宗见亲。欲知千子,即贤劫千佛是也。”[7]597吠舍厘即毗舍离。此言“千子归宗侧不远”的“窣堵波”,与《长阿含经》之《阿?夷经》所称的多子塔,应为同一座石塔。
东晋法显译《大般涅槃经》卷上载:
一时,佛在毗耶离大林中重阁讲堂,与大比丘千二百五十人俱。尔时,世尊而与阿难,于晨朝时,着衣持钵,入城乞食,还归所止,食竟洗漱,收攝衣钵,告阿难言:“汝可取我尼师坛来,吾今当往波罗支提,入定思惟。”作此言已,即与阿难俱往彼处……世尊须臾,从定而觉,告阿难言:“此毗耶离,优陀延支提、瞿昙支提、庵罗支提、多子支提、娑罗支提、遮波罗支提,此等支提,甚可爱乐。”[8]
毗耶离即毗舍离,多子支提即多子塔,应即《阿?夷经》所言四石塔之西的多子塔。
《法显传》载:“(释迦牟尼佛)将般泥洹,与诸弟子出毗舍离城西门,回身右转,顾看毗舍离城,告诸弟子:‘是吾最后所行处。后人于此处起塔。城西北三里有塔,名放弓仗。”[9]又载:“后世尊成道,告诸弟子:‘是吾昔时放弓仗处,后人得知,于此处立塔,故以名焉。”[9]80
毗舍离城是毗舍离国的都城。放弓仗塔是多子塔的异名。从前引文知,摩揭陀国都城王舍城、毗舍离国都城毗舍离城皆有多子塔。又据吉迦夜、昙曜译《杂宝藏经》卷1《鹿女夫人缘》知,古代印度波罗奈国亦有多子塔[10],详见下节引文。已知多子塔有古庙式,用砖瓦土木石等材料建筑;还有石塔式,只用石头垒砌。这些多子塔皆为建筑实体,可睹可触,且长久矗立着。玄奘、法显笔下的多子塔,必为二位高僧既闻传言或据佛籍而知,又亲自目睹瞻仰礼拜后实录的,真实可信。总之,与贤劫千佛密切相关的多子塔必为塔式建筑体,多子塔的内外会有“多子(千佛)”形象及相关内容绘塑的美术作品;若无,则为单纯纪念性质的称名纪念塔。
二 贤劫千佛从莲花中诞生的诸说
佛教经论关于贤劫千佛诞生的本生说,可谓异说多端,兹择取与前述第197窟壁画内容密切相关的莲花、千子且具有故事情节的代表性二说,其内容大同小异。
《大唐西域记》卷7《吠舍厘国·五·千佛本生故事》载:
(释迦牟尼)佛告涅槃期侧有窣堵波,千子见父母处也。昔有仙人隐居岩谷,仲春之月,鼓濯清流,麀鹿随饮,感生女子,资貌过人,唯脚似鹿。仙人见已,收而养焉。其后命令取火,至余仙庐,足所履地,迹有莲花。仙人见已,深以奇之,令其绕庐,方乃得火。鹿女依命,得火而还。
时梵豫王畋猎见华,寻迹以求,悦其奇怪,同载而返。相师占言,当生千子。余妇闻之,莫不罔计。日月既满,生一莲花,花有千叶,叶坐一子。余妇诬罔,咸称不详,投殑伽河,随波泛滥。
乌耆延王下流游观,见黄云盖乘波而来,取以开视,乃有千子,乳养成立,有大力焉。恃有千子,拓境四方,兵威乘胜,将次此国。
时梵豫王闻之,甚怀震惧,兵力不敌,计无所出矣。是时鹿女心知其子,乃谓王曰:“今寇贼临境,上下离心。贱妾愚忠{1},能败强敌。”王未之信也,忧惧良深。鹿女乃升城楼,以待寇至。千子骑兵,围城已匝。鹿女告曰:“莫为逆事!我是汝母,汝是我子。”千子谓曰:“何言之谬!”鹿女按两乳,流注千岐,天性所感,咸入其口。于是卸甲归宗,释兵返族。两国交欢,百姓安乐{2}。
千子归宗侧不远有窣堵波,是如来经行旧迹,指告众曰:“昔吾于此归宗见亲。欲知千子,即贤劫千佛是也。”[7]586-597
释迦牟尼佛自述其“归宗见亲”之事,此千子即贤劫千佛。贤劫千佛是指过去拘留孙、拘那含牟尼、迦叶、释迦牟尼之四佛及贤劫中陆续出世的慈氏、师子焰乃至楼至等一千佛,而释迦牟尼既是过去佛又是现在佛,亦即贤劫佛。
《后汉录》失译者名《大方便佛报恩经》卷3《论议品第五》载:
此多先贤止住其中故,号圣游居山。其山有一仙人止住南窟,复有一仙住在北窟。二山中间有一泉水,其泉水边有一平台。
尔时南窟仙人在此石上,浣衣浣足已,便还所止。去后未久,有一雌鹿来饮泉水,次第到浣衣处,即饮是石上浣衣汁,饮此衣垢汁已,回头返顾,自舐小便处。尔时雌鹿寻便怀妊,月满产生。
鹿生产法,要还向本得胎处,即还水边,住本石上,悲鸣宛转,产生一女。尔时仙人闻此鹿悲鸣大唤。
尔时南窟仙人闻是鹿大悲鸣声,心生怜愍,即出往看,见此鹿产生一女。尔时母鹿宛转舐之,见仙人往,便舍而去。
尔时仙人见此女儿,形象端正,人相具足,见是事已,心生怜愍,即以草衣裹拭而还,采众妙果,随时将养,渐渐长大,年至十四。
其父爱念,常使宿火,令不断绝。忽于一日,心不谨慎,便使火灭。其父苦责数已,语其女言:“我长身以来,不曾使此火灭。汝今日云何令此火灭?北窟有火,汝可往取。”
尔时鹿女即随父教,往诣北窟,步步举足皆生莲华,随其踪迹,行伍次第,如似街陌。往至北窟,从彼仙人乞求少火。尔时仙人见此女福德,如是足下生于莲华,报言:“欲得火者,汝当右绕我窟,满足七匝。”行伍次第了了分明,随其举足,皆生莲华,绕七匝已。语其女言:“欲得火者,复当在此右边还归去者,当于汝火。”尔时鹿女为得火故,随教而去。
其女去后未久之间,波罗奈大王将诸大臣、百千万众,前后围绕,千乘万骑,入山游猎,驱逐群鹿。波罗奈王独乘名象,往到北窟仙人所,见其莲华绕窟行列。尔时大王心生欢喜,叹言:“善哉!善哉!大德神仙!大仙导师!福德巍巍,其事如是!”尔时仙人即白王言:“大王!当知此莲华者,非我所能。”王言:“”非大师者,是谁所为?”报言:“大王,是南窟生育一女,姿容端正,人相具足,世间难有。其女行时,随其足下皆生莲华。”王闻是语,即往南窟彼仙人,头面礼足。尔时仙人即出问讯:“大王,远涉途路,得无疲极?”尔时大王报仙人言:“闻君有女,欲求婚姻。”尔时仙人报大王言:“贫身有此一女,稚小无知,未有所识,少小已来住此深山,未闻人事,服食草果。王今云何乃求顾录?又此女者,畜生所生。”即以上事向王是说。王言:“虽尔无苦。”问其父言:“鹿女者,今在何许?”报言大王:“在此草窟。”尔时大王即入窟中,见其鹿女,心生欢喜,即以沐浴香汤,名衣上服、百宝璎珞庄严其身,乘大名象,百千导从,作倡伎乐,还归本国。尔时鹿女从生已来,未曾见如此大众,心惊怖惧。
尔时其父上高山头,遥望其女,目不暂舍,而作是念:“我今遥观我女,远去不现,当还本处。”悲号懊恼,流泪满目:“我生育此女未有所知,与我遠别。”复作是念:“我今住此,不应余转,何以故?若我女反顾后望不见我者,令女忧苦。”佇立良久,女去不现,竟不回顾。尔时其父心生恚恨,而作是言:“畜生所生,故不妄也。我小长养,今得成人,为王所念,而反孤弃。”即入窟中诵持咒术而咒其女:“王若遇汝薄者,皎然不论。若王以礼待接汝者,当令退没,不果所愿。”
尔时波罗奈王到宫殿已,拜为第一,名曰鹿女夫人。诸小国王、百官、群臣皆来朝贺。王见此已,心生欢喜。来久数日,便觉有娠。王自供养夫人,床卧饮食皆令细软。至满十月,望其生男,绍系国位。月满产生,生一莲华。仙人咒力令王嗔恚,而作是言:“畜生所生,故不妄也。”王即退其夫人职,其莲华者,使人遗弃。
其后数日,波罗奈王将诸臣入后园中,游戏观看,作倡伎乐,斗其象马,并诸力士。中有力士,踉■顛蹶,以脚蹴地,地有震动,动莲华池。其华池边有珊瑚,于珊瑚下有一莲华迸堕水中。其华红赤,有妙光明。王见此华,心生欢喜,问群臣言:“如此华者,未曾有也?”即使使者入池取之。其华具足五百叶,于一叶下有一男童,面首端正,形状妙好。尔时使者即前白王:“此莲华者,未曾有也。大王当知,其莲华具足五百叶,于一叶下有一童男。”王闻此语,心惊毛竖,慨叹所以,问使者言:“审实尔耶?此非是我鹿母夫人所生莲华也?”即问青衣:“鹿母夫人所生莲华者,遗弃何处?”答言:“埋此池边大珊瑚下。”王审实其事,知鹿母夫人所生。王自入宫,向鹿母夫人自责悔过,而作是言:“我实愚痴无智,不识贤良,横生恶贱,违逆夫人。”忏悔讫已,还复本位。
王大欢喜,召集群臣、诸小国王并诸婆罗门师,一切集会。抱五百太子,使诸相师占相吉凶。卦曰:“道德所归,国蒙其福。若在家者,四海顒顒,鬼神保之;若出家者,必断生死,超度欲流,超生死海,获得三通六明,具四道果。”王闻是语,遂增欢喜,即便宣令国土,选取五百乳母。
尔时鹿母夫人白大王言:“王莫耗扰国土召诸乳母。宫中自有五百夫人。诸夫人者,妒我生男。王今可以一太子与一夫人,令其乳哺,非其子耶?”王报夫人:“五百夫人常怀嫉妒,恼害鹿母。鹿母今者,欲令我鞭打杖策,摈出驱遣,夺其命者,不逆夫人。夫人今者云何于怨嫌中放舍?此事甚难及也。又复能开天地之恩,以其太子与诸夫人?”
尔时五百夫人心大欢喜:“鹿母夫人施我安隐快乐,云何复能以太子与我?”欢喜无量。尔时无量百千大众闻是事已,心生欢喜,皆发道心。
尔时大王报夫人言:“未曾有也!吾不及汝。”夫人言:“贪恚所生,皆由嫉妒。谏恶以忍,谏怒以顺。我从生已来,未曾与物诤。诸夫人者自生恼害。譬如有人夜行遇杌,便起贼想,或起恶鬼之想。寻时惊怖,四散驰走,或投高岩,咸覆水火,荆棘丛林伤坏身体。因妄想故,祸害如是。一切众生亦复如是,自生自死,如蚕处茧,如蛾赴灯,无驱驰者。一切众恶从妄想起,诸夫人亦复如是。我今不应与彼群愚,起诸诤讼。”五百夫人即前礼鹿母夫人,自谢悔过,奉事鹿母,如蒙贤圣,如母姊妹,所养太子,如生不异。
时五百太子年渐长大,一一太子力敌一千;邻国反叛不宾属者,自往伐之;不起四兵,国土安隐;天神欢喜,风调以时,人民丰壤炽盛。
时五百太子乘大名象,林野观看,游戏自恣,快乐难量;父母爱念,如护眼目。
尔时五百太子年渐长大,于后一时集一处,坐莲华池边,见其形容,水底影现。时诸太子共相谓言:“一切诸法,如幻如化,如梦所见,如水中形,体无真实。我等今者,亦复如是。虽复豪尊,处在深宫,五欲自恣,壮年美色不可久保;物成有败,人生有死,少壮不久,会当有老,饮食不节,会当有死,百年寿命,会当有死。”诸太子即忧愁不乐,不能饮食,即还宫殿,白父母言:“世界皆苦,无可乐者。父母今者,听我等出家。”王报太子:“生老病死,一切共有,汝何以独愁?”白父王言:“不能以死受生,劳我精神,周遍五道。”王不忍拒,即便听许。母报子言:“汝出家者,莫舍我远去,可于后园,其中清净,林木茂盛,四事供养,不令乏少。”
时诸太子即便出家,受其母请,住后园中。一一太子皆得辟支佛道,如是次第四百九十九太子皆得道果,往诣宫中,至父母前,报言父母:“出家利益,今已获得。”时诸比丘身升虚空,东踊西没,西踊东没,南踊北没,北踊南没;或作大身满虚空,复以一身作无量身;或身上出水,身下出火,身下出水,身上出火。为其父母作种种神变已,即便烧身,取般泥洹。时鹿母夫人收取身骨,于后园中即起四百九十九塔供养。最小太子过九十日已,亦得辟支佛道,亦为父母现大神变,现神变已,即取泥洹。尔时其母收取身骨,起塔供养。[11]
此说从莲花中诞生的太子数为五百,仅千之半;所立之塔是五百太子各为一座,其塔数为五百座,不是共为一塔;起塔供养者是其生母鹿母夫人,非他人或后人。“收取身骨,起塔供养”,说明这五百座塔是舍利塔。这些都与其他诸说相类相异,也没有说与贤劫千佛的关系。此类从莲花中诞生说,流传版本大同小异,可互参互证,显示出此类神话传说故事流传广而久,具有一定的泛化性,有增广有变异,则不专一。
元魏吉迦夜、昙曜译《杂宝藏经》卷1《莲华夫人缘》载:
过去久远无量世时,雪山边有一仙人,名提婆延,是婆罗门种。婆罗门法,不生男女,不得生天。此婆罗门,常石上行小便,有精气,流堕石宕。有一雌鹿,来舐小便处,即便有娠。日月满足,来诣仙人窟下,生一女子,华裹其身,从母胎出,端正姝妙。仙人知己女,便取畜养;渐渐长大,既能行来,脚踏地处,皆莲华出。婆罗门法,夜恒宿火。偶有一夜,火灭无有,走至他家,欲从乞火。他人见其迹迹有莲华,而便语言:“绕我舍七匝,我与汝火。”即绕七匝,得火还归。
值乌提延王游猎,见彼人舍有七重莲华,怪而问之:“尔舍所以有此莲华?”即答王言:“山中有梵志女来乞火,彼女足下生此莲华。”寻其脚迹到仙人所,王见是女端正殊妙,语仙人言:“与我此女。”即便与王,而语王言:“当生五百王子。”遂立为夫人,五百婇女最为上首。王大夫人,甚妒鹿女,而作是言:“王今爱重,若生五百子,倍为敬之。”
其后不久,生五百卵,盛著箧中。时大夫人,捉五百面段,以代卵处,即以此箧封盖记识,掷恒河中。王问夫人言:“为生何物?”答言:“纯生面段。”王言:“仙人妄语。”即下夫人职,更不见王。
时萨躭菩王,在于下流,与诸婇女,游戏河边。见此箧来,而作是言:“此箧属我。”诸婇女言:“王今取箧,我等当取箧中所有。”遣人取箧,五百夫人,各与一卵。卵自开敷,中有童子,面目端正,养育长大,各皆有大力士之力,竖五百力士幢。
乌提延王从萨躭菩王常索贡献。萨躭菩王闻索贡献,忧愁不乐。诸子白言:“何以愁恼?”王言:“今我处世,为他所凌{1}。”诸子问言:“为谁所凌{2}?”王言:“乌提延王而常随我,责索贡献。”诸子白言:“一切阎浮提王,欲索贡献,我等能使贡献于王。王何以故与他贡献?”五百力士遂将军众,伐乌提延王。乌提延王恐怖而言:“一力士尚不可当,何况五百力士?”便募国中能却此敌。又复思忆:“彼仙人者,或能解知。”作诸方便,往到仙人所,语仙人言:“国有大难,何由攘却?”答言:“有怨敌也。”王言:“萨躭菩王有五百力士,皆将军众,欲来伐我。我今乃至,无是力士,与彼作对。知何方计,得却彼敌?”仙人答言:“汝可还求莲华夫人,彼能却敌。”王言:“彼云何能却?”仙人答言:“此五百力士,皆是汝子,莲华夫人之所生也。汝大夫人,心怀憎嫉,掷彼莲华所生之子,著河水中。萨躭菩王于河水下头接得养育,使令长大。王今以莲华夫人乘大象上,著军阵前,彼自然当服。”即如仙人言,还来忏谢莲华夫人。共忏谢已,庄严夫人,著好衣服,乘大白象,著军阵前。五百力士举弓欲射,手自然直,不得屈申,生大惊愕。仙人飞来,于虚空中,语诸力士:“慎勿举手,莫生恶心,若生恶心,皆堕地狱。此王及夫人,汝之父母。”母即按乳,一乳作二百五十岐,皆入诸子口中。即向父母忏悔,自生惭愧,皆得辟支佛。二王亦自然开悟,亦得辟支佛。[12]
此则莲华夫人的故事,叙述了莲华夫人及其母与仙人的关系,一胎多卵出生的五百太子不是从莲花中出生的;莲华夫人退敌,母子相见相识与从莲花中诞生說大同也有小异,更未涉及贤劫千佛、多子塔。这则故事仅是一胎多子神话的异说。
《法显传》载:
(释迦牟尼)佛将般泥洹,与诸弟子出毗舍离城西门,回身右转,顾看毗舍离城,告诸弟子:“城之西三里有塔,名放弓仗(塔)。”以此名者——
恒水上流有一国王,王小夫人生一肉胎。大夫人妒之,言:“汝之生,不详之征。”即盛以木函,掷恒水中。下流有国王游观,见水上木函,开看,见千小儿端正殊特 ,王即取养之。遂便长大,甚勇健,所往征伐,无不摧伏。次欲伐父王本国,王大愁忧。小夫人问:“何故愁忧?”王曰:“彼国王有千子,勇健无比,欲来伐吾国,是以愁耳。”小夫人言:“王勿愁忧,但于城东作高楼,贼来时著我楼上,则我能却之。”王如其言。
至贼来时,小夫人于楼上语贼言:“汝是我子,何故作反逆事?”贼曰:“汝是何人,云是我母?”小夫人曰:“汝等若不信者,尽张口仰向。”小夫人即以两手構两乳,乳各作五百道,俱堕千子口中。贼知是其母,即放弓仗。二父于是思惟,皆得辟支佛。二辟支佛塔犹在。后世尊成道,告诸弟子:“是吾昔时放弓仗处,后人得知,于此处立塔,故以名焉。千小儿者,即贤劫千佛是也。”佛于放弓仗塔边舍寿。[9]79-80
郦道元《水经注》引此文,文字稍异。此说后人得知包括释迦牟尼佛在内的贤劫千佛往世为王太子时识母认亲,冰释敌意,放下弓仗。“后人得知”此事立塔纪念,名曰放弓仗塔,即千子塔。此说所记与玄奘《大唐西域记》所载都言明贤劫千佛与多子塔的关系,多子塔就是纪念贤劫千佛出生事的纪念塔。
后世,我国禅宗典籍多涉多子塔,今举其要者如下:
《大庄严论经》卷6载:
此塔(即多子塔)崩毁时,出大音声,喻如多子塔。佛往迦叶所,迦叶礼佛足:“是我婆伽婆{1},是我佛世尊。”佛告迦叶曰:“若非阿罗汉,而受汝礼者,头破作七分。我今因此塔,验佛语真实。”[13]
《五灯会元》卷1载:
世尊在灵山会上,拈花示众,是时众皆默然,唯迦叶尊者破颜为笑。世尊曰:“吾有正法眼藏,涅槃妙心,实相无相,微妙法门,不立文字,教外别传,付嘱摩诃迦叶。”世尊至多子塔前,命摩诃迦叶分座令坐,以僧伽梨围之,遂告曰:“吾以正法眼藏密传于汝,汝当护持。”[14]
《六祖大師法宝坛经序》载:
妙道虚玄,不可思议,妄言得旨,端可悟明。故世尊分座于多子塔前,拈花于灵山会上,似火与火,以心印心。[15]
《佛所行赞》卷4《大弟子出家品》载:
尔时有二生,迦叶族明灯,多闻身相俱,财盈妻极贤,厌舍而出家,志求解脱道,路由多子塔,忽遇释迦文……领解诸深法,成四无碍辩,大德普流闻,故名大迦叶。[16]
南宋晦翁悟明《联灯会要》卷1载,释迦牟尼佛曾于多子塔前分座,传法于迦叶。此为禅宗之说。另法显译《大般涅槃经》卷上,普济《五灯会元》卷1,睦庵《祖庭事苑》卷8等皆涉事多子塔。
从上引材料可知古印度曾有多座多子塔,分布多地,今已不存,难明其规制,仅知有石塔式、塔庙式。推测这些多子塔内外似乎没有绘塑的多子(千佛)图像。笔者孤陋寡闻,从未见到既是塔又绘塑多子(千佛)的多子塔。就莫高窟第197窟所谓的多子塔而言,只见子(千佛)不见塔,却定名“多子塔”,而“塔”是多子塔成立的先决条件,无塔则不能称之为塔。从佛教典籍看,多子塔名塔,似乎没有绘塑雕造子(千佛),设想既有塔又有子(千佛),可谓完美的多子塔了。可以肯定的一点是多子塔可以没有子(千佛)的,但绝不能没有塔,故我们认为第197窟断然不可定名为“多子塔”。
三 莫高窟第197窟的两铺贤劫
千佛诞生变
斯坦因1906—1908年中亚探险时,从莫高窟王园禄手中廉价骗购藏经洞(今第17窟)出土的大批敦煌遗书、绢帛纸画等。斯坦因将一部分入藏于印度新德里中亚古代博物馆(今印度新德里国立博物馆),其中有一幅纸本白描多子塔图(图3),画面内容是一座多层楼阁式的塔和众多结跏趺坐在有梗茎(仅见部分)的大莲花上的菩萨形千佛{1}。这些千佛大部分双手于胸前合掌,少数双手抚膝或一臂上举展掌,莲花座彼此间莲茎勾连。松本荣一先生认为:“是一件未完成的作品,但画面有几处描绘非常有特色,引人注目。图绘一六角形基坛,铺设华丽,上作一圆形塔,其间安放有四十七枝莲花,每一枝莲花上坐一菩萨形尊像。每朵莲花皆为长茎,其中半数相互联系并结成一根主干。此图制作年代应为唐末,尤其尊像的姿态具有中印度特色。图中可计数的尊像有四十七身,其背面尊像无法画出,假设背面有的话,尊像总数应超过九十,四十七应为一略数字,主要在于表现在众多莲花上配置尊像而形成一座塔形的旨趣。”并认为这幅图就是依据《大方便佛报恩经·论议品》《大唐西域记·吠舍厘国·千佛本生故事》等绘制的多子塔图[17]。
多子塔图的构图三大元素是“菩萨形尊像(千子)”“圆形塔”“每朵莲花皆为长茎”。长茎莲花把“子”与“塔”勾连为一体,千子皆坐在仰覆双层花瓣的大莲花上,表达了千子从莲花中诞生的本生因缘。半数莲花的长茎相互勾联,意在表达千子是一母所生的同胞关系。“塔”则是这一非凡之事的纪念性建筑体,故其名曰多子塔。而多子塔图则是佛教绘画作品,恐非佛教典籍所言地标性建筑多子塔的写实描摹,现实中可能并不存在。佛教典籍所载多子塔实体建筑今已不存,难言此图的多子塔与古印度史上的多子塔建筑体是否相同或相像。
相较而言,莫高窟第197窟两铺所谓“多子塔”的壁画(图1、2),仅有“多子塔图”三大元素的“多子(千佛)”和关联其出生的艺术构思出的虚拟“莲花树”,却未表现多子塔图所具有的独特特征的标识根本元素之一的“塔”,也就是说,只有“子”和“莲花”而无“塔”,反而定名为“多子塔”。称其为“塔”,实则无塔,如此定名失据,不免有空穴来风、捕风捉影之嫌了。既然理据不足,名实不符,那么“多子塔”之名自然也就不能成立了。
第197窟的这两铺所谓“多子塔”的壁画,画面中仅有“多子(千佛)”和一棵一干而多枝多花的大“莲花树”,是在表达多子是同根同宗一母多胎之子,表现了贤劫千佛从莲花中诞生的本生因缘,与“塔”并无丝毫关系,据学界约定俗成的定名规则,这两铺壁画应当定名为贤劫千佛诞生变。这是敦煌石窟壁画中的又一类贤劫千佛本生变,不同于此前判定的贤劫千佛本生变——贤劫千佛金瓶掣签决定出世次第的本生变,即《敦煌石窟内容总录》所称的“千佛变”,见于莫高窟第7、9、16、35、85、94、121、138、196、333、256窟者和榆林窟第12、16、36、38窟者。
类似于第197窟贤劫千佛从莲花中诞生的美术图像作品早已有之并流传,内容元素、构图布局与第197窟的贤劫千佛诞生变的意境十分相似。日僧觉禅《觉禅钞》“阿弥陀”条收录第1幅52身像图,俗称五通曼荼罗或叶上曼荼罗。此图描绘1棵大树,枝叶左右对称地层层伸展,叶片繁密茂盛,枝叶上结跏趺坐着52尊像(1身佛51身菩萨),其中1身绘在莲台上,位于上方中央(图4)。关于该图的流传,《觉禅钞》“阿弥陀”条载文:
见唐传记,有阿弥陀曼荼罗。
天竺鸡头摩寺有五通菩萨,现身往极乐向佛云:“娑婆世界众生念弥陀佛,无其所据云何?”佛言:“汝还娑婆,彼国可示现。”
于是菩萨还本寺,其寺树木叶上画佛菩萨像,采集此树叶之有五十二体佛菩萨。以之唐朝图绘人以为本尊。[17]{1}
唐传记所言“阿弥陀曼荼罗”就是“五通曼荼罗(叶上曼荼罗)”。松本荣一先生说:“由此可见,应五通菩萨所请,五十二尊佛菩萨现身于天竺鸡头摩寺大树枝叶上。经文所说唐传记恐怕就是道宣《集神州三宝感通录》,可知这类图例出现于中国的时期相当早。”[17]277
道宣《集神州三宝感通录》卷37载:
阿弥陀佛五十菩萨像者,西域天竺之瑞像也。相传云:
昔天竺鸡头摩寺五通菩萨,往安乐界请阿弥陀佛,娑婆众生愿生净土,无佛形象愿力莫由,请垂降许。佛言,汝且前去,寻当现彼。及菩萨还,其像已至,一佛五十菩萨各坐莲花在树叶上。菩萨取叶所在图写,流布远近。
汉明感梦,使往乞法,便获迦叶摩腾等至洛阳。后腾之姊子作沙门,持此瑞像方达此国,所在图之。未几,赉像西返,而此图传不甚流广。魏晋已来年载久远,又经灭法,经像湮除,此之瑞迹殆将不见。隋文开教,有沙门明宪,从高齐道长法师所得此一本,说其本起与传符焉,是以图写流布宇内。时有北齐画工曹仲达者,本曹国人,善于丹青,妙尽梵迹传模西瑞,京邑所推,故今寺正阳皆其真范。[18]
道世《法苑珠林》卷15《感应缘》之隋沙门慧海《隋五十菩萨瑞像》一文,与道宣《集神州三宝感通录》之“阿弥陀佛五十菩薩像”文字相同,只是在文末加双行小字注“右一验出西域传记”[19]。《集神州三宝感通录》所言“阿弥陀佛五十菩萨像者”,就是五通曼荼罗(叶上曼荼罗)。
敦煌莫高窟初唐第332窟主室东壁门南侧,《敦煌莫高窟内容总录》《敦煌石窟内容总录》条记项中所称的“五十菩萨图”亦即五通曼荼罗(今此窟开放供游人参观,为保护壁画安全装了隔离玻璃屏风,不便拍摄照片)。
我们于此所讨论的第197窟两铺壁画即属于此类美术图像的衍化派生作品,画面意涵随之而变。
日僧觉禅《觉禅钞》说“其寺树木叶上画佛菩萨像”。《觉禅钞》所载日本劝修寺本的鸡头摩寺五十二身像的“佛菩萨皆坐在树叶上”的,而我国道宣《集神州三宝感通录》说“一佛五十菩萨各坐莲花在树叶上”,而其句中的“各坐莲花”于此颇具佛学意涵。这一点就是由五通曼荼罗改造演变的贤劫千佛诞生变变通的关联点,也正是贤劫千佛从莲花中诞生的标识本质特征之一的关键点——从莲花中诞生。
我们把第197窟的两铺壁画(图1、2)与五通曼荼罗(图4)相比较,显而易见,二者的画面内容元素、构图布局极为相似,第197窟者是在五通曼荼罗的基础上稍作了些许变通改造——把莲花树造型改造得更加美观,又把叶上趺坐的佛菩萨改换作枝端莲花上趺坐的禅定佛(千佛)。如此改造之后,画面所表达的佛学意涵就大不相同了,第197窟者就成为一母多胎从莲花中诞生的贤劫千佛诞生变了。
明乎此,再看榆林窟第36窟后甬顶道称作“千佛图”“多子塔图”的壁画。
敦煌研究院编《中国石窟·安西榆林窟》之霍熙亮编《榆林窟、西千佛洞内容总录》载榆林窟第36窟:“主室甬道平顶五代画千佛图一铺。”[20]第36窟有前后甬道,前甬道“多经修抹无画”,此《内容总录》所指甬道,当为主室后甬道,言其壁画是“千佛图”。敦煌研究院编《敦煌石窟内容总录》失载,仅言“甬道平顶”[2]218,意谓无画,实则有画。张伯元著《安西榆林窟》载“甬道……顶……多子塔图一方”[21],此甬道当指后甬道。此铺壁画既非习见的千佛图(图5),更非多子塔图,而是金瓶掣签决定出世次第的贤劫千佛出世变[22]{1}。
四 莫高窟第169、351窟贤劫千佛诞生变
第169窟同样位置的主室西壁龛外两侧,也有相同内容元素,与第197窟大同小异结构布局的两铺壁画。第169窟亦在莫高窟南区,位于第197窟之南由下而上的第二层,坐西向东,是一个小型洞窟。
关于第169窟的始建年代,敦煌文物研究所整理《敦煌莫高窟内容总录》和敦煌研究院编《敦煌石窟内容总录》分别在其“修建年代”“时代”条目项中笼统言“唐代”,而在“内容”条目项中皆言“龛内西壁盛唐浮雕百花卷草火焰佛光,两侧露出盛唐画屏风各一扇”[1]68[2]66-67。具体而言,第169窟始建年代当为盛唐,之后不知何故大部分绘塑原作损毁,时至宋、清两代前后大规模地再绘塑妆修。于此讨论的就是今存宋代重修绘制的两铺壁画,其位置亦在主室西壁佛龛帐门南北两侧。
这两铺壁画,各以半团花纹饰带分隔为上下两个单元(图6、7)。
上部者,绿地,皆绘千佛横列三排,每排二身,结跏趺坐在仰覆两层的今呈或白色或黑色的大莲花上,皆着袒右袈裟,双手于胸前结定印;皆具今呈黑白灰三色的圆形头光、身光,顶悬今呈黑白两色的珠宝华盖;从禅定千佛趺坐的大莲花底部伸展出无枝叶的绿色长茎,顶端是今呈黑白二色的莲花花苞或半开的莲花花朵,遍布于千佛左右。
下部者,白地,各绘丛生高干的绿色花树,于此亦称之为莲花树,是佛教艺术创作的神性树。树干互生羽状绿叶,分节盛开今呈或白色或黑色的五瓣花朵,顶端是今呈或白色或黑色的待放花苞。花树挺拔直立,生机盎然。
帐门北侧者,画面最为清晰,稍有颜料层脱落而致画面残缺。帐门南侧者,颜料层多处脱落,不过画面形象基本能辨识,无碍内容的识读。综合上下两个单元的内容,有莲花上趺坐禅定千佛、莲花树及千佛左右的长茎莲苞和莲花,究其意趣皆与第197窟者相同,而其结构布局及莲花树造型却与第197窟者大不同。
由于这两铺壁画皆以半团花纹饰带分成上下独立的两个单元画面,故敦煌石窟考古工作前辈们即作如是观:《敦煌莫高窟内容总录》在窟室条记中称“帐门南、北侧上各画千佛,下花卉”[1]58;《敦煌石窟内容总录》沿袭前说,在其条记中说“龛外南、北侧上宋各画千佛,下花卉”[2]67,较前者指明为宋画。然而,张大千先生《漠高窟记》将第169窟编号为第295窟,并说“千佛,四壁”[3]596,谢稚柳先生《敦煌艺术叙录》则称“四壁 千佛”[4]392。既言“四壁”,当然包括西壁佛龛帐门南北两侧者。张、谢二位先生把西壁龛外两侧壁面视为一壁(西壁)而观,而且将其壁画内容仅称为“千佛”,没有特意指明其中的“花卉”,显然将下面单元的“花卉”视为与上面单元的千佛是一体的整铺千佛画。此视角、此观点与笔者不谋而合。
联系前述第197窟已拟名的贤劫千佛诞生变来考虑,笔者认为第169、197窟,二者构图元素完全一样,意涵亦同一,所表达的是同一个佛学义理题旨,即贤劫千佛是一母多胎而从莲花中诞生的本生故事。故可说第169窟者亦為贤劫千佛诞生变,只不过与第197窟者的结构布局有异,再有莲花树造型不同,故可认为盛唐第169窟宋代补绘者是中唐第197窟者的另一种版本的表达样式。如此认识,略陈管见如下:
其一,所谓“花卉”者,是各种花和草的总称。第169窟两铺壁画下部,不是一般能特指的某一种花或某一种草。画面中,只见直干有叶、类似芝麻直干分节开花、顶端有待放花苞,而直立高干密布互生羽状绿叶,不是扇状的荷花叶。节节盛开今呈或白色或黑色的五瓣单层花朵,花心都有柱状白色花蕊。花朵酷似少瓣单层莲花,花苞酷似待放莲苞。莲又称荷、芙蓉,其花称莲花、荷花、芙蓉花。莲是多年生草本植物,生在浅水中,地下茎肥大而有节,圆形扇状叶子高出水面,其花淡红色或白色,有香气,地下茎称藕。莲茎不会露出水面而直立的,地下茎生长出梗且显露于水面上,而其顶端孕育花苞,花苞开敷则为莲花,没有茎干直立于水面上分节开花的。显然,画面中的是虚拟似莲非莲而具神性的“花树”,是不同于第197窟者的另一种形态的“莲花树”,其旨趣亦寓意“千叶莲花”。
其二,笔者孤陋寡闻,才疏学浅,未见中外佛教美术作品中有此类的作品,故于此说,第197窟的中唐画师参酌隋代曹仲达描摹流行的五通曼荼罗和莫高窟唐第332窟的“五十菩萨图”,变通创作了贤劫千佛诞生变。但是,此时及其后敦煌佛教以致中国佛教广为尊崇大乘佛教,对于小乘佛教所尊崇的千佛信仰已经淡化,甚至把千佛作为装饰图案的构图元素。因此第197窟的贤劫千佛诞生变未能流行开,即现即灭。时过数百年而至宋代,又偶一为之于第169窟再绘贤劫千佛诞生变。宋代画师可能参酌先代中唐第197窟之作,再构思布局绘制了第169窟的贤劫千佛诞生变,但是一味过分地强化龛外帐门两侧的对称装饰性,从而于一铺画面中间平添了一条半团花的装饰带,又再构想造型出不伦不类的“莲花树”,似莲非莲。如此,误导观者一分为二地看待这两铺千佛变,故有“上千佛”“下花卉”之说。
其三,饶有趣味的是,上部千佛之间散布着许多长茎的含苞莲蕾和半开的莲花,而其长茎皆从千佛趺坐的大莲花下伸展出来,如此就把上下两单元的意境联系起来而为一体,即可解读为贤劫千佛从莲花中诞生的题旨了。
其四,第169窟的画师把“子(千佛)”和“千叶莲花”分处于上下两个独立的单元画面中,可能是为了加强佛龛帐门两侧庄严美观的对称效果,而在上下画面之间增加了半团花纹装饰带,是增加了屏风的对称美,也增强了稳定感,但是生硬地割裂了上下二图的同一题旨密切的关联性,不可分割的一体性,可谓画蛇添足的败笔了。
如此解读第169窟的这两铺壁画,“千叶莲花”和“千子(千佛)”两大主题元素及其千佛左右皆有二者密切关系的与第197窟者不无二致,稍有千佛造型和莲花树的造型之不同,构图布局之迥异,但是并没有使表达的主题思想发生根本性的颠覆,第169窟者仍可认为是贤劫千佛诞生变,只不过是不理想、不完美的生涩晦暗的另一种样式。
其五,第169窟主室其他三壁,宋代还绘制了大面积的横竖成行成排、密密麻麻的千佛(图8、9、10)。南、北、东三壁皆为绿地,千佛衣着、坐姿、手印、莲座等皆与西壁龛外两侧者一模一样。引人注意的是,这些千佛之间散布着有茎的莲蕾莲花,其茎皆从千佛趺坐的大莲花下伸展出来,彼此勾连。这些画面意趣皆与本窟及第197窟西壁龛外两侧者如出一辙,并无不同。第169窟四壁壁画总体结构布局是一致的。南、北、东三壁上部均为上述情景即千篇一律的千佛,下部皆有墙裙,其内绘壸门、供宝(今多已漫漶模糊)。佛龛所在的主体壁面西壁、龛内绘塑都无千佛或与千佛诞生事相关者,于此不作讨论。从全窟总体布局看,四壁是统一的,即上为千佛,下为装饰性的壸门、供宝等,西壁有神圣佛龛而为其主壁,龛外两侧的内容以屏风式绘出,既以对称规整之美庄严了佛龛,又给人以耳目一新之感,引人入胜。西壁为与其余三壁在布局结构上一致,画师在龛外两侧表达贤劫千佛从莲花中诞生事的画面中间平添了一条半团花纹的装饰带,此半团花亦即半个莲花,而莲花又与上下莲花联系起来了,此种机械式的装饰,实不可取。不过,话又说回来,这种装饰也不是一无是处,如此之装饰,形成的佛龛外两侧壁面的总体效果,犹如打开的殿堂大门平贴于两侧壁面。大门上如棂窗,下如门板,佛寺道观等大都如此。如此构图布局,倒使佛殿(龛)有了稳定感和庄严感,甚至具有了神秘感。在此意义上,第197窟者似乎有些死板。这一点也是笔者审视第169窟这两铺壁画的着眼点。
由第169、197窟佛龛外两侧的贤劫千佛从莲花中诞生变,再审视第169窟的东、南、北三壁大面积的千佛图,千佛周侧散布着有茎的莲蕾、莲花,而且花茎皆与千佛所坐的大莲花勾连(图11)。再联系经文鹿女“生一莲花,花有千叶,叶坐一子”,以及第169、197窟壁画表现此一佛学意涵的贤劫千佛诞生变中的莲花树、千佛,有理由认为此三壁的千佛图皆为同一个主题——贤劫千佛从莲花中诞生,是此种本生变由繁而简的表达,可以说是贤劫千佛诞生变的另一种样式。
这种千佛图大别于一般只单纯绘千佛而无周侧绘莲苞、莲花、莲茎从千佛所趺坐的大莲花底部伸展出的千佛图。这种“贤劫千佛,开碧莲而化现”{1}、“千佛分身,莲花捧足”{2}的图像与贤劫千佛一母多胎、从莲花中诞生的佛学意趣是相一致的,“诞生”“化现”是其宗旨,二者结合,既有“莲花捧足”之诞生,又有“开碧莲而化现”的出世,如此,这种千佛图像就有诞生面世和化现出世的双重佛学意涵了。《敦煌莫高窟内容总录》《敦煌石窟内容总录》以及张大千、谢稚柳等所称的“千佛”者,仅仅是泛称,似乎大家都忽视了图中的莲苞、莲花,特别是莲茎从千佛所趺坐的大莲花底部伸展出以致互相勾连图像的佛学意涵,没有关注这种图像的个性特征。第169窟的壁画就是表现贤劫千佛从莲花中诞生的题旨,因而我们说第169窟是一个贤劫千佛诞生窟。
由第169窟又推及第351窟。
第351窟位于莫高窟北区下层藏经洞(第17窟)南侧,五代开建,逮及西夏,敦煌僧众进行了大规模的修缮,再绘了大部分的壁画,再及至清代,道士王园禄和信众补塑了主室西壁平顶敞口内的佛、弟子、菩萨,于龛外北侧塑了乘象普贤菩萨、南侧塑乘狮文殊菩萨。
西夏时,于其龛外南北两侧壁画绘制了相同内容、相同布局结构的壁画:上部千佛,下部莲花树;又于龛沿下相对上部莲花树的位置,再绘一方与上方莲花树同样造型、布局的莲花树。《敦煌莫高窟内容总录》条记项中记:“龛外南、北侧各画千佛,下花卉。”“龛下画花卉。”[1]128《敦煌石窟内容总录》亦于条记项中记:“龛外南、北侧西夏各画千佛、下花卉。”“龛下西夏画花卉。”[2]143二内容总录所言“花卉”,亦即前文所拟称的“莲花树”。
第351窟西壁龛外两侧西夏所绘千佛、莲花树,一如前文所述第169窟宋代所绘者,特别是千佛左右也有从千佛所坐的大莲花下伸展出长茎莲花,合其上下画面所呈现的意境——佛学义理,我们也认为是从莲花中诞生的贤劫千佛诞生变。而第351窟与第169窟的画面不同之处在于:其一,龛两侧上千佛、下莲花树之间没有横隔画面的装饰带,上下合为一体;其二,第351窟又在龛沿下再绘一方造型、布局与上面完全相同的莲花树,凸显现了莲花树于此贤劫千佛诞生之根本——从莲花中诞生。表面看是重复,但从表达主题思想看,可认为是在强调。
第351窟南、北、东壁皆绘千佛,左右从千佛所坐莲花下伸展出长茎的莲花(图12、13、14),其所表达的佛学义理完全与第169窟南、北、东壁者一样,故我们认为第351窟南、北、东壁也是简约式的贤劫千佛诞生变。
结 语
本文所讨论的莫高窟第197窟主室西壁佛龛两侧的画面内容、构图布局完全相同的两铺壁画,不是多子塔图。今据《大唐西域记》卷7《吠舍厘国》之《千佛本生故事》、《大方便佛报恩经》卷3《论议品》和《杂宝藏经》卷1《莲华夫人缘》等,判定其为贤劫千佛从莲花中出生的贤劫千佛诞生变;由此推及莫高窟第169窟主室西壁佛龛两侧者亦为贤劫千佛诞生变,是此种本生变的另一种样式;再由此推定第169窟南、北、东三壁壁画为简化式贤劫千佛诞生变。由第169窟又推及莫高窟第351窟主室西壁佛龛两侧者亦为贤劫千佛诞生变,而南、北、东壁亦为简约式贤劫千佛诞生变。
如此,敦煌石窟壁画有三种样式的贤劫诞生变:生动形象精致者,第197窟;差强人意者,第169、351窟佛龛两侧;上两种的简化形式者,第169、351窟主室南、北、东壁。目前,从贤劫千佛本生变的内容言,可分为两种:一种即本文所讨论者——贤劫千佛从莲花中诞生的本生变,其样式有三种;另一种即早年笔者所判定者——贤劫千佛金瓶掣签决定出世次第的本生变{1},其样式有八种[22]。
千佛,是泛称。具体而言,千佛有过去世庄严劫千佛、现在世贤劫千佛、未来世星宿劫千佛,故有“三世三千佛”“三千佛”之说。而今所论者仅是贤劫千佛本生因缘事,为有别于过去世庄严劫千佛、未来世星宿劫千佛,故应确切地称之为贤劫千佛诞生变、贤劫千佛出世变。
敦煌石窟的贤劫诞生变,始于莫高窟中唐(第197窟),中间经宋代(第169窟),终于西夏第351窟;贤劫千佛次第出世变,始于莫高窟晚唐第9、85、138、196窟,历经五代第12、16、38、121窟,終于宋代第7、16、35、233、256窟和榆林窟第12、16、36、38窟,前后历时约200年。贤劫千佛诞生变,窟数、铺数虽少,可谓寥若晨星,吉光片羽,但还是有佛学、佛教美术史等些许研究价值的,亦可谓敦煌石窟壁画浩如烟海中闪光的火星。至少可以说,贤劫千佛诞生变是敦煌石窟壁画的一个内容和一种样式。
参考文献:
[1]敦煌文物研究所. 敦煌莫高窟内容总录[M]. 北京:文物出版社,1982:67.
[2]敦煌研究院. 敦煌石窟内容总录[M]. 北京:文物出版社,1996:77.
[3]张大千. 漠高窟记[M]. 台北:台湾故宫博物院,1985:596.
[4]谢稚柳. 敦煌艺术叙录[M].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392.
[5]辟支佛因缘论:卷下[G]//大正藏:第32册. 东京:大正一切经刊行会,1925:477.
[6]佛陀耶舍,竺佛念,译. 阿?夷经[M]//长阿含经:卷11. 中国佛教文化研究所,点校. 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1994:187.
[7]季羡林,等. 大唐西域记校注:卷7:吠舍离国:千佛本生故事[M]. 北京:中华书局,2000:594.
[8]法显,译.大般涅槃经:卷上[G]//大正藏:第1册. 东京:大正一切经刊行会,1925:191.
[9]法显. 法显传校注[M]. 章巽,校注. 北京:中华书局,2008:79.
[10]吉迦夜,昙曜,译. 杂宝藏经:卷1:鹿女夫人缘[G]//大正藏:第4册. 东京:大正一切经刊行会,1925:447.
[11]大方便佛报恩经:卷3:论议品第五[G]//大正藏:第32册. 东京:大正一切经刊行会,1925:138-140.
[12]吉迦夜,昙曜,译. 杂宝藏经:卷1:莲华夫人缘[G]//大正藏:第4册. 东京:大正一切经刊行会,1925:451-452.
[13]马鸣. 大庄严论经:卷6[G]//鸠摩罗什,译. 大正藏:第4册. 东京:大正一切经刊行会,1925:287.
[14]普济. 五灯会元:卷1[G]//新纂卍续藏:第80册. 东京:株式会社国书刊行会,1975-1989:31.
[15]宗宝. 六祖大师法宝坛经序[G]//大正藏:第48册. 东京:大正一切经刊行会,1925:345.
[16]马鸣. 佛所行赞:卷4:大弟子出家品[G]//昙无谶,译. 大正藏:第4册. 东京:大正一切经刊行会,1925:433.
[17]松本荣一. 敦煌画研究:上册[M]. 林保尧,赵声良,李梅,译. 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00:276.
[18]道宣. 集神州三宝感通录:卷中[G]//大正藏:第52册. 东京:大正一切经刊行会,1925:421.
[19]道世. 法苑珠林:卷5:感应缘[M].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125.
[20]霍熙亮. 榆林窟、西千佛洞内容总录[M]//敦煌研究院. 中国石窟:安西榆林窟. 北京:文物出版社,东京:株式会社平凡社,1997:262.
[21]张伯元. 安西榆林窟[M]. 成都:四川教育出版社,1996:164.
[22]梁尉英. 敦煌石窟千佛变相[C]//敦煌研究院. 1994年敦煌学国际研讨会文集:石窟考古卷. 兰州:甘肃民族出版社,2000:26-5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