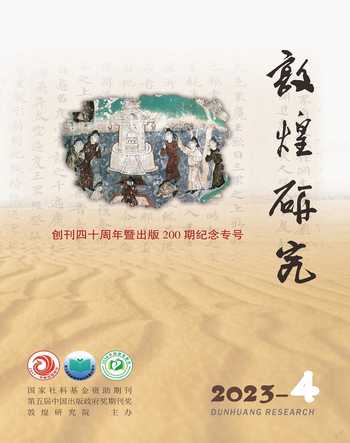犍陀罗美术中的阿弥陀信仰
2023-09-28宫治昭/著根敦阿斯尔/译
宫治昭/著 根敦阿斯尔/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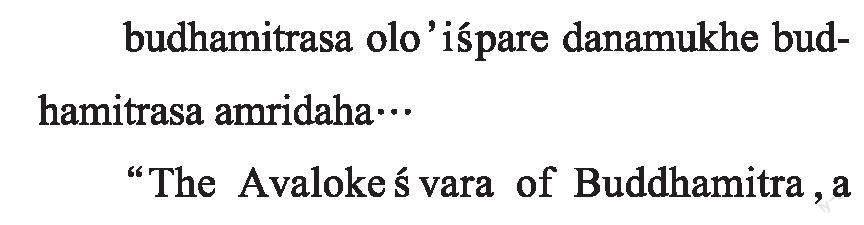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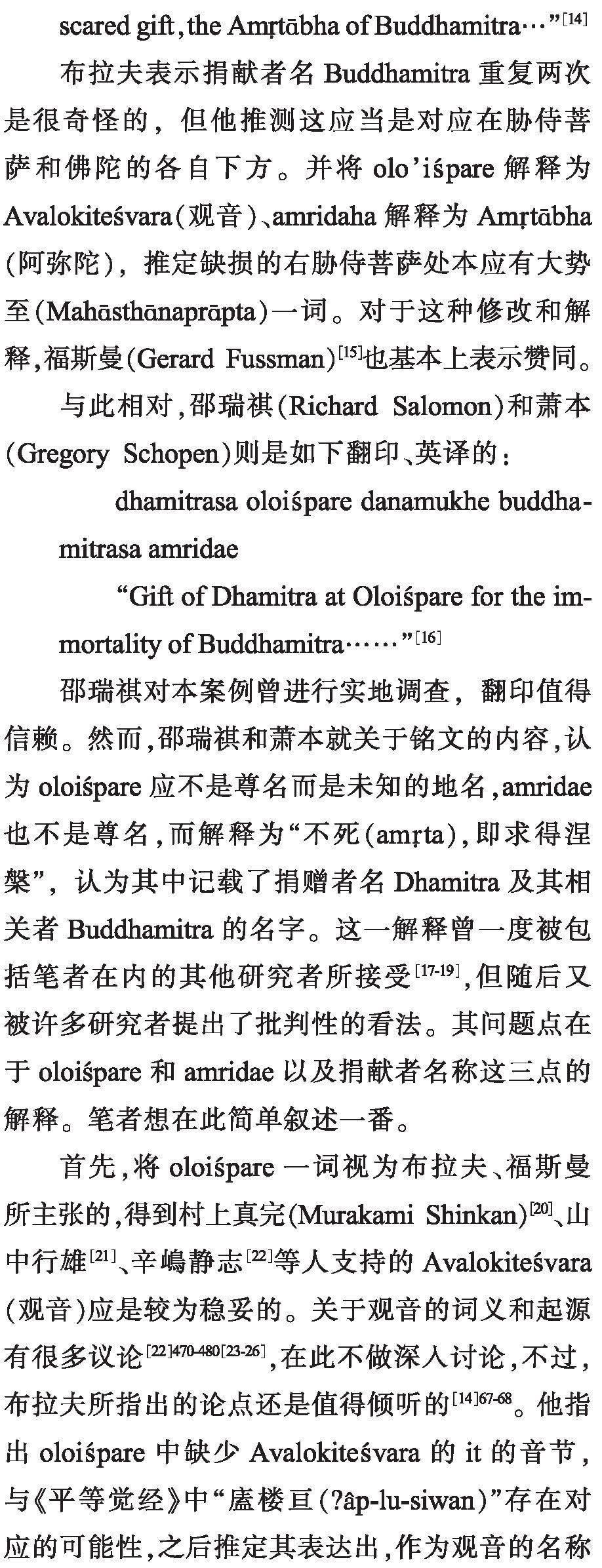
内容摘要:概观犍陀罗美术与大乘佛教,费切尔列举的“舍卫城神变”场景中的8件犍陀罗雕像,与初期主要的大乘经典《大品般若经》《法华经》《华严经》《无量寿经》等中所说佛陀的“大光明(放光)神变”关系颇深。通过详细考察犍陀罗阿弥陀三尊像和犍陀罗莲花型大构图雕塑,阿弥陀佛信仰的源流可以追溯至犍陀罗时期,阿弥陀佛五十菩萨图的祖型可能是犍陀罗的莲池型与笈多王朝的“舍卫城神变”图像在中亚融合后形成的。
关键词:犍陀罗美术;大乘佛教;阿弥陀佛信仰;东亚传播
中图分类号:J196.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4106(2023)04-0036-22
Amitabha Faith in Gandharan Art
MIYAJI Akira1 Trans., GENDUN Asier2
(1. Nagoya University, Nagoya 464-8601, Japan; 2. Center of Buddhist Studies, Dunhuang Academy, Dunhuang 736200, Gansu)
Abstract:A general review of Gandharan art and Mahayana Buddhism indicates that the eight Gandharan sculptures in the scenes of“Miracles at Sravasti” listed by Alfred Foucher are closely related to the event known as the“Maha-Pratiharya miracle” performed by the Buddha and mentioned in the main scriptures of early Mahayana Buddhism, including Pancavimsati-sahasrika-prajnaparamita, the Lotus Sutra, the Garland Sutra, and the Aparimitayur-sutra. By carefully examining sculptures of the“Three Holy Ones of Amitabha in Gandhara” and“large-scale Gandharan sculpture in the form of a lotus,”the author concludes that faith in Amitabha can be traced back to Gandharan civilization, while the Buddhist theme of “Amitabha Buddha and Fifty Bodhisattvas” was likely formed after the lotus motif of Gandharan art and images of the“Miracles at Sravasti” from the Gupta dynasty had disseminated throughout Central Asia.
Keywords:Gandharan art; Mahayana Buddhism; faith in Amitabha; religious dissemination in East Asia
(Translated by WANG Pingxian)
前 言
筆者意在从与大乘佛教起源相关的犍陀罗佛教的重要性谈起,尝试探寻犍陀罗美术中阿弥陀信仰的面貌。
对中国、朝鲜半岛、日本起到巨大影响的大乘佛教,是何时何地、如何兴起的,这一“大乘佛教起源”的问题,多年以来一直为佛教学者所关心,近年来也有多个研究成果得以发表{1}。佛教学者的主要研究对象自然是佛教文献,尤其是作为印度佛教原典的梵文经典(梵本)最为人所重视。佛教曾在印度消亡,而成批的梵文抄本,我们只知道它们不是出土发现的,就是于尼泊尔传承下来的{2}。前者中知名的是,在巴基斯坦北部吉尔吉特近郊的佛塔遗址中发现的所谓吉尔吉特抄本,除部派所传的经律外,以《一万八千颂般若经》《法华经》《药师经》等大乘经典(抄写于6—7世纪左右)而闻名。而后者中虽有以《无量寿经》为代表的大量大乘经典,但它们被认为基本是在12世纪以后书写的。
在这一状况下,1996年以后,在阿富汗巴米扬、哈达、巴基斯坦的巴焦尔等地出土了大量的佛教抄本,让全世界的佛教学者都为之震惊。目前,已有多个国际性项目在进行解读和研究工作。这些抄本研究的成果,不论是对于犍陀罗美术的研究而言,还是对佛教东亚传播问题的研究而言,都将因此而大放光彩。
新近在广域犍陀罗地区(阿富汗东南部、巴基斯坦北部)出土的佛教抄本比人们以往所知的抄本更古老,令人吃惊的是,其中还包含犍陀罗语、佉卢文(1—4世纪左右)所写成的《八千颂般若经》《阿閦佛国经》《贤劫经》等大乘经典。另外,与部派所传的经律一起报告存在的还有由笈多王朝婆罗迷文写成的《法华经》《无量寿经》等大量的大乘经典(6—7世纪)[1-4]。
这一发现必然也与犍陀罗美术的繁荣交相呼应。公元前3世纪的阿育王时代,佛教传入印度次大陆西北部的犍陀罗地区,还创设了大卒婆塔(塔克西拉的达摩拉吉卡大佛塔、斯瓦特的布特卡拉大佛塔),此后至9世纪左右,佛教虽几经盛衰,但终迎来繁荣。卒婆塔(佛塔)、祠堂(供奉佛像、小型佛塔、圣遗物)以及僧院(也包括有僧房、讲堂、冥想室、食堂、仓库等)组成的许多寺院遗址、出土的雕刻都能说明这一繁荣。自1979年前苏联军队入侵阿富汗以来,在长期政局不安的情况下,非正规的发掘横行,市场上出现的雕刻品数量甚至超过考古发掘出土的数量。事实上佛教抄本的发现、出现也出自同一背景。
总而言之,为了厘清印度佛教的实际状态,在文献学中抄本的研究是极其重要的。从佛教遗址中发现的“抄本”可以说是考古学意义上的遗物,与同样是考古学出土物的碑铭、雕刻、绘画等一同,都必然是“活的”时代遗产。为了阐明已经消亡的佛教的实际状态,通过佛教文献学、写本学、碑铭学、考古学、美术史学等跨学科、综合性的研究,有望取得巨大的进展。
本文以犍陀罗大乘佛教为中心,从美术史学的立场出发,特别是在阿弥陀信仰的面貌上,笔者虽见解有限,但仍想试论一番。佛教兴起于公元纪年前后,那一时期的印度次大陆,特别是从西北印度至北印度间,曾是大动荡的时代。公元前326年亚历山大大帝东征后,继承其东征成果的是塞琉古王朝,以及兴都库什山脉以南孔雀王朝的统治,紧接着是希腊·巴克特里亚王国独立,自南而下成立印希王国(公元前2—前1世纪中叶),更有中亚游牧民族塞迦族,印度帕西亚族的入侵,再有强大的马背民族贵霜帝国(公元1—3世纪中叶)的统治与繁荣,之后是萨珊波斯的入侵(贵霜·萨珊王朝),匈人(寄多罗,嚈哒)、突厥的支配,直到9世纪为止,西北印度的历史一直处于连绵不绝的异族统治之下。
在这样动荡的时代,虽然没有留下人们生活状态的相关记录,但正如大乘经典中法灭句“如来灭后五百岁,正法欲灭时”所说的那样,释尊已然是遥远的存在,能明显窥探到其中正法灭亡的危机意识。在这种危机意识的背景下,一定包含着上述连续不断的异民族入侵的历史现实。但是另一方面,也不难想象,如贵霜王朝时代那般,在国家强大稳定的支配权下,通过与帝政时代罗马世界的交易带来了经济上的繁荣,得力于皈依佛教的富裕的王侯、贵族、商人们的供养,也不难想象佛教的大为昌盛了。留存在西北印度的众多佛教遗迹即表明了这一点。
在思索着这一点的同时,笔者将首先概观“犍陀罗美术与大乘佛教”,并详细考察犍陀罗阿弥陀三尊像和犍陀罗莲花型大构图雕塑。最后,作为结语,笔者将阐述从美术中所观察的犍陀罗阿弥陀信仰的特征及有关其东亚传播的问题。
一 犍陀罗美术与大乘佛教
犍陀罗美术几乎都为石塑和泥塑,也存有少数金铜像、壁画,从主题上看,大致分为佛传图(包含本生图)、佛菩萨像、守护神像、捐赠者(供养者)像、装饰类等。这些雕塑大多安装于卒婆塔(主塔或奉献塔)的基座或圆筒部等处,但也有为数不少的大型佛、菩萨、守护神、捐赠者等雕像被安置于祠堂内。在这些主题中,佛传图占绝大多数,其使用数量达130以上(未比定的说话图也所占不少)。
在这些雕像中,佛传美术无论在部派还是大乘中都有造像,因而很难将两者区分开来。与大乘佛教相关的造像中,首先是能识别出佛、菩萨像的,但只要没有尊像铭和特别的特征,就很难确定它们是部派佛教的释迦佛、悉达菩萨、弥勒菩萨,还是大乘的佛陀(阿弥陀佛、阿閦佛、毗卢舍那佛等)和菩萨(观音、文殊、普贤等)。在这种情况下,犍陀罗美术中有一组浮雕雕刻,学者认为表现出了大乘佛教的主题。这就是曾为犍陀罗美术研究奠定基础的费切尔(Foucher)所解释为佛传说话之一的“舍卫城神变”的场景。他对印度的“舍卫城神变”图进行了广泛考察,其中列举了8件犍陀罗雕塑。现在强有力的见解是,将这些雕塑不视作佛传,而视其表达出了关于大乘佛教的主题{1}。然而,关于其表达的内容还是有很多讨论,仍旧有许多不明确的地方{2}。本文将重新审视笔者之前的论文{3},进一步重新深入研究。自费切尔的论述与考察以来,与这一部分石板雕刻相似的例子也广为人知[5-8],虽然丰富多变,但从图像形式来看大致可分为A. 三尊型、B. 发出型、C. 楼阁型、D. 莲池型四种[7]246-247[8]146-152。
A. 三尊型是以在莲花座上结跏趺坐、结转法轮印的佛陀为中心,两侧有不同图像的胁侍菩萨,一方为束发、髻型的梵天—婆罗门型,另一方为头巾冠饰的帝释天—刹帝利型(图1、2)。
B. 发出型是佛或菩萨结跏趺坐于莲花座,结禅定印,左右放射状的立像化佛或印度教众神(图3)。A、B型部分的石版雕刻的高度大多是在数十厘米到1米以内。与之相对,C、D型的高度超过了1米,图像也由于更为复杂而转为了大构图。
C. 楼阁型是佛陀坐在楼阁建筑内的莲花座上,结转法轮印,胁侍菩萨配于两侧柱子间,上方表现天人赞叹,以及众多佛、菩萨的坐像。更上层则表现的是佛塔以及佛传与授记的场景(图4、5)。
D. 莲池型下端以莲池和坐在莲花座上结转法轮印的佛陀为中心,两侧有众多形态各异的菩萨,佛陀头顶可观察到有花树和手持伞盖的天人(图6、7、8)。
4种类型虽各有不同,但在图像构成和圖像主题之间相互具有密切关系,主要表现为:主尊佛陀在莲花座上结跏趺坐,结转法轮印(但B为禅定印),以佛陀和两侧胁侍菩萨组成的三尊形式为基本构图(A、C),多见菩萨像,也有小佛陀和小菩萨的坐像等。笔者推测,这一组犍陀罗雕刻,与初期主要的大乘经典《大品般若经》《法华经》《华严经》《无量寿经》等中所说佛陀的“大光明(放光)神变”关系颇深,从中可一探大乘的佛身观、菩萨观、世界观所表现相关的内容。关于这一问题,在笔者的另一文章中有所解释{1},本文中则对A三尊型中与阿弥陀信仰有关的例子,以及D莲池型展开研究,并适当提及与其相关的其他类型。
二 犍陀罗的阿弥陀三尊像
刻文中有一处被认定为阿弥陀三尊像(但缺少右胁侍菩萨)的犍陀罗的例子,对此展开分析,就先要对三尊型进行说明。与大乘佛教相关的4种类型的图象中,三尊型例子较多(40例左右)[7]278-279,为基本类型。在犍陀罗,佛传美术广受人们欢迎,虽有众多释尊说法的场景,但在佛传场景中,未见到坐于莲花座上、手结转法轮印(胸前收拢左手指,右手握于其上的印){2}的姿态。坐于莲花座[8]81-83[9-12],结成转法轮印的姿态,恐怕与大乘的佛身观有关,释尊所说佛法即使入灭后,虽无形仍会以法身永存。法身在这个世界上作为应身而显现化,表相为向人们进行全新(大乘的)说法的姿态。
佛陀两侧有:(1)手拿水瓶,束发或结发髻的梵天、婆罗门型菩萨;(2)手拿花彩或莲花、戴头巾冠饰的帝释天、刹帝利型的菩萨作为两侧胁侍,构成佛三尊像。虽然两胁侍的左右位置不固定,但可以认为,(1)的菩萨是上求菩提、自利的实践,(2)中的菩萨是下化众生、利他的实践。这一大乘菩萨的基本实践与性质作为图像,被象征性地表现出来[7]263-269[13]。揭示主尊佛陀的(大乘)说法是通过菩萨的两种补充性实践来实现的。犍陀罗的三尊型几乎无一例外地具有这样的特征。
接下来,引起人们关注的阿弥陀三尊像出土地点不明,1961年塔克西亚(巴基斯坦)的私人收藏,现在则是佛罗里达州立约翰与梅波林林艺术博物馆的藏品(图9)。主尊佛陀在莲花座上结跏趺坐,披僧伽梨,偏袒右肩,胸前結转法轮印,其背后为头光和身光。左胁侍坐在台座上,左脚低踩在莲台上,右脚放在左膝上,右手食指指于额头呈思索状;左手下垂,手持莲花,头戴头巾冠饰{1};头上为伞盖,两端垂下华鬘。右胁侍菩萨以及佛陀的头上虽然有所缺损,但大概曾雕刻着花树,可能是假想为花树一部分的两朵大花(从花芯垂下华鬘)。
在朝向我们右边,佛陀所坐的莲花座旁,雕刻着合掌而坐的小比丘,应是后述刻文中记载的捐献者之一。正如在其他例子中所看到的那般,当初在与这个比丘呈对称状的位置一定还表现了另一位捐赠者。有关该雕刻的创作年代,最初介绍并研究本作品的布拉夫(John Brough)曾指出是2世纪左右,但与其他多个三尊型的雕刻样式相比较之后,推测其为3世纪左右。
本作品是三尊型中几乎共通的造型,引人注目的是刻在台座上的佉卢文字、犍陀罗语的铭文。布拉夫以基佛(Ch.Kieffer)在当地所得到的一张照片为基础,解读并研究了刻在台座上的铭文。他的翻印与英译如下:
最后,关于刻文中所记载的捐赠者名,布拉夫和福斯曼推测第一处dhamitra和第二处出现的buddhamitra为同一人,第一处缺失了bu。然而,尽管dhamitra这个名字听着生疏,定方晟在将平山郁夫丝绸之路美术馆所藏,单独的半跏思惟菩萨像(图2)中莲台上所刻的佉卢铭文,翻印并解读为“dhamitrassa navakar(mika?)”后,指出了其与阿弥陀三尊像的捐赠者Dhamitra为同一人物的可能性[29]。Navakarmika一词虽仍有不明确的部分,但作为建筑监督者之意的词,其可能想表达为达米特拉的作品(navakarma)的意思。
这尊阿弥陀三尊像正如布拉夫[14]67、村上[20]130、辛嶋[22]478指出的那样,从右向左读刻在台座上的佉卢铭文,与之相对应,观音像和阿弥陀像下面则刻着尊名。因此,比较稳妥的方式应是将铭文理解为“达米特拉捐献的观音、布达米特拉(捐献)的阿弥陀”。作为捐献者,记载了达米特拉和布达米特拉两名,在缺损的胁侍菩萨下面,则刻着“……寄进的大势至”。然而,一般认为在阿弥陀佛所坐的莲花座两侧,每尊旁只配有两名捐赠者,因此三名捐献者呈现为两名。平山郁夫丝绸之路美术馆所藏的半跏思惟菩萨像的台座两侧,表现着一对男女在家捐赠者像,如果达米特拉是其中的男性捐献者(朝向右方)的话,在阿弥陀三尊像中看到的合掌比丘则是布达米特拉了。
本像是三尊型的作品中,唯一刻有尊名的阿弥陀三尊像,十分珍贵。笔者在此试图考虑一番阿弥陀三尊中两侧胁侍菩萨的样子。由观音和势至来担任阿弥陀佛的两胁侍,其基础在于《初期无量寿经》(《阿弥陀三耶三佛萨楼佛檀过度人道经》,以下称《大阿弥陀经》)、《无量清净平等觉经》(以下称《平等觉经》)中记载,“此二菩萨(盖楼亘和摩诃那钵)常侍奉于阿弥陀佛左右”[30],《无量寿经》中也记载这两位(观世音、大势至)最为尊贵[31][33]273b。引人注目的是,本阿弥陀三尊中,观音被刻画为左手持莲花、右手触额头的半跏思惟形的姿态。这是因为,在犍陀罗中独尊的半跏思惟像有20多例为人所知,而其中多数被推定为左手执花纲或莲花的观音菩萨,这与本像的刻文相一致[32]。
另一方面,与半跏思惟形的观音相对,有所缺损的势至又是以何种姿态呈现的。作为佛三尊像中,配有半跏思惟形胁侍菩萨的相似例子,有白沙瓦博物馆收藏的三尊型实例(图10)和加尔各答印度博物馆所藏楼阁型中的三尊像(图4){1}。这两个实例中的菩萨像在持物和印相上同样有所缺损,也有部分不明确的地方,但戴头巾冠饰、左手持花彩、左脚下踩的半跏倚坐像和把头发梳成圆髻、左手持水瓶的交脚倚坐像形成一对,那么阿弥陀三尊像中的势至菩萨则也一定是手持水瓶的梵天型形象{2}。
日后在东亚,作为阿弥陀三尊像的两侧胁侍,在头前附有化佛的观音菩萨和附有宝瓶(水瓶)的势至菩萨逐渐定型化,而这种观音和势至的形象出自《观无量寿经》(以下简称《观经》),其中观世音菩萨为“顶上毗楞伽摩尼妙宝,以为天冠。其天冠中有一立化佛”,势至菩萨为“顶上肉髻如钵头摩花,于肉髻上有一宝瓶”[33]。三尊型的两菩萨中,戴头巾冠饰的帝释天型和束发结髻的梵天型呈一对,这与《观经》所说的观音头戴天冠、势至头有肉髻正相吻合,也可以将其考虑为犍陀罗美术的传承被引入了《观经》之中。另外,观音头有化佛的例子,在犍陀罗的头巾冠饰型菩萨像中也有表现,有可能就是观音(但是在《观经》中为立化佛,在实例中几乎都是坐化佛)。然而,以笔者拙见,不论是在犍陀罗还是印度内部,都不曾见到将水瓶附在肉髻上的例子。大概《观经》的编撰者们是在梵天型菩萨手持水瓶的基础上,为对应于观音天冠中的化佛,创造了势至的肉髻上附有水瓶的内容。
颇为有趣的是,这一记载,出现于劝人往生阿弥陀佛国观想的十三观,“(第十)观音观”和“(第十一)势至观”上,并且在“(第八)像观”中明确表示,阿弥陀佛及其左右的观音和势至,分别坐于莲花座上。而观想实践的意象富于变幻,喜左右相对称,因此可以看出,以犍陀罗美术的传承为基础,在经典编纂时发生了改变。关于《观经》的成书虽有很多议论,但从美术史学的见解来看,可以推测《观经》是在中国新疆吐鲁番周边编纂的{3}。在印度则没有《观经》流传的痕迹。
以上,笔者分析了台座上留有刻文的阿弥陀三尊像及其相关问题。犍陀罗中,明确的阿弥陀佛和阿弥陀三尊像几乎不明,正因如此,可以称其为极其重要之作,但包括刻文的解释在内,笔者还希望今后从各种各样的观点展开详细的探讨。在三尊型中,除了本像以外,也不能否定作为阿弥陀三尊而造像的例子存在的可能性,但是正如笔者另一文章中所论述的那样[13],犍陀罗三尊型的主尊佛陀,基本可以认为,将作为以大乘佛身观为基础的应身佛的释迦佛,视作被转用为报身佛的阿弥陀佛是比较妥当的。
三 犍陀罗莲池型的大构图雕刻
在与犍陀罗大乘佛教相关的4种雕刻中,关于采用大构图的莲池类型表现了怎样的内容,学者们提出了很多见解。就一直以来的见解而言,有罗森福(John Max Rosenfield)的“佛陀的神之显現”[34],宫治昭的“佛陀的大光明神变”[35],福斯曼的“一般性的佛国土”[15],李柱亨(Rhi,Juhyung)的“超越性的佛陀的壮丽显现”等[10][37]。另一方面,源丰宗很早即指出,莲池型的雕刻可能与阿弥陀信仰有关这一见解[37],此后亨廷顿(John C.Huntington)[38]、夸利奥蒂(Anna Maria)[39]、哈里森(Paul Harrison)和卢扎尼兹(Christian Luczanits)[8]、壬生泰纪[40]等人也有所提及。特别是哈里森和卢扎尼兹的大部分论考,从文献学和美术史学两方面进行的详细分析,极富启发性,但也如两者所承认的那样,尚未得出充分的结论。在此,笔者在这些先行研究的基础上,在分析备受好评之处和问题所在的同时,披沥个人之见。
一直以来,作为莲池型的代表作,学者们主要以(1)穆罕穆德·纳里出土的大石板雕刻(图6)这一著名实例为中心进行了讨论。在本文中,首先举出与该例呈现大致相同图象的(2)萨尔依·巴赫洛出土(图7)的实例进行讨论。之后,笔者想通过分析(3)穆罕穆德·纳里(?)出土(图8)的例子,其在中央区表示莲池型的图像,在上下的区域则表示其它的图像,以明确这些莲池型的图像内容。想必那时,再通过基于《初期无量寿经》(《大阿弥陀经》《平等觉经》)所探讨出的内容,将浮现出与单一的阿弥陀净土图所不同的面貌。另一方面,也存在可以通过《无量寿经》来解释的部分,需要将两者都纳入视野,进行综合分析。
1. 莲池型的基本构成
高浮雕的石板雕刻的下端表现为莲池,从那里的水流、鱼、莲、莲花中,可以看到露出上半身的莲花化生的人物等。沿着莲池中央伸展出装点着宝石的粗茎,出现一朵大莲花,许许多多花瓣的形状饱满而自然。粗茎两侧是精灵般的神,男女成对地从莲池露出上半身〔(1)中可以看到带龙盖的纳加和纳吉〕。大莲花上有一尊格外巨大的佛陀结跏趺坐,披僧伽梨,偏袒右肩,结转法轮印。两侧的部分,(1)中有五层,(2)中有六层,很多菩萨坐在椅子(多为藤制椅)上,仰望佛陀,赞叹供养,与邻者交谈、思索,形体自由而生动。上层,在龛状的小楼阁内,结转法轮印的交脚菩萨,以及呈思惟相的半跏趺倚坐菩萨分别成对出现〔但在(2)中左侧有缺损〕。另外,在各层菩萨之中,引人注目的是,朝向我们的右上层,能看到一尊佛陀坐在岩座上(后述)。
在例(1)的最上层(第五层)的两端可以看到发出类型的佛陀。也就是,结禅定印的佛陀在莲花座上结跏趺坐,两侧呈放射状地各表现出四尊佛立像。禅定印佛陀不仅有头光,还构成容纳在圆形光背中的举身光,塑造出从禅定三昧佛陀的放光中散射出的许多化佛。
最上层的中央部分,虽然例(2)中很遗憾的有所缺损,但可观看(1)较好保留下的部分。在主尊佛陀的头上,和楼阁型一样,两个小佛徒(裸形童子)手举花环祝福,而且上面的顶部被假想的花树(宝树)覆盖,从花叶上露出上半身的四名天人中的两人双手奉上伞盖,其余两个人合掌。石板的整个画面从莲池到顶部,其意图是表现从地下到天上的上升性,强调出由莲花座的粗茎,结转法轮印的佛陀的双手和头部,以及肉髻到伞盖竿的中心轴。整个画面左右对称性强,而两侧众多菩萨都各有动作,栩栩如生,表现丰富。
2. 岩座与莲花座-释迦佛与阿弥陀佛
如前节所见,在主尊佛陀两侧的五、六层中显示有许多菩萨。仔细观察的话,菩萨们的脚下,以及菩萨所在的小楼阁的下部都显示有莲花。与此相对,从画面的右上方〔(1)、(2)同样是第四层〕可以看出,整体并不全是由菩萨构成,也有身缠僧伽梨、坐在岩座上的佛陀。岩座的下部不是莲花。坐岩座的佛陀、坐大莲花座的主尊佛陀,以及脚下或者建筑物下以莲花表示的菩萨们之间有明确的区别。
(1)(图11)中,佛祖坐在树下的岩座上,脸部朝向右下方,左手握住衣服的边缘,右手向上举起。可以看见佛陀转向的右侧是持金刚杵的执金刚神。执金刚神的下方是一位左膝立起、合掌作礼、望向佛陀、与佛陀对话姿态的人物。此人虽然缺少头部,但以(3)为例来看,可以判断出是一位比丘(图12)。(2)(图7)是同样的图像,但佛陀与此人都缺失了头部。
正如亨廷顿指出的一样,坐在岩座上的佛陀与比丘对话的与《无量寿经》中所记载的情节相吻合[8]109[38]658。他根据《无量寿经》梵本(英译)指出了这一点,更确切地说,是与《初期无量寿经》相符合[40]369-371。也就是说,在《初期无量寿经》的结尾(三毒五恶段之后),释迦牟尼询问阿难是否想看阿弥陀佛与菩萨、阿罗汉们所在的佛土时,阿难大喜,立膝合掌,向佛祖说“请对我展示一切”。然后就如释迦牟尼所说,阿难朝向太阳西沉的方向礼拜阿弥陀佛,头伏于地说:“南无阿弥陀佛”,阿弥陀佛放大光明,照遍十方无数佛土[33]316b-c,298b-c。《无量寿经》与梵本的内容大致相同,只是记录的是阿难如佛祖所说,整理衣服,向西合掌(没有记载立起膝盖),五体投地,阿弥陀佛放大光明[31]151-153[33]277c-278a。
雕塑可以解释为,佛坐在岩座上,与阿难比丘面对面交谈,阿难单膝立起,双手合十,佛举起右手表示主尊阿弥陀佛的场景。仔细看岩座的话,可以看到有狮子的头从洞中探出,被认为是转用了佛传“帝释窟说法”的图像{1}。讲述该佛陀是来自佛传中的释尊,如哈里森和卢扎尼兹、壬生所考察的一样,将坐大莲花座的主尊认定为放大光明的阿弥陀佛比较妥当{1}。在这里,将努力修行的、身为法藏菩萨的报身佛阿弥陀佛,在释尊与世自在王佛的带领下发愿普度众生,与其佛土的对比表现。这一点通过研究阿弥陀佛的放大光明和周围菩萨们的表现可以明确。
3. 阿弥陀佛放大光明
另一篇文章提到[13]2-4,《大品般若经》《法华经》《华严经》等经书中,放大光明(神变放光)是释迦佛入定三昧后,为普度众生(大乘的)说法的前兆[41],但正如前节提到的,在《初期无量寿经》中,阿弥陀佛放大光明是为了回应释尊对众生的代表——阿难的“启示”。阿弥陀佛不入三昧、放出普度众生的大光明,可以看作是阿弥陀佛前生身为法藏菩萨的誓愿与实践的报身佛的特质{2}。
《初期无量寿经》中强调“阿弥陀佛国放光明威神,以诸无央数天人民,及蜎飞蠕动之类,皆悉见阿弥陀佛光明,莫不慈心欢喜者。诸有泥犁禽兽薜荔诸有考治勤苦之处,即皆休止不复治,莫不解脱忧苦者”[33]316b-c,298b-c,详实地讲述了阿弥陀佛光明四溢的姿态和功德。相比之下,《无量寿经》以及梵本中对应的部分被简化,淡化了阿弥陀佛的光明性格。尽管如此,《无量寿经》和梵本中有的地方也会提及阿弥陀佛的大光明(放光),仍然是一个主要的特征[31]98-101,151-53[33]270a-b,272a,277c,278a。
以保存完好的举例(1)的画面构成,大莲花粗壮的茎,佛陀结转法轮印的双手、脸、头,头顶上方有翼佛徒高举花冠,以上面的花树与两位天人所持的天盖为中心轴贯穿的同时,坐在大莲花座上的阿弥陀佛的存在感极大。例(2)中,大莲花座和阿弥陀佛的造型极其震撼人心。而且周围充满了众多各种姿态的菩萨的同时,注意左右的相对性,构图具有向心性。(1)和(2)中,从下往上的第1、2、3层的内侧共计6位菩萨的视线,都抬头望向主尊的脸部,从造型上也可以看出菩萨们惊叹从阿弥陀佛的白毫中放出光芒的样子(图13)。同时,处于外侧的菩萨们也有转头交谈,向外构成离心性的姿态。以主尊为中心,具有向心性与离心性的构图,让人感受到阿弥陀佛的光明与威严的广阔。
4. 周围的菩萨们
在主尊的两侧,第5、6层很多倚坐菩萨的脚下和小楼阁的下面会用莲花来表示,也有直接站在莲花座上或者坐在莲花座上的菩萨(图14、15)。这样用莲花或者莲花座来表达,可能是为了表达与婆娑世界的不同,身处阿弥陀佛国土的菩萨们或者是出生在那里的人们。他们以带有圆光的菩萨来表示,坐在椅子上,或单手举起望向佛陀的方向,或合掌赞叹,或与邻者交谈,或结禅定印做冥想状,或双手抱膝,或手托下巴沉思等其他各种自由的姿势。也有手持莲花或者经书的菩萨。
这些菩萨的样貌让人联想到《初期无量寿经》中所描述的阿弥陀佛国的菩萨和出生在那里的人们的姿态。也就是说,在记载法藏菩萨发愿后,阿弥陀佛成佛以及佛国的情况的卷上,描述了在阿弥陀佛国的菩萨、阿罗汉们的修行,“讲经者、诵经者、说经者、口受经者、听经者、念经者、思道者、坐禅者、经行者”[33]305c-306c,285c[42](经书中不仅提到阿弥陀佛国的菩萨,还提到了阿罗汉、声闻们,但在美术中,大家都是菩萨,会强调菩萨的存在)。在下卷中,讲述了三辈观之后的出生在阿弥陀佛国人们的情况,“出生在阿弥陀佛国的出家人、在家人,聚集在用七宝造成的池子里,坐在大莲花上,讲述他们自己的功德与善行。还讲述了在前世中遵守的戒律,行的善法,往生的经过,喜爱的经典,教义的智慧和所行的功德(中略)人们彬彬有礼,温柔相待,都充满喜悦”(大意)[33]311b,293b,[43]。但在《无量寿经》中并没有关于阿弥陀佛国的菩萨和往生者们的样子。
哈里森和卢扎尼兹列举了后者(下卷)的出生在阿弥陀佛国人们的样子指出其相互交流的姿态与莲池型的菩萨们的姿态很相近[8]77。的确,在(1)中,可以在下方的两侧看到两组与邻者交谈的人物,但在上方可以看到不少在单独说法或者思惟像的人物。在(2)中,交谈的人物下端似乎各有一组(缺损),多表现为单独的禅定、交脚、半跏趺的菩萨,与上卷的内容相近。
例(1)(2)中菩萨们的表现,可以说是生动形象地描写出了在婆娑世界的灵鹫山,释尊向阿难展示阿弥陀佛和佛土,与在那里的菩萨和往生的菩萨们为佛道努力的样子。特别是(2)中的雕塑,雕刻得很深,接近整雕程度,对菩萨们丰富的写实表现很精彩。此外,不仅有互相交谈的人,还有静静冥想的人,像是惊叹一样望向阿弥陀佛的人等,画面整体都有一种生动感。这样的表达方式,表现阿弥陀佛国并不是一个庄严的净土世界,在惊叹于阿弥陀佛的大光明的同时,也展示出这片佛土是努力修行的菩萨们的活动场所,可以说是对《初期无量寿经》表达的宗旨和意图的巧妙塑造。
顺便说一下,观音和大势至两位菩萨在菩萨中占有特别的位置。《初期无量寿经》记载,观音和大势至这两位最尊贵的菩萨,经常侍奉在阿弥陀佛的左右,在阿弥陀佛般涅槃之后,观音和大势至会相继成佛,成为阿弥陀佛国的教主,佛法得以继承[33]308b-309a,290a-291a。《无量寿经》和梵本中没有说阿弥陀佛的般涅槃,只是作为最尊贵的菩萨提到了两位尊者的名字[33]273b[35]136。但不管怎么说,这部分成为阿弥陀三尊的典故。然而,莲池型中并没有明确三尊的形式{1}。在(1)(2)的菩萨们中,站在主尊的两侧,双手捧着花彩的两位菩萨可能是观音和大势至,但在整体构图中,与其他的菩萨相比也并不突出,应该只是供养菩萨{2}。
5. 莲池型是阿弥陀净土图吗?——放大光明的阿弥陀与其佛国的显现
没有在莲池型中表现观音、大势至两位菩萨的原因,如下所述,莲池型并不是表现西方遥远彼岸的阿弥陀净土,主要着眼于在婆娑世界显灵的阿弥陀佛与在佛土努力修行的菩萨们(参照后述的阿弥陀佛五十菩萨图)。
正如我们所见,莲池型以阿弥陀佛为主尊,周围有很多菩萨莲花座,或者是建筑下有莲花的菩萨,乍一看很容易被认为是阿弥陀净土图。在中国和日本,一般会以莲花化生的表现形式来描写往生者自莲中出生的场景,但是在这里仅见于下方的莲池。而且此处用同一个画面表达了在婆娑世界与阿难对话的释迦牟尼佛,并且在阿弥陀佛的大莲花座的两侧可以看到合掌的男女像。从他们的服装上可以很明显地看出是世俗人物,没有圆光,但是两人都是站在莲台上的。这种表达方式让笔者想起,在《初期无量寿经》中,“善男善女听到阿弥陀佛的名字,如果一整天都在颂扬阿弥陀佛的光明美妙的话,便会自阿弥陀佛国出生”(大意)[33]303a,282c的“善男、善女”{3}(《无量寿经》中简称为“众生”)。这里的意思似乎是說,世间中虔诚的善男善女一定会在阿弥陀佛国转生。包括旁边很多富有现实感的菩萨的表现在内,在这里,婆娑世界与阿弥陀世界相邻,都呈现在同一阁画面内。这方面与东亚的阿弥陀净土图大不相同。
莲池型中,表现阿弥陀佛国的同时,如释尊向阿难所示一样,它是以我们的婆娑世界为基础,在那里显现了闪耀着大光明的阿弥陀佛国。所表现出的众多菩萨的现实修行、冥想、思惟、谈话、说法等活动,也可以说是婆娑世界的投影,应该是与菩萨们的诸多实践有关。
(1)(2)中,上层的小楼阁内的交脚倚坐的说法菩萨和半跏思惟菩萨,是特别圣化的菩萨像,在楼阁型中也可以见到,也被认为与另一篇文章中提到的《小品般若经》《十地经》中所述的高位菩萨有关[11]262[34]11-12。如上所述,(1)(2)的下层的菩萨们的样子与《初期无量寿经》的记载相对应,但上层的小楼阁内的菩萨也与《无量寿经》中描述的菩萨有关系。也就是说,在同一卷的上、中,关于净土的情景描写占了大半,其中叙述了大量的声闻、菩萨(梵本中只有声闻)[31]101-102[33]270,但在该卷的下中,身为在阿弥陀佛国往生的菩萨们探求一生补处,前往十方世界供奉诸佛,回归净土。另外,菩萨们经常宣讲正法、禅定、详细阐述、赞颂优越的智慧[31]137-144[33]273c-274b。藤田说:“在《无量寿经》中,详细叙述了在净土往生的菩萨们是如何出色的行菩萨道,(中略)一般大乘经典中菩萨道的理想形象几乎被描述的淋漓尽致。‘不退转,‘一生补处和‘正定聚等术语成熟于早期的大乘经典,都是行大乘菩萨道和佛果阶段的术语。”[18]42(1)(2)的交脚倚坐的说法菩萨和半跏思惟菩萨,应该都是运用了这种对高位菩萨的象征性和视觉性的表现形式。
另外,在(1)的最上层的两端发出型的图像的表示也受到了关注。结跏趺坐在莲花座上的佛陀结禅定印,两侧呈放射状各有四尊立像的化佛,显示有放光。放射状的化佛下都表示有莲花。此图无疑是大乘经典(《大品般若经》序品,《大智度论》,如来藏经等)中所说的“大光明神变”,即“佛陀为了拯救众生二入定三昧,放大光明,光明变成了无数的莲花,自莲花中出现佛陀”[44-46]。
《无量寿经》上卷的最后有对大光明神变的深刻记述。在释尊细说了阿弥陀佛国的美好之后,他说:“净土的世界充满了莲花,自每一朵花中会发出无量的光,每一缕光中会出现无数的佛。每尊佛会放出光明为十方(的众生)讲法。”(大意)[33]272a-b这一部分无论是在《初期无量寿经》还是梵本中都不曾出现,但这里叙述了从净土无数的莲花中产生无量的光,从那些光中出现的无数佛陀会为了十方世界的众生说法。最上层的两端表示的发出型禅定印佛陀,是引导所有众生顿悟的佛陀身边的表现,也可以理解为是法藏菩萨实现了誓愿,成为了阿弥陀佛。同时,暗示最上层两端的是在表现其影响超越了其他时空的佛国{1}。
像这样,雕塑在造型上将过去、现在、未来的时间轴,在空间上把婆娑世界、十方佛土和阿弥陀佛国,都表现在同一画面上。因此,(1)(2)的石板雕刻上并不是在描写阿弥陀的西方极乐净土世界,而是借由阿弥陀佛的放大光明来显示释尊所在的我们的婆娑世界,也可以说是表现了以阿弥陀佛、那个世界的菩萨们,以及往生在那里的善男善女为中心,更是包含了其他佛土在内的十方世界的光景{2}。
6. 对弥勒菩萨的嘱托——例(3)的图像解释
最后来考察例(3)(图8)。这块石板雕刻分为上、中、下三区,中央的大块区域呈莲池型构图;上方的半圆形区域是以交脚菩萨为中心配置菩萨和天人的构图;下端的横长区域则是以佛钵为中心表现礼拜的人们(图片左下方缺损)。
中央区虽然看不到莲池,但有结跏趺坐于大莲花座上、结转轮印的阿弥陀佛;头顶上方有两位手捧花环的佛徒(童子),在上方有宝华。两侧有三段左右对称的坐在椅子上的菩萨,计十尊(但左下角缺损两尊);佛陀的两旁是持花彩的两尊供养菩萨;上面是站立守护和在礼拜的执金刚神和女神。从下往上数第三层的左右表现有在楼阁内的禅定佛。最上层的右边,坐在岩座上的佛陀举起右手,与旁边跪坐合掌的比丘对话的样子。与之对称的左边可以看到的是有身光并在放光、结禅定印的坐佛和一匹马的侧面。
该中央区的图像的构图是例(1)(2)的简略化,从最上层的右方可以看出主题是坐在岩座上的释尊与跪着的阿难(图12),阿弥陀佛放大光明,可以认为是表现了自身和阿弥陀佛国菩萨们的状态。第三层的两尊小楼阁内的禅定佛应该是有意味的其他佛土的菩萨们的姿态。另外,最上层的左侧在放光的禅定印坐佛(或者禅定印坐菩萨{3}),可以看出是(2)的最上层的发出型的变化,或者是为了与右边释尊向阿难显示阿弥陀佛的表现相对应。总之,中央区的图像与(1)(2)是同一类型,可以说是展示犍陀罗阿弥陀信仰面貌的重要例子之一。
这个例子的有趣之处在于中央区上下的区域所表现出来的图像。上区中心的交脚倚坐菩萨,高髻,左手持水瓶,右手掌心向内的手势,无疑是继承了梵天图像的弥勒菩萨[47-48]。而且还带有华盖,被飞天散华、像胁侍菩萨的两尊菩萨赞叹。下方两侧各有两尊菩萨(抑或是天人)向弥勒菩萨合掌(右边的一尊转头看向旁边的人)。两端思惟相的两尊菩萨以左右对称的形式来表现。这样的弥勒菩萨构图还有其他的类似犍陀罗的例子,可以认为是中国在北魏时代定型的“兜率天上的弥勒菩萨”的祖型[48]308-315[49]。
在下方区域,可以看到在中央台座上的佛钵的右边有四位礼拜的人(左边只残存有一个人的像)。在犍陀罗雕刻中有很多礼拜佛钵的表现。这与犍陀罗的白沙瓦曾经供养佛钵,或者说佛钵信仰有关{1}。法显到据说是由迦腻色迦王建造的供养佛钵的寺庙进行访问,记载了供养的繁盛情形[50]。这个佛钵是在释迦牟尼成道后,被四天王献给世尊的有来历的石钵(世尊接受了四个钵,将之合成一个后,四季就很分明了),据斯里兰卡的印度僧说,原来在毗舍离,现在在犍陀羅,数百年后先后辗转于西大月氏国、于阗国和龟兹国,最后升上兜率天,有弥勒菩萨供养,说“钵若去,则佛法渐灭”[50]865c。由此可见,佛钵作为佛法的象征被信仰。
《无量寿经》的末尾(流通分)讲述了该经典的付嘱。《初期无量寿经》中,释尊对阿难和阿逸(弥勒)菩萨说:“我涅槃后,会有不相信阿弥陀佛国的人,所以尽显阿弥陀佛国。(中略)我将此经交给汝等。”(大意)[33]317c,299c这里可以理解为对阿难和弥勒菩萨们,以及后来的人们的一般嘱托。与此相对,《无量寿经》中,释尊对弥勒菩萨说“我今为众生说此经法,令其领略了无量寿佛与其国土一切。(中略)即使将来经法尽灭,也要心怀慈悲,哀悯,将此经书流传下去”,并暗示之后将此教诲告之弥勒[33]279。梵本中关于这一部分明确地表示了对弥勒菩萨的嘱托:“阿逸多啊,我已经解释了关于善根的一切。你们现在,专心吧,行动吧。阿逸多啊,为了不让佛门灭亡,(我)会正式嘱托的。”[31]166
根据以上的研究可以得出,例(3)的目的在于:中央区向人们展示阿弥陀佛和其佛土的样子;下方区的礼拜佛钵暗示那是释尊的教诲(佛法);上方区中,即使将来佛法会在这个世间灭亡,在兜率天的弥勒菩萨那里接受继承这个教诲的话,就可以继续流传下去。因此例(3)与《无量佛经》和梵本有着紧密的关系,可以说阿弥陀信仰与未来佛弥勒信仰的结合。
四 结语与阿弥陀佛五十菩萨图的关联
作为与犍陀罗信仰有关的美术作品,分析了阿弥陀三尊像1例、莲池型石板雕刻3例。在中国和日本,阿弥陀三尊像和阿弥陀净土图是阿弥陀佛信仰最基本的美术,从这一点来看,阿弥陀佛信仰的源流可以追溯至犍陀罗时期,可以说这是一个非常有趣且重要的问题。
在印度内部,有可以从刻文中看出是阿弥陀佛,中印度马图拉的两脚残存立像(图16)。台座上有刻文(婆罗米文)“婆湿色伽王通过那伽拉库西卡造了阿弥陀佛像。为了供养一切诸佛。愿此善根,使一切众生获得无上佛智。”这是现存的2世纪中叶时期,波罗王朝之前的印度内部唯一明确的阿弥陀佛的实例{1}。刻文记载,捐赠者那伽拉库西卡是商队主的父亲,也是商主的孫子,是富裕的商人家族。在贵霜王朝时期,因为逐渐加深与马图拉和犍陀罗交易、交流,因此阿弥陀信仰可能来自犍陀罗。到了波罗王朝(8世纪中叶—11世纪下叶,包括奥里萨邦),阿弥陀佛画作为金刚界五佛之一被造像的案例非常多,在密教中被确认为是作为位于西方的佛陀的信仰(图17)[51]。但是,在印度并没有发现阿弥陀三尊像和阿弥陀净土图的案例。
这样看来,仅从美术来看,传到中国和日本的大乘佛教的阿弥陀信仰有很大的可能性与犍陀罗有渊源。另一方面,对比犍陀罗的莲池型与中国的阿弥陀净土图也有很大的差异。中国最早期的阿弥陀净土图出现在西魏、北齐时期,如初唐时期出现的敦煌莫高窟壁画一样,图像的构成可以说很成熟。其第一个特征:大莲池中配置的阿弥陀三尊像,头顶有华丽的花树、华盖,以及壮丽的楼阁和宝树等情景描写;第二个特征:是强烈地意识到了《观经》中的九品往生观,在莲池中有刻画莲花化生的往生者;第三个特征:阿弥陀净土图给人一种强烈的、远离婆娑世界的、西方极乐净土的印象,看不到莲池型中,释尊在我们婆娑世界的变现。
在东亚的阿弥陀净土图中,看不到在莲池型中所重视的阿弥陀佛国往生在那里的菩萨们,统一的在赞颂净土、供养的形象;或者在净土修行、互相交谈的样子。大概是因为中国的阿弥陀信仰虽然是以《无量寿经》为基础,但重要的是没有传到犍陀罗、印度的《观经》{2},视觉上更直观地强调净土的壮丽以及如何才能往生到净土世界。
但是另一方面,犍陀罗的莲池型图像也有可能在中国和日本进行传播并产生了影响,最后关于这一点进行论述。在中国四川省梓潼卧龙山千佛岩1号龛、莫高窟第322窟(图18、18a)、日本法隆寺金堂壁画6号壁(图19、19a)等处看到的阿弥陀佛五十菩萨图(也称“阿弥陀并五十二菩萨图”)。该图像被认为收录于道宣撰写的《集神州三宝感通录》(664),大略是由来与五通菩萨言语:
昔天竺鸡头摩寺五通菩萨。往安乐界请阿弥陀佛。婆娑众生愿生净土。无佛形像愿力莫由。请垂降许。佛言。汝且前去。寻当现彼。及菩萨还。其像已至。一佛五十菩萨各坐莲花在树叶上。菩萨取叶所在图写流布远近。汉明感梦使往祈法。便获迦叶摩腾等至洛阳。后腾姊子作沙门。持此瑞像方达此国。所在图之。未几宝像西返。而此图传不甚流广。魏晋以来年代久远。又经灭法经像泯除。此之瑞迹殆将不见。(中略)时有北齐画工曹仲达者。善于丹青。妙尽梵迹传模西瑞。京邑所推。故今寺壁正阳皆其真范。{1}
与印度的五通菩萨有关的这幅图像,在前面提到在卧龙山千佛岩的阿弥陀佛并五十二菩萨上显示有贞观八年(634)造像题记[52-53],因形成了唐代阿弥陀信仰的一个流派而备受关注。近年来,在四川省巴蜀地区和河南省龙门石窟等地,调查研究了很多类似的案例,图像的变化也很丰富{2}。但是该图像的基本特征是,以坐在莲花座上的阿弥陀佛和两尊菩萨为中心,自下方的莲池生长出很多同根多枝的莲花,主尊的两侧以各种各样的姿势坐着许多菩萨,阿弥陀净土图中,一般没有描写宝池、宝树、楼阁等场景,莲花化生的童子也不是很显眼。这一点与犍陀罗的莲池型在构图上看起来很相似,先行研究中也有指出两者是有相似之处的[37][54]。
这里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如上所述,犍陀罗的莲池型并不是单纯的阿弥陀净土图,而是根据释尊对阿难的讲述,阿弥陀佛放大光明,向我们所在的世界展现在净土世界修行的众多菩萨,这才是与“阿弥陀佛五十菩萨图”中描绘的,应五通菩萨的请求,在婆娑世界显现的阿弥陀佛五十菩萨的相似点。也就是说,两者都是阿弥陀佛和众多菩萨在我们居住的婆娑世界显现(或者垂降)。在经典中,净土的大地是平坦的,没有山脉,但在犍陀罗雕刻上则是显示释尊和阿难是坐在岩座上的,这一点无疑是阿弥陀佛五十菩萨图中山岳和土坡的原因[55-56]。另外,表现出有很多各种各样姿势的菩萨也是有理由的。一般认为阿弥陀信仰的目的是往生去阿弥陀净土,但正如《初期无量寿经》中所说的犍陀罗莲池型一样,阿弥陀净土被描述为容易修行的场所,所以,有很多菩萨或交谈,或冥想,或思惟,或说法。
如此,中国和日本的阿弥陀佛五十菩萨图的图像构成是以阿弥陀佛为中心,在其周围表现出众多各种各样姿势的菩萨,继承了犍陀罗的莲池型雕刻的图像传统。另一方面,两者也有不同的图像表现形式。最大的不同是,阿弥陀佛五十菩萨图中,菩萨们坐的莲花座是用莲茎连接而成的“同根多枝”来表达的,而犍陀罗的莲池型中虽然表示出有莲茎,但莲茎很多,没办法连接起来。其目的一定是为了表现阿弥陀佛放大光明,由光化成莲花。
与此相对,“同根多枝的莲花”是基于中印度式的想法,源自于古代满瓶(装满说的壶中莲花繁茂生长的图像),特别是与笈多王朝的鹿野苑和伐迦陀迦时期的阿旃陀石窟的雕刻和壁画中出现的“舍卫城神变”(千佛化现)的佛传场面(5世纪中叶—6世纪中叶)的表现相似[57]。在那里屡次出现释迦佛手结转法轮印,结跏趺坐在由两位龙王支撑的莲茎粗壮的莲花座上,周围用同根多枝的莲茎连接,在周围有很多释迦佛的化身(化佛)或站或坐在这些莲花座上,遍滿天上(图20)。基于《Divyāvadāna》第12章《Prātihārya-sūtra》(《根本说一切有部毗奈耶杂事》),释尊为了降服外道,进入深度冥想后,化现出行住坐卧的各种姿势的表现,在印度,作为释迦八相图之一在笈多王朝之后流行起来了[54]380-397,405-407。但是“舍卫城神变”以释迦佛为主尊,周围莲花上的尊像表示的是佛陀(化佛)而不是菩萨。
阿弥陀佛五十菩萨图的祖型可是犍陀罗的莲池型与笈多王朝的“舍卫城神变”图像在中亚融合后形成的。同时也考虑将阿弥陀佛五十菩萨图是由粟特族出身的画家曹仲达流传的这一传说纳入研究的范围,期待今后研究的进展。
参考文献:
[1]Allon Mark,Richard Salomon. New Evidence for Mahayana in Early Gandhāra[J]. The Eastern Buddhist,2010,41(1):1-22.
[2]松田和信. アフガニスタン写本からみた大乗仏教[G]// シリーズ大乗仏教1:大乗仏教とは何か. 春秋社,2011:151-184.
[3]辛嶋静志. 大乗仏教とガンダーラ:般若経:阿弥陀:観音[J]. 創価大学国際仏教学高等研究所年報,2014(17):449-485.
[4]Strauch. Early Mahāyāna in Gandhāra:New Evidence from Bajaur Mahāyāna Sūtra[G]// Harrison,Paul. Setting out on the Great on the Way:Essays on Essays on Early Mahāyāna Buddhism,2018:207-242.
[7]宮治昭.ガンダーラの三尊形式の両脇侍菩薩の図像[G]//涅槃と弥勒の図像学―インドから中央アジアへ―.東京:吉川弘文館,1992:245-280.
[8]Harrsion Paul,Christian Luczanits.New Light on(and from) the Muhammad Nari Stele[C]//Katsura,Syoryu. Special International Symposium on Pure land Buddhism.Research Center for Buddhist Cultures in Asia,Ryukoku University,2012:69-130,197-207,Fig. 1-17 .
[10]Rhi,Juhyung(李柱亨). Early Mahāyāna and Gandhāran Buddhism:An Assessment of the Visual Evidence[J]. The Eastern Buddhist,2003,35(1/2):166-171.
[11]Rhi,Juhyung(李柱亨). Looking for Mahāyāna Bodhisattva:A Reflection on Visual Evidence in Early Indian Buddhism[G]// Harrison,Paul. Setting out on the Great on the Way:Essays on Early Mahāyāna Buddhism,2018:244.
[12]安田治樹. ガンダーラ仏と蓮華座[J]. 法華文化研究,2005(31):1-23.
[13]宫治昭. ガンダーラにおける大乗仏教美術の様相―〈三尊タイプ〉〈発出タイプ〉〈楼閣タイプ〉を中心に―[J]. 密教図像,2021(40):6-7.
[15]Fussman,Gerard. La place des Sukhāvatī-vyūha dans le bouddhisme indien[J]. Journal Asiatique,1999,287(2):523-586.
[17]Rhi,Juhyung(李柱亨). Bodhisattva in Gandhāran Art: An Aspect of Mahāyāna in Gandhāran Buddhism[G]//Pia Brancaccio,Kurt Behrendt. Gandhāran Buddhism Archaeology,Art,Text. Vancouver and Toronto:University of British Columbia Press,2006:169.
[18]藤田宏達. 浄土三部経の研究[M]. 東京:岩波書店.2007.
[19]宮治昭. 舎衛城の神変と大乗仏教美術の起源:研究史と展望[G]//インド仏教美術史論. 東京:中央公論新社,2010:145.
[21]山中行雄. ガンダーラにおける阿弥陀信仰についての一考察[J].仏教大学総合研究所紀要. 2010(17):118-120.
[22]辛嶋静志. 大乗仏教とガンダーラ―般若経:阿弥陀:観音―[J].創価大学国際仏教学高等研究所年報,2014(17):478.
[23]辛嶋静志. 法華経の文献学的研究(二):観音Avalokitasvaraの語義解釈[J]. 創価大学国際仏教学高等研究所年報,1999(2):39-66.
[24]山田明爾. 観音菩薩像の成立と展開:序章:観音信仰[G]//シルクロード学研究(1),シルクロード学研究センター(なら·シルクロード博記念交流財団),2001:5-11.
[25]斎藤明. 観音(観自在)と梵天勧請[J]. 東方学. 2011(122):1-12.
[26]斎藤明. 《般若心経》とアヴァローキテーシュヴァラ(観自在)[J]. 東洋の思想と宗教,2019(36):1-22.
[27]梶山雄一. 初期浄土教をめぐる最近の情報[G]//梶山雄一著作集:第6巻:浄土の思想. 東京:春秋社,2013:41-47,56-57,註5-17. 初出,成田山仏教研究所紀要,1992(15):95-110.
[28]藤田宏達. 原始浄土思想の研究[M]. 東京:巖波書店,1970:320-321.
[29]定方晟. 寄進者ダミトラ[J]. 東海大学名誉教授年報.2006(1):78-82.
[30]无量清净平等觉经[G]//大正蔵:第12册:東京:大正一切經刊行會,1925:308b,290a.
[31]藤田宏達. 新訳梵本和訳無量寿経:阿弥陀経[M]. 東京:法蔵館,2015:135-136.
[32]宮治昭. 半跏思惟像の展開[G]//インド仏教美術史論. 東京:中央公論新社,2010:109-111.
[33]佛说观无量寿经[G]//大正蔵:第12册:東京:大正一切經刊行會,1925:343c-344a.
[34]Rosenfield,John M. The Dynastic Arts of the Kushans[M]. Berkeley and Los Angels,1967.
[35]宫治昭. ガンダーラの半跏思惟の図像[G]//涅槃と弥勒の図像学―インドから中央アジアへ―.東京:吉川弘文館,1992:321-353.
[36]Rhi,Juhyung(李柱亨). Wondrous Vision:The Mohamad Nari Stele from Gandhara[J]. Orientations,2011,42(2):112-115.
[37]源豊宗. 浄土変の形式[J]. 仏教美術:第7册. 1926:60-73.
[38]Huntington,John. A Gandhāran Image of Amitāyus Sukhāvatī[J]. Annali dell Istituto Orientale di Napoli,1980,40(30):652-672.
[40]壬生泰紀. 初期無量寿経の研究[M]. 東京:法蔵館,2021:369-371.
[41]梶山雄一. 神変[G]//梶山雄一著作集:第3巻:神変と仏陀観:宇宙論. 東京:春秋社,2012:237-285. 初出,仏教大学総合研究所紀要,2:1-37.
[42]辛嶋静志. 《大阿弥陀経》訳注(四)[J]. 仏教大学総合研究所紀要,2003(10):28.
[43]辛嶋静志. 《大阿弥陀経》訳注(七)[J]. 仏教大学総合研究所紀要,2006(13):2.
[44]放光般若经[G]//大正藏:第8册. 東京:大正一切經刊行會,1925:1b.
[45]光赞经[G]//大正藏:第8册:東京:大正一切經刊行會,1925:147b-c.
[46]摩诃般若波罗蜜经[G]//大正藏:第16册:東京:大正一切經刊行會,1925:457a-c.
[47]Taddei,Maurizio.Harpocrarates-Brahmā-Maitreya:A
Tentative Interpretation of a Gandharan Relief from Swāt [J]. Dialoghi di Archaeologia,Anno III,1969(3):364-390.
[48]宫治昭. ガンダーラの弥勒菩薩の図像:梵天·バラモン行者の図像との混淆をめぐって[G]//涅槃と弥勒の図像学:インドから中央アジアへ―. 東京:吉川弘文館,1992:281-320.
[49]打本和音. ガンダーラにおける《兜率天上の弥勒》への信仰:《出三蔵記集》《梁高僧伝》を中心に[J]. 密教図像,2012(31):1-18.
[50]法显. 高僧法显传[M]//大正藏:第51册:東京:大正一切經刊行會,1925:858b.
[51]宫治昭. パーラ朝の密教五仏[C]//インド仏教美術史論. 東京:中央公論新社,2010:594-631.
[52]勝木言一郎. 中国における阿弥陀三尊五十菩薩図の図像について:臥龍山千仏巌の作例紹介とその意義[J]. 佛教藝術,1994(214):61-73.
[53]肥田路美. 美術史料として読む《集神州三宝感通録》:釈読と研究(十)[J]. 早稲田大学大学院東洋美術史,2017:1-15.
[54]小野英二. 山景をそなえた阿弥陀仏五十菩薩像について[J]. 密教図像,2009(28):18-31.
[55]小野英二. 阿弥陀仏五十菩薩図像の成立と展開について[G]//美術史研究:48冊. 早稲田大学美術史学会,2010:109-130.
[56]肥田路美. 法隆寺壁画に画かれた山岳景の意義[G]//初唐仏教美術の研究.東京:中央公論美術出版社,2011:371-399.
[57]宫治昭. インド仏教美術史論[M]. 東京:中央公論新社,2010:124-132,431-43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