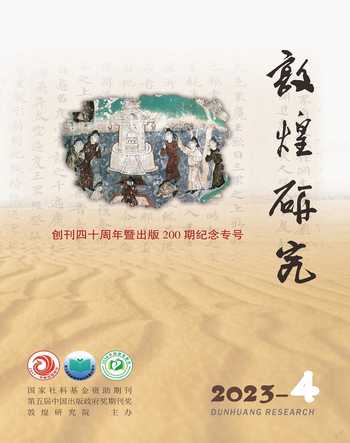略谈敦煌学的扩展与进展
2023-09-28荣新江
荣新江
内容摘要:文章通过四篇有关敦煌学的书序,对敦煌美术史、佛教文献和图像、胡语文书、敦煌学学术史等方面的研究做了回顧,指出这些著作代表了敦煌学的拓展,并根据相关新书的内容,对上述四个方面的研究做了展望。
关键词:星宿崇拜;十王经;回鹘文文献;伤心史
中图分类号:G23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4106(2023)04-0024-06
A Brief Discussion on the Expansion and Progress of
Dunhuang Studies
—Four Prefaces to Monographs on Dunhuang Studies
RONG Xinjiang
(Department of History, Peking University, Beijing 100871)
Abstract:Through four prefaces to monographs on Dunhuang Studies, this paper presents a review of recent research on Dunhuang art history, Buddhist documents and iconography, documents in non-Chinese languages, and the academic history of Dunhuang Studies, and demonstrates that these works represent the expansion of Dunhuang Studies. The paper concludes with a discussion of the prospects for future research in the above-mentioned fields based on the contents of recently published books.
Keywords:celestial worship; Sutra of the Ten Kings; Uighur documents; tragic history
(Translated by WANG Pingxian)
近年来,敦煌学获得较快的发展,敦煌学的领域也在不断扩大,特别是在敦煌美术史、佛教文献和图像、胡语文书、敦煌学学术史等方面,较之于传统的敦煌历史、文献等方面的研究有较大的进步,新的成果不断产出。笔者蒙几位敦煌学同仁信任,以新撰著作征序于我,正好涉及上述四个方面。笔者借作序之机,在回顾相关研究成果的同时,阐发对美术史、佛教文献、胡语文书、学术史四个方面的一些展望。今值《敦煌研究》创刊四十周年纪念,检出未刊四篇书序,刊发于此,以为祝贺。
一 孟嗣徽《文明与交融:中古星宿崇拜图像研究》序
今年年初,孟嗣徽老师寄来她的书稿——《文明与交融:中古星宿崇拜图像研究》,命我做序。这是北京入冬以来最冷的一天,在这样冰冷的天地里,在新冠疫情借寒冬又有些反弹之际,我无法用冷冰冰的话回绝这一请求,所以就热情地答应下来,其实我也有些话要说。
孟嗣徽老师长年供职于故宫博物院的展览部(现在叫展宣部),这个部门的日常工作是办展览,所以是一个博物馆中最为忙碌的地方,很多还是体力活。孟老师其实是在利用“业余”的时间,从事真正的学术研究,而这些“业余”时间里出来的成果,却不是业余的,而是非常专业的。
这本书的主题,是“中古星宿崇拜图像研究”,选题极为精深。这类图像有的出自唐朝集贤院待制梁令瓒的精心描绘,有的则是敦煌民间占卜术士的随手摹写,它们涉及星象与星命,是中古民众宗教信仰的反映,需要从思想史的角度给予解释;同时这类图像又是星象与图像,是古代各个阶层的画家所描绘的形象世界,需要从美术史的角度加以解剖。我曾经“业余”研究一点天文历法史,深知对这些文本和图像的认知不是很容易的一件事,所以对孟老师所做的课题一直抱有浓厚的兴趣,也很关注她的工作成果。
美术史的研究有时候需要非常细致地观察作品原件或高清图片,这些图像并不是很容易就有机会看到,因此需要较长时间的准备,不能急于求成。孟嗣徽老师在故宫工作,时而有得天独厚的看画机会,她自己也勤于求索,走访过海内外多家博物馆,曾在美国弗利尔·赛克勒美术馆(史密森尼国家亚洲艺术博物馆)从事研究,并走访北美多家中国美术品收藏单位,也时常到国内各地的佛寺、石窟去观察原作,包括山西、河北的寺庙,新疆、甘肃、宁夏等地的石窟,了解作品周边的生成环境。经过一段时间的观察、品味、琢磨、研究,等火候一到,就抛出一篇。
1995年我开始协助几位老先生编辑《敦煌吐鲁番研究》学术专刊,到处搜寻有水平、有分量、有厚度的稿子,当时看到孟嗣徽的《炽盛光佛变相图图像研究》一文,对其材料的收集和内容的解说都倍感钦佩,于是力争将此文纳入编审范围,经专家评议后,发表在1997年出版的《敦煌吐鲁番研究》第2卷上。由此,我和孟嗣徽老师熟悉起来,时常受她关照,去故宫看展。她也常常来北大参加我们主办的学术会议、讲座和读书班。我知道她住在北京东城,距离北大很远,但她有一段时间坚持每周来参加我主持的“马可波罗读书班”,没有特殊的事情,她从不缺席,到了期末,她还拿来积攒的“故宫”牌好酒,请读书班的小朋友们一起聚餐,共庆一个学期辛勤的劳动成果。
孟嗣徽老师有关中古星象崇拜图像的研究不断有新的发现和突进,我常常能够听她不动声色地给我们讲起:最近终于弄懂了哪个图讲的是什么,有点小收获。我知道她一定会有新的研究成果,所以在组织科研课题或学术工作坊时,常常邀她参加,像收入本书的《西来“设覩噜”(Satru)法:占星术中祈福禳灾的秘密空间》一文,就是她参加我和党宝海主持的“马可波罗研究项目”的成果,收入我们主编的《马可·波罗与10—14世纪的丝绸之路》,2019年6月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近年来她又是我主持的“敦煌与于阗:佛教艺术与物质文化的交互影响”课题团队的主力队员,不论是去和田、敦煌等地的艰苦考察,还是按期提交学术论文,都不辞劳苦,大力支持。她撰写的《〈护诸童子十六女神〉像叶与于阗敦煌地区的护童子信仰》一文,借助敦煌藏经洞发现的图像及传世文献等材料,正确地判断出丹丹乌里克新发现的一组杂神,应当是属于“护童子十五鬼神”像。我对此组图像一直未得正解,读了她这篇三万余字的文章后,豁然开朗。孟老师的文章,大多如此。
故宫是一个为人仰望的皇家宝地,在这里工作,可以养尊处优,无所事事;也可以向各科专家讨教,使学业精进。孟嗣徽老师充分利用了故宫深厚的学养和丰富的收藏,利用“业余”时间,完成一篇又一篇学术专论。这里汇集了她有关中古星宿崇拜图像的研究成果,并冠以“文明与交融”的总题,纳入故宫博物院的《故宫学术丛书》中,这不仅是对本职单位的贡献,也是相关学术领域的新成果。我有幸先期阅读书稿,受命为序,因略述与本书有关之学理与学谊,聊以为序。(2021年1月25日完稿)
二 张总《〈十王经〉信仰》序
在佛教思想的影响下,中古时期产生的《十王经》在中国乃至东亚世界有着广泛的影响,不仅衍生出更加繁复的文本,还以雕像、绘画、版画等形式传播,这从汉字文化圈的敦煌、韩国、日本发现的《十王经》文本和图卷可以得到印证,而非汉字文化圈的西州回鹘、西夏王国以及西藏地区发现的回鹘文、西夏文、藏文《十王经》写本和刻本,也更加说明这种中土冥界故事传播之广远。
有关《十王经》的研究有着十分丰厚的学术积累。日本学者从疑伪经的角度很早就关注到《十王经》,并努力发掘和整理日本及敦煌所藏的文本。1989年兰州大学杜斗城教授出版《敦煌本〈佛说十王经〉校录研究》,汇集了当时可以找到的所有《十王经》文本,并做了文本分析和研究。在此基础上,结合西方炼狱(Purgatory)观念,太史文(Stephen F.Teiser)教授于1994年出版《〈十王经〉与中国中世纪佛教冥界的形成》(夏威夷大学出版社,有张煜译、张总校的汉译本,上海古籍出版社,2016年),对《十王经》信仰做了详细的阐述,特别是以敦煌写本为依据,对各种《十王经》文本的制作做了详细的解说。另一方面,拥有大量吐鲁番出土回鹘语文献的德国学者,早在1971年就专论过吐鲁番回鹘文绘本反映的中亚地藏信仰和炼狱思想,此即葛玛丽(Annemarie von Gabain)的英文和德文论文(“The Purgatory of the Buddhist Uighurs. Book illustrations from Turfan,”Mahavanist Art after A.D.900. Percival David Foundation of Chinese Art,London 1971,25—35;“Ksitigarbha-kult in Zentralasien,Buchillustrationen aus den Turfan-Funden,”H.H?覿rtel,et al.(eds.),Indo-
logen-Tagung 1971,Verhandlungen der Indologischen Arbeitstogung im Museum für Indische Kunst(Berlin)7—9 Oktober 1971,Wiesbaden 1973,
47—71);此后茨默(Peter Zieme)教授续有贡献,近年来又和拉施曼(S.-C. Raschmann)合作整理了圣彼得堡东方文献研究所所藏古代突厥语《十王经》残片(The Old Turkish Fragments of The Scripture on the Ten Kings in the Collection of the Institute of Oriental Manuscripts,RAS,波波娃、刘屹主编《敦煌学:第二个百年的研究视角与问题》,圣彼得堡,2012年,第209—216页)。《十王经》的图像也很早受到学者的注意,有松本荣一的《敦煌画研究》(东京东方文化学院,1937年;最近有林保尧、赵声良、李梅汉文译本出版,浙江大学出版社,2019年)。以后雷德侯(Lothar Ledderose)等续有发现,而王惠民、张小刚、郭俊叶利用敦煌材料,更加详细地推进了地藏菩萨图像的美术史研究。
在纷纭复杂的十王信仰研究史中,本书作者张总先生有着独特的贡献。他从北京大学图书馆善本部的艺风堂藏拓中,找到唐贞观十三年(639)齐士员献陵造像碑上阎罗王图像,并且在献陵东北一公里处找到造像碑原物,撰写了《初唐阎罗王图像及刻经——以〈齐士员献陵造像碑〉拓本为中心》。我忘记在什么场合听他说起这个发现,立即向他约稿,随后发表在我主编的《唐研究》第6卷(2000年)。此文置于卷首,因为这个发现不仅把十王信仰的关键内涵较前人认知的时间大大提前,而且是唐朝长安周边——唐帝国核心区域的材料,意义非同一般。我知道他在研究《十王经》,所以特别把我1997年访问美国弗利尔美术馆时见到的一件原庐山开元寺所藏《阎罗王授记经》藏川本提示给他,没想到他很快获得这件写本的彩色图版,并考订清楚文本的流传过程,阐发其价值。我也把他包含此卷的有关研究论文《〈阎罗王授记经〉缀补研考》,收入《敦煌吐鲁番研究》第5卷(2001年),并刊出两件彩色图版。这个庐山文本证明该经在敦煌之外也有流传,特别是在南方的传承。这两个例子,说明张总先生视野广阔,除了石窟造像和写卷文本之外,留意到石刻拓本、考古遗物、佛塔遗物等等许多方面,大大扩充了《十王经》研究的范围。
2003年,张总先生出版《地藏信仰研究》(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但有關《十王经》的研究仍在持续进行,不断扩展。最近终于完成大著《〈十王经〉信仰——经本成变、图画雕像与东亚丧仪》,汇总了迄今所见文本和图像材料,并把地域范围延展到整个东亚和中亚地区,利用新见陕西耀州神德寺塔出土品、浙江台州灵石寺本、西夏文本和藏文本,构建了《十王经》的传播谱系,深入阐述了与《十王经》信仰相关的丧葬礼仪、风俗信仰、社会生活、中外文化交流等诸多方面。
张总先生知道我一直关注他的《十王经》研究,也每每在各种见面的场合和我讲述他的最新发现。今年9月在敦煌见面,他说文稿已经杀青,有待付梓,希望我写一篇序。虽然论辈分我没资格给他的书写序,但又欣喜他说了多年的大著终于脱稿,故此勉力为之,谨略述《十王经》研究之大略及张总先生之贡献,是以为序。(2021年12月18日完稿)
三 阿依达尔·米尔卡马力《国家图书馆藏回鹘文文献研究》序
自19世纪末叶以来,吐鲁番、敦煌等地发现了大量回鹘语文献,其中不乏一米七八的长卷和数十叶的册子本,其内容以佛教典籍为主,也有大量摩尼教、基督教文献,还有不少官私文书。就其中的佛典而言,既有写卷,又有刻本,它们构成了回鹘佛教大藏经的方方面面,是今人研究回鹘宗教信仰、佛教思想、东西文化交流,以及佛教社会日常生活的主要依据。由此之故,自回鹘语文献发现以后,一百多年来语文学家已经把大量文本转写翻译出来,成为各方面专家学者取材的对象。
中国国家图书馆自京师图书馆到北京图书馆时代,一直致力于收集敦煌、吐鲁番文献,其中包括清末从敦煌莫高窟调运的藏经洞文书,还有许多是历年来通过调拨、征集、捐赠、购买等各种方式所得。这些收集品当中,包含有不少回鹘语材料,追本溯源,有些来自敦煌藏经洞,有些出自莫高窟北区,更多的应当出土于吐鲁番盆地的佛寺与石窟。但由于分属不同部门或不同类别,国家图书馆的回鹘语材料只有归入“敦煌遗书”文库的部分,收入2005年至2012年出版的《国家图书馆藏敦煌遗书》,而放在民族古籍部门的藏品则不在其中,除馆内人员和个别专家,外人不知其详。
阿依达尔·米尔卡马力教授多年来致力于回鹘语文献的调查、整理和研究,发表了相当丰富的研究成果。近年来他与国家图书馆工作人员合作,对国图所藏回鹘语文献做了透彻的调查和整理。本书就是他这些年來整理国图藏卷以及相关其他家藏品的集大成之作,其中有阿含、般若、华严、密教诸部经典,也有金刚、法华、圆觉、阿毗达磨等各种论疏,还有伪经、占书及佛教斋会所用的劝请、随喜、礼忏、发愿等文本,给已有的回鹘语佛典宝藏,增添了不少绚丽的花朵。这些大多译自汉文佛典的回鹘语译本,不仅成为回鹘大藏的组成部分,其实也是中华佛教藏经大家庭中的一员,将其整理出版有着多重的学术意义。
阿依达尔生长在新疆伊宁,曾在中央民族大学和新疆大学学习和攻读,又曾两度在日本京都大学长期访学,与回鹘语专家庄垣內正弘先生合作研究,现执教于新疆大学中国语言文学学院。在本书完成之前,他陆续发表了多篇回鹘语佛教文献的研究成果,涉及敦煌莫高窟北区、吐鲁番柏孜克里克石窟出土以及普林斯顿大学等地所藏文献,成绩斐然。这次他把国家图书馆藏回鹘语文献汇为一编,不论从敦煌吐鲁番研究来讲,还是从回鹘语文献研究来说,都是一项重要的成果。
回鹘语文献作为宝贵的文化遗产,也是我多年来调查追寻海内外敦煌吐鲁番宝藏的组成部分,曾先后在英、法、德、俄、日等国的收集品中留意这些回鹘语文献的收藏,部分情况写入拙著《海外敦煌吐鲁番文献知见录》。而1985年去巴黎调查敦煌文书期间,曾拜访回鹘文专家哈密顿(James Hamilton)教授,就敦煌回鹘语文献向他请教;1990年我东访日本半年,受回鹘语专家百济康义先生邀请,和他多有交流探讨;1996年我在柏林三个月期间,又有机会与回鹘文大家茨默(Peter Zieme)教授切磋学术,曾一起比定回鹘文占卜星历方面的断简;此外,还有机会与耿世民、庄垣內正弘、梅村坦、森安孝夫、张铁山、阿不都热西提·雅库布、松井太、橘堂晃一等回鹘语学者交往,不断充实有关回鹘语文献的知识储备。近日获读阿依达尔教授有关国家图书馆所藏回鹘语文献的大著,又补充了不少新知,尤其对不同收集品之间的关系有了新的认识。
去年下半年,阿依达尔在段晴教授的强力推荐下,来北京大学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院访学,也在历史学系付马的回鹘语课上给同学们讲授心得,我忙于他事,未能聆听,今日读完他的新作,也算是补课。阿依达尔教授不嫌我是回鹘语外行,让我给他的新书作序,义不容辞,也正好补我疏漏。因略叙回鹘语文书之价值,及阿依达尔著作之学术史地位,是为序。(2022年11月26日完稿)
四 刘诗平、孟宪实《寻梦与归来:敦煌宝藏离合史》序
刘诗平、孟宪实两位的这本书源于2000 年——敦煌藏经洞发现一百周年时出版的《敦煌百年:一个民族的心灵历程》,可以看出当时两位作者的心境,是想通过百年敦煌学的历史,来诉说中华民族的心灵历程。如今,作者对内容进行增补修订,加入大量有关敦煌石窟艺术研究的内容,并补充近二十年来敦煌学各方面的发展情况,包括国际学界的交往和竞争,还以大量图片辅佐文字,使本书更加丰满。书名《寻梦与归来:敦煌宝藏离合史》,似乎也更加符合大众读者的趣味。
然而,在我看来,这是一部敦煌学学术史著作,尽管学术史难做,但这部书可以说是一部难得的学术史。两位作者在前人许多个案研究的基础上,加上自己的研究和整理,对百年来的学术史做了系统的阐述,包括敦煌藏经洞的发现、文献流散,各国探险队的攫取、豪夺,早期敦煌学研究的艰难历程,特别是中国学者远渡重洋,抄录整理敦煌文献的经过,以及最近四十年来敦煌学的迅猛发展和各国学者之间的合作与争先。虽然没有像纯学术著作那样出注,但明眼人一看就知道,他们的叙述无一字无来历,是一本相当全面又可读性很强的敦煌学学术史。
敦煌学的历程必然与百年来中国的命运联系在一起,所谓“伤心史”、何处是“敦煌学中心”等话题,是每一部敦煌学学术史都无法回避的。本书两位作者站在中国文化的本位立场之上,同时兼有国际视野与同情之理解,把个别事件放到整个敦煌学的发展过程之中来看待,揭示出当年相互之间,因为国家强弱、党派分野、脾气秉性之不同而产生的许多矛盾和纷争,用“长时段”的历史眼光去看问题,把许多事情的前因后果给梳理出来。这些方面的论述,给我很深的印象。
两位作者,孟君是与我年龄相仿的学术挚友,诗平是曾经跟随我读硕士的学生,他们对于我有关敦煌学的论述非常熟悉,私下里也有很多讨论或论辩。我很高兴他们两位在本书中采用了我的不少观点,也利用了一些我发现的敦煌学史新材料,特别是在一些大是大非问题上,他们与我的观点保持一致。我既欣慰于他们能采用我的成果,更欢喜他们在我的研究基础上又有许多推进,特别是把许多分别论证的问题联系起来,因此常常更加深入。
这本书的最终成稿和后来的增补,诗平用力较多。诗平本科、硕士先后就读于武汉大学历史系和北京大学历史系,因此对武大的吐鲁番文书研究和北大的敦煌学研究情形都比较清楚了解。毕业后他进入新闻行业,有机会多次走访包括敦煌在内的地方,增长见识,同时由于撰写新闻稿件,有很好的写作训练。读者不难看出,这本书的文风有一些新闻写作的味道,把敦煌学史上的事情一件一件地“报道”出来,用引人入胜的话语带着读者深入阅读。这本书中,不论是“民族的心灵历程”,还是“宝藏的聚散离合”,都更像是敦煌学圈外的媒体人更为关心的话题,也是沟通敦煌学专业学者与大众读者之间的桥梁。
作者让我给本书写一篇序,使我能够先睹为快。掩卷之际,把阅读的感想写出来,聊以为序。(2022年10月17日完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