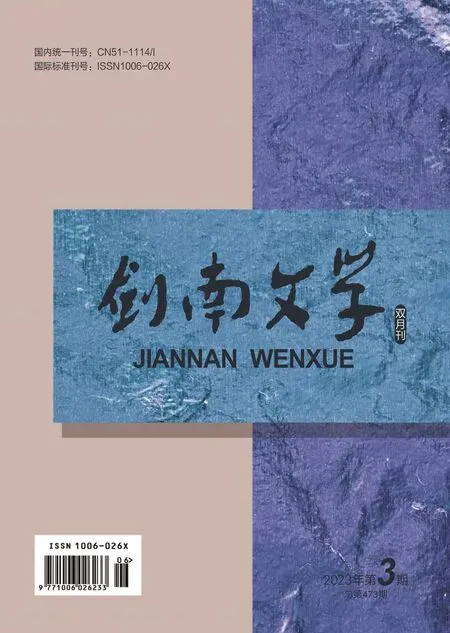金华山上拜先贤
2023-09-28李龙剑
□ 李龙剑
冬末时节,川中大地依然被浓浓的水雾笼罩着,那隐隐约约的一抹阳光,从浓雾中挤出脸来,折射出浅红色的淡淡光芒,整个世界似乎都被大雾紧紧地裹着,让人有些透不过气来。金华山,在这浓雾的紧锁下时隐时现,给人神秘和联想。
金华山距离射洪市区二十余里,位于涪江东岸。涪江系长江支流,松潘岷山蕴育,经平武,过绵阳、三台奔流而下,突然间在金华山西侧小憩,滋生金湖。清澈透明的湖水,似一把刀子,扎在了山的脚下,让陡峭的环山小径变得冷清幽静,金华山好似披上了一层迷人的薄薄面纱,显得极富灵气。
海拔只有300 多米的金华山,因其历史悠久、风景秀丽而闻名于世。早在梁天监年间(公元502 年—519 年)就建了“金华山观”,之后又经过多次重修或者培修,留下了一个很有特色的古建筑群,被古人誉为“贵重而华美”。更因为山上有一座“古读书台”,这个被称为“海内文宗” 的唐代大诗人陈子昂幼年读书的处所使金华山身价倍增,名震巴蜀,吸引了各地游人。
据史料记载,陈子昂(659 年—700 年),字伯玉,梓州射洪(四川射洪)人,唐代文学家,初唐诗文革新家。因曾任右拾遗,后世称 “陈拾遗”。陈子昂青少年时轻财好施,慷慨任侠,24 岁举进士,以上书论政得到女皇武则天赏识,授麟台正字,后升右拾遗。他直言敢谏,言多切直,触忤权贵,被降职。曾因“逆党”反对武后而被株连下狱。在陈子昂26 岁和36 岁时,曾两次从军边塞(今河西走廊张掖一带),对固疆边防颇有见地。38 岁(698 年)时,陈子昂因父老,解官回乡。不久父死,陈子昂居丧期间,权臣武三思指使射洪县令段简罗织罪名对其加以迫害,致使陈子昂冤死狱中,时年仅42 岁。诗人含冤而去了,留下的是“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的千古绝唱。
在金华山前山山麓,有一泓溪水淙淙流淌,溪上有一小桥,为独拱石桥,长约百尺,名百尺桥。陈子昂在《春日登金华山观》中有“鹤舞千年树,虹飞百尺桥”之句,故此桥又名“虹飞桥”。
穿过百尺桥,是通往金华山前山门的一条厚重石阶。站在石阶放眼一望,四周云缠雾绕,金华山若隐若现,随着太阳的爬升,才渐渐露出了一些峥嵘。石阶365 级,传说一阶象征一天,登完石阶,预示一年的祈盼就能变为现实。在金华山的前山门,有联:“天下无双景,人间第一山。”这溢美之辞虽然有些夸张,但也反映了书联人对金华山的秀丽景色和历史文化的倾倒之情。
牌坊正中“涪江保障”四个大字跃然入眼。大门两侧的华表石柱上,刻有唐代大诗人杜甫来读书台拜祭陈子昂时留下的诗作《野望》和《冬到金华山观,因得故拾遗陈公学堂遗迹》。这两首诗是照杜甫手迹的拓本镌刻而成,为行草,笔法遒劲自然,秀丽潇洒,十分珍贵。晩唐诗人牛峤在他的 《登陈拾遗书台览杜工部留题慨然成咏》一诗中曾有“北厢引危槛,工部曾刻石”之句,证实杜甫曾在射洪留题石刻。
站在山门远望,此时的太阳已经升入半空,先前铺天盖地的浓雾也慢慢地被阳光驱散了。天空变得澄澈明朗,远山如黛,被浓雾笼罩的金湖也显露出宽阔平静的尊容。金湖的东面,是一座座密林覆盖着的青山,一条高速公路从山的半山腰穿过。金湖的正中央横躺着一座孤零零的小岛,小岛名叫黑水呇,与金湖构成一体,交融成一片,似乎显得格外引人注目。
进入大门,被誉为“蜀中四大名观”之一的金华山道观便呈现眼前。靠右沿山脊的边沿建有一道墙垣,墙形为巨大卧龙,长约二百余米,龙尾从前山灵祖殿靠东的崖边砌起,沿山脊随山势蜿蜒而上,龙头却在玉京观前的忠义殿侧面,龙头倒卧,造型生动。所以山上的回文诗碑上有“龙头倒卧见高峰”的句子。
金华山山巅,是一片开阔的平地,建有长廊与几座殿宇,四周密匝的古柏松树,与鳞次栉比的亭台楼阁交相辉映,情景交融,充分验证了“天下无双景,人间第一山”的美誉。天空中,几只白鹭张开硕大轻巧的翅膀,从山下的金湖中飞来,向着山中参天的密林中飞去,转眼之间,又悠闲自得地飞向金湖中的一叶孤岛。那洁白无瑕的翅膀,从头顶上掠过,似乎将人间的尘俗和烦恼都带走了。
从山间密林中的小道穿过,浓浓树荫掩映着一栋飞檐翘角的古老建筑,错落有致,陈子昂读书台就静悄悄地伫立在这红墙黛瓦、云烟苍茫之处。读书台古朴典雅的大门前竖“唐右拾遗陈伯玉先生读书处”石碑,古坊额上有碎瓷镶嵌的“古读书台”四字。在大门两则,镌刻着清代举人马夫忂的手书门联 “亭台不落匡山后,杖策曾经工部来”。“匡山”指李白幼年读书之所,“工部”即指杜甫。杜甫因避安史之乱流亡入川,在四川生活了将近10 年。宝应元年(公元762 年)11 月,51 岁的杜甫沿涪江乘舟而下,来到射洪。杜甫与陈子昂,同为唐代著名诗人,在万紫千红、流派分立的唐代诗坛,一个是登上高峰的旗手,一个是筚路蓝缕的先驱。杜甫虽比陈子昂晚生了近五十年,但他对这个唐代诗歌的开山鼻祖十分仰慕,倍加推崇。在他年老体衰的晚年,还拄着拐杖登上射洪金华山瞻仰陈子昂少年时的读书之所,去射洪武东乡拜谒陈子昂的故宅,留下了感人至深的诗篇,为一代雄才的不幸遭遇发出深沉的慨叹。
读书台原名读书堂,是陈子昂少年时代读书的地方。他“年至十七八未知书,尝从博徒入乡学,慨然立志”。这里所说的“乡学”,是当时的射洪县学,校址即在金华山观后。但读书堂不知何年倒塌湮没了,直到清道光十年才由兼掌射洪的府尹汪霁南移建于此。陈子昂在金华山苦读三年,博闻强记经史百家,为后来革新诗歌打下了厚实的基础。
进入读书台,感遇厅便映入眼帘。这一刻,感受到里面那庄严肃穆的气氛,似乎害怕踏入那座被人们瞻仰了千年的神圣殿堂。
读书台内,清风徐徐,翰墨芳香,让人如入浩瀚书海。在沈鹏先生“三唐冠冕”匾额下,便是陈子昂汉白玉全身塑像,翩翩少年手握诗卷,气宇轩昂,凝目沉思,一身白玉正象征诗人一身清廉、正直。正面的板壁刊刻着陈子昂的生平,回廊满是诗人不朽的诗文。此情此景,眼前仿佛呈现出当年诗人在金华山上潜心求学的模样,仿佛闻到了从古读书台上飘来的浓浓墨香,仿佛聆听到了那朗朗的读书声音,让人心底里泛起阵阵仰慕之情。
陈子昂一生创作诗歌120 多首,其中有《感遇》38 首,《蓟丘览古》7 首及《登幽州台歌》等,他的主要著作有 《后史》《江上人文论》《奏议》《陈伯玉集》(10 卷)等。其代表作《登幽州台歌》被誉为古典诗歌中的“千古绝唱”。他的作品虽不太多 但他为唐诗的发展所起的开拓性作用却是巨大的,影响是深远的。他一生在矫正时政弊端的同时,又自觉地肩负起了革除诗歌弊端的重任。为了扫除齐梁以来形成的诗风,他从理论和写作实践两个方面做了英勇卓绝的斗争。他看到初唐诗歌沿袭六朝余习,风格绮靡纤弱,挺身而出,力图扭转这种倾向,强调兴寄,提倡诗歌要继承《诗经》 “风”“雅”的优良传统,要有感而发,不作无病之呻吟,注重现实内容和刚健质朴的表现形式。他所创作的120 多首诗歌,具体实践了他自己的诗论主张,以其清新的语言、丰富的感情、爽朗刚健的风格,一扫齐梁及初唐宫廷诗人颓靡的诗风,为唐诗的健康发展奠定了基础,因此被李白、杜甫誉为“麟凤”“雄才”,被王适奉为“海内文宗”。现代史学家范文澜称他为“唐古文运动最早的奠基人”。
在读书台的正北方向,“明远亭” 屹立在悬崖峭壁之上。凭栏远眺,悬崖下宽阔的金湖,群山倒映,波光粼粼。一群白鹭,时而临空飞舞,时而扎入水中。蓝天上,白云在天空中自由地飘荡,好似一副精妙绝伦的山水画卷,寄托着人们对先贤的无限敬仰。
“兰若生春夏,芊蔚何青青。幽独空林色,朱蕤冒紫茎。迟迟白日晚,袅袅秋风声。岁华尽摇落,芳意竟何成……”在远眺之时,先贤陈子昂的《感遇》诗,仿佛又从远古的盛唐飘来,让人回味无穷,感慨万千。
山不在高,有仙则灵。金华山,虽不算高,但子昂文化、诗酒文化古今相融,在这里交织、碰撞,滋生了川中深厚的诗酒历史文化底蕴。
站在金华山上,望着那些满目的千年古柏松林和青山绿水,心底升起对子昂先生的仰慕之时,又忽感自身的渐愧和缈小,眼眶里更是不知不觉地有些潮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