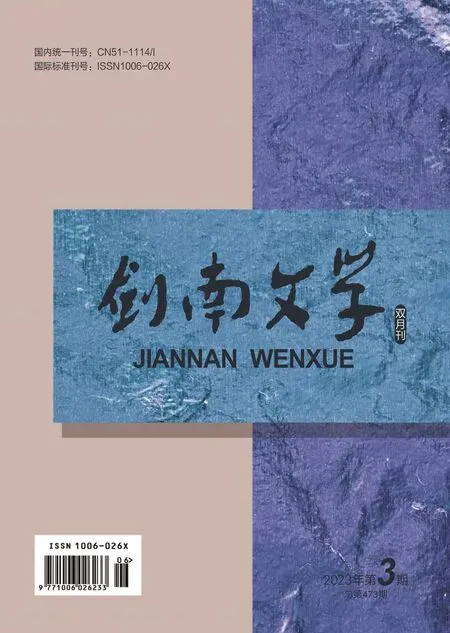野花与少年
2023-09-28朱盈旭
□ 朱盈旭
1
彼时少年。光阴里野花灿灿,古老的小村分明是清新得犹有露水香的乡野风情画。
穷孩子也爱美。人家的姑娘有花戴,爹爹钱少买不来。可是野花遍地是呀,想扯哪朵扯哪朵。干巴瘦没返青的柳条子似的土妞们,互相插戴起来。
哪哪都能戴。旧衣襟子上,细脖颈上,枯巴黄的辫梢子上,五颜六色的碎布头拼起的小书包上……明晃晃,邪魅魅。七七八八眨着野性的眼睛,一点也不老实。乡下野丫头似的。使劲嗅一嗅,似乎一点香气也没有,一股青腥气。
那些野花就像我们这一群衣衫粗朴的乡下丫头,没有体香。哪有淑女的样子?十一二岁,疯疯癫癫,走没走相,站没站相,粗拙枯涩,不显眼,像脚踩腚坐的野花一样。除了头上有两根拧巴得像麻花的小辫子以外,小胸脯子更是平板得瘦骨根根分明,和那群猴小子有啥区别?
野花的香气,被大野浩荡的风打了劫,被村子里鸡鸣狗跳的喧闹打了劫,被劫落进厚厚的泥土里去了。
上学的路上,女孩子与男孩子之间常常有一场场小“恶战”。起因是鼻涕邋遢瘦猴似的小小子,嘲笑满头戴花的小妮子,围追堵截着喊“花大姐”“傻大妞”。
我带着她们几个,晃着满头缤纷的花朵,挥舞着细瘦的胳膊,小书包虎虎生威,直把二柱子他们几个打得落花流水,抱头鼠窜,狼狈逃进小土路下的泥水沟里。他们噼里啪啦踩着黄汤似的塘水逃跑,一手提着鞋子,一手拖拽着书包,湿答答的黑屁股上像兜着一滩黄腻腻的屎。
我们几个小丫头子,辫子散了,花也落了,一副钗横鬓乱的样子。小书包做武器,挥舞得呼呼生风,那叫一个爽!嘎嘎疯闹,笑疼了小肚皮。
蓦然惊醒,哑蝉似的闭了口。低头看看,新做的小布衫子撕裂了长长的口子。沮丧在垄上吹来的大风中猛烈飘荡,像战败的旗子。小书包只剩了空空两张皮,里面的书本、铅笔,还有娘给烙的饼、煮熟的鸡蛋……都被那些猴小子嘻嘻哈哈捡拾了,囊括而去……
收拾残花破衣,硬着头皮回家挨打吧。娘手中那刚刚发芽的嫩柳条子,一定小鞭子似的挥舞个得心应手,鞭鞭野花开。篱笆外一定藏匿着很多双得意的小眼睛,幸灾乐祸的小小子们,窃笑如狗。
我们有小野花般蔓生自愈的野生能力。乡下丫头,绣花鞋也穿出歪瓜裂枣的粗陋脾性,哪有半分女孩子的娇嫩?记吃不记打,小土狗一样的没心没肺,不知人间忧戚,更不知“端淑”二字。瞧那一个个脸蛋,黑红饱满的,像蜜汁充溢的野生桑葚子。白黄瘪干的,像未熟的青杏晒半枯。
彼时少年,虽然活得粗糙,寒酸穷苦,却因了有野花的殷殷陪伴,那日子也荡悠悠地,过得舒缓有兴味。那般无邪,心上纯净。
小野花们,以它们的点点花色,琐琐碎碎,演绎着民间的热闹与生动。拙朴莽荡的绿色中冒出来的点点猩红与蓝白,多么野趣与朴实!是人世间最素朴干净的饱满,像小民的日子。
黄脸蛋,红脸蛋,野花般篱前晃一晃。躲躲藏藏的小身影竟生出几分羞涩来。
四奶奶的老屋里来了客人。一张胭脂红的嫩脸蛋照亮了黑篱老宅。
城里来的女孩,像四月的蔷薇,唇红齿白,红裙子,黑头发,白白的小皮鞋子,冲门口的穷丫头们笑一笑,脸上的红云重重叠叠洇开来,像打翻了胭脂盒子在水中。
我们都看傻了,一个一个被四奶奶牵着进了门去,木门槛绊了脚,踉跄木呆像小土狗。惹得那女孩掩着嘴低低笑。
红裙子女孩送给我们每人几颗水果糖。花花绿绿的玻璃糖纸,裹着甜甜的糖块。拆开,放口里,淡淡的味,像娘种的薄荷。
我第一次觉得那些野花呀,原来是有着独特香味的。那是一块水果糖的味道。城里人拿野花的香味做了花花绿绿的水果糖。平日里我却对它们熟视无睹,甚至弃之如敝屣。彼时,心头泛起一丝丝愧疚,对野花,有了生平第一份歉意。
她给我们背唐诗,讲故事,唱歌,细嫩的嗓音清新得像杏花边上的一缕白云。她的小手好白。忍不住摸一摸,像花瓣一样柔滑。指甲上泛着微微的红,像涂了一层花汁子。再低头看看自己的,又干又瘦像鸡爪子,大力一撅嘎巴断。不免怯怯插进阔荡的衣袋里藏起来,几分自卑。
女孩给我们跳舞。一转身,一跳跃,身上旋起一股香气。我贪婪地闻一口:咦!居然是熟悉的味道。到底是小野菊呢,还是野鸢尾?不,甜甜的,清爽的,可不就是红蜀葵的味道么?
原来,小野花也有香气。像乡下的女孩子,也各有体香,只是那般幽微,都被莽荡的季风和柴草的焦香给不容分说地一把掳了去。仔细闻一口,还是暗藏一二分各自的香气,另外那八九分,都是泥土香。
泥巴的小村,泥巴的娃娃,土里长出来的野花般的穷孩子,自带属性,扔进人海里,还是能被故乡认领的。只要故乡不抛弃他们。
故乡怎么会抛弃自己的孩子呢?就像娘与孩子,就像土地与野花。铲了,还会生发。撵了,打了,还会回来。就像故乡那句老话:家鸡打得团团转,野鸡不打满天飞。我们都是贫穷小村子的小家鸡。我们还是故乡不嫌家贫的小土狗呢。狗不嫌家贫,子不嫌母丑。
红裙子的女孩,着实让我们这些疯丫头们自彼时起,知道了自己这趟人间的真实身份——不折不扣的女孩子。野小子,假小子,都是诨号。我们虽然小野花一样好养活,不精致,给一把泥土就摇头晃脑抽枝开花,但我们毕竟是花呀!野花也是花。村人的眼里沦为野草也是花。小野花有小野花的卑微,小野花也更有小野花的倔强,像乡下土妞。
在野花与少年的时光里,有谁知道他们与它们各自的不甘与惆怅?
从彼时起,我不再和奶奶犟嘴,不再欺负瞎大伯的羊羔,不再摘三爷爷家的青杏子挤水泡玩,不再和那群猴小子打架,不再把娘新做的小布衫上树挂破……
红裙子的女孩回城里去了。我能想象出她的样子:勤奋读书,斯斯文文地唱歌,脸上手上搽红红白白的雪花膏,小白皮鞋一尘不染,每天清脆地敲击着干净的柏油马路去上学,身边是鲜艳的月季与蔷薇。那些花朵是人工栽植的,带着文气与贵气,有城里女孩子一样的书香与端雅……
摆一摆小脑袋,我依然是野花一样的乡下穷丫头。红裙子有红裙子的快乐,小布衫有小布衫的富足。我小野花一样在故乡的黄土地上粗茁野趣地生长。盛开的野花和明朗的日月,是我们的,美得摧枯拉朽。野花不卑,也是我们的。它们紧紧和故乡的土地缠绕在一起,迅速蔓延,很稳妥地开花结籽,向暖而生,从不知妥协与畏缩,像世世代代瘦瘠而坚韧的村人。
放学的路上,淋着滂沱的大雨。突如其来的大雨总把我新穿的小布鞋和厚厚的泥土揉面似的搅拌在一起。我湿淋淋落水小狗似的拖着两脚黄泥回家。
娘一迭声地喊着乖乖,把我从雨帘里扯出来,三下五除二粗暴地扒去我的湿衣服,褪去我分不清鼻子眉毛的泥巴鞋,把我摁进热气腾腾的大木盆里暖着,洗着,口里气恼地直骂我是榆木脑袋,被驴踢了的脑壳,咋就不知道找破瓜庵子躲一躲雨?直着脖子被冷雨浇个透心凉……
我窝在腾腾热气里傻傻笑,心里是欢喜的。她每一句骂声,我都当成她简单粗暴的爱。她是爱我的,虽然我被她兜头的热水浇得睁不开眼睛,喘不上气。
娘粗糙的手掌在我小身体上刷洗,淘草缸似的拉搓,生疼。她继续气咻咻:女孩子花一般娇贵,知不知道?能和那些小小子一起疯着浇冷雨么?会种下病根的。你小妮姑姑不就是身上来月信时暴雨里浇透了,得了女儿干,死了……
她手不识闲,嘴也不识闲,唠唠叨叨,骂骂咧咧。我却低头看见水盆里漾出一团红来,丝丝缕缕荡漾开了,像开了一朵红睡莲……
自从那日来了月信,我突然变得很女孩起来。
很女孩起来的第一感觉,就是那种爱美之心,从瘦瘦的小骨头里挺起腰身了,探头探脑,而后一发不可收拾。
2
成了乖女孩子的第一件事,就是爱上了花花朵朵。
在乡下,野花遍地是。最富足,最莽荡,最大的家族,就是野花。
老屋前后,篱前篱上,大野里,沟渠上,都是。甚至牛蹄子下,猪嘴边,都是。它们不挑环境,不讲条件,不多占阳光,有巴掌大的空地,都行。有一种兵荒马乱的稠密。有一种颜色绚烂的感动。
野花的名字美得很。带着泥土香,带着草木香。像从《诗经》里走来的新妇,或是从南歌里走来的女孩,也许是从明清的瓷器上步下来的侍女。小门小户的,却美得不像话。
紫花地丁,一年蓬,婆婆纳,野老鹤,醉鱼草,田旋花,指甲花,地雷花,蜀葵……
红红紫紫,粉粉白白,蓝蓝碎碎。葱绿的,玫红的,月白的……小朵的花,纤细的蔓,空气里仿佛也已经繁花满枝了。乡下的女孩子像一只只调皮的小蜜蜂、蒲公英、雀舌草、点地梅……都扇着翅膀来瞧一瞧。
爱花爱朵的女孩子们,跑去扯。哪里是采花呀!没有那般风雅,没有那般怜香惜玉。分明是大把大把地掳掠。手掌上浸染了它们折断了的绿茎子流出的饱满汁液,几天都洗不掉。个个成了绿手掌的小妖。
采了花做什么?依然是戴花呗。
从前,编成明晃晃的花环,戴在头上,套在细脖颈里,大摇大摆满村子蹿,像小花妖,更像大观园里的俗气婆子刘姥姥,明黄红紫插满头。惹得篱前的妇人常常捉到跟前去,手指拨弄着花花朵朵,讥嘲地问一句:戴了花了,是要出嫁了么?小相公是哪家的?给我家二柱子做媳妇罢?婶子我可疼你了。中不中?
小丫头挣脱了身子,逃到远处,回头狠狠啐一口:呸!老母猪上树——不可能。等着瞧,看我咋收拾你家宝贝蛋!粗呖呖一张小恶嘴,匪里匪气像小女贼。凶狠狠拽下头上鲜嫩花朵,小脚尖愤愤然踏了个香消玉殒。
妇人大骇。破鞋底子遥遥扔过来:疯丫头子,野丫头,疯疯癫癫没谁要。你再敢挠花俺二柱子的脸,瞧我不把你小鸡爪子剁下来……
如今呢?依然戴了花。却偷偷摸摸小贼般在旧木窗下翻出娘的小镜台,指尖先点一点白白香香的雪花膏,再点一点胭脂红,在小掌心里细细轻轻地化开,一点一点,对着小镜子,把一张小脸涂抹得千里莺啼绿映红。最后斯斯文文地在辫梢绑两朵沾着露水的红凤仙,悄悄搭在胸前。低着头在篱笆院里溜着墙根走,生怕撞见爹爹和哥哥。
天不怕地不怕满头戴花的野丫头,不知怎么就突然知道了世间有“羞涩”二字了。
爹爹扛锄归家,睁大诧异的眼睛,回头看了看怯静如猫的小丫头,不解地悄声探头去问娘:六丫头这是咋啦?莫非生病了?这般文弱。娘在灶间忙活,眼皮子也不抬,鼻子里不屑地哼一声:哼!作妖呗!
出门撞上二柱子他娘。怕鬼有鬼嘛!低头,碎步,悄没声息,脚步像长了小白猫的肉脚垫般软乎。那妇人惊愕,走出老远,尚频频回头,口里喃喃:奇了怪了,这不是老朱家的六丫头么?这是被她娘打坏了脑子咋的?傻了?呃,怪可怜见的。
女孩与男孩的关系,也突然变得微妙起来。
从前,一起摔跤,滚在一起,鼻涕汗水蹭到彼此脸上的野孩子,突然就有了距离。特别是身体,手也不拉了,也不捉迷藏时抱在一起躲麦秸垛里了,更不搬着一条腿跳着玩斗鸡互相碰撞了……
村子里突然就安静了许多。只有各色小野花喜眉喜眼地安安生生地开。再没有男孩女孩扯旗子扮山妖大呼小叫追逐撕闹了。大人们不用扯着嗓子喊忘了吃饭、睡觉的野孩子了。也不用急头白脸地扯着自己挨打的小小子去疯丫头家告状了。小羊羔们也不恐惧被绑嘴了,咩咩甜叫像撒娇。最高兴的似乎是那些小野花们,再不用担心小花贼们没轻没重、不会怜香惜玉而辣手摧花了,它们可以在晚风中像模像样地扭动花梗与花朵,眉清目秀地进行晚妆了……
女孩不再和男孩打仗。男孩子开始让着女孩子。
男孩子偷偷给女孩子提着上学放学时沉沉的书包。女孩子在前面放开手走路,开始发育的小胸脯子鼓鼓的,像偷揣了两片小馒头。真是羞死人了,忍不住哈了哈腰。一低头,一股清微微的体香从脖颈里冒出来,暖香香地扑着脸去。原来,爱洗澡了,而且换下来的小布衫子自己用香胰子洗了,死活拽着不让娘拿去塘里浣洗。因为亲眼看见大灰鸭大白鹅那些嚣张的家伙翘着屁股在塘水里拉了屎呢。也特别爱惜起来那小布鞋上绣的白的杏,红的桃。走路一跳一跳的,小白兔似的专挑那硬实光洁的土路走,小心地绕过坑坑洼洼的稀泥水。
娘与西篱东篱的妇人们悄悄说:你说怪不怪?假小子突然就变得文气了。从前是踢岔葫芦弄岔瓢,不知糟蹋了多少双好鞋子呢!现在可是花儿朵儿的都爱惜着呢!
可不是么!她们纳着鞋底一脸喜气地笑。树大自然直,妮子总比小子好拉扯,大了,就腼腆了。彼时她们也从庸常的世俗里开溜出来,唠嗑,话家常,若没有身边与脚畔热闹的野花陪着,又哪得如许的欢喜和舒心!
紫花地丁在唠嗑的妇人们脚边悄悄铺开一块紫色的花毯,小蝴蝶似的小小花朵讨好地靠近黑布裤管处裸露的脚踝。那肤色一片阳光色,一点也不白嫩。
写了作业,跳绳吧。两三个女孩子摇着粗大的草绳,那是爹爹春天刚结的,透着清新的草木气。娘在檐下挑粮食,胳膊压在簸箕里,眼睛望着十一二岁的闺女,目光温柔,像花香。
指甲花开得茂盛。红红的,重瓣,一朵一簇小火苗。我们收了绳子,气喘吁吁地跑过去,你一朵,我一朵,嘻嘻哈哈地给对方插在扣眼里,绑在辫梢上,别在耳朵后。软红的小布衫子,泛着潮红的汗脸蛋,小指甲花一般喜气。
娘远远喊一嗓子:夜里包指甲吧?趁着花开得正好,后半晌我掐些麻叶去。
月亮白着脸盘子从东边二奶奶的篱笆上爬上了天空。
我们几个丫头在月光地里包指甲,个个是小巧匠。终于安安静静、切切私语地做了一件女孩子的事:舂花汁子,捣明矾,包指甲,缠麻线。十个手指头,个个都穿上了臃肿的绿麻衣,悄悄各自回屋睡了。一夜无梦,生怕做梦粗暴蹭掉了厚厚的指甲包。
次日,小鸡子刚打鸣,野鸟刚扇翅,就迷迷糊糊起了床。急不可待掀掉萎了颜色的绿麻叶。呀!凤仙花开在了指甲上,明艳艳的十朵花瓣儿。顿时闪掉了眼睛里的睡意,水洗般地盛满清澈的惊喜。
小妮子们挤在老枣树下写作业。一张旧木桌腿脚不稳,挤挤挨挨像一窝黄喙的小鸟,亮着鲜艳艳的爪。
写一会,低头瞅一眼红指甲,只觉有花香漫上心头,有一股细细的书香与雅气攀上眉头,心里莫名一片帆似的鼓胀起喜悦与冲动来。一种名字叫理想的东西悄悄膨胀起来,小野心也在旧衫子里挺起了腰身。
突然,有一种走出泥巴小村的勇气与冲动,脚底下野花似的,明晃晃生长起来。不想做小野花一样的泥巴妞了,向往那种村外的生活。那是一种怎样的生活呢?谁知道呢?反正与眼下的一定不一样。是红裙子女孩那样的城市生活么?可以脱离繁重的垄上劳作,去干净体面地上班。去做手执教鞭的神气教师,做白衣的医生,做黑衣的法官,做英气的公安……像彼时电影里的那些人一样。长大后,走出长满野花的泥巴故乡,去做自己喜欢的事……
彼时,花妮子她们也目光迷蒙,咬着小笔头,似乎各怀心事。半晌,花妮子说:城里的女孩也包指甲么?真想给她们也染红指甲、蓝指甲、绿指甲。她们的手多白多嫩多好看呀!染了花色的指甲,一定更好看……
多年后,花妮子果然实现了少年时的理想。她在城里开了美容院,连锁的,手下有一批又一批凤仙花般美丽的女孩,她们不仅给城里的女孩们做蔻丹,还有更多更好的美容项目。
野花,成就了野花般女孩的梦想。花妮子是故乡走出的最美的花朵。
后来,还有喜欢画野花的花枝子,喜欢拿野花瓣做汤药的花梗子,喜欢拿野花当学生扮老师的六丫头,她们最终都把心中的理想,野花般灼灼地沐浴着故乡的阳光,吮吸着故乡的雨露,汲取着故乡大地最朴素的养分,茁壮成长,长成了各自最美好最理想的模样。她们分别成了画家,中医,教师……
还有那个偷偷和二柱子扮新郎新娘的花妞。当初,少年时,我们把小女孩打扮成羞答答的花媳妇,头上戴了满头的红蜀葵,手腕上戴了紫花地丁的紫花串,小绿布衫上挂了婆婆拿小花朵串起的蓝花环。扯起长长的红布条,和木讷呆萌的男孩拜天地。天作房,地作床,簇簇野花作伴娘。彼时,虽是少年的游戏,却美得不像话,像远古时代的童话。穷孩子是童话里的公主和王子。因为,彼时的少年拥有那么富足欢喜的野花。花开如笑,童话不会老,不会褪色。长大后的他俩,果然成了夫妻,甜蜜得光阴都能拧下花汁子来。
前些年回故乡,在白发如雪老神仙似的二柱子他娘的老宅子里,遇见了当年的花妞与二柱子。中年的他们,在故乡承包了好多亩土地,打造了一个极大极大的芍药园,成了药材基地,成了新农村旅游景点。
少年的野花,成就了一对芍花夫妻。
彼时。故乡是贫瘠的,但野花永远繁华。野花与少年,都带着野草的霸气和花朵的清甜。
野花,点亮了贫瘠的少年时光,也点燃了少年心里那簇理想的火焰。野花与少年,虽然长成了各自喜欢的模样,但根始终扎在故乡的土地里,所以,总有一脉草木香,总有一茎泥土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