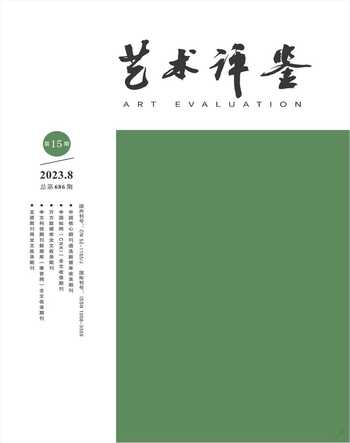广西三江侗族大歌的文化记忆建构
2023-09-20张雅贤
张雅贤


【摘 要】在长期的生产实践和社会实践中,侗族人民创造了侗族大歌,研究侗族大歌的文化记忆建构,理解侗族大歌包含的文化符号和集体记忆,有助于理解民族民间音乐对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意义。从“文化记忆”的角度来看,侗族大歌的建构可以从“物化表现”“身体实践”和“政策支持”这三个层面来分析。侗族大歌作为一种非物质文化遗产,它的实质是一种文化记忆,以文字、影像和建筑为载体,呈现出文化记忆的塑造性特点,起到存储、激活和回忆的作用;技艺、仪式和组织活动,体现了文化记忆的能动性,具有沟通、重构和获得族群认同的功能;在政策、规划活动等方面,反映出文化记忆的制造性,具有规范、引导的作用。
【关键词】文化记忆 侗族大歌 文化遗产
在漫长的生产生活和社会实践中,侗族人创造了大量的民族民俗文化。侗族人擅长唱歌,侗族人居住的地方被称为“诗的家乡,歌的海洋”。在许多侗歌中,口传心授为其主要的传承方式。扬·阿斯曼认为,作为一种文化体系的文化记忆,其存在的意义是超越个人的,因为记忆不仅仅有文本、图片和影像,还有很多的文化载体。人们对现实世界的持续建构和诠释等都是建立在对过去的反思之上,唯有如此,民族和文化才能代代相传。研究三江县侗族大歌的文化记忆建构范式,可以拓宽民族文化研究视野、丰富中华民族文化内涵。侗族大歌作为一种非物质文化遗产,它的实质是一种文化记忆,以文字、影像和建筑为载体,呈现出文化记忆的塑造性特点,起到存储、激活和回忆的作用;技艺、仪式和组织活动,体现了文化记忆的能动性,具有沟通、重构和获得族群认同的功能;在政策、规划活动等方面,反映出文化记忆的制造性,具有规范、引导的作用。基于此,笔者以分析文化记忆理论优势为起点,以三江等地侗族大歌非遗保护的实践为基础,以侗族大歌文化记忆建构传承特性的塑造性、能动性、制造性三个角度进行分析。
一、塑造性:侗族大歌的储存与激活
文化记忆理论提出,对其进行控制的方法是建立符合身份特征的、具有一致性的、结构性的符号体系,包括文字、图片、建筑、宣传等,这些符号体系组成个人、群体间的文化认同基石,从而构建出他们的行为方式和价值标准。这个符号体系就是储存记忆和功能记忆的物质载体,也就是文字、图像和地点。文字是永生的媒介,文字、图片、身体、场所等存储媒介是文化记忆的主要载体,技艺、仪式、心理等互动方式是获得文化记忆的身体实践。侗族大歌的文化记忆建构呈现出演唱与文本两种形态。“汉人有字传书本,侗族无字传歌声;祖辈传唱到父辈,父辈传唱到儿孙。”侗族大歌以其特有的唱腔、独特的组织方式,继承了侗族悠久的历史文化,侗人美妙的歌喉将诸多优良的文化传统、生活习俗、社会礼仪等世世代代流传下来。侗族大歌既是一种音乐艺术,又是侗族社会结构、婚姻关系、文化传承、精神生活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在社会史、婚姻史、思想史、教育史等方面都具有很高的学术意义和研究价值。
(一)语言符号传递价值规范
侗歌是侗族人的百科全书,通过口口相传的模式传承下来。在纪录片《指尖上的传承》中,侗家人贾福英靠记忆和请教老人,用汉字将侗族大歌记录下来。侗族尊崇礼仪,注重道德教化。侗族大歌最突出的文化特色就是“以歌育人”,三江侗族大歌因其文化内涵不同,可以分为伦理大歌、叙事大歌、声音大歌、柔声大歌、鼓楼大歌、童声大歌、戏曲大歌、社俗大歌、混声大歌七种。内容大多歌唱自然、劳动、爱情及友情,如:《蝉之歌》《松鼠歌》《三月歌》《叹惜青春歌》《父母恩情歌》等。这些大歌体现了侗族在不同时期的生存状况与精神风貌,如叙事大歌,讲述了远古时代的神话,以及先辈们对自然、历史、生产、生活的开拓探索,如今的侗族人民明白幸福生活是先辈努力的结果,通过赞美祖先和民族英雄,在潜移默化中对青年人进行教育,传递价值规范。
1.传承历史
叙事古歌是流传最久的歌种之一,描述了侗族先人开天辟地、不畏艰辛的精神品质。以歌传史,侗歌是侗族民族精神与理想信仰的重要载体,也是侗族人民世世代代生活的真实写照。最古老的侗族歌谣也承载着侗族的历史,比如“开天辟地”“姜良姜妹”等侗族的传奇故事,在今天仍然以叙事大歌的形式被广泛传播着。侗族民歌《侗族祖先哪里来》中,对侗族先民的起源进行了较为详尽的描述;而侗族迁徙的史诗《祖公之歌》,则生动描绘了侗族长期的迁徙历程,展现了侗族祖先不畏强权、战天斗地、努力创业的壮丽画卷。这种对侗族历史知识的描述就是以口头传唱的方式,叙述其历史发展过程中的不同时期。一代又一代的侗家儿女叙唱与展演,使得他们的民族在歌声中共享这一历史记忆,并共同形成了他们的民族凝聚力和民族认同。
2.载道育人
“全民参与、全民学习”的侗族大歌社会化程度高、思维引导能力强,能充分发挥侗族大歌承载做人道理,以及对后辈子孙的教育功能。
(1)抒发男女之情,表达爱意
三江地区有七十多条大小河流纵横交错,就连地域名字也是来源于榕江、浔江、苗江三條大河。榕江河水清又清,这婉转动听的歌声仿佛经过江水的洗涤纯净美好,又像河上的波浪,时而轻柔荡漾,时而浪花滔滔。河边不知年岁的老榕树相依而生,奇特的姿态真像一对情人“生死相恋”,引来一阵感怀。这江水隔断了与阿哥相见的路,无奈又不甘,只能在老树下唱起思念的歌,和着水车的吱呀吱呀、流水的哗啦哗啦,说不尽的忧伤。若清风有情,快把歌声和爱带到对岸,带到阿哥身边。
榕江河水浪滔滔,
两岸树木高连天。
妹想连哥隔江水,
隔水难与哥相连。
何时能与哥成对,
共盆洗脸心才甜。
——节选侗歌《榕江河水浪滔滔》歌词大意
(2)教育人们珍惜时光和热爱生命
珍惜美好时光,热爱生活是侗歌所表达的希冀之一。侗歌主要内容是歌唱自然、劳动、爱情、友情,生活的美好在侗歌歌词中生动展现出来。
我们的声音虽不比蝉的声音好,
生活却让我们充满激情。
歌唱我们的青春,
歌唱我们的爱情。
——节选侗歌《蝉之歌》歌词大意
(3)劝告大家尊敬父母,学会感恩
孝顺父母,学会感恩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侗族大歌中蕴含着教育侗族儿女感谢父母养育之恩的深刻内涵。
嗨~兄弟
你还记得吗
第一次走路是父母教会你
第一次说话是父母教导你
第一次唱歌跳舞是父母教会你
第一次唱故乡歌曲纳里西莫也是父母教会你
——节选侗歌《父母恩情歌》歌词大意
(4)引导人与自然和谐共存
侗族人世代都在努力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大自然是侗族大歌创作的天然源泉,侗族大歌的和声模拟自然声音,是侗族大歌的一大特点,比如:鸟叫声、虫鸣声、溪流声等,侗歌表达了人与自然、人与人的和谐旋律。正如陶渊明所谓的“桃花源”一般。三江侗族八江镇布央村的居民在采茶的时候,唱着这样的歌。
布谷催春把种下,
我们的劳动,我们的爱情,
都等到秋天里收获。
布谷,布谷,
河边的柳树重发新芽。
——节选侗歌《布谷催春》歌词大意
(二)非语言符号引发情感共鸣
地点是记忆的主体,也是记忆的载体,在文化回忆空间建构中,地点非常重要,可以让回忆被确认、证实,且非常持久。侗寨是族群的社会组织基础,也是侗歌传承的重要文化载体,侗族人民在日常生活中的歌唱活动,既是一种与集体文化生活相结合的活动,又是传承民族传统的一种群体文化行动,更是人们了解自己所在社会和文化的一种方式。从认知功能角度看,侗族大歌在个人和群体(侗寨)两个层次上都起到了“大歌”作用。侗族歌谣对于个体而言,有着陶冶情操的功能,个体可以通过歌谣实现自我认知,主动参与到群体(侗寨)文化生活中,拥有文化归属感。对于群体(侗寨)来说,侗族大歌具有团结民族意志、规范民族行为、树立民族理想、凝聚民族力量等作用。侗族大歌在侗族生活中有着共同的认识作用,这是侗族大歌在社会生活中的共性。相似的生活方式导致侗族大歌在认知功能方面产生趋同性。处于广西三江的侗寨,侗族大歌的传唱已经成为侗寨的一种特色文化,侗族在集体文化生活中确立了自己的文化认同和文化价值。
克拉克·威斯勒认为:“部落文化的个性都会在其最独特的特质中显示出来。”“侗家有三宝,大歌、鼓楼、风雨桥”这句谚语也佐证了这点。侗族大歌综合体、鼓楼、风雨桥等都是侗族生活状态的最直观反映。侗族人每日在侗寨的鼓楼、风雨桥上载歌载舞,一个侗寨里有一到十多个侗族歌舞队。每年农历的“二月二”,梅林乡的侗族“千人舞”也是一种独具特色的活动,梅林乡由此享有“中国民间文化艺术之乡”的美誉。
图1 侗族大歌与传唱地点(鼓楼、风雨桥)关系图
二、能动性:侗族大歌的认同与传承
作为“社会认同”的文化记忆在唤醒和建构中,个体或组织起到了关键作用,具有能动性。文化记忆始终拥有专职承载者负责传承。“身体”是除文字、图片、场所外的重要文化记忆载体,展现了技术、仪式、心理的互动,这些互动方式是其“潜在”实现的过程,是其建构与获得文化记忆的实践,是文化记忆的支撑,而功能性记忆则反过来又能转换成存储记忆。侗族大歌的传播方式主要有:师徒传承、亲子相传、群体传授。这些传播方式严格上来说都属于人际传播范畴,都需要人以口头授艺的形式进行教学与传播。所以侗族大歌能否得到有效存续,关键点在于民间传承人的“在场”和“主动传授”。
图2 侗族大歌传承方式示意图
侗族大歌對三江侗族社会起到了共通语义和群体象征的身份识别作用,具有教育和传承功能。虽然侗族也有自己的语言,能够在族群中交流沟通,但是侗族却没有自己的文字,因此,侗族需要采取积极的措施传承自己的民族文化,例如通过歌曲、舞蹈、音乐等不需要文字记录的载体进行传承。在众多选择中,“歌”成为侗族人传承民族文化载体的不二之选,侗族大歌成了侗族进行文化传承最重要的途径。“大歌”传统不单单是个人修养、男婚女嫁、家庭婚姻,以及不同年代和同性、异性之间建立适当关系的重要方式,更是村寨关系协调和相互认可的基本纽带。在村寨之间,通过“集体拜访”和“定期拜访”,促进两个村寨人之间友好互动交流,从而促进异性同龄人之间的友好往来和婚姻关系。从这个角度来看,正是侗族特殊的生产和交流方式孕育了独具特色的“大歌”文化。假设“侗族大歌”文化表达和外部特征受到自然因素影响,那么侗族大歌文化内容和本质就可以由社会和历史因素来决定,便是“以歌为生,以歌为媒,与歌互动”。根据田野调查,“侗族大歌”传承断裂,后继无人,这是导致其传承走向消亡的一个重要原因。为此,国家每年都会专门拨款,给全国各地会唱侗歌的歌师,让他们集中精力去传播侗族大歌。作为一名精神领袖,歌师具有很强的民族认同感,而国家级传承人的地位和津贴发放更加强了这种认同感。侗族大歌的优良传承环境与歌者的领袖作用,以及侗族人民强烈的族群认同感密不可分。
“身体可以通过养成某种习惯来巩固记忆,并通过强烈情感力量使回忆得到加强。” 侗族大歌的保护与传承重点在于“人”,侗族大歌的传承者、管理者和当地居民是侗族大歌的身体实践者,以各种文化交流形式,持续唤醒、建构、传播着个人记忆,从而使个体记忆与团体文化相结合,将个体记忆扩大为群体记忆,从而影响到文化遗产的继承方式与发展方向。因此,歌唱侗族大歌,能让侗族人民意识到自己的身份,是增进文化认同的实践,也是侗族大歌得以传承的文化基础。
三、“制造”性:侗族大歌的增殖与重构
“记忆并非固定不变或者不可改变,而是对现实的表达,经过主观构建以符合当前的情况。”阿莱达·阿斯曼认为,文化记忆是“建立群体身份的连接结构”,但是文化記忆并不能自行产生,须依靠媒介和政治,并在制度性层面上“受着有目的的政策控制”。2009年,侗族大歌被列入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后,它的传播现状可以分为三方面:一是侗族大歌在现代化影响下,其生存环境发生变化,濒临消逝;二是因为地处偏僻,交通不方便,所以在乡村里,人们还保持着“大歌”的传统风俗;三是政府颁布政策,采取措施,部分唱侗歌的村落作为旅游区被保护起来,侗族大歌也逐渐形成了一种文化产品。广西三江侗族自治县在相关部门支持下,健全非遗保护机制,开展系列保护工程。
(一)政策扶持:展演功能内涵增殖
随着近代国家和民族管理体制的逐渐完善和全面渗透,侗族大歌在历史上根据亲缘—地缘关系因素所形成的存衍空间就被近代管理体制重新规划和重建了,“乡村”不再“自成一体”,而且随着国家对外出演出的支持,侗族大歌以“他者”的形式,继续向“乡村”之外更广阔的社会文化空间延伸。
尤其是20世纪后期,随着社会经济和旅游业蓬勃发展,侗族大歌所在地区在当地经济发展、侗族大歌建设中的积极作用日益凸显。其中一个典型的事例:为了吸引游客,扩大当地知名度和市场,各地政府联合外部力量,通过各种手段,以“大歌”为侗族符号,打造地方形象、打造旅游品牌,并把它变成了一种文化产品。在国家领导和指导下,通过举办各类节日庆典、展览等形式,把侗族大歌作为一种文化象征,与当地空间联系起来。三江侗族自治县举行了“侗族多耶节”和“侗族歌舞节”等盛会,多耶广场上,男男女女、老人、孩子们穿着华丽的服装,载歌载舞,唱着美妙的乐曲,抒写着对幸福生活的向往。“侗族多耶节”是桂湘黔地区乃至全国最具影响力、最具代表性的传统节日,也是中外旅游者认识中国侗文化的一个重要窗口。
(二)地方“制造”:多种力量共同操纵
大部分学者从“国家与社会”视角探讨了中国民间社会与文化的关系,并提出了当前过分重视“国家权力”对民间社会文化的单向作用,忽略了“地方”——民间力量对侗族大歌的发展与塑造。“侗族大歌”自20世纪50年代起,就被“地方”各级政府、社会各种力量、各民族单位通过“节庆”“制造”、生产。侗族大歌之所以能在20世纪50年代相对“自成体系”并延续,与民间力量的推动密切相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由于“国家权力”的作用,侗族大歌的发展也受到了一定影响,但由于时间、地域不同,其存在的程度、力度、使用的资源、策略等各有不同,因而侗族大歌的发展方向、形式也就不同。除了人们常说的国家与乡土(或民间)/族群社会以外,还有很多与两者有关的力量,这就是学术界所谓的社会中介组织,例如:学术界、媒体、市场、社会公益机构。在个人方面,三江侗族自治县“侗族大歌”的代表性传承人分为两类,一类为“非遗”的传承人,另一类是志愿者。侗族大歌的传承者,形成了由老、中、青三代的接力式传承。三江县梅林乡是侗族大歌的发源地,一名叫吴光祖的老人出生于此,他是一位三代歌唱家,2008年入选“侗族大歌”国家级非遗传承人。吴光祖老师为三江侗族自治县“侗族大歌”无偿讲学已有数年,多次赴高校讲课,专门教学生唱“侗族大歌”,教他们唱地道的“侗族大歌”,为“侗族大歌”的传播与传承做了大量工作。覃奶号也是“侗族大歌”国家级非遗传承人,从1956到现在,她一直在务农,同时,也在悉心教导孩子们唱侗族大歌。在学校层面,三江侗族自治县三江中学如火如荼地开设侗族艺术课,把“非遗”、侗族歌曲、侗族乐器等“非遗”文化引入校园、教室,同时,侗族歌舞团也在县里举办各类竞赛,让同学们在各种形式的活动中充分体会民族音乐的无穷魅力,彰显自己的文化自信。在学术界,在抗击新冠肺炎的过程中,许多侗族音乐人都用自己的笔创作和演唱了一首首侗族民谣,用来宣传抗疫精神。《病毒拦在寨门外》是广西艺术学院三江侗族男高音潘永华副教授根据“侗族大歌”的“拦路歌”改编而成的歌曲,以侗族优秀的民族传统音乐来展现一名侗族艺术家在“抗疫”期间的职责与义务。
根据田野调查的结果得出,除了“政治展演”,侗族大歌表演还呈现出“舞台艺术”“民俗旅游表演”的不同倾向。表演的总体特点是“政府统筹,地方各级政府、侗族社区、市场等角色各司其职”。
“地方”是“一个可以服从超级地方政治秩序的地方,但也可以用作表达抗议和竞技场的基层社区”,是能够构建地方身份认同的场所。至于“地方制造”,所谓“地方”,就是“一个既受超地方性政治秩序约束,服从于超级地方政治秩序的地方,又能作为表达抗议和竞技场的基层舞台与社区”,它是一个可以构建地方身份认同的场所。对于“地方制造”的过程,是为了有目的地生产、制作和操控各种社会力量活跃竞争。侗族大歌在地方制造中,增强了侗族大歌的政治性展演功能,经过个人、学校和学术界“社会中介组织”的“操纵”,侗族大歌的文化内涵拓展其边界。但在大歌展演中发现,侗族大歌已经走向了商品化趋势,在一些民俗馆、风情园、餐厅里随处可见,有些人改变原先的曲子和风格,变成如今流行的曲子,为了迎合游客,政府将侗族的传统文化重新塑造,将侗族大歌“艺术化”,让侗族大歌重新登上舞台,这样的加工塑造也使得侗族大歌的文化内涵发生变化。
四、结语
侗族大歌构建路径对应文化记忆理论“过去—回忆—建构”的循环范式,以文字、影像和建筑为载体,呈现出文化记忆的塑造性,起到存储、激活和回忆的功能;技艺、仪式和组织活动,体现文化记忆的能动性,具有沟通、重构和获得族群认同的功能;在政策、规划活动等方面,反映出文化记忆的制造性,具有规范要求、引导方向的作用。侗族大歌一方面通过文字、图像、建筑等结构性符号系统唤醒文化记忆,另一方面通过仪式展演和情感认同强化文化记忆,有利于探究侗族民众的认同实践。首先,侗族大歌是侗族在漫长历史进程中所产生并发展起来的,是侗族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以及深刻的集体记忆,对增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起着重要作用。其次,以侗族大歌为结晶的侗族精神建构了一种民族地域文化与中华文化之间经由文化脉络而发生联系的知识谱系。最后,在三江侗族自治县,侗族大歌从最初的形式,到挖掘、政府规划、市场推广和民间演唱等还有很长的发展之路,其中的象征符号、仪式表演、口传文化等形式塑造着中华民族共同体,促进地方民族的团结凝聚,并促使当地人民认可中华文化。
侗族大歌是侗族精神文化和历史记忆的重要载体。通过传承与演唱侗族大歌,侗族人的自我身份认同感得到加强,同时昂扬的歌声传递出民族自信和文化自信。采取一边“唤醒”一边“强化”的方式实现了国人对民族身份的“认同”,完成了文化记忆建构,凝聚社会共识,唤醒民族意识,激发民族热情,提升文化自信,增强国人的文化归属感,强化了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参考文献:
[1]谭厚锋.侗族大歌研究八百年史述[J].贵州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9(06):1-109.
[2]扬·阿斯曼.文化记忆:早期高级文化中的文字、回忆与政治身份[M].金寿福,黄晓晨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
[3]甘群.广西三江侗族自治县“侗族大歌”传承经纬的探讨[J].广西教育,2020(35):174-176.
[4]宋彦斌.侗族大歌多声部音乐形态研究[J].中国文艺家,2020(11):120-121.
[5]王焯,张继焦.潜在与现实:文化记忆视角下文化遗产传承与建构的三个特性[J].思想战线,2022(03):87-95.
[6]扶燕.侗族大歌的功能研究[J].艺术评鉴,2022(10):5-10.
[7]王晓丹.“侗族大歌”文化的生成性解读与现代审视[J].贵州民族研究,2017(09):94-97.
[8][美]桥本明子.漫长的战败:日本的文化创伤、记忆与认同[M].李鹏程译,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19:5.
[9][德]阿莱达·阿斯曼.回忆空间:文化记忆的形式和变迁[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6:6.
[10]李延红.“地方制造”与节庆表演——当下“侗族大歌”的地方建构与认同[J].中国音乐,2020(06):34-4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