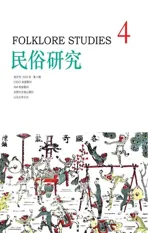分合之间:日式酒吧跨文化交换中的商品与礼物
2023-09-20张一璇
张一璇
有关资本主义与非资本主义交换系统中物的存在方式的差异问题,人类学中最经典的讨论非礼物与商品之分野莫属。资本主义通过商品化的方式将物抽象为交换价值和使用价值,并以金钱形式表现;而在非资本主义经济系统之中,物则通过其所联结的社会关系、承载的声望与期待等获得不同于金钱价值的其他价值。(1)David Graeber, “Value: Anthropological Theories of Value,” in James G. Carrier (ed.), A Handbook of Economic Anthropology. Cheltenham: Edward Elgar Publishing, 2005, pp.440-450.换言之,物在不同的交换系统之中所获得的价值并不相同。礼物因其紧密嵌于有道德的社会关系之中,使之所获得的价值往往与人相关,所参与的交换亦是人的社会关系的传递。相反,商品意味着物脱离了其诞生的环境、从属的关系以及其中的人,此时物只有在被通约化的交换价值所表示之后才能参与交换。因而异化问题被视为礼物与商品之间价值分野的核心。非异化的礼物和礼物关系通常发生在非资本主义交换系统中,异化的商品和商品关系发生在资本主义交换系统中。(2)George Tharakan C.,“Gift and Commodity: On the Nature of Muduga Transaction,” Anthropos,vol.102, no.2(2007), pp.441-454.由是观之,礼物与商品所代表的不同的经济体都有其单独的创造价值的逻辑。(3)参见[美]罗安清:《末日松茸:资本主义废墟上的生活可能》,张晓佳译,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20年,第145页。如果说人类学经典中描述的礼物经济是独立于资本主义的一套有其价值逻辑的交换体系,那么在现代社会中礼物所属的交换体系不可避免地与资本主义相遇。在讨论资本主义如何将非资本主义的价值体系吸纳为自身所用时,罗安清提醒我们关注非资本主义价值体系在资本主义内部的运作方式,尤其要注意活跃在商品的生命历程中的具体行动者,他们承担了“价值转译”(value translation)的作用(4)参见[美]罗安清:《末日松茸:资本主义废墟上的生活可能》,张晓佳译,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20年,第145-149页。,即通过赋予商品以其他价值形式,使资本主义中的商品转化为其他价值体系所认可的物,进而令资本主义能够与其他制造人和物的方式共存。一个明显的过程是诞生于工业流水线上的商品被人们赋予文化价值或符号价值,将其去商品化之后作为礼物赠予他人。相反的过程体现为,原本作为礼物的物进入市场获得交换价值后亦能够成为商品。既有研究暗示着礼物与商品之间的转换发生在线性的时间序列之中,发生在不同背景与社会关系的转化之中,物只有脱离一套社会关系与价值逻辑、进入另一套关系之中,其属性才发生改变。
>然而,以在中国工作的日本男性上班族为顾客群体的日式酒吧(5)本文的日式酒吧指开设在中国城市中的以日本男性上班族为顾客群体的酒吧。这些酒吧提供酒水小吃以及卡拉OK设备等,经营者通常是中国女性,年龄多在25岁至40岁之间,工作内容包括为顾客准备酒水小吃、与顾客聊天等。顾客多为日本男性,以30岁至60岁的在当地日资企业或中日合资企业中工作的上班族为主。他们被公司外派至中国工作,大部分人独身前来,妻儿留在日本。中国女性经营者与日本男性顾客之间用日语交流。在日本,类似的场所提供了工作之余娱乐消遣的空间,上班族男性在下班之后与同事、客户到此类场所消费,女性服务人员提供制作酒水及与客人聊天的服务。中国的日式酒吧在一定程度上是对日本的类似场所以及上班族夜生活文化的复制。,展现出了有关商品与礼物的另一番景象。日式酒吧的中国女性经营者借酒发出邀请,以酒结友;日本顾客则以购酒、请喝酒、赠送高昂的酒等方式回馈中国女性经营者,看似是酒的商品消费过程,同时也是回赠礼物的过程。其中,还时常发生利益与真情的拉扯,女性经营者有时铤而走险地算计酒背后的金钱利益,有时又以酒回馈顾客表达自身的真挚情感。在同一种背景与社会关系之中,酒水同时获得商品与礼物的双重属性,作为商品的金钱价值与作为礼物的象征价值并存于酒水之上。这一经验现象在理论上既挑战了商品与礼物二分背后不同价值的相斥的假设,又挑战了社会关系对物的影响的假设——即便物所嵌入的社会关系不发生改变,物也能够同时保有看似相斥的属性。此处,礼物与商品形成了一种互为条件的关系,商品即礼物,礼物即商品。
纵观既有关于日式酒吧的社会学与人类学研究,对酒水交换的分析几乎缺失。前人研究集中讨论日本本土酒吧中女性劳动者的劳动过程,几乎没有涉及日本之外的日式酒吧。主要研究视角包括:从性别视角分析女性服务员在情感劳动(emotional labor)中的性别气质展演过程,及其在再生产男性顾客的男性气质中的作用(6)Anne Allison, Nightwork: Sexuality, Pleasure, and Corporate Masculinity in a Tokyo Hostess Club. Chicago: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94, pp.25-26.;从移民角度讨论移民身份对劳动控制的影响,以及外籍女性服务员与男性顾客的互动(7)Lieba Faier,“Pilipina Migrants in Rural Japan and Their Professions of Love,”American Ethnologist,vol.34, no.1(Feb., 2007), pp.148-162; Rhacel Salazar Parreas, Illicit Flirtations: Labor, Migration, and Sex Trafficking in Tokyo. Californi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1, pp.11-14.;从日本社会经济背景的变化切入,分析女性服务员情感劳动过程的变化及其与社会环境的互动等(8)Gabriele Koch,“Producing Iyashi:Healing and Labor in Tokyo’s Sex Industry,”American Ethnologist,vol.43, no.4(Nov., 2016), pp.704-716.。既有研究聚焦于情感劳动过程理论,探讨女性劳动者与男性顾客的互动与关系,从本质上说,这些视角均以人为分析中心,并没有将构成酒吧整体的重要部分,即作为物而存在的酒水纳入考察范围。在此框架下,酒水或者被视为情感劳动过程或者劳-客买卖关系之中的附属品,是女性用以谋利的手段(9)Rhacel Salazar Parreas, Illicit Flirtations: Labor, Migration, and Sex Trafficking in Tokyo. Californi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1, pp.122-123.,或者被视为彰显顾客男性气质的工具。(10)Anne Allison, Nightwork: Sexuality, Pleasure, and Corporate Masculinity in a Tokyo Hostess Club. Chicago: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94, pp.45-46.在商品买卖关系的刻板印象下,女性与男性往往被置于买卖双方进行经济理性博弈的叙事之中。然而,正如前文经验观察所指出的,酒水背后呈现出商品与礼物的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复杂性,在看似被金钱价值与理性算计逻辑支配的关系中,多元价值逻辑的互动影响着酒水交换。
此外,发生在中日之间的跨文化背景同样值得注意。此处的跨文化有两层含义:第一,参与交换的双方来自不同文化背景;第二,日式酒吧作为一种整体意义上的文化现象在海外重新“组装”,产生了与日本本土酒吧并不完全一致的新形态。在以往的民族志作品以及笔者的调查中,日本本土酒吧普遍实行高度规范化的酒水买卖制度,酒水的出售与消费遵守着商品制度之下的交易规则。然而,中国日式酒吧的酒水交换有着极为灵活的空间,酒水买卖的制度化程度较低,双方根据具体情景时常对买卖过程进行变通。(11)日本本土的日式酒吧是制度化与标准化的产业。服务者的雇佣关系、酒水销售制度等都较为规范和成熟,行业市场完备。例如,在帕瑞秋(Rhacel Salazar Parreas)有关日本一家菲律宾籍女服务员构成的日式酒吧的民族志作品中,她介绍了其中的酒水消费制度,顾客根据酒吧设定的套餐标准进行消费,女性服务者无法自行改变其价格或出售形式,酒水消费是高度程式化的商品交换过程。在笔者进行田野工作时,不少日本顾客表示日本本土酒吧中的酒水消费制度十分完善,不会存在女性服务者随意更改酒水价格、给酒水“动手脚”等情况。对比笔者的调查,中国的日式酒吧虽已形成一定的经营规模,但其标准化与制度化程度都较为薄弱,是松散的个体户经营模式,缺乏行业统一标准,女性经营者可以根据场景随时更改酒水价格与销售方式等,具有极高的灵活性。相关研究参见Rhacel Salazar Parreas, Illicit Flirtations:Labor, Migration, and Sex Trafficking in Tokyo.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1, pp.79-80.换言之,当日式酒吧挪移至海外时,其运行的文化逻辑与日本本土酒吧并不全然一致,在海外跨文化的互动中催生了商品交换体系变化的新可能。
借物的交换透视人的关系或连带(association)是人类学研究的经典取向。笔者希望在日式酒吧的研究中引入物的视角,从酒水交换体系出发讨论物的流动过程,重新审视物所嵌入的社会关系,发掘支撑看似高度理性的经济交换行为背后的文化逻辑。鉴于此,本研究希望考察如下问题:礼物与商品两种属性何以在中国日式酒吧的酒水身上合二为一?在同一场景与社会关系之中,礼物与商品背后看似冲突的价值逻辑何以共存?不同价值的叠加与竞争如何维系跨文化交换的运转?不同文化背景的行动者双方如何进行价值抉择以实现物的交换?萨林斯指出,经济活动是文化序列中一个不可分割的领域,对经济活动的理解离不开与其息息相关的生活领域。(12)参见[美]马歇尔·萨林斯:《石器时代经济学》,张经纬、郑少雄、张帆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9年,第1页。泽利泽也认为,看似高度经济理性的行为背后往往有文化价值与道德准则的支撑。(13)Viviana A. Zelizer, The Purchase of Intimacy. Princeton.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5, pp.25-29.本文尝试以发生在跨越中日两国行动者之间的交换,考察经济行为与文化因素的互动,在理论层面上回应礼物与商品的相关研究。
一、礼物与商品:从二元之争到价值转换
人类学中关于礼物与商品的讨论,经历了从主张二者的互斥性对立到关注二者间转化的过程。早期理论主张礼物和商品的绝对对立。作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产物的商品外在于人、异化于人,被交换价值和使用价值所表示。(14)参见[德]卡尔·马克思:《资本论》,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译,人民出版社,2019年,第88-90页;James G. Carrier,“Gifts, Commodities and Social Relations: A Maussian View of Exchange,”Sociological Forum, vol.6, no.1(Mar., 1991), pp.119-136.商品交换过程是发生在彼此独立的双方之间有关异化的物的交换,交换双方是一次性、随机的关系。(15)James G. Carrier, Gifts and Commodities: Exchange and Western Capitalism since 1700. New York:Routledge, 1995, pp.31-33.与之相反,礼物意味着人与物不分的非异化性(inalienable)(16)Annette Weiner, “Inalienable Wealth,” American Ethnologist, vol.12, no.2(May., 1985), pp.210-227.,参与礼物关系中的人与物处于混融状态,礼物承载着建立人与物、人与人之间道德关系的力量。(17)James G. Carrier, “Gifts, Commodities and Social Relations: A Maussian View of Exchange,” Sociological Forum, vol.6, no.1(Mar., 1991), pp.125-126; Strathern Marilyn, “Qualified Value: The Perspective of Gift Exchange,” in Caroline Humphrey and Stephen Hugh-Jones (eds.), Barter, Exchange and Value: An Anthropological Approach.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2, pp.169-170;王铭铭:《物的社会生命?——莫斯〈论礼物〉的解释力与局限性》,《社会学研究》2006年第4期。在莫斯笔下,礼物意味着包括送出、接受、回礼在内不可分割的“总体社会事实”(total social phenomena)(18)参见[法]马塞尔·莫斯:《礼物:古式社会中交换的形式与理由》,汲喆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6-18页。。对这组二元对立的讨论逐渐超越了物本身,上升为对不同的社会秩序运作方式以及社会演化趋势的讨论,即礼物经济(gift economy)和商品经济(commodity economy)或市场与非市场这组社会形态的二元对立,前者通常意味着非资本主义的礼物交换系统,后者则指代资本主义的商品交换系统。(19)James G. Carrier, “Gifts, Commodities and Social Relations: A Maussian View of Exchange,” Sociological Forum,vol.6, no.1(Mar., 1991), pp.119-136; Costas Lapavitsas, “Commodities and Gifts: Why Commodities Represent More than Market Relations,” Science &Society, vol.68, no.1(Spring, 2004), pp.33-56.尽管对礼物和商品之间分野的强调,可能并非莫斯在《礼物》一书中写作的初衷(20)参见余昕:《实质的经济:〈礼物〉和〈大转型〉的反功利主义经济人类学》,《社会》2019年第4期。,但不置可否的是对不同经济体系的比较,特别是资本主义经济体系与非资本主义经济体系之间的比较,提醒我们发现与反思不同社会的差异(21)参见[美]罗安清:《末日松茸:资本主义废墟上的生活可能》,张晓佳译,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20年,第145页。。
将礼物与商品视为对立两极的观点受到了挑战。阿帕杜莱指出,对分野的强调潜藏着人类学对前资本主义社会的浪漫化处理。(22)Arjun Appadurai, “Introduction: Commodities and the Politics of Value,” in Arjun Appadurai (ed.), The Social Life of Things: Commodities in Cultural Perspective.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6, p.11.礼物与商品之间的分野,在一定程度上正是被人类学的讨论所建构出来的,作为理想类型的二者在现实中的差别可能很难厘清。(23)Yan Yunxiang, “The Gift and Gift Economy,” in James G. Carrier (ed.), A Handbook of Economic Anthropology. Cheltenham: Edward Elgar Publishing, 2005, pp.254-255.人类学对礼物和礼物经济的偏爱,也暗示着对经济学的抵抗,在将礼物经济奉为圭臬的同时使商品被长期排除在人类学的研究范围之外。(24)Dannier Miller, “Consumption and Commodities,” Annual Review of Anthropology, vol.24(1995), pp.141-161.然而,当人们生活的周遭世界里越来越多的物参与资本主义生产和商品交换时,现实提醒人类学家重新审视资本主义社会里礼物与商品的关系。物的生命历程理论便是对此问题的回答,这一脉的学者认为,礼物和商品是物的整个生命历程中的不同阶段,物因外在条件的变化而发生改变。(25)Arjun Appadurai, “Introduction: Commodities and the Politics of Value,” in Arjun Appadurai(ed.), The Social Life of Things: Commodities in Cultural Perspective. New York: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86, pp.11-13; Igor Kopytoff, “The Cultural Biography of Things: Commoditization as Process,” in Arjun Appadurai(ed.), The Social Life of Things: Commodities in Cultural Perspective.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6, pp.66-69.同时,学者们也注意到,现代社会中礼物关系与商品关系反映的是人与人之间关系的不同形态。(26)Chris A. Gregory, Gifts and Commodities. London: Academic Press, 1982, p.41; Jonathan Parry, “The Gift, the Indian Gift and the ‘Indian Gift’,” Man, vol.21, no.3(Sep., 1986), pp.453-473.在更加宏观的意义上,社会背景决定了交换的类型与物的形态,在一种环境中是商品的物,到了另一种环境中可能成为礼物。(27)Tharakan C. George, “Gift and Commodity: On the Nature of Muduga Transaction,” Anthropos, vol.102, no.2(2007), pp.441-454.尽管不再一味地突出礼物与商品的截然对立,但学者们并没有否定礼物和商品之间的核心差异,即一个物不能同时保有异化特征与非异化特征,倘若物在礼物和商品之间转化,必须克服一种属性才能进入另一种属性之中。因此学者们才会强调社会情景的转化,当社会情景以及社会关系发生变化时,物的特征才会改变。
如今,礼物交换已不再是民族志所书写的独当一面的经济运作体系,但在我们自身的社会中,礼物关系隐藏在表面之下且依旧发生着作用。(28)Marcel Mauss, The Gift: The Form and Reason for Exchange in Archaic Societies.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2002, p.5.在当代大多数社会中,礼物经济与商品经济并存,礼物经济嵌入在商品经济之中。(29)Pnina Werbner, “Economic Rationality and Hierarchical Gift Economies: Value and Ranking among British Pakistanis,” Man, vol.25, no.2(Jun., 1990), pp.266-285; YanYunxiang, “The Gift and Gift Economy,” in James G. Carrier (ed.), A Handbook of Economic Anthropology. Cheltenham: Edward Elgar Publishing, 2005, pp.254-255.因而资本主义社会中的礼物交换何以实现,成为这一领域的新议题。相关讨论大致集中于两个方向:其一,商品与礼物之间的转换;其二,资本主义之下的文化背景对礼物交换产生的影响。价值的视角为回答转换问题提供了新思路。价值在人类学中被理解为人们用以看待世界的一套符号系统,它界定着人们所认为重要的、有意义的、值得追求的事物。价值理论能够用以研究包括自由市场下的资本主义在内的任何交换系统,因为交换是围绕价值组织起来的意义系统。(30)David Graeber, “Value: Anthropological Theories of Value,” in James G. Carrier (ed.), A Handbook of Economic Anthropology. Cheltenham: Edward Elgar Publishing, 2005, pp.452-453.价值并非凭空生成,物的价值依赖于自身与其他物的相对关系中的位置,以及在此基础上人们做出的评判。(31)Marry Douglas and Baron Isherwood, The World of Goods: Towards an Anthropology of Consumption. London: Routledge, 1996, p.22.就此而言,物的价值因其所处的交换系统中价值逻辑的不同而发生变化,商品和礼物是不同价值逻辑影响下物的外在表现形式。作为商品的物在参与交换时,其交换价值被激活,礼物交换则赋予物以人的身份、声望、道德、社会关系等主观建构的价值,物因为这些价值才得以参与礼物交换。(32)Annette Weiner, “Inalienable Wealth,” American Ethnologist, vol.12, no.2(1985), pp.210-227.这正是礼物的象征价值之所在,因为上述价值皆隐含的是人与礼物的紧密关联,即通过礼物象征和保持着它和赠予者与接受者之间的联结和认同。(33)参见[美]杨美惠:《礼物、关系学与国家:中国人际关系与主体性建构》,赵旭东、孙珉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169页。然而,交换价值一度成为超越其他价值的压倒性的衡量标准,这是资本主义同化能力之所在——抽象的关系掩盖了人的关系。这种抽象化的机制将物品从其生产和消费的时空背景及社会关系中抽离。(34)参见余昕:《燕窝贸易的三重世界——南洋华人的价值理论、物质性与生产》,《社会》2021年第3期。与之相对,礼物的价值在于它们并不是无差别的物,它们可以有名字、个性、过去、故事以及与具体的人的关联,正是个体性造就了它们的价值,使之与单一的、固定的市场价值相区分。(35)Pnina Werbner, “Economic Rationality and Hierarchical Gift Economies: Value and Ranking among British Pakistanis,” Man, vol.25(1990), p.282;[美]罗安清:《末日松茸:资本主义废墟上的生活可能》,张晓佳译,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20年,第372页。诸如库拉礼物中的价值——对声望的追求——被当地人称为“豪”,而非政治经济学中的交换价值。
因此,商品和礼物之间的转换问题可以视为物在不同价值之间的转换。在消费社会全面展开的今天,大多数礼物源于批量生产的工业制品、购买获得的商品,将商品转化为礼物意味着改变其交换价值为其他价值,作为主体的交换者在商品的再社会化过程中使物从商品阶段进入礼物阶段。(36)James G. Carrier, “Gifts in a World of Commodities: the Ideology of the Perfect Gift in American Society,” Social Analysis, vol.29, no.29(Dec., 1990), pp.19-37;Yan Yunxiang,“The Gift and Gift Economy,” in James G. Carrier(ed.), A Handbook of Economic Anthropology. Cheltenham: Edward Elgar Publishing, 2005, pp. 254-255.比如礼物的包装和卡片就承担了此功能,它们使原本毫无差异的商品变成具有送礼者个人特征的象征物,使物获得了象征人际关系的价值。(37)Theodore Caplow, “Rule Enforcement without Visible Means: Christmas Gift Giving in Middletown,”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vol.89, no.6 (May., 1984), pp.1306-1323;参见[美]杨美惠:《礼物、关系学与国家:中国人际关系与主体性建构》,赵旭东、孙珉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164-165页。同样的过程也可能发生在礼物向商品转化的过程中,当为了实现功利性目的时工具性价值出现,礼物会变为工具性礼物并获得某种商品的属性。(38)Yan Yunxiang,“The Gift and Gift Economy,” in James G. Carrier(ed.), A Handbook of Economic Anthropology. Cheltenham: Edward Elgar Publishing,2005, pp.254-255.这也从价值角度呼应了物的生命历程理论——礼物和商品各自都具有向对方转化的特质,礼物包含着利益的导向,商品同样涉及双方之间的义务。(39)Ronald Dore,“Goodwill and the Spirit of Market Capitalism,” The British Journal of Sociology, vol.34, no.4(Dec., 1983), pp.459-482; Duran Bell, “Modes of Exchange: Gift and Commodity,” The Journal of Socio-Economics, vol.20, no.42(Summer, 1991), pp.155-167.价值视角的引入提醒我们警惕将商品与礼物本质化的倾向,物的形态受制于其所处的具体关系、意义体系以及价值逻辑。
“尽管礼物交换存在于所有的人类社会,其形式却依据所根植其中的特定文化而千变万化。”(40)阎云翔:《礼物的流动:一个中国村庄中的互惠原则与社会网络》,李放春、刘瑜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205页。一个社会中的文化因素影响了何种价值被用以造就礼物(41)例如Garrier指出,美国社会中由商品转化成的礼物延续了美国社会的人际关系文化特征,形成了一种完美礼物的意识形态(the ideology of the perfect gift),它强调礼物应当是送礼者个人情感的诠释、自由自主的彰显,而不应该为了送出者与接受者双方之间强制性的义务和利益而存在。而其他一些社会中用商品转化而来的礼物用以建立双方之间的强制关系,如中国社会里的香烟和白酒、日本社会里的松茸等,都是从商品转化而来的用以建立报偿性人际关系的礼物,可参见阎云翔、罗安清的相关研究。,背后蕴含的更大问题是“全球性物质力量的特定后果依赖于它们在各种地方性文化图式中进行调适的不同方式”(42)[美]马歇尔·萨林斯:《人性的西方幻象》,赵丙祥、胡宗泽、罗杨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9年,第6页。。当然,其实现依赖于作为行动者的人。具体的行动者承担着“价值转译”的工作,他们使物获得或消去不同的价值。在交换过程中,价值的影响由人传递至物,又从物延展到人。交换者之间形成一系列或浅或深的价值共识,在交换过程中不断生成与修改,进而形成一套价值政体(regimes of value),它能够解释随着商品流动而造成的文化边界的穿梭与跨越。(43)Arjun Appadurai,“Introduction: Commodities and the Politics of Value,” in Arjun Appadurai(ed.), The Social Life of Things:Commodities in Cultural Perspective.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6, pp.14-15.这提醒我们关注文化影响下不同价值逻辑之间的交融所产生的新变化,关注行动者在其中的能动性及其与物的双向影响。
从非资本主义到资本主义,从二元对立到相互转化,既有理论展现了礼物和商品研究的基本框架,价值视角的引入更使我们直击这些讨论的本质。然而既有研究仍存在一些尚待处理的问题。首先,礼物和商品在理想类型上的分野提供了抽象的分析工具,然而这又在一定程度上将经验世界中物的张力机械化,二分模型与线性转化解释都是从物所处的社会关系及背后的强势价值为视角来界定物,但却忽视了参与交换的行动者的能动性对物的关系和价值的诠释,行动者的行动往往并非单一价值的结果,而是多元价值博弈的过程。本文尝试将行动者对物与关系的主观阐释纳入考察范畴,讨论行动者如何构建商品与礼物之于自身的意义。其次,既有研究较少涉及跨文化交换,全球化背景下不同文化的人们之间的交换活动日益频繁,跨文化交换提供了一处比较参与者之间价值逻辑的观察场,关于跨文化价值逻辑下交换体系的实现过程有待实证探索。
本文以中国日式酒吧中日双方行动者之间以酒水为中心的交换体系为研究对象,通过分析中国女性经营者与日本顾客双方对酒水的解释,结合跨国社会关系的背景,讨论跨文化交换场景与多元价值的互动对物的影响,为理解跨文化价值逻辑中物的流动研究提供案例。本文田野材料源自笔者2021年3月至10月在长三角地区岚市的两家日式酒吧进行的田野调查,两家酒吧分别名为“彩”与“响”,经营者均为中国女性,顾客是外派至中国工作的日本男性。(44)本文对地名、酒吧名、人名均做匿名处理。岚市自20世纪90年代初成立经济技术开发区以来,引进众多日本企业入驻。随着日企的入驻,生活在当地的日本人数量逐渐增多并形成了日本人聚居区。聚居区内包括公寓、日本料理店、日本超市、日式酒吧等面向日本人的各类生活娱乐场所。笔者走访了该区域内的许多日式酒吧,发现它们普遍规模较小,由2-4位女性经营者共同出资、以合作的方式经营。笔者分别以员工和顾客的身份参与观察了双方围绕酒展开的大量交换实践,并通过非结构访谈的方式获得了双方对酒水交换实践的解释。下文分别从中国女性经营者和日本顾客的视角出发,还原双方围绕酒水展开的交换及其意义的解释,勾勒出酒的商品买卖与送礼实践的交织过程,分析相互竞争的价值逻辑及新背景中社会关系何以影响交换体系。
二、酒的改造:商品之下的“本真性礼物”
本真性(authenticity)是将商品化的关系还原为有道德的礼物关系的重要手段。在物质文化发展的过程中,标准化使商品越来越缺乏本真性。(45)David Graeber, “Consumption,” Cultural Anthropology, vol.52, no.4(Aug., 2011), pp.489-551.本真性意味着打破因标准化而形成的同质化特征,意味着商品的去商品化和独特化,使商品成为具有独特文化意义的象征物。(46)Brian Spooner,“Weavers and Dealers: The Authenticity of an Oriental Caprpet,” in Arjun Appadurai(ed.), The Social Life of Things:Commodities in Cultural Perspective.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6, p.223.在日式酒吧里,女性经营者对酒进行了改造,使之成为“本真性礼物”,即酒被不断赋予有意义的、独特化、个人化的特征,从同质的商品逐渐变为个人特征和人的关系的承载者,进而将酒所连接起的双方之间的商品买卖关系转变为有道德的礼物关系。改造体现为三种具体实践,即存酒、给酒冠名,以及以酒为载体构建人际纽带。其结果是酒成为人的关系的象征物,其礼物的一面逐渐浮现。
(一)存酒:时间维度的延长
五月的一天晚上,顾客宫本到日式酒吧“彩”喝酒,他是一位第三次光顾这家店的客人。第一次宫本与日本同事一起到店喝酒,之后购买了整瓶酒存在店中。加奈(47)女性日语昵称的音译。每位中国女性经营者都有一个日语昵称,日本顾客以此称呼她们。是在这家店工作两年多的一名中国女性。晚上上班前,她给宫本发微信寒暄,询问他今天要不要来店里喝酒。九点半左右,宫本来到店中,加奈坐在他旁边和他聊天。桌子上摆着宫本购买的瓶装威士忌以及两人的酒杯,他们的酒都来自于那瓶威士忌。宫本酒杯中的酒喝到剩下一半时,加奈便给他“做酒”——在玻璃杯中加入冰块,倒入威士忌,再倒入苏打水搅拌均匀。眼前的这瓶威士忌即将见底,加奈问宫本要不要再来一瓶,他说这次想喝三得利角瓶。(48)日本三得利(SUNTORY)公司生产的一款威士忌酒,是日式酒吧里常见的瓶装威士忌酒。于是加奈拿来了一瓶新的三得利角瓶威士忌,并拿出修正液在酒瓶上涂鸦。先是写上了宫本的名字,然后在他的名字周围画了四颗爱心,加奈边画边说:“我们店里有四个女孩子,就给你画四颗爱心吧。”宫本看到之后非常高兴,说“把大家的名字也写上去吧”。于是加奈在每颗爱心里分别写上了店里女孩们的日语名字。
这样一个饮酒、做酒、售酒、聊天的片段,便是当地日式酒吧每天上演的场景。日式酒吧有关酒的重要特征之一是存酒消费模式,即日本顾客需要购买整瓶酒存放在店中,通常为威士忌和日本烧酒,一瓶酒可以喝半个月以上,存放期限3个月左右。与存酒模式相结合的是座位费制度,根据店的不同,日本顾客每次需要支付100元至200元不等的座位费。存酒与座位费的结合,区分出了作为常客的日本顾客与偶尔光顾的中国顾客之间的两套“喝酒”规则,日式酒吧不收中国顾客座位费,也不要求他们存酒,中国顾客消费自由,参与的是一般意义上的商品交换:
不收中国人座位费,(中国客人)来了我们就按中国酒吧那样,鸡尾酒,简单的我们都能做。中国客人是流动的……喝一两杯鸡尾酒就走了,不会再来。(49)访谈对象:加奈,女,1984年生,日式酒吧经营者;访谈人:张一璇;访谈时间:2021年4月28日;访谈地点:日式酒吧“彩”店内。
相反,日本顾客进入的是不同于一般商品买卖的交换关系。中国女性经营者通过存酒模式有意识地将双方的关系在时间维度上延长,酒被人为地赋予时间维度,为双方关系的推进提供了条件。喝酒的同时,也伴有漫长的聊天过程。喝酒、聊天、做酒、存酒将双方关系重组,商品关系之外的更加鲜活的人际往来慢慢延展开。
(二)冠名:酒的个人化
存酒之后更重要的环节是给酒冠名。店内酒柜上整齐排列着写有客人名字的酒瓶。冠名的做法是女性店员用白色修正液在酒瓶上进行标记,首先写上客人的姓氏或昵称,其次进行涂鸦装饰,如前文展示的场景,店员在顾客的酒瓶上写上自己的名字、画上爱心,再比如画上顾客的形象或者其他一些象征顾客的标记,给客人的酒盖上装饰帽子、在酒瓶上贴照片等。一位姓汤川的客人的酒瓶上写的不是“汤川”二字,而是“铁公鸡2号”。作为酒吧老板即“妈妈桑”(50)“妈妈桑”是女性经营者中领头人的称呼,来自于日语“ママさん”的中文音译,其中“妈妈”指的是经营店铺的女性老板,“桑”则是日语中经常连接在人名之后的尊称,无实际含义。的亚美对我解释道:“他小气,他是铁公鸡2号,1号是横山。”(51)访谈对象:亚美,女,1985年生,日式酒吧经营者;访谈人:张一璇;访谈时间:2021年9月7日;访谈地点:日式酒吧“响”店内。横山酒瓶上也写着“铁公鸡”。此外,酒柜上还会保留一些喝剩下的空酒瓶作装饰,上面也有客人的名字与涂鸦,其中不乏一些已经返回日本的客人。
将酒瓶标上个人的名字是一个容易忽略的举动。表面上它表达了一种“所有权”的宣誓,即消费者对商品的长期占有甚至永久占有。虽然可以从“营销策略”“服务业特征”等角度理解这个举动,但这些看法无法摆脱“外部视角”,即外在于当事人的、看似“科学”的视角,其后果是留下大量无法解释的“剩余物”。(52)参见[法]路易·迪蒙:《论个体主义:人类学视野中的现代意识形态》,桂裕芳译,译林出版社,2014年,第2-3页。如果从“当地人出发”,就可以体会到具体生活中的人的“近经验”,体会他感受到的世界。(53)参见[美]克利福德·格尔茨:《地方知识——阐释人类学论文集》,杨德睿译,商务印书馆,2016年,第91-92页。给酒冠名不仅仅是宣示“所有权”——由谁来写,写哪些人的名字,何种含义的涂鸦,背后是怎样的挑逗与玩笑等正是有待解释的“剩余物”。它们恰恰是“去商品化”的符号,使酒获得有真实含义的象征价值,其意义远远超过宣示对一件商品的“所有权”。如果说商品掩盖了社会关系,那么符号便将酒激活,使其不仅代表人,更代表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让酒变得有灵性,让酒从死的商品变成“活物”。名字写在酒瓶上,酒瓶放在酒柜中,仿佛是日本顾客将自身的一部分、自己与女性经营者、与酒吧的关系存放了起来。可以说,符号激活了酒作为礼物的属性。
(三)邀请:以酒结友
酒作为媒介将中国女性经营者与日本男性顾客联系在一起,成为双方关系的象征物,这是酒之上的“本真性”最重要的体现。不同于一般商品买卖关系中交易达成之后双方关系结束、义务终止,礼物的送出反而促进了双方关系的达成。(54)James G. Carrier, “Gifts, Commodities and Social Relations: A Maussian View of Exchange,” Sociological Forum, vol.6, no.1(Mar., 1991), pp.119-136.日式酒吧中,酒的商品交易的达成意味着双方关系的开始,日本顾客成为回头客,双方的关系不断巩固。通常第一次到店后,女性经营者便与顾客交换联系方式,之后她们时常询问顾客要不要来喝酒,上班之前她们会发信息邀请客人来喝酒:下班了吗?今天工作辛苦了,要不要来喝酒?主动发出邀请是中国女性经营者对待每一位日本顾客的方式。其目的不仅是喝酒,更是不断强调双方的关系不是一次性的,酒是连接双方的桥梁,通过酒来建立和日本顾客之间超越商品关系的、更加个人化的关系:
叫客人的意思就是叫他来和我们一起喝酒聊天。给客人发信息,慢慢就熟了……只要来过一次,我们就会和他保持联系,发信息问他要不要来喝酒,和客人熟了才有生意做……客人跟我们就像朋友一样。(55)访谈对象:加奈,女,1984年生,日式酒吧经营者;访谈人:张一璇;访谈时间:2021年5月17日;访谈地点:日式酒吧“彩”店内。
“先做朋友再做生意”是酒获得本真性的关键。借助酒生成的人际关系对每个女性经营者而言具有超越买卖关系的意义——她们并没有将对方视为完全意义上的顾客或消费者,而是从建立关系之初便夹杂着人情交往,她们称之为“做客人”。“做”有制造之意,也有成为之意,既表达双方关系的生成过程,也暗示着只有结成特定社会关系之后才能成为交换体系的行动者。换言之,通过“做客人”区分出了纯粹商品交换关系与私人情感的人际纽带。“做客人”源自中国日式酒吧的特定背景,一方面日本顾客有限且相对集中,类似熟人社会的小群体互动是其特征;另一方面取决于日本顾客独身海外生活的背景,他们通过结识日式酒吧通晓日语的中国人构建起陌生国度里的社会关系,中国女性经营者扮演了其海外生活里的支持者的角色:
在日本,和酒吧女孩的关系基本上是顾客和服务提供者……在中国,这个关系上有加号的部分,比如成为朋友……是依赖者和支持者……十几年前我到中国工作时也感觉是这样,果然和中国这边的女孩关系会变深,有许多私人的东西,因为她们能帮你很多事情。在日本只是喝酒时和酒吧里认识的女孩聊天,平时生活中不会找她们。(56)访谈对象:笠原,男,1971年生,日本顾客;访谈人:张一璇;访谈时间:2021年10月15日;访谈地点:日式酒吧“响”店内。
相比于日本本土酒吧里女性服务者与男性顾客之间明确的劳-客、买-卖关系,日本顾客倾向于将在中国的关系情感化,把到酒吧喝酒消费解释为支持对方的生意、回馈对方,视为人际关系中的来往。海外生活的苦闷与孤独,初来乍到的好奇与不安,异国生活的复杂情绪找到了一个新的诉说途径,延展至更广阔生活世界中的交集促使更亲近的人际纽带生成。从存酒到冠名再到以酒结友,酒被双方有意识地制作为黏合双方私人关系的媒介,酒所嵌入的买卖关系被改造为夹杂私人情感的人际关系,经行动者的阐释,酒获得了超越商品交换价值的意涵。
三、酒的回馈:商品之下的“金钱式礼物”
如果说存酒与喝酒是日常的回馈,那么日本顾客还有另一种回礼方式——送出“金钱式礼物”。日本顾客购买酒吧中的香槟和红酒与女性经营者们分享,它们便是“金钱式礼物”。购买、分享酒的过程就是回礼的过程。作为“金钱式礼物”的酒售价高昂(57)根据田野调查,进价百十块钱的香槟在这里售价可达1500元以上,红酒的情况也与之类似。,远超威士忌和烧酒,日本顾客购买这类酒之后,会与女性经营者们当场分享,将之快速消耗掉,并不存储。这类酒可以说是极致商品化的物,它们意味着高昂的金钱利润。然而有趣的是,金钱本身表达的亦是一种礼物关系:日本顾客通过购买香槟和红酒的方式帮助女性增加营业额、回馈女性经营者,因而本文称其为“金钱式礼物”。从女性经营者自身出发,她们有充分的动机全力销售这类酒来获得盈利,但在田野观察中呈现更多的是日本顾客有意将“金钱式礼物”送出。虽价格高昂,但这些酒并不意味着炫耀性消费,几乎没有一位顾客是因昂贵的酒象征了金钱或者纯粹为了消费而购买它们,购买的真正意义在于其礼物功能——将营业额送给女性:“虽然也有真正喜欢喝香槟和红酒的客人,但是大部分客人并不是这个目的……红酒和香槟是送给女孩子们的,支持她们的工作。”(58)访谈对象:浅野,男,1968年生,日本顾客;访谈人:张一璇;访谈时间:2021年7月31日;访谈地点:日式酒吧“响”店内。
“送酒”带有极强的义务特征。一些顾客时常请女性们喝香槟和红酒,自己却完全不喝,他们将之视为对女性的回馈而不计成本。此时,酒转化为披着金钱外衣的礼物参与到双方关系之中。商品的金钱价值本是交换价值的外在表现,然而在商品与礼物合一的过程中,金钱本身成为了礼物。金钱价值被日本顾客用作衡量礼物价值的标准,不回馈会令其感觉不妥当:
我在店里存的酒喝得不快,大概两个月喝掉一瓶,和常客比太慢了。这样的话,每次买单的时候只有150元座位费,非常不好意思。所以上周去店里请大家喝了1000多元的红酒,这样才合适。(59)访谈对象:上田,男,1976年生,日本顾客;访谈人:张一璇;访谈时间:2021年10月10日;访谈地点:某咖啡店。
此时,酒意味着回馈,酒的金钱价值被视作对双方关系的认可,说明在特定的社会关系之中,价值逻辑的作用并不唯一,即便是看似理性的金钱利益也被行动者阐释之后成为感性的情感表达。深层上看“金钱式礼物”的发生源自私人关系中的义务和强制。礼物交换具有强制和义务的特征,送礼与回礼是相互强化、反复发生的过程,礼物交换意味着关系的生成和巩固。礼物关系的强制性特征在以红酒和香槟为代表的“金钱式礼物”上表现得颇为明显,日本顾客将“送酒”视为理所应当的回馈,酒寄托了日本顾客对双方关系中的义务的执着,故会产生不回馈的不适感。顾客山口几乎每周都请香槟,他认为这是通过对店铺经营施以帮助来表达自身的感谢:
“妈妈桑”经营这家店很辛苦啊。现在因为疫情,很多日本人不能来中国出差,所以店里很少有新客人。这样的话,如果客人很少的话,会很为难吧,房租、电费、女孩们的工资……没有客人的时候,我会请大家喝香槟,因为知道店的困难,这是最好的应援方式。(60)访谈对象:山口,男,1972年生,日本顾客;访谈人:张一璇;访谈时间:2021年4月3日;访谈地点:日式酒吧“彩”店内。
顾客矢野也表达了类似的看法。初来中国时语言的障碍、突然转变的生活方式,以及与家人的分离使他异常痛苦,甚至时常在住所里哭泣。就在此时,日式酒吧提供了一个契机,他结识了日语流利的亚美,渐渐转变了孤立无援的处境,之后他常以“开香槟”的方式表达感谢:
刚来中国的时候非常痛苦,听不懂中文,哪里也不熟悉,生活突然变了,非常孤单……认识亚美之后,她帮了我很多忙,生活上的很多事情……下班之后经常到店里喝酒聊天,心情变得好起来了,慢慢才会觉得在这里工作可以坚持下去。香槟的钱啊没有什么关系,因为想感谢亚美,把感谢的心情传达给她,钱没有关系。(61)访谈对象:矢野,男,1972年生,日本顾客;访谈人:张一璇;访谈时间:2021年9月12日;访谈地点:某餐厅。
值得注意的是,礼物交换中的义务不是简单的、外在的强制,而必须转化为自主的意愿才能实现自身。(62)汲喆:《礼物交换作为宗教生活的基本形式》,《社会学研究》2009年第3期。在日本顾客的解释中,回礼是自主意愿,它扎根在广泛的日本社交文化价值之中:
彼此之间关系加深,对日本人来说会产生义理,义理取决于关系的深浅。如果一个日本人在这里度过了愉快的时光,或者得到了帮助,关系越来越深,他会非常感谢对方照顾自己,会想回馈对方,因为产生了义理,所以日本人会这样做。(63)访谈对象:笠原,男,1971年生,日本顾客;访谈人:张一璇;访谈时间:2021年10月15日;访谈地点:日式酒吧“响”店内。
义理的日语为“義理”,是理解日本人处理自我与他人关系时的重要概念,指人们共同认可的、相互可以依赖的人际关系,受恩受惠是构成义理的一个重要契机,当人在受恩惠时会产生一种心理上的负罪感,义理借此机缘发展成其相互扶助的关系。(64)参见[日]土屋健郎:《日本人的心理结构》,阎小妹译,商务印书馆,2006年,第20-21页。日本顾客认为自身接受了来自中国女性的恩惠与帮助,无论出于感谢对方提供了一处闲暇休憩的场所,还是感谢陌生环境里新的社会关系,抑或是感谢对方在遇到烦恼时伸出援手等,随着时间的推移,义理自然而然浮现出来。义理作为一种社交文化价值重组了行动者对待物的价值逻辑,对酒的价值判断深受义理的影响。义理所代表的感恩与回馈成功地将酒从金钱价值与交换价值中解放,印证了当商品在某种文化价值体系中被吸纳为礼物时,文化价值会对关系进行道德化的改变,进而凸显出群体的道德独特性。(65)Pina Werbner, “Economic Rationality and Hierarchical Gift Economies: Value and Ranking among British Pakistanis,” Man, vol.25, no.2(Jun., 1990), pp.282-283.从这一角度理解,日本顾客在将香槟与红酒解释为礼物的同时,也是对自身道德意义的再生产。
总之,代表着“本真性礼物”与“金钱式礼物”的酒各自发挥着作用。“本真性礼物”构建起双方的私人化关系,情感价值促使酒成为人情关系的象征物;“金钱式礼物”承载着日本顾客的感恩与回馈,在义理的影响下,看似充满金钱利益的酒被诠释为象征人情的礼物。感恩与回馈的价值逻辑将商品交换中物的金钱价值打破重组,使买卖双方的关系得以重塑。
四、分合之间:跨文化交换的破坏与保护
交换体系中的价值并非一成不变,不同价值之间互相竞争乃至产生破坏性的张力拉扯着礼物与商品之间的平衡。金钱价值中的理性算计与谋利仍旧是破坏性力量,体现为女性经营者利用男性顾客回馈礼物的过程促成更多营收。与此同时,感恩与回馈的文化价值也在暗自维护商品与礼物的平衡,对抗着理性算计的侵蚀。在规则尚未完全定型的交换体系中,商品关系与礼物关系在相互之间分与合的拉扯中促成跨文化交换的实现。
(一)作假与算计
日式酒吧中有两套“做酒”方式,一是女性经营者在顾客面前准备酒的过程被称为“做酒”,另一套隐藏的给酒作假的过程也称为“做酒”。笔者曾观察到几次隐蔽的“做酒”过程,当人数众多的团体顾客光顾时,“妈妈桑”示意其他女孩在准备酒时隐蔽地将酒瓶中的酒倒出一部分,兑入矿泉水,再将倒出的酒“复制”出另一瓶,以原价出售给顾客。(66)大部分情况下,顾客的酒不会被动手脚,兑水的现象几乎都发生在团体顾客的情形中。此时的“做酒”意味着掺水作假,是经营者为了盈利而采取的手段。小百合将中国酒吧与日式酒吧里都存在的逐利现象做对比,她认为日式酒吧里的作弊有着与中国酒吧不同的意义。她认为:“我们是兑水,中国酒吧用的是假酒。”(67)访谈对象:小百合,女,1985年生,日式酒吧经营者;访谈人:张一璇;访谈时间:2021年6月14日;访谈地点:电话访谈。她要强调的是兑水之后的“假”与中国酒吧的“假”并不相同,后者的“假”是商品关系里为了获得盈利的纯粹欺骗,它无差别地面向所有抽象意义上的顾客,而自己所处环境中的作假在一定程度上被默许,因为“做酒”是日本顾客明确知道并被包容的:“知道(兑水)。因为那也是她们工作的一部分,能理解……日本人很珍惜和她们的关系,不是太过分的话都不会说。”(68)访谈对象:上田,男,1976年生,日本顾客;访谈人:张一璇;访谈时间:2021年6月26日;访谈地点:某咖啡店。
倘若没有对礼物关系的默认,“做酒”便不会被接受,因为纯粹的商品关系代表着平等的市场交换规则,不得僭越。亚美讲述了一次自己被揭穿的经历:一位中国人和他的日本同事前来喝酒,发现亚美在酒瓶中掺水,中国顾客当场揭穿并希望日本顾客也进行指责,而日本顾客却将事情含糊了过去。(69)访谈对象:亚美,女,1985年生,日式酒吧经营者;访谈人:张一璇;访谈时间:2021年7月20日;访谈地点:日式酒吧“响”店内。两者应对方式的差异正是因为中国顾客与日本顾客对此处关系的理解并不相同,中国顾客将之视为一个纯粹的商品交换场所,作假违背了平等和诚信的市场规则,因而不会接受其中的欺诈。但日本顾客则将此处的关系视为超越单一的商品买卖关系,礼物关系里个人化的情感容忍了商品买卖里的偷换和作假。这进一步说明,礼物与商品之间的共生与依赖共同维系了整个交换体系的运转,此时礼物关系中的情感与人情对利益算计给予了一定的空间。
“金钱式礼物”同样经历了被算计的过程,香槟与红酒背后高额的利润、一次性快速消耗的特点,促使女性经营者利用日本顾客回礼的倾向劝诱他们消费更多此类商品,称为“开酒”或“做业绩”。她们有时会利用顾客主动回礼的意愿掩盖利益的获取,但更多时候,她们会将之视为双方互相付出与回报的结果:
大部分客人都很好,只要我们稍微表达一下“请我喝酒可以吗”“很久没喝香槟了”,他们会开(酒)的,跟我们关系很好的客人都是主动开……不能“当时加盐当时咸”,平时对客人好,他也对你好。(70)访谈对象:遥香,女,1989年生,日式酒吧经营者;访谈人:张一璇;访谈时间:2021年4月4日;访谈地点:日式酒吧“彩”店内。
女性经营者正是在金钱与情感的复杂关系之中寻找平衡。通过突出自己的付出,例如对顾客照顾周到、真心相待、帮助他们处理生活中的问题等,她们将顾客的回馈解释为自身付出的回报,双方都在努力争取一种有来有往的道德平衡,尽管有时伴随着偏离与越界。如此一来,酒被灵活地放置于各种价值的交叉之中,再次揭示出酒之上礼物与商品价值能够互相促成、互为己用,即礼物关系中的情感与回馈价值容忍了理性算计的存在,同样理性算计反向利用情感促成金钱价值。
(二)“情义比钱重要”
如前文所述,商品的金钱价值拉扯着礼物,双方在冲突爆发前寻求平衡。然而,当冲突真正来临时,金钱价值与道德价值之间可能会发生商品与礼物之间的割裂,此时行动者需要在价值中做出选择,从而决定物与关系的走向。奈央过生日的经历是一次透视商品关系与礼物关系之间博弈的契机。通常在女性经营者过生日时,与其关系较好的男顾客会到店庆祝,并送出“金钱式礼物”,奈央的生日同样如此。“妈妈桑”暗示她可以借庆祝之机让顾客多购买香槟以增加营业额,然而奈央拒绝了,她认为借机“做业绩”会破坏自己和客人之间的人情关系,拒绝将礼物的工具性放在首位,从而在金钱的诱惑面前保护了礼物关系:
我不想那样。我过生日,客人主动给我开香槟就很感谢他了。要是那样的话,会让我觉得是趁着生日搞客人的钱。那种话我说不出来,一个劲儿劝客人开酒开酒,以后朋友还做不做了?虽然是要做生意,但是我不想做个生意搞得跟什么似的……情义比钱重要。(71)访谈对象:奈央,女,1983年生,日式酒吧经营者;访谈人:张一璇;访谈时间:2021年9月16日;访谈地点:日式酒吧“彩”店内。
“情义比钱重要”,体现出女性经营者对人际纽带的珍视。她们同样看到了酒的金钱价值等同于表达双方人情关系的象征价值。女性经营者的价值判断,一方面来自于对日本顾客身上的义理关系的理解,尽管没有明确使用“义理”一词,但她们在与日本顾客打交道的过程中概括出了类似的意涵:“日本人很重感情”,“他越觉得亏欠你,越会对你好”;另一方面,她们还受到中国本土文化中经商道德基准的影响,欺骗与算计有违中国人自身的道德与情理,“不挣亏心钱”是许多女性经营者的底线。无论是与日本顾客之间的新纽带背后的日本社交价值,还是中国人自身的道德关照,都指向人与人之间的真诚与情感。人们共通的互惠价值跨越了文化的边界,何尝不是理性价值的广泛支配之下的另一种通约!
五、结 语
在谈及资本主义经济对其他经济的同化时,萨林斯说道:“将诸多社会属性化约为市场价值的潜能恰恰使得资本主义能够操纵文化秩序。”(72)[美]马歇尔·萨林斯:《人性的西方幻象》,赵丙祥、胡宗泽、罗杨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9年,第11页。一方面,资本主义强大的通约能力将不同的人群关系和事物体系,统统转变为以成本-收益来衡量其价值;另一方面,文化逻辑也在吸纳资本主义,使其帮助自身实现不断的再生。以之概括中国日式酒吧里发生的跨文化交换故事十分贴切。在日式酒吧中,酒在中日双方行动者对价值的选择与阐释下成为礼物交换,行动者以多元的价值逻辑重新界定了买卖关系,赋予其人情、回馈、义理等情感与道德的象征,从而使嵌入其中的酒被赋予超越商品交换价值的礼物价值,实现礼物与商品的合一。同时,礼物价值又反向为金钱、理性、算计作了铺垫,酒作为商品在礼物的伪装与遮掩下继续参与交换。日式酒吧的交换体系,既挑战了商品与礼物两种价值逻辑之间的对立,又突破了物的价值转译所发生的线性过程。商品与礼物的相互嵌入是酒得以交换的互为条件,礼物不能脱离商品,商品亦依赖礼物,二者彼此促成。
实现这一交换体系的动力,来自于行动者对既有关系和价值的重新阐释。无论礼物还是商品,抑或其他物的形式,它们所反映的都是物与人的关系、人与人的关系。(73)Yan Yunxiang,“The Gift and Gift Economy,” in James Carrier(ed.), A Handbook of Economic Anthropology. Cheltenham: Edward Elgar Publishing, 2005, pp.256-257.日式酒吧的交换体系不仅反映了各种关系,更说明即便社会场景与社会关系固定的情况下,物的价值依然能够被重新界定,并同时获得礼物与商品的属性。行动者的自主性对物与人的关系进行了多元阐释:看似支配性的经济理性关系被理解与实践为人情的表达,在这一过程中物也被编入人类文化的意义之网(74)参见[美]克利福德·格尔茨:《文化的解释》,韩莉译,译林出版社,1999年,第5页。,成为人类用以说明自我的物质表达。(75)参见彭兆荣、葛荣玲:《遗事物语:民族志对物的研究范式》,《厦门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2期。正因如此,最终我们看到的是中日双方行动者在新的生活空间中所共同编织的意义之网——买酒、饮酒、送酒、做酒共同串联起有道德的人情纽带。
资本主义逻辑使日式酒吧的双方走向同一种生活状态。日本男性在跨国公司的全球扩张安排中被迫远走海外,中国女性经营者则在资本将人的一切转化为商品的劳动力市场中付出了情感劳动,双方都被卷入更大的资本主义进程之中,在一个看似高度商品化的消费空间相遇。然而,资本主义的理性算计,既非日式酒吧交换体系中的支配价值,也非唯一价值,我们在行动者双方身上看到了共通的互惠规范。古尔德纳认为,互惠作为一种文化要素,是可以在所有价值体系中找到的普遍尺度,它在社会系统尚未完备的情形中充当起了启动社会关系的道德黏合剂的作用。(76)Alvin W. Gouldner, “The Norm of Reciprocity: A Preliminary Statement,”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vol.25, no.2(Apr., 1960), pp.161-178.与日本本土高度制度化与规范化的娱乐行业相比,中国的日式酒吧只是在全球化的缝隙中生长出的复制品。也正因如此,在资本主义规则与价值尚未形成霸权支配之时,充满道德意涵的互惠约定勾连了跨文化场域中的双方,从另一种视角看去,或许是资本主义在文化的维度上进行着自我拯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