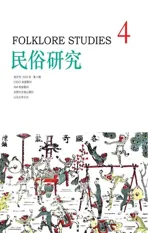方法论的本土与世界:以钟敬文与松村武雄的学术交流为核心
2023-09-20彭牧沈燕
彭 牧 沈 燕
在中国近现代学术史上,日本的影响是不容忽视的。留日学生不仅学到了日本较为现代的文化和技术,而且通过日本这个桥梁和窗口,接受了大量的西方最新思潮。由于大量的日译西书及日语对中国人的亲近,比起用西文、译西书来,当时人把翻译日译西书看作了解西方的一条捷径:“至各种西书之要者,日本皆已译之,我取径于东洋,力省效速,则东文之用多。”(1)张之洞、何启、胡礼垣:《劝学篇·劝学篇书后》,湖北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153页。因此留日学生在日本感受到的,是一种双重的学术思路:一方面是日本人自己尝试建立现代学术的各种努力与探索;另一方面,则是来自西方的传统。这种双重的学术思路与国内直接从欧美等不同国家接受的复调的西方思想交织在一起,又与本土的思想传统相碰撞,最终共同构成了中国近现代学术的多重底色。日本因此既是中介,亦成为可以借鉴的方法。(2)参见吴晓东:《作为“中介”的日本》,《长江学术》2017年第3期。
中国民俗学的开端与发展就是这样。在中国民俗学史上,周作人、谢六逸、钟敬文、何思敬等都有留日背景,特别是钟敬文,他从1929年秋到杭州,到1934年赴日两年的一段时期是其民俗学学术思想与方法成熟的关键阶段。那么,日本学界如何影响钟敬文?在其学术构型与整合中,日本、西方与中国又是何种关系?在此期间,有多位日本民俗学者都与钟先生有过交往,其中最为突出、关系最为密切的,可以说是松村武雄博士,本文即对他们的交流过程进行分析。
一、松村武雄及其神话学研究
松村武雄(1883-1969)是日本著名的民俗学家、神话学者。他与日本另一著名神话学者高木敏雄同为熊本县人,高中时代在熊本五高曾师从高木学过德语,毕业后进入东京帝国大学文科大学英文科,读书期间即开始对神话研究感兴趣,但是基本上只能在图书馆自己摸索着学习。1910年,松村原计划以《神话研究》为题毕业兼申请进入大学院(3)当时日本有三种途径成为博士:课程博士、论文博士、推荐博士,而大学院是设立在著名大学中的培养课程博士的研究机构。继续专攻神话研究,但因当时其所在的科为英文科,在教授会建议下,不得不将题目改为《英国文学中的神话研究》。进入大学院的第二年,他又提出以“神话学”为研究主题,但再一次被教授会拒绝,随即选择离开了大学院。1919年,松村开始担任东大文学部讲师,讲授希腊神话。1921年,他以论文《古希腊文化表现的诸神宗教纠葛研究》获文学博士学位。从1923年4月起,他曾作为日本海外研究员到英、德、法、奥等国留学两年。松村先生出版了多种重要著作,如《童话与儿童的研究》(1922)、《童话教育新论》(1929)、《神话学论考》(1929)、《民俗学论考》(1929)、《神话学原论》(上、下,1940-1941)和《日本神话研究》(全四卷,1955-1958)。特别是《日本神话研究》,是松村神话学的代表著作,从根本上奠定了他作为日本神话学史上继高木敏雄之后最重要的神话学者的地位。然而在创作这部巨著期间,松村的妻子患上了不治之症,卧床四年后去世,而他也在日夜不停地照护中身心俱疲,高血压、心脏衰弱、白内障并发,最终在完成这部巨著后卧床不起。此后到他1969年去世的十年间,松村没有进行任何著述活动,也未能培养自己的学术继承人。(4)参见大林太良:《松村神話学の展開ーことにその日本神話研究について》,《文学》1971年第11期,岩波書店。并可参考乌丙安:《日本神话学三个里程碑的主要代表人物》,《日本研究》1988年第3期。
在神话研究方面,松村先生凭借其语言优势继承了高木敏雄的“世界视野”,采取比较神话学的方法研究日本神话。在《日本神话研究》第一卷中,他明确指出以往的日本神话研究者,几乎都在重复使用同样的古文献资料,未能有所创见,而要打破这一僵局,就需引入三类重要的“次善”资料,即后代的文献材料、后代的民间传承(民俗)资料,以及异国异族的民俗及其记录。(5)参见松村武雄:《日本神話の研究》(第一巻序説篇)第四章《次善の資料》,培風館,1954年,第393页。其研究方法,则提倡首先以民俗学的方法,其次以人类学和民族学的方法,同时辅以语言学、古文献学、宗教学、社会学、文化史学等各种方法(6)参见松村武雄:《日本神話の研究》(第一巻序説篇)第五章《採らんとする研究法》,培風館,1954年,第433-434页。并可参考乌丙安:《日本神话学三个里程碑的主要代表人物》,《日本研究》1988年第3期。,体现出鲜明的多学科综合比较的风格。
具体而言,松村的神话学比较研究有以下特色。(7)关于松村神话研究的特色,可参见大林太良:《松村神話学の展開ーことにその日本神話研究について》,《文学》1971年第11期,岩波書店。其一是“学问的孤儿”(8)松村武雄:《神話学者の手記》,培風館,1949年,第16页。。这里的“孤儿”既指他在神话学求学之路上的孤独,又指他在探索神话研究方法时的独立性,同时还指他一生为之苦斗的孤独的神话学志业。其二是深受民俗学、人类学、民族学之影响。这一方面与其早年阅读西方进化论人类学派著作及留学欧洲有关,另一方面又与当时日本国内民俗学、民族学的发展息息相关。我们也可从其20世纪20年代至四五十年代发表的论文及著作中找到大量相关文献的引用,前者如弗雷泽(James George Frazer)、安德鲁·朗(Andrew Lang)、泰勒(Edward Burnett Tylor),后者如南方熊楠、柳田国男、伊波普猷、折口信夫(9)柳田国男已为中国民俗学者所熟悉,在此不再多做介绍。南方熊楠(1867-1941)有14年的欧美旅居史,学贯中西,掌握植物、动物、矿物、天文等各领域的博物学式的知识,以比较研究见长。伊波普猷(1876-1947)被称为“冲绳学之父”,一直为民俗学在野之学者。折口信夫(1887-1953)可比肩柳田,在学术研究方面创造了诸多“理想型”,后被称为“折口名汇”。关于以上学者的详细介绍,可参考[日]岛村恭则:《柳田之外:日本民俗学的多样化形态与一贯性视角》,李常清译,《民俗研究》2022年第3期。,而且他也常常给《乡土研究》《民族》《民俗学》等杂志投稿。其三是内深法(intensive method)与外伸法(extensive method)并重的比较研究。(10)参见松村武雄:《日本神話の研究》(第一巻序説篇)第五章《採らんとする研究法》,培風館,1954年,第457页。早在20世纪20年代,松村已提出在研究一国或一民族特有的国民神话学的同时,也要看到神话的共通性与普遍性,提倡进行比较神话学研究。与之相对应,到了20世纪30年代,他将内深法与外伸法作为一对概念提了出来。针对日本神话传统研究只注重内深法、排斥外伸法的现象,他又在20世纪40年代提出,要将日本神话作为世界神话的一环来进行研究,就必须重视外伸法。20世纪50年代,他在《日本神话研究》中进一步对外伸法进行了详细论述,如外伸法的利弊、使用时的注意事项等,并将之引入到高天原系、出云系等日本古典神话体系的研究中。
正是松村先生的这种神话学方法,使他十分重视中日神话的比较。松村不仅西文出色,中文也很好。他曾涉猎了大量的中国古籍,编成一部《中国神话传说集》(1927-1928),此书多次再版,并被编入世界神话传说大系(11)此书首次由近代社出版后,又分别由大京堂、大洋社多次再版,五年后即出到了第六版。多次再版原因,与时局相关。当时日本国内民众对中国的兴趣开始高涨,而松村这本书并非针对中国神话的学术研究,而是作为日本神话研究之比较材料的通俗读物,因此很受大众欢迎。参考伊藤清司:《解説》,松村武雄编:《中国神話伝説集》,社会思想社,1979年,第209-210页。,松村先生也因此和中国民俗学界保持了较为密切的交往。
二、松村武雄与钟敬文的学术互动
从20世纪20年代开始,松村的著作至少有如下几部被译成中文:《文艺与性爱》,谢六逸译,开明书店1927年初版;《欧洲的传说》,钟子岩译,开明书店1931年初版;《童话与儿童的研究》,钟子岩译,开明书店1935年初版;《八头蛇》,叶炽强译,启明书局1941年初版。(12)此书又以《日本故事集》为名,在三友书局和启明书局再版过。其中,《文艺与性爱》是松村根据美国人摩台尔(Albert Mordell)的《近代文学与性爱》节写的,是用精神分析法研究文学。后来摩台尔的原书,也由钟子岩、王文川译出,开明书店1931年出版。《欧洲的传说》《八头蛇》为作品集,后者是日本的,前者介绍了欧洲的十几种史诗、传说故事,如贝奥武甫、亚瑟王、尼伯龙根等,每种前有“解题”作简要说明。《童话与儿童的研究》则是松村民俗学理论的代表著作,该书中译本的出现跟原书初版也不过相差13年。此书共分十二章,从儿童的心理与生活、童话的民族心理学、民俗学与历史学以及未开化民族的心理这三方面对童话做了系统的研究。(13)松村武雄上述图书翻译出版信息可参考中国历史文献总库·民国图书数据库,http://mg.nlcpress.com/library/publish/default/Booksearch.jsp,检索时间:2023年3月10日。
虽说从数量上看,上述译著已不算少,但更为丰富且影响更大的,则是松村先生的论文在中国学术刊物上的译介。1931年6月,在钟敬文、娄子匡主编的《民俗学集镌》第1辑中,白桦翻译了松村先生的《地域决定的习俗与民谈》,此文1931年7月亦在《开展》月刊第10卷第11期发表。松村在文中探讨了“如何划定地域界限”的习俗与反映它的民间故事,文章虽然短小,但其旁征博引已足见松村风格。在编后记中,编者写道:“(松村)所著《民俗学论考》与《神话论考》[按:此处应为《神话学论考》],读之,都使人钦佩其精博。这里所译出的,是博士著作中较短篇的一个论文,但他的学殖,思想(当然指关于民俗学方面的),也足据以略见一斑了。”(14)《编后缀言》,钟敬文、娄子匡主编:《民俗学集镌》第1辑,1931年,第406页。可见当时中国民俗学界已对松村的著作多有了解。钟敬文自己曾述及在杭州时读过松村先生的《民俗学论考》和《童话与儿童的研究》。(15)参见钟敬文:《我与中国现代民间文艺学——〈民间文艺学及其历史〉自序》,钟敬文著,董晓萍编:《钟敬文文集·民间文艺学卷》,安徽教育出版社,2002年,第772页。
也正是在这个过程中,松村武雄和当时的中国民俗学者特别是钟敬文有了直接的交往。而据钟敬文回忆,他与日本学界的交流也是通过松村先生。(16)参见[日]加藤千代:《钟敬文之日本留学——从日中交流方面论述》,何乃英译,钟敬文编著,董晓萍整理:《钟敬文全集》(10),高等教育出版社,2018年,第397页。1932年10月,在钟敬文编的《民间月刊》第2期“老虎外婆故事专辑”上,秋子女士(即钟敬文夫人陈秋帆)翻译了《日本童话集》中的《山姥的手》,钟敬文(以敬文的笔名)在编者序中说:“我们邻国的民俗学者松村武雄博士,去年冬间,曾亲简述他本国(日本)这故事的情节见赐,盛情实深感佩。”(17)敬文:《写在专辑之前》,《民间月刊》第2卷第2号“老虎外婆故事专辑”,1932年,第3页。可见,至迟到1931年冬天,松村武雄与钟敬文就有了通信往来。1932年,钟敬文翻译了松村先生的《西班牙童话特色》。(18)[日]松村武雄:《西班牙童话的特色》,钟敬文译,《亚波罗》第11期,1932年。1933年,在松村先生的帮助下(19)参见金穗对钟敬文的访谈,钟少华:《早年留日者谈日本》,山东画报出版社,1996年,第28页。,钟敬文的《中国民谭型式》一文在日本民俗学会会刊《日本民俗学》第5卷第11期发表。正是这篇文章,使钟敬文受到了日本学者的注意,不仅使著名学者关敬吾先生开始关注口承文艺的研究(20)参见[日]加藤千代:《关敬吾先生与中国民俗学》,朱丹阳译,《北京师范大学学报》1992年第5期。,也最终促成了钟先生的留学。在此文的日译自叙中,钟先生曾谈到了他与松村先生的学术交流:“作者年来承东京民俗学界诸君子——尤其是松村博士——底撰文底嘱咐,在拟写作的《中国太阳神话研究》《中日共同的民间故事》《中鲜民谭底比较》等论文,一时尚未能完成交卷之前,这篇草案底送出,也算稍酬答了远在日本海彼岸三数同志底可感的热望……”(21)钟敬文:《〈中国民谭型式〉日译自叙》,《民间月刊》第2卷第9期,1933年,第276页。
钟敬文留日期间(1934-1936),曾为上海的《艺风》杂志写稿,并主编“民俗园地”栏目。在这个杂志上,多次刊登了译介松村先生论著的文章。如1934年12月出版的第2卷第12期“人类学、考古学、民族学、民俗学特辑”上,刊登了松村武雄的简介,照片下面有署名“野苍”的题记,介绍了松村先生的生平、著作,并称之为“日本之有世界地位的民俗学者、神话学者的一人”(22)野苍:《民俗学家松村武雄博士象》,《艺风》第2卷第12期,1934年,第48页。。在1935年10月的第3卷第10期上,钟敬文翻译了松村先生的《神话传说中底话根和母题》,在附记中,他写道:“这篇短文,是我所译述的神话传说概论(原名神话及传说)中底第三节……因为拙译稿全部底付印,尚待时日,而这一节文字又是完全可以独立的,所以把它先发表在这里了。”(23)[日]松村武雄:《神话传说中底话根和母题》,钟敬文译,《艺风》第3卷第10期,1935年,第82页。而在《艺风》第3卷第3期(1935年3月)上所列出的中国民俗学会丛书书目中,钟敬文译《神话传说概论》也在其中,标明“将出”(24)《中国民俗学会丛书》,《艺风》第3卷第3期,1935年,第73页。。从此书目和上述附记中的“译稿全部底付印”看,钟敬文很可能已译完了该书,但后来不知何故没有出版。
此外,在《艺风》第4卷第1期的“民间文艺专号”(1936年1月)上,石鹿翻译了松村先生的《中国神话传说短论》,此文即上文提到的松树先生那本影响广泛的《中国神话传说集》的卷首序言,文中着重讨论为什么中国神话少而传说多,认为“中国神话之少与其民族之实际的性情的关系,不在此性情自始即阻碍了神话的发生上,而是在后来采取了不适于神话存续的态度上”(25)[日]松村武雄:《中国神话传说短论》,石鹿译,《艺风》第4卷第1期,1936年,第46页。。该文还特别谈到了中国所谓志怪小说的丰富在世界上首屈一指,他称之为“文艺化了的怪奇小说”而不是简单的民间传承的故事。(26)参见[日]松村武雄:《中国神话传说短论》,石鹿译,《艺风》第4卷第1期,1936年,第48页。这种观点对我们如何看待中国笔记小说中大量的鬼怪、奇谈的记录至今颇有启发。这些文本,既不仅仅是民间口头传承的简单记录,也不仅仅是文人个人的创作,而是在一种大致相同的社会文化心态下,口头文学与书面文学交织互动的产物。而这些志怪小说,其实也一直是钟敬文民俗学研究中的重要材料。在同期《艺风》上,秋子女士在其《诸国咄中吐人故事的来源》一文末尾,亦引用松村先生的阳羡书生故事从印度起源,一面向欧洲,一面向中国传播的观点作结,可见当时松村先生的影响。(27)参见秋子女士:《诸国咄中吐人故事的来源》,《艺风》第4卷第1期,1936年,第73-76页。
钟敬文与松村学术交流的顶峰,则是对中日相关话题的比较研究与共同探讨。1933年,松村武雄应邀为钟敬文等主编的《民众教育季刊》“民间文学专号”撰写了《狗人国试论》一文,由周学普译成中文。(28)参见[日]松村武雄:《狗人国试论》,周学普译,《民众教育季刊》“民间文学专号”,1933年2月,第7-34页。其文以当时最新的西方理论解说中国典籍中的狗人国传说、盘瓠神话与狗王传说,行文颇似弗雷泽,旁征博引世界各地的例证为补充,但他对中文典籍精当的引述和运用所带来的亲切感与熟悉感,却是中国学者很少能在当时西洋学者谈及或引用中国材料的研究中感受到的。钟敬文受此文的启发,1936年在东京写成《盘瓠神话的考察》一文,发表于日本《同仁》杂志第10卷第2、3、4号上。钟文从松村先生文中一个并非重心的推断“盘瓠是某个南方少数民族的图腾”出发,运用一些口传的新材料和图腾理论,对松村先生的文章作了进一步的深化发展。(29)参见钟敬文:《盘瓠神话的考察》,钟敬文:《钟敬文民间文学论集》(下),上海文艺出版社,1985年,第103页。此文从中国古籍、民间口承等方面入手,运用民俗学、人类学理论在世界范围内比较分析,虽说不一定完全依照松村先生的思路,却也颇有相似之处。而松村先生则于1948年在其《仪礼及神话的研究》一书中,接受了松本信广、明石贞吉等人关于盘瓠传说包含狗人国观的主张,将上文修订、发展成《狗人国传说研究》一篇。文中认为狗人国传说、盘瓠故事和狗王传说就产生于中国南方苗、瑶、畲等族对狗的图腾崇拜,比起原文来,材料更为丰富,论证也更清晰、完整。(30)参见松村武雄:《狗人國傳説の研究》,松村武雄《儀禮及び神話の研究》,培風館,1948年,第271-324页。作者在文中仔细反驳了杨宽在《盘古盘瓠与犬戎犬封》》一文中提出的盘瓠故事本来是北方夷狄部族的传承的观点。
钟先生在杭州时期,松村除了为他编的刊物写文章,还为他陆续代买过自己主编的《世界神话传说集》,两人的交往应当是相当密切的。因此钟敬文1934年初到日本时,就去拜访过松村先生。(31)参见金穗1995年对钟敬文的访谈,钟少华:《早年留日者谈日本》,山东画报出版社,1996年,第28页。他留日两年多的时间中,虽“似乎并未形成以他为师的关系”,但还是与松村会面过两三次。(32)参见[日]加藤千代:《钟敬文之日本留学——从日中交流方面论述》,何乃英译,钟敬文编著,董晓萍整理:《钟敬文全集》(10),高等教育出版社,2018年,第404页。钟敬文92岁高龄时,还清晰地记得初次拜访松村时的情景,并谦虚地提到松村先生《一个神话学者的手记》中说到他时,“称我为‘知友’,是相识的人的意思”(33)“知友”一说,原文见松村武雄:《神話学者の手記》,培風館,1949年,第283页。松村在“風變りな益友”这一节中提到一位研究中国的日本益友时,说到中国地大物博,民间潜藏着数量众多的口承文学,由此说到“我的知友钟敬文等,孜孜不倦地搜集着,感觉非常可靠”。这里的“知友”,不仅仅是“相识的人”之意,更是指在学术上对他的研究有所启发和帮助的“益友”。亦参见钟少华:《早年留日者谈日本》,山东画报出版社,1996年,第28-29页。。
三、文化史、比较方法与本土立场
钟敬文居杭和留日的20世纪30年代,其实也正是柳田民俗学形成的关键时期(34)王京、王晓葵:“解说”,[日]柳田国男:《民间传承论与乡土生活研究法》,王晓葵、王京、何彬译,学苑出版社,2010年,“解说”第1页。,而钟先生对柳田的研究亦非常熟悉。1934年8月,柳田的《民间传承论》出版,1935年5月,钟敬文就在《艺风》上翻译了该书的导言,称该书是柳田的“新著同时也是名著”(35)[日]柳田国男:《民间传承论导言》,钟敬文译,《艺风》3卷第5期,1935年,第107页。。国内学者中,鲁迅和周作人很早就关注了柳田国男的乡土研究。《远野物语》初版一共只印了350本,大部分送了亲戚熟人,周作人竟有幸成为购得初版者之一,并将其学说介绍到了中国。(36)参见[日]今村与志雄:《鲁迅、周作人与柳田国男》,赵京华译,《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1992年第1期。但1949年前,柳田著述的中译文除了上述钟先生的译文,只有直江广治和一位中国学人的3篇文章。(37)检索全国报刊索引数据库https://www.cnbksy.com/,截至1949年,柳田国男著述的翻译除了钟先生翻译的上述导言,只有直江广治1944年在《华文北电》上分6期连载的《日本民谭型式》和罗伯建1943年在《中国留日同学会季刊》翻译的《山歌》和《说话的鱼》2篇(均是从其著作中节译的单篇文章),检索时间:2023年4月10日。而从上述松村的论著、论文的译介情况和他与中国民俗界乃至钟先生个人的学术交流来看,他在当时中国民俗学界的影响是相当大的。单从译文的数量和交往的频繁来说,他远远超过了柳田国男。
那么,对于当时的中国民俗学界,为什么松村武雄的吸引力与重要性会超过柳田国男?原因当然很复杂。钟先生留日期间,并未去拜访柳田。他晚年的解释是:“原因一来他是研究一国民俗学的;二来我看了他的著作,觉得自己还没有请教他的资格。”(38)参见金穗1995年对钟敬文的访谈,钟少华:《早年留日者谈日本》,山东画报出版社,1996年,第29页。简单的表述背后,其实揭示出柳男和松村所分别代表的日本民俗学内部在研究方法、学科目标上的不同取向与路径。
与柳田的一国民俗学主张不同,松村武雄所代表的这一路径,主要是借鉴西方的理论,特别是当时人类学派进化论的理论,以比较的方法,展开跨国、跨地域的文化史研究,其学术视野并不为一国所局限。在这种学术思路下,中日两国历史文化的相似性与关联性,就构成两国学者交流的根本基础和主要动因。钟先生和松村围绕盘瓠故事的研究,正是这种交流的典型体现。他们都应用来自西洋的文化理论,在比较的视野中进行阐释,由此展开文化史的探讨。钟敬文在其《中国民谭型式》日译自叙中写道:
据我个人近年来涉猎了许多日本和中国底传说、民谭的结果,觉得这两个比邻的国家底“民间口碑”,是有着极亲密的关系的。为东亚文化史(广泛点说,世界文化史)正确的究明底资助,不,为了它(东亚文化史)正确的究明底工程部分的完成,我们不能不致力于两国底这最有力的史料之一的“民间口碑”的搜集、比较和研探。……我很知道,我们邻国三数斯学先进像南方熊楠,高木敏雄,松村武雄诸先生,在那方面,早就做过一些可贵的稽考和比较的工作,虽然大都是限于文献上底材料的。(39)钟敬文:《〈中国民谭型式〉日译自叙》,《民间月刊》第2卷第9期,1933年,第276页。
显然,钟先生把自己的研究放到了南方熊楠等几位学者的比较文化史的路径中。这三位代表性学者中,除了德国文学科毕业的高木在即将留德前英年早逝,都具有西洋留学的背景。南方熊楠就是一位在美国学农学出身,又游学英伦多年的博学之士,精通中文和多门西洋语言,熟悉各地的典籍文献。由于这些日本学者对西方理论方法更为熟悉,研究也较中国为早,在中日相关话题的研究方面对中国学界多有启发。加藤千代曾评价说,松村先生虽然是将日本神话学“提高到世界水平的建设者”,但其学风“并非倡导新学说树立新学派,而是将所读破的世界万卷书忠实地予以介绍,附以自身之解释者,在某种意义上可谓担负了启蒙的、普及的工作”。(40)[日]加藤千代:《钟敬文之日本留学——从日中交流方面论述》,何乃英译,钟敬文编著,董晓萍整理:《钟敬文全集》(10),高等教育出版社,2018年,第404页。比起西方论著中对中国民俗现象颇为隔膜的零星涉及,松村先生运用西方的理论,比较世界各地的类似现象,对古籍中民俗材料的解读,这对中国民俗学者来说,无疑是更为合理、切近而可资借鉴的。特别是他讨论的中国或中日共同的民俗现象,几乎为中国学者指明了一整套的学术思路与方法。钟敬文在回忆自己留日期间所受的学术影响时,明确点明的首先是从西村真次那里接受的英国哈顿(Alfred Cort Haddon)的文化传播论,其次就是“松村武雄博士对神话的多角度的研究方法”。(41)参见钟敬文:“自序”,钟敬文:《钟敬文民间文学论集》(上),上海文艺出版社,1982年,“自序”第6页。这所谓的多角度,无疑就是上文所说的松村先生提出的以民俗学、人类学、民族学为主,以其他多种学科为辅的方法。最为重要的是,这一代日本学者都能熟练使用西文和中文,因此充分地演绎出西方理论关照下中文古籍文献所具有的崭新的学术魅力。对于钟先生这一代谙熟传统考据方法的中国民俗学者来说,从日本接受的,并不是纯粹西式的理论与方法,而是一种已然经过其本土化转化的方法,这既是日本作为桥梁的作用,也是日本学界对中国学者再次进行本土化的方法论提示。
虽然钟敬文在上述自叙中将其研究定位于世界文化史,但如果纵观他和松村的研究,并与进化论学派泰勒、弗雷泽等人的代表性研究相对照,会发现中日学者的时空框架和西方的学者依然有所不同。如果说英伦学者的研究具有鲜明的全球视野,目标是以单线进化论的线索书写以工业文明为顶点的世界史与文化史,那么,中日学者的视野显然没有这么宏大。松村的学术生涯由于种种原因以希腊神话研究为开端,并且强调神话的普遍性,但是从根本上让他殚精竭虑的依然是日本神话,他努力将日本神话作为世界神话的一环,纳入西方框架的文化史书写。钟敬文的关注则是以区域性的东亚文化史为核心,其根本的出发点和立场则是中国。他的目标是借鉴进化论线索中的各种理论假说,如图腾、婚姻制度等理论,来阐释中国本土特定区域与族群背后的历史。
在民族主义兴起和现代国家形成中诞生的民俗学,在很多国家承担着构建民族文化、界定民族身份的作用。民族语言、民族文学、民族历史因此成为民俗学构建的三个关键基石。因此,赫尔德把德语和德语文学看成是德意志民族文化的载体,“只有通过语言,一个民族(a people)才得以存在”(42)Johann Gottfried Herder, Sämtliche Werke. Bernhard Suphan(ed.), vol.18, p.387; vol.2, p.13. Hildesheim: Georg Olms Verlagsbuchhandlung. 转引自 Richard Bauman and Charles Briggs, Voices of Modernity: Language Ideologies and the Politics of Inequalit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3, p.169.。通过其继承人格林兄弟德语词典的编撰和格林童话这一德语文学的典范创造,终于为德意志的民族文化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而在现代芬兰独立前,芬兰语、芬兰文学,甚至独立的芬兰民族历史都需要进行合法性构建,《卡勒瓦拉》的发掘整理就是满足这三方面需求的产物。(43)William A. Wilson, Folklore and Nationalism in Modern Finland. Bloomington: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1976,pp.8-9, p.30.
相对于欧陆民族国家的形成与兴起,东亚的中国面对着相似但又不相同的问题。中国显然有自己的语言和文字,也有悠久的文献记载的历史。但是如果说传统的历史书写是王朝的、纪年的和局内的历史的话,现在需要将它纳入世界史的脉络,转换成局外标准的世界时间。在这个过程中,正如汪晖所指出的,顾颉刚古史辨派的“疑古”是按照西方文明的历史框架和实证主义方法,将“一切在时间的线索上、在事实的证据上无法被实证的古史内容,都必须一并被纳入神话、传说、演义乃至作伪的范畴放逐出历史的边界”(44)汪晖:《历史幽灵学与现代中国的上古史——古史/故事新辨(上)》,《文史哲》2023年第1期。。疑古派在上古史领域中腰斩古史、截断众流,“意味着将古史中无法征信的内容纳入神话、迷信、谶纬或民间故事的范围,而后再以非历史的和非事实的形式植入历史叙述”(45)汪晖:《历史幽灵学与现代中国的上古史——古史/故事新辨(上)》,《文史哲》2023年第1期。。经过科学史观研判的历史被纳入了信史,而由神话和传说等承载的历史如果要合法地植入历史叙述,则需要经过学者以人类普遍的文化史框架进行阐释与转换。虽然拥有浩如烟海的文字记载,但作为一个多民族的现代国家,中华民族的历史显然需要重新书写。
正是在这样的现代史背景下,中国民俗学承担起了构建民族文化与民族历史的重任,需要利用口头语言为基础的文学和民间文化重新书写信史所无法包含的,包括各少数民族的,中华民族的民族史。民国时期中国神话研究热潮的根本动因正在于此。钟敬文虽然不是中国神话研究的代表性学者,但神话始终是他的关注点之一,出发点也是面对中国神话贫乏问题。居杭期间,钟先生即写作了《中国的植物起源神话》《中国神话之文化史的价值》(46)参见钟敬文:《中国的植物起源神话》《中国神话之文化史的价值》,钟敬文:《钟敬文民间文学论集》(下),上海文艺出版社,1985年,第149-162、357-363页。等文章。他后期一直萦绕于心并最终交由杨利慧完成的关于女娲的大文章,自己原拟作的主题是“原始文化史”(47)钟敬文:《女娲神话研究的新拓展——序〈女娲的神话与信仰〉》,《中国文化研究》1996年2期。。
也正是在这里,我们看到钟敬文与柳田国男所代表的日本民俗学在另一条路径上的契合。柳田国男所提倡的关注日本的一国民俗学,并不是自我封闭,而是充分了解东西方世界之后深思熟虑的选择与构想。1921-1923年,柳田作为国际联盟的托管委员在日内瓦任职两年,期间阅读了大量的西方人类学、社会学著作,这点从《民间传承论》和《乡土生活研究法》中对西方学术的大量引用和精当介绍可以看出。而对于中国,他也完全不陌生。王京曾详细分析了柳田国男青少年时代的汉文阅读与写作的深厚积累,以至于他三十多岁时依然能用汉文写作。而1917年春两个多月的中国之旅,则对他的民俗学思想从山民到常民的转向产生了重要影响。(48)参见王京:《明治时期的柳田国男与中国——从汉文典籍到怪谈、民间信仰》,《文化遗产》2021年第5期;王京:《1917年柳田国男的中国大陆之旅及其影响》,《文化遗产》2018年第2期。柳田的一国民俗学,是在融会贯通西学和体察中日文化互相影响的背景之下,独创日本民俗学学科道路的努力,其目标是理解大和民族普通人的历史。中村哲曾指出:“柳田是在西欧文化的刺激下推进自己的学术发展的。不过他虽然接受了泰勒、佛莱则等学说的影响,但并没有走往比较民俗学的方向,而是以异常敏锐的感受性和心理追求来推进自己对民俗的内在本质性之观察的。……柳田一面感受着西欧民俗学的刺激及问题意识,一面又使之内化为自己的感受,并抱着日本人独自的构想采取了从民族内部观照其民俗对象的态度。”(49)中村哲:《柳田国男的思想》,法政大学出版局,1974年,第5页,转引自赵京华:《周作人与柳田国男》,《鲁迅研究月刊》2002年第9期。
钟敬文亦是在西方和日本的共同刺激下思考研究中国民间文化最合适的方式。在留日后期的1935年11月,他完成了《民间文艺学的建设》一文,奠定了他日后学科思考的基本方法论与取向。(50)参见钟敬文:《民间文艺学的建设》,钟敬文:《钟敬文学术论著自选集》,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1994年,第3-15页。在这篇论文中,他彻底超越了自己前期对民俗文化纯文学的理解,借鉴民族学、民俗学、原始社会史及文化史等理论,特别是法国社会学理论,强调民间文艺的社会性,把民俗看作文化现象,把民间文艺学界定为一门区别于普通文艺学的文化科学。(51)参见钟敬文:《我与中国现代民间文艺学——〈民间文艺学及其历史〉自序》,钟敬文著,董晓萍编:《钟敬文文集·民间文艺学卷》,安徽教育出版社,2002年,第775页;钟敬文:《我在民俗学研究上的指导思想及方法论》,杨利慧编:《钟敬文学术文化随笔》,中国青年出版社,1996年,第166-167页;钟敬文:《我的“民俗文化学”思想形成的来龙去脉——〈民俗文化学的梗概与兴起〉自序》,钟敬文:《雪泥鸿爪——钟敬文自述》,山西人民出版社,1997年,第294页;钟敬文:《自传》,钟敬文:《雪泥鸿爪——钟敬文自述》,山西人民出版社,1997年,第304页。这是钟先生第一次展示出对民间文化及其学科方法比较全面的理论思考。这也是他融汇西学与日本学者的探索,面对中国革命中“民众已将从奴隶的地位,回复到主人”(52)钟敬文:《民间文艺学的建设》,钟敬文:《钟敬文学术论著自选集》,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1994年,第7页。的社会现实,做出的学术回应。1998年,钟先生曾更详细地解释了他留日期间虽然柳田的著作就天天放在案头,但没有去拜访他的原因是:柳田主要研究日本大和民族,甚至不关心日本的少数民族,对于中国的事情比较疏远。(53)钟敬文:《在欢迎福田教授来华讲学开幕式上的致词》,钟敬文编著,董晓萍整理:《钟敬文全集》(10),高等教育出版社,2018年,第141-142页。与之对照,基于中国文化的社会历史现实,钟先生的选择是开放的,其关注的是包括各少数民族在内的中华民族。
对钟敬文而言,松村武雄与柳田国男的两条路径其实都有所助益,虽然看上去取径于松村更多,但是最终目标却与柳田更为接近,那就是立足于中国文化自己的本土传统,广泛吸收各种当时先进的和科学的方法,重新阐释中国本土文化,特别是民间文化的价值、意义与历史。在向全世界开放的视野中深入地洞察本土与地方,才是钟敬文与柳田在学术上共同的出发点与立足点。然而,各自本土的民族文化历史与现实终有差别,钟敬文并没有照搬柳田的一国民俗学,而是强调多民族的一国民俗学。
四、余论:中国民俗学的历史维度
众所周知,基于西方进化论时空观的比较方法带有西方中心主义的深刻烙印。(54)Johannes Fabian, Time and the Other:How Anthropology Makes Its Object.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83.如果说在当时的时代背景下,钟敬文还无法超越这种单线进化论的整体框架,也无法设想中国文化是否有溢出这一框架的可能,但是其努力的方向是发掘、呈现并阐释本土性民族文化史的丰富存在。对于当时的中华民族,这无疑是民族合法性和自信心的源泉。那么在当代的中国,当后殖民理论家如迪佩什·查克拉巴蒂(Dipesh Chakrabarty)等号召将欧洲归位于一个全球普通的地方,消除其现代化进程以来既充当全球标尺又充当裁判的霸权地位时(55)Dipesh Chakrabarty, Provincializing Europe: Postcolonial Thought and Historical Difference.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0; Richard Bauman and Charles Briggs, Voices of Modernity: Language Ideologies and the Politics of Inequalit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3, pp.1-5.,我们能否尝试在全球多样性的背景下,书写超越西方中心主义时空观的、地方性的中国文化史?
虽然美国文化本身亦是属于欧洲文化的演变发展,但从很大程度上看,美国民俗学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表演中心(performance-centered)的范式转型,亦是试图对比较研究及其时空框架的超越。(56)Roger D. Abrahams, “After New Perspectives: Folklore Study in the Late Twentieth Century,” Western Folklore, vol.52, no. 2/4(1993), pp.382-384.但由于美国缺乏悠久的历史,历史的维度成为表演理论中一个多少缺失的面向。(57)作为一位来自巴勒斯坦的犹太民俗学者,丹·本-阿莫斯(Dan Ben-Amos)深谙历史的重要性,他多次在课堂上提及人们对表演理论缺乏历史维度的批判。在表演中心的研究中,时间被凝缩到了表演过程的短暂时空中。福田亚细男曾质疑日本年轻学者把历史仅限于个人亲身经验的短暂时间段,强调长时段历史变迁的意义,反对将只有短暂历史的美国的民俗学方法简单搬到具有深厚历史积淀的日本。(58)参见[日]福田亚细男:《日本现代民俗学的潮流——福田亚细男教授北师大系列讲座之四》,王京译,《民间文化论坛》2017年第1期。那么在今天我们引入以表演为中心的研究方法时,中国民间文化悠久的历史是否只能被简单地归入传统与传承的笼统概括?朝向当下,当然是民俗学学科存在的必然。但是中国文化厚重的历史感、时间感是否应该孕育一种不同于美国民俗学的当下之学?这也许是致力于书写中华民族文化史的钟先生留给我们每个人的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