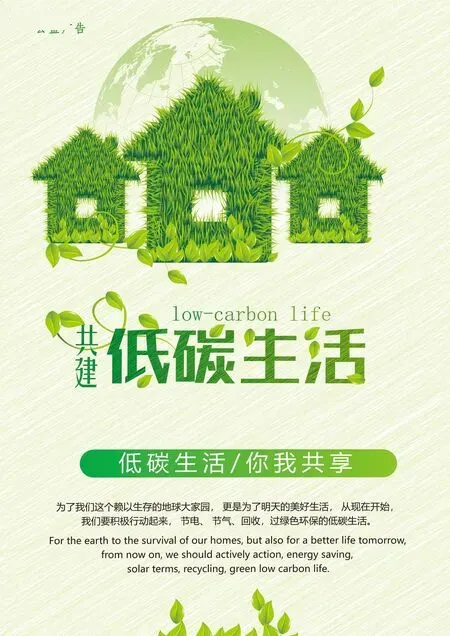浅论未成年人犯罪原因及预防对策
2023-09-19段晴
段晴
山东农业大学
一、未成年人犯罪概述
(一)未成年人犯罪概念界定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17 条规定14-16 周岁未成年人要对八大罪承担刑事责任、已满12 周岁的要为相应的行为承担法律责任,将刑事责任年龄的下限界定在12 周岁。依照我国刑法规定,未达到刑事责任年龄不成立犯罪,因而未成年人犯罪的年龄下限为12 周岁。犯罪在一般情况下具有刑事违法性、社会危害性及应受惩罚性三大特性。《中华人民共和国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界定了不良行为与严重不良行为。犯罪学往往将违反治安管理法规的违法行为甚至是不良行为也纳入犯罪范围,远远大于刑法学角度的犯罪。本文所研究的未成年人犯罪是指不包括不良行为与严重不良行为,由已满12 周岁、未满18 周岁的自然人主体实施的具有刑事违法性、社会危害性及应受惩罚性的犯罪行为。
(二)未成年人犯罪的特殊性
1.犯罪主体的低龄化
13 岁大连男孩将10 岁女孩杀害的事件让整个社会为之震惊。2018 年至2022 年,检察机关受理审查起诉未成年人犯罪32.7 万人,年均上升7.7%;其中不满16 周岁的未成年人犯罪从2018 年4600 多人上升至2022年8700 多人,年均上升16.7%。根据相关方面的研究分析,每1000 件重大案件中至少有30 件是青少年犯罪,而在青少年违法案件中,14 岁以内的未成年人犯罪比例也在快速攀升。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未成年人获取信息的渠道更加丰富,在这个一知半解的年龄中更易受到暴力、色情等不良信息的影响,从而产生某些问题上的认知偏差。在好奇心与冲动情绪的驱使下,未成年人往往以某件小事为导火索,从而爆发实施了犯罪行为。
2.犯罪事件的突发性
相较于成年人犯罪时动机的针对性和犯罪准备阶段的充足性,未成年人犯罪事件多具有突发性和不确定性。他们因生活经验不足,思想和心智尚未完全成熟,无法做到是非分明,易受周围群体影响。在成长过程中不能有效释放父母以及自身所处环境对其施加的压力,难以控制自身情绪,以致其冲动犯罪。
3.犯罪手段的智能化
当代未成年人生长于网络快速发展的时代,对新兴技术兴趣十足。在犯罪过程中,犯罪手段趋于技术化、智能化。在犯罪过程中,他们往往采用网络技术性手段,例如投放病毒,盗窃媒体账户、网络诈骗、钓鱼网站等。2019 年至2021 年,检察机关分别起诉未成年人涉嫌利用电信网络犯罪2130 人、2932 人、3555 人,同比分别上升37.65%、21.25%。其中,未成年人涉嫌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明显上升。
4.恶性案件的多发性
广西13 岁少女因嫉妒杀死同学并肢解尸体案;湖南13 岁男孩锤杀父母案;12 岁男孩连续砍下二十刀致母亲死亡等恶性案件的发生无不彰显了犯罪手段的残忍性。未成年人在实施犯罪时,由于深感个人力量过于单薄,为消除单独行动的恐惧,往往会采取共同犯罪的方式—找帮手。犯罪人数的增多会导致矛盾的过度激化,使得恶性案件多发。《未成年人检察工作白皮书(2021)》显示,2021 年检察机关受理审查起诉未成年犯罪嫌疑人数居前五位的分别是盗窃罪、聚众斗殴罪、强奸罪、抢劫罪、寻衅滋事罪,占比超未成年犯罪总人数的三分之二。由此可见,未成年人犯罪的手段多采用暴力且具有团队作案的特征。
二、未成年人犯罪的原因分析
(一)自身心理原因
未成年人由于涉世未深,世界观、价值观尚未成型,外界的“单向化”吸收使其更易受外界不良事件影响。未成年人自我感觉利益受损,需求不能得到满足,于是就产生了不良心理质变与消极情绪增值,诱发了激情违法犯罪动机。因为情绪的起伏,他们的意志也很容易动摇,缺少毅力和自我控制。在情感与意志上的矛盾若没有正确的引导,未成年人往往会选择以违法的方式彰显其“勇敢”“讲义气”,具有“英雄主义”的特点。
(二)家庭学校教育原因
对于家庭教育的原因,一方面是家长对孩子过度溺爱,家长无条件地满足孩子们的所有要求,养成了孩子们有求必有应的习惯,家长们也并未指出孩子们的不良习惯,反而使其放纵。另一方面是家长过于追求给孩子们创造良好的物质条件,忽视了他们的精神需求,此时他们往往会选择忤逆父母行为通过放纵来引起家长注意与关心。在家中父母的相处方式也会影响未成年人的成长,父母之间动辄打骂,以暴力方式相处,极具模仿性的孩子们也会在潜移默化中养成暴力等不良行为。在当代社会中,学校过于追求升学率,只注重教学成绩,忽略德智体美劳的全面发展,忽视青少年成长时的心理健康。将青少年根据成绩分为三六九等,让孩子们从内部产生压力却又无处释放,对成绩差的学生区别对待,或以暴力相向,将其推向社会,使差生产生心理偏差,从而走向违法犯罪之路。
(三)社会环境原因
当代社会上有许多不良风气,在经济市场中有金钱至上的观念;在文化市场中有封建迷信、淫秽色情的内容;在网络环境中有的凶杀暴力的画面,它们都腐蚀着未成年人的思想。农村中早早辍学无所事事的未成年人往往会选择加入其他社会青年的队伍,他们好惹事端,依仗人多势众,赌博打架等无所不为,往往体现为共同犯罪的形式。社会不良环境以及社会上的一些不法分子对他们的行为与思想起到了诱导的作用,使他们性格越来越暴戾,行为越来越粗鲁,最终为了达到目的不择手段。
(四)未成年人犯罪成本低、刑事责任年龄制度不完善
因对刑法本质认知不同,刑事责任年龄的修正观点中有降低论、维持论、个别调整论之争。按照当今理论界占据支配地位的意思能力说,刑事责任能力即行为人辨认或者控制自己行为的能力。刑事责任年龄的下调适应了当今未成年人心理发育提前成熟的现象。但是只一味地降低刑事责任年龄并不能解决未成年人犯罪的根本问题。《刑法修正案(十一)》对未成年人应当追究刑事责任的情形,在行为性质、犯罪后果和适用程序等方面均做了严格限制,案件适用较为有限。未成年人身心发展素质具有极大的不确定性,仅仅依据“一刀切”的纲要化规定来判断未成年人认知与自我控制能力的成熟与否,不能从根本上预防与解决未成年人犯罪问题。
法律追究未成年人的犯罪行为特定化,对于除此外的其他犯罪行为,刑法并未规定追究刑事责任。因不满十六周岁不予刑事处罚的,责令其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加以管教,仅仅采取管教和批评教育方式,且未成年人的刑罚适用高概率为自由刑,又因对其应当从轻或者减轻处罚的规定,一般适用短期刑期,短期自由刑罚的效果难以保障。对于他们而言,以未成年人之名实施犯罪行为成本较低。并且这种较低的犯罪成本还会更深一步地引发更多更严重的未成年人违法犯罪。
三、未成年人犯罪的预防对策
(一)加强未成年人心理辅导
家长及学校要充分关注未成年人的心理。对于一些心理出现问题的未成年人,应该及时采取心理辅导加以干预。未成年人处于青春期,心理状态不稳定,政府相关部门可规定在校园或社区内部开设心理活动中心,每个地方驻派专门的心理咨询师,定期对青少年收集心理问卷。加强青少年身心素质的培养,引导青少年走向健康心理的道路。
(二)家庭心理防御
家庭环境在所有国家中都是影响未成年人健康成长最重要的因素,因而家庭对于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有着重要的作用。家长们在日常教育未成年人过程中要注意方式方法,不可过度溺爱,不可使用暴力等极端教育方式,教导孩子明辨是非,及时指出行为错误之处并强令其改正;在日常生活中,向孩子们普及法律知识,增强未成年人法律意识;不要一味追求物质生活的优越,重视孩子们的精神需求与心理状态,及时进行精神需求的满足和心理状态的辅导。
(三)学校预防
学校不仅是传递知识的地方,更是青少年形成正确的价值观、养成健全的人格、培养良好的品质的场所。学校全面贯彻党和国家新时期的教育方针, 进一步加强思想道德教育,坚持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培养方针;关注未成年人的心理健康,引导学生向老师倾诉烦恼,及时处理学生矛盾,减少校园暴力的发生;分阶段、分批次向不同年级的青少年普及法律知识,结合不同学生的认知能力,开展法律课程教育。
(四)社会层面
预防青少年犯罪是一项长期而艰巨的任务,各级政府无论是从组织上还是制度上都要保证全面贯彻落实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的各项措施,担负起在预防青少年犯罪方面的责任。政府及相关部门加强文化市场、网络市场监管,对于暴力、色情内容的传播要遏制在摇篮里;对于不适合青少年进出的酒吧、网吧、歌舞厅等场所的活动内容进行严格限制,街道、居委会要主动净化社区或所在社会环境,相关地区公安部门严厉打击黑恶势力,防止青少年被不法分子利用;加强法治宣传教育,利用网络、电视广播、新闻媒体等方式进行普法宣传教育,通过设立图书馆、文化馆、体育馆等丰富青少年的课余活动。
(五)完善法律制度
1.健全法律制度体系
总体上应当健全青少年法律制度体系,完善相关法律制度。我国目前有关青少年犯罪的法律法规比较简略,空白多、线条粗,导致实际操作难度大。应当完善具体法规制度,通过新增一些预防青少年犯罪科学的惩罚措施,提高未成年人犯罪成本,要加强法律责任的多元化、加强对犯罪的认识和惩罚的细化,既要为受害者和家人讨回公道,又要维护法律的公正,最大限度地抑制未成年人犯罪。增加对未成年人父母义务的规定,对于无法追究刑事责任的犯罪人可适当追究父母责任,增加罚款等行政责任,必要时承担相应的刑事责任。在司法过程中,法院可邀请当地青少年观摩犯罪庭审,结合相似案例进行普法教育,增强青少年法治观念。
2.移植重塑“恶意补足年龄制度”
在刑事责任年龄方面,各个国家根据自己的政治、经济等相关情况,有着“四分法”“三分法”“绝对二分法”与“相对二分法”的划分。美国大部分州遵循一般法,即7 岁以下完全不具备刑事责任能力,将刑事责任年龄规定得较低。依笔者之见,我国不必将刑事责任年龄下调至七岁,在未成年人犯罪数量连续多年下降趋于平稳后有所回升的形势下,在立法上可以考虑移植重塑英美法系的“恶意补足年龄制度”。“恶意”是指行为人对危害行为所具有的辨别能力,即行为人可以认识到该行为在法律上或道德上是错误的。恶意补足年龄制度原则上可以推定未达到法定年龄的人不具有刑事责任能力,但是控方若能够证明他们是在犯意的支配下实施行为,可以补足年龄,使其承担刑事责任。若要将“恶意补足年龄制度”本土化,基于传统观念中的“恤幼”思想以及《刑法修正案(十一)》对刑事责任年龄的下调,依笔者之见,该制度的主体范围应当规定在12 到14 周岁,罪行范围限定在《刑法》中规定的相对负刑事责任的八大恶性犯罪。对恶意的认定应当结合事前是否预谋、事中手段是否残忍、事后有无掩盖罪证等因素。通过专业机构,经过特定程序,展开社会调查与心理评估,并综合实施类案检索,为“恶意”的认定提供依据。控方应保证证据确实、充分,排除合理怀疑,严格要求入罪证明标准。为遏制司法腐败现象,可在程序中规定应当经过最高人民检察院核准追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