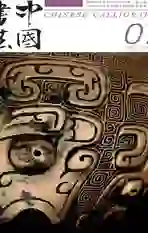从西夏陵出土汉文碑刻书风看宋金西夏间的书法传播
2023-09-14邵军王怀志
邵军 王怀志



关键词:西夏陵 碑刻 汉文书法
西夏陵园及周边西夏墓葬在近些年的考古发现中,持续出土了大量的残碑。这些残碑包括了西夏文和汉文两种类型,其中汉文碑残石总数量超过一千块,总字数达到数千个。这些碑刻不但具有重要的文献和文物价值,而且具有一定的艺术价值,是我们认识和了解西夏书法艺术、研究汉字书法在西夏的传播等问题的重要材料。由于西夏特殊的历史原因以及文献资料的匮乏,学界对西夏的书法艺术研究不多。有之,则主要是对神秘的西夏文书法的探索,对汉文书法则较少关注。[1]
西夏立国长达一八九年(一〇三八—一二二七),加之其陵墓都曾遭到大规模破坏,因此出土的碑刻具有时间跨度大、残损严重、文字零散和信息不全等特点,这给我们认识和研究西夏汉文碑刻书法艺术造成了很大的难度。笔者曾在西夏王陵管理处工作,较多地接触了这些残碑,感到只有从书风的类型及其流行变化、艺术的渊源与成就、主陵碑和陪葬墓碑的相互关系等问题进行相对深入的研究,才能窥见西夏汉文书法的大略。否则,面对数量如此庞大的碑刻残石,虽然感到它的重要,但仍会无所适从。有感于此,笔者尝试从书风及其类型的角度对有关西夏陵墓出土的汉文碑刻做一些清理和研究,并对其与宋金碑刻书法的关系略作探讨,请方家指正。
西夏陵墓汉文残碑的出土概况
西夏陵园现有帝陵九座,陪葬墓二百五十五座,其中帝陵和等级较高的陪葬墓都建有一个或两个碑亭。此外,在西夏陵园区周边,还存有一定数量的西夏贵族墓地,有的亦建有碑亭。一些经过正式发掘的陵墓先后出土有数量不等的汉文石碑残块,另在部分陵墓的地表清理和日常管理中,也发现了一定数量的汉文石碑残块。残碑上的字形大小以3-5c m为主,较小者约2c m,较大者约7-8c m。现将这些陵墓出土汉文石碑残块的情况概述如下:
帝陵出土的汉文石碑残块:西夏帝陵中经过发掘的只有现编号为六号陵(原编号为八号)的一座。此陵在一九七二年发掘了墓道和部分地表遗迹,其中就清理了两座碑亭。在西碑亭发现西夏文残碑石四百多块;在东碑亭发现了西夏文残碑石三百多块,汉文残碑石三百二十一块。二〇〇七至二〇〇八年再次对六号陵的回填土及地面遗迹进行了清理发掘,又发现了一定数量的西夏文和汉文残碑。这些残碑表面呈黑色,或为墨拓抑或火烧所致。[2]汉文残碑中,最大的存二十余字,最小的仅存一字。字大小约3-4 c m见方,青砂岩,阴刻楷书。
現编号为七号(原编号为二号)的一座主陵亦出土大量汉文残碑。一九七五年九月,宁夏考古工作者对此陵的两座碑亭进行了清理。西碑亭出土残碑全为西夏文,计有一千二百六十五块;东碑亭出土残碑全为汉文,计有五百一十块。根据西夏文及汉文残碑额有﹃护城圣德至懿皇帝﹄(此为西夏第五代皇帝仁宗仁孝的谥号)字样,知此陵为西夏﹃寿陵﹄。此陵两碑亭虽然汉文和西夏文完全分开,但据学者考证,文字内容则基本相同。[3]此碑亭出土汉文碑刻保存相对较好,碑面呈朱色,字皆鎏金,最大残石存字三十一个,十字以上残石达数十块。字大小约3-4cm见方,阴刻楷书。
现编号为五号陵(原编号为十号)的一座帝陵,一九七七年当地考古工作者对其碑亭和献殿进行了简单清理,获得了一定数量的西夏文和汉文残碑石。此陵的西碑亭为西夏文碑,东碑亭为汉文碑,出土残碑约有十八块。汉文碑残石中最大的一块约存三十七字,字约2-3cm见方,阴刻楷书。
此外现编为四号陵、八号陵的两座帝陵碑亭中亦采集到一定数量的汉文残碑,尤其四号陵出土一块残碑尚存十五字,风格独特,对研究四号陵的年代应有意义。这些残碑石多为砂岩,阴刻楷书或略带行书。现编号三号陵的地表经过科学发掘,在其碑亭中仅出土了大量西夏文残碑,未见一块汉文残碑块。[4]现编为一、二号陵的两座帝陵亦出土了一些石碑的边饰,但尚未发现文字碑块。
陪葬墓出土的汉文碑残石:西夏陵园区经过完整考古发掘的陪葬墓主要有MⅢ-107号(原编M177)、MⅣ-001号(原编M182)号等少数几座。这些陪葬墓和MⅢ-093号、MⅢ-057号、MⅣ-014号等一些墓的碑亭中皆出土数量不等的汉文残碑。MⅣ-001号陪葬墓出土了目前为止西夏陵墓碑刻中汉字数最多的残碑,这些残石共二百一十六块,其中最大的一块存有近一百字,总共可见汉文字数在一千五百字左右。[5]这些残碑不仅数量巨大、信息丰富,而且面貌多样,风格各异,反映了西夏汉文书法的水平。
汉文残碑的书风类型及分期
西夏陵出土的残碑,绝大部分为楷书,其书风以取法唐楷为主。笔者整理了目前所能搜集到的汉文残碑,并对其书风进行了辨析,其中遗存数量较大且书风较为明显者,如表一。
西夏陵区的陵墓前都设有碑亭,帝陵一般都有东西碑亭,高规格的部分大型陪葬墓也建有东西两座碑亭,部分中型、大型陪葬墓则只建有一座碑亭,小型墓葬则未建碑亭。[6]从已有的考古发现来看,碑亭中所立之碑绝大多数同时有汉文碑和西夏文碑两类,少数碑亭所立仅见西夏文或仅见汉文碑。通过残碑的出土信息推断,同一陵墓碑亭中发现的这些石碑未必是在同一时期所立,但多数情况汉文碑和西夏文碑是分立在东西碑亭的,[7]当然也有混合在一起的情况,东西碑亭在制度上是否有汉文、西夏文的区分,并不能十分确定。即便如此,从考古发现来看,虽然每个陵墓的汉文残碑风格并不完全统一,但是基本一致的,从中可以看出其主要的书写风格。
西夏陵区所发现的汉文残碑中,数量最多的一类是柳体书风。七号陵、八号陵以及MIV-001等陪葬墓都能看到大量柳体残碑。七号陵为夏仁宗仁孝之寿陵,出土的汉文残碑有篆书碑额以及记录、赞颂仁孝生平及功德的文字。从七号陵东碑亭出土的崇宗乾顺《灵芝颂》诗句残碑来看,其字形方中见长,结体宽博,落拓大方,仪态冲和,其笔画硬挺沉着,方整中见遒媚,属较为浓郁的柳体风格。部分字的书写,在起笔及笔画转折处顿笔较为明显,右竖加粗,又使得该碑略有颜体书风之特色。这与晚唐、五代以来流行的成熟柳体楷书有明显不同,其来源值得我们注意。我们从西夏陵三区、四区的一些陪葬墓碑亭遗址采集的残碑块,虽然残存的字数不多,但多数与七号陵残碑柳体书风是高度一致的。
具有欧体特征的书风在西夏陵发现的汉文碑刻中也比较常见。六号陵是经过现代考古发掘的墓葬,其西碑亭遗址出土的汉文残碑中存约三百五十字。[8]这些字点画劲挺,多用方笔,主笔外拓,字形略偏长形,结体严整峻峭,有挺拔俊秀之感,具有唐楷歐体的特点。其中,一些字的笔画又有魏碑特点,如上点写作横势,捺画出现捺脚,加之刀砍斧剁般的方笔,可以看出,六号陵碑石上的字其书风是在欧体的基础上又融合了魏碑的特点。四号陵虽然没有进行考古发掘,但从其碑亭遗址采集的一块残碑存十五字,其书风亦为欧体,不过圆笔较多,略带虞风。五号陵东碑亭出土的汉文残碑其字形虽较小,但笔画显细劲,方圆并包,结字严谨隽秀,行笔流畅爽利,有浓郁的欧虞之风。一些陪葬墓也流行欧体书风,如M I V-014(M188)陪葬墓汉文残碑数量虽不多,但残存的字数不少,最大的一块有三十多字,书风与五号陵完全一致,也是欧虞风格(另有几块残碑略近柳体)。不难看出,西夏陵汉文残碑中近欧体书风者,多带魏碑或虞世南风格。
此外,西夏陵区还出土了一定数量的唐代褚遂良风格和颜真卿风格的碑刻残石。M I V-001(M182)号陪葬墓因其残碑中﹃梁国正献王神道﹄﹃谥曰正献(王)﹄等文字,被学界认为墓主是活动于毅宗、惠宗至崇宗时期的梁国正献王嵬名安惠,是崇宗乾顺显陵的陪葬墓。[9]此墓出土汉文文字量大,内容丰富,其碑刻书风虽有几种,但主要是褚遂良一路。从遗存字数较多的几块残碑来看,笔画以方笔为主,方圆并用,细劲雄肆,开合有度,结体谨严之中,又见其婉媚,宕逸多姿,其审美旨趣外柔内刚,近于褚遂良《房玄龄碑》,所谓﹃看似离纸一寸,实乃入木三分﹄,[10]是非常成熟的褚体风格。目前发现有此类书风残碑的墓葬虽不多,但皆比较典型。另外,除大量的与柳体书风糅合在一起的碑刻外,在一些墓葬碑亭中也采集到比较典型的颜体书风残石标本。六号陵地宫中发现的石经幢上所刻文字近于魏碑书风。在帝陵和陪葬墓的碑亭中都发现了风格一致的小篆碑额残石,在个别的陵墓碑亭中还采集到了行书碑的残片。
从以上初步的分类清理中我们不难发现,西夏陵区发现的汉文残碑,其书风类型还是比较清晰的,即以柳体为主的一类和以欧体为主的一类。书风的流行有其时代性,根据一些年代比较确定的陵墓出土的汉文残碑书风,我们可以尝试区分西夏陵区汉文残碑流行书风的前后关系。
柳体书风流行的时代主要是在西夏中后期。出土柳体书风残碑最多的是七号陵以及八号陵,还有这两座陵墓周边的三区、四区的部分陪葬墓。七号陵陵主公认为仁宗仁孝,一一四〇至一一九三年在位。七号陵汉文碑约立于桓宗纯佑时期,距西夏灭亡约三十年。八号陵位置上距七号陵较近,汉文残碑书风一致,按照昭穆葬法推断,当为仁宗仁孝后之帝王,最有可能为桓宗纯佑之庄陵。MIV-001陪葬墓墓主一般认为是梁国正献王嵬名安惠,其墓前虽只建一座碑亭,但出土了大量汉文和西夏文残碑,内容丰富。梁国正献王约卒于一一二九年前后,此时乾顺在位,但安惠家已经失势。此墓汉文碑可能为后世所立,其中一块残碑中有明确纪年,是在光定五年,即梁国正献王去世八十多年后的遵顼时期。[11]此时已是西夏末期,碑文为柳颜书风,与七、八号陵是一致的。MIV-001残碑中又有偏于褚遂良风格的一类,似乎与上述柳颜书风残碑不是同一块碑,如果下葬时有立碑,或即是这类褚体书风的残碑。可见柳体为主的书风主要流行于仁宗仁孝及以后的约八、九十年间。
以欧体为主的风格则主要流行于西夏开国前及开国后的一段时间,六号陵可为代表。关于六号陵的年代问题,虽然有不同的看法,但一般还是认为其属于西夏比较早期的一座陵墓。[12]闽宁村西夏墓地虽然不在西夏陵区范围内,但由于其为野利家族墓地,[13]地位尊显,其七号墓出土残碑石十一块,除篆书碑额一块外,其余均为汉字楷书。闽宁村西夏墓地二号碑亭遗址出土石碑残块所存汉字,有魏碑遗风;其三、四号碑亭遗址出土有汉文残碑石二百多块,书风不统一,但总体仍有魏碑书风特点,略兼欧风,与西夏陵区六号陵出土汉文残碑风格基本一致,可见二者时代略近。从墓葬形制分析,其属于唐五代与西夏陵区墓葬的过渡形制,[14]符合西夏早期的特征,加之野利家族也主要活动于西夏前期,可以确定,西夏前期碑刻中流行这种欧风兼带魏碑的书风。四号陵残碑书风与六号陵一致,其陵主无论是属于李继迁还是李元昊,也都是建于李元昊时期,属于西夏前期。
近年来,西夏文书法的研究逐渐受到学界重视,有关西夏文书法的发展时段问题也有讨论。[15]根据目前看到的汉文残碑观察,结合学者们对西夏文书法的分期,我们可以尝试将西夏陵汉文书风分为两期,即从西夏立国至崇宗乾顺中期为前期,乾顺后期至西夏灭国为后期,中间或者存在一种过渡时期,这需要更多的出土材料来予以更细的区分。
书风来源与宋金西夏碑刻书风传播等问题
有学者认为西夏地区汉字书法水平整体是较为低下的,[16]如果仅仅以目前看到的西夏陵出土的残碑以及黑水城等地出土的少量墨迹书法来看,可能的确有一种未臻完美的感觉,特别是与同时期中原地区的名家书法比较起来,就显得差距尤其明显。但是,考察西夏陵汉文碑刻的书法水平及其风格来源,不能不考虑和比较同期宋、金等地同类作品的风格和水平。
西夏虽然是西北党项民族建立的政权,但在陵墓书法的制度上与中原地区的北宋、辽以及金、南宋都关系密切。北宋皇陵出土的大量墓志、辽庆陵出土碑刻以及金代遗存的大量石刻都可以作为考察西夏陵出土碑刻书法相关问题的重要参照。《嘉靖宁夏新志》载:﹃贺兰山之东数军巍然,即伪夏所谓嘉、裕陵是也,其制度仿巩县宋陵而作﹄[17],这就是说西夏陵墓的形制等各方面与宋陵是一致的,虽然西夏陵在前部所设的碑亭,在宋陵前没有,[18]但宋陵同样以石刻的方式留下了大量的墓记碑和墓志石。从书体来说,西夏出土的汉文碑刻,绝大多数为楷书,只有极少数为略带行书笔意的行楷书,碑额为小篆书,这从目前发现的七号陵残碑、梁国正献王墓残碑等材料中可以清楚见到。这与北宋出土的墓志、墓记情况是完全一致的。在百余方北宋皇陵墓志材料中,[19]行书仅两方,志盖为楷书一、隶书一。此外,西夏陵区几乎每座陵墓碑亭发现的残碑中,都发现了围绕文字所刻的线刻纹饰,纹饰绝大部分为卷云纹、卷草纹或波浪纹,在七号陵的残碑中,还看到了卷云纹与云龙纹交替的二方连续纹饰。这种做法,在北宋皇陵所出的各类墓志石及墓记碑中,也是常规做法,从《新中国出土墓志·河南卷》《北宋皇陵》等书所收录的拓片看,一般也是在四周刻有卷云或卷草纹。再从书写者来说,﹃立蕃字、汉字二院,汉习正、草,蕃兼篆隶,其秩与唐、宋翰林等﹄[20],可见西夏是仿唐宋例,在朝中设有类似翰林学士一类专事汉字书写的官员。虽然不能从西夏陵残碑中获得直接的书写者姓名,但按照《凉州重修护国寺感通塔铭碑》中汉文的书写者张政思为西夏﹃供写南北表章﹄的官员这一点来看,与文献记载相合,西夏皇家陵园碑文的书写者也当为朝中专事书写的官员。北宋皇陵的书写者也多为朝中文学之士,如《赵玄祐墓志》的书写者即为﹃翰林待诏朝奉郎守秘书丞同正赐绯鱼袋﹄裴瑀。[21]从这些方面来观察,西夏陵汉文碑刻的书写,整体还是受到了来自宋、金等中原地区的影响。
西夏陵碑刻汉文的书风也主要是接受了来自中原地区的影响。六号陵及一些陪葬墓碑亭中发现的汉文残碑的欧体兼魏碑的书风,应是北宋前期魏碑书、欧体书风流行的反映。西夏前期流行欧体兼魏碑书风,与北宋皇陵墓志石及墓记碑中大量流行魏碑及欧体书风是高度一致的。从河南巩义出土的大量北宋时期的墓志或碑记中,我们能看到魏碑风格、欧体或二者间杂的这类作品从北宋初年直至公元一一〇〇年后仍在流行。如宋嘉祐五年(一〇六〇)《赵世及墓志》就是非常典型的欧体书风,而元符三年(一一〇〇)的《潘氏墓志》则是兼有欧体和魏碑的那类风格。[22]可见西夏陵汉文残碑中欧体结合魏碑的书风,亦能在北宋的碑刻中见到其渊源。此外,辽代的书法可能也对西夏前期的魏碑体书风有一定影响。辽代的造像记中主要流行魏碑,其书风﹃还保留着北魏以来的风气﹄[23],在西夏的对外文化交往中,前期也与辽往来密切。不过,辽代碑刻﹃辽金并起朔方,而辽碑最少,苦无士气﹄[24],可能是以﹃斧凿代书丹﹄技术完成的,西夏陵及周边墓葬中(如野利家族墓碑)某些有浓郁稚拙之感的魏碑风格或者與辽碑的此种特点有关。
以仁宗仁孝寿陵汉文碑刻为代表的柳体书风,其典型特征是兼有颜体的一些特点,与敦煌藏经洞所出晚唐柳公权书《金刚经》已有非常明显的差异,[25]它显然不是对晚唐以来柳体书风的刻意模仿,而是接受了来自中原地区碑刻书风的影响而得以形成。西夏后期与金并存,而金代碑刻书风,主要流行颜、柳书风:
金碑文体学苏,书体学颜、米……其时正书之学颜者,任南麓(询)、赵黄山(沨)是也……金末石刻风气又变,学米之行书已稀,传世碑版,正楷复近颜、柳。
金代石刻多出自党怀英之手,赵秉文《中大夫翰林学士承旨文献党公神道碑》中云:﹃小楷如虞、褚,亦当为中朝第一。书法以鲁公为正,柳诚悬以下不论也。古人名一艺,公独兼之,亦可谓全矣。﹄[27]从中可见颜、柳书风在金代碑版书及士人中流行的情形。
从金代遗存的碑刻作品来看,我们能很清晰地看到类似的这种融合了颜、柳的书风。叶昌炽说:﹃忻州《普照寺碑》学柳诚悬,世有出蓝之誉,金碑第一﹄[28],此碑虽毁,但从残碑拓片来看,当不是虚言。此碑为集柳字,可以看到柳风在金地流行之盛。明昌六年(一一九五)赵沨所书楷书石刻《时立爱神道碑》的书风则融合颜、柳,这与西夏陵流行的柳、颜风格是一致的。《普照寺碑》书于金皇统四年(一一四四),西夏仁孝于一一四〇年登基,七号陵的碑刻约书于桓宗天庆初年,天庆元年为一一九四年,从中不难看出,西夏陵碑刻中的柳、颜风格与金地碑刻风格高度同步,关系密切。同时,我们从北宋末期的一些碑刻中,也能看到柳、颜体书风的风尚。《庚子消夏记》卷七云:﹃柳公名墨行世者,李西台爱《柳尊师志》,欧阳公爱《高重碑》,蔡君谟爱《阴符序》,米元章爱《金刚经》,薛道祖爱《崔陲碑》﹄[29],在宋夏的文化往来中,这种风气也对西夏汉字书风有所影响。
西夏中后期在政治及文化上与金联系非常紧密,是一种主从关系,[30]金代中原地区的文化向河西地区传播,是此时文化交融的典型特征。中原地区流行的碑刻书风也在西夏打下了深深的烙印。西夏七、八号陵及周边陪葬墓流行的柳、颜书风,是金地柳、颜书风盛行和影响下的产物。
西夏上自帝王,下至一般士人,皆有精工汉字书法者,也产生了成就较高的书法家。这些书法家有的本身就来自中原地区,有的则出自西夏本地,因为出使等原因有大量接触中原书作的机会。他们的出现和书法活动是汉字书法向西夏地区传播的自然结果。《西夏书事》卷四:﹃(端拱元年)太宗因召赴阙,赐姓名,亲书金花五色签赐之,授夏州刺史,充定难军节度使及银、夏、绥、宥、静等州观察处置押蕃落等使。﹄[31]又《宋史·夏国传》上:﹃表求太宗御制草诗隶书石本,且进马五十匹,求《九经》《唐史》《册府元龟》及宋正至朝贺仪,诏赐《九经》,还所献马。﹄[32]这是宋朝帝王书迹进入西夏的实例。往来宋夏、金夏的使臣,书家也不在少数,他们将宋朝的书迹以及各种汉字书写的规范、书风等带入了西夏,并产生一定的影响。西夏则从帝王至一般文士,亦从这种往来中,熟悉并擅长书写汉字。《西夏书事》卷三十九:﹃遵顼端重明粹,少力学,长博览群书,工隶篆。﹄[33]又《西夏书事》卷二十四:﹃故事:受中国给赐,必遣使赉表谢﹄[34],以当时情形来看,西夏谢表的书法水平及书风特点,当是与北宋接近的。西夏颇有成就的书法家刘志直就有出使中原金朝的经历,[35]刘志直,官翰林学士,工书法,他曾取黄羊尾毫制成毛笔,在西夏颇为流行。[36]从中更可看出,西夏派往金的这类善书的使臣在中原地区活动,不可能不对中原地区的书法有所留意和学习,进而对西夏本土的汉文书法产生影响。
西夏陵残碑书风既多种多样,又有大致流行的时代特征。史金波说它们﹃圆浑雄健,匀整端庄,颇有汉字颜体风韵﹄﹃古朴敦厚,遒劲有致,又有汉字欧体特色﹄﹃筋骨犀利,结构劲紧,有汉字柳体的格调﹄﹃端庄古茂,在楷隶之间﹄,[37]这虽是就贾敬颜所藏西夏陵残碑书风而言,但也反映出西夏陵碑文书法主要风格并存的情形。同时,我们也应看到,这些书风有其明显的来源,且大致与中原宋金地区流行的碑刻书风一致。西夏陵汉文碑刻书风的前后变化以及其与宋、金的碑刻书风的密切联系,一方面有助于我们认识十一至十三世纪各民族书法交流的密切情形,另一方面也能帮助我们认识和进一步理清西夏陵及陪葬墓的前后关系,有助于西夏学相关研究的进一步深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