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上丝绸之路的语言共变:基于广州的语言景观分析
2023-09-11巫喜丽范露
巫喜丽 范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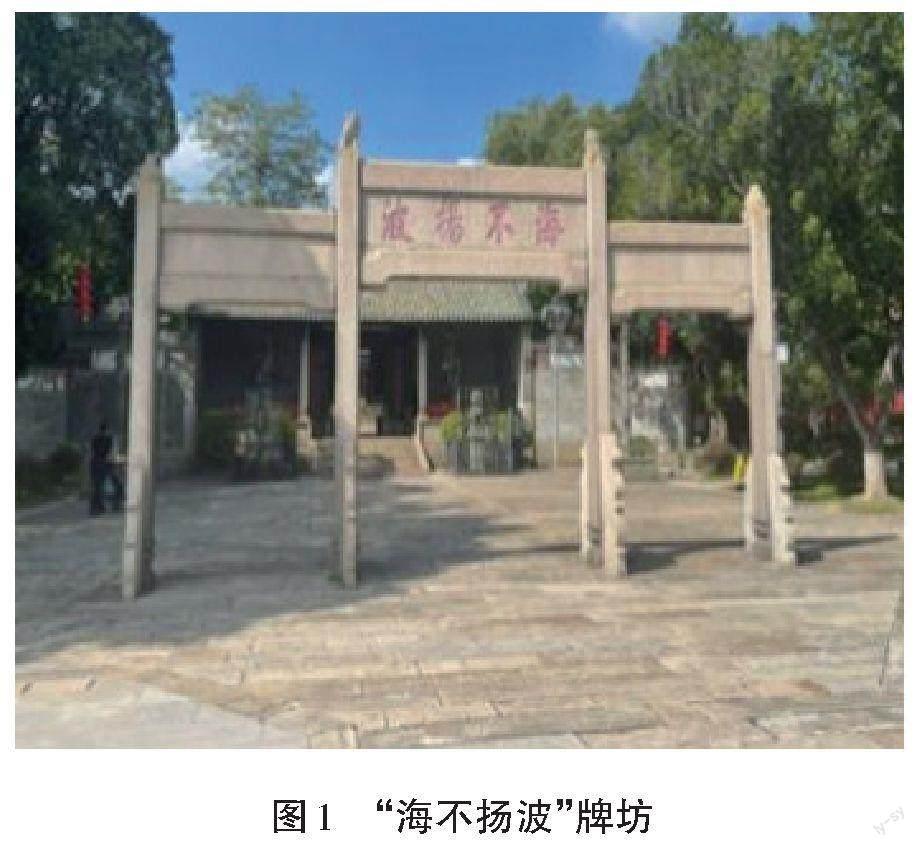


摘要:语言景观作为公共空间的普遍语言实践,能为社会变迁提供重要的历史物证。对外交流引起语言的变异发展,语言的发展又推动着对外交往的发展变化。本文通过对海上丝绸之路相关史料的钩沉,以广州海关港口、宗教文化交往的遗迹遗存和广州外销画中的语言景观为线索,分析海上丝绸之路带来的语言共变现象。结果表明:语言景观变化与社会语境高度耦合。南海神庙、粤海关等遗址的语言景观经历了建筑命名、设置主体、语码选择等变化,特别是对外交往的语言在近代曾由汉语为主体短暂转换为汉英双语,反映出不同历史时期广州的海上贸易发展以及海事政策变迁对语言的影响。光孝寺、怀圣寺、石室圣心大教堂、巴斯墓地等宗教商贸交流遗迹的语言景观多语现象明显,其语言选择与异域宗教文化传入中国密切相关,体现了海上丝绸之路对民间话语景观的影响。广州外销画的语言景观则反映了十三行时期广州对外传播的双语化和英语本土化特征,在中国形象的海外传播上发挥了积极的建构作用。本研究为广州作为海上丝绸之路中外交流枢纽提供了语言学方面的佐证, 有助于深化理解语言与社会的互构、互证关系。
关键词:语言景观;海上丝绸之路;广州十三行;语言共变
【中图分类号】 H13.5 doi:10.3969/j.issn.1674-7178.2023.03.008
引言
广州自秦汉以来便是岭南地区的商贸和文化中心,凭借优越的地理条件成为古代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发祥地,海外贸易史延续两千多年。明清时期,广州逐渐成为世界主要的贸易中心之一,自广州出发的航线经东南亚、南亚、阿拉伯等,最终抵达东非和欧洲,极大地促进了中国与沿线国家和地区的经贸往来与文明互鉴。
国内外学界对于广州在海上丝绸之路的历史地位著述颇丰,既有研究多与考古学[1]、历史学[2]、建筑学[3]、文化研究[4]、地理学[5]等学科相关,通过梳理历史文献、考证文物遗迹,或探讨不同历史时期广州的对外贸易史、航海史、宗教传播史,或考察海上丝绸之路对广州城市形态和文化景观塑造的影响,但鲜见从语言学视角探析广州的对外交往史以及海上丝绸之路给广州带来的社会和语言发展变化。2017年4月,习近平总书记到广西北海考察,在合浦汉代文化博物馆参观海上丝绸之路文物精品展览时,做出“要让文物说话、让历史说话、让文化说话”[6]的重要指示。如何让海上丝绸之路的语言历史说话?这是本研究的根本出发点。
语言是人类相互交流和认识世界的重要媒介,语言文字的演变与社会变迁、跨文化交流等密切相关。1964年,美国语言学家威廉·奥利弗·布莱特(William Oliver Bright)提出“共变论”来解释社会与语言的相互影响关系[7],中国社会语言学的主要开创者之一、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前主任陈原在《社会语言学的兴起、生长和发展前景》一文中也解释了何谓社会与语言的共变:“语言是一个变数,社会是另一个变数。两个变数互相影响、互相作用、互相制约、互相变化,这就是共变。”[8]语言的发展变化不仅能折射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的变迁,对社会变项也有不同程度的建构作用。语言景观是公共空间的普遍语言实践和重要符号资源,能为研究城市变迁提供视觉化线索。广义的语言景观通常指公共标识牌书面文本的集合体,既包括路牌、警示牌、广告牌、店名标牌等典型标牌,也包括电子显示牌、车身广告等多模态或流动性标牌[9]。在中国文化中,传统语言景观涵盖了建筑字刻、碑刻、匾额、对联、招幌以及流动语言物件等多种形式。作为城市空间不可或缺的话语资源,语言景观往往共时与历时并存,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研究區域的语言使用实态,折射出城市发展轨迹,也深刻地塑造着城市的人文地理空间。但迄今为止,国内语言景观多为横断研究[10-12],历时研究数量有限[13-14],将语言景观与城市史相结合的历时研究较为匮乏,相关视角有待丰富。
鉴于此,本文通过考察广州海上丝绸之路相关的历史遗迹遗存以及图片史料中的语言景观历时变化,为勾勒和还原历史现场提供语言证据,深入挖掘因海上丝绸之路带来的语言景观与社会的共变关系。
一、研究方法
为深入了解广州在海上丝绸之路的历史地位,本研究重点选取海上贸易、宗教往来、艺术交流等三大类代表性海丝遗迹遗存作为研究对象,具体包括:南海神庙及明清码头遗址、粤海关、光孝寺、怀圣寺、石室圣心大教堂以及含语言要素的清代广州外销画。笔者查阅了广州海上丝绸之路相关的史籍文献、主题展览图册、地方志等史料,对涉及上述遗迹遗存的语言景观图片进行收集整理,同时还对主要的遗迹点开展实地调查,用数码影像设备拍摄历史遗存的各类标牌图片,获取有效样本163个。
在语料分析过程中,本研究沿用了Backhaus(2007)[15]使用的方法,将每个具有独立边框的语言标牌计为一个分析单元,对个别特殊语言景观(如对联)采用整体法进行统计,同时参照Scollon & Scollon(2003)[16]的场所符号学分析框架,对标牌的语码种类、语码偏好、文字矢量(即文字的阅读方向)等变量进行编码。其中,语码偏好指双语或多语标牌中不同语码的优先关系,主要依据语码的置放顺序确定。一般来说,在中心包围排列式中,出现在中心位置的为优势语码;在上下排列式中,优势语码位于上方或者顶部;在左右排列式中,优势语码一般位于左侧,而对于文字阅读方向为从右到左的语言(如传统汉语),优势语码多数位于右侧[17]。字刻主要包括字体(如字体大小和颜色等)和材质。此外,为进一步厘清语码的地位关系,本文根据Reh(2004)[18]提出的多语信息类型,将双语标牌按语码和信息组合形式分为复制式(duplicating)、重叠式(overlapping)、互补式(complementary)和片段式(fragmentary)。其中,复制式多语指两种语码提供的信息量相等;重叠式多语则指两种语码提供的信息既有重叠又有不同;互补式多语指两种语言提供完全不同的信息;片段式多语指一种语言提供全部信息,另一种语言提供部分信息。本研究中的显著语码是指标牌中具有视觉凸显效果的语码,主要结合字体大小、置放顺序、文字矢量等参数确定;主要语码则依据语码提供的信息量确定:信息量最多的为主要语码;如果两种语码提供的信息量均等,该标牌的主要语码与显著语码一致。
二、研究结果
广州是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口岸城市,拥有丰富的海上丝绸之路文化遗产。通过具有代表性的海关港口遗址、宗教文化遗迹和广州外销画遗存中的语言景观等案例,挖掘语言景观背后隐藏的历史文化意蕴,探析不同历史时期海上丝绸之路的语言景观与社会的共变关系。
(一)海关港口遗迹:官方话语的主体稳定性
在对外交流过程中,中国是一个极为重视保持民族语言文字主体性的国家,翻译自古有之,目前可见的文字记载始于周代。根据《周礼·秋官》的记载,官职“象胥”的职责是“掌蛮夷闽貉戎狄之国,使掌传王之言而谕说焉,以和亲之。若以时入宾,则协其礼与其辞言传之”[19]。由于中国的官方翻译事务自古由礼宾和文化机构管理,有一套严密的制度,因此既能保存汉语的主体稳定性,又能主动吸纳外来语言文化的精华为我所用。例如,《后汉书·南蛮西南夷传》有“越裳以三象重译而献白鴙,曰:道路悠远,山川阻深,音使不通,故重译而朝”[20],在朝贡体制下,番邦和外国来朝必须以汉语“上表”朝廷才算来朝成功。又如,印度重口传声教,而中国重文字流传,佛经汉译将以音声为主要传授方式的印度佛教,改造成以文字传授为主的中国佛教。但汉译在佛典传入初期也有争议,如隋代彦琮(557—610年)以汉文和梵文不能“纯实”对应而主张“废译”,要求直接口传梵文原典。仅数十年后,玄奘(602—664年)主持的译场就将中国的佛典翻译事业推向了巅峰,他的译场虽经三迁,但有严格的制度和人员配备保障,先后译出佛经达75部1335卷。唐代的译场职司分工很细,共有11种职务:译主、证义、证文、度语、笔受、缀文、参译、刊定、润文、梵贝、监护大使。由于古印度和中亚的语言大量进入,带来全新的事物,早期译师们只能直接大量音译,为控制音译泛滥,玄奘立下“五种不翻”的规矩,译师们引入“梵文六合释”等新的构词方法,创造出大量新的汉文复合词,极大丰富了汉语词汇。梁启超在《翻译文学与佛典》一文中曾指出,日本人编的《佛教大辞典》所收三万五千余语,“实汉晋迄唐八百年间诸师所创造,加入吾国语系统中而变为新成分者也”[21]。可以说,在对外交流中,历代活跃于朝野的象胥、舌人、译者,对汉语的捍卫保留、弘扬发展做出了极大的贡献。
这些历代层累于城市的历史文化遗迹,如匾额、牌坊和碑刻等常见的语言景观空间载体蕴含丰富的文本和符号资源,除具有标记建筑名称、提供语言状况信息、表达义理哲学外,还留存社会语言共变的印迹,映射出不同语言族群的权势地位等多重功能。
南海神庙是我国现存规模最大、最完整的海神庙,也是我国古代海上丝绸之路始发港的重要遗存,在历史上数次重建。南海神庙最初是沿海居民出海航行前祈求“海神”祝融保佑的场所,随着远洋贸易的发展,隋开皇十四年(594年)开始成为官方祭海场所[22],也就是国家祭祀岳镇海渎的重要内容,以及确立统治区域的一个载体。天宝十年(751年),唐玄宗首次敕封南海神为“广利王”。随着海上交通兴起、外贸活动活跃,南海神庙所在的扶胥古港见证了中国古代海上丝绸之路“广招天下财利”的繁荣兴盛,“南海神”一跃成为国家四方海洋信仰祭祀体系中位次最为尊贵的海神[23]。明成化八年(1472年),广州府判余志主持翻修南海神庙,将大门旧匾额所题“祝融”改为“南海神祠”[24],以符合官方礼制。清康熙为南海神庙亲笔题写“万里波澄”御匾,清道光二十九年至三十年(1849—1850年),将头门之前的红石牌坊改为麻石牌坊,上刻“海不扬波”四字(图1),寓意风平浪静、一帆风顺。南海神庙主体建筑共五进,门头一般采用“匾额+对联”的中国传统语言景观呈现形式,如头门的木门匾用金字书写“南海神庙”,两侧附有对联(图2)。匾额是南海神庙语言景观中最常见的标牌类型之一。作为建筑物命名的载体,匾额体现了官方意志或其他标牌设置主体对公共空间的驯化。南海神庙匾额的数次易名折射出社会历史的动态演变过程[25]以及历代朝廷对海上交通贸易的重视程度。
南海神庙还因碑刻数量众多,被称为“南方碑林”。头门后两侧有唐代和宋代碑亭各一座。东侧的韩愈碑亭,有唐韩愈撰写的《南海神广利王庙碑》,由循州刺史陈谏手书,著名刻工李叔齐镌刻。碑文中首次使用了“海事”一词。西侧的北宋开宝碑亭,记录了北宋祭祀南海神的史实。从仪门庭院到大殿东西两侧的复廊中,共陈列唐、宋、元、明、清等各代碑刻45通,包括明洪武碑、清康熙碑等御碑。碑文内容涉及政治、经济、文化、宗教、制度、人物等诸多内容,其中海上贸易是重要主题。通过这些碑刻可以清晰地了解中国的海上贸易史和海事文化的发展进程。碑刻是中国古代常用的字刻载体,在公共空间中具有持久影响力。作为一种不可再生的历史文化遗产,碑刻具备文物和文献的双重属性,主要发挥了刻文记事的功能。另外,古人对于石质载体的偏好也反映了对历史文化传承的美好意愿。
南海神庙碑林的不少碑文中,深刻反映出沿海上丝绸之路而传入的外来文化对中文词汇的丰富以及对汉语语法及文体的影响,例如“塔”“僧”“微妙”“神通”“世界”“祈祷”“如意”等词汇新增自梵文,今已“日用而不知”。另一大在构词上的影响是赋旧词以新意,如重神性和意象的中国“龙”获得印度“龙”(那伽,nāga)的多财富、多法力、布雷行雨的意蕴。早在鸠摩羅什创译《大智度论》(Mahāprajnāpāramitā?āstra)中即有“那伽,秦言龙”的记载,但中国民间真正将中国的龙与印度的那伽融为一体的时间则是在唐传奇兴起以后,一个重要节点是元和年间李朝威撰写的《柳毅传书》开始流传之后。这其中,韩愈广为流传的《南海神广利王庙碑》一文起到有趣的助推作用。韩愈于元和十四年(819年)因上《谏迎佛骨表》劝阻唐宪宗奉迎佛祖舍利子而被流放,元和十五年(820年)受好友广州刺史孔戣的邀请,著文纪念孔戣修葺祭祀南海神庙一事。韩愈在碑文开篇写道:“海于天地间为物最钜。自三代圣王莫不祀事,考于传记,而南海神次最贵,在北东西三神、河伯之上,号为祝融。”[26]祝融原本为上古大神,在这篇碑文以前,无论是作为火神、南方神、南海神、夏神、城隍、灶神还是五行神之一,都没有祝融“神次最贵”的明确说法。唐玄宗敕封四海,南海广利王并不居首,与东海广德王、西海广润王、北海广泽王大致齐平。但是,当时张九龄凿通大庾岭,海上贸易繁华空前,为唐王朝增加了丰厚的收益,因此“广利”的封号既有“让众生获得大利益”的意思(佛教“二种广利”说),又有了“广招天下财利”的期盼。其二是唐代受印度文化影响,首次出现龙子龙女的形象,最著名的无过于《柳毅传书》中的龙女。这部传奇深受佛教因果观影响,其中一段极力描写洞庭湖龙宫富丽堂皇,“人间珍宝毕尽于此”,显然已经将印度“龙”与中国“龙”的形象融合。写作于同一时期的碑文与传奇,在流传中互相影响,“龙”这一中文词汇也不断获得新的意蕴。北宋天宝六年(973年)的“大宋新修南海广利王庙之碑”碑额即雕刻上了精美的盘龙,到清雍正二年(1724年)南海神被雍正直接加封为“昭明龙王之神”,自此南海广利王祝融与南海龙王合而为一。印度传统文化中的“那伽”演变复合为中国的“龙”这一案例,显示了在古代海上丝绸之路这一和平对外交往时期,中国语言文化兼容并蓄、稳定而强大的主体性。
粤海关旧址是中国海洋贸易近代史的重要遗存。粤海关创立于清康熙二十四年(1685年),是清政府管理中外贸易的官方机构,具有征收关税和采办贡品的双重职能。乾隆二十二年(1757年),清政府下令独留粤海关(广州)为唯一合法外贸口岸,广州由此进入“一口通商”带来的繁盛时期。作为政府的专设机构,粤海关的语言景观由官方设立。图3、图4显示了位于广州“外城”五仙门内的粤海关监督署旧址,大门前侧的两面旗幌竖排写着“钦命粤海关”。“钦命”二字彰显出粤海关作为国家机构的官方地位。图5的粤海关旧址是粤海关税务司署,曾先后拆建过三次,现楼于1916年建成,俗称“大钟楼”。大楼主入口拱心石上竖刻繁体字“粤海闗”铭文,两侧断檐分别刻有英文“CVSTOM”“HOVSE”。英文“Custom”和“House”中的“U”均被替换为“V”,因为根据英语词源学,“U”是由“V”演变而来的,为了追求复古效果,建筑师在印刷体大写字母中以V代替U,避免了椭圆字体相连,视觉效果更加美观。该建筑字刻采用了重叠式多语文本,即汉语和英语提供的信息部分重合。具体而言,“海关”这一核心信息用汉英两种语言分别呈现,而表明机构属地的“粤”仅用汉语书写。汉语是提供信息的主要语码,且处于中心凸显位置。英语位于左右两端,字体大小与汉语无明显差异,具有相当程度的凸显效果。图6为粤海关旧址的奠基石,采用汉英双语记录大楼改建时间、设立者等信息,汉语位于奠基石的右侧,采用了竖排从右至左的传统汉语文字矢量。英语置于左侧,采用横排从左至右的文字矢量。这一置放形式保证了汉语和英语双重凸显的效果。该碑刻使用了片段式多语文本,英语是主要语码,提供的信息量略多于汉语,标牌中并无明显的语码强弱关系。
总体而言,粤海关的语言景观出现了由汉语单语转向汉英双语的历时变化,见证了广州作为清末唯一对外通商口岸到鸦片战争之后中国关税自主权和海关行政管理权逐渐丧失的特殊历史时期:1860年10月开始,推行外籍税务司制度的粤海新关(俗称洋关,即粤海关税务司署)正式成立。洋关期间,粤海关税务司署及高级职员均由外国人担任。1863年开始制定并实行由外国人管理的半殖民地海关制度。这也解释了粤海关税务司署语言景观中汉语并无绝对优势地位,而英语作为“现代化”“西方文化”的象征符号具有较高的可视性和凸显性的可能原因。这一语言地位的模糊化策略印证了“洋人把持海关”的屈辱历史。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粤海关更名“广州海关”,英文铭文被水泥沙石封蔽。2007年粤海关“大钟楼”做“修旧如旧”保护,拱心石两侧英文铭文被清理出来,字迹清晰如故。
作为海上丝绸之路的海关港口遗迹,南海神庙及粤海关的语言景观均为官方主导的话语实践形式,经历了官方外事语言由上千年的汉语单语主体向汉英双语短暂转变的过程,在建筑物命名及设置主体、语码选择及语言地位等方面均具有明显的时代特征,集中体现了官方意志和政治变迁对公共空间语言景观塑造的影响,也折射出广州作为千年古港的海上贸易发展轨迹。
(二)宗教商贸文化遗迹:民间话语的多元共存
以海上丝绸之路为纽带,宗教文化交流和对外商贸活动在广州留下了诸多代表性历史遗迹,光孝寺、怀圣寺、清真先贤古墓道、石室圣心大教堂见证了佛教、伊斯兰教、天主教等经海路传入中国的历史,而巴斯墓地遗址则为巴斯(Parsee)商人(信奉琐罗亚斯德教的商人)来华贸易提供了明确佐证。
位于广州市越秀区的光孝寺被誉为“岭南第一古刹”,是佛教经由海上丝绸之路传入中国并传播的重要历史见证。光孝寺在历史上曾数次易名:三国时期,东吴著名经学家、骑都尉虞翻谪徙广州,居此聚徒讲学。因园中多植苹婆、诃子成林,被人称为“虞苑”或“诃林”(图7)[27]。虞翻病逝后,该寺被官方改建为佛寺,更名为“制旨寺”(亦为“制止寺”),意为“奉皇帝之命建造”,主要用于接待西来番僧。光孝寺也逐渐成为中外佛教文化交流的一处名刹。会昌元年(841年),崇信道教的唐武宗李炎发动灭佛事件,改寺名为“西云道宫”。南汉时期,光孝寺又以高祖刘岩的年号重新命名为“乾亨寺”,在当时的佛教寺庙中享有极高地位。然而,12世纪末13世纪初,随着佛教在印度式微,光孝寺在中外佛教文化中的交流和地位也逐渐式微[28]。因明太祖朱元璋早年出身于僧侣,明朝廷有鉴于元代崇奉喇嘛教的流弊而加强了皇权对佛寺的干预,同时也推动了汉地佛教的世俗化。明成化十八年(1482年),明宪宗敕赐“光孝禅寺”匾额(图8),奠定了光孝寺在佛寺中的地位,光孝寺之名得以流传至今。光孝寺匾额的命名以及设置主体的更替体现了不同历史时期官方对佛教态度的变化,也间接反映出佛教在中国南方的发展历程。
怀圣寺建于唐贞观元年(627年),是中国第一座清真寺,也是伊斯兰教通过海路传入中国的第一站。怀圣寺以及清真先贤古墓道的匾额、碑刻等语言景观的语码种类多样,包括汉语单语、阿文单语、汉阿双语等形式,双语现象明显。图9所示的寺院匾额采用了汉语单语竖排的形式,保證了汉语的绝对主导地位。图10为怀圣寺看月楼背面的单语匾额,用阿拉伯文篆刻了《古兰经》第三章的部分经文[29]。图11为元至正十年(1350年)《重建怀圣塔寺之记》的碑记拓片,使用了汉阿双语,篆额“重建怀圣塔寺之记”八字由右至左分4行直书,下方有3行半阿拉伯文,记录了该碑重建者、重建时间及伊斯兰教义[30]。汉语碑文描述了怀圣寺塔的外形及内部结构,也记述了伊斯兰教在中国的传播[31]。相比之下,清康熙年间的《重建怀圣塔寺之记》拓片中已不见阿拉伯文,通篇使用汉语篆刻(图12)。究其原因,唐初广州首开市舶,由于航海条件有限,来广州贸易的外国商人需要等待信风返航,逐渐形成了以怀圣寺为中心的外商聚居区“蕃坊”。然而,元代之后,由于朝代更迭、战事频仍以及其他贸易港口兴起等种种原因,居住在广州蕃坊的蕃客大量减少[33],阿拉伯人、波斯人等与广州的贸易日渐式微,阿拉伯语在广州公共空间的使用也随之减少。
与怀圣寺密切相关的清真先贤古墓位于广州的桂花岗,是伊斯兰教信众的墓葬之处。图13为“先贤古墓道”牌坊正面,门额正中用汉语刻写建筑名称,且字体明显大于四周的阿拉伯文,具有绝对的视觉凸显效果。四周的阿拉伯文内容为《古兰经》,左右两侧的耳门额是阿拉伯文书写的两段“圣训”,意为:“死亡足以发人深省”“现世足以分晓逝迁”[34]。牌坊两侧石柱上则刻有汉语对联:“远涉重洋莅临东土先哲毕生传圣教;阐扬经训理通西域穆民万世仰高风”,抒发对伊斯兰教先贤的缅怀与敬仰。牌坊正面采用互补式多语文本,汉语和阿拉伯文提供的信息完全不同。牌坊的背面石额正中间及左右两侧均用阿拉伯文刻写伊斯兰教教义(图14)。该石牌坊具有双语特点,汉语是显著语码,在放置位置和字体选择上均保证了视觉凸显效果,但阿拉伯文的可视性也不容小觑。
在上述伊斯兰教相关的历史遗迹中,汉语保持了强势语码的地位,通常被用于标记建筑名称及提供背景信息,同时彰显民族文化认同,信息功能和象征功能兼具。阿拉伯文则被用于宣扬伊斯兰教教义文化,主要发挥象征功能及教化作用,被用于增强在地伊斯兰教信众的归属感与认同感,激活伊斯兰教的符号意蕴。阿拉伯文在广州的伊斯兰教宗教文化场所中普遍使用,反映出当时广州对外开放程度高,官方对伊斯兰教文化较为尊重和包容,有力推动了异域文化与中国文化的交融。
继佛教、伊斯兰教先后传入中国之后,天主教也在广州留下了重要遗迹——石室圣心大教堂。该教堂是我国现存最完整、规模最大的石构哥特式天主教教堂。1857年,英法联军入侵广州,将两广总督行署夷为平地。后法国政府强行租借该部堂衙门废址,在其上修建教堂。教堂始建于1863年,落成于1888年,历时25年。图15为教堂外观仅有的两块文字石刻,东侧的角石上刻有英文“Jerusalem,1863”,西侧的角石上刻有意大利文“Roma,1863”,取义为天主教创立于东方的耶路撒冷,而兴于西方之罗马[35]。汉语虽为官方语言,但在这座象征西方话语符号的天主教建筑中几无可见度,从侧面反映出当时中国处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历史阶段。
经由海上丝绸之路,广州不仅是佛教禅宗的“西来初地”,伊斯兰教、天主教来华的南大门,更吸引了不计其数的外商群体。巴斯墓地遗址为清代广州海上丝绸之路商贸活动的重要遗迹。巴斯商人是广州十三行时期重要的洋商群体。作为古波斯人的后代,巴斯人因宗教信仰被迫流亡。为融入当地,他们放弃波斯语,学习当地的语言。在广州现存的巴斯墓葬碑刻中,英文、古吉特拉文(Gujarati)双语特征显著,记录了巴斯商人的姓名、宗教信仰、亡故日期等信息。英文和古吉特拉文在墓碑中的普遍使用与印度巴斯人积极“欧化”密切相关[36]。部分碑刻中出现的英文“BOMBAY”(孟买),标明了来穗巴斯商人的原乡。
上述历史遗迹语言景观的语码选择趋于多语化,通过汉语、阿拉伯语、英语、意大利语、古吉特拉语等不同语码的选择激活家国认同、宗教身份以及不同语言族群的权势地位等符号意蕴。该类语言景观是民间话语主导的实践产物,具有高度的开放多元性,间接反映了不同历史时期广州的政治社会变迁和中外文化交流互鉴状况。
(三)廣州外销画:对外传播话语特点
18—19世纪,中外贸易蓬勃发展,中西艺术交流也愈加频繁。广州外销画是中国外销艺术品的一个主要门类,是中外文明交流的图像载体。伴随着清朝“一口通商”政策的实行和“十三行”这一对外贸易专业行商的兴起,广州外销画在来华商人中深受欢迎。清代广州外销画一般由底层工匠绘制,具有浓厚的商业性质,取材广泛,画种繁多,写实性强,以“兼采中西”的绘画技法描绘近代广州的社会风物和市井民生,是中西文化融合的产物。部分画作以图文并茂的形式呈现,是为数不多的含有语言要素的外销艺术品,可视为一种非典型、流动性的语言景观,具有独特的研究价值。
街头店铺是广州外销画的一个主要题材。店铺类型涵盖外销画室、打包铺、茶叶店、丝绸店等,充分反映出当时广州对外贸易的主要业态,体现出鲜明的口岸城市特色。图16为外销画《TINGQUA洋画铺》,画铺内既有中国传统的竹石水墨画,也摆放了西式风格装裱的肖像画、风景画等外销画。画铺正上方悬挂的是英语单语店名标牌“TINGQUA”,处于店面上方的中心凸显位置,两侧的汉语楹联写着“一帘花影云拖地,半夜书声月在天”,字体明显小于英语店名。该店名标牌与18世纪另一历史遗存的著名画室店名标牌高度相似(图17),可见这一标牌样式在当时较为常见,在一定程度上印证了外销画的主要销售对象是来华客居的外国人。外销画室通常与中国传统店铺“前店后厂”的形式一致,销售与画室合为一体[37]。“十三行”时期,大量外销画室集中在广州以商馆区为中心的同文街或靖远街一带[38]。这些画室多使用带“qua”(音译为“呱”)字的英语单语或汉英双语店名标牌,对外国受众较具可读性和友好度,有利于商业形象的塑造。其中,“qua”字的来源尚无定论,目前学界普遍认为“呱”可能来自行商别号中的“官”字,多半是为了便于洋人称呼和记忆,为招徕生意提供便利。
从现存的广州外销画可以看出,“十三行”时期广州街道的店名标牌通常有两种挂法:将商号悬挂于店面正中顶头或右侧。图18外销画《大章号绫罗绸缎铺》中,商号“大章号”悬挂于店铺大门正中,左侧悬挂木匾“绫罗绸缎”。图19的《同吉号打包铺》店名标牌则采用左右式的置放顺序和从右到左的文字矢量。右侧为凸显位置,用于展示店名“同吉号”,左侧的广告牌“同吉打包”则提供店铺的经营范围信息。
在本研究样本中,相当一部分外销画涉及中国古代的商业标牌——招幌,招幌可分为形象幌、标志幌和文字幌,融合了中国传统文化理念和美学元素,主要用于展示店名、提供商品种类或服务范围等信息,是中国传统商业文化中广告的重要载体。清代的广州商品经济发展较成熟,招幌运用广泛,形式也复杂多样。店铺招幌有横招、竖招、墙招等,一般通过不同载体将商号、行标或广告呈现于门梁、屋檐、墙壁或柜台上。文字幌使用相对较少,一般以单字或双字展示经营的商品品种,或提供店名、品名或商家信誉等内容。
在外销画风靡之际,广州的外销画家不同程度地采用西洋绘画技法,在保留本土市井文化特色的基础上,也迎合了当时西方人的语言识读能力、身份认同和审美趣味。图20为外销画《通草水彩手绘风景人物节日贺卡》系列。贺卡选取了西方人熟悉的圣诞节主题,主画面描绘了广州社会生活的人物百态,正上方用“广州英语”书写节日祝词。如图21所示的“Christmas true belong number one, me thinkee so fashion, because do muchee chow-chow”,“广州英语”通常会在以t、ch、k等结尾的单词后面增加一些尾音[34],“chow-chow”在这里指“极好的事物”,而“me”是对“I”的误用。这组外销画从侧面说明“广州英语”在当时的社会语言生活中享有较高的声望和地位。这一语码选择既保证了对海外受众具有一定的可读性,又蕴含了浓厚的地域风情,是英语本土化的特色产物。
“广州英语”是“一口通商”时期广州商人出于对外交流的需要自发创造出的一種皮钦语(pidgin),在发音、词汇和句法等方面深受澳门葡语、汉语、粤方言的影响[39]。该英语变体主要以口语的语体形式运用在对外贸易的特定情境中。19世纪30年代之后,随着中西经济贸易的持续深入,《广州番鬼录》《红毛通用番话》等与“广州英语”词汇相关的书籍和词典相继刻印发行,“广州英语”开始出现书面语体,其适用范围也逐步扩大[40]。直至鸦片战争结束后,由于“五口通商”和对外贸易中心的北移,发音以粤方言为本底的“广州英语”逐渐被以上海话发音为主的洋泾浜英语取代。据汤姆·罗伯聃(Robert Thom)记载,在广州以外的通商口岸,英语的流通性较低,因此有必要用汉语官话对英语进行注音,以便快速培养对外贸易的通事[41]。用官话标注的英语开始取代“广州英语”,成为洋泾浜英语的主流[42]。19世纪中叶开始,随着上海逐渐发展成为中国最大的通商口岸,上海洋泾浜英语也取代“广州英语”成为当时中国最流行的英语变体。不同英语变体的兴衰反映出当时中国对外贸易格局的变化。
作为一种非典型语言景观,外销画融合了图像、文字多种模态,成为超越语言、历史、文化等差异的视觉语言[43]。因其流动性特征,外销画兼具对外传播的功能,在影像技术尚未发明和普及的背景下,成为西方人了解中国传统文化、了解中国社会民生的重要媒介,有力地促进了中西文化交流,进一步建构了西方对中国形象尤其是清代广州地区的认知[44-45]。18世纪中叶至20世纪初期,大量外销画在广州绘制和售卖,并通过海上丝绸之路远销海外,在一定程度上提升了广州在海外的传播度和认可度。“Canton”逐渐成为广州这座当时的世界贸易中心和繁华之地的代名词,诸多与Canton有关的英语词汇应运而生,包括Canton ware(指从中国出口的青花瓷器,尤指18-19世纪的瓷器)、Canton china(广东瓷器,尤指青花瓷)、Canton ginger(广东蜜饯姜)等[46]。
广州是海上丝绸之路的发祥地之一,也是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枢纽,其海上丝绸之路历史遗迹遗存的语言景观在汉语的主体稳定性下呈现出不同语言相互交融、外来语言地位此消彼长的总体特点,为中国自古以来开放包容、兼收并蓄的文化环境提供了视觉化线索,有力印证了习近平总书记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强调的中华文明突出特性,即突出的连续性、创新性、统一性、包容性、和平性。分析广州海上丝绸之路相关的语言景观历时变化,既有助于理解汉语言文字如何能数千年生机勃勃、长盛不衰,又有助于鉴古通今,为寻找城市历史文脉、保留城市历史记忆提供一扇窗口,为更高水平对外开放及在文明交流交融中推进文化传承发展提供鲜活有力的借鉴。
参考文献:
[1] 娄建红:《汉代广州与海上丝路——探究广州在海上丝绸之路中的地位和作用》[J],《人民论坛》2012年第2期,第138-139页。
[2] 耿元骊:《五代十国时期南方沿海五城的海上丝绸之路贸易》[J],《陕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4期,第79-88页。
[3] 刘明洋:《中国化清真寺建筑的历史演变 以广州怀圣寺为例》[J],《中国宗教》2019年第2期,第74-75页。
[4] 罗伊:《广东特色“海上丝绸之路”文化遗产初论》[J],《南方文物》2020年第3期,第269-277页。
[5] 赵焕庭:《番禺是华南海上丝路最早的始发港——对关于中国古代“海上丝绸之路”最早始发港研究述评的意见》[J],《地理科学》2006年第1期,第118-127页。
[6] 新华网:《习近平广西考察:写好新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新篇章》[DB/OL],2017年4月20日,http://news.cnr.cn/native/gd/20170420/t20170420_523716169.shtml,访问日期:2023年5月17日。
[7] William Bright (ed.), Sociolinguistics: Proceedings of the UCLA Sociolinguistics Conference [C], The Hague: Mouton,1964: 324.
[8] 陈原:《社会语言学的兴起、生长和发展前景》[J],《中国语文》1982年第5期,第321-327页。
[9] 尚国文、周先武:《非典型语言景观的类型、特征及研究视角》[J],《语言战略研究》2020年第4期,第37-47、60页。
[10] 杨荣华、孙鑫:《互动顺序视域下城市历史文化街区语言景观研究:以南京为例》[J],《外语电化教学》2018年第6期,第100-105页。
[11] 巫喜丽、战菊:《全球化背景下广州市“非洲街”语言景观实探》[J],《外语研究》2017年第2期,第6-11、112页。
[12] 聂鹏、木乃热哈:《西昌市彝文语言景观调查研究》[J],《语言文字应用》2017年第1期,第70-79页。
[13] 李永斌:《西藏文化的多元变迁研究——基于拉萨市语言景观的历时调查》[J],《西藏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0年第3期,第61-69页。
[14] 李永斌:《改革开放以来西藏语言使用的不同年代比较——基于拉萨市语言景观的历时调查》[J],《中国藏学》2019年第4期,第209-214页。
[15] Peter Backhaus, Linguistic Landscapes: A Comparative Study of Urban Multilingualism in Tokyo [M], Clevedon: Multilingual Matters, 2007: 66-67.
[16] Ron Scollon and Suzie Wong Scollon, Discourses in Place: Language in the Material World [M], London: Routledge, 2003: 116-165.
[17] 《中國社会语言学》编委会:《中国社会语言学》[M],商务印书馆,2019年,第47页。
[18] Mechthild Reh, “Multilingual Writing: A Reader-oriented Typology — With Examples From Lira Municipality (Uganda)” [J],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the Sociology World, 2004, 170:1-41.
[19] 钟智翔、颜剑:《缅汉翻译概论》[M],军事谊文出版社,2002年,第15页。
[20] 同[19] 。
[21] 梁启超:《翻译文学与佛典》[A],载郁龙余编《中印文学关系源流》,湖南文艺出版社,1987年,第2页。
[22] 韩维龙、易西兵:《海上丝绸之路广州史迹》[M],广州出版社,2017年,第116-177页。
[23] 李朗宁:《走向善治:城市庙会的现代转型——基于广州南海神庙波罗诞的观察》[J],《城市观察》2021年第6期,第120-134页。
[24] 同[22],第136页。
[25] Hao Wang, “Geographical Names as Cultural Symbols: The Law of Naming Systems Evolution in Southwest China” [J/OL],《学术界》英文版2020 年第12期,第228-234页,DOI: 10.3969/j.issn.1002-1698.2020.12.022。
[26] 段汉武、吴晓都、张陟:《蓝色的诗与思——海洋文学研究新视阈》[M],海洋出版社,2010年,第123页。
[27] 程建军:《广州光孝寺》[M],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16年,第10-14页。
[28] 胡巧利:《光孝寺》[M],广东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100-101页。
[29] 杨棠:《广州阿拉伯文雕刻史料》[J],《阿拉伯世界》1988年第4期,第39-43页。
[30] 中元秀、马建钊、马逢达:《广州伊斯兰古迹研究》[M],宁夏人民出版社,1989年,第3-4页。
[31] 同[22],第157页。
[32] 同[22],第158页。
[33] 同[22],第160页。
[34] 同[29],第39页。
[35] 林雄:《经典广东》[M],广东教育出版社,2009年,第254-255页。
[36] 郭德焱:《清代广州的巴斯商人》[D],博士学位论文,中山大学历史学系,2001年。
[37] 广州博物馆编:《海贸遗珍18—20世纪初广州外销艺术品》[M],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第14、74页。
[38] 同[37],第14页。
[39] 吴义雄:《“广州英语”与19世纪中叶以前的中西交往》[J],《近代史研究》2001年第3期,第172-202页。
[40] 王淑芳:《“广州英语”在中西交往中的历史地位解析》[J],《兰台世界》2013年第22期,第81-82页。
[41] 汤姆·罗伯聃:《华英通用杂话》上卷[M],出版社不详,1843年,序言。
[42] 张明杰:《晚清洋泾浜英语发展历史及产生的原因探究》[J],《兰台世界》2013年第25期,第101-102页。
[43] 殷洁:《清代广州地区外销画的研究意义》[J],《艺术百家》2014年第6期,第241-242页。
[44] 殷洁:《他者印象:广州外销画对中国形象的建构》[J],《艺术百家》2020年第6期,第47-51页。
[45] 王岩:《异质文化冲突与融合:18—19世纪清代外销画研究》[J],《南京艺术学院学报(美术与设计)》2022年第6期,第189-193页。
[46] 中共广州市委宣传部:《中国广州:海上丝绸之路发祥地》[M],广东人民出版社,2017年,第172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