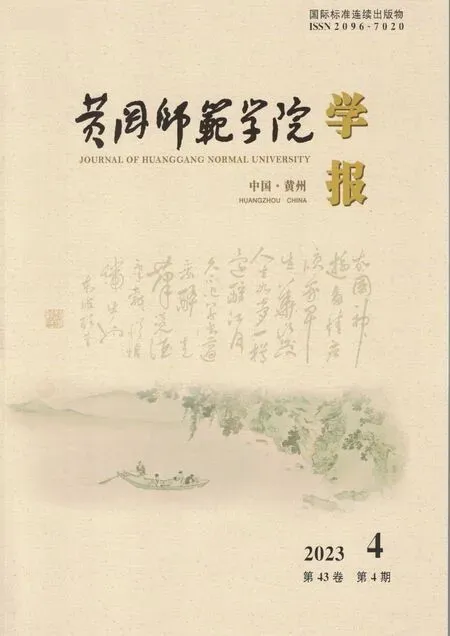基于WOS的国际“世界英语”研究可视化分析
2023-09-08王莎莎
王莎莎
(1.北京外国语大学 英语学院,北京 100089;2.黄冈师范学院 外国语学院,湖北 黄冈 438000 )
伴随着英语的全球化,英语与世界各国本土语言和文化的结合促使了“世界英语”(World Englishes)的涌现[1]。“世界英语”的概念始于20世纪七八十年代,Kachru(1985)提出了三个同轴圈理论模型,将世界上的英语变体划为“内圈”(本族语变体,如英国、美国、加拿大英语)、“外圈”(英语作为第二语言的变体,如印度、肯尼亚、巴基斯坦英语)、“扩展圈”(英语作为外语的变体,如中国、日本、韩国英语)[2]。这种观念使英语成了复数,打破了英、美英语的霸权地位,认为各种英语变体之间的地位是平等的,各个变体内部均有自己的标准。本文结合文献计量软件,采用定性与定量相结合的方法,从年度发文趋势、关键词共现、期刊共被引、作者共被引、文献共被引以及学术合作六个方面对国外“世界英语”研究进行系统阐述。
一、研究工具及数据来源
CiteSpace是美国德雷塞尔大学计算机与情报学陈超美教授基于Java语言开发的一款引文可视化计量软件。该软件是一款用于分析科学文献中蕴含的潜在知识,并在科学计量学(Scientometric)、数据和信息可视化(Data and information visualization)背景下逐渐发展起来的一款多元、分时、动态的引文可视化分析软件[3]。通过此类方法得到的可视化图形被称为“科学知识图谱”(Mapping knowledge domains, MKD),它具有“图”和“谱”的双重性质和特征,展示知识单元或知识群之间网络、结构、互动、交叉、演化或衍生等诸多隐含的复杂关系[3]。本文使用的CiteSpace版本为CiteSpace.5.6.R5。
本研究的数据来源是Web of Science引文索引数据库,包括SCI、EI、SSCI、 A&HCI、CPCI。按照Kachru(1985)首次提出的“World Englishes”(“世界英语”)概念,我们在WOS网站以“World Englishes”作为主题词展开检索,检索时间段为1979-2019年,文献类型精炼为Article,共得到文献373篇。利用WOS文献输出功能,通过CiteSpace除重处理后,有效文献为368篇,时间跨度为1996-2019年。
二、可视化分析与讨论
(一)年度发文规模变化 某一学科或领域的发文规模在一定程度上直观反映了该学科或领域的研究水平与研究热度,是判断其成熟程度的重要标志[4]。1996-2019年间,国际“世界英语”相关主题研究的WOS总发文量是368篇,总体研究年度发文量趋势见图1。国际“世界英语”研究年度发文量可以概括为三个阶段:萌芽期(1996-2006年)、缓慢发展期(2007-2011年)、高速发展期(2012-2019年)。第一篇论文是Kachru于1996年发表在Journal of Aesthetic Education的World Englishes: Agony and Ecstasy。随后几年(1997-2001年)无相关文献出现,一直到2002年,Vavrus在Tesol Quarterly发表1篇文章:Postcoloniality and English: Exploring language policy and the politics of development in Tanzania。之后几年发文量也较少,直到2008年有了较明显的增长,2009年和2018年分别出现了小高潮,之后的发文量有所回落,但整体上发文量呈现出增长趋势,尤其2012-2018年间,发文量增长迅猛。

表1 基于CiteSpace的关键词中介中心度值及共现频次排名

图1 1996-2019年国际“世界英语”主题研究WOS文献的年度发文量变化
(二)关键词共现分析 研究热点是在某个领域中学者共同关注的一个或多个话题,关键词是对主题和文献内容的高度概括,能够反映某一领域的研究话题。CiteSpace中提供了对研究主题的词频、时间趋势、突发性等分析功能。通过运行CiteSpace,选择节点类型(Node Types)为Keyword,可以通过关键词共现功能探索“世界英语”主题下的研究热点和研究趋势,得到图2的科学知识图谱。
中介中心性(centrality) 是某一节点与附近其他节点之间的关系参数,描绘的是某一节点在一群关联节点中的中心性程度,具有较高中介中心性的节点表示该节点在相关关联结构网络中的重要程度较高。中介中心度>0.1的词或词组有17个,分别为World Englishes(“世界英语”)、 Language(语言)、Lingua Franca(世界通用语)、 English as a Lingua Franca(ELF英语通用语)、Identity(身份)、Globalization(全球化)、Corpus(语料库)、Construction(建构)、Global Englishes(全球英语)、Acquisition(习得)、China English(中国英语)、Belief(信仰)、China(中国)、Learner(学习者)、Communication(交流)、World(世界)以及EIL(English as an international language英语国际语)。
如图2所示,节点大小代表它的总被引次数,节点越大总被引频次越高。表1展示了共现频次和中介中心度排名前十的关键词,这些关键词代表了居于核心的研究主题,对“世界英语”研究的未来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值得注意的是,中介中心度值排名第6位和第9位的关键词分别是China和China English,说明中国环境下的英语研究以及中国英语研究得到了国际广泛关注,成为“世界英语”研究热点之一。 Schneider认为,中国英语已经呈现“本土化发展方向明显”(Nativization is clearly in flux)的趋势,所以研究问题具体化是大势所趋[5]。
通过表1统计的高频和高中介中心度关键词,能够分析出当前国际“世界英语”主题研究的热点主要有七大板块:其一,术语的界定与解读。与“世界英语”(World Englishes)概念相关的有:作为通用语的英语(English as a Lingua Franca)、作为国际语的英语(English as an International Language)以及全球英语(Global Englishes)等,不同学者对这些术语进行了界定并阐述了它们之间的联系与差异,如Jenkins,Pennycook,Trudgill等;其二,英语变体特点研究,包括对英语变体诸如词汇、语法、语用特点的微观研究,以及宏观英语变体的理论模型建构研究;其三,语言身份研究,涉及英语所有权问题、语言政策、民族身份认同以及话语权研究;其四,语言态度研究,随着英语标准的多元化以及变体研究的增加,对“世界英语”态度的考察也吸引了越来越多学者的注意;其五,语言教学研究,“世界英语”研究范式下如何发展英语教学;其六,以语料库为代表的实证研究,大数据时代如何进行大规模文本挖掘,语料库语言学家通过建设语料库研究语言变体,为“世界英语”研究提供了新的视角,注入了新的活力,成为国外研究主要趋势;其七,以中国英语为代表的扩展圈国家英语变体研究,Schneider(2003)预测:在20世纪,英语主要传播地为外圈(outer circle)国家和地区;近年来越来越多的研究正转移到扩展圈(expanding circle)国家和地区上,正是在这里,英语正以极快的速度发展和传播[6]。因此,扩展圈国家英语变体成为研究的热点话题。
(三)期刊共被引 期刊共被引能揭示学科领域结构,反映出期刊在该领域的地位。节点类型选择Cited Journal,运行CiteSpace,得到图3期刊共被引网络图谱。

图3 基于CiteSpace的期刊共被引网络图谱
节点代表期刊,节点越大,说明该期刊被引频率越高。由表2可知,被引频次排名前十的期刊为:WorldEnglishes,AppliedLinguistics,TesolQuarterly,EnglishToday,ELTJournal,AnnualReviewofAppliedLinguistics,EnglishWorld-Wide,JournalofEnglishasaLinguaFranca,Thesis,JournalofSociolinguistics,被引频次见表。其中,AnnualReviewofAppliedLinguistics(0.20),AppliedLinguistics(0.17),JournalofSociolinguistics(0.1)被引频次和中介中心度排名均靠前,是本领域的重要期刊,是“世界英语”研究的主要传播载体。

表2 基于CiteSpace的共被引期刊频次排名
由表2列出的“世界英语”研究重要期刊可以看出,“世界英语”研究呈现出跨学科发展趋势,其与社会语言学、应用语言学、语言教学、跨文化交际等学科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 20世纪70年代后期到80年代,结构主义方法和社会语言学理论被引入“世界英语”的研究中[7],社会语言学把语言使用作为一种社会现象来描述,试图阐释语言和社会的关系。主要代表有Fishman,Bolton,Trudgill,Hannah,Kachru,Xu等。语言态度研究是社会语言学的重要方面也是社会心理学中态度研究的子类。语言态度的研究对于语言政策的制定以及语言教育的改革都具有重要意义[8]。“世界英语”的应用语言学研究始于20世纪60年代,代表人物主要有Strevens,Halliday,Jenkins,He, Li,Kirkpatrick,Matsuda等,主要探讨英语变体作为教学的标准问题,以及如何开展英语教学实践。从跨文化交际研究角度,“世界英语”的提倡者倡导语言模式的多样化和文化模式的本土化,只要交际者之间能够互相理解话语意图即可,研究重点是言语形式的可理解性和可接受性[9]。
(四)作者共被引 节点类型选择Cited Author,运行CiteSpace,得到图4:作者共被引网络图谱。表3列出了被引频次和中介中心度值分别排名前十的作者。统计数据表明,Pennycook, Cristal, Canagarajah, Trudgill, Mesthrie, Blommeart, Schneider, Kachru, Bolton, Bamgbose是中心度值排名前十的学者,表明该领域的研究成果主要通过他们的研究成绩得以实现。 Kachru, Jenkins, Canagarajah, Seidlhofer, Cristal, Kirkpatrick, Bolton, Schneider, Matsuda, Pennycook是被引频次排名前十的学者,说明他们的学术成果受到该领域的普遍关注和认可,具有深远影响力。以上学者引领着“世界英语”研究的发展走向,具有重要学术地位。

表3 基于CiteSpace的作者共被引频次及中介中心度值排名

图4 基于CiteSpace的作者共被引网络图谱
由表3可以看出,Kachru, Cristal, Pennycook, Schneider, Bolton,Canagarajah几位学者被引频次和中介中心度都处于前十位,在本研究领域具有重大影响力。美国语言学家Braj Kachru基于对印度英语的研究,提出了著名的“三大同轴圈”(The Three Concentric Circles)理论,是“世界英语”理论的主要代表人之一。英国班戈大学语言学名誉教授David Crystal认为,未来的英语可能是某种混合体,是世界各地所有英语的混合体。澳大利亚悉尼科技大学教授Alastair Pennycook认为,“世界英语”理论框架以民族主义为核心,而英语的使用应当趋于多元,并提出“多元英语”的概念。针对新变体的语言演变,雷根斯堡大学Edgar Schneider教授提出了动态模型(Dynamic Model),认为语言创新按特定的演变阶段进行,实体性的词项较早被借用,后阶段会出现新的构词和句法规则。香港大学Kingsley Bolton教授搜集和研究了大量有关香港和中国的英语描述和历史,对其进行了语言学和社会语言学研究。美国宾州州立大学Suresh Canagarajah教授挑战第二语言习得和英语语言教学的传统方法,认为英语能力测试应基于地方语言特色来考量(based on local institutionalized varieties),一个人对英语的“精通”是指当他穿梭在具有文化特色的不同种类的英语之间,能熟练、精确使用这一语言。
(五)文献共被引 知识基础是由共被引文献集合组成的,而研究前沿是由引用这些知识基础的施引文献集合组成的[3]。通过选择节点类型Cited Reference,运行软件得到文献共被引可视化知识图谱,见图5。中介中心度越大,代表该文献越重要,按照中介中心度排名,前五名分别为Cogo(2012)(0.21),Bolton &Kachru(2006)(0.20),Alsagoff, et al(2012)(0.18),Kachru(2005)(0.14),Blommaert(2010)(0.13)。文献的被引频次能在一定程度上反映该文献的影响度,被引频次排名前五为:Seidlhofer(2011)(49),Jenkins(2006)(27),Blommaert(2010)(26),Kirkpatrick(2007)(24),Jenkins(2007)(24)。通过突现算法可以识别出该文献在时间上的被引变化趋势,通过依次选择Burstness,Refresh以及View来获得共引文献的突发性探测结果,如图6。由图6可知,突现强度排名前五为:Jenkins(2006)(9.9),Kirkpatrick(2007)(7.7),Jenkins(2007)(7.1),Schneider(2007)(6.8),Jenkins(2015)(4.7)。 突现时间较早的文献有Jenkins(2006)(突现年份2016-2012)和Brutt-Griffler(突现年份2006-2010),表明早期受到关注,Schneider(2007)(突现年份2016-2019),Jenkins(2015)(突现年份2017-2019),Matsuda(2011)(突现年份2017-2019),表明近期受到关注。Seidlhofer(2004),Jenkins(2006),Jenkins(2007)三篇文献突现时间较长,反映该文献长期受到关注。

图5 基于CiteSpace的文献共被引网络图谱

图6 基于CiteSpace的共引文献突发性探测结果
综合考虑中介中心度、被引频次以及突现强度,列出“世界英语”研究领域的高影响力文献20篇,见表4。

表4 基于CiteSpace的“世界英语”研究领域重要文献
Cogo(2012)提出了有关ELF概念和使用的问题及其对ELT的影响,并展示了ELF交流的可变性、丰富性和创造性[10]。Bolton &Kachru(2006)认为,1980年以前,人们普遍认为英语学习的主要目标是英国的“标准英语”,然而,在20世纪80年代,人们对识别和描述全球英语变体的兴趣开始增长,标志着关注的焦点从“English”转向了“Englishes”[11]。多语种和多元文化社会中的英语教学需要新的视角、原则和实践,Alsagoff, et al.(2012)阐述了这种需求并讨论了与EIL教与学相关的基本问题,为多语言和多元文化背景下语言教育的相关研究提供了关键资源[12]。Kachru(2005)探讨了英语在亚洲的形式和功能、文化适应及本土化,为“世界英语”相关研究尤其是亚洲英语研究提供了至关重要的基础[13]。Blommaert(2010)重新审视了语言交际,构建了一个社会变迁中的语言变化理论,对地域、语言储备、能力、历史和社会语言学的不平等进行了反思[14]。Brutt-Griffler(2002)强调非母语英语使用者的作用,并介绍了一种新的语言模式,即语言群体的第二语言习得:宏观习得[15]。Graddol(2006)特别关注印度和中国这两个新兴经济大国的影响,以及它们对全球英语使用产生的影响,认为当前的全球化让位于更大的地区主义,以及更复杂的语言、经济和文化力量模式[16]。Jenkins(2007)探讨了对ELF相关态度、其对学生身份的影响、教师教育中存在的问题、英语教材和测试方法[17]。Schneider(2007)认为,英语的全球传播导致了世界各地出现了各种各样的后殖民语言变体,后殖民英语为这些变体的演变提供了清晰而新颖的解释,他的研究引起了社会语言学家、辩证法家、历史语言学家和句法家的注意[18]。Seidlhofer(2011)认为,ELF是一种适应性和创造性的语言使用,类似于社会语言学研究中的一般语言变异,而不是英语母语者的偏差或错误版本[19]。Jenkins(2006) 探索了最近关于WEs和ELF的研究、其对TESOL的影响、对英语语言标准的影响,以及长期存在的本地和非本地教师之间的争论[20]。Kirkpatrick(2007)审查和重新评估诸如“标准”“多样性”“母语人士”和“非母语人士”等概念,并验证多语种和多文化英语教师所发挥的作用,认为语境和学习者需求应决定教学的英语变体[21]。Jenkins(2015)从社会语言学、ELF与跨文化交际领域的协同效应,以及其对SLA和ELT的意义等角度,对英语作为一种通用语进行了实证研究[22]。Mauranen(2012)探讨了英语在学术语境中的使用,开创了学术环境下英语作为一种通用语言的新兴领域[23]。Matsuda(2012)批判性地审视了当前的英语教学实践与英语作为国际通用语言的使用,弥合了理论讨论与英语教学实践之间的差距,并提出了在国际语境中培养合格英语使用者的各种方法[24]。Jenkins, et al(2011)讨论了ELF研究的主要领域,并从词汇语法、音位学和语用学三个层面揭示了ELF的语言流动性[25]。He &Li(2009)将“中国英语”定义为“世界英语”概念的一种表现形式,指出中国大陆大学英语理想教学模型是“中国英语”,而不是以英语母语为基础的标准英语。这种首选的模型是一种标准的英语变体(如美式英语和英式英语),同时具有明显的中国英语特色[26]。Seidlhofer(2009)比较了“‘世界英语’(WEs)范式”与“英语作为一种通用语(ELF)范式”,认为二者都关注语言接触、语言变异、语言规范、语言所有权和社会身份等问题[27]。Mesthrie &Bhatt(2008)研究了在前英国殖民地东非和西非、加勒比海、南亚和东南亚发展起来的英语作为第二语言的英语变体,对导致这些变体的共同环境作了历史综述,并详细解释了他们相似的结构、使用模式、词汇和口音[28]。Canagarajah(2013)认为,多语言者将自己的语言和价值观融入到英语中,这为他们打开了各种谈判策略,帮助他们解读其他独特的英语变体,并构建新的规范[29]。
(六)作者、机构和国家合作分析 通过选择节点类型为Country,运行CiteSpace,得到图7:国家合作网络。其中被引量最大的是美国(88),其次是中国(52)、澳大利亚(39)、英国(32)、德国(21)、新加坡(18)、加拿大(14)、日本(12)。最大聚类是以美国为中心的合作网,包括土耳其、新加坡、芬兰。与中国合作频繁的国家有新加坡、新西兰、澳大利亚、德国等。

图7 国家合作网络图谱
通过选择节点类型为Institution,运行CiteSpace,得到图8:机构合作最大聚类图谱。合作机构被引频次排名前十位的是蒙纳士大学、香港城市大学、伊利诺伊大学、南洋理工大学、香港中文大学、新加坡国立大学、普渡大学、亚利桑那州立大学、海峡大学、开放大学。最大聚类是以伊利诺伊大学为中心的合作网,主要有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和韩国外国语大学。广东外语外贸大学与考文垂大学、中山大学以及宾夕法尼亚州立大学均有合作。

图8 机构合作最大聚类图谱
通过选择节点类型为Author,得到作者合作频次排名前六位的依次为Bolton, Collins, Sharifian, Davis, Xu, Nelson。Davis和Bolton,Graddol和Bolton,Xu和Sharifian有明显学术往来。
三、结论
本文应用文献计量软件CiteSpace对WOS中的368篇关于“世界英语”研究文献进行了可视化分析,研究发现:第一,近年来“世界英语”研究呈增长趋势,研究热度上涨;第二,研究主题和热点主要有相关术语的界定与探讨、英语变体特点、语言态度、语言身份、语料库、语言教学及扩展圈英语变体等;第三,“世界英语”研究作者和机构主要来自美国、中国,澳大利亚、英国、德国、新加坡等国家,国家、机构、作者合作明显;第四,该领域有重大影响力的学者有Kachru,Pennycook,Cristal,Canagarajah,Trudgill,Mesthrie,Blommeart, Schneider,Jenkins,Seidlhofer,Kirkpatrick, Bolton,Matsuda等;第五,“中国英语”变体研究受到国际的普遍关注,成为“世界英语”研究热点之一。Xu,Kirkpatrick,Schneider,He,Li,Bolton等学者均对中国英语变体进行了探讨,成果在国际具有重要影响力。
“中国英语”研究是未来“世界英语”研究框架的重要构成部分。目前我国的“世界英语”与中国英语相关研究也在不断地深入,具有良好的发展前景。国内学者如文秋芳、李文中、汪榕培、高超、高一虹、俞希、战菊等应用“世界英语”研究范式对中国英语特点及教学进行了考察。但是,相对于国际“世界英语”研究来说,国内研究具有明显差距,国内学界在今后研究中,需要加强和其它国家的研究合作以及协同创新,借鉴国外先进的科学研究方法,更新研究范式,进一步拓展和深化“世界英语”和中国英语研究主题,挖掘中国特色。总之,应当注重全球视野和本土意识的培养,紧跟时代潮流,把握民族话语权,增强国际影响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