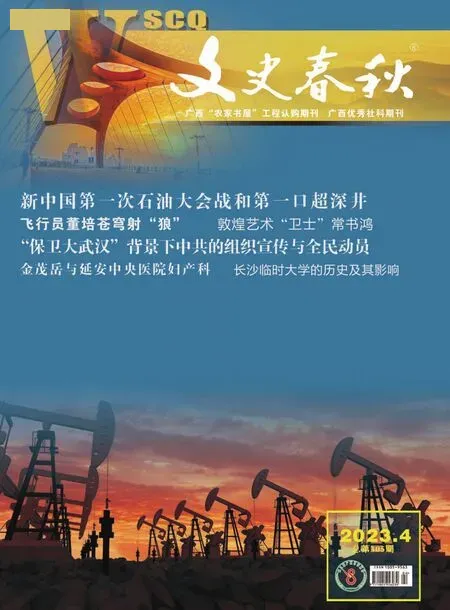长沙临时大学的历史及其影响
2023-09-07王宝山
● 王宝山

1937 年抗战全面爆发后,北平(今北京)的国立北京大学、国立清华大学和天津的私立南开大学三校南迁长沙,合建国立长沙临时大学,这也被视为西南联合大学的前身及序曲。这段建校历史虽然只有短短7 个月,然而其在特殊时代下艰难的创办与磨合历程,对教育界产生了重要影响。
长沙临时大学组建及教学情况
1937 年七七事变后,抗战全面爆发。华北之大,早就“已经安放不得一张平静的书桌了!”北方各高等学校纷纷告急,一批名教授和爱国知识分子深为学校存亡担忧,主动向校长和政府提出保学建议。不久,平津沦陷。8 月中旬,《教育部设立长沙临时大学计划纲要草案》决定,“政府为使抗敌期中战区内优良师资不至无处效力,各校学生不至失学,并为非常时期训练各种专门人才以应国家需要起见”,选定适当地点,筹设若干临时大学,其中临时大学第一校区设在长沙,由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南开大学组成国立长沙临时大学。
陈岱孙在《国立西南联合大学校史》(西南联合大学北京校友会编,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序言中介绍,之所以选址长沙,是从办此新校的物质条件出发——清华已为特种研究所修筑校舍,可做暂时驻扎的打算。早在1935 年,清华大学已将教研工作所急需的图书、仪器,秘密南运至汉口,可以随时运往长沙新校(此前清华大学获得湖南省政府赠予的长沙河西左家垅原湖南省立高级农业学校地皮)。
1937 年8 月28 日,教育部下令成立长沙临时大学筹备委员会,指定南开大学校长张伯苓、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北京大学校长蒋梦麟为筹备委员会常务委员。长沙临时大学筹备委员会从当年9 月6 日开始在长沙商谈,9 月13 日正式举行第一次筹备委员会会议,就校舍与设备、经费筹集与开支计划、院系设置、师资遴选、招生、行政组织、教学设施、学生困难救济等事宜进行商量和安排。9 月28 日正式启用“国立长沙临时大学”关防,蒋梦麟、梅贻琦、张伯苓为学校常务委员,主持校务。
学校从10 月18 日开始学生报到,10 月26 日举行开学典礼。11 月1 日,长沙临时大学正式上课,标志着学校的全面运行。这一天后来也作为西南联合大学的校庆纪念日。由于长沙的校舍不够用,教学分长沙、南岳两个教学区进行。1938年1月24日至29日(校历计划是14 日至19 日),学校举行学期期末考试,1 月底结束第一学期的教学工作。原计划第二学期于2 月21 日在长沙开学,由于1937 年底南京沦陷,武汉震动,严重影响长沙的安宁。1938 年1 月,校务委员会作出迁校的决定,蒋梦麟请示蒋介石并经教育部批准许可后,2 月,开始搬往云南省会昆明。有一部分学生从军或去战地服务,有的学生去西北学习或转到别的学校。2 月20 日起,其余800 多人分三路西迁,其中200 多人组织湘黔滇旅行团翻山越岭,步行1800 多公里赴滇,约4 月下旬基本到达昆明。
1938 年4 月2 日,按照教育部关于长沙临时大学改变校名的电文,将“长沙临时大学”更名为“国立西南联合大学”。5 月2 日,西南联合大学在昆明举行开学典礼,开始西南联合大学新的奋斗历程。

长沙临时大学旧址
长沙临时大学是在仓促间组建的,湖南各界对建该校给予了大力支持。如湖南国货陈列馆为该校提供了急需的部分图书。考虑到筹建实验室的场地、经费以及时间的关系,筹备委员会决定将工科学生实验全部安排在湖南大学进行,电影、机械两系学生寄宿湖南大学,理科实验设备、场地全由湘雅医学院支持。
由于长沙临时大学的筹备时间很短,来不及也没有财力建设新的校舍,教育部与湖南省教育厅商定租用长沙韭菜园圣经学校(美国教会经营)的校舍,但该学校只有3 层正楼1 栋,仅可以用于办公室、教室、图书室和实验室,宿舍3 栋,只能做单身教职员宿舍,且只够职员和助教两人共住一间,无学生宿舍,只好在附近的中央警官学校借用四十九标的营房3 座做男生宿舍,在韭菜园涵德女校租一栋楼房做女生宿舍。尽管这样,也容不下1000 人,不能满足学校需要,只够供理、法商、工3 个学院上课和学生住宿。因此,电机、机械两系的学生约160 人只好全部寄宿在湖南大学上课。文学院教职工约30 人、学生约190 人迁到南岳圣经学校,设立分校。
南岳教学区的条件同样艰苦,学生宿舍拥挤,室内无法看书写字,女生住房与办公合在一小楼房内。教师住在小山坡上的一所楼房,两人一室,不挑人,也不挑房,用抽签方式决定。就连闻一多住的房子,也免不了刮起风来两扇窗门“噼噼啪啪”打得很响,打一下,楼板就震动一下,天花板的泥土便掉下一块。条件如此,但教授们表现出吃苦耐劳、关心国家、咬紧牙关尽心尽力为国家培养人才的精神,学生们呈现出立志为胜利后建设国家而刻苦学习的风貌。
尽管教学和生活都异常艰苦,教授们营造的学术空气依然较浓。三校原来的研究所能够恢复的都很快进入工作状态。比如无线电研究所在极其困难的条件下,一面从事短波无线电之研究,一面训练电机、物理两系学生,注重无线电之实用。文学院的教授白天上课,晚上就铺开写作摊子,如闻一多考订《周易》,朱自清钻进南岳图书馆搜集资料,继续撰写《文选序〈事出于沉思义归乎翰藻〉说》,金岳霖写出《论道》。1937 年至1938 年发表的大量论文不少是当时科研的结晶。当然,由于实验条件的限制,许多自然科学的研究受到严重影响。
传播抗日火种
长沙临时大学的建立,是全面抗战形势下催生的产物,三校南迁从一开始便带有保存国家文化、维持民族命脉,以期日后复兴教育的使命感。
长沙临时大学在抗日的炮火中诞生,决定了其办学宗旨为抗日服务。为了适应抗日需要,长沙临时大学采取军事性的建制。
一是在着装方面。学生们均身着草绿色的大衣,制服与棉大衣的领上有两个铜质的“临大”领章,穿起制服,戴上军帽,披上大衣,像个军曹,这在战时的长沙无形中也是一重要的安全保障,女同学没有人用华丽衣饰来耀人眼目。
二是在管理方面。三校学生一律编组成队,军事管理,全体住校,睡双人床,每天升旗、降旗,甚至睡的位置,都按照军队中编制的次序;三校决定把军事训练列为学生的必修项目,任命张伯苓为军训队队长兼学生战时后方服务队队长。
三是在课程设置方面。三校应时事之需,增设一些新的课程,如文学院增添国际形势、国际概论学科,理工学院增加化学战争、堡垒工程、当代工业3 个学科,以期为学生随时走向战场提供理论准备。
四是邀请一些社会名流来校作讲演。湖南省政府主席张治中主讲抗战形势,劈头痛斥国难当头,不上前线作战服务的一批青年人;国民党军委政治部部长陈诚把大家比喻为国宝,国家以后的命运全都在青年身上,说得大家飘飘然;国民党高级将领白崇禧讲授“战略与士气”等问题;《大公报》主编张季鸾主讲战后形势发展的预测;八路军驻长沙办事处负责人徐特立先后3 次来校讲演,介绍延安八路军情况以及动员民众参加抗日战争。这些讲演者虽然观点各异,但总的说来都使学生进一步认清战争形势,对于坚持抗战起了积极作用。
长沙临时大学11 月1 日开学上课,12日侵华日军占领上海,12 月13 日南京失陷。侵华日军逆江而上,威逼武汉和长沙。国难殷深,长沙临时大学掀起一股从军的热潮。1937 年12 月10 日,学校召开常委会,决定成立“国防服务介绍委员会”和“国防技术服务委员会”。29 日,常委会又决定将这两个委员会合并为“国防工作介绍委员会”。学生高涨的抗战热情,加上学校的大力支持和配合,不到两个月,据教务处登记簿,提出申请保留学籍、领取肄业证明和参加抗战工作介绍信的就有295 人,占全部学生的20%。从军学生的去向有3 个:有的直接参加国民党军的部队,有的加入各种战地服务团,有的到敌后参加抗战。其中13 人去延安参加八路军。留校学生则组织宣传队向当地民众进行抗日宣传,组织演剧队慰问抗日军队。
爱国激情促使长沙临时大学师生开展各种形式的抗日运动。不少学生向学校建议实施战时教育,1937 年10 月,长沙临时大学中共党支部成立。1937 年12 月13 日,南京大屠杀发生,长沙临时大学党支部组织在校1067 名学生举行抗日誓师大会,随后在党支部的号召下,组成40 多人参加的湖南青年战地服务团,和300 多名长沙临时大学的学生一起奔赴延安。长沙临时大学的学生还组织宣传队向当地民众进行抗日宣传,组织演剧队慰问抗日军队,其组建的话剧团与当地戏剧团体联合举办劳军汇演,演出阳翰笙的《前夜》。这批学生无不继承着从北平沿袭的五四运动和“一二·九”运动的光荣传统;有的教师表示一心等待政府的指示,或上前方参加战地服务,或留后方从事战时生产,为民众教育尽点力。
长沙临时大学在湖南存在的时间虽然不长,但学校围绕抗战开展了系列活动,使战时的湖南成为全国抗日教育的重要阵地之一。
弘扬兼容并包的文化传统
最初关于长沙临时大学能否成立,还受到过人们的怀疑。1943 年11 月,陈序经回忆说:“在那个时候,就是一般教育界的人士,以至北京、清华与南开这三个大学的同仁,也很怀疑临大的能够成立。因为这三个大学,不只因为历史、环境、学者有不同之处,而且因为经费上的支配,课题上的分配,以及其他好多问题,并不容易解决。”(陈序经:《联大六周年感言》,载《大公报》1943 年11月1 日)
事实上,三校的关系并非想象中的复杂。从历史上看,三校本来就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素有“通家”之誉。校级负责人中,南开校长张伯苓担任过清华董事,曾为全美清华同学会总会长的北京大学教授胡适又是南开校董,而清华校长梅贻琦是南开第一期的毕业生;院系级负责人中,清华大学文学院院长冯友兰、中文系主任朱自清均毕业于北京大学;南开大学教务长黄钰生、北京大学哲学心理系主任汤用彤和政治学系主任钱端升,均毕业于清华大学;北京大学算学系主任江泽涵、物理系主任饶毓泰,都担任过南开大学教授。

出于加强和密切关系的考虑,长沙临时大学在建校之初的人事分派和组织机构的设立上即有所考虑:一是在校级领导层面,由三校校长张伯苓、梅贻琦、蒋梦麟组成长沙临时大学筹备委员会常务委员,共同负责临时大学各项事务,不设校长,采取集体领导制;二是在院系机构领导方面,临时大学共设4 个学院,院长人选除了工学院是清华独有,其他三院均是一校出一人,文学院院长由北大的胡适担任(因胡适未到改由冯友兰接任),理学院院长由清华的吴有训担任,法商学院院长由南开的陈序经担任;至于经办校政的总务长、教务长、建设长也是一校出一人担任;至于学系的系务,当时未设系主任,而是各系的教授互推一人为系主席,办理系务;三是三校虽然组合,但是各自仍保持着自身的系统,有独立于长沙临时大学之外的各校机构。
长沙临时大学在组织机构方面做到“三校合一”、各有特色的同时,三校的学术精神也得到很好融合。当时的三校有“山、海、云”之称:南开稳定如山,北大宽容如海,清华智慧如云,三校师生齐聚长沙临时大学,在交流中取长补短。
长沙临时大学组建时,租用的宿舍大多条件简陋,秋冬雨季,外面下大雨,屋内下小雨,食堂里只有桌子没有凳子,大家都是站着吃饭。尽管种种困难摆在面前,但总也敌不过师生们的乐观情绪。三校校长把五四运动倡导的“反帝、爱国、民主、科学”大旗高挂在长沙临时大学的校舍——长沙韭菜园圣经学院旧址上。圣经学院校舍的3 座楼前是一个四方形的大院子,课余闲暇,许多学生喜欢拿着书或卧在草坪上,交流学习心得或议论时政;由于长沙临时大学在长沙的校舍有限,文学院则迁往南岳衡山分校。分校的教学条件也很差,夜晚菜油灯光线暗淡,教授和学生都没法在灯下看书,便聚集在宿舍里讨论问题,师生接触的机会比较多,关系融洽,其热烈的交流气氛颇有古代书院的风味。
当时大量中国学术界泰斗云集湖南,虽然时间短暂,但他们以各种途径传播开放自由的学术精神、民主科学的治学理念,丰富、活跃了战时湖南的文化气氛。
正由于上述远因近果,长沙临时大学便具有双重意义:“一个是表面的意义,那当然就是如其名称所揭,是一个‘学校’,是一座研究学问、传授知识的最高学府;但在另外却还有一重不为人们所见的引申意义,那就是一个领导舆论、思想的政治中心。”(《学府纪闻——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回忆录)》)
提升了湖南教育的综合实力
长沙临时大学成立后,其中理学院和工学院二、三年级学生大都在湖南大学借读。湖南大学还接纳来自平、津、宁、沪等地的流亡学生和遭驱赶回国的留日学生共300 多人借读,彰显了“纳于大麓”的襟怀与担当。1937 年9 月5 日,教育部电令湖南大学收容100 名战区学生借读。湖南大学经两次登记与严格审查并举行甄别考试,共收容借读生157名,后来长沙临时大学西迁昆明,失学者增多,湖南大学决定自该学期起再收容借读生120 名。这些借读学生成为一群特殊的新湖南大学人。他们穿着不同的校服,成立了借读生同学会,把救亡工作写入章程,与湖南大学同学一起读书不忘救国。1937 年至1938 年,除北大、清华、南开3 所高校,外省迁湘的学校还有南京国立戏剧学校、北平民国学院、国立杭州艺术专科学校、山东省立戏剧学校等。
抗战的全面爆发,是导致大量北方学校迁湘和大批学生失学的重要因素,而在因战争迁入湖南的失业知识分子中间,有相当一部分人纳入当地的教师和学生队伍,他们都成为战时湖南教育发展的重要力量。
抗战时期湖南各级各类学校的数量急剧增多,教育出现蓬勃发展的势头:1937 年全面抗战之前,湖南有中学81 所,其中省立6 所,县立23 所,私立52 所,学生人数为30782 人;到了1946 年,湖南中学已达到294 所,其中省立16 所,联立10 所,县立67 所,私立201 所,学生已达103180 人,学校数量比1937 年增加2.6 倍,学生人数增加2.3 倍;高等教育也取得相当的发展,除原有的湖南大学、湘雅医学院,国立师范学院等院校也纷纷兴起。
当然,促成战时湖南教育界新气象是多重因素构成的,但是长沙临时大学的迁入,毕竟使大量的知名学者、优秀学生涌入湖湘大地,尽管时间短暂,但他们在湖南的行动、传播的思想所形成的影响,必然深入湖湘儿女的心中,无疑对湖南教育的发展起到巨大的导航和引领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