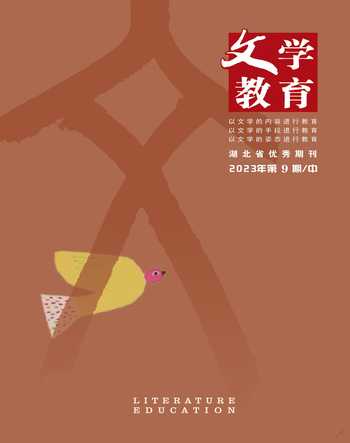从亨利·米修视角谈中国文化自信的底气
2023-09-04张水燕
张水燕
内容摘要: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指出“必须坚定历史自信、文化自信,坚持古为今用、推陈出新”。中国文化自信的底气亦见于不同文化背景的人对中国文化的认同。法国作家亨利·米修生长于欧洲,却对欧洲文化没有认同感,试图逃离欧洲,探索新文明。1931年,米修抵达亚洲,撰写了《一个野蛮人在亚洲》。之后,米修留下了几部作品来回味中国文化。“野蛮人”米修对中国文化的品评以及中国文化对米修的毕生影响,彰显出中国文化自信的底气。
关键词:亨利·米修 野蛮人 旅居中国 中国文化
亨利·米修于1899年出生在比利时那慕尔省。1914-1918年,德军占领比利时,15岁的米修亲历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当时,整个欧洲战火弥漫,萧条不堪。面对这场“集体自杀”,米修对整个欧洲文明深感绝望。《厄瓜多尔》中,米修犀利地表达了他对欧洲文明的不认同:
保罗·瓦雷里很好地定义了现代的欧洲文明;我没有等到他提供的那些关于欧洲文明的局限的具体例子,就已经对它感到厌恶之极。
......
啊!是的,欧洲文明,是的,瓦雷里先生,不管是你们的罗马人、希腊人,还是基督徒,都已经不能再为任何人提供氧气了。[1]
受友人邀请,米修于1927年出发去往厄瓜多尔。到达厄瓜多尔后,米修发现厄瓜多尔随处可见西方殖民压迫留下的印迹,西方文明的影子[1]。
米修认为,“这次旅行是件蠢事”。[1] 他在这里并没有真正地逃离欧洲。一座座高耸的教堂,教堂里庄严的仪式,当地人口中说出来的西班牙语,都带着浓厚的欧洲色彩。就探索新文明来说,厄瓜多尔之旅是失败的。还未到返程期,米修已经想离开了。[1]
返回巴黎后,米修并未放弃他对新文明的探寻。1931年,米修开启了亚洲之旅,去了印度、中国、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和日本,在亚洲逗留了八个月。1933年,米修出版了作品《一个野蛮人在亚洲》。
《一个野蛮人在亚洲》的中国部分,米修开篇便对中国人灵巧的工艺进行了描述:“中国人是天生的工艺师。凡是能在干零活时发现的东西,中国人都发现了。独轮车、印刷术、雕版、火药、火箭、风筝、出租马车、水磨、人体测量、针灸、血液循环,或许还有指南针以及大量别的东西。”[2] 在他看来,中国人非常灵巧,也注重实用。所有这些发现都有着“实践价值”[2]。
与宗教氛围浓厚的西方不同,中国人务实,不过于迷信宗教。米修出生不久后便行过洗礼,十二岁时上了耶稣会中学,在天主教的氛围中长大,却不信仰天主教。米修博览群书,并受到洛特雷阿蒙(1846-1870)作品《马尔多罗之歌》的启发,走上写作之路。《马尔多罗之歌》创作于1868-1869年,烙上了鲜明的时代色彩:当时法国政治黑暗,思想界寻求挣脱束缚,人们开始对他们信仰的上帝提出质疑。奈瓦尔呼吁“上帝死了”,“出生不要神甫,结婚不要神甫,死亡不要神甫”的口号在大学生中广为流传。洛特雷阿蒙在《马尔多罗之歌》写道:“我在生命的最后一刻不会被神甫围绕。” [3]《马尔多罗之歌》对基督教和上帝的深刻抨击在米修心中引起了共鸣。米修作品中充斥着对基督教的抨击和讽刺。[4]
米修在中国寺庙里看到的则是另外一幅景象:“在一个寺庙里,中国人完全自由自在。他抽烟、谈笑。在小祭坛的两边,算命人按照完全印好的表格预卜未来。”[2] 因而米修认为“中国人,如同在别处听到的那样,没有特别的宗教精神。”[2]
孩提时期的米修一直学着天主教的规矩,来到中国,他看到中国的孩子未曾受过宗教的束缚,而是接受着礼仪教育。[2]
西方的宗教正是米修所憎恶的。在西方,宗教势力渗透到政治、经济、文化领域,凌驾于社会生活之上,宗教沦为教会的牟利工具。[1]
中国人的务实精神不仅在于不耽于宗教,也体现在不畏惧死亡。在米修看来,“中国人觉得死亡没有任何悲剧意味。”“中国人生前就准备了他的棺材。他悠然地对待死。”[2] 中国人注重现实生活,追求物质财富,因而骨子里流着经商的血液。[2]
为了证明做买卖已渗透到中国人的思维方式中,米修戏谑地引用了李汝珍《镜花缘》十一回:“观雅化闲游君子邦,慕仁风误入良臣府”中的典故。作者李汝珍本意欲跳出实用主义,然最终仍未能摆脱这种做买卖的思维。[2]
米修笔下的中国人务实到极致,充满烟火气和小商贩气息,描述幽默诙谐又略带讽刺意味,而这种实际、脚踏实地的生活气息却是米修在他乡寻求多年而不得的人间真实。1927年,米修前往厄瓜多尔,开启了他的第一场海外旅行。1929年,父母逝世后,米修又先后去了土耳其、意大利、北非。1931年,米修旅居亚洲。从米修1932年5月5日写给友人Renéville的信中可得知,米修是在亚洲找到了“有意义”的国家和人民[5]。
中国人注重实用,并不影响中国成为伟大哲学思想的发源地。米修对东西方哲学做了如是评价:“西方哲学使人脱发和减寿。东方哲学使人生发并延年益寿。”[4] 道家思想对米修产生了毕生的影响。米修在《一个野蛮人在亚洲》的序言前引用了老子的名言“治大国如烹小鲜”,可见米修对道家思想的敬仰。米修读过《道德经》的译文,《一个野蛮人在亚洲》中,米修道出了老子的智慧和高深莫测。[2]
米修从小憎恨华丽的辞藻,认为世上的作家大都是些美丽词语的制造者,是些“造句者”,从而妨碍了对最精髓、最实质性的东西的追求。而老子、庄子,在他们的哲学中,有一种“节约用词”[2]的风格。他崇尚老子的文风,在他看来,老子的文字硬得像块石头,但在坚硬的壳之下,有着鲜美的汁液。只有“得道者”,才能理解。老子的文风在米修的作品中留下了深刻的烙印。老子的作品文字简洁,内容深刻,米修的诗句也具备这两个特征。作品《经验,驱魔》(Epreuves, exorcismes)的开篇诗便表现出这种“节约用词”的文风,诗句多由短短數词构成。
除了道家哲學,米修也阅览了中国政治哲学方面的书籍,很赞同中国的政治哲学观,并认为在政治上,欧洲应该向中国学习。关于中国政治哲学上的先见之明,米修引用了孙中山的观点。
孙中山说得很对:“在政治方面,中国没有什么需要向欧洲学习。”确切地说,它教欧洲,甚至教印度,它做了一切,实行了一切,一直到政府体制的方面的分离。[2]
米修的引用来源于《孙中山全集》第九卷《三民主义·民族主义》。孙中山就中国政治和欧洲政治进行了论述:
欧洲之所以驾乎我们中国之上的,不是政治哲学,完全是物质文明。(……)中国没有的东西是科学,不是政治哲学。至于讲到政治哲学的真谛,欧洲人还要求之于中国。诸君都知道世界上学问最好的是德国,但是现在德国研究学问的人,还要研究中国的哲学,甚至于研究印度的佛理,去补救他们科学之偏。[6]
哲学之外,米修亦醉心中国艺术。《一个野蛮人在亚洲》的中国部分,米修用大量笔墨道出他对中国艺术——音乐、绘画和戏曲的见解,同时对中欧艺术做了对比。
谈及中国音乐,米修引用了孔子听韶乐,“三月不知肉味”的典故:“喜欢中国音乐的欧洲人不多。然而,孔子不是一个夸张的人,绝不是,却被一种乐曲的魔力所吸引,他三个月没吃好。”[2]在米修看来,“中国音乐始终有一种清澈的灵魂。”[2]
米修亦谈到他对中国绘画的印象,中国绘画和欧洲绘画的对比:
中国绘画干净利落,没有浪漫画风,没有颤动。(……)
欧洲人希望能够触摸。他们画的空气是厚重的。他们的人体画几乎总是淫荡的,即使取自《圣经》的主题也是这样。热力、欲望,都可以触摸到。[2]
于米修而言,中国绘画画风清新,中国人“没有丝毫的下流”,甚至“中国的春宫画也充满思想”。[2]中国的绘画表现出“极度的节制”。“中国绘画主要是山水画,事物的生动性,不是靠其厚度及其重量来表现,而是靠其线条来表现,可以这么说。”[2]
中国文字的表现方式和绘画有着异曲同工之妙。米修对中国文字颇有研究。中学时代,米修的同窗,诗人Norge见证了米修对中国文字的狂热。《一个野蛮人在亚洲》中,米修对中国文字的品评引用了伦敦皇家学院教授G.Owen的作品《汉语的发展》。1975年,米修发表作品《中国象形文字》。中国文字注重“暗示”,很难从字面结构认出来。“在二万汉字中,没有五个字能一眼猜出来。”[2]p70这种神秘感深深地触动了米修。
“用细部象征整体的倾向”在中国戏曲上也运用到了极致。米修认为,“只有中国戏是一种真正的精神戏。只有中国人懂得真正的戏剧演出。欧洲人,长期以来,不再表现什么。欧洲人展示全部,舞台上应有尽有,什么也不缺,连我们从窗子里看到的景象也不缺。”[2]《一个野蛮人在亚洲》中,米修引用了《拾玉镯》、《时迁盗甲》、《游龙戏凤》中的情节来表达中国戏曲表现方式的精妙。
米修在多部作品里面谈及树:欧洲的山毛榉,厄瓜多尔的热带森林,中国北京的柳树。树,在米修的笔下,也被赋予了象征意义。[5]
山毛榉是北欧的代表树种,对山毛榉的憎恶事实上象征着对欧洲的恨。在厄瓜多尔,米修见到了另一番景象:“热带的树,看上去有点天真,有点愚蠢,大大的叶子,是我要的树。”[1] 热带森林里的树充满了生机,而北京的柳树,正如中国人的品性,低调、不炫耀,给了米修教益。[2]
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在米修看来,“中国人觉得死亡没有任何悲剧意味”,而欧洲充斥着悲。[2]
米修认为“整个欧洲文学是苦难的文学,从不是智慧的文学”,而“中国人伤心的诗写得很少,不抱怨,因此,只对欧洲人构成轻微的诱惑”。[2]
“百善孝为先”,中国传统文化注重孝道。原生家庭给童年的米修造成的阴影影响着他的一生。米修的第一次远洋之旅,是在圣诞节——阖家团圆的节日前夕出发的。而中国式亲子关系让他感受到了强烈的反差。
中国人一般不强调对人类的职责,而强调对他的父亲和母亲的职责;实际上,这要求灵活和美德,欧洲圣徒几乎做不到。[2]
20世纪30年代初的中国社会动荡不安,米修却认为“虽然在绝对必要的时候参战,中国仍然是一个爱好和平的民族”,“天生的热烈、易怒和好斗性与中国人无涉”。[2]p77中国人“有某些强大、沉重的东西”,让米修有安全感。“与北京的前门相比,星形广场的凯旋门显得很轻,可以换掉。” “世界上没有哪一个城市具有与北京同样厚实、同样美观、同样让人放心的城门。”[2]
《一个野蛮人在亚洲》的中国部分,米修用32个小章节讲述了他旅居中国期间的观感,从一个西方人的视角对当时的中国文化和中国人作了品评。中国音乐、绘画、诗、戏剧给米修打开了艺术新思路。中国哲学,包括儒家、道家哲学对米修构成一种文化冲击。作品文风犀利,米修时而对所见给予褒扬,时而揶揄。因而,仅凭这部作品,无法断言米修是否在中国找到了他真正向往的新文明。
亚洲之旅后,米修还留下几部有关中国的作品:《中国人肖像》(1936-1938),《过往》(1950),《中国象形文字》(1975),《墨戏》(1960-1984)。
《中国人的肖像》用简短的篇幅对当时米修记忆中的中国人进行了刻画。在米修看来,中国文化是“有滋有味”[5]的。
米修在其作品《过往》中道出了中国文化给他看世界的角度带来的变化:
少女的脸上刻着她出生所在文明的印迹。[7]
中国少女的脸庞,当我第一次在香港、广州见到时,便是无比美妙。在中国少女的脸上,中国永远十五岁,带着最初的梦想去感受生活,历经沧桑后,依然明艳,细腻无双。(……)
从此,我用另一种眼光看。[7]
1967年,米修对《一个野蛮人在亚洲》进行了修订,作了新序,对中国部分作了新的批注,并重新出版。新版作品的序言部分,米修再度提及中国和印度文化对其世界观的影响,不再用戏谑的语调,而是饱含深情:“当我看见印度,当我看见中国,这个地球上的人,第一次让我觉得,值得成为真实的人。”[4] 米修一直在试图逃离,逃离欧洲,拒绝欧洲文化,到处漂泊,甚至多次吸食致幻剂麦司卡林,让自己陷入幻境来逃离现实,而中印文化给了他一道光,让他认为生活在现实世界是值得的。
米修不曾学过中文,但从小对中国文字表现出极大的热情。1975年,米修通过作品《中国象形文字》,从文字形状、历史演变的角度诠释了中国象形文字的神秘和精妙。[8]
晚年的米修减少写作,研究集中于绘画。米修的画作多为水墨画,而非欧洲主流的彩色油画。1954年米修出版的“运动系列”画作展示出了米修对毛笔的运用。2004年出版的《亨利·米修全集》(卷三)中汇编了大量晚年米修的水墨画。2020年9月9日至2020年10月11日,米修的画作在上海当代艺术博物馆展出。本次画展的主题为“米修与木心”,旨在呈现米修和木心的畫作内在关联和迥异之处,充分展现了米修画作中的中国元素。
《墨戏》是米修晚年留下的作品,用简短的篇幅写出他对中国水墨画的理解。《墨戏》中,米修对华裔法国画家赵无极进行了评论:
多年来,出于对油画的热情,赵无极偏离了水墨画。这种绘画必须得是中国人,拥有十足的中国人品质才能以轻盈、空灵的方式做到。[8]
作为赵无极的绘画知音,1951年,米修再度鼓励赵无极用水墨进行创作,因为他拥有十足的中国品质。最终,“赵无极,以他自己的方式,重拾了墨戏。”[8]
中国唐代诗人、画家王维对水墨的运用令米修惊叹不已:
一千多年前,有位诗人画家——王维,仅用稀墨水画出了这个世界上最令人难忘的瀑布之一,还有许多山、小路、树林、陡坡、生长在高处岩石上成群或分离的松树。对展现在面前的美景,他仅使用一种颜色,唯一的一种,而且还是黑色。由浅入深,千差万别,剩下的全凭他奇妙的本能。
“他找到了一种方式可以画出云的气息……他的山被当成墨戏。”[8]
米修旅居中国之后的余生都在回味中国文化。中国文化对米修看世界的方式,对米修的创作产生了毕生的影响。米修以一个西方人的视角对中国文化的回味,将中西文化所作的对比,言辞中对中国文化所流露出的敬仰,彰显出中国文化自信的底气。
参考文献
[1]亨利·米肖:《厄瓜多尔》,董强译,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9:20, 96, 124, 161, 182, 251.
[2]亨利·米修:《一个野蛮人在中国》,刘阳译,中国学术期刊电子出版社,1994-2019: 66-78.
[3]洛特雷阿蒙:《马尔多罗之歌》,车槿山译,四川文艺出版社, 2020:19.
[4]Michaux, Henri. Un barbare en Asie. Gallimard. Collection LImaginaire. 1967. Pour la nouvelle édition revue et corrigée:13, 26, 31.
[5]Michaux, Henri. Oeuvres complètes Tome I. Gallimard. Collection de la Plé?觙ade. 1998:XCVI, 169-170, 540-541.
[6]孙中山:《孙中山全集》第9卷,中华书局,1986:230-231.
[7]Michaux, Henri. Oeuvres complètes Tome II. Gallimard. Collection de la Plé?觙ade. 2001:305-306.
[8]Michaux, Henri. Oeuvres complètes Tome III. Gallimard. Collection de la Plé?觙ade. 2004:821, 1410-1411.
项目基金:宁波大学校科研基金项目,编号为XYW20007,项目名称:从亨利·米修视角谈中国文化自信的底气.
(作者单位:宁波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