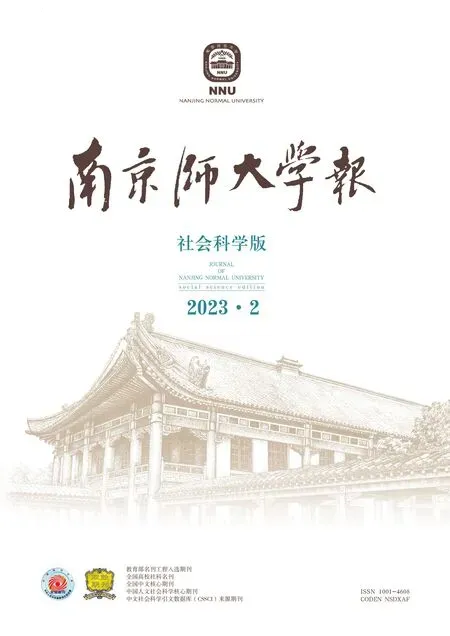从心理学审视胡塞尔现象学的困境与出路
——对一项哲学史任务的阐明和初步探索
2023-09-03高申春
高申春
胡塞尔作为现象学的创始人,其思想的发展和成就,与心理学有着千丝万缕、剪不断理还乱的复杂关系。这种复杂性逐层深入地意味着:任何试图以快刀斩乱麻的方式人为地切断二者关系的努力,都只能带来对胡塞尔思想的不同误解;无论从现象学方面就现象学是什么、还是从心理学方面就心理学是什么的追问来说,似乎都还不能给出明确的回答;只有通过分析二者在胡塞尔思想中的关系,进而揭示现象学和心理学内在的和必然的同一性关系,才能同时肯定地理解二者,并在此基础上推进二者的共同发展。此外,心理学与哲学之间的学科分隔,还进一步强化了上述第一种趋势:概言之,无论在关于现象学作为哲学的研究中,还是在心理学研究中,当涉及现象学与心理学的关系问题时,都倾向于以对这个关系的外在性理解为前提,这种倾向总的来说是不得要领的。也因此,虽然有人将关于胡塞尔现象学与心理学的关系问题作为哲学史任务提出,但一直未能得到原本可以预期的回应;另一方面,对这个哲学史任务的阐明,将成为引导本文后续讨论的有效线索之一。
一、一项哲学史任务的提出及其性质的进一步阐明
在《现象学运动》中,施皮格伯格在评述胡塞尔时颇具直观基础地指出,“对于理解胡塞尔哲学来说,最重要的必要条件之一是要阐明他的现象学与心理学之间的关系”(施皮格伯格,1995年,第199页)。他将胡塞尔的现象学当作一个哲学体系或哲学史的一个环节,并指出,除其他方面外,还必须在与心理学的关系中考察并阐明这个关系,才能理解作为哲学的胡塞尔的现象学是什么。因此,他的这一评论实质上是提出了一项哲学史任务。确实,如果考虑以下事实,即在有关胡塞尔及其现象学的研究中,相比于其他主题,他的心理学普遍被忽视,那么,施皮格伯格的上述评论确乎是意味深长、发人深省的:如果不能同时阐明胡塞尔的心理学思想,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阐明他有关心理学的思考在引导他走向现象学的过程中所起的作用,那么,我们便难以达到对胡塞尔现象学的系统理解。
关于这样一个哲学史任务,施皮格伯格本人是多少有些自觉的,虽然他因为意识到其中可能蕴涵的理论主题之困难而暂时“不想进行这个方面的尝试”(施皮格伯格,1995年,第200页)。结合有关胡塞尔现象学研究的学术史背景看,类似施皮格伯格所意识到的困难,是研究者们普遍地对这个哲学史任务未表现出应有的敏感性的根本原因之一。施皮格伯格指出了这种困难的相互关联的两个大的方面。其一是读者或解释者方面的,又包括以下两个方面:“一方面,在人们的印象中,胡塞尔在反对心理主义的斗争中,甚至在他随后对当时的心理学的批判中,是心理学本身的不共戴天的敌人”;“另一方面,胡塞尔从‘纯粹逻辑’返回到对主体性的研究,被广泛地解释为倒退到心理主义,实际上是倒退到一种心理学上最严重的过错,即‘内省主义’”。其二是胡塞尔本人作为作者方面的:“甚至胡塞尔本人,在他的整个哲学发展过程中,也很难一劳永逸地确定他对于心理学的态度,规定在他的不断改变着的现象学概念的框架内他指派给心理学的确切作用。”所以,“直到现在还很难把握胡塞尔对于心理学和现象学之间关系的解释,在某种程度上,这也涉及他哲学发展的各个时期”(施皮格伯格,1995年,第199—200页)。
关于我们在这里面临的任务及其困难,虽然总体而言,施皮格伯格上述笼统的分析和说明,似乎是明确的,但当我们具体地深入相关主题之中时却发现,我们实际遭遇的困难要复杂得多,并由此得以反过来洞察,如下文将证明的,施皮格伯格的分析和说明潜在地具有误导性,似乎“胡塞尔的现象学”和“心理学”各自是某种现成的、已完成了的什么:一切以此为前提的关于现象学与心理学之间关系的讨论,都不是对这里提出的哲学史任务的执行,而是服务于其他的目的。
如果我们要严肃地把施皮格伯格的上述评论作为一项哲学史任务来执行,那么,关于胡塞尔的现象学及其作为哲学的发展,我们就必须要有以充分的信心为基础的勇气指出:一方面,他自己并没有能够以决定性地明确而确定的方式说明现象学究竟是什么;另一方面,无论是关于现象学作为整体还是关于现象学所涉及的具体主题,都形成了各式各样、甚至互相对立的解释(德布尔,1995年,序言第9页),这个历史的事实亦根源于此。以这个洞察为基础,我们才能把握施皮格伯格的评论作为哲学史任务可能包含的内容和意义。首先,胡塞尔的现象学是在与心理学的密切而紧张的对峙关系中兴起的;就与心理学的关系而言,其中同时包含着否定的成分和肯定的成分。其次,如果说胡塞尔的现象学作为理想或观念尚未得到完全的实现,那么,施皮格伯格的评论便意味着,它的完全的实现将依赖于阐明心理学对它的必然要求,而这又进一步意味着,必须就心理学本身是什么具备明确的洞察和阐释。我们将发现,正是这个工作构成了施皮格伯格的评论作为哲学史任务的核心;也是在这个水平上对胡塞尔思想作为现象学与心理学之间关系的阐明,是理解胡塞尔哲学的全部秘密所在。再次,这个水平上的分析将揭示,正如上述第一个方面涉及的胡塞尔对待心理学的态度已暗示的关于心理学本身是什么,同样是一个尚未实现的理想或观念。因此,从心理学的角度并为了心理学的缘故,借用施皮格伯格的评论并通过关键词的置换,我们可以说,对于理解心理学来说,最重要的必要条件之一是要阐明心理学与胡塞尔的现象学之间的关系。总之,只有通过对现象学与心理学彼此对对方的必然要求的分析,揭示二者之间彼此规定的关系,才能达到对二者的统一理解。
二、若干历史的尝试及其无效性的根本原因
如果不是以施皮格伯格上述评论隐含的哲学史任务为背景,而是局限于心理学的研究,我们立即就联想到,关于心理学与现象学之间的关系,在心理学中已有相当多的研究文献。然而在这种情况下,无论就其中每一个文献进行深入挖掘、还是比较总体性地考察这些文献,其系统的意义是难以把握的;如下文论证将证明的,只有将其放置在由这里突显的哲学史任务所划定的意义坐标中,这些研究工作的系统意义才能显现出来。另一方面,如上文已暗示,在现象学研究的背景中,还没有过自觉而系统地把施皮格伯格的评论作为哲学史任务来执行的尝试;施皮格伯格虽然受到他自己对胡塞尔现象学理解的制约,但毕竟潜在地意识到了这个哲学史任务,所以,我们可以以他在这个方面完成的工作为线索,从正反两个方向上系统地揭示由这个哲学史任务划定的意义坐标,并理解这些文献作为执行这个哲学史任务的历史尝试之无效性的根本原因。
甚至在构思《现象学运动》时,施皮格伯格就意识到,现象学的意义远不限于哲学,所以,“原来的计划本想增加关于现象学对诸如心理学、精神病理学、甚至精神病学,对于数学、自然科学、社会科学、人文科学,最后但并不是最不重要的,对于宗教研究等非哲学研究的影响的全面评述”(施皮格伯格,1995年,第10页)。换言之,现象学的意义广泛地渗透于全部属人的世界,甚至构成后者的基础,起着为后者奠基的逻辑职能。所以,在完成《现象学运动》后,他又以差不多十年的努力,完成了在他自己看来可以算作是《现象学运动》姊妹篇的《心理学和精神病学中的现象学》。如果我们严肃地理解上述哲学史任务,那么,只需粗略地阅读就足以把握到,尽管后一部著作有其相对独立、甚至是重要的意义和价值。但若把它视为对上述哲学史任务的执行,那么,它便使这个哲学史任务的性质发生了根本的改变,甚至使这个任务的重要性降低到可有可无的程度。如施皮格伯格在书中反复强调的,这本书的主导动机是想“尽可能清晰地阐明”现象学作为“一个确定的哲学运动”如何对诸如“心理学这样的研究领域”作为确定的科学门类产生影响并推动其发展(Spiegelberg,1972,p.xxxiii)。简言之,在这本书中,他把现象学和心理学各自作为确定的知识领域来阐明二者之间的关系;如此阐明的这种关系,即使在“阐明”一词的真实意义上是可能的,其性质的基调也必然是外在的。但上文关于施皮格伯格的评论作为哲学史任务及其性质的阐释表明,必须将胡塞尔的现象学和一般意义上而言的心理学各自作为尚未确定的什么,在二者内在的、并因而甚至可能是同一的关系中同时阐明他的现象学和心理学一般,而且,这种阐释工作是要服务于对胡塞尔现象学作为哲学的理解的。总之,必须在与心理学紧密相关而又充满张力的内在关系中感受胡塞尔思想的动向和发展,才能既在肯定的意义上把握胡塞尔现象学的理论指向,又在否定的意义上洞察他在走向现象学的道路上某些步骤的盲目性。事实上,我们知道,一方面,胡塞尔终其一生未能就现象学是什么形成一个含义明确而又系统统一的理论解说,所以一般而言,“虽然我们一再地讨论‘现象学’或使用‘现象学’这个概念,但往往是在一种相当含糊的意义上”(倪梁康,2000年,第4页);另一方面,如果一定要把先验现象学当作胡塞尔哲学的核心或最后目标,那么,正是这个目标“将会把他引向绝路”(施皮格伯格,1995年,第219页)。考虑到这两个方面的事实,如果我们将施皮格伯格的评论作为哲学史任务在严肃的意义上加以执行,我们从一开始就可以预感到,这样的研究工作,相对于胡塞尔关于现象学已经完成的工作而言,必然同时是批判性的;从服务于对胡塞尔现象学的肯定理解而言,这种批判工作将是对胡塞尔开创的事业的继续和推进,而不仅仅是对胡塞尔及其现象学作为历史现象的被动解释。
造成这一切的根本原因在于,在从《现象学运动》到《心理学与精神病学中的现象学》的过渡过程中,施皮格伯格的思想态度发生了一种稍微反思就可以把握到的转变。在前一本书中,他以现象学(运动)为主题展开系统研究的基本结论为:“以上对现象学运动的叙述可能很容易使人们产生这样一种印象,即现象学只不过就是它在各式各样现象学家五花八门和变动不居的思想中表现出来的现象学的历史。这样一种印象甚至包含相当大的真理成分……但是这种情况并不能为回避思想比较严谨的读者一再提出的下面这个问题进行辩解,即:说到底究竟什么是现象学?”虽然他紧接着指出,“既然在我们冗长的叙述中已有充分的理由说明,为什么用一句简短的话不能提供有意义的回答,就更加需要做出确定的努力以满足一种合理的甚至是值得欢迎的要求,即对这个问题加以阐明和澄清”,但事实证明,他回避了对这个提问的直接回答,而是转向方法论的归纳,试图仅从方法的角度来“介绍现象学要点”(施皮格伯格,1995年,第916、918页)。总之,在《现象学运动》一书中,在“说到底究竟什么是现象学”的问题上,施皮格伯格谨慎地保持了一种沉默,不预设胡塞尔已经明确而确定地说明了现象学是什么,得以以开放的态度开展关于现象学(运动)的研究;这个态度意味着,通过共同的努力从不同的角度进一步追求关于现象学究竟是什么的理解,依然是一个悬而未决的哲学史任务。但是,在《心理学与精神病学中的现象学》一书中,或许决定于研究主题的转换,他以一个独断论的并因而盲目的设定为前提,即设定现象学作为一个“确定的哲学运动”,其中当然同时也就隐含地设定了关于现象学是什么的一种“确定的”理解(但我们切不可忘记,这个“确定的”理解尚未达成、甚至应该说是不存在的),并在这个前提下开展关于现象学与心理学之间关系的研究。这个思想态度的转变,同时还影响了关于心理学的理解:如果设定了现象学是一个确定的什么(在这个设定中,在否定的意义上可以说现象学不是心理学),那么,心理学就必然是外在于现象学的另一个并因而也可能是“确定的”什么,如此展开的关于二者关系的研究,即使是可能的,也只能是外在的而且是单向地服务于心理学的实践,而与我们在这里面临的哲学史任务无关。
事实上,在心理学中,特别是在作为人本主义心理学主导趋势和主要表现形式的所谓现象学心理学和存在主义心理学中,类似施皮格伯格《心理学与精神病学中的现象学》的研究成果已经相当丰富且不断增加。例如,早在1958年,罗洛·梅等就编辑出版了《存在:精神病学和心理学中的一个新维度》(May等,1958)。总体而言,这种类型的研究工作,其主导动机是要借助现象学的理论资源在心理学中表达关于心理学的与所谓主流的自然主义心理学不同的另一种声音,而不关心现象学本身。顺便指出,这种努力恰恰证明了心理学尚不是一个“确定了”的什么;与“说到底究竟什么是现象学”一样,我们由此也可以对心理学设问:说到底究竟什么是心理学?也正因此,如科克尔曼斯指出的那样,在这种类型的著作中,作者虽然都会公正地承认,他们关于现象学的观念或理解源起自胡塞尔的原创,但却很少返回或深入到胡塞尔本人的文本之中,而是依赖于关于胡塞尔现象学的第二手、第三手的解释资料,甚至以他们自己的常识感悟为基础(Kockelmans,1967)。但另一方面,就科克尔曼斯自己的工作来说,虽然他确实是尽可能广泛地以对胡塞尔文本的分析为基础,却先入为主地把胡塞尔的“现象学心理学”当作一个确定的心理学学科来理解和论证:“我们的研究工作将首先涉及胡塞尔自己关于现象学心理学的观点。我们将特别关注胡塞尔自己作为一个现象学心理学家的发展。只有这样,我们才能理解现象学心理学的性质和任务,并同时把握它与经验心理学和与先验哲学的关系”(Kockelmans,1967,p.26)。总的来说,他的工作就基调而言属于被动地为胡塞尔辩护的类型,而与这里讨论的哲学史任务无关。
三、由现象学心理学的概念分析引导出的思考方向
众所周知,胡塞尔在弗莱堡大学于1925年夏季学期开设了一门题为“现象学心理学”的讲座课程(Husserl,1977)。单从心理学方面看,这个名称是很迷惑人的:除了展开地细究这个名称将揭示的其可能蕴涵的各种含义和关系外,它首先让人联想到、甚至是期待:它应该是拥有自己独特内容和结构的一门具体的心理学学科。然而,当我们带着这样的预期进入《现象学心理学》文本时,不免产生一种意想不到的困惑或失望:虽然在否定的意义上就其一般态度而言是明确的,即否定当时流行的自然主义的、实验的、生理的、心理-物理的心理学,但在肯定的意义上,无论在“现象学心理学”作为心理学的特殊意义上、还是在心理学作为一门统一的科学学科的一般意义上,这个文本都没有提供一个清晰可见的结构或体系。从前一个方面来看,《现象学心理学》的英译者斯坎农甚至将这种否定性理解为全书思路的统一的主基调:他在指出胡塞尔的讲稿不构成“一部结构严密的著作”、其中并未提供一个“现象学心理学的严密体系”的同时认为,构成该书内容的这些讲稿也并非漫无目的的闲谈,而沿循一种统一的“方向”“主题”或“路线”,这个路线就是“将所有那些为了彻底批判心理学中的物理主义所必需的(前提或条件)逐步展现出来”(Husserl,1977,p.xii.)。从后一个方面来说,如施皮格伯格在参照《纯粹现象学和现象学哲学的观念》一书题名与其主体内容的关系时提议的那样,《现象学心理学》一书更准确的题名应为“……(现象学心理学)的指导性观念”(Guiding Ideas Toward……)(Spiegelberg,1972,p.11)。他的这个提议还进一步暗示着,如果说《纯粹现象学和现象学哲学的观念》一书实际完成的内容,作为对“纯粹现象学”和“现象学哲学”之“观念”的阐明,尚未达到完满、统一的清晰性,二者之间尚有一定的距离,那么,《现象学心理学》实际完成的内容,作为对“现象学心理学”之“观念”的阐明,其清晰性程度更弱,二者之间的距离更远,所以应该题名为现象学心理学的“指导性”观念。当然,对胡塞尔本人来说,《现象学心理学》讲座的目的不单纯是心理学的,甚至应该说主要地不是心理学的,而是要服务于对先验现象学的进一步阐明,所以,一方面,如他自己解释的亦被后人普遍接受的那样,《现象学心理学》同时执行两个功能,即通过对经验心理学基本概念的现象学澄清而为之奠基和作为通向先验现象学的道路之一;另一方面,如无论如何可以设想的那样,必须在胡塞尔思想作为整体及其历史发展的背景中来理解《现象学心理学》的可能意义。总之,决定于胡塞尔思想进程及其未完成性和《现象学心理学》文本就主题和内容而言的不成熟性,关于以《现象学心理学》文本为代表的胡塞尔的心理学思想,可以形成而且事实上也形成了各种不同的解释。
在这里,我们不妨暂时离开《现象学心理学》的文本以摆脱它对我们思想的制约,从而有可能对“现象学心理学”这个名称就其字面含义获得一种更加自由的揭示和理解。由此,我们首先从其构词的形式特征意识到,“现象学心理学”是一个复合词,而不是对一个单一的意义意向的语言表达,其含义或意义决定于它的构成成分:对“现象学”和/或“心理学”分别形成的不同理解,将决定“现象学心理学”的不同含义。换言之,当我们试图理解“现象学心理学”时,其结果将取决于我们既有的思想背景和在其中兴起的理论动机,具体说就在于我们是把“现象学”还是把“心理学”作为理解的意义意向的主体。如果我们把“现象学”作为理解的意义意向主体,那么,“现象学心理学”就可以逐步递进地意味着:(1)以现象学为基础的心理学;(2)现象学作为思想其中蕴含的心理学;(3)现象学作为思想所必然要求的心理学。在这个理解方向上,如果我们没有忘记,胡塞尔终其一生未能明确而确定地阐明现象学是什么,那么,前两个层次的可能含义在系统的意义上必将落空。而第三个层次的可能含义,即“现象学作为思想所必然要求的心理学”,只要我们认真对待,就会引导出完全不同的问题意识和思想空间:姑且不管这种心理学可能是什么,但正因为它是现象学作为思想(及其体系的完成或实现)所必然要求的,所以,这种心理学便构成现象学的题中应有之义;又因此,如果不能在这种意义上将心理学是什么明确地揭示出来,那么现象学便不能得到明确的规定。可以理解,通过这个层次上的追问,心理学与现象学必将达到统一,因为如布伦塔诺已指出的,在原理的水平上,只能有一个心理学,而不能有多个不同的心理学(Brentano,1995,p.xxviii)。
在另一个理解方向上,如果我们立足于心理学,把“心理学”作为我们尝试理解“现象学心理学”这个名称的意义意向的主体,那么,我们所面对的问题和局面,比在上述第一种理解方向上所面对的问题和局面要复杂得多:就历史发生的事实而言,在胡塞尔提出“现象学”或“现象学心理学”的观念之前,心理学已经以胡塞尔称之为自然主义心理学的形式作为一门独立科学获得其存在,并显示了其未来发展的强大生命力。但我们知道,胡塞尔提出并发展现象学及现象学心理学,正是以这种自然主义心理学为对立面、在否定这种心理学的同时试图恢复和重构心理学本身的性质和存在。在这里,在胡塞尔思想发展的起点处,我们就已经可以预感到现象学与肯定地理解的心理学之间必然的和内在的同一性关系;也正因此,我们甚至可以预期,对现象学本身的实现而言,如果胡塞尔思想的发展因不同缘故而失去这种同一性关系的制约,那必将是不幸的和危险的。这也是这里突显施皮格伯格的评论作为哲学史任务的根本意义所在。因此,对胡塞尔来说,心理学不是一个已经实现了的什么;相对于它的自然主义的异化形式而言,心理学作为科学的观念只能是而且必须是“现象学的”,才能实现它自身。类比上文立足于现象学时展开的分析,我们也可以说,暂且不管现象学将如何得到实现,正因为它是心理学作为科学的观念及其实现所必然要求的,所以,现象学便构成心理学的题中应有之义;如果不能将现象学是什么明确地阐释出来,心理学及其作为科学的观念亦不能获得其真理形态的实现。又因此,反过来说,对胡塞尔哲学作为现象学的发展而言,他必须直面心理学是什么的问题并接受由此获得的关于心理学的理解的制约,以统一地阐明现象学是什么;而不像他的思想发展实际经历的那样,一方面受逻辑学思维的主导,另一方面又失去心理学思维的制约(因为在与心理学的若即若离的关系中,他终于未能决定性地阐明心理学是什么),从而走向先验现象学的思想迷宫。
四、现象学与心理学内在同一的必然趋势
因此,对于理解胡塞尔哲学来说,我们切不可受各种误导性因素的影响先入为主地认为,“现象学”在他那里已经完满地实现为某种确定的思想体系,如先验现象学;否则,如关于胡塞尔和他的现象学的学术研究的主流历史证明的那样,我们只能陷入被动地为胡塞尔辩护的有限而非创造性的思想空间。事实上,胡塞尔是历史上最为雄心勃勃的哲学家之一,引导他思想发展的最内在的动机,指向了对全部传统世界结构的根本颠覆,并在颠覆之后的废墟上重构世界的逻辑。只要洞察到这一点,我们就可以理解,一方面,胡塞尔作为哲学家个人以其毕生精力是难以完成如此伟大的“使命”的,由此决定了他的思想的未完成性及其处于流变过程中的历史性质;另一方面,追求他的思想作为“现象学”的完全的实现,乃是我们共同的事业和使命。关于前一个方面,没有人比胡塞尔遗著的编辑者们体会更深刻的了,如《第一哲学》编者鲍姆指出的那样,“特别是《第一哲学》的第二部分,‘体系的’部分的思想进程,具有一种——由其‘体系的’意图引起的——沉思风格,这种风格例如不仅允许而且有时还可能要求,似乎是将这整个思想进程的一个完整部分打断,并在以后——特别是按照后来随之而来的新步骤——赋予它以一种新解释,这种新解释咋看上去只能显示为一种几乎是毁灭性自我批判的外观”(胡塞尔,2006年,第3页)。从后一个方面来说,只有当我们系统地分析与全部已有知识要素的关系后,才有可能明确地规定并阐明现象学是什么;在其中,如布伦塔诺已证明的,心理学突显为一个关键的知识门类,因为只有(有效地实现的)心理学,才普遍被寄予厚望以“更新人类的全部生活,并加速和保障其进步”,而且,“它也必定成为社会及其最高贵成就的基础,并因这个事实也必定成为全部科学事业的基础”(Brentano,1995,p.3)。在这个比较背景中,胡塞尔的现象学,就其一切本质特征而言,与布伦塔诺的心理学是内在地同一的。
当然,我们同样不能假定,心理学在布伦塔诺那里获得了其真理形态的实现。在这里,我们似乎要陷入一种解释学循环的困境:在现象学和心理学各自尚未实现为确定的什么的前提下,如何阐释二者的关系呢?但是,只要真切地置身于这里所说的哲学史任务并感受其中思想的张力,我们就可以洞察这个困境的虚假性,因为我们在这里面临的真实任务,是要在尚未实现的“现象学”和尚未实现的“心理学”彼此对对方必然要求的系统追问中,同时阐明并实现二者。只有以如此理解的这个哲学史任务为背景,我们才能整体把握胡塞尔现象学的本质特征及其发展的是非曲直。
就历史发生的基本事实宏观地看,一方面,胡塞尔现象学无疑兴起于布伦塔诺的心理学;另一方面,作为各种错综复杂关系共同作用的结果,胡塞尔哲学一般地走向了先验现象学。系统分析证明,在先验现象学中,即使采纳布伦塔诺的心理学观念亦必然遭到否定。这就是胡塞尔哲学作为现象学的整体最内在的冲突或矛盾。就与心理学的关系而言,除上述与布伦塔诺的联系外,在先验现象学中,我们可以指出以下三个趋势,并通过对它们的综合比较把握现象学与心理学的关系对胡塞尔思想发展的或引导或误导的作用。其一,且不论先验现象学领域是什么、能否被证成,胡塞尔是必然地经由心理学而“设定”其存在的:“因此,每一个心理经验,经过现象学还原,都有一个纯粹现象与之对应,而纯粹现象则将它的内在本质展现为一个绝对的被给予性”(Husserl,1999,p.34)。但是,在如此“设定”之后,他又否定了与心理学的关系,因为先验现象学研究的“不是人类的认识,而是认识一般”(Husserl,1999,p.34)。因此,其二,在先验现象学中,心理学的性质发生了根本变化而从属于对胡塞尔而言具有先入为主性质的先验现象学,如上文对《现象学心理学》文本的分析揭示的那样。在这个水平上,即使胡塞尔自己关于心理学的讨论,亦不属于这里强调的哲学史任务的范畴,而服务于对先验现象学的论证。其三,综合地比较分析上述趋势就已经可以把握并揭示先验现象学作为思想迷宫的性质;包括海德格尔在内的后继者,主要是在这个意义上反对胡塞尔的。对此,胡塞尔本人更不可能不有所自觉,并尝试突破先验现象学作为思想迷宫的困境,这就是他晚年以“生活世界”“前述谓经验”等主题表达出的向心理学回归的趋势。
对这些问题的进一步阐释需要专门的讨论,限于主题和篇幅,这里不再展开。我们可以参照比梅尔的工作成就提示其一般方向。在胡塞尔遗著的编辑者中,从心理学方面说,比梅尔是最具发言权的。通过对《欧洲科学的危机与超越论的现象学》和《现象学心理学》等文本的编辑整理,他不仅认识到须以胡塞尔思想的整体为背景来理解他的心理学,而且还具体地在前一部著作的导言中指出:一方面,现象学要揭示“心理学本来应该是的东西”并使之成为可理解的;另一方面,只有“从这样理解的生活世界和心理学出发”才能发现“通向现象学的自然的道路”(胡塞尔,2001,第7页),又在后一部著作的导言中以设问的方式提出,“要是基于以上所说,假如现象学心理学是以作为关于意识的描述及先天的科学之面貌出现,那它不就是取代了现象学的位置吗?胡塞尔之关注心理学的问题,从一开始不就表明现象学最终走向心理学?”(胡塞尔,2017年,第11页)在这两部著作中,比较比梅尔的导言和胡塞尔的文本可以发现,在关于现象学和心理学的关系问题上,比梅尔的解释已超出胡塞尔文本的原意,但受《胡塞尔全集》编辑原则的制约,他的解释还是很有节制的。所以,当比梅尔利用独立研究的机会自由地表达他自己的理解时,他更明确地表达了对二者内在同一性的认定。他将胡塞尔现象学观念的兴起甚至追溯到1887年《论数的概念》,并通过详细分析证明,“正是在这里,隐藏着以下事实的起源,即胡塞尔贯穿其学术生涯的一生都把心理学看作是最具根本意义的一门科学……现象学的基本洞察正在于:只有当心理行为通过反思被把握为是意向性的时,某种本质性的东西才能被理解”(Biemel,2005,pp.348-349)。
最后附带指出,比梅尔的工作是独立于这里所说的哲学史任务的。因此,如果我们将他的工作置于这个哲学史任务的背景中来理解,收益是双向的:既显现了他的思考的深刻性,又印证了这个哲学史任务的系统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