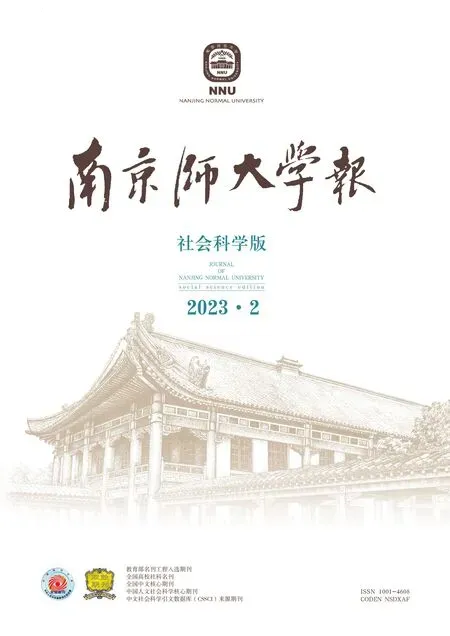论中国儿童文学与现代文学的“一体性”
——兼及新形态“现代文学”的建构问题
2023-09-03朱自强
朱自强
中国儿童文学已有百年的历史。在这一百年的历史中,有一段独特的历史时期,那就是中国新文学发生后的前二十年(1917—1937年),在这二十年里,中国儿童文学与现代(成人)文学呈现出“一体”的状态。这种“一体”的状态,就现象来说,表现为周作人、鲁迅、郭沫若、茅盾、叶绍钧、郑振铎、冰心、张天翼等一大批新文学家同时从事着儿童文学与现代(成人)文学的创构工作;就本质来说,表现为儿童文学与现代(成人)文学具有发生的同时性、“现代性”这一同质性、共同建构一种整体形态的“现代文学”的同构性。
长期以来,在中国现代文学史研究和中国儿童文学史研究领域,中国儿童文学与现代文学具有“一体性”这一研究意识并没有清晰地、广泛地树立起来,因而生产出来的大都是有结构性缺失的研究成果。近年来,随着中国社会的现代化进程的推进,儿童文学研究在相关学术界得到关注甚至重视。儿童文学研究者们也越来越重视儿童文学与相关学科之间的交流、互动。其中,中国儿童文学与现代文学的“一体性”问题的提出及其研究就是一个十分重大的学术动向。对这一“一体性”问题,如果进行严谨的规划和深入的阐释,不仅能拓展中国儿童文学学术版图,而且有可能建构出一个新的中国现代文学的形态。
在本文的题目中,不加引号的现代文学是指迄今为止剥离了儿童文学,只包含成人文学的既成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所建构的现代文学形态,副标题中加了引号的“现代文学”是指通过中国儿童文学与现代(成人)文学的“一体性”研究,使儿童文学与现代(成人)文学实现“同构”之后的新的现代文学形态。本文对中国儿童文学与现代文学的“一体性”所作的研究,指向的不仅是中国儿童文学研究的拓展和深化问题,而且更是新形态的中国“现代文学”的建构问题。
一、“一体化”研究的提出及其问题内涵
在儿童文学领域,最早的中国儿童文学与现代文学具有“一体性”这一研究意识出现在我于2000年出版的《中国儿童文学与现代化进程》一书中。我指出:“世界各国儿童文学发展基本都呈现这样一个大的走势:最初阶段是作为整个文学的一部分而生成、发展,到了成熟以后,便在运行上从一般文学中分离出来,成为独立操作的文学门类。中国儿童文学在五四时期,便是作为新文学的有机组成部分而出现的。”(1)朱自强:《中国儿童文学与现代化进程》,杭州:浙江少年儿童出版社,2000年,第150页。“……五四时期的新文学是包括儿童文学在内的。在五四新文学的整体中,儿童文学是有机组成部分。甚至可以这样说,最能显示五四新文学的‘新’质的,也许当推‘儿童’的发现和‘儿童的文学’的发现。”(2)朱自强:《中国儿童文学与现代化进程》,第153—154页。在该书中,我提出并实践的是“打通”这一研究方式:“如果我们将‘自扫门前雪’的现代文学研究和儿童文学研究打通起来,一方面研究儿童文学时将其放在现代文学的整体格局中进行,一方面,研究现代文学时,将儿童文学也收入视野之中,那么,无论是儿童文学研究还是现代文学研究,都会出现新的研究领域,产生新的理论发现。”(3)朱自强:《中国儿童文学与现代化进程》,第154—155页。
在2013年发表的《论新文学运动中的儿童文学》中,我进一步深化了对中国儿童文学与现代文学的“一体性”的认识:“作为中国现代文学的有机组成部分的儿童文学,不是现代文学的‘量’的增加,而是‘质’的生成。‘儿童’和儿童文学的被发现,不仅给中国现代文学这一‘人的文学’以具体的内容,而且强化了它的现代性质地,提高了它的现代性价值。”(4)朱自强:《论新文学运动中的儿童文学》,《上海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3年第4期。
2012年10月,山东师范大学中国现当代文学学科主办的“现代中国文学史编写”高层论坛在济南召开,我受邀在会议上作了题为“论儿童文学与中国现代文学的一体性”的发言。这是我第一次发表关于“一体性”研究的观点。我在正式出版物上明确提出“儿童文学与中国现代文学一体化”这一观念是在2015年。我在《“三十”自述——兼及体验的当代儿童文学学术史》一文中说:“我对儿童文学与中国现代文学的一体化问题的思考由来已久。写作《中国儿童文学与现代化进程》时,就已经具有把现代儿童文学放入现代文学的整体格局中加以把握的研究意识。……2010年以来,我所做的儿童文学与中国现代文学一体化研究,其实是对《中国儿童文学与现代化进程》所开启的研究的一个接续。”(5)朱自强:《朱自强学术文集》(第1卷),南昌:二十一世纪出版社集团,2016年,第50—51页。文中列举了自2010年起的四年间,我发表的“一体性”研究的数篇论文。(6)《“儿童的发现”:周氏兄弟思想与文学的现代性》(《中国文学研究》2010年第1期);《“儿童”:鲁迅文学的艺术方法》(《东北师大学报》2010年第1期);《“儿童的发现”:周作人的“人的文学”的思想源头》(《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13年第10期);《论新文学运动中的儿童文学》。
2019年,《文艺报》发表了吴翔宇的《百年中国儿童文学发展的“整体性”思维论纲》(7)吴翔宇:《百年中国儿童文学发展的“整体性”思维论纲》,《文艺报》2019年2月15日,第5版。一文。尽管吴翔宇的文章中没有出现“一体化”这一字样,但是栏目主持人李利芳指出:“本期推出的吴翔宇一文聚焦我国儿童文学与现代中国文学的‘一体化’整合研究理路,有力地打破了长期以来禁锢我国儿童文学发展的学科壁垒,对于两个学科积极的双向汇入均有非常重要的价值。”2020年,吴翔宇发表《边界、跨域与融通——中国儿童文学与现代文学“一体化”的发生学考察》一文,(8)吴翔宇:《边界、跨域与融通 ——中国儿童文学与现代文学“一体化”的发生学考察》,《文学评论》2020年第1期。如论文的副标题所示,“中国儿童文学与现代文学‘一体化’”这一问题是该论文论述的核心。
吴翔宇说:“中国儿童文学与现代文学的一体化研究的理论前提是系统把握两者各自发生发展的演变历程。”(9)吴翔宇:《边界、跨域与融通 ——中国儿童文学与现代文学“一体化”的发生学考察》。作为方法论,他强调的是“两者各自发生发展”。吴翔宇这篇论文的副标题是“中国儿童文学与现代文学‘一体化’的发生学考察”。但是,当我也对“中国儿童文学与现代文学‘一体化’”作“发生学考察”时,我在新文学发生以及其后20年间的历史中,所看到的两者却既不是“边界、跨域”这一关系,更不是“各自发生发展”的关系,而是两者融合为“一体”来发展的同构关系。
虽然我和吴翔宇先后用了“儿童文学与中国现代文学的一体化”“中国儿童文学与现代文学‘一体化’”这种相同的表述,但是,我所谓的“一体化”与吴翔宇所谓的“一体化”,是两种性质不同、方法亦不同的研究。
我与吴翔宇对中国儿童文学与现代文学的“一体化”所作的不同理解和阐释,蕴含着以下三个重大的学术问题:(1)中国儿童文学与现代文学的“一体化”是仅限于1917年以后20年间的现代文学时期,还是贯穿于五四至今的百年文学史(包含1949年以后的当代文学史)?(2)中国儿童文学与现代文学的“一体化”研究是“系统把握两者各自发生发展的演变历程”,即进行“异”的研究,还是将“儿童文学的运行和生产,都归属于整个文学的结构之中”(10)朱自强:《论新文学运动中的儿童文学》。,即进行“同”的研究?(3)在“一体化”中,中国儿童文学与现代文学两者之间是“边界、跨域与融通”(吴翔宇论文的题目)这种关系,还是一种“同构”关系,即两者共同构成了一个此前学术研究所盲视的、处于更高阶位的、新的“现代文学”形态?
对上述三个重大学术问题的回应,构成了本文的以下论述。
二、“一体性”:同时性、同质性、同构性
从现在开始,我将用“一体性”取代“一体化”这一表述。我认为“一体性”是比“一体化”更准确、更有效的一个学术概念。“一体化”有“改变”“变异”进而成为“一体”之意,而“一体性”则表示“分化”之前的当初就具有“一体性”这一性质。从“现代文学”史的事实来看,在1917—1937年间,儿童文学与现代文学是处于“未分化”的一种状态,具有“一体性”。
中国儿童文学与现代文学的这种“一体性”包含着以下三个性质。
(一)同时性
中国儿童文学与现代文学的“一体性”研究,属于文学史研究这一范畴。中国儿童文学史研究,存在着中国儿童文学“古已有之”和中国儿童文学是“现代”文学这两种截然对立的观点。这两种不同的观点,标示出对于中国儿童文学的发生时间的不同划分。我本人就是中国儿童文学是“现代”文学这一观点的最早提出者。(11)参见朱自强:《中国儿童文学与现代化进程》。关于中国儿童文学发生的“起点”,与中国儿童文学“古已有之”论者以具体作品的出现来判断“起点”这一方法不同,我是借鉴福柯的“知识考古学”,采用考察“儿童文学”这一观念在何时发生这一研究方法。正是因为采用这一研究方法,中国儿童文学与现代文学发生的“同时性”出现于我的学术视野。
在近些年的中国现代文学史研究中,关于现代文学的“起点”研究,在时间上从“五四”向民初、向晚清越推越早。比如,郜元宝“倾向于将现代的上限定在1907年左右”,因为“此时的鲁迅创作的一系列才气焕发的论文”,“宣告了中国现代文学观念的喷薄而出”。(12)郜元宝:《尚未完成的“现代”———也谈中国现当代文学的分期》,《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1年第 3 期。而孔范今则又把“起点”往前推了十几年——“我认为,以19世纪90年代前期刊行的韩邦庆的《海上花列传》为其起点标志是比较符合实际的。”(13)孔范今:《论中国文学的现代转型与文学史重构》,《文学评论》2003年第4期。持同一观点的还有范伯群,他说:“我在《〈海上花列传〉:现代通俗小说开山之作》一文中提出,中国文学从古典型转轨为现代型的起点标志是1892年开始连载、1894年正式出版的《海上花列传》。”(14)范伯群:《论中国现代文学史起点的“向前移”问题》,《江苏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6年第5期。严家炎则以1890年陈季同的《黄衫客传奇》(英文版)的出版,作为标示“起点”的重要考量。(15)严家炎:《中国现代文学的“起点”问题》,《文学评论》2014年第2期。
我不同意上述关于现代文学“起点”的观点。从方法论的角度来看,上述观点都有以局部代替整体、以要素代替性质之缺陷。我将现代文学的“起点”置于1917年、1918年这两年间。因为只有在这两年间,蕴含着“语言革命”和“思想革命”的现代文学形态才得以确立。所谓现代文学形态,用胡适的话说,就是“我们的中心理论只有两个,一个是我们要建立一种‘活的文学’,一个是我们要建立一种‘人的文学’,前一个理论是文字工具的革新,后一种是文学内容的革新。中国新文学运动的一切理论都可以包括在这两个中心思想的里面。”(16)胡适:《〈中国新文学大系·建设理论集〉导言》,《中国新文学大系·建设理论集》,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03年,第18页。
以活的白话代替死的文言,这一现代文学的语言变革主张,是由胡适于1917年在《文学改良刍议》一文中提出来的(17)胡适:《文学改良刍议》,《新青年》1917年第2卷第5期。,而仅仅一年后的1918年,周作人就发表《安德森的〈十之九〉》,批判陈家麟、陈家镫翻译安徒生童话《打火匣》时,把“小儿的言语,变了大家的古文”,(18)周作人:《安德森的〈十之九〉》,《新青年》1918年第5卷第3号。第一个指出了在儿童文学中,文言表现与儿童的生活水火不能相容。
胡适指出的新文学运动的另一个“中心思想”——“人的文学”,当然指的就是周作人在《人的文学》(1918年)一文中提出的新文学(现代文学)理念。在《人的文学》一文中,“儿童的发现”构成了周作人的“人的文学”的思想源头(19)具体论述见朱自强:《“儿童的发现”:周作人的“人的文学”的思想源头》,《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13年第10期。,而就在1920年,“发现儿童”的周作人发表的《儿童的文学》,宣告了“儿童文学”这一观念的诞生。
由上述事实可见,中国儿童文学与现代文学的观念发生具有同时性。
(二)同质性
吴翔宇在论述中国儿童文学与现代文学的“一体化”时说:“显然,这种关系的重构并非基于历史推进而做的文学史内容的添补,而是围绕着两种文学的边界、跨域与互通而展开的关系研究。”(20)吴翔宇:《边界、跨域与融通 ——中国儿童文学与现代文学“一体化”的发生学考察》。对于“一体性”研究来说,儿童文学与现代(成人)文学并不是如吴翔宇所说的,是有着不同的“边界”,需要“跨域”的“两种文学”,而就是一种文学——现代文学。中国儿童文学与现代文学的“一体性”研究的立论前提,不是“把握两者各自发生发展的演变历程”,而是确认中国儿童文学与现代文学的“同质性”。
在“一体性”问题的研究上,将儿童文学与现代(成人)文学看成是有着不同的“边界”,需要“跨域”的“两种文学”,是缺乏历史的现场感的一种判断。如果回到历史的现场就可以看到,在儿童文学与现代(成人)文学“未分化”的“一体性”时期,当时的文学家们并没有将儿童文学与现代(成人)文学当作“两种文学”。我们可以看一些历史上的实例。
孔罗荪写于1935年的《关于儿童读物》一文,是把儿童文学视为“新文化运动”的产物的——“过去的作品,可以说也只有叶绍钧先生的《稻草人》和张天翼先生的《大林和小林》可以说是新文化运动以来,关于童话的两个时期中的杰作了。”(21)孔罗荪:《关于儿童读物》,王泉根评选:《中国现代儿童文学文论选》,桂林:广西人民出版社,1989年,第297页。
1935年,郁达夫编《中国新文学大系·散文二集》,他特别青睐于冰心的散文,收入集中的篇数多达22篇(仅次于周氏兄弟),而其中写给儿童的散文《寄小读者》的篇什,就占了三分之一。郁达夫在《导言》中是这样评价冰心及其散文创作的:“冰心女士散文的清丽,文字的典雅,思想的纯洁,在中国好算是独一无二的作家了……”“我以为读了冰心女士的作品,就能够了解中国一切历史上的才女的心情;意在言外,文必己出,哀而不伤,动中法度,是女士的生平,亦即是女士的文章之极致。”(22)郁达夫:《导言》,郁达夫编:《中国新文学大系·散文二集》(影印本),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03年,第16页。我相信,郁达夫在写下上述话语时,心里完全没有将儿童文学的《寄小读者》与冰心的其他写给成人的散文加以区别,当成“两种文学”这种意识。
胡风在1936年还在将儿童文学与新文学同一而视。他有一篇文章的题目是“关于儿童文学”,可是在论述儿童文学的《稻草人》时,他却是这样说的:“五四运动以后不久出现的《稻草人》,不但在叶氏个人,对于当时整个新文学运动也应该是一部有意义的作品。”(23)胡风:《关于儿童文学》,王泉根评选:《中国现代儿童文学文论选》,第155页。胡风表露出的是明晰的“一体性”认知。
再拿当时新文学的重要发表和传播的阵地《新青年》和《小说月报》这两份杂志来说,两者尽可能地发表了大量儿童文学创作、翻译、研究的成果,这与现今将儿童文学与成人文学看作“两种文学”的杂志截然不同。
对于中国儿童文学史研究而言,儿童文学与现代(成人)文学具有“同质性”(都是“现代”文学)这一认知非常重要,因为我们已经看到了缺乏这一认知而导致中国儿童文学史研究中的概念的混乱和阐释失当这一现象。
因为认定具有现代性质的儿童文学没有古代形态,所以,我从未采用过“现代的儿童文学”“中国儿童文学的现代发生”这一类说法。因为这样的说法暗含着还有“古代的儿童文学”和“中国儿童文学的古代发生”这一意思。但是,吴翔宇由于把“一体性”研究的理论前提置于中国儿童文学与现代文学的“各自发生发展的演变历程”之上,置于“两种文学”之上,而不是置于两者是“同质”的现代文学之上,因此,在中国儿童文学是不是“古已有之”这一问题上的立场就是暧昧甚至摇摆的了。比如,吴翔宇说:“在经历了中国古代漫长的‘自在状态’后,中国儿童文学的现代发生、发展起步于‘五四’时期。”(24)吴翔宇:《百年中国儿童文学跨学科拓展的依据、路径与反思》,《学术月刊》2020年第7期。这段引文中,“经历了中国古代漫长的‘自在状态’”的主语是“中国儿童文学”,也就是说,吴翔宇认为中国儿童文学拥有“古代漫长的‘自在状态’”。这种儿童文学史观与否定中国儿童文学的“现代”性质的“古已有之”论,不过是五十步与百步的区别。
(三)同构性
如果说,中国儿童文学与现代文学的“同时性”“同质性”这两个问题基本属于对事实或事物属性进行判断的问题,那么“同构性”则既有对中国儿童文学与现代文学的关系的判断,又涉及需要进行实践的一种动态的学术建构行为。
本文提出的“同构”,是借鉴自视觉美学的“同构现象”这一概念。视觉美学的所谓“同构”,指的是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图形不是单摆浮搁地拼合在一起,而是共同建构出一个全新的图形。也就是说“同构”是一种具有超越性、创造性的再生过程。
简明扼要地说,中国儿童文学与现代文学所具有的“同构性”里的“同构”,不是名词,不是指两者有相同的结构,而是动词,是指两者共同建构了一个新的“现代文学”形态。
不必讳言,以往的中国儿童文学史研究和中国现代文学史研究,鲜有“同构性”这一研究意识和学术操作,因而,各自所建构的大都是结构单一的或者是结构不完整的文学史形态。我们举例来讨论。
钱理群等学者所著《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中的鲁迅小说研究具有诸多创新性阐释,可是,如果怀着中国儿童文学与现代文学“一体性”这一研究意识看去,就能发现其研究存在着重要的缺失。该书中有这样的论述:“正是从这样的‘启蒙主义’的文学观念出发,鲁迅开创了‘表现农民与知识分子’两大现代文学的主要题材。”(25)钱理群、温儒敏、吴福辉:《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第39页。说鲁迅的小说秉持的是“‘启蒙主义’的文学观念”无疑是正确的,不过,鲁迅的“启蒙主义”小说所开创的现代题材,却不只是“农民”与“知识分子”,而是还有“儿童”(“童年”)。而且,就现代文学关于“人”的启蒙这一母题而言,“儿童的发现”无疑更具有“开创”性,具有更高的思想和艺术价值。鲁迅之前的数千年的中国文学史,即使有的叙事性作品写到了“儿童”,其形象也是被动的、缺乏主体性的,只有到了鲁迅这里,才出现了崭新的、能动的、具有主体性的“儿童”艺术形象。如果抽掉鲁迅的文学世界中的“儿童”“童年”,鲁迅文学将在很大程度上失去现有的现代性思想和艺术的高度。在我看来,鲁迅投入新文学的创造,其最根本的动力是出自“救救孩子”的愿望和努力。
因为缺失了“儿童”“童年”这一“同构”中的一维,《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中的鲁迅小说研究,不仅对《故乡》《孔乙己》的阐释与作品本身存在着隔膜,而且对《社戏》这一具有全新美学风格的小说只提篇名却只字未论。
但是,也有重视鲁迅小说的“童年”书写的学者。李长之于1935年写作《鲁迅批判》,就将《社戏》归入自己选出的“有永久的价值”“在任何国外的大作家之群里,也可以毫无愧色”的八篇小说之中。他不仅大段加以评论,而且这样评价:“像《孔乙己》,《风波》,《阿Q正传》,《离婚》之写农民一样,像《故乡》,《祝福》,《伤逝》之写伤感一样,《社戏》之写轻巧,松散的童心,同样是不朽的。”(26)李长之:《鲁迅批判(增订本)》,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21年,第66页。李长之的这种研究就具有我所讨论的“同构性”研究的性质。
胡丰(即胡风)在20世纪30年代所著《张天翼论》中,对张天翼的研究也是将成人小说和儿童文学放在一起来研究,进而产生出一定“同构性”的著述。
胡风在指出张天翼的小说创作中的人物简单化的毛病时说:“当然作者的目的是想简明地有效地向读者传达他所估定了的一种社会相理,但他却忘记了,矛盾万端流动不息的社会生活付与个人的生命决不是那么单纯的事情。艺术家底工作是在社会生活底河流里发现出本质的共性,创造出血液温暖的人物来在能够活动的限度下面自由活动,给以批判或鼓舞,他没有权柄勉强他们替他自己的观念做‘傀儡’”。(27)胡丰(胡风):《张天翼论》,沈承宽等:《张天翼研究资料》,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年,第279页。胡风同时又指出:“他的熟悉儿童心理和善于捕捉口语,使他在儿童文学里而注入了一脉新流,但我们还等待他去掉不健康的诙谑和一般的观念,着眼在具体的生活样相上面,创造一些实味浓厚的作品……”(28)胡丰(胡风):《张天翼论》,第295页。在胡风这里,张天翼的“不健康的诙谑和一般的观念”,是由成人文学和儿童文学两者共同显示出来的。其实,如果再将《大林和小林》,特别是《秃秃大王》《金鸭帝国》这样的作品也一道拿来进行“同构性”研究,张天翼文学的特质将会更加丰富而醒目地呈现出来。
中国儿童文学与现代文学“一体性”的“同构性”研究,既可以是针对作家创作个体,也可以是针对作家创作群体,还可以是针对特定一段文学史的整体。
有创作个体的“同构”研究。鲁迅的《怀旧》《故乡》《社戏》《孔乙己》等小说以及《朝花夕拾》《野草》中的一些散文,虽然并不是作为儿童文学来创作的,但是儿童文学的研究视角却能为相关研究带来“同构性”。对周作人、郭沫若、叶绍钧、冰心、茅盾(沈德鸿)、张天翼等作家,都需要进行“同构”研究。对这些研究对象,如果不作“同构”研究,仅仅凭单一的儿童文学视角或单一的成人文学视角,都难以获得贴切、深入、全面的阐释。
有创作群体的“同构”研究。比如,研究“文学研究会”,就不能将文学研究会所推动的“儿童文学运动”排除在外。我在《现代儿童文学文论解说》一书中曾指出,叶绍钧的童话集《稻草人》所表现的“成人的悲哀”,郑振铎评论《稻草人》时,对“未免过于重视儿童”这一立场的质疑,都是对他们两位此前持有的“儿童本位”立场作出的重要修正。这是中国原创儿童文学初创期的一个颇为重要、颇具暗示性的事情。叶绍钧和郑振铎的转变,仅从儿童文学自身这里是难以找到原因的。我认为,“叶圣陶和郑振铎的这种转变,都与文学研究会的成立有关。他们两人均为文学研究会的发起人,而且又是主张‘为人生’的写实主义(现实主义)的茅盾的好友。”(29)朱自强:《现代儿童文学文论解说》,北京:海豚出版社,2014年,第197页。
当我们针对一个个创作个体,一个个创作群体的“同构性”研究做到位之后,就自然会形成对特定一段文学史的整体的“同构”研究。这样的“同构”研究,指向的就是“现代文学”新形态的建构,会生成规模更大、内涵更丰富、结构更复杂的“现代文学”的一段历史,进而描绘出中国现代文学史的新的面貌。
在现有的中国现代文学史著作中,虽然十分罕见,但已经出现了具有“同构性”的学术研究。
魏建、吕周聚主编的《中国现代文学新编》一书,专列出“儿童文学”一节,以近万字的篇幅讨论“现代文学第一个十年”里,“与整个新文学融为一体”的儿童文学。“五四时期的新文学是包括儿童文学在内的,在五四新文学的整体中,儿童文学是有机组成部分。……如果没有‘儿童’的发现和‘儿童的文学’的发现,五四新文学的新质将大打折扣。”“成就周作人的儿童文学理论的是五四新文化、新文学运动。”“《新青年》作为新文化、新文学的大本营和策源地,理所当然地在发现‘儿童’、儿童文学的过程中发挥着最为重要的启蒙作用。”“中国现代文学的第一个十年的儿童文学作为一场运动,它有风潮性、群体性的特征。在‘儿童文学运动’中,文学研究会发挥了极为核心、极为重要的作用”。(30)魏建、吕周聚主编:《中国现代文学新编》,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12年,第82—86页。书中的这些论述,都直接呈现出“现代文学第一个十年”里,儿童文学与现代文学“同构”出的“现代文学”的整体面貌。
朱晓进等学者著《作为语言艺术的中国现代文学发展史》明确指出:“‘儿童文学’这一文学样式的产生,是中国现代文学发生中的一个重要内容。”(31)朱晓进等:《作为语言艺术的中国现代文学发展史》,北京:人民出版社,2015年,第18页。该著作是将“儿童文学”与“新诗”“现代小说”“现代散文”“话剧”并列为“现代文学文体”之一加以研究的。应该说,该著作从语言艺术这一重要的研究维度,已经在一定程度上呈现出了一种新的“现代文学”史的形态。
但是,也不能不指出,反倒是儿童文学学者的“一体性”研究出现了错误阐释。吴翔宇曾反复表述,儿童文学对于成人文学是“依赖”的、“附属”的、“被动性”“融入”的这种关系(32)吴翔宇主编:《百年中国儿童文学史》,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22年,第6—8页。。吴翔宇所阐释的上述关系,在儿童文学与现代文学的“一体性”时期,是找不到文学史的事实作依据的。
三、“一体性”研究的方法论问题
方法是自觉、是方向、是效率。中国儿童文学与现代文学“一体性”是一个特殊而范围很大的学术研究对象,对其进行研究需要建构方法论,这样才能保证研究的可靠性和深入性。我根据自己的研究体验以及对研究对象的分析,提出“一体性”研究的以下三个方法。
(一)以“现代性”为价值尺度
在学理上,研究中国儿童文学和现代文学的“一体性”要以“现代性”为价值尺度,这几乎是一个不言而喻的问题,但是,如果看具体的研究实践,还真不能说这是已经解决得很好的一个问题。
以“现代性”为价值尺度,才能作出中国儿童文学与现代文学是同时发生、具有相同性质这样的考察,进而得出两者具有“一体性”这一结论。只有以“现代性”为价值尺度,才能将包括了儿童文学和现代(成人)文学在内的中国“现代文学”置于文学史上的正确位置,并对其“一体性”作出合理的阐释。一方面,如果放弃“现代性”这一价值尺度,可能导致中国儿童文学“古已有之”这种观点的成立,而持着“古已有之”论,中国儿童文学必然与现代文学发生“分离”;另一方面,如果对“现代性”的标准定位不准,对现代文学的“起点”研究也会摇摆不定、进退失据,如此一来,也必然造成现代文学与儿童文学的分离。
儿童文学思想具有自身的主体性,它本身就是“现代性”思想资源的十分重要的组成部分。如果对五四时期的“现代性”思想内涵有切实的了解和正确的理解,就不会出现儿童文学要“依赖”“成人文学”的“思想资源”(33)吴翔宇主编:《百年中国儿童文学史》,第8页。这种观点。事实是,周作人在《人的文学》一文中建构“人的文学”这一现代文学理念时,在汲取“妇女的发现”这一妇女解放思想的同时,也汲取了“儿童的发现”这一儿童文学的思想资源。因此,儿童文学要依赖“成人文学”的“思想资源”这一观点,是对现代性思想的错误阐释。
在此,我想稍稍将问题延伸一下。自20世纪末以来,学术界经常出现依据激进的后现代理论来质疑甚至否定五四新文化运动、新文学运动这种观点。近些年,中国儿童文学学术界也有否定五四新文学运动的反启蒙立场。针对否定“五四”启蒙思想的那些观点,有学者从不同的面向作出了反驳和批判,不过,如果在“现代性”价值尺度下进行中国儿童文学与现代文学“一体性”研究,就会在五四新文化运动、新文学运动的“重审”和批判这一问题上获得更加有力的理据——不管五四新文化运动、新文学运动存在着怎样的历史局限,但是仅凭其对“儿童的发现”和对“儿童文学的发现”,就可以有力地回击否定五四新文化运动、新文学运动的思想风潮。卡尔·波普尔曾说:“我确定孩子们是最大的贫苦阶级”,(34)[英]卡尔·波普尔:《二十世纪的教训》,王凌霄译,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12年,第64页。所以我坚信,一种关爱和解放儿童、造福于儿童的新文化运动、新文学运动,其思想的质地是不会错的,是值得信赖的。与此相联系,那些将新文学的“起点”不断地往晚清推移的学者们,只要他们不能证明晚清已有完整的儿童文学观念的发生,那么,其主张可能也是颇为可疑的。
总之,就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中国儿童文学研究而言,依然可以借用哈贝马斯的话说,“现代性”还是“一项未竟的事业”。
(二)进行“同”的研究而不是进行“异”的研究
中国儿童文学与现代(成人)文学“一体性”研究是“同”的研究,而不是“异”的研究。
“一体性”是个历史的概念,有它特指的、有效的时间范围,而不能把所谓的“百年”中国文学史都划进来。具体来说,“一体性”时期是指1917年至大约1937年这段时期。在这段时期里,儿童文学与现代(成人)文学是一体的,处于尚未分化的状态。周氏兄弟、郭沫若、茅盾、叶绍钧等新文学作家和研究者都是同时进行着儿童文学与现代(成人)文学的创构工作,只是到了1937年前后,儿童文学才开始逐渐从整体的“现代文学”中分化出来,出现了严文井、陈伯吹、贺宜、金近等近于“专职”的儿童文学家。
如果回到历史的现场,考察“一体性”时期的儿童文学观念,就会看到人们是不将儿童文学与现代(成人)文学区别对待,即不进行“异”的研究的。那时,儿童文学并没有作为一个学科而独立存在。20世纪20至30年代的几种《儿童文学概论》《儿童文学研究》都没有将儿童文学与成人文学相区别这一研究意识。比如,魏寿镛、周侯予的《儿童文学概论》所画的图示里,是将“儿童文学”放在整体的“文学”之中,而并未在“儿童文学”的对面区分一个“成人文学”出来。(35)魏寿镛、周侯予:《儿童文学概论》,王泉根编:《民国时期的儿童文学研究》,太原:希望出版社,2020年,第11页。张圣瑜所编《儿童文学研究》明确说道:“儿童文学之领域,即文学领域之一部也。”(36)张圣瑜:《儿童文学研究》,王泉根编:《民国时期的儿童文学研究》,第202页。
中国儿童文学与现代(成人)文学“一体性”研究是“同”的研究,而不是“异”的研究,还有学术逻辑的依据。
毫无疑问,在当今的研究者看来,儿童文学与成人文学,既具有相同性,也具有差异性。但是,中国儿童文学与现代(成人)文学“一体性”研究是文学史的研究,而不是文艺学的研究。文学史研究和文艺学研究是两个不同的学术维度,这决定了两者不同的学术进入的角度和区域。对1917年至大约1937年这段“一体性”时期所作的文学史研究,要处理的是中国儿童文学与现代(成人)文学的同时性、同质性、同构性问题,而对儿童文学与成人文学存在的差异问题并不需要进行学术处理。转换到另一维度,当我们从文艺学维度进入儿童文学与成人文学的关系研究时,我们就要处理两者之间的差异性这一问题了。儿童文学从整体的“现代文学”分化以后,学科开始独立,儿童文学与成人文学的“差异”性研究就成为儿童文学的理论课题。就我本人来说,我发表的第3篇儿童文学研究的论文题目就是《论儿童文学与成人文学的差异》(37)朱自强:《论儿童文学与成人文学的差异》,《东北师大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7年第4期。。
儿童文学与现代文学的“一体性”研究的指向“同”而不研究“异”,与文艺学研究的指向“异”(当然也会研究“同”),两者并不互相否定。举例来说,如果我们要在鱼、鸡、鸭、鹅之中找出一个异类,你说鱼是异类是对的,但你说鸡是异类也是对的。说鱼是异类,是因为它不能像鸡、鸭、鹅一样在岸上生活;说鸡是异类,是因为它不会像鱼、鸭、鹅那样在水里游泳。两个不同答案是出于不同的逻辑维度,两者并不互相否定。
儿童文学与现代(成人)文学之间有差异,就像男人与女人之间有差异一样,虽然男人与女人有差异,但是,他们作为人是一体的。反对种族主义时,是将黑人男性和黑人女性作为一体的,需要进行“同”的处理;而反对性别歧视时,则又要将黑人男性与黑人女性区别开来,需要进行“异”的处理。同理,在特定时期的文学史研究中,讨论儿童文学与现代(成人)文学的“一体性”问题,没有必要考虑两者之间的差异。所以,吴翔宇的“边界、跨界”这种研究意识,非但是无效的方法论,反而会造成对“一体性”的消解。
“一体性”研究的逻辑维度在“同”而不在“异”。在“一体性”历史时期里,儿童文学与现代(成人)文学同是“现代文学”。鲁迅文学的“童年”题材与知识分子题材、农民题材是“同”而不是“异”,它们同是现代题材,共同构成了鲁迅的小说艺术世界。周作人的现代文学理念中,“人的发现”包含着成人(男子和妇女)的发现和“儿童的发现”,但是在“人的发现”这一现代性维度,成人与儿童是“同”而不是“异”,成人的发现与“儿童的发现”共同构成了“人的发现”的现代性内涵。在“一体性”研究中,“童年”题材与知识分子题材,“儿童的发现”与妇女的发现即使存在差异,也是同中之异。有如伽利略研究自由落体运动时不把空气阻力这一因素考虑在内一样,“一体性”研究也是不需要考虑儿童文学与现代(成人)文学之间的差异的。
我感到,吴翔宇之所以将中国儿童文学与现代(成人)文学“一体性”研究的理论前提设定为研究“两者各自发生发展的演变历程”即指向“异”的研究,这一方面是出于研究维度上的逻辑错乱,另一方面则是由于他的缺乏历史感的“后知后觉”这种研究意识。如前所述,在中国儿童文学发生之初的1920年代,在历史的现场,儿童文学与现代(成人)文学并没有构成“边界、跨域”这种“异”的关系。出现儿童文学与成人文学两个学科间的差异性研究,这是儿童文学从整体的“现代文学”中分化出来,学科独立之后的事情。所以,我们今天的研究者不能拿着儿童文学学科独立后所产生的儿童文学与成人文学存在差异性这一观念,去处理“一体性”时期的儿童文学与现代(成人)文学的关系。在文学史研究中,王德威式“后知后觉”的操作方式是需要警惕的,它很可能造成对文学史中的事实的扭曲。
(三)“谛视”性阐释方法
我所说的“谛视”,不仅有辞典上的仔细看之义,而且有透过现象,看到研究对象的本质之义。“谛视”的谛,是真谛的谛。“谛视”性研究强调的是思想、理论上的创造性阐释。“谛视”性研究指向的是阐释的深刻性和创造性。
虽然学术研究都需要进行“谛视”性阐释,不过对于中国儿童文学与现代文学的“一体性”研究来说,“谛视”性阐释需要特别予以重视和强调。
“一体性”研究属于文学史研究,因此在历史中发现现象、事实的研究也非常重要。比如,对《新青年》《小说月报》中的“儿童文学”内容的发现,对周作人、鲁迅、郭沫若、茅盾、叶绍钧、冰心等作家的儿童文学创构工作的发现,对文学研究会推动的“儿童文学运动”的发现,都是重要的“一体性”研究工作。不过,当这些现象和事实被发现以后,进一步的学术深化的工作,就需要“谛视”性阐释来完成了。
本文在前面论述过中国儿童文学与现代文学“一体性”所内含的同时性、同质性和同构性,作出这些发现就需要进行“谛视”性阐释。这里再举一个作家研究的事例来说明什么是“谛视”性研究。冰心的《寄小读者》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重要作品。如果我们对这部写给儿童的散文集作“谛视”性研究,可以做的一个思考是,为什么留学美国的冰心的硕士论文研究的不是给郭沫若的《女神》以深刻影响的,“把一切的旧套摆脱干净了”(38)郭沫若评惠特曼诗风语。参见张大明、陈学超、李葆琰:《中国现代文学思潮史》(上册),北京: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1995年,第302页。的美国现代诗人惠特曼的诗作,而是写下了《论李清照的词》。如果我们对《寄小读者》作进一步的“谛视”,又会发现《寄小读者》中的确有很多李清照词作中的“寻寻觅觅,冷冷清清,凄凄惨惨戚戚”和“只恐双溪舴艋舟,载不动许多愁”的意境。它们让人想起夏志清对冰心的评语:“冰心代表的是中国文学里的感伤传统。即使文学革命没有发生,她仍然会成为一个颇为重要的诗人和散文作家。但在旧的传统下,她可能会更有成就,更为多产。”(39)夏志清:《中国现代小说史》,刘绍铭等译,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53页。于此,我们就可以从冰心的儿童文学创作这里,看到她作为新文学作家的一种局限,从而丰富和深化对这位作家的认识。
最后,我想进一步强调,本文所论中国儿童文学与现代(成人)文学的“一体性”研究,最终的学术工作是使儿童文学与现代(成人)文学融合在一起,进而产生“同构”这一具有创造性的建构功能。这样的“一体性”研究所要达到的学术目标是在中国儿童文学与现代(成人)文学的“一体性”时期(1917—1937年),建构出一个处于更高阶位的、结构上更为丰富完整的“现代文学”新形态。这样的创新性学术工作,对于有志从事“一体性”研究工作的学者都提出了知识拓展和知识升级的学术挑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