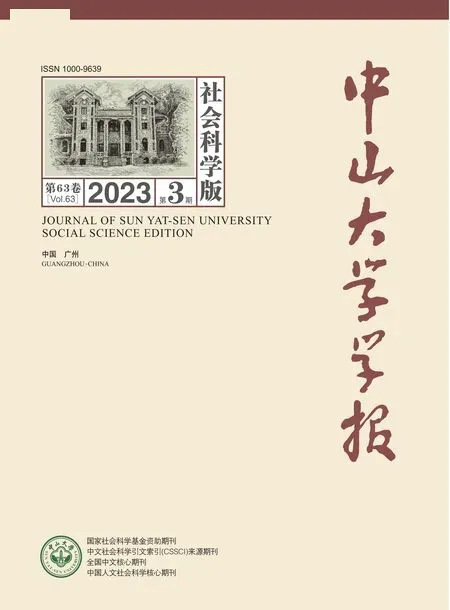明前期广西编户人口流失的根源与后果 *
2023-09-03任建敏
任建敏
自何炳棣对明初以降人口进行的开创性研究之后,学界对明代户口数字的性质有了更为深入的理解。何炳棣认为洪武年间的人口统计“无论就其条令规则还是实际效果而言,都相当接近现代人口调查”,具有“较高的价值”①何炳棣:《明初以降人口及其相关问题:1368—1953》,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0年,第3—4页。。当然,洪武年间的人口数字也并不十分完善,曹树基指出:洪武时期的户口数字只统计了民籍系统,未包括卫所人口,也不包括明朝境内外的少数民族部落。即使是民籍人口的统计,也常常有忽略女性人口的现象②曹树基:《中国人口史》第4卷《明时期》,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0年,第55页。。
地处西南一隅、“民夷杂处”的广西,属于何炳棣所认为的人口漏报最严重的“边远地区”。现存文献中明初广西各府以下的户口、编里数字,已经严重残缺,对研究者认识明代广西的编户系统的形成与变化带来了很大的困难。此外,明代两广地区动乱频繁,造成了大量编户人口的流失。本文以广西柳州府马平县为中心,兼及广西东部地区相关州县的类似情况,探讨明初广西编户人口的实质内涵及明前期广西编户人口流失的根源与后果。
一、洪武年间广西“蛮獠”人群的入籍与脱籍
元明更替之后,广西户数的增长,很大程度上应该归因于周边的“蛮獠”人群的归附入籍。如洪武年间,南宁府宣化县“外有如和、太平、思龙三乡,接连万承、菓化、归德嵠峒,民撞乌杂,愚昧无知。自归附以来,渐以效顺,输纳赋税”。武缘县则“外有近拨管属述昆乡大小安定里人民,其性凶险,原系蛮獠,不知理法,不伏科差。自洪武四年以来,才方向化,止是输税而已”①《南宁府志》,马蓉等:《永乐大典方志辑佚》第5册,北京:中华书局,2004年,第2945页。。
洪武十四年(1381)正月,明朝“命天下郡县编赋役黄册”②《明太祖实录》卷135,洪武十四年正月之末条,台北:“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62年,第2143页。。这是明朝第一次大造黄册。同年八月,南雄侯赵庸“平阳春县蛮寇,奏捷京师”,明太祖发出了“岭南民人入籍既久,屡叛屡征”的感叹③《明太祖实录》卷138,洪武十四年八月乙丑条,第2180页。。可见,在洪武十四年前,广西地区就已经将大量“岭南民人”纳入户籍之下,但没有解决“屡叛屡征”的难题。
地处广西中部的柳州,位于土流分界线的东侧④苏建灵:《明清时期壮族历史研究》,南宁:广西民族出版社,1993年,第120页。,“猺、獞、狑、犽、㺜、狼、[犭氷]、獠诸丑类,偕汉民错杂而居者,十居七八”⑤乾隆《柳州府志》,《故宫珍本丛刊》第197册,海口:海南出版社,2000年,第1页。。洪武十八年(1385),为应对不时“窃发”的动乱,柳州府马平县主簿孔性善给明太祖进言柳州的“溪洞猺獞”问题:
溪洞猺獞,恃险窃发,杀掠吏民。及官军讨捕,则退入深谷。操强弓,注毒矢,潜守隘口,卒不能获。凶顽自恣,为患益深。乞于贼人出没之地,立寨置兵,扼其襟喉,断其出路,譬犹穴中之鼠,技穷食尽,可以尽剿。然此虽盗贼,岂无良心?昔者陈景文为知县时,猺獞皆应差役,厥后长吏抚字乖方,始复反侧。诚使守令得人,示以恩信,谕以祸福,彼虽凶顽,岂不革心向化为良民乎?⑥《明太祖实录》卷172,洪武十八年四月丙辰条,第2633—2634页。
孔性善进言所提到的“昔者陈景文为知县”时的情况,非常值得注意。按陈景文,雍正《广西通志》称其为广东海康人,洪武初任马平县知县⑦雍正《广西通志》卷56《秩官》,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图书馆藏清刻本,第19页。。乾隆《马平县志》则称其为元仁宗皇庆年间的马平县尹⑧乾隆《马平县志》卷6《官制》,国家图书馆藏清刻本,第5页。。比较而言,前者似更可靠。一是因为孔性善提到陈景文时称其为“知县”,而不是用元朝的“县尹”。且孔性善对陈景文任职期间的政绩与情况颇为熟悉,时间应该相距不远。明初这些“应差役”的瑶僮人口在洪武十四年第一次编定黄册时,是否纳入马平县的编里之内,因史料有阙,难以确考。不过,洪武末至建文初年任桂林府学教授的陈琏曾提到:“皇明统一寰宇,教化盛行,椎髻卉服之人皆变为冠裳,穷发不毛之地率隶于编户。又宿重兵以临之,选循吏以牧之,虽古称难治者,今莫不革心向化,奔走服役。”⑨宣德《桂林郡志》卷20《南蛮》,《国家图书馆藏地方志珍本丛刊》第755册,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2016年,第76页。陈琏任职的桂林,与柳州府相邻,其所见所闻,应该比较真切。因此,在洪武一朝,广西应该有大量“椎髻卉服之人”是“隶于编户”的。
正如孔性善所注意到的,由于“长吏抚字乖方”的缘故,早在洪武十八年,不少原本“应差役”的瑶僮人口“复反侧”。这必然导致洪武十四年编造黄册时登记的瑶僮人口再次脱离了国家的掌控范围。“复反侧”带来了两个直接后果,其一是地方社会的治安与秩序将会受到冲击与破坏,其二是洪武十四年编立黄册所确定下来赋役负担难以足额完纳与应差。乾隆《柳州府志》回顾明初历史时,将其描述为:“民田皆没于獞,县官拥空籍而已。”⑩乾隆《柳州府志》卷30《猺獞》,《故宫珍本丛刊》第197册,第245页。这一句话,前半句把民田的减少归咎于僮人占据,但显然也有一种情况是,明初的“民”,成为了后来的僮;而后半句,则道出了在籍户口与田地的流失,导致官府手头据以征收赋役的黄册成为了有名无实的“空籍”。
二、编户剧减的解释:永乐年间广西动乱之说
由于史料所阙,明初广西的编户情况只有零星记载存世。现存《永乐大典》尚有明初南宁府、梧州府、郁林州的相关编户人口的记载,但柳州府所在的“柳”字韵今已不存,殊为可惜。明初柳州府的户口数,最早文献见于嘉靖《广西通志》所载洪武二十四年(1391)35,963户、231,926口①嘉靖《广西通志》卷18《户口》,美国哈佛燕京图书馆藏明刻本,第3页。。
以柳州府首县马平县为例,在当地人的历史记忆中,明初马平县有过大量编户因战乱而锐减的黑暗历史。这段历史,在明中叶马平县当地人的回顾中屡屡被提及,而且都指向了以梁公竦为首的“獞寇”作乱与总兵韩观征剿之事。
现存有关记载,最早出现在弘治六年(1493)南京户部员外郎、柳州马平人周琦所上《条陈地方利病疏》:
如永乐年间马平县五都贼人梁公竦等作乱,胁从者不过七八百人,攻劫本县水南街等处,都督韩观乘以征进交趾退回兵力,将本县地方通六都,每都三里,共一十八里,不分善恶,一扫而平。遗下残民,止得六里,因致民地空虚,无人居住,乡村田土俱系獞侵。至今延蔓数多,百姓日渐消磨,逼依城廓,并今六里亦无。②嘉靖《广西通志》卷56《外志七》,第12页。
周琦认为,梁公竦为首的“贼人”与胁从者一共不过七八百人。而永乐年间韩观以征剿梁公竦为理由,率大军把马平县的里民“不分善恶,一扫而平”,导致民地空虚,田土最后被僮人所侵占。到了周琦所处的时代,连六里之额都达不到了。
此外,正德二年(1507)广西布政司左参政王臣所作《平蛮碑》,借当时柳州知府刘琏之口,更详细地说明了马平县编里减少的过程:
于是,柳州知府刘琏进而述父老之词谓:马平在国初本十有八里,永乐三年③永乐三年:嘉靖《广西通志》本作“永乐十三年”。,獞寇起,有韩总兵者,督兵捕之,而芜其田,乃为庆远宜山、河池之獞所夺,遂并十八里而为七。宣德三年,有山总兵者,调兵剿之,而反为寇所袭,置④置:嘉靖《广西通志》本作“移”。横罗、归安堡以守御之。景泰初元,群寇蠭起,聚至万余,围柳州城几陷,贼势益炽,遂并七里而仅存一里之半。⑤雍正《广西通志》卷105《艺文》,第10页。又参嘉靖《广西通志》卷56《外志七》,第16页。
王臣转述的“父老之词”,和周琦的说法可以互相印证,但是细节有所不同。首先,王臣之说提到韩观“芜其田”的对象是马平县本地的“獞寇”,后来因为这些本地“獞寇”被韩观剿杀后,其田地被“庆远宜山、河池之獞”所夺,才使马平县18里并为7里。由此反推,王臣之说中的本地“獞寇”本来也是属于马平18 里编户之中。其次,王臣提到宣德三年(1428)总兵山云调兵进剿不胜,遂设置了横罗、归安等堡防守。按照明代广西设置兵堡的惯例,设堡的同时,往往要设置一定数量的堡田作为堡军的衣食之资。再次,景泰元年(1450)“群寇”围柳州城,导致的后果是马平县的7个编里仅存1.5里。
另外,正德年间湖广衡州府知府、马平人计宗道曾作《上当道乞减马平县余田加征状》,也讲述了类似的故事:
马平王田经元兵燹后,多猺獞所据,民存如晨星落落。国朝洪武间,贼势日炽,朝廷命都督韩公观捕剿之,玉石俱焚,地旷田荒。至永乐二十年,拉其残民,仅七里,较之前代,已亡十之八九。⑥嘉靖《广西通志》卷19《田赋》,第12页。
计宗道之说与周琦、王臣之说又略有不同。其中韩观进剿的时间被提前到了洪武年间,而马平县合并为7里的时间则为永乐二十年(1422)。
比较周琦、王臣、计宗道三人的说法,相互印证,但略有出入。计宗道明确提到他的数据来源于“版籍”,他关于明初马平县编里数量的说法应该比较准确,即洪武十四年马平县编里数为17里。至于王臣提到的永乐三年(1405)的18 里,一种可能是在洪武十四年至永乐三年间,马平县新立了一个编里。另一种可能是来源于马平县的都里划分习惯。据乾隆《柳州府志》,清代马平县的村落有在厢与在乡之分,在厢共25村,在乡则分六都,“每都分上中下三里,每里村落多寡不等”①乾隆《柳州府志》卷6《村墟》,《故宫珍本丛刊》第197册,第51页。。按此计算,六都一共为18里,与周琦、王臣之说相合。这其实是将作为乡村区域范围的“都里”与作为赋役单位的“编里”混淆的结果。
永乐以后马平县的编里数变化,以王臣的记载时间线索最为清晰。王臣提到,永乐三年时18 里并为7里,到景泰元年进一步合并为1.5里。这与计宗道的“今则里半”之说吻合。不过,嘉靖《广西通志》载马平县编户数字仍为7 里②嘉靖《广西通志》卷1《图经》,第9页。。与王臣之说相合,比周琦之说多1 里。这其中的矛盾很好解释,7 里之数,应该是在厢算1里,六都各算1里。所以王臣计算的是马平县的总里数,而周琦计算的是除了在厢之外的六个里。由上看来,在景泰元年进一步归并编里后,原来的以在厢加上六都各算一里的组成的马平县7里数字,在地方志书等官方文献中长期不变。只是在实际的赋役运作时,进一步按照1.5里进行编排。这种册籍上的编里数与实际运作的编里数之差别,在其他地区也有出现。如《皇明制书》中,广西平乐府修仁县“编户半里”③张卤:《皇明制书》卷19《大明官制》,《续修四库全书》第788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第703页。。而嘉靖《广西通志》中修仁县“编户二里”④嘉靖《广西通志》卷1《图经》,第16页。。
总而言之,综合以上不同来源的说法,永乐年间马平县编里的大幅度归并确是事实。要讨论永乐年间马平县编里流失的根源,应该先弄清楚梁公竦之乱的实质。据《明太宗实录》记载,永乐元年(1403)五月:
柳州等府、上林等县獞民梁公竦等六千户,凡男女三万三千余口,及罗城县上酉韦公成乾等三百余户复业。初韦公等作耗,獞民多亡入山谷,与之相结。事闻,遣御史王煜等招抚复业,至是俱至,仍隶籍为民。⑤《明太宗实录》卷20上,永乐元年五月丁亥条,台北:“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62年,第363—364页。
该记载提到了“獞民梁公竦”,就是周琦、刘琏所称的永乐初马平动乱的“贼首”,从实录的记载来看,以梁公竦为首的六千户“獞民”是在永乐元年五月复业,“仍隶籍为民”。由“仍”与“复业”来看,这些“獞民”原本已经入籍,只是因“韦公等作耗”而脱籍,但在永乐元年五月之后,他们再次重新登记为民籍。六千户并非一个小数目。与洪武二十四年柳州府的户口数比较,仅梁公竦等六千户“獞民”,就占了洪武二十四年柳州府造册户数的16.7%、口数的14.2%。这进一步可以印证,马平县所宣称“国初”的十八里,有相当一部分出自这六千户“獞民”。
在《明太宗实录》相关记载中,永乐元年梁公竦归附后,再未见其“作乱”的记载。但永乐五年(1407)确实有一场以柳州为中心的征讨“诸蛮”的行动。综合实录相关记载,其大致过程如下:永乐五年二月,明成祖给广西总兵韩观下了一道敕谕,要求其“于交阯缘途各堡措置毕”后征讨作乱的“柳浔二州诸蛮”⑥《明太宗实录》卷64,永乐五年二月庚寅条,第910页。。至是年六月,韩观上奏称:“蒙敕兵(按,兵字疑为衍字)移兵剿捕柳州等处蛮寇。今年四月初一日,兵至柳州,贼闻风遁入窠穴,难剿除。请俟秋冬益进兵讨。”朝廷采纳了韩观的建议,同时派人前往“湖广、广东、贵州三都司选壮士三万同锦衣卫指挥程远,期以十月初一日至广西,与观军合攻之”①《明太宗实录》卷68,永乐五年六月壬辰条,第957—958页。。此外,还降敕交阯总兵官、新城侯张辅,提到“交阯已平,惟广西柳浔等州叛寇未灭。班师则预报都督韩观,克期合兵剿之”,要求“必殄灭此寇,毋遗民患”②《明太宗实录》卷68,永乐五年六月乙未条,第959页。。可见,永乐五年十月初一日的征剿行动,是由明廷统一部署,由广西总兵韩观所率征进交阯回师大军,加上锦衣卫指挥程远所率湖广、广东、贵州三都司所调三万人协同参加的军事行动③按:湖广等三都司所选军士之数字,《明太宗实录》卷68各条有三万、二万两种说法,除上条外,六月乙未条敕张辅文作三万,六月戊戌敕程远条作二万。今从三万之说。。此役可以说是明成祖在征进交阯大局已定的情况下,通盘考虑解决广西“蛮寇”作乱的一次大征。实录载,两路大军从十月初一日动兵,二十七日奏捷,用时不超过一个月,且范围十分广泛,以柳州为中心,遍及庆远、浔州等处的十余个州县。其战功之和,斩首加擒获也只是两三万人的规模④《明太宗实录》卷72,永乐五年十月丁未条,第1011页。。以此规模计算,马平县即便是征剿重点,韩观所率大军停留在马平县的时间大概不会超过半个月,斩获占比也应该不超过四分之一。因此,韩观大军不太可能在短短半个月的时间就将马平县的编户“不分善恶,一扫而平”。当然,这场征剿对广西地方而言,仍然是极为惨酷的。明军在平定动乱时杀戮过当之举并不少见⑤《明太祖实录》卷244,洪武二十九年正月癸卯条,第3548页。。无怪乎在数十年以后,马平县当地人回顾这段历史的时候,仍然心有余悸地将里甲残破的原因归于韩观的征剿。
综合实录与周琦等人的相关叙述来看,明初马平县的所谓18 里编户,相当一部分是梁公竦这样在永乐元年归附的“獞民”。在里甲身份登记层面而言,大量归附的僮与民一样,同属马平县的编户。所以永乐五年韩观出征剿杀梁公竦等“隶籍为民”的僮,当然会导致马平县编里的减少。在后世看来,这种以征剿“蛮寇”为名的军事行动,自然就是“善恶不分”。
这场征剿结束之后,马平县的里甲系统无疑受到了较大的打击,但其影响却是逐渐显现的。永乐年间曾有三次大造黄册的记录,分别是永乐元年、十年、二十年⑥韦庆远:《明代黄册制度》,北京:中华书局,1961年,第98页。。计宗道提到的“至永乐二十年,拉其残民,仅七里”,恰好是造册之年。也就是说,即便在永乐五年的征剿结束后,永乐十年造册时也没有一下子将马平县编里合并为七里,而是要等到永乐二十年才归并。只是自永乐五年到永乐二十年这15年的时间里,马平县的编户一直在逐渐流失。因此,永乐五年韩观的征剿,只是一个开端。正如乾隆《柳州府志》回顾这段历史所言:
永乐间五都獞梁公竦等作乱,都督韩观剿擒斩首万余级,民多逃亡,存者数十户耳。沃壤荒芜,往往募獞人耕种。獞日繁而剽掠滋甚。宣德四年,公竦余党复抅洛容诸蛮出劫,指挥王纶纵兵剿之,良民多被屠戮。⑦乾隆《柳州府志》卷30《猺獞》,《故宫珍本丛刊》第197册,第245页。
韩观征剿行动结束后,除了大量“蛮寇”被杀被擒,还有大量原本就与僮关系密切的“民”也大量“逃亡”。其结果则是马平县的大量土地“往往募獞人耕种”。“民”是否真的“逃亡”了,不能一概而论,因为永乐元年的18里的编民中,有相当大部分就是僮。所谓“民”逃而僮存,不过是归附之僮脱离了里甲系统,重新成为了无籍之僮。
此外,经过永乐年间的编里调整,马平县有大量区域不再属于官府直接管辖。如万历《宾州志》引“吴邦柱氏旧志载”《宾州永图歌》称:“八寨原为八所屯,年深事改增奸府。三都旧是马平民,国初此地俱编户。”①万历《宾州志》卷14《杂志》,《日本藏中国罕见地方志丛刊》第3册,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0年,第154页。按万历《宾州志》卷8《选举》记载,吴邦柱为上林县人,嘉靖时贡生,曾任保昌教谕。此处“三都”,指的应该是马平县三都,而非宾州三都。如该志提到,十寨(在八寨基础上增加了龙哈、咘咳二寨)“其地东连柳州三都、皂岭、北四诸峒”②万历《宾州志》卷11《经略》,第110页。。马平三都是明代柳州地区重要的“动乱”源头。直到清雍正年间,三都地区仍然“逃避正赋,在迁江既非管辖,而马平又无额征。几致三都地方不归州县管束”③金鉷:《定三都告示》,雍正《广西通志》卷119《艺文》,第21页。。由上可见,马平县三都之民在明初时曾隶编户,而其脱离编户的时间,应该就在马平县编里大规模合并的永乐年间。可以说,永乐二十年马平县7里体制的确立,使得马平县的民和僮的分界线才比较固定下来。仍然留在里甲系统的7里,获得了编户的身份,被视为“民”。而被排除在7里之外的,才是僮。但从宣德四年(1429)指挥王纶以剿捕“公竦余党”为由屠戮“良民”的行为来看,“良民”与僮二者的身份依然是具有弹性的。
除马平县,在明前期桂东地区还有不少州县同样有里甲大量流失的情况。如桂林府荔浦县④弘治四年(1491),桂林府荔浦、修仁二县改属平乐府。,当地志书记载了一个名为周文昌的“荔浦甘棠寨编民”,自洪武中至永乐中“大肆劫掠十有余年,被杀者十有五六”。至永乐六年(1408)“查勘绝杀人户”时,原编17里只存8里,永乐九年时进一步减少到5里,自此“居民鲜少,田地荒芜。遂往柳庆招募民垦佃”。笔者既有研究已指出,洪武四年(1371)荔浦县的乡里村数,不仅包括了元代至正年间的“居民”,也包含了大量“猺獠”。周文昌之乱,不过是当地社会刻意强调的理由,用来解释荔浦县编里在永乐年间急剧下降的原因。实质仍然是使明初形式上登记在里甲之内的僮人脱离了编户系统的结果⑤任建敏:《明中前期两广瑶僮地区招主控制体系的形成与扩散》,《中央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1年第1期。。
马平、荔浦二县里甲残破的原因非常相似,时间都在洪武中到永乐中之间,只是杀伐的主角从韩观变成了周文昌。荔浦的记载也同样宣称大乱之后,当地社会招募了柳庆的僮人来耕种荒芜的田地。
以上二县以地方动乱为理由来解释洪武、永乐间编里大量减少之说,在南岭一带并非孤例。如广西桂林府灌阳县,据弘治年间该县正二保老人文世㫤的奏疏提到,该县原额42 里,洪武二十八年(1395)“猺民作乱,调军征剿,遗下残民招抚,并作十四里”⑥康熙《灌阳县志》卷3《赋役》,国家图书馆藏抄本,第3页。。而在天顺年间成书的《大明一统志》载,灌阳县编里进一步降至8里⑦李贤:《大明一统志》卷83《桂林府》,西安:三秦出版社,1990年,第1266页。。又如湖南郴州宜章县,康熙《宜章县志》记载:“旧志称古额四十九里……仅存八里及三堡屯田。其故何也?盖以明洪武初蓝山杜回子等煽乱,大兵征剿,玉石不分,遂致土旷人稀,什亡大半。”原编户的大量土地“为招募堡屯田,属郴州军”⑧康熙《宜章县志》卷2《乡都》,《国家图书馆藏地方志珍本丛刊》第664 册,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2016 年,第219页。。谢晓辉也提到湖南辰州府麻阳县,明洪武十四年编有39里,10年后降为24里,至永乐年间仅存7里⑨谢晓辉:《制造边缘性:10—19世纪的湘西》,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20年,第74页。。
可见,明初在两广、湖南等地州县,在洪武末至永乐中已呈现了大量里甲残破、编户流失的现象。各地地方文献对这种现象的解释与叙述模式,都归结于地方动乱以及明军平乱所导致的“玉石不分”。不过,编户的流失并不一定意味着人口绝对值的减少。在马平县与荔浦县,填补编户位置的,是据称来自柳庆地区的僮人。而灌阳县、宜章县、麻阳县则由当地的卫所屯军填补。
综上而言,在明初完成了里甲登记之后不久,以马平、荔浦为代表的广西州县就因为各种动乱的原因导致编户大量流失,作为赋役计量单位的编里也相应减少,登记耕地也因而下降。如嘉靖《广西通志》记载,洪武二十四年柳州府有3.5 万户、23 万口,这一数字是明代柳州府户口的顶峰。该志又称柳州府的户口“自永乐至天顺俱无考”,成化至嘉靖元年的户口数虽略有变化,但都在2 万户、12 万口左右变动①嘉靖《广西通志》卷18《户口》,第3页。。相对洪武二十四年的数字减少大约一半。
三、卫所、豪民与瑶僮:编户流失与“余田”的形成
上述广西编里流失的例子,其作乱的源头不一,但往往指向明朝军队的介入而导致地方上大量编户人口流失。其结果是附着于编户人口的赋税与差役的征收都没有了着落。体现在官府的管理层面,则是归并残破里甲,减少州县相应的赋役总额。虽然赋役总额减少了,但“抛荒”的田地仍在,这就给后来填补相关编户流失的“移入者”带来了赋役负担减少的契机。
在这些编户流失的州县中,后来的“移入者”主要分为两类,一类是被称为瑶僮的非汉人群,另一类则是卫所的屯军。这两类人群虽然在很多场合中是征剿与被征剿的敌对关系,但其实往往有千丝万缕的联系。明代广西也因此形成了以“招主”为代表的代理人体系②有关西南民族地区代理人的研究意义,参见温春来:《西南的代理人与王朝秩序的展开》,《原生态民族文化学刊》2022年第3期。。再以马平县为例,计宗道提到:
田之美者,民取出庸,次者拨作屯田,又其次者皆野峒深山,草木交结,城郭远甚,民所不敢蹑,付诸猺獞耕者,名曰余田也。田虽余,粮则仍在。正统间管屯田佥事王受分田为上中下三等,广募猺獞佃之,然不能必其足数,任其所出,民为代输督粮者,请兵深入催征,犹不能绝其侵渔,及致骚扰。景泰元年,激其围城,连攻七日,束书于矢射入城中,曰:“官给田我耕,本以安我,而追征严重,所以致此。”虽托朝廷威福,幸城不陷,而四境之内,已被其残破矣。于是掌户部事太保金(琏)[濂]议之减田租之半,俯就夷情。自是以来,催科者率以为常例。③嘉靖《广西通志》卷19《田赋》,第12页。
计宗道是明初马平县都博镇土巡检计仲政的后代④张江华:《传说、风水与一个多民族宗族的生成 柳州“计氏豢龙传”故事的演化及社会过程》,《社会》2022 年第3期。,因此其立场,不仅是关心桑梓情况的士大夫,也一定程度上反映了马平地方豪强的利益。计宗道指出:“田之美者”,由民耕种,并且交纳赋税和承担差役(出庸);次等田地,由卫所占据,拨为屯田;再次等的田地,则位于“野峒深山”之中,成为“余田”,余田的性质是“田虽余,粮则仍在”。可见,计宗道所述之上等或次等,不是指田土本身的肥瘠,而是指税则的高低。这三种田地的产生,可以与洪武、永乐间编户流失的历史背景联系起来。同样是田地,由里甲户耕种并承担赋役的,就是“田之美者”。由卫所屯军耕种,交纳子粒的,就是屯田。而“付诸猺獞耕”并由“民为代输督粮”的,则是余田。
如前所述,耕种余田的瑶僮,其实是有相当一部分是纳入洪武年间的户籍登记体系之内的。但经过永乐年间韩观的征剿,马平县大量户籍登记人口流失。官府自然也不会承认没有户籍身份的瑶僮对相关耕种土地的所有权。编户流失造成的“无主”田地,就成为了“余田”。可见,余田其实就是明初登记到马平县赋役体系内的田地,只是到了马平编里归并之后,这些田地就藉此机会摆脱赋役负担,成为了“余田”,但在官府的登记中这些田地原编粮额还在,只是很难征收(相应的差役自然也无从落实)。官府对“粮则仍在”的余田,只能交给以“招”的名义钤束瑶僮的招主“代输督粮”①参见任建敏:《明中前期两广瑶僮地区招主控制体系的形成与扩散》,《中央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1年第1期;《招僮防瑶与以“狼”制僮:明中叶桂东北的社会结构与族群关系》,《中央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5期。。实际耕种余田者,仍然是原来“皆应差役”的瑶僮。只是他们在脱离里甲系统后成为了控制余田之“民”的佃户,不再为地方官府所直接掌控。
计宗道还提到,正统年间屯田佥事王受对这一田地控制模式进行了调整。王受于正统八年(1443)被任命为广西等地按察司佥事,专督屯田②《明英宗实录》卷110,正统八年十一月己卯条,台北:“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62年,第2227页。。在王受就任之前,正统六年广西提学佥事黄润玉亦曾针对瑶僮与屯军的问题进行了讨论。黄润玉发现,广西屯田往往被“官旗军豪”以“荒田”为名占种,或被屯军盗卖。而广西的两种“土蛮”之中,“獞人”自己“力田足食”,部分还为官府当差服役。而“猺人”则“少田缺食”。因此,黄润玉建议“招致猺人下田往种”,一方面可以使“猺人”不再“穷扰乡村”,另一方面也使屯田数量得以增加。黄润玉的方案,是要把“荒田”变成“屯田”,把“猺人”变为屯军的佃户③黄润玉:《南山黄先生家传集》卷53《广西事宜》,爱如生历代别集库收录明蓝格抄本。毛亦可指出,明代屯田以宣德十年至正统二年“诏免正粮上仓”为界,分为领种制与租佃制两个阶段。在这个意义上,本文所讨论的瑶僮,可以视为屯田租佃制下的特殊“佃户”。毛亦可:《论明清屯田的私有化历程》,《中国经济史研究》2017年第2期。。而王受的方案,是用卫所屯田的名义,招募瑶僮为卫所耕种。黄润玉的建议与计宗道提到的王受方案在理念上十分相近,都是要通过招募瑶僮耕种“荒田”来增加屯田。但在实际操作过程中,卫所仍然要依赖作为“招主”的豪民“代输督粮”。由此形成了以瑶僮耕作“余田”,以卫所作为武力保证进行“催征”,以“民”收取瑶僮田租代为输赋于官的格局。
马平县余田的赋役征收与屯田、民田有何分别,因史料所限,已难细考。乾隆《马平县志》载,万历年间“官民田地塘”税赋的简单平均值为3.59升/亩④乾隆《马平县志》卷4《赋役》,第2页。。至于屯田,按正德《明会典》,正统元年(1436)后,朝廷规定“各处屯种,每军止征余粮六石”,以一军授田50亩来计算,其税则为12升/亩⑤实际上广西因为山多田少,每军平均领种屯田数字肯定达不到50 亩。王毓铨指出,南方诸卫所,军屯分地亩数一般在十二亩到三十二亩之间。见王毓铨:《明代的军屯》,北京:中华书局,1965年,第72页。。正统八年(1443)朝廷再下令:“屯田有自开垦荒地,每亩岁纳粮五升三合五勺。”⑥正德《大明会典》卷19《户部四》,东京:汲古书院,1989年,第239页。可以说,以上是正统年间明朝官方确定的军屯正余田的一般税则。但是,各地在实际执行过程中,会有所出入,如康熙《灌阳县志》所载明代灌阳县屯田粮的税则,正田大致在18—20 升/亩,余田大致在6—9 升/亩⑦康熙《灌阳县志》卷3《赋役》,第7—9页。。康熙《平乐县志》载,平乐县原额屯余田的税则大致为11.4升/亩⑧康熙《平乐县志》卷4《屯余》,《故宫珍本丛刊》第199册,海口:海南出版社,2001年,第130页。。比较而言,灌阳、平乐屯田的正余田的税则比正统年间定例略高,估计马平县余田的税则也不会差别太大。对比民田与屯田的税则,民田的税则只有余田的大约1/2,正田的大约1/4。但这只是赋税的比较,更大的差异在于,仍然登记在籍的民田,除了赋税外,还需要承担各种差役。而在里甲残破后作为“荒田”存在的余田,则摆脱了各项杂泛差役的义务。大量民田转变为了余田的情况表明,户籍人口的里甲正役负担加上附着于民田的杂泛差役负担要远高于余田与民田间的赋税差额。正如梁方仲所指出,明代里甲的负担,很早就已超出催征钱粮和勾摄公事的力役范围之外⑨梁方仲:《论明代里甲法和均徭法的关系》,载梁方仲著,刘志伟编:《梁方仲文集》,广州:中山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237页。。至于余田的规模与数额,马平县当地官府在很长的时间里根本无法掌握。如乾隆《柳州府志》提到:“柳州卫屯余田原无税亩升科,不征本折粮米,止纳编银。该米六百六十六石七斗五升八合,每石编银一钱八分,共银一百二十两零一分六厘零。”①乾隆《柳州府志》卷7《田赋》,《故宫珍本丛刊》第197册,第72,71页。若按照6升/亩的税率计算,大约可以折合111顷左右,而万历清丈后的马平县田地总数也不过1,080顷②乾隆《柳州府志》卷7《田赋》,《故宫珍本丛刊》第197册,第72,71页。。
计宗道指出,“余田”的赋税问题是激发马平频繁动乱的根本原因,景泰年间饱受卫所与招主侵渔的瑶僮就曾因此围城七日,反抗官府的“追征严重”。朝廷为安抚才下令“减田租之半”。此事在《明英宗实录》也有所记载,但只是用“良民数少,猺獞数多……欲乞俯就夷情”来一笔带过朝廷批准蠲免“獞民”税粮的原因,回避了瑶僮围城的危机③《明英宗实录》卷194,景泰元年七月己巳条,第4103页。。不过,由于耕种屯地的瑶僮并非官府登记册中的土地主人,其税粮需要招主代为交纳。正如计宗道所言:“大抵广西土田于猺獞代耕,非如中土皆百姓自为也。”减半征收的受益者,很大程度上还是像马平计氏这样控制瑶僮佃耕余田的豪强。计宗道抗议当时马平官府不依据景泰时的税则,而依正统旧册征税,更大程度上是为豪强争取减免赋税,只是理由就变成了防止瑶僮反抗作乱。
总之,景泰元年瑶僮围城之举还是实现了其诉求。朝廷不仅暂停征收“屡年拖欠税粮”,同时对“獞民屯耕田地”实行了“减半征收”。值得注意的是,同样在景泰元年,广西总兵官武毅上奏,经户部尚书金濂覆议,朝廷“准该省地方被官军剿戮遗下田亩,行令当地土民召人佃种。其召到流獞人等佃,令田主钤束,但纠合出劫者连坐”④张学颜:《万历会计录》卷12《广西布政司田赋·沿革事例》,《续修四库全书》第831册,第790页。。这一道“钤束”之令,大概就是因应瑶僮围城之事而要求“田主”对“流獞人等佃”加强控制。
由上可见,在广西的编户人口因为各种“动乱”而逐渐流失的同时,瑶僮与卫所的势力则在逐渐扩张。不过,卫所招募瑶僮所耕之余田,并不计算入卫所的屯田之数中。《万历会计录》有一则事例非常值得注意:“本年以广西各县田地开设屯所,拨官军屯种自食,不纳税粮。马平县拨田粮二千一十余石与皂岭屯。来宾县……迁江县……共拨田粮五千四百二十余石给各屯官军把守地方。”⑤张学颜:《万历会计录》卷38《屯田·沿革事例》,《续修四库全书》第833册,第89页。从该则上下文的时间来推断,这批数额巨大的田产,应该是在永乐五年韩观“玉石不分”的征剿对当地编户人口带来的巨大流失后才拨给卫所屯军的。马平、来宾、迁江等县这些拨给官军屯种的土地,很可能就是由原编户耕种的民田转变为瑶僮耕种的余田⑥王毓铨很早就注意到这类屯田与普通军屯的区别,他指出:西南少数民族的士兵,如“瑶民”,“他们虽也是强制迁移,虽然也编甲屯种,但有些像民屯,和军屯不同”。见王毓铨:《明代的军屯》,第3页。。万历《广西通志》记载了柳州卫的两个屯田总数,一个是“原额田”,共409.43 顷,另一个是“实在田”,为252.37 顷。可见,虽然卫所通过与招主的合作对余田进行了控制,但是屯田的数额依然是在流失的。
马平县的“余田”问题,只是明代中叶广西田地问题的一个典型,但并非孤例。正如计宗道所言:“此特始举马平一邑论耳,若通一省究之,又不忍言也。”⑦嘉靖《广西通志》卷19《田赋》,第12页。试举数例:
一是同属柳州府的宾州。据万历《宾州志》记载,宾州守御千户所原额屯田15,064.58亩。其中“宣德五年内宾州豪民谢再鲜、林鉴等佃种隐占绝军蒙丁贰等五十五户屯田四十一顷八十九亩一分九厘”、“上林县豪民韦汝利、潘茂等佃种隐占绝军温仲占等六十一户屯田五十四顷八十八亩六分三厘”、“正统年间被豪民韦汝利等盗卖与土官知府岑瑛共三十三顷九十二亩四分二厘”⑧万历《宾州志》卷10《兵防》,第98页。。这些豪民共“佃种隐占盗卖”屯田13,070.24 亩,占原额屯田的86.8%。被豪民所盗卖占耕的屯田,很大程度上应该成为了地方豪强的私产,耕种这些土地的,也是无籍的瑶僮。
二是地处广西东北部的桂林府全州灌阳县。该县在洪武二十八年“猺民作乱”归并里甲后,“其剿绝人户二十八里,田粮无人种纳,奏奉勘合,已拨桂林中右二卫并灌阳千户所军余屯种前田,认纳粮六千余石。田归军种,粮存于民。只得分派虚貱,积年拖欠不完”①康熙《灌阳县志》卷3《赋役》,第6页。。灌阳县的编里流失与田地转移的情况,与马平县颇为相似。只是灌阳守御千户所的军余在承领这些“无人种纳”的田粮时,“田归军种,粮存于民”,造成了军民之间的赋税不平衡。
三是位于广西西南部的南宁府。据嘉靖《南宁府志》记载,南宁有军余田和民余田两个名目,共计160余顷,并附小字说明:
右二项余田,系正统、景泰间,八寨木头洞猺贼越过州境占据军民田土,因而荒芜者无算。后贼渐平,民逃他境者,或被杀绝,无主开耕。有州卫舍余、军民有力之家,告愿开垦增粮在卫,名为余田。②嘉靖《南宁府志》卷7《屯田》,《日本藏中国罕见地方志丛刊》第2册,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0年,第443页。
嘉靖《南宁府志》对南宁“余田”来历的说明,和马平县的余田非常相似,是相同的叙事模式,都是因为编户流失导致田地“无主开耕”,使得“有力之家”趁机承垦。这些田地也因此从民田系统流失出去,其所增之“税粮”也由卫所征收。
综上所述,周琦、王臣、计宗道等人的叙述,隐隐约约看得到广西“里甲残破”这一叙事背后“户亡田在”的实质,这些士大夫与柳州当地豪强力量是有密切关系的,所以关键的地方往往回避,同时创造出一个明初广西已经有完备里甲体系的“传说”。如果站在没有直接利益关系的角度,对上述问题的认识就大不相同。如广西提学佥事兼署抚夷事王宗沐在嘉靖三十二年(1553)左右为曾任广西副总兵的张经所修《桂林图志》作序,对广西动乱频发的情况进行了解释。王宗沐认为,“夷”之所以要造反,问题出自“有司不得其职”,核心则“起于赋役”。他批评的是整个赋役体系的不合理,因为一里的赋税是有定额的,如果一家逃亡,其留下来的赋税都要“责偿于留者”。至于那些需要纳赋的“夷”,他们与官府之间并不能直接打交道,而是需要通过豪长、隶书这类中介人作为二者的沟通。王宗沐很生动地把这一个逼迫“夷”造反的过程描述出来:有司(官员)不能与“夷”直接打交道,因此“夷”交到官府的赋税是没有准数的,豪长、隶书上下其手,一分的正供钱粮,他们要向“夷”索取九分额外的供应。当这些“夷”没办法承担这么重的赋税时,就只能抛弃妻子,落草为寇。逃亡者的赋税负担又会分派给该里未逃亡的家庭,这样其他家庭的赋税负担因而增加,逃亡的人也会越来越多。逃亡者愤不能平,所以逃而为“盗”,亦即脱离了官府的里甲系统。当官府不能坐视,派兵进剿时,则兵锋所向,不仅烧杀抢掠,而且是为了获得“首虏”来请功。但是为盗之徒,要么因为弱小而被豪强所吞噬,要么因为强大而被豪强所庇护。官兵进剿的时候为了首功而滥杀,又导致这些逃亡者的亲族也揭竿而起。当官兵力量不够时,就不得不招抚。不仅“夷”如此,而且连编民也同样因此被迫驱而为盗③王宗沐:《敬所王先生文集》卷2《桂林图志序》,《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集部第111 册,济南:齐鲁书社,1996 年,第51页。该序中提到王宗沐嘉靖二十九年任提学,至此已“三岁余”。。
结 语
刘志伟认为,明代广东“盗寇”,由两股力量汇合而成,一是脱籍的编户,二是居于山海之中的“蛮夷”,其根源问题是明朝繁苛的赋税征派①刘志伟:《在国家与社会之间:明清广东里甲赋役制度研究》,广州:中山大学出版社,1997年,第93—108页。。这一论断虽然针对的是广东,但对广西同样具有相当的解释力。明初广西的编里包含大量官府控制薄弱的附籍的人口。地方上的各种“动乱”往往是很好的理由,让原来附籍的人口脱离了官府的编户系统,脱籍后的人口,就被视为了无籍的瑶僮。明朝广西地方官府,往往依赖地方上的“有力之家”对瑶僮进行钤束。这些钤束瑶僮之人,在明代文献中就被称为招主。编户流失的结果,是大量人口虽然脱籍了,但土地还在,只是在地方官府的认定中,成为了无主的“荒田”或余田。田地的耕种者,则变成了无籍的瑶僮(至于这些瑶僮是否属于流失前的里甲编户,因史料所限,难以确考)。也就是说,通过在户籍与田地登记上的种种操作,编户成为了瑶僮,民田成为了“余田”。围绕着这些瑶僮与“余田”的控制权,地方官府、卫所、豪强之间互相竞争,又互相依赖。官府要收上赋税,需要豪民的配合,豪民也需要卫所的武力作为后盾,作为控制瑶僮交纳租税的手段。卫所、豪民与官府之间的博弈,就是编里减少、税额降低。编里减少的最极端的情况,就是桂林府理定、古田县,平乐府立山县这样的情况,整个县都不在官府控制之中。当这些控制土地的势力不再与官府合作,官府就收不上赋税。在官方记录中就会把这种情况归结为地方上瑶僮作乱的结果,同时也掩盖了瑶僮之上的各种势力的真实影响。
从明初广西州县编户流失的情况来看,明初广西的户籍登记的涵盖范围是比较大的,包含了大量非汉人口,但其组织显然又是比较松散的,因此在洪武、永乐之际的地方动乱中就产生了大量编户脱籍的现象。在明朝的社会背景下,编民的身份本身就是一种重要的资源,也是一把双刃剑。拥有编民的身份,意味着可以在王朝体系之内与官府打交道。编民一方面有义务承认官府的权威并向官府交纳赋税,另一方面也能借此换取官府的承认与保护,不致“玉石不分”,甚至还能利用官府的权威,震慑甚至控制周边的瑶僮。而脱籍之后的瑶僮,一方面虽然会沦为官府与军队打击的对象,另一方面也摆脱了编户的沉重赋役负担。因此,在官府、卫所、编民与瑶僮各有盘算的情况下,这种自洪武末到永乐中开始大量出现的编户流失现象,成为了各方势力博弈的一个均衡点,并在很长时间内得到维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