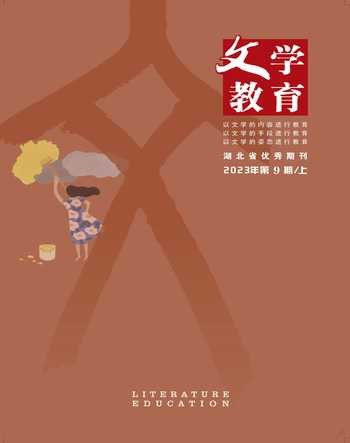《红字》中人文主义理想社会的建构
2023-09-01刘思雨
刘思雨
内容摘要:霍桑《红字》中宗教审判与自我救赎的交替出现既丰富了小说的层次,又向读者传达了深厚的宗教哲学思想,作品呈现了海斯特勇敢地面对审判获得自我救赎;丁梅斯代尔逃避审判被迫赎罪,以死亡为代价获得解脱。分析《红字》中主要人物在宗教审判与自我救赎两种方式达成赎罪、获得解脱的过程,解读作家对人性与信仰平衡的肯定、对宗教虚伪性的无情揭露,表现了霍桑以人文主义精神对清教的重新审视,凸显其构建理想宗教社会的美好愿望。
关键词:《红字》 审判 救赎 人文主义
清教发源于英国的加尔文教,主张自我节制,禁欲苦修,以此来减轻上帝对惩罚。清教在美国隶属英国殖民地期间传入美国,并产生了巨大影响。小说《红字》作者纳撒尼尔·霍桑是美国19世纪著名的浪漫主义作家,他热爱历史,在对殖民地历史和家族史的研究中了解到了受制于封建宗教思想的社会是如何将人生吞活剥。霍桑一方面在美国长大,从小就受到清教观念的影响,保留了清教的观点和思考问题的角度,另一方面,他又看到了清教对人性的摧残,批判清教禁欲主义对人的压迫。在对清教复杂的态度下,《红字》饱含着霍桑对起清教愚昧陈规的批判与思考应运而生。
《红字》背景发生在清教思想盛行下的北美殖民地时期,故事围绕着海斯特·白兰与丁梅斯代尔的通奸罪展开,已婚的海斯特与牧师丁梅斯代尔相恋,并生下了珠儿,珠儿的降生暴露海斯特违背伦理道德的通奸罪行,致使她被送上行刑台接受惩罚。审判海斯特的牧师认为海斯特是被人引诱才堕落的,要求海斯特供出孩子父亲的身份,让他受到应有的惩罚,否则将佩戴一个红A字终生不得摘下。出于对恋人的爱,海斯特拒绝道出孩子父亲的身份,独自接受惩罚,而与海丝特一同犯下通奸罪的丁梅斯代尔在袒露罪行中却表现出延宕。
一.宗教与人性的冲突
北美殖民地时期盛行的清教压抑人性,用封建迷信的教义与宗教仪式掌控人的思想,以严苛的惩罚方式残害人的生命。霍桑对黑暗的宗教统治产生反思,以海丝特、丁梅斯代尔作为清教戒律的“反叛者”接受审判,在人性与清规戒律的冲突下悲剧得以产生,致使海斯特和丁梅斯代尔承受痛苦。
(一)宗教的压抑
“圣经故事中记载人类始祖亚当与夏娃违背上帝意愿偷食了禁果,因此被驱逐出了伊甸园,在世俗的磨难和诱惑中人性开始逐渐堕落,偷食禁果之罪成为了整个人类的原始罪过,被称为原罪。”[2]原罪是基督教神學理论中的一个重要观点,而清教作为基督教的一个分支,同样将《圣经》奉为圭臬,肯定人具有原罪。清教提倡勤俭节约、辛勤劳作,反对华丽奢靡、繁文缛节,否认以爱情作为婚姻的基础,纵欲更是有违伦理道德之举,以封建迷信的宗教形式作为约束民众行为规范的武器,以不合理、不公平的方式处决有罪之人。制度本身只是一把衡量价值观念与行为准则的尺,而人的贪欲和恶念一旦萌生就难以控制,掌控着至高权力的教会凭借一把扭曲又倾斜的尺,对蒙昧无知的百姓实行极端的压迫与摧残。
《红字》的创作与霍桑的先祖曾参与过巫审案有关,家族中先祖“由于固守愚昧的观念残害了无数无辜女性,将数位妇女以女巫的身份送上了绞刑架,无辜受到审判的人因无法忍受非人的折磨只好承认自己是巫师,有的受害者为了‘赎罪被逼‘供认出其他无辜的人。这样越来越多的无辜者牵涉到审巫案中,最终有19名男女‘巫师被判处死刑。”[4]《红字》也是霍桑企图洗涮家族曾带来的冤屈,与先祖划清界限而作。宗教信仰固然具有引导劝诫的作用,然而过度信仰却会演变成宗教狂热。在北美殖民地时期宗教观念统治一切的社会环境中,不止是无辜的男女被当作女巫施以绞刑,一切拥有自我意愿,不心甘情愿地服从于宗教思想管束的人都会被视为异类,成为教徒口中的罪人送上行刑台。
(二)欲望的释放
海斯特的丈夫齐灵沃斯身材畸形、面容丑陋、年近迟暮,与海丝特姣好的容貌难以相称,在迎娶海丝特后,他又将热情都投入到医学研究中,吝啬对妻子的关爱,所以海丝特虽已为人妇,她的婚姻却并无掺杂爱情成分。在迁新居时齐灵沃斯同样因忙于处理自己事物未与海斯特同行,之后数月又杳无音讯,众人猜测他早已殒命在大海的波涛之下。饱受孤独折磨的海丝特在新居住地邂逅了年轻英俊、学识广博的牧师丁梅斯代尔,两人情投意合互生情愫,爱情的滋润使海丝特将已婚的身份抛之脑后,按耐不住情欲与牧师相恋,直至孕育了珠儿,她通奸的罪行才得以暴露。
海斯特出于对恋人的爱意包庇了丁梅斯代尔,帮助他逃避了面对公众接受审判的代价,却也使得他暴露出人性的脆弱。他身为牧师却难抑情欲,与海斯特犯下通奸罪,又不敢在行刑台上坦白罪行,害怕丢失神职人员的名利与荣誉。教义与欲望的天枰最终向人性倾斜,罪恶之种在丁梅斯代尔的心中发芽、生长,在它的心中滋生出欲望。霍桑设计以一位广受群众爱戴,学识渊博的牧师作为这段有违清教教规的恋情中的男性主体,成为背弃了教义的反叛者,针对清规戒律中冷漠与严苛的批判昭然若揭;又以丁梅斯代尔胆怯与承认罪行这一情节的描述,对在公众心中象征绝对正义的神职人员进行讽刺,他的罪行既表现了殖民时期清教神职人员的虚伪,又企图伪饰其虚伪的真面目。
二.宗教审判与自我救赎
海斯特在接受审判时承受了巨大的痛苦,惩罚结束后她依靠能干的双手主动帮助他人,以苦修的方式进行救赎,最终获得解脱;丁梅斯代尔在审判时未能坦诚罪行,逃避惩罚,导致他在救赎中异常痛苦艰难,最终付出了生命的代价。海斯特与丁梅斯代尔通过宗教审判与自我救赎两种赎罪方式获得解脱的过程,体现了霍桑以人文主义精神对清教的重新审视。
(一)上帝的审判
当海斯特从监狱牢门走到行刑台的路程中,她收紧怀抱婴儿的臂膀,除了出于对孩子的呵护,更想通过这一举动掩饰红A字这个象征着通奸的耻辱标志,佩戴红A字的海斯特成为了荡妇的代表,遭到所有人的排斥。她的内心在是否认同通奸罪责的矛盾中痛苦纠结,海斯特一方面反抗没有感情的婚姻,并不认为对爱情的追求是错误的,另一方面为了袒护恋人又不得不承认自己的罪行,清教残酷的惩罚使海斯特在反抗违背人性的伦理道德之中又产生出罪恶感,加剧她的痛苦
红A字在小说中同样以一种隐蔽的方式出现在丁梅斯代尔的身上,他由于愧疚总在深夜对自己施以鞭刑,鞭子抽打过的痕迹却奇迹般的组成了一个红色的A字形,成为隐藏在丁梅斯代尔正统服饰下罪恶的象征。这一情节具有魔幻色彩,却印证了丁梅斯代尔身为最接近上帝旨意的神职人员、清教最虔诚的信徒,经受的审判正是来源于上帝,帮助这个不敢公布自己罪行的罪人确立身份。
海斯特在行刑台接受审判时,作者着重描写了台下一群妇女对海丝特的批判,她们是一群恪守清教思想的“正统”女性形象,穿着枯燥而质朴,话语中充满着对海斯特的鄙夷与痛恨,与海丝特张扬的美丽、叛逆的罪行形成鲜明对比。她们用最恶毒的话评判海丝特,并且企图用更加残忍、超越教规的方式惩罚她,用恶毒的话语和眼神对海斯特进行攻击。霍桑对这群身为教会成员的女性描写以批判态度保留了她们的恶毒,而对海丝特的描写以尊严、倔强等赞美之辞冠之,在两种完全对立的女性描写,以及将怀抱着珠儿的海丝特与圣母玛丽亚的光辉形象联系起来,却用“法国恐怖党人的断头台般”[1]来比喻行刑台,霍桑在小说开端便表明了他反对清规戒律的立场。
(二)灵魂的救赎
红A字既是海丝特耻辱的象征,也是她展示自己高超的手工刺绣技艺的标本。清教徒反对铺张奢华,服饰以简单朴素的黑色为主,而海丝特用金银丝线缝制出精巧细致的装饰点缀了枯燥沉闷的衣着风格,她的刺绣在小镇中逐渐流行起来,使她获得了依靠自己劳动赚取生活开销的机会。然而面对如此受欢迎的市场环境,海丝特却将大量的时间投入在为穷苦的人民们缝制粗布短衣中,海斯特通奸的行为在殖民地时期虽然是错误的,但她勇敢、坚强、善良、能干的高贵品质使她赢得了所有人的尊重,她成功改变了在居民心中的形象和地位。
丁梅斯代尔内心力量的软弱让他付出的代价是难以承受的,“牧师既非一般意义上的‘虚伪,其性格塑造更非为衬托海丝特的勇毅,相反,他是真诚的。”[6]丁梅斯代尔的痛苦来自于他的善良和信仰上帝的赤诚之心,他曾倾诉过如果自己是一个十恶不赦的坏人,是一个没有任何羞耻感可言的自私之人,那么他一定不会有任何负罪感,反而会窃喜自己逃避了处罚。但是由于他对上帝的忠贞,导致他的信仰沦为对他最大的折磨。
丁梅斯代尔在参加最后一次宗教布道之时想要坦白自己的罪行,他撕开身前的衣物,身上的红A字一览无遗,坦诚地展示自己拥有隐秘的红字,证实自己的罪过。齐灵沃斯曾向他说明过这个世界无论天涯海角,都难以逃过他的折磨,对于丁梅斯代尔来说唯一安全的地方只有行刑台,丁梅斯代尔因胆怯逃避上帝的审判,于是沦为魔鬼的目标,唯有重新接受行刑台的审判,回归上帝的怀抱中,才有机会逃脱魔鬼对他的迫害,更进一步说明了救赎离不开宗教的约束。
三.人文主义理想社会的建构——海斯特形象解读
海斯特形象的塑造打破了传统观念中女性处于弱势,需要男性解救的地位,她反抗封建婚姻,追求自由爱情,在奇灵沃斯与丁梅斯代尔所代表的男性力量面前也显得更加坚韧强大。不仅如此,海斯特的反叛和对珠儿的教育方式也冲击了宗教社会伦理道德,对社会环境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她的救赎正体现了霍桑以人文主义精神对宗教理想社会的建构。
(一)光辉的女性形象
霍桑一方面否定海丝特通奸的行为,将她“送”上行刑台接受审判,另一方面又不吝啬對海丝特的赞美,赋予她匀称的五官与身材,精致的刺绣手工,和崇高的道德修养,将其塑造成一位光辉的女性形象。她的存在既提供了一种典型的罪责,又揭示了一条有别于传统严苛赎罪方式的救赎之路,她部分继承了先前的经验,又拓展了赎罪方式的新选择,在与传统理念的分离中获得拯救。她对罪行的接受正属于自我批判的成分,并以此修正行为,在不断的自我改进中获得救赎,达成主体的完整状态。
海斯特在结局重新回到小镇并佩戴上红A字,看似是又回到原点,但实际上完成苦修的海斯特早已脱离了负罪的状态,她的回归是以一个完成了自我身份和红字意义的转化,获得救赎之人的身份重新审视历史,给予还在迷茫中的百姓引导和帮助,此时海斯特不同于往日对传统伦理挑战、对家人保护时的激烈、叛逆的状态,而是在回归中达到了平和的新境界。完成了人格的净化。
珠儿的出生是海丝特罪恶的象征,但海斯特从未拒绝过红字带来的屈辱,也从未厌弃过如红字般的珠儿,没有将她视为罪孽的产物。她对珠儿悉心教导,在物质上也给予珠儿力所能及的一切,海丝特还拒绝以清教徒家规中常见的厉声责骂或是用戒尺鞭打教育孩子,总是以温柔劝说或轻声呵斥的方式对珠儿进行管教。在海斯特慈爱的关怀下成长的珠儿宛如在伊甸园中的天使,不受世俗的约束,珠儿知晓教规中的规矩依然随心所欲,正是霍桑心中理想的成长方式,通过珠儿的成长经历,作者赞美了纯真美好的人性。
(二)和谐的宗教社会
在小说中海斯特接受惩罚时写道:“他们不愿意严格行使我们正义的法律来惩罚她,论罪那是要处死刑的,但是他们的慈悲心肠只判决白兰太太在绞刑台上站三个钟头。”[1]对海斯特处罚的改变正是霍桑对宗教社会理想样式的希冀,不应该不教而诛,过于严厉地进行处罚,而应该实事求是,根据犯罪的程度量罪,并通过教导与指引给予犯罪者赎罪的机会。
海斯特对居民的帮助也是良好社会氛围的开端,她博得了小镇居民的好感乃至尊重,重建与他人的社会关系,通过海丝特的高尚德行,小镇的群众逐渐被她在行刑台上独自承担罪责的行为所打动;被她对穷苦的人们无微不至关怀所吸引;被她技艺高超的手工刺绣制品所折服。海丝特由一个罪人转变成一个道德高尚的人,可见霍桑认为通奸虽然触犯了清规戒律,但是只要主体愿意自我救赎,依然有机会获得拯救,过于违背人道主义精神的宗教审判形式只会增添不必要痛苦与杀戮。
海斯特既认同自己的罪行,进进行自我救赎,又在恋人丁梅斯代尔需要帮助的时候毫不犹豫施以援手,甚至萌生私奔的打算,看似一错再错的背后是爱唤醒了海斯特的人性,让她从一位恪守清规戒律的清教徒变成一位觉醒的人文主义者,海斯特突破了宗教伦理道德对女性的束缚,在封建社会中关注人自身的状态,又人与社会的联系,依凭自身努力营造了和谐的社会氛围,她是一位破除封建迷信的先行官,以一种温和的方式来对抗禁锢人性的伦理法规,体现出人文主义思想。霍桑通过认同海斯特的赎罪方式反对以暴力维持社会秩序的行为。
海丝特既是被审判、惩罚的对象,又是一位彰显了人文主义精神、充满反叛精神的女性形象,通过红字这一线索连接男女主人公审判和救赎的抒写,霍桑以饱含人文主义精神的进步思想,追求人生选择与恋爱的自由,歌颂世俗爱情,宣告对清教徒冷漠残忍清规戒律的鞭挞,赋予清教充满活力与人文主义精神的新内涵。
霍桑在小说中肯定了原罪的存在,也论述了获得救赎的可能性,一方面肯定了宗教信仰对社会的整治作用,另一方面也表现出否定过于沉迷宗教教规,演变成宗教狂热残害他人性命。但海斯特又没有完全觉醒,她认为珠儿身上拥有与她相似的叛逆与反抗精神是不应该的,于是她企图对珠儿的自由与野性加以约束,可见海斯特的叛反抗具有向清教教会屈服的成分,其自我赎罪、惩罚的情节同样体现出保守成分,以及丁梅斯代尔的赎罪方式仍具有宗教色彩,这些都体现出了霍桑反抗封建制度的不彻底,其思想仍具有保守性。
参考文献
[1][美]纳撒尼尔·霍桑.红字[M].侍桁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1.
[2]郑彩霞.论霍桑的罪恶观和救赎观——以《红字》为例[J].西部学刊,2020(22).
[3]聂玲凤.霍桑是清教徒吗?——从《红字》中的“罪”谈起[J].英美文学研究论丛,2021,(02):245-254.
[4]江春奋.《红字》与审巫案——故事文本与历史的互文性解读[J].宜宾学院学报,2010(04).
[5]钟再强.人性的救赎——霍桑《红字》的重要主题[J].南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6(02).
[6]苏欲晓.罪与救赎:霍桑《红字》的基督教伦理解读[J].外国文学研究,2007(04).
[7]肖旭,黄维.论《红字》中爱的伦理价值[J].内蒙古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7,46(05):143-146.
[8]诸葛晓初,吴世雄.人性与信仰的张力——《红字》中丁梅斯代尔救赎历程的认知阐释[J].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学报,2020(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