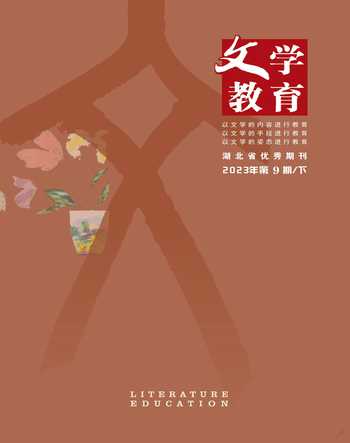影片《满江红》当代民族寻根意识的拾遗
2023-09-01马雯迪
马雯迪
内容摘要:《满江红》在2023年春节档上映,作为商业片票房取得瞩目的成绩,成为第五代导演张艺谋的又一力作。《满江红》成为商业片的同时又不失影视创作的审美艺术价值。张艺谋延续其影视创作强大的历史文学背景依托,与以往以文学作品为依托不同,这次所依托的是一词压两宋的《满江红》,叙述宏大历史背景下小人物的家国情怀,彰显民族寻根的意识形态。此外,充分运用融合影像叙事和情节叙事,展现写实与写意,再现与表现为一体的审美价值。
关键词:《满江红》 意识形态 影像叙事 情节叙事 民族寻根 家国情怀
《满江红》是张艺谋导演的2023年春节贺岁档电影。看到片名也不难想到,影片依托的是岳飞精忠报国的历史故事,一首《满江红》激起国人的家国情怀,全军复诵《满江红》也成为影片的高潮部分。张艺谋沿袭第五代导演以及他自身一贯的创作思路,创作历史的叙事主题,更多的依托文学文本进行改编创造。他的处女作《红高粱》是改编莫言小说《红高粱》和《高粱酒》而成;看了苏童的《妻妾成群》而创作影片《大红灯楼高高挂》;影片《菊豆》也是来自于刘恒的小说《伏羲伏羲》改编而成;《秋菊打官司》改编自陈源斌《万家诉讼》;《活着》更是余华的经典文学作品;《摇啊摇,摇到外婆桥》改编自李晓的作品《帮规》等等,张艺谋所拍摄的影片多数依托文学文本。这次的《满江红》同样让影片充满着文学性,但与此前拍摄影片不同的是,这次依托的是一首词,一段历史,展现的是小人物的家国情怀。
电影的文学性一直是影视传媒在艺术领域一个经久不衰的话题。这一话题开端于1980年,由张峻祥在导演总结会上提出。此后各种电影刊物围绕“文学性和电影性”展开讨论。程耳曾表示“文学是电影的土壤,文学修养的高低决定了未来电影的好坏”。在我看来,电影的文学性是区别于文学文本生活感的唯美感与真实感的体现。文学性一词本身就是一个抽象概念,它包含了理想化,又或者说是静止性。这与戏剧语言中的人物立体性恰恰是一组对立的概念,即人物需要有内在的矛盾,才能发生戏剧冲突。这样的带有立体感的人物就如文学作品语言中的圆形人物一样,他们具有多个侧面去推动未来情节(戏剧冲突)的发展。而文学的理想化是为了诗意而诞生的,它与戏剧中人物的立体性不同,它并不要求内在矛盾,而是要纯粹,表达的方式也常常比较极端,给人一元性、永恒和静止的感觉。因为它并不像戏剧性那样暗示之后的变化。《满江红》中除了有许多人物冲突的戏剧性拍摄外,还有许多静止画面,其中色彩光影的构图可以打造出绘画摄影般的效果。
电影的文学性也包含着虚构的内涵。该影片的历史背景是在南宋时期岳飞死后,一个金国的使者突然死在了宰相秦桧的驻地,并且他有一封要交给秦桧的密信不翼而飞,效用兵张大和副统领孙均也卷入了这场事件中,因此秦桧就派他们彻查此案并找到密信,时间限定在秦桧启程去秋凌渡前的一个时辰内,地点在乔家大院中。影片完全遵循戏剧的“三一律”准则,剧情层层深入,跌宕反转,展现出“情理之中,意料之外”的影视效果[1]。《满江红》的剧本从文学角度出发进行分析,具有“大处不虚,小处不拘”的特点。影片以岳飞的《满江红》作为依托,进行艺术虚构。故事是发生在死后四年,也就是公元1146年。将剧中小人物打更夫丁三旺、车夫刘喜、艺妓瑶琴、效用兵张大集结起来,让岳飞的遗作《满江红》重现世人为岳飞沉冤昭雪,传承岳飞精神。他们藏匿秦桧身边多年,潜心谋划,不惜舍去性命决定在金人使者来访时实施“刺秦行动”。除了故事情节的虚构外,另一处虚构就是将《满江红》认定为岳飞遗作。具有效的历史考证,岳飞所做《满江红》之时,是在宋金之战交战过程中,我们分析全词可以感受到悲痛惋惜,但词的下阕“驾长车,踏破贺兰山缺!壮志饥餐胡虏肉,笑谈渴饮匈奴血。待從头,收拾旧山河,朝天阙”又可以看出岳飞以及岳家军壮志满满的战斗精神。那么,仅从全词的主旨内涵方面分析,就不能将《满江红》一词设为岳飞遗作。其次,有历史记载岳飞死前在牢狱之中写下“天日昭昭,天日昭昭”的绝笔。这样看来,影片将《满江红》设为岳飞遗作实为艺术虚构。编剧陈宇这样设置的目的无疑是将《满江红》中所代表的家国情怀无限放大,使影片更具有戏剧性,在影片中的体现就是“全军复诵”的高潮环节,这样的复诵正体现了一种传递感,当我们把这样一首词慷慨激昂的仪式般的吟诵出来时,深藏在我们民族血脉里的家国情怀喷涌而出,从而达到引起关注共鸣的艺术效果,激发出我们中华民族积淀在内心的崇高民族意识与家国情怀。
一.意识形态的介入——民族寻根与家国情怀
法国哲学家德·特拉西在19世纪首次提出“意识形态”一词,它的意思是“关于观念的科学”。此后,“意识形态”在多种含义上被西方学者使用,主要指意识的系统化。人类意识控制自己的实践活动,并体现自己的主观能动性。而实践又会反作用于人类的意识活动,从而形成人类的不同意识形态。文学很显然就是具有意识形态属性的,并且文学活动是带有审美意识形态性质的。在《意识形态和意识形态国家机器》中,阿尔都塞更加强调意识形态的想象性质。他提出了一个命题:“意识形念展现了个人同其真实行在情况的印象关系(‘印象关系应译作‘想象关系)。”无论是文学形式还是戏剧影视都强调创作者(导演)的想象能力。在张艺谋的受访谈话中他就提到:《满江红》的剧本就是他和编剧陈宇打磨了四五年之久,他在冬奥会之前就已经在构思该剧本。他们通过做初稿,再修改二稿、三稿,不断补充内容。由于影片的悬疑属性,需要想到剧本的各种反转;喜剧属性也要求剧本台词的“包袱”数量。总之,《满江红》的剧本创作无不体现着编剧和导演的创作才华。
其次,阿尔都塞的意识形态理论还将从政治层面对意识形态进行考量,分析意识形态与国家政治之间的关系。而文学艺术的研究也常常从此角度进行分析。第五代导演的电影拍摄恰逢80年代中国新时期改革开放,当时的艺术领域掀起“伤痕”、“反思”、“寻根”等热潮,从文学到影视,各种艺术门类无一幸免。第五代的导演们似乎也热衷于这样的历史叙述主题的拍摄,他们的代际共性就是用影片拍摄的手段去寻找民族生存根基、民族文化深层土壤中的精神气质。例如陈凯歌的《霸王别姬》,试图找寻京剧在我国现代人中的遗失。这样的拍摄初衷在某种程度上就构成了意识形态的介入。从另一个角度分析电影的意识形态介入,电影是“人的电影”,本身是一种“人学”,这种意识形态性也表现在用拍摄电影的方式挖掘深藏在人物内心的民族共同因子。从唯物主义反映论出发,创作与社会是反映与被反映的关系,创作与社会背景关系密切是第五代一贯的叙事主题与美学特征。
《满江红》以爱国将领岳飞“精忠报国”的故事作为影片所依托的内容,且《满江红》一词最能代表岳飞精神。当我们读到这样一词压两宋的《满江红》,可以领略到“靖康耻,犹未雪。臣子恨,何时灭”的惋惜与悲愤,但又有“架长车,踏破贺兰山缺!壮志饥餐胡虏肉,笑谈渴饮勾奴血。待从头,收拾旧山河,朝天阙”的积极战斗精神,北伐中原收复失地是岳飞平生的夙愿[2]。影片中也出现效用兵张大背部刺字——“精忠报国”的情节。有关岳飞刺字的说法有很多记载,但是何人所为考证尚未确定。明朝末期,《精忠旗传奇》中记载:“史言飞背有‘精忠报国四大字,系飞令张宪所刺”。这样的史料就证明岳飞“精忠报国”是张宪所刺;而另一种则是“岳母刺字”的说法,可以证明该说法的史料最早见于清乾隆年间,杭州钱彩评《精忠说岳》的第22回,篇章题目为“结义盟王佐假名,刺精忠岳母训子”。影片中暗藏秦桧身边多年的岳家军,他们背后带有岳家军图腾般的印记——“精忠报国”,影片中这四个字的出现也造成情节的一大反转,同时也引起了观众的共鸣,这四个字中的“爱国”以及“忠义”的内涵深深的连接了华夏儿女的民族血脉,这正是一种集体无意识情感的展现。在意识形态领域我们还经常提到“英雄史观”与“人民史观”。在《满江红》的人物塑造中正是遵循了“人民史观”的原则,诉说大的历史事件中小人物舍生取义的家国情怀。从打更夫丁三旺、马车夫刘喜、舞姬瑶琴再到小团体的组织者领导者张大和亲兵营的副统领孙均,张艺谋所关注的是底层的人物的内心活动和心理世界。正是在他们的底层社会中,也有着亲情和爱情的书写,除了家国情怀,亲情和爱情也是他们唯一重要和难以割舍的一部分。影片描写了刘喜和桃丫头无法相认的场景,即便如此刘喜还是以身犯险决定刺杀秦桧,如此体现了家国不能两全的无奈;身为舞姬的瑶琴摒弃了我们以往“商女不知亡国恨”的认知,她同样有勇有谋,不顾张大劝说亲自上阵,她与张大的爱情同样令人动容。最终开展刺杀行动的小人物都死了,但是还剩下年纪尚小的桃丫头,她躲在石狮子后面吟诵着《满江红》,这代表着希望代表着传承,预示着我们岳飞精神会永远流传。张艺谋喜用“小见大的美学原则”[3],从他的《一秒钟》、《悬崖之上》、《狙击手》等影片不难看出他对宏大历史背景下小人物叙事的关切,他正在挖掘的是“底层主体性”的拍摄,这样的底层叙事更契合时代社会的变化以及观众的观影心理,使影片内容更贴近底层百姓芸芸众生,更容易唤起观众的共鸣。
不止是《满江红》,张艺谋的《悬崖之上》和《狙击手》也都延续了这样一个家国情怀的主题。张艺谋自己在接受采访时也坦言:家国情怀是流淌在我们所有中国人血液里的东西,是我们的文化,也是我们的根。而做电影的主要任务就是要讲好中国故事,丰富观众体验,传递家国情怀。
二.影像叙事与情节叙事的融合
第五代导演除了在影片中展现意识形态的代际共性以外,在影片创作中还有一个很大的突破与革新,那就是将影像作为电影叙事的本体语言,电影成为影像本体的叙事艺术,将影像叙事与情节叙事在电影中有机融合,展现写实与写意,再现与表现为一体的审美价值[4]。他们充分吸收了巴赞的电影影像本体理论,主张电影应该在时间与空间关系上表现得真实,又应该创造现实的幻景,表现人物内心的真实。电影《满江红》恰好满足了这样的影像本体美学。
《满江红》的拍摄没有局限于物质现实的实景复原,而是通过构图、象征、光影、色彩、音乐效果以及运动镜头等拍摄手段,展现写实与写意,再现与表现为一体的审美价值。张艺谋曾说:“视听效果是让观众进入电影院的先决条件”[5]。所以他的影片创作极其重视视听造型的展现。视听美学也是塑造一部成功影片的重点内容之一,导演们“力图在电影的照相技术本性所具有的最大再现性中,赋于表现性的意趣,在形似基础上捕捉神似”[6]。在拍摄《满江红》的构图方面,张艺谋再次选择山西作为取景地,建设了两座古宅,将它们横向打通,所有的故事均在这座老宅中发生。影片中有迷宫似的走廊,有中国文化特色的亭台楼阁,将悬疑的剧情设置在迷宫一样的走廊中,使影片情节更加迷幻、节奏更加紧凑。关于影片色彩方面,张艺谋抛弃了以往对红色色彩的偏爱,而采用一种青蓝色调,灰色调进行拍摄,这与影片所处的时间线是相呼应的,正是黎明前的两个小时。所以无论是影片中的舞姬、侍女的人物衣着还是武器盔甲、砍刀等都舍去了大红大绿的色调,换用灰色调。从另一个角度来看,这样的青灰色调往往也可以制造悬疑效果。影片的拍摄也处处体现光影的拍摄效果,如影片開头的牢房里以及秦桧房间的光影效果等。在音乐音效方面,张艺谋也结合了中华传统戏曲文化的内容。他采用河南豫剧,带有浓郁的民俗特色,同时加入电声和摇滚,用走马灯的节奏形式,将演员的“跑”与音效结合,每当剧情有新的线索与反转时,就会出现几个演员在走廊中“跑”的剧情,并且在各种角度进行拍摄以及无人机空中拍摄。在镜头的运用方面,张艺谋坦言曾想做出一镜到底的大胆尝试,一镜到底两个小时,每天拍两遍[7]。但最终为了展现出演员全部的表演效果张艺谋决定放弃一镜到底的拍摄方案。整部影片多运动镜头、连续式摇镜头等,例如演员在长廊里快走的镜头。以上的几个方面都使得《满江红》在视听感官层面胜出一筹,这样的影像语言的塑造无疑是非常成功的。
张艺谋在重视影像叙事的同时并没有忽略情节叙事。编剧陈宇看来,《满江红》不同于以往的古装片,它更加强调叙事性[8],它的悬疑属性决定了它要通过不断的反转来推进情节发展,通过人物与人物之间的关系造成戏剧冲突。首先在情节结构设置上,影片充分运用戏剧“三一律”原则[9],法国戏剧理论家布瓦洛曾在《诗的艺术》中阐释过“三一律”原则。将时间设置在秦桧出发去秋凌渡前的一个时辰内,地点在乔家大院内。此外,影片的创新之处在于将悬疑和喜剧元素结合,就连张艺谋自己也坦言是第一次将喜剧完整地放入一部影片中[10]。他大胆尝试选用众多喜剧演员来出演该片,将“悬疑”和“喜剧”这两种难以兼容的影片类型有机融合,在宣传海报上也写到“悬疑管够,笑到最后”。我们在电影中看到的反转都是人性的挣扎,张艺谋在叙事的同时也在挖掘人物内心。
《满江红》的拍摄在张艺谋的风格化镜头语言和编剧陈宇的多次反转的剧情设定的指导下,在某种程度上形成了美学共鸣,展现出独特的创作风格。其次,喜剧风格的大胆创新也为影片增色不少,使观众在嬉笑中找寻共同的民族文化积淀,寻找到我们血液中共同的民族意识与家国情怀。
参考文献
[1]程波.《满江红》:悬念的情动与喜剧的崇高[N].中国电影报,2023-02-01(002).
[2]齐莉莉.电影《满江红》的家国叙事与文化传承[N].中国电影报,2023-05-10(011).
[3]范志忠,金玲吉.《满江红》:历史语境的焦虑与救赎文本[J].当代电影,2023(02):30-34+185.
[4]洪宏.论中国第五代导演的现代电影创造[J].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学报,2013(03):6-12.
[5]张明主编。与张艺谋对话[M].北京:中国电影出版社,2004.
[6]罗艺军 探索电影集 序二[M].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87.
[7]丁亚平.《满江红》:一部“意识影片”的辩证法[J].电影艺术,2023(02):80-82.
[8]赵丽.张艺谋新片《满江红》:以小人物视角 拥抱家国情怀[N].中国电影报,2023-01-18(005).
[9]杨雯.《满江红》:在商业与艺术间找到平衡[N].中国新闻出版广电报,2023-03-15(008).
[10]张艺谋,曹岩. 《满江红》:在类型杂糅中实现创作突围——张艺谋访谈[J].电影艺术,2023(02):92-9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