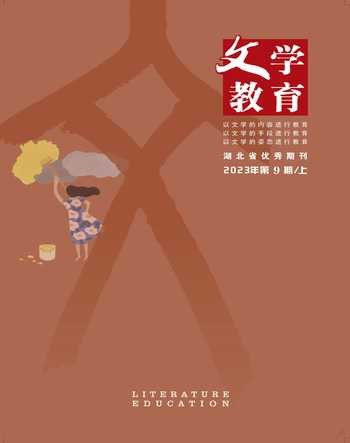可畏的想象:《白鹿原》暴力书写的再发现
2023-09-01潘志恒黄行云
潘志恒 黄行云
内容摘要:《白鹿原》作为新历史小说代表作,通过对情欲、命运等进行书写,呈现出丰富深刻的暴力意蕴——它们奉现代之名,以生活的、日常的姿态,在情节艺术层面上更有效率的,也更合理的,规约着小说人物,形成独特的美学特征,展现历史对个体造成的深层创伤。在文本意义层面上,使作品意义上升到一个全新高度,体现作者对真善美的呼唤。
关键词:陈忠实 《白鹿原》 暴力书写 历史时空
《白鹿原》作为一部“民族秘史”,其细腻深沉的笔触、可畏的想象,脱离了“历史+英雄”的传统叙述模式,以家族日常世俗经验描述了近代以降,以中国传统儒家文化为根基的土地,在各种力量角逐下,发生的血腥悲剧。同时,从民族文化高度,思索乡村、民族的变迁因由与轨迹沉浮,冷静呈现宏大叙事下,历史暴力与个体生命间繁复多姿的互动,奠定了沧桑悲凉的文学基调。
本文所谓的暴力书写其来有自,“不仅是诸如战乱、饥荒、瘟疫等历史变迁所带来的天灾人祸;更体现着现代化进程中,国族的、阶级的、身体的意识形态与心理机制,加诸个体的图腾与禁忌。”[1]虽然有泛化之弊,却正如“奥斯维辛之后,诗不再成为可能”——它辩证于历史与再现历史、前现代与现代性之间,作为一种意蕴丰富的创作倾向,介入文本叙事中。主要有两重内涵:第一,显在书写层面。如历史变迁中,“战乱、革命、饥荒、疫病等所带来的惨烈后果”[2]直接作用于个体的创伤及主张、实行某些群体性观念而导致上述内容的书写;第二,潜在隐性书写层面。主要有伦理、心理两层内涵:首先,伦理层面主要指社会主、潜流的伦理禁忌、宗法习俗、意识形态之下,预设、暗含的暴力文化;其次,心理层面则是长期受伦理指涉影响,并与人性原恶所混杂形成的有意无意的心理暴力机制,“由于创伤的不可言说性,由碎片化的创伤记忆构成的见证/证词,往往超越理性和诠释的能力”[3],形成加诸个体的隐秘规训。以上两者环环相扣,互为表里。
《白鹿原》的暴力书写,不仅是小说创作成就和文学价值的集中体现,更点出二十世纪上半叶中国农村变迁晦暗不明的历史盲点,体现了作者对传统文化的现代反思、人性的理性剖析, 以及对历史社会命运的深刻认识。这为我们探讨不同历史时空中,文学现代性价值观获取与民族品格嬗变提供一个重要研究界面。本文即从显性、隐形两个层面,点选典型人物、情节,探讨暴力书写的特点、意义与价值。
一.显在层面的暴力书写
纵观《白鹿原》,可以发现外在自然或社会环境的变幻莫测,导致不同时期群体主流观念经历着随之而来的异动。从而建构历史时空中,如疾病、饥荒、战乱等形式导致的外在显性暴力,让读者直面死亡恐惧,观看他者死亡过程,从而走向对个体生命的深层把握和主体意识的思考,体现作者对民族苦难历史的悲悯意识。
第一,来源于疾病的暴力。在《白鹿原》中较为标志性的自然灾害是病痛、干旱及其带来的饥荒。小说开篇不久,就对白嘉轩早殇的孩子、妻子及白父在“瞎瞎病”的折磨中死去进行了叙述。作者以一种近乎零度的笔触,以数量的堆砌和语言的幽默,营造出一种逼近死亡的氛围,留下强烈的阅读冲击,反衬个体如何在自然病痛面前所承受的极致痛苦,及其对抗的无力感。
第二,来源于自然灾害的暴力。小说从第十八章开始,用三个章节描写白鹿原大旱的不同寻常之处。小说写道,那年的干旱始于春季末,一直持续到中秋节,到处流传着人吃人的传说,人们对死亡已经习以为常。白嘉轩的儿媳妇死了,但她的娘家只派了一个亲人来参加葬礼,而当他来到时,却在厨房偷吃东西而忘了来时目的。最后,灾难以在鹿三供认自己是杀害田小娥的凶手,期盼已久的雨终于到来而结束。文本描绘的饿殍遍地、尸橫遍野惨烈景象与旱灾结束时“整个白鹿村响欢闹声,叫声哭声咒骂声一齐抛向天空”,共同营造出嘉年华式的狂欢化叙事效果,将旱灾轻描淡写地掩盖过去。在自然灾害面前,苦难的大众亦是喋血的大众,人性的弱点不可避免地表现出来。点面结合的自然暴力书写消解了主流伦理规范,祛除了历史崇高的话语外衣,抽离出人性内核。
第三,来源于战乱的暴力。群体宏观意义上看,党派纷争、家族恩怨、土匪侵掠等群体性暴力直接作用于原住居民,造成个体的伤残、毁灭。而文本的意义在于,关注战时场域中文化心理结构的异化和人性的消亡:首先,战争暴力带来文化原乡的没落。土匪、军队的入侵导致传统文化美德、淳朴乡情的乡土中国在战争中被解构,生命个体也在战争中萎缩。其次,改变了人物命运。文本中田小娥、白孝文等人的命运轨迹在战争书写中被不断改写,作为传统宗法符号的白嘉轩被打断腰,预示着儒家文化的退场、传统伦理的破碎和民族文化内在损伤。
第四,来源于瘟疫的暴力。其中,典型的情节是白嘉轩率众修筑白塔,消除田小娥“阴魂”带来的一场“没有什么能够伫立其间,以阻挡这种疯狂”[4]的集权式暴力恐惧。其内部体现着两层运作机制:第一,是扮演共谋角色的普通百姓。他们对瘟疫的恐惧被白嘉轩、朱先生为代表的统治阶层以简单二分法操纵,变为反对“怪异信仰”的共同体。第二,是起主导角色的统治阶层。乡土宗法势力以消除“瘟疫”为契机,以伦理权威性、宗教神秘性、大众敬畏心态为武器,向田小娥的异质性发起猛烈反击。他们以惩恶、祛魅之名消解其诉求的正当性,维护封建礼教观念的统治地位,企图巩固绝对话语权威,加强对治理辖区内蒙昧大众的控制。此间,以情欲放纵、受尽屈辱为符号的瘟疫肆虐、宗法礼教的虚伪训诫、男权传统对女性的异化,三者混杂为一,呈现出集体内部相互扼杀的悲剧现象。
二.潜在层面的伦理暴力书写
伦理暴力往往伴随着宗法习俗、伦理禁忌、意识形态——三者共同搭建的历史暴力展台,诸如白灵、黑娃等人的人生轨迹,无不体现着伦理暴力的统摄。伦理暴力将三者融入宏大历史进程中的微观社会单位,在放映伦理暴力对个体伤害过程同时,拓展了主流权力观图解之外的历史运转机制。
第一,作为宗法习俗暴力承受者的孝文、孝武。宗法暴力交汇在祠堂这个“异托邦”空间中,孝武对孝文的鞭笞情节上。当白孝武毫不手软“刷抽去”时,乡土宗法伦理对个体情欲放纵、叛逆的规训——一种行刑狂欢的“剧场向度”,掺杂着大众病态而复杂的猎奇情感、道德优越感和施虐倾向,封建宗法暴力在群体“看客”的包裹下,疯狂摧残着自然亲情关系,宣泄着对年轻生命力不可言说的妒恨,成为“砍头情结”[5]的又一呈现方式。
第二,作为伦理禁忌暴力发出者的鹿子霖。鹿子霖之死仿佛是一则恶之花的寓言,是暴力美学集中呈现的场面之一。他受白鹿两家明争暗斗的不甘、纵欲乱伦的刺激、自然病痛等因素影响下死去。其外在污秽形象,隐喻其一生以统治阶级的合法名目,为自身辩护开脱,掩盖道貌岸然下冷酷自私的嘴脸,体现乡土之恶在现代性转向中的毁灭路径。
第三,作为意识形态暴力承受者的白灵、黑娃。
首先,白灵在沉闷的乡土宗法氛围中,跳跃于革命与情爱、历史想象与欲望实践间,为小s说带来青春气息。她丰富着“革命+恋爱”的叙述模式——不仅具有女性启蒙先声意识、叛逆意识,更提出了女性逃逸他律生命轨道实践的可能性,成为近代知识女性反抗封建压迫的缩影。
然而,历史的暴力总是无孔不入,人性向善的面向总笼罩在暴力的阴影之下:首先,本应属于私人领域的情感,被潜藏的政治伦理动员起来,成为主流话语的一种表述方式,一种蕴含集体性建构的诉求。如白灵对鹿氏兄弟的情爱需革命话语包裹以表达。个体微观的情爱被宏大叙事赋予超量内涵,高度政治化叙事造成了感觉结构异化。这种出于政权合法性建构的媾和式书写,极易导致女性叙述处于“在而不属于”的尴尬处境。其次,以跨代抒情叙述呈现其暴烈之死,体现暴力写实论述的种种情感政治吊诡:第一,在这一现代性阐释过程中,白灵获得政治、经济等社会意义上的翻身同时,还获得了爱情解放,这无形中使她对“浪漫革命”景观产生认同,参与建构阶级性、群体性政治乌托邦共同体。但在激进的政治运动催化下,其女性意识消融于集体、消融于崇高,为暴力以更隐秘的方式控制。第二,革命内部不同面向所产生的荒谬,只能以主体的毁灭来进行抗争。第三,个体对美和自由的向往,如同她与鹿兆海“掷硬币”的情节,笼罩着叛逆带来的某种无意识“过失性”色彩。这从一而终地隐喻着人物的宿命,为小说的蒙上一层波希米亚式的反讽帐幕。
其次,黑娃高傲倔强、追求自由的个性使他独步于等级森严沉闷压抑的封建宗法氛围。公共层面看,在“风搅雪”运动中,黑娃作为施暴者,打断白嘉轩脊梁的寓意性描写,暗示着:第一,新兴政治力量的某种单向见证带来的庸俗社会学处理方式,对暴力的二元对立式理解使他埋下了另一批暴力的种子,模糊了同情与共谋的界限。第二,在小说反复强调儒家传统美德之下,一种无法泯灭的原始野蛮滋长。显然,黑娃并没有做好迎接“革命第二天”的准备,体现着革命初期部分人观念的不成熟和信念的不坚定,没有把个人命运同民族和国家前途密切联系,缺乏鲜明的阶级意识和继续革命的目标,最终只能复归于堕落与罪恶。
黑娃始終带有一种原始的生命意识,无法与现代革命相适应,超越了基本社会伦理道德,精神世界的荒芜使得他陷入一次次危机之中,屈服于命运,并回归到曾经憎恨的生活模式。纵观全文,他彷徨于乡土和革命这两股精神生殖力之间。他的悲剧与创伤的发生,昭示着:苦难不应等同于施加暴力的合法性,创伤更不应成为凌驾于他人之上的资本。私人层面看,他和田小娥之间的爱恨恩怨,铺陈一个深受伦理暴力伤害,隐含在伤痕矛盾里的表意系统——一方面想要抹除伤痕,一方面却又不断追忆暴力现场。在检视个体伤痕的同时,受暴的记忆魂兮归来,以暴制暴的叙事循环于焉成形。
三.潜在层面的心理暴力书写
心理暴力受历史、伦理影响,与人性原恶所交杂,导致欲望、意识的异变、扭曲,并以日常的、合理的姿态活跃在文本里,更细腻地揭橥暴力与身体政治间错综复杂的论辩。从鹿三杀害田小娥等典型情节中,人性暴力因子显而易见,体现作者对儒家文化花果飘零、乡土传统—现代革命、文明转型的复杂态度、隐忧与无奈。
第一,鹿三杀害田小娥的暴力书写。在特定历史时空中,田小娥仍不得不依靠强势话语,来抵御外界人为或自然暴力,以保证女性个体的畸形完满,其悲剧性不言而喻。然而,鹿三秉持一种近乎朴素的正义意识杀害了她,这深层次的暴力拥有着天然的合法性、正当性。深入其间会发现,鹿三杀人动机是浸淫于封建忠君、红颜祸水思想中,所形成的无意识行为冲动,暗示着底层个体长期受到历史暴力,已然将意识层面的执行准则转化为横越普遍良知的公理,并为群体所认可的最高准则,袭扰着复仇与正义的现代性逻辑。
第二,鹿家先人发家史的暴力书写。在鹿家家史的叙述中,为实现“掌勺”梦想从而发家,鹿家先人以暧昧的性别身份,遭受既得利益者的蹂躏。当鹿家先人获得相应资本、地位后,受性暴力扭曲的内心支使他以暴力的方式加倍奉还。作者以同性暴虐的另类书写,揭示了历史血脉中,性与社会、国族间的混乱不公和精神阉割造成的焦虑;言说着在社会转型的废墟上,本能欲望与禁忌余威的错综复杂间,性别反串引起的性别角色错乱和性别自主权所面临的威胁。这种具有受内外双重压迫特征的献祭式行为所形成的性别症结,对中国现代性转向的表征体系俨然形成威胁,妨碍了欲望的正常生长、流通,与小说叙述者对鹿家难以启齿的扭曲、断裂家史及人格预言若合符节。
第三,冷秋月、鹿兆鹏婚姻的暴力书写。冷秋月原欲的被压抑与鹿氏兄弟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鹿兆鹏逃离包办婚姻自然有其合理性,但是,其追求自由恋爱,与弟弟所爱的白灵结合,其对鹿兆海、冷秋月的双重背叛,看似合乎五四传统叙事,却映衬出鹿兆鹏自私虚伪的人性阴暗面。这不得不让人思考文本所剥离出的如下命题:以鹿兆鹏为代表的保有新知优越感、歧视蒙昧大众、家庭角色缺位、文化脐带断裂的新青年群体,是否能如其所说,在乡土革命空间中,承担感时忧国历史使命的同时,克服自身局限,弥合觉醒理想与现实约束的鸿沟?所谓新知不应是部分知识精英阶级的专利乃至新型暴力工具,该如何实现大众传播,以应对历史暴力?革命正当性在历史洪流中,又该以何种姿态面对原乡文化?
同样,对于冷秋月而言,封建守贞伦理、蒙昧传统的规约与鹿子霖带有家长权威的情欲相交错,共同形成一种“全景敞视监狱”,压抑规训着冷秋月原欲资源的援引与分配——这种凝视被冷秋月的心理认知结构所框范整合,从而造成她生命最后阶段一种疯癫状态。同样,这不啻隐喻着一段缺失断裂的、无法言说的暴力经验——它拒绝认识、叙述和符号化,如梦魇般不断回归,直接作用于无意识层面,形成重复强制的表征模式,形成其内心深处的创伤经验,成为一种具有代表性的近代女性文明症候。
综上所述,《白鹿原》构筑的历史展台,有三种文学意义:
第一,对民族秘史进行发掘、再现。作者在“记史”的掩盖下,将正史转化为一种符号,突出民间历史的本来面目,重构本然存在的记恶想象;实现传统二元对立的既往历史叙述模式的超克,具备一种解构历史、重写历史的理性意识。这响应了市场化进程下,人们反思过往历史,阐释社会现实与文化状态的心理渴求。
第二,文体创造意识增强,对小说人物见解独到。作者注重探索特定历史时空中的命运与人性,深刻剖析、批判了人性暴力的无情;以现代视野进行再认识,重构个体历史话语。体现在文本时间和现实时间的复调书写中,知识分子身份转换带来的社会角色和文化功能边缘化、价值立场与话语体系破碎的焦虑。
第三,着眼于拟构一种具体真实的文化历史氛围。小说从更深层次突入历史现场,发掘现代化转型的错综复杂。呼应了九十年代主流意识形态、文化知识分子精英文化与大众文化间的复杂态势。同时,小说带有作者关于时代人文精神貶值、缺失的思考。文本从哲学高度关注人类生存历史及生命本源,深层体现作者的危机意识、反思意识—控诉社会与政治的不义,忧心群体的蒙昧与残酷。
总而言之,当历史的暴力成为个体日常生活看似正常的一部分,文学所虚构的幽暗而真实的层面才得以鲜活展现:在《白鹿原》这曲悲歌中,暴力的凄风冷雨,交相肆虐这个伤痕累累的历史展台。作者跳脱出此消彼长的一般历史行进规律,书写大言炎炎之下,芸芸众生的涕泗飘零。小说再现历史的罪与罚,反射人性的傲慢与偏见,探觅真善美灵根自植的柳暗花明。同时,暴力书写所产生的一种巨大文本张力,提供了烛照“现在”的有效可行的意义框架,奠定了作品苍凉悲壮的艺术基调,升华了小说作为“民族秘史”的文学意义。如此可畏,如此独特,这也许正是《白鹿原》的绝对价值所在。
注 释
[1]王德威.历史与怪兽:历史、暴力、叙事[M].麦田出版社,2011,p5.
[2]同[1].
[3]陶东风.奥斯维辛之后的诗——兼论策兰与阿多诺的文案[j].《文艺研究》,2020(12).
[4]孔飞力.叫魂:1768年中国妖术大恐慌[M].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上海三联书店,2014,p291.
[5]王德威.想象中国的方法:历史·小说·叙事[M]. 百花文艺出版社,2016,p135-13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