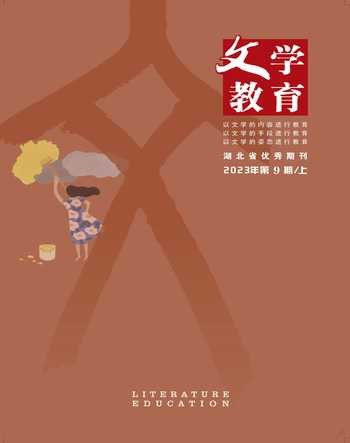阿来《云中记》的仪式书写探析
2023-09-01宁海雪
宁海雪
内容摘要:在《云中记》中,阿来保持一贯的民族文化自觉意识和文化反省意识,通过呈现一个藏族村落的山神祭祀、招魂仪式和净化仪式等形态,铺展出本教的祭祀仪式和嘉绒藏区的民风习俗,以文学的仪式书写修复地震幸存者的心理裂痕,民间话语与科学话语之间的文化裂痕,完成了震后精神重建。
关键词:阿来 《云中记》 仪式 震后精神重建
“仪式”是人类学的一个概念,自19世纪被作为一个分析的专门性词语以来,已为人们耳熟能详且频繁使用。但关于仪式的概念和界定,不同领域、不同时代的学者在各自的研究语境下,做出过各式各样的解释。早期人类学关于仪式的概念始终囿于神话与宗教,直至20世纪初,涂尔干将仪式概念扩至世俗社会,才打破了传统仪式研究过于狭窄的局限。20世纪中叶,仪式的内涵越来越宽泛,维克多·特纳认为仪式“指的是人们在不运用技术程序,而求助于对神秘力量的信仰的场合时的规定性正式行为”[1]23,并指出象征符号是仪式的最小单位,克里福德·格尔茨则认为仪式是意义模式和社会互动形式,强调社会变迁对仪式的影响。但对“仪式”的界定主要集中在文化属性、象征符号、社会行为三个方面,借当代人类学家约翰·费斯克的话来说,“仪式就是组织化的象征活动与典礼活动,用以界定和表现特殊的时刻、事件或变化所包含的社会与文化意味。”[2]243它既可以是某族群内的神圣献祭活动,也包含大众之间的世俗人际交往,还贯穿着个体生命历程的每个阶段。人类需要仪式,个人需要通过仪式行为来融入社会环境,实现成长的过渡与转变,族群需要举行仪式以凝聚情感,强化认同,区分“我群”与“他群”。
2008年发生的“5·12汶川地震”,其震中地汶川县恰好在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即阿来所在的自治州。汶川地震十周年之际,阿来写下《云中记》以兹纪念,该部作品于2018年10月完稿,2019年4月出版,但阿来写这场灾难的想法从灾难发生时便有了,酝酿十年,终于面世。不同于此前的汶川地震文学书写,阿来在《云中记》中凸显了宗教神性,通过一个藏族村落——云中村,最后一个祭师回乡祭祀山神和抚慰鬼魂完成了震后精神重建。在这部作品中,阿来保持一贯的民族文化自觉和文化反省意识,将本教的祭祀仪式和嘉绒藏区的民风习俗交织铺展,以文学的仪式书写修复地震幸存者的心理裂痕,民间话语与科学话语之间的文化裂痕。该书发表后获中宣部精神文明建设“五个一工程”奖,并拿下多个奖项的年度最佳长篇小说。本文聚焦于《云中记》的仪式形态、过程和功能,结合宗教文化、地域特性与作家的文化观,探析阿来如何通过仪式书写完成了震后精神重建。
一.人与自然的神圣对话:祭山
阿来在一次访谈中提到:“我出身的族群中有种古老的崇拜体系,是前佛教的信仰……这种信仰与纯粹的宗教不同之处在于,后者需要的只是顺从,而前者却能激发凡人身上潜在的英雄品质。”[3]阿来在此谈到的前佛教信仰实际就是藏族最古老的宗教:本教,在公元7世纪以前,即佛教传入藏区之前,藏民普遍信仰的宗教。本教在万物有灵的基础上构建了“上部神之地、下部水神之地,中间人之地”[4]的三界宇宙观,即天上、地上、水里的三维空间,是人类早期与自然和宇宙等外部力量积极互动的印证。
祭山神是本教原始祭祀活动之一,而煨桑,也称烟祭,是山神祭祀最主要、最便捷的仪式,煨桑既有净化、驱除污秽之目的,亦有达神、迎神之意。《云中记》的山神祭祀方式主要采取的便是煨桑仪式。主人公阿巴祭祀山神的日子是回村后的第七天——地震发生那年所定下的山神节举行时间:5月15日。这个祭祀时间在农耕区的云中村是根据庄稼生长情况而定,但5月15日在虔诚的藏民心中有着特殊意义。藏历5月15日是“世界焚香日”[5],这一天藏族人民在各大寺院、山间河流、田间地头焚香祭神,因此文中把祭山神的日子定在5月15日有其偶然性和特殊性。当天早上八点钟,阿巴就穿上了祭师的全套行头,带着两匹马托着祭祀用品上山了。上山前到云中村的神树前对着空荡荡的村子摇铃击鼓,告知这一项事关全村人的神圣活动。阿巴在山神前架起火堆,绕着火堆一边迈动着祭山神的舞步,一边击鼓摇铃,并不断往火堆加入含有芳香气味的杉树和柏树枝,燃烧起来的青烟源源不断,直至变成一根烟柱直达上天。
“阿吾塔毗闻到桑烟里柏树和杉树的香气了。阿巴且歌且舞,往火堆里投入糌粑,青稞……现在,烟雾里又携带了云中村庄稼的香气,飘到了天上。阿吾塔毗闻到云中村糌粑和麦子的香气了。烟柱扶摇直上,连接了天与地,连接了神与人,阿吾塔毗和他的子孙可以互相感知了。阿吾塔毗应该下界来了,此刻应该在他的后世的子孙们中间了。”[6]161-162本教的煨桑仪式选择柏树和杉树等易于采集且带有香味的植物,燃烧这类植物不仅有净化场地的作用,而且燃烧产生的香气融入青烟,一同直上,以此愉悦神灵、供奉神灵。同时,人们也可通过烟柱将美好祈愿带给神灵,求取护佑。在火堆燃烧中撒以糌粑和谷物亦是对神灵的一种供奉,神灵顺着青烟在人们的欢呼声中降临,享受供奉,示泽众生。
祭祀山神除举行煨桑仪式外,最重要的是向山神献马献箭,马非真马,而是本教牲祭改造后采用的纸马,箭非真箭,而是旗旛。小說中写到,阿巴在回来的当天晚上去宗教用品商店备好了献给山神的“马”和属于本教的旛。在祭祀山神当天,他把纸马奋力上抛,呼喊着“胜利了!胜利了!”[6]165又在祭台插上箭杆,杆上彩旗迎风招展。这一切都在重演云中村来历的故事,重演祖先阿吾塔毗战胜土著矮脚人的神话,而将纸马洒向天空,任其在风中飞翔,是胜利的象征,扛着旗幡奔跑啸叫,是为迎敌冲锋助威。薛艺兵在阐述仪式的虚拟性特征时提到“大凡与信仰有关的仪式表演,并不是对现实世界的摹拟,而是对神秘世界的虚拟。表演神话的仪式,正是将无形的(语言的)神秘传说拟化为有形的神秘世界的一个过程。”[7]这场祭山神仪式表演无疑便是对神话中阿吾塔毗战胜矮脚人斗争场面的模仿,它创设了一场先祖披荆斩棘开创伟业的情境,在虚拟的神话世界中表达对英雄阿吾塔毗的追思与感恩。
阿巴在现实与回忆的混杂中完成了一个人的山神祭祀,还原了以往祭祀山神的热闹场景。在阿巴的回忆里,云中村的男女老少都沉浸在这一欢乐、神圣的氛围里,此时他们都是山神阿吾塔毗的子孙。社会学家欧文·戈夫曼认为,个体的自我是一种嵌入在具体情境中的自我,具有特定的社会特征,并被赋予神圣属性,建立在此基础上的互动仪式和道德秩序是社会生活的重要构成。云中村的山神祭祀实际就是一场互动仪式,云中村人沉浸在祭祀的狂欢中,积极地与创业先祖进行一次神圣互动。这种族群内的互动仪式连接了整个族群,具有神圣性和集体性,能够唤醒集体记忆,凝聚集体情感。云中村人地震后搬迁到移民村,他们不得不在他乡落地生根,被迫接纳他乡文化,淡化过往生活。因此,村民所说的身上已没有云中村的气味,正暗含着村民们过往的生活正日渐远去,云中村人的身份意识逐渐淡化,族群文化走向衰落,他们所需要的正是身份认同感和文化归属感来消解在他乡的不安。祭祀山神是为了强调村民们曾经来自同一个村落,有着同一个祖先,守着最原始的本教信仰,纵然无法改变他乡变故乡,故乡葬岷江的事实,但真正的消失不是从世界上而是从记忆里消失,故而在活着的云中村人心里,记得自己,记得阿巴,那么云中村便一直存在。
二.生命尽头的终极抚慰:招魂
藏族有灵魂崇拜习俗,这仍与本教的“万物有灵论”有关。本教不相信来世和转生,它的灵魂观是“靈魂体外寄存”,认为人无论是活着亦或死去,其魂魄会离开躯体,在空中飘荡或寄魂于动植物等物体,为了使即将离开躯体或已经游离在外的魂魄回归躯体,“与其本原和寿命聚合。”[8]165招魂则有了必要。
藏族的招魂仪式分为两种:为患者招魂和为死者招魂。其中为死者招魂又分非正常死亡和正常死亡。为非正常死亡者招魂称“伏”:“一种为非正常死亡者进行的丧葬祭祀仪式”。[9]地震属于意外的自然灾害,是不可预测之灾难,因而葬身地震的人属于非自然死亡,在云中村的观念里,这些非自然死亡者其魂魄仍在村里飘荡。地震发生后村民们纷纷表示听到了鬼魂的哭声,看见了鬼魂的影子,苦苦哀求阿巴安抚亡灵,只会祭祀山神的阿巴特地跑到一位老喇嘛那里学习如何招魂。而当云中村活着的人已经迁到移民村,这座坐落在山腰的村庄已是一片荒芜,荒芜之地,鬼魂无依。活着的人归政府管,死去的人归祭师管。来自祭师世家的阿巴,其职责是侍奉神灵和抚慰鬼魂,为此,阿巴返乡除了祭祀山神,还背负着抚慰鬼魂的使命:对逝者再一次进行招魂,让死去的人得到安宁,让活着的人好好活着。
回乡后的第四天,即五年前地震发生的时间,阿巴在下午两点五十分,即地震结束的时刻,开始进行招魂。他穿着祭师服,舞着青烟腾腾的香炉,摇铃击鼓,抛撒粮食,一家挨着一家地呼喊着;“回来,回来!”[6]103回顾每一户村民的生平过往和地震当天的惨死状况,那些死去的村民在阿巴脑海里活过来了,在阿巴的一声声呼唤中得到安抚。从白天到黑夜,从黑夜到黎明,阿巴走完了三十六户人家,疲惫得睡了一天。在远古时期,巫术和医术是合为一体的,从这个意义而言,阿巴充当的是医师角色,而招魂仪式实际为一种心理疗法。祭师通过诸如熏香、施食、喊魂等一系列行为,达到与鬼神交流,为活人禳灾之目的,较之药物治疗,这种心理疗法更适合消解死亡的恐惧,安抚生者的情绪。
因秉持着“灵魂体外寄存”观念,藏民认为寄魂物会产生超自然的力量,从而形成了对寄魂物膜拜则会获取保佑,不敬则会遭遇惩罚的寄魂物崇拜,如《空山》中机村人认为是神灵金野鸭保佑着机村风调雨顺,兔子弟弟抽搐着说胡话是因践踏风信子被花妖迷惑。因此,寄魂物一旦呈现濒死之态,祭师也会对其进行招魂。在《云中记》中,寄魂物为村前的老柏树,村民称之为神树,地震前一年,树神已生衰老垂死之相。为此,阿巴展开了各种招魂仪式挽留神树。他曾盘腿唱起了悲怆的古歌,努力祈祷树神继续活下去;亦在树前摆开香案,摇铃击鼓,向东、向西舞出金刚步,浑身解数以挽留树神;继而又在树下磕头撒酒,虔心请求树神不要离开。然树神去意已决,阿巴无奈拾起树皮和枯叶,在祭祀山神的祭台焚烧,让树神化身青烟与山神交谈,希冀山神能让树神回心转意。
这种对植物人格化并对其进行招魂的行为,不仅是藏民“灵魂体外寄存”观的体现,亦蕴含了藏民朴素的自然观,平等对待自然界的动植物,细心呵护每一个生灵,由此树立了保护自然环境的生态意识。但无论是安抚鬼魂亦或崇拜寄魂物,体现的是藏民对灵魂的虔诚与慎重,而灵魂事关生命,因此,招魂的终极指向仍是敬畏生命。故而,招魂乃是一场生命尽头的终极抚慰。
三.世俗生活中的至纯至洁:净化
洁净是一种健康卫生的生活方式,也是一种虔诚的象征。人类从出生的“洗礼”,成年的“割礼”到死亡的“净身入殓”,无不体现着从身到心的洁净追求。在民俗学家范热内普看来,这些净化仪式属于是分隔和聚合之间的一种过渡仪式,只有经过净化之后,人才能从原来的状态分隔出来,进入到新的阶段。如我国旧俗中婴儿在出生的第三天需举行“洗三礼”,一则祈愿母子平安健康,二则意味着婴儿从母亲身体里分隔出来,成为独立个体;又如藏族女子成人礼要举行“戴天头”仪式,在仪式中需洒净水和以水蒸气熏洗全身,以洁身清垢,驱除邪念。宗教对洁净的追求更为极致,不仅将各种净化仪式生活化,融于教徒的世俗生活中,而且直接将身体的洁净上升至灵魂的洁净,伊斯兰教就规定穆斯林男子在11岁之前必须完成“割礼”仪式,否则不能做礼拜,因为这会影响对到信仰的虔诚,基督教也会对新教徒举行侵礼。
受宗教文化影响,藏民追求空间和灵魂的圣洁,即便是在日常生活中,也会设置诸多禁忌,以避免因不洁行为惹怒神灵,招致灾祸。为了保持洁净,藏民常常采用净化仪式驱除妖魔,消除污秽。前文所提的“煨桑”,亦为净化仪式之一。《格阔除污桑祭文》中追溯“煨桑”的起源神话,其中便记载了象雄初期的本教徒们,砍下芳香植物的叶子供净化之用,焚烧生烟消除贪念之毒,《神桑供赎大祷文》中甚至直接写道:“‘桑能净化万物!”《云中记》中所写的“煨桑”净化作用,更多体现在云中村人的日常生活中。阿巴遭遇泥石流滑坡之后,失忆十年,母亲认为阿巴的脑子陷入混沌,点燃了父亲遗留下的熏香炉,尝试以柏树香气驱除污秽,唤醒阿巴。此外,母亲也会用香烟熏水壶,以保持水的洁净,阿巴正是听着壶中泉水荡漾的声音而顿时神清气爽。这均是藏民在日常中熏香净晦的行为,古老的传统使他们相信“煨桑”所产生的烟雾既洁净可见之杂质,亦净化不可见之污秽。
水的净化作用也是不言而喻的。“净”在字形上从水从争,意为水能洗除尘垢,洗涤时与尘垢互相争斗。藏区有着高山雪域造就的天然湖泊,藏民自然不会忽略水的净化作用,其古老的净水仪式早已融入日常生活。时至今日,净水仪式虽已简化,但其基本形式未变,《云中记》所写的柳枝净身可资为例。阿巴曾在溪边用柳枝蘸上溪水,浑身上下抽打,特地提到这是云中村老辈人的习惯,认为用这种方式可以抽打掉尘土和看不见的邪崇。小说中写到的另一种净化仪式更能体现水的净化作用。阿巴恢复记忆后仍浑浑噩噩,村里唯一的喇嘛让阿巴看着铜盆里的泉水,用眼睛和心盯住水,在波纹的激荡中阿巴越发清醒,最后一次喇嘛直接将泉水倾倒在阿巴头上,彻底治愈了阿巴的受灾后遗症。这种净化仪式实质是以至洁的泉水清除杂念,洗涤心灵以及治愈疾病。无独有偶,阿来在中篇小说《遥远的温泉》中借贡波斯甲之口,道出了泉水不仅能把不光鲜的皮肤洗得光鲜,还能治愈眼病、偏头痛、风湿症等疾病,乃至人只需在温泉水里一洗,从里到外就干干净净了。
这些诸如煨桑、柳枝抽身、泉水疗愈等净化仪式,其共同之处是追求精神层面的洁净,这与藏民保持灵魂纯洁的“洁净观”密切相关。细究这些净化仪式则会发现,熏香使人心神安宁,柳枝抽身能够驱逐邪魅,泉水疗愈是为平静心灵,每一项净化仪式均被生活化,无不彰显着藏民在世俗生活中对极致纯洁的追求。
四.文学仪式书写与现实精神重建
在一定意义上,自然灾害的发生没有冲突双方,受害者没有明确的埋怨和指责对象,心理创伤最终只能自我疗愈,疗法常指向宗教信仰和世俗文化,而作为宗教信仰具象化、世俗生活规范化的仪式便发揮了不可替代的作用。仪式能够唤醒和引导人类各种强烈情感,充分发挥仪式的调解、凝聚、塑造和教育等功能,能够有效化解精神危机,维护社会秩序。人类学自诞生起,就已注意到仪式,仪式研究的成果不胜枚举。就仪式理论而言,笔者认为格尔茨关于仪式的论述颇为适宜诠释《云中记》的仪式书写。格尔茨认为,在仪式中,生存世界与想象世界借助一套符号体系混合起来,变成相同的世界,而宗教仪式“一方面是有情绪和动机,另一方面是形而上的概念”[10]138,两者缠绕在一起,形成了一个民族的精神意识。《云中记》所写的山神祭祀便是通过煨桑所产生的青烟、带有宗教寓意的纸马与旗幡等象征符号,连接了云中村的现实世界和神话世界,在真实与虚拟的交织中创设了一场人神同乐的情境。同时,在宗教信仰的驱使下,宗教意识渗透到藏族日常生活而产生的各种仪式,诸如招魂仪式、净化仪式等,更是蕴含着藏民的敬畏生命、追求纯洁的生活观和万物皆有灵的世界观,形成了独特的民族文化和民族精神。
格尔茨亦不单重视仪式的意义,更是将仪式置于社会互动中进行分析,重视社会变迁对仪式的影响,这和阿来书写现代文明冲击藏族传统文化的内容是不谋而合的。在社会变迁进程中,大量的象征符号、传统信仰遭到摧毁、瓦解,古老的仪式正在不可避免地走向简化、衰落甚至消亡,阿来十分清楚无论是个体、族群还是族群文化终将会消逝,正如陈晓明所说“他处理的历史或现实,都隐含着一个消逝的地域及其文化的主题。”[11]但在《云中记》中,阿来并没有刻意惋惜一个村庄的消亡,也没有对逐渐失去信仰的人们严加指责,反而是坚定地“要写出生命的庄严,写出人类精神的崇高与伟大”[3]。或许自然的无妄之灾加诸于人类本就令人哀恸不已,灾难文学创作更为紧要的任务是精神重建。
事实上,阿来的确承担起了灾后精神重建的职责。不同于此前地震文学铺天盖地的煽情和无暇打磨的清浅,阿来是通过祭师阿巴的记忆呈现云中村的诞生、分化、变动和消失过程,挖掘出仪式的文化价值和精神价值,以乐章式的结构,颂歌般的语言谱写一曲人文赞歌,完成一场精神抚慰。这曲赞歌的内容是向死而生的勇气、人与人之间的情谊,人与自然的相互理解,这场精神抚慰的对象不是亡灵,而是生者,目的是希望能够安抚地震幸存者的痛苦与不安,颇有斯人已逝,生者如斯的用意。在这个意义上,阿来的写作实际也是一场仪式化过程,他参与过汶川地震的救援活动,目睹苦难在大地上肆虐人民,这种创痛一直深埋于心。直至汶川地震十周年的号笛响起,阿来泪流满面,终于提笔书写这场灾难,伴随着莫扎特《安魂曲》庄重而悲悯的吟唱,将内心沉积的情感释放于文字。在书写过程中,他回顾着埋在泥土的死者,随泥沙消失的村落,随村落消亡的文化,他同祭师阿巴一起承担起传承文化、祭祀亡灵、抚慰生者的责任,一同完成了这场灾后精神重建,读者无论是从小说情节中还是阿来的创作意识里都能感受到庄重、神圣的仪式感。
当然,作为一个有着深刻的民族文化自觉和文化反省意识的作家,阿来并不止于仪式书写,而是一如既往地深入民族文化问题,他的作品常含着强烈的文化自觉意识和文化反省意识。在《空山》中,面对现代化进程中传统文化被破坏、道德防线被摧毁的现状,阿来开出药方是求法于古老的民族文化和民间文化,试图挖掘原始人民的家园意识和底层人民的美好品性弥补现代人的精神缺失,在和而不同的民族性下寻求文化认同和文化归属,谋求文化多元化发展。在《云中记》中,阿来延续了他的文化观,文中虽然不时谈到本教与佛教之分化、汉族与藏族文化之差异、民间话语与科学话语之纷争,但细读可发现,阿来并没有刻意强化它们之间的对立,而是写宗教之间互相融通、文化之间互相影响、立场之间互相尊重,充分认识到了文化只有在交融中方能维持其生命力。这样的文化观使得阿来虽以藏族为书写对象却不拘于狭隘的民族主义观念,既彰显了民族性,又连接了世界性,对当前的民族文化发展和输出极具启发性。
仪式与文学中对于人的精神世界的呈现有着天然的契合,尤其是宗教仪式的神圣性能够直接触及人的精神层面,在文学创作中融入仪式书写不单是为文本内容增色,更为重要的是在文本之外能够建构起某个群体的精神支柱。对于汶川地震的文学书写,阿来清醒地认识到触景生情很正常,悲天呼号无价值,他所关心的是精神重建。因此他把笔触伸向宗教仪式,铺展出了一个族群纷繁多元的仪式景观,唤醒人们深厚的宗教情怀和家园之思,为流散他乡的同胞找到心灵归宿。这是阿来的境界,是对灾难文学的突破,也是仪式书写的典范。
参考文献
[1]维克多·特纳.象征之林[M].赵玉燕,欧阳敏,徐洪峰,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1.
[2]约翰·费斯克等.关键概念:传播与文化研究辞典[M].李彬,译.北京:新华出版社,2004.
[3]阿来.关于《云中记》,谈谈语言[J].扬子江评论,2019(6):5-8.
[4]阿旺嘉措,才让扎西.从敦煌文献看苯教宇宙观的形成及演变[J].中国藏学,2022(2):52-62.
[5]恰白·次旦平措,达瓦次仁.论藏族的焚香祭神习俗[J].中国藏学,1989(4):40-49.
[6]阿来.云中记[M].北京:北京十月文艺出版,2019.
[7]薛艺兵.对仪式现象的人类学解释(上)[J].广西民族研究,2003(02):26-33.
[8]曲杰·南卡诺布.苯教与西藏神话的起源:“仲”、“德乌”、“苯”[M].向红笳,才让太,译.北京:中国藏学出版社,2014.
[9]桑杰端智.浅谈藏族招魂仪式[J].青海民族研究,1999(2):24-26.
[10]克利福德·格尔茨.文化的解释[M].韩莉,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14.
[11]陈晓明.阿来长篇小说《云中记》:文学的通透之境[N].文艺报,2019-06-1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