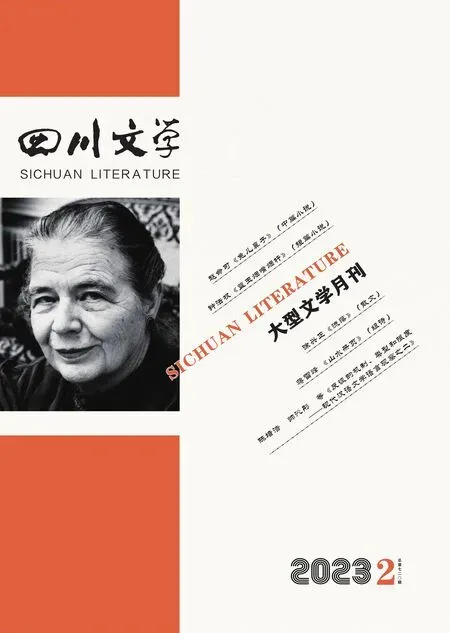我的小说语言观
2023-09-01房伟
□文/房伟
大学毕业之前,我算是个“文学青年”,写诗,也写小说,也只是胡乱摸索。大学毕业后,我在国企工作过5年,文学阅读在继续,创作搞得不多,写的文字大多是公文和新闻稿件。后来,我去读研究生、博士,基本变成了一个文学研究者和文学批评从业者。这种状态,一直持续到我留在高校任教,评上教授为止。作为一个“文学中年”,我重新拾起少年时的梦想,在相对放松状态下,继续创作小说。
从创作体验出发的小说语言观,和从研究角度出发的小说语言观,有着很多差异性,也有很多共通性。大体而言,我认为,一个在小说语言上没有追求的作家,不会是一个“真正成功”的作家。小说语言,会在故事之外,赋予小说更多“附加值”。故事讲述的时代过去了,激动同时代人的记忆、概念、术语和情感体验也已过去了,然而,高度艺术化的小说语言,能将这些东西放在艺术坩埚中熬煮,锻打出更浓缩与精粹的形式,将逝去的人类思想与情感,提升为某种人类共通经验,不断产生精神共鸣。于是,经受不断的“重读”,犹如经受时间海水对建筑物的冲刷,最终留下的,才是经典的东西。
小说语言问题,在于是否能通过“有效的艺术语言”,将读者代入某种特殊小说情境,并与作者所呈现出来的故事、人物、情感,产生深度共鸣。一个作家的语言有时会随着心境、身体、年龄等情况的变化而变化,但某种核心东西,一旦形成,也不会轻易改变。其实很多作家的语言,并没有特点。“好的语言千差万别,坏的语言却有迹可循”。他们的小说语言,大多只是讲述故事,给读者最深的印象,也是故事情节,而真正形成独特的艺术语言,是一个小说家成熟的标志,也是其辨识度的标志之一。
一个好的小说家,有一种对语言的天然敏感,也最好有些训练。写小说初期,要向名家学习,认真揣摩。比如,有的作家更注重小说语言修辞训练,比如,钱钟书的《围城》有很多精彩比喻,“老实人的恶毒,像饭粒的砂砾或者出骨鱼片里未净的刺,给人一种不期待的伤痛。”这是通过比喻说理,讲出某种不为人注意的道理,另一个例子,“她(唐晓芙)眼睛并不顶大,可是灵活温柔,反衬得许多女人的大眼睛只像政治家讲的大话,大而无当”,将这种理性态度,融合到对人物的描写,形象生动之余,兼具讽刺效果。
开笔写小说,最好也进行诗歌练习,或保持对诗歌的敏感。诗歌的好处,一是锻炼语言的简洁生动,二是锻造语言形象性和直观性,三是容易形成对细节的把握。我们看毕飞宇的小说语言,就有很强的诗性,且这种诗性,还形成了语言形象化,比如,小说《白夜》,他形容晚上看到的玻璃:“这些玻璃比白夜要黑,比黑夜要白”,他形容躲在棉花垛偷情的男女,他们眼中的星星“都像棉朵般地燃烧着”。又比如,张炜写诗,也写小说,很多细节令人过目不忘。他形容一只鹅的头部:“大兵的额头红肿肿的,像小孩的脚后跟”。莫言虽然不写诗,但小说语言汪洋恣肆,在感觉运用上,有着炉火纯青的表现。当然,诗写太多,也会对小说语言形成妨碍,主要是诗歌语言是跳跃的、晦涩的,且也是间接的,比如太喜欢象征和隐喻,这就会忽略小说语言最重要的品质,即准确性。
在我看来,小说的语言锻炼,更接近科学的训练、智性的思维,而不是纯粹感情思维。它也有象征与隐喻性,但在基本层面会服从准确性。鲁迅的小说语言,有着冷峻简洁的风格,让我们印象最深刻的,还是他的准确性。这也许得益于他的医学训练。这种准确性语言标准,在诗与散文之中也是有的,都不及小说文体的要求高。小说要讲故事,只有准确性才能让读者信赖你提供的真实。这种真实性,也是作品感动人、感染人,让读者沉浸某种代入性氛围的基础。批评家谢有顺曾说:“但凡大作家写的生活,往往是可以被还原的,这种还原性就为小说的真实感提供了值得信任的依据,信任是小说和读者之间不可或缺的契约。”这种准确性,不仅在于描写人物的行动与内心,叙述故事过程,更在于塑造典型环境,打造典型细节,大家都熟悉的,就有《故乡》中闰土那一声“老爷”的描述。
当然,准确性还有内在一层意思,即丰富性。丰富性与准确性,表面上看,似一对冤家对头,实际起到相辅相成作用,类似一体两面,准确性让我们对事物状态有了清晰认知,这种准确性背后,又包含丰富的言下之意和无尽生命体验。例如,鲁迅小说《祝福》那段脍炙人口的描写:“五年前的花白的头发,即今已经全白,全不像四十上下的人;脸上瘦削不堪,黄中带黑,而且消尽了先前悲哀的神色,仿佛是木刻似的;只有那眼珠间或一轮,还可以表示她是一个活物。她一手提着竹篮。内中一个破碗,空的;一手拄着一支比她更长的竹竿,下端开了裂:她分明已经纯乎是一个乞丐了。”这里的语言,就是准确又丰富的。“木刻般的眼”犹如医学眼光般精准,写出祥林嫂的麻木,“间或一轮”则在死气沉沉的眼中,突兀施加动作,以动衬托静,以活写死,更有一种在死与活之间挣扎的惊心动魄的恐怖感。祥林嫂的装扮,也极有深意。“空的破碗”可见乞食生活的困苦,“比她还长的竹竿”则形成视角的对比,“下端开裂”更显小说语言准确性力量,凸显祥林嫂的生活窘迫。“开裂”的原因很多,走的路太多,竹竿可以开裂;用它来赶走野狗,也可以开裂。而“开裂的竹竿”,更能形成视觉的隐喻性——竹如其人,祥林嫂就是强撑着的竹竿,已是强弩之末而已。这些精准描述背后,是鲁迅对极度苦难的人类精神面貌的感受。这便是没有说出的言下之意,包含丰富复杂的情感,如痛惜、同情、愤怒和感同身受的绝望……
另外,小说语言的准确性与丰富性,也与旋律性相联系。好的小说语言还要有旋律性,也就是内在音乐性。王小波曾言:“文学是用来读的,而不是用来看的,看起来黑鸦鸦的一片,读起来就大不相同。”这种对于旋律性的追求,不仅给读者听觉上的享受,也扩大了小说间接的审美感受,这种内在旋律性,也不仅是故事层面的“听”,更是内在生命体验的集中性爆发,它改变线性的小说故事结构,将小说变成一种情绪、思想的艺术结晶的产物,例如,昆德拉的《生命不可承受之轻》,茨威格的《一封陌生女人的来信》,杜拉斯的《情人》,卡尔维诺的《树上的男爵》等,都有这种特点。
语言形成风格,是一件好事,因为有了鲜明辨识度,然而,风格太过固定,也会让读者和作家产生审美疲劳。读者的疲劳,在于没有了新鲜阅读期待;作家的疲劳,在于写作惯性包裹着他,让他顺着既定轨迹,顺畅又没阻碍和难度地前进,失去了那种新鲜勇猛的力量,流于某种“情调化”。这种语言风格的束缚,在以中短篇见长的小说家身上尤为突出。中短篇小说更看重语言审美特质,要在较短篇之内吸引读者,除了别出心裁的脑洞、新鲜的题材之外,还要有新颖别致的表述。现代小说发展到成熟的一个外在表现,就在于中短篇小说高度形式化,叙事压倒描写,甚至深度侵蚀了描写,将描写的视觉功能和信息功能,简化、压缩、融合到叙事,在更短篇幅内,给读者更强烈冲击。它们像一个个精美陶瓮,更复杂也更让人沉迷,充满超越故事层面的、神秘的生命体验性,比如,海明威的电报体写作。另外有些作家,将描写发展到繁复至极的地步,这种描写不是一种认知的知识层面功能,而具有高度凝练的象征性,比如,王安忆的《长恨歌》,繁复不仅形成了风格,且具有了恢宏的史诗体量长度。中短篇创作之中,有些作家也刻意强化描写功能,比如,安吉拉卡特具有哥特风格的小说《烟火》。还有舒尔茨的《鳄鱼街》这样具有强烈现代派绘画风格的荒诞小说。这种描写大多具有限制性视角,不管第三人称叙事,还是第一人称叙事,这种描写能在较短篇幅内,展现出对于世界的某种隐喻态度。它的故事性被压缩,描写成了有限性风景的一部分,这种中短篇的语言,本质也近乎诗歌了。
另外,对于通俗小说而言,语言问题是否同样重要?金庸的小说语言,简洁生动,法度严谨,有史传传统的影响,梁羽生温文尔雅,吟风弄月,有诗文传统之风,古龙的小说语言,则充分吸收意识流等西方现代小说特质,温瑞安更像金庸和古龙“融合加强版”,却多了天马行空的想象力。再将时代背景向上推,民国时期孙了红的“侠盗鲁平”系列小说,至今读来依然津津有味,给大家印象深刻的,不仅是精彩故事,且是作家充满爆发力的语言。李渔曾说过:“雅俗同欢,智愚同赏”,通俗小说要成为经典,也要在语言下一番功夫。有些批评家认为,那是过时的纸媒阅读规范,网络小说不必遵守,或者说超越过去了。网络文学不需要“经典”这类纸媒艺术的“特权话语”。这是简单的看法。文字披上层“网络”马甲,情感、思想与外在形态,当然会发生变化,但如果想继续流传下去,依然要遵守艺术规则,只不过网络时代的艺术规则,其经典标准尚未确立,尚在摸索之中,而不是说不需要艺术提升。不能说,纸媒艺术精品,和刻在竹简上的好文字,完全无法“理解”,也无法在经典化层面沟通。这是“媒介决定论”的观点,也要引起人们的反思。
总而言之,还是那句话,“好的小说语言千差万别”。语言是一种态度、一种观念,也是一种美学理念的显现。一个作家可以在小说中形成稳定的语言风格、表述习惯,也可以在不同小说中,有不同的语言。我在创作上就是“喜新厌旧”之人,从不喜欢将自己固定于某种特别的“腔调”与“程式”。不同作家的作品,也会出现同质化语言形态接近的情况。小说语言可以磨炼与训练,但归根结底,还是其特殊艺术气质和思想的产物。有的小说家语言刚劲有力,有的则温温吞吞,绵里藏针。这无所谓“好坏”问题,关键还在于小说语言的艺术化程度与内在的丰富性。汪曾祺曾说过,“好的小说语言,犹如树上长的树叶,风吹大树,树叶也会随风摇摆”。汪曾祺的小说,是散文化的,也有着生活化的体验。他的小说语言观,就体现那种自然随意,又充满生命意识的艺术结构心理。有时候,一个好的作家,可能看不上另一个好作家的作品,语言也是重要原因。王小波不喜欢张爱玲。冯骥才也批评过鲁迅。作家比一般人更敏感,更能感受作品背后所郁结的情感和思想,也就愈发对其外在艺术形式,充满了“不可调和性”。这种东西,对批评家而言,是不好的,它会让你的口味流于偏狭,但对于作家而言,却又是好的,这说明你的艺术感觉足够敏锐,你的小说语言也有着足够的辨识度和艺术特质。
当然,现在越来越多的作家,不再追求小说的准确性、丰富性与旋律性,而简单地让小说语言服务于故事的需要,服务于营销的需要。“小说的语言,正在变成一种完全的表象”。这种真实的空心化、语言的表象化,不仅是小说过度商品化的悲哀,也正在成为一种确定的“虚拟真实”——现代人的心灵逐渐粗糙,更多被虚拟体验与物化感受所支配。小说语言文学性的退化,也表现出作家们描写语言能力的退化,风景描写的消失,立体人物变成扁平苍白人物,小说缺少令人过目不忘的细节,很少有作家花大工夫打造语言准确性,苦心孤诣地追求语言丰富性与旋律性。如何在后现代化与网络体验化“后人类社会”追求小说语言艺术性,这关乎小说艺术生死存亡,也关乎印刷阅读的文学经典体验转型问题。这种激烈的转变,无论更好,还是更坏,也许都出乎我们意料,也都是人类命运的一部分。作为一个小说作家,我们能做到的,只有保持永不停息的好奇心与天真的热情、朴素的真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