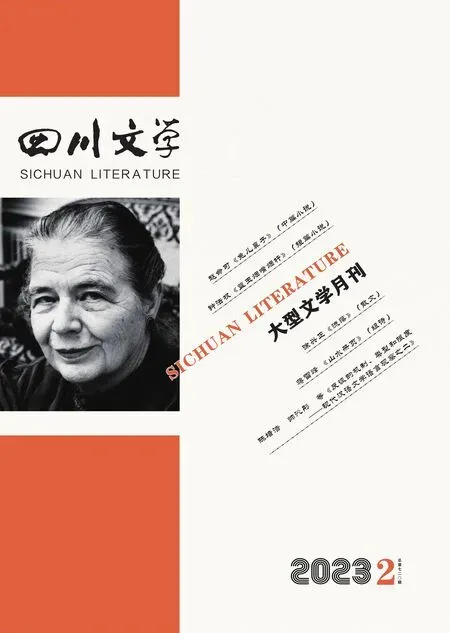深巷
2023-09-01杨艳萍
□文/杨艳萍
父亲早就盯上了那块荒芜已久的土地。挨着四妹儿家的后花园,这块地应该会非常自卑。后花园里杏树、樱桃、大丽菊、十三太保、栀子花……一个个昂首挺胸,青枝绿叶。那块地的营养充足,那些树啊、花的每天都吃饱喝足,挺着肚子,偶尔还伸展一下腰肢。这块地除了杂草还是杂草,蔫不拉几。
父亲似乎有许多我不知道的潜能。1981年春天,他用草、灰、木头和为数不多的几块砖,大多数时间一个人在那块荒地上折腾,大半年后,竟起了一幢二柱四的房子。之前我们家住在黑漆漆的巷子里。和一大家人一起住了有好几十年,父亲应该早习惯了巷子的黑。但从巷子里分出来,和四妹儿家并排着,却是父亲一直想做的事。很久以来,我都不知道自己一直想做的事情是什么。在一片荒芜的土地上,我没有信心能种出一棵像四妹儿家那样的树,更不要说种出一幢房子。我也像那块地上的杂草,该怎么长,就怎么长。我还太小。父亲正年轻气盛。
那棵樱桃树正好贴着新房的西墙根,我踩着吱呀的楼板,一伸手就可以摘到刚鼓包的青疙瘩樱桃。虽然离成熟还早,但我已经有些急不可耐。我的味蕾没太多见识,只要是和盐巴酱油不同的滋味都会让它喜不自禁忘乎所以。二楼的墙已经没有砖可以砌。父亲用竹篾做骨架,红泥和着土灰箍上去,几个太阳晒干了,也挺结实。巷子的二楼住的是大伯一家,我们一直住在低矮的楼下。我很少站这么高。一得意,把樱桃核使劲吐了出去。核落下去,砸了树下身材肥大的四眼黑狗。它本来趴在树下打盹,猛地跳起来,疯咬一阵。我差一点就跌下去。还好父亲筑的墙瓷实,我顶了一下墙往后退了几步,按了几下扑扑狂跳的心脏。那四眼狗凶得很,又肥又壮,咬一口,必然血肉模糊。
“人生下来就注定不一样,比如你和四妹儿。”父亲说这话的时候总是很焦虑,皱着眉,叹口气。说一次也就算了,隔三岔五就说,比我们思想品德课的老师还啰唆。我觉得父亲的焦虑有些多余。不一样是件非常自然的事,更何况,焦虑也没有什么鸟用。
我和四妹儿从同一条巷子进出各自的家。巷子向着街道的开间太窄。时间一长,一户分成三户,三户分成好几户。巷子是一根藤,往后面不断生长,两旁修修补补,今天加一个杂物间,明日起个小阁楼,再明日楼梯改个方向,雨棚再支出来一点,日子磨损一些物什,也生出一些新的需求。巷子越来越黑,也越来越挤。那是个万物复苏的年代,太阳特别的大,雨水也特充足,周围的巷子似乎也在生长,而且势头强劲,生怕过了这个村就没有这个店似的,到后来,不得不往空中生长。
那条巷子四妹儿走的时候和我走的时候都一样黑咕隆咚,并没有因为她父亲是工人就多一丝光亮。出了巷子,往左拐,五十米左右就是城厢第二小学,我们同一个年级同一个班,调皮的男生并没有因为我是农民的女儿就敢欺负我。倒是四妹儿,常会含着泪水来向我求助。我伸手去抓叉头扫帚的时候,那个牛高马大的男生已经转身往外跑。我从不虚张声势,对于敢欺负我们的人,我是一定会让他长记性。他们知道跑起来没多少人能比上我的速度,更何况我下手狠,再悍壮的男生我也能不要命地往前冲,扫帚、皮筋、跳绳,劳动用的锄头、铁锹都可以是我的武器,他们要是不认错求饶,我肯定不会罢手。四妹儿远远地看着,露出欣慰而解气的笑容。我是班长,学习好,体育好,爱劳动,又勇敢。这是我认为的不一样。年少的时候,谁又不是只肯相信自己。
那个不一样的自己留在了那里。很多年以后,我胆怯而柔弱,学会了低头,会习惯性地回头找那个不一样的自己。她一直在那里,无知且无畏。她让四妹儿站在身后,自己从高台上向台边的柳树扑过去,顺着被磨得光滑发亮的树干,旋转而下。“没什么害怕的,来啊,我接着你。”她抬起头喊高台上的四妹儿。她什么都不怕,但我把她留在了那里。
四妹儿是否也会像我一样常常想起那条黑咕隆咚的巷子,我没问过她。我们的一生都是从童年开始发芽。巷子种在我心里的是暗影,于她却可能是彩虹。
我们从学校回家后,都喜欢待在她的房间。房间是木头的板壁,她父亲还用旧书纸一张一张糊上去,缝对缝,十分端正。那些书纸上写满了各种各样的故事,我的眼睛随便往哪个方向一看,一些人物和事情便向我扑过来,古时的、现代的,黑人、白人,其他民族和国家的,甚至其他世界的,反正都不是我身边的,就装在这个屋子里,甚至天花板上。还能闻到一股墨香,就像她父亲的味道。她的父亲经常在旁边他自己的房间里写毛笔字。他的手指白晳而颀长,好像天生就是用来写字的。有时候,我怀疑,她和父亲是否真有相同的血脉?
坐在四妹儿房间的凉席上,我高声诵读课文,读得摇头晃脑。四妹儿正在吃番茄。我家的地里没有番茄。后来才知道它又叫西红柿。菜市偶尔会有。一个番茄能抵好几斤白菜。她吃得太细腻,在顶端咬一个小口,吧嗒着小嘴,将里面的汁一点点吸出来。每一次吸一小口,在嘴巴里回味一会儿才接着又吸一口。呼哧哧的声音,打扰了我读书。我不会吃番茄,我不喜欢那个味。但番茄绯红的色彩透着亮光,和我见过的所有蔬菜水果都不一样,很是诱人。那颜色像是会顺着她的手流下来,把整个房间都染红。“春天来了,燕子从南方飞回来了……”我不该想入非非,低下头又继续大声地读书。他父亲从门外探头看了我一眼,笑着夸我读书很用功。
新家和四妹儿家已经肩并着肩了,但可能她家的房檐要靠向东边一点,支出去的檐口正好挡住了几缕阳光,春天才会先到她家转一圈然后才能拖着尾巴到我家来看一眼。也可能阳光也会分一个先来后到吧,毕竟,她家的房子是祖上留下的,就是翻补也早在我家之前。四妹儿家已经用上了自来水,她家洗衣服用的是洗衣机,水龙头就在她家后花园,挨着我家窗户,流水声哗哗作响,洗衣机嗡嗡转动,二重唱一样欢快。洗衣粉稀缺,她的父亲坐在一株海棠旁边非常有耐心地削肥皂。他是县上养路段的一名工人。“敲钟吃饭,盖章拿钱”,端的“铁饭碗”,父亲这样形容。这样的人下班时间不用再去考虑别的问题,有时间把肥皂片削得又薄又长,卷起来,像一朵朵花,虽然最后还是会加点水熬成半乳状,但那样的过程一定要美好得和他的生活一样。不像父亲,整日奔波,吃一顿饭都鸡飞狗跳敷衍了事。
《霍元甲》也是挤在她家天井里看的。一到周末,忙的、不忙的,大的、小的,还有别家院子的,都挤在那个方盒子面前等着续接上回分解。一周两集,倒是让日子有了盼头,有了盼头的日子就会有使不完的劲,就算是每天可有可无的重复也有劲。四妹儿的父亲很好客,一早就把凳子给大家摆好,他自己在一旁小几上放了一碟花生米、几颗泡菜,小口小口吸啜手中杯子里的酒,漫不经心地看着一园子人嬉闹。四妹选了最中间的位置,和巷子里的小伙伴一边打闹,一边等着前面的广告结束。四妹和他的父亲一样,在人群里总会高出一截,却也能笑嘻嘻地低下头。
一个五官立体、个子高高、透着一股青春英气的小伙出现在四妹家堂屋里。我第一次听到那么好听的说话声音。我和四妹儿躲在门后偷看她未来的姐夫。我小声问她姐夫是不是和大姐一个单位。她弯着腰,眼睛从门缝移不开,没有回答我。那天她穿了大姐送她的白底黑条小套裙,那年最流行的款式,胸前已经有小小的峰峦,非常好看。她像是在谋划着什么,眼神迷离。好半天,她回过神来,看着我,点了点头,脸颊绯红,嘴角露出从未见过的神秘微笑。有时候,一个表情告诉你的事实,会远远多过无休止的唠叨。我从她上扬的嘴角确认,四妹儿应该是看到了自己顺理成章的未来,和大姐一样单位分房,有一个她喜欢的人,无忧无虑。
这样的顺理成章让她在巷子里像一颗星星带着光芒。而我却看不见自己。
父亲说过的那些话,早就很无趣地各自飘荡开去。可能是四妹儿的微笑磁场强大,它们又开始从四面八方汇聚而来,有的落在地上“铛”地响一声,有的砸在玻璃上被弹了回去,有的落在我的头上,让我老想着未来是不是也能像四妹一样,有一个英俊标志、知书识礼、声音还很好听的男子等着我。这念头让人脸红,难以启齿,却像一股旋风一般提着我的头发,扯着我的脸皮,来了又去,去了又来。
这条巷子,生来如此。离开它,是父亲终其一生的梦。但眼下,他束手无策。他所有的日子都得从土地里面来。他不喜欢拨弄土地,也不擅长各种农技,却由不得他。就算他不理解为什么一根藤上结了不同的瓜,他是扁的那一个,没有生成圆的,还带点苦涩,也没办法。
父亲肯定是被逼急了,自己没机会,便把包袱扔给我。我也被那些砸痛了脑袋的话挑拨得蠢蠢欲动,想着做点什么,不一定非要像棵草子一样烂在那块地里。
突然有一天,家里堆满了黄灿灿、金子一样的玉米粒。半间客厅和我们的小卧室全是。我和二妹费力地踩到堆顶,又开心地滑下来。睡觉的时候要踩着这些晒得又干又脆的玉米才能爬上床。床底下也是玉米。它们相互摩擦发出又脆又亮的声音,让我俩兴奋,还有一种莫名的饱胀。我们并不知道这是父亲寻的新营生。生产队长磨盘上睡了一觉——想转了,竟然允许父亲承包生产队的拖拉机。那些玉米竟不是母亲种出来的,而是父亲从四乡八面老乡手里一小袋一撮箕装进拖拉机弄回来的。
没过几天,父亲又把那些粮食全又装上拖拉机。他用摇手柄摇那玩意儿,使出了浑身力气。那家伙叫了两声,又偃了气——上了年纪瞌睡太多,得反复摇上几遍它才勉强“突突”又叫了两声,然后像续上了力气一样挺匀称地一直叫着。父亲跳上车,慢慢下了家门前那个坡,消失在我们的视线里。
父亲的玉米成了成都周边各大酒厂的抢手货。父亲顺带给我买回来一个皮革书包,淡蓝色,有浅浅的白色格纹。我把母亲缝的那个布书包换下来,背着它到处炫耀。一直到我毕业,我保证,学校里没有出现过第二个这样的书包。
风刮起来,吹过学校里的那两棵柳树,又吹进巷子里。有的人可能一直藏着翅膀在等风,有的人只是觉得风带来了凉爽,并无特别。风总是会吹乱很多东西,也可能把乱的东西吹正。我去了重点初中,和四妹儿没能继续在一所学校。初中毕业可以选择报考中专或者中师,毕业直接分配工作。父亲说,就能和四妹一样有个城镇户口。这次,他只说了一遍。
父亲去粮站帮我办《商品粮供应本》。他一定要自己去。他想让别人都知道,他的女儿以后也吃公家的粮食了。他见人就笑,那些人也向他笑,整条街的人都笑,他们说:
“好啊!这条街终于有个孩子跳出农门了。”
“多好,以后就什么也不用愁了啊!”
“多不容易啊,千军万马挤独木桥喃呐。”
父亲把粮食本子交给我,黄黄的,巴掌大,我的名字旁边盖了红印章。我把它带到学校去,每月能领到30斤大米;以后工作了,每月拿着它去粮站才买得到米面。父亲笑了好几个月。偶尔我也有些许遗憾,但想到可以和四妹儿一样了,那些遗憾便轻飘飘的,没有任何分量。
曾经我觉得巷子又暗又深,最黑的那一段,捉迷藏的时候手和脚撑着两边,噌噌往上,可以躲在顶上的暗影里,他们都找不到我。我一直没有让他们知道我藏在那里,不然下次他们就会知道我可能躲在那里。一个秘密泄露了一次,就不会再继续供你藏身。而我心里的秘密终究泄露了。我有了新的朋友和生活,也可能是因为我长高了,那条巷子黑暗的顶子似乎伸手就可以摸到。
父亲总是不在家,每次回来总是会带回一些我们从没见过的物什,如鸡蛋般大的红李子、紫色的纱裙、各种名目的书籍……那些东西新奇而奢侈,有好长一段时间,我都没再去惦记四妹家的樱桃。
没几年父亲又一次在巷子西边不远的地方修了一幢一楼一底的砖房,这次用的全是砖和水泥,带一个花砖镶的小阳台。我一点忙也没帮上,他说读书才是我的正事。二柱四的房子给了姑姑。
别人不知道他吃了多少苦。吃再多的苦,没日没夜,风餐露宿,甚至有时候命悬一线,他也是乐意的,浑身都是劲。母亲做完承包田里的活偶尔也跟他出去一趟。那辆拖拉机,常常在半路歇气,甚至不听使唤。名山区“和尚脑”那个坡,上坡怕拖拉机爬不动,下坡又疯了一样乱跑,甚至有一次没了刹车,把坐旁边的母亲颠下了车,擦着靠山一边的沟渠才停下来。那一回光是修车就用了两个星期。他嘴上说着后怕,车子一打燃又出门去了。
四妹没有考上高中。她或许就没有想过一定要考上什么。她的未来就是一幅画好了的画,放在那里,她走过去捡起来就行。我俩躲在门后偷看她姐夫的时候,就没怀疑过。
我们以为我们会一辈子住在巷子里,万事万物都会那么依然如故地生长下去,不知道一生说短也长,可能会遇上很多改变,可能会拐一个弯,也可能甚至不复存在。
那时我们并不知道为什么突然就不允许接班了。四妹儿心思单纯,每日吃吃耍耍,不担忧什么,也不期待什么。还是她的父亲决定让她去职业中学学会计。
四妹儿结婚的时候从巷子里搬了出去,住进了夫家。我们就像两条船,在潮汐里被冲往不同的方向,很久很久,没再遇上。我的工作换了很多个岗位,从乡村到城里,从教师到乡镇干部,一路奔波,辗转浮沉,天天年年,却在这样一个小小的县级城镇里,一次也没有遇到过四妹儿。连做梦都没有遇到过。其实我一直都很想念她。童年是一个人一生的根源。我们是彼此的印记。
工作十几年后,终于有一天在一家文具店里,突然发现给我介绍钢笔的是四妹儿。我们都很惊讶,都说:“是你啊?”也都突然不知道接下来该说什么。她笑起来还是眯着眼睛,衣着比以前朴素。问了几句家里人的情况,突然停下来,两个人又不知道要说些什么。
和我想象的重逢不太一样,各自走了那么久的时光,有那么多的细节可以追究,随便一个童年的话题便可以聊上半天。她看着我笑,那张脸多了些许风霜。我也笑,她和我只是隔着柜台,却又像隔了很远很远。我们似乎应该一起吃顿饭、喝喝茶,以后可以经常去串串门,然后和以前一样成为彼此的生活。可是我买了笔转身就走了。
“我一直记挂着你啊!”我想说这样的话,可是我终归没有说出口。她的心里也一定藏着这样一句话。可是说不说出来,又有什么意义?我们还会一直记挂着彼此,但在这样一个小小的县城里,还是很难再遇上。
我和父亲一起在县城新区又修了一幢房子。他说,这是最后一次,再也不修了。
去老城区,得穿城而过。巷子已经没有了,2008年汶川大地震,天全受到波及,巷子拆了,整条街都重建了,整个城都重建了,一切都是新的,再也找不到那些藤、那些蔓了。
我们再回去,甚至连大门在哪里都需要问别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