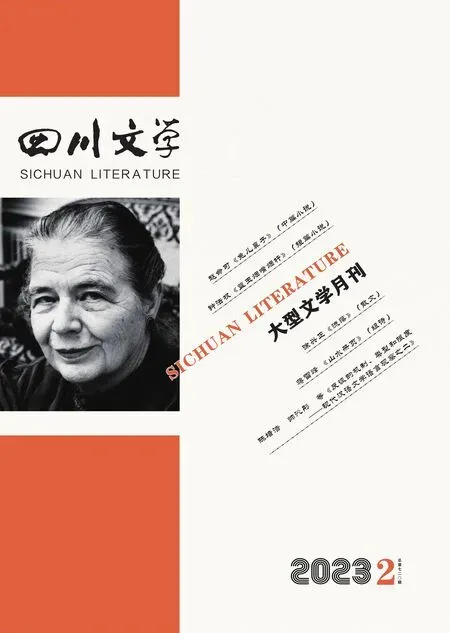流落
2023-09-01徐兴正
□文/徐兴正
谁能在铁板上钉钉子?世界真是铁板一块吗?徐家寨的确像一枚钉子被钉进了世界这块铁板?一切疑问都悬而未决。一个人在这里出生,最后在这里死去,中间过程无论如何,都算善始善终。如果生前流落他乡,死后就是孤魂野鬼。这是徐家寨的固执、偏执。
这种固执、偏执,还不局限于徐家寨人自身,就连对待小动物、大牲口,也都是如此。
小动物主要养猫、狗。猫从哪里来?一开始,是去镇上买来的。口袋卖猫,不知是黑是白。徐家寨不在乎猫的颜色,也不在乎猫的大小、强弱,只要是只猫就行了。一家买回一只男猫,另一家买回一只女猫。男猫女猫相遇,交配,女猫生下小猫来,主人送给徐家寨的邻居,也送给别处的亲戚养,但不卖出去。小猫生得太多,不能全送出手,剩下的,主人只好都养起来,养得最多的竟然超过十只。鼠药发明出来,在镇上售卖。徐家寨不满于养这么多猫却仍有鼠患,也买来鼠药投放。猫食用被毒老鼠,会被毒死。以至于徐家寨又去镇上买猫。别处肯定也投放鼠药,猫大量减少。所以,一时猫贵。徐家寨的猫重新多起来,这里不再投放鼠药。无论镇上猫卖到多高价钱,徐家寨都无人去卖猫。
狗和猫不一样,就连镇上都没有狗卖。卖狗!预示这家人越来越穷。偷狗!则表明这个人实在缺德。狗,只限于你讨要、我赠送。徐家寨的狗,一开始也是去别处讨要来的。一家讨回一条公狗,另一家讨回一条母狗。顺便说一下,不知什么原因,徐家寨将猫说成男女,却将狗说成公母。接下来,狗的情形就类似于猫了。不过,狗没有被毒死过,它们只是一次又一次被捕杀。理由都是狂犬病,但有时候确凿无疑,有时候又似是而非。还有时候,镇上来捕杀一条狗,说是送去检验狂犬病毒,其实是有酷爱吃狗肉的人到镇上来了,用于接待、款待、招待。这种时候,剩下的狗往往因为这条狗没有检验出狂犬病毒而幸存下来。
在猫、狗最兴旺昌盛的年份,它们各自成员都接近甚至超过徐家寨人口了。猫眼的蓝,一只又一只猫眼的蓝,能让阳光透红,月光泛白。没有太阳的白天,猫眼的蓝是浅蓝。没有月亮的夜晚,猫眼的蓝则是深蓝。雨天,猫眼的蓝比较阴暗。雪天,猫眼的蓝又明快起来。电闪雷鸣时刻,猫眼的蓝也会惊恐不安。这样一来,猫眼里的徐家寨就变成一个令人恍惚的世界了。总有狗叫声。不是这条狗在叫,就是那条狗在叫。没有两条狗的叫声是雷同的。有热切的狗叫,也有冷清的狗叫。有勤勉的狗叫,也有偷懒的狗叫。有撒欢的狗叫,也有沮丧的狗叫。有热闹的狗叫,也有荒凉的狗叫。有高昂的狗叫,也有低沉的狗叫。有嘹亮的狗叫,也有沙哑的狗叫。有密集的狗叫,也有稀疏的狗叫。有愤怒的狗叫,也有顺从的狗叫。有得意的狗叫,也有失意的狗叫。有欢乐的狗叫,也有悲伤的狗叫。各种狗叫起伏、穿插、叠加,徐家寨的世界就不那么单调乏味了。
洗骨师到徐家寨来做法事,说过一番神神鬼鬼的话:猫属阴,狗属阳。猫养多了,阴气重;狗养多了,阳气重。徐家寨可能并不懂得这一点,但这样养猫养狗,阴气阳气恰好扯平了。徐家寨人想想也是啊,猫、狗减员各有各的原因,但大体上都是这样:猫多狗也多,猫少狗也少。这种平衡,恐怕只能解释为上天自有安排吧。那也可以说,上天还是看顾这里的。
徐家寨的猫、狗身上还藏着一个不为外人所知的秘密,眼明心亮的洗骨师也未能洞悉。这个秘密其实是一种偏见,徐家寨认为一只猫、一条狗,自有其性情,而它们的性情又取决于主人。什么样的人家,就注定养出什么样的猫、狗来。这种偏见肯定不符合事实逻辑。一户人家,不止养一只猫,也不止养一条狗,几只猫是一种性情吗?几条狗呢?难道猫和狗也是一种性情?而所谓主人的性情,每个家庭那么多成员,究竟是谁的性情?不可能几个人一种性情吧?所有这些,完全不能自圆其说。可是,徐家寨并没有人能驳斥自身偏见,也没有人能免受它影响。
我家倒是多年间都只养一只猫、一条狗,一直养到它们因衰老而死去。这只猫几乎不离开家里,最多会到三家共用的院子,也只限于在院子里晒太阳,追逐一根飘飞的鸡毛。别的猫跑到它的领地来吃食,它一声不吭。见它如此软善,就吓唬甚至攻击它,它也总是退让、避开。它还十分谨慎,遇上逃跑不力、奄奄一息、业已死去的老鼠,立即放弃捕获、进食,因此鼠药投放期间免遭间接毒害。这条狗的软善与谨慎,还真像这只猫。镇上来人捕杀,不可能在寨里其他地方碰到这条狗,进到院子,早被我们藏起来了,这种时候它从不叫。它不曾吓到过路人,更不用说咬伤谁了。它的本分是防御,而非攻击。陌生人来了,一声声狗叫,它会退守到家门口,主人出门打招呼,它马上放行,还友好地摇尾摆尾。
族间、邻居都喜欢我家这只猫、这条狗。寨里有不少猫是凶残的,狗是凶恶的,有人感到害怕,还得提防它们。但是,他们却因我家这只猫、这条狗,看不起我们一家,特别是看不起我父亲,觉得他的软善与谨慎,猫、狗不如,太过分了。
徐家寨人对猫、狗的偏见,与对我父亲的成见交织起来,他们更觉得他一无是处。身为生产队长,我父亲在村公所和镇政府面前,比任何一个社员都还要俯首帖耳。之前,我父亲曾到外县一个水库、水电站工地干活,参加夜校学会许多汉字,文化程度达到可以作会议记录,不认识的字知道以同音字替代。我父亲胆小怕事,那些会议记录竟然让他魂飞魄散,1962年离开工地回到故乡。只要徐家寨还有一个识字的人,人们也不想让我父亲当生产队长。如果我父亲经得起哪怕一点风浪,不从水库、水电站工地跑回家去的话,就可能拥有工人身份。
徐家寨人在我父亲面前表现出这种看不起,甚至有人当众羞辱说“你看你家的猫样!你看你家的狗样!”他都一直保持沉默。看来,我父亲不但害怕会议记录的话,而且也害怕当面听说的话。这种害怕是彻底的,彻底到他绝不迁怒于我家的猫、狗。我父亲比所有人家都还要善待自家的猫、狗。猫、狗先后死去,我父亲偷偷将它们葬在山冈,可是,具体埋在什么地方,他连我们都没有告诉。此后,我父亲没让家里再养别的猫、狗。或许,他还是有耻辱感,想摆脱族间、邻居的偏见吧。
但是,在继猫、狗之后,让我们一家特别是我父亲蒙受羞辱的,还有一头牛。
徐家寨二分之一人家养牛,三分之二人家养马,四分之一人家既养牛又养马。相对于猫、狗这样的小动物来说,牛、马这样的大牲口更有脾气。寨里出现过恶牛、恶马,顶撞人,踢人,还造成伤残,伤残者有主人也有他人。我家的牛个子小、腰身短,徐家寨地块像药膏一样贴在山坡上,这种体形的牛最适合进这些地块去拉犁铧了。这头牛临近一岁,在最恰当的时候,我父亲教会它拉犁铧。秋天的黎明,这头牛被牵到地里。我父亲吆喝,鸟雀打鸣,这头牛也偶尔叫两声。三天早晨下来,这头牛能听懂我父亲的指令,踩边、跟沟、慢慢、调头、走起,也能顺从执行。踩边,到地里犁第一铧土,牛踩着地块边缘拉犁铧。跟沟,从犁第二铧土开始,牛跟着上一铧沟走。慢慢,犁铧尖嵌进石头缝隙,或者套进树根,牛慢下来,以便取出犁铧重新插入泥土。调头,拉犁铧到地块尽头,牛折回。走起,牛开始新犁一铧土。这头牛可能是寨里最容易教会拉犁铧的牛了。它相当温顺,哪怕连续拉犁铧,至少也要在七天之后,而且黄昏了还不歇下,它才会抗议一下,抗议方式仅仅是放慢速度。它是母的,一辈子辛苦,仅在怀孕后和生产前各两个月,不拉犁铧。不过,我们一家善待它,常年有充足草料,不缺玉米面、盐巴;拉犁铧时,我父亲只是吆喝,手里连鞭子也不拿。徐家寨养出恶牛的,不敢用来拉犁铧,知道这头牛好使,就来借用。他们当中有人不爱惜借来的牲口,将犁铧插得太深,鞭打这头牛,它拼命拉犁铧,导致痨伤便血。出现了这种情况,我父亲还是无法拒绝他们借用这头牛,他就跟着去掌犁铧,不让它过于受累。十岁,这头牛进入暮年,没有力气再拉犁铧了。我们一家开始锄地。我父亲决定不宰杀这头牛,待它衰老而死,也像那只猫、那条狗一样葬到山冈上去。这个决定遭到徐家寨取笑,包括我父亲的同辈,以及他的晚辈。他们羞辱我父亲的话,又增加了一句:你看你家的牛样。
我们一家忍不住抱怨我父亲这个决定,他自己也终于坚持不下去了。这头牛被我父亲送给路过徐家寨的牛贩子。徐家寨牛、马不卖给外人,如今竟然还有这种地方,牛贩子觉得匪夷所思,而我父亲拱手送给这头牛,他认为不可理喻的同时也感到喜出望外。绳子交到牛贩子手里,这头牛静默站立,泪珠滚落地上。这让我父亲十分愧疚。我父亲更加愧疚的是,这头牛在途中倒毙了。得到这个消息,时间已经隔了半年多。我哥哥从镇上中心小学附设初中二年级辍学三年了,开始琢磨木匠活,打算建房时自己做木工。于是,去集镇买尺规之类的木匠工具。尺规由一段长六寸的硬木条,与一段长一尺二寸的软木片,呈直角衔接在一起。硬木条上粘合一层经工艺处理过的牛肋骨,用以标记寸、分的刻度。尺规匠人给我哥哥讲,这批尺规的牛肋骨特别好,因为年份足够长,质地过硬,保证不变形。又讲,匠人曾路遇牛贩子,同行至集镇附近,牛群里一头牛挣扎几下,轰然倒毙。牛贩子随身携带刀,用刀剥下牛皮。匠人借用牛贩子的刀,取出牛肋骨。其他一律丢弃在那里。不知道后来有没有人分割取走食用。如果没有的话,最终可能被野狗、乌鸦、蚂蚁和微生物消耗一空。因为牛肋骨白捡的,所以上好的尺规还按过去的价钱售卖。我父亲左手握紧我哥哥买回的这把尺规,右手拇指在硬木条牛肋骨上划过来又划过去。我父亲手指皮肤粗糙如砂纸(掌心还有好多硬茧),寸、分刻度被拇指一遍又一遍打磨,我哥哥担心会被磨平到无法辨认。我父亲移开右手拇指,寸、分刻度仍清晰可见,我哥哥这才松了一口气。这年我哥哥十五岁。这把尺规一直被我哥哥小心使用、保存,随着年岁增长,他也像我父亲一样,从牛肋骨上看到这头牛的缩影,它一辈子拉过的犁铧,临终走过的道路,一并缩短为六寸长。
这头牛和这只猫、这条狗不同,徐家寨没给它归宿之地,还是流落出去了。
不过,它们都算是得到我们一家的礼遇,特别是我父亲的礼遇。后来说起这个,因为亲历时我年纪尚小,知道的事情不可能太多,所以我哥哥向我保证,这样的例子徐家寨再也找不出第二个了。我哥哥也提醒我,不得不承认另外一个事实:我们礼遇小动物、大牲口,但别人并不会这样礼遇我们。我哥哥之所以辍学,是因为他在学校遭受羞辱、殴打,宿舍里的床单、被子被人卷到操场上烧掉,灰烬还被撒尿淋湿。镇上中心小学附设初中撤销了,我到县城上初中,也遭受过羞辱、殴打,欺凌者踩在我枕头上,让我用床单给他们擦皮鞋,只是我没有因此而辍学。
我父亲礼遇猫、狗、牛,尽管在牛这件事情上他坚持不下去了,致使它流落出去,也仍然一直打动我。
相比之下,遭受到羞辱,有人会作出激烈反应。美国作家罗恩·拉什短篇小说《艰难时世》就写过这样一些场景:
“有东西潜入我家的鸡舍,偷走了一些鸡蛋。”埃德娜说,“只偷走鸡蛋,所以肯定不是狐狸或黄鼠狼干的。”
“所以你怀疑是我家的狗干的。”
埃德娜没有出声,哈特利放下了手中的麻袋,从工装裤里摸出一把斩刀,又轻轻地叫来自家的狗,后者听话地向哈特利走去。哈特利单膝跪下,左手捏住狗的后脖颈,同时用斩刀刀刃抵住狗的喉咙。他的女儿和老婆静静地伫立一旁,面无表情,仿若面团一般。
“我不认为是你家的狗偷走鸡蛋的。”雅各布说。
“可你也不是百分之百确信。还是有这种可能。”哈特利一边说,一边用食指抚摸爱狗的头颅,狗随之抬起了脑袋。
雅各布还没来得及回话,刀刃就切开了狗的气管。狗没有大叫或咆哮,只是在哈特利的手里垂下脑袋,溅洒出的狗血染红了道路。
这是血性吗?我不能确认。也不敢去想,我父亲、我哥哥,以及我自己,如果真有这种血性的话,它究竟意味着什么。还有,徐家寨、我哥哥的附设初中、我的县城中学和别的很多地方,是否配得上我们爆发这种血性?
很多年里,我父亲经常说一句话,“你吃饭要认得牛辛苦。”我父亲感激牛,与加拿大作家阿利斯泰尔·麦克劳德短篇小说《秋》所写的那位父亲对马的恩情倒是如出一辙:
很久以前,父亲的主业是帮人运煤。还是单身的时候,可能是因为寂寞,有时就会去喝个大醉。二月份昼短夜长,在一家卖私酒的店里,父亲喝酒、谈天、一醉不醒,全然将屋外的冰雪世界抛诸脑后。直到第二天早晨,身体被酒精抽干,他绝望地走到门口,看到马和雪橇就在他昨晚走开时的位置,其实它们全然不必留在那里。雪花像精细的粉末,覆盖雪橇上的煤块,却掩不住它们的黑光。这样的雪不像雨水落下,倒像是凭空出现的露珠,即使是最冷冽之时,它们也来。而那匹马,则在凌晨的冥暗中站成一个鬼影。在它黑色毛皮的外面,昨天的汗液已经结成一层层灰白的冰雪,鼻子下面悬着几根微小的冰凌。
父亲无法相信在如此酷寒之下,这匹没有拴住的马,毫无必要等了他一夜。此刻,马蹄把地上的雪踏得嘎吱作响,结冰的马具下看得出它肌肉的颤动。那一晚之前,父亲从未被世上另一个活物守候过。他把脸埋在马鬃和白霜中,伫立良久。厚重的黑色马毛覆盖住他的脸,颊上凝起冰珠。
与麦克劳德小说中那位父亲不同,我父亲一直担惊受怕,过于谨小慎微,年轻时也不曾有过喝酒、大醉的时刻。这是我父亲一生无数遗憾之一,当然,他的不安也可能会因此而少一点。
事实并不完全像我哥哥所认为、我们兄弟所经历的那样,到了我哥哥中年、我父亲晚年,整个徐家寨开始蔓延着一种情绪。我哥哥自己做木工在徐家寨建房,然后去昆明打工不到一年,回来就再也没有离开过。我离开徐家寨,偶尔回去一次,短暂时还待不上一整天,深夜才抵达,早晨即返回。我哥哥身在其中,能感受到徐家寨这种情绪,却说不清道不明。我像个局外人,反而更清楚、明白,这种情绪比较复杂,它至少包含着愧疚不安和惊慌失措。
徐家寨为什么会发生这种变化呢?
因为许多年过去,这里还是遭遇重大变故了。
从我哥哥去昆明打工那时起,先是年轻人外出,接着是中年人也外出,再后来还有老年人外出。一开始,外出者还回徐家寨过年。久而久之,他们过年也不一定回来了。有人在别处安家,从此不回来了。至今常年居住在徐家寨的,主要是老人和孩子,他们比过去总人口四分之一多、三分之一少。谁能够离开,谁只好留下,或许都是命中注定。而我们这一代人,仅有我哥哥一家。现在,也只有我哥哥还养着一匹马。几乎没有人家再养猫、狗。最多养几只鸡,用来生蛋,或者宰杀,都是为了吃它们。小动物、大牲口,猫、狗和牛、马,都近乎绝迹;就连人本身,也寥寥无几……情况到此程度,徐家寨的固执、偏执还能一以贯之吗?
我父亲这一代,在世者,他最年长。徐家寨破除对我父亲的偏见、成见,原因不在于时间久远,而在于流落太多。见不到猫眼,听不到狗叫,孤零零一匹马。稀稀疏疏二三十人,还好意思因为什么猫、狗、牛,一直取笑我们一家,羞辱我父亲吗?
徐家寨开始怀念过去养过的猫、狗、牛,牵涉我们一家,特别是我父亲。他们向我父亲打听那只猫、那条狗葬在哪座山冈,而之所以打听这个,可能因为那些年,其他猫、其他狗要么被宰杀吃了,要么死后被扔到山沟,只有我父亲将猫、狗埋了,但我父亲不告诉他们埋在哪里。他们不向我哥哥打听那头牛的下落,谁也不知道它附身于一把尺规被我哥哥从镇上买回徐家寨。他们开始觉得对不起它们。
其实不必愧疚。
他们确实驱赶、捕杀、偷食过寨里的猫、狗,但我家的猫、狗并没有落到他们手里。
我家的牛给他们拉过犁铧,一两家人曾经亏待过它,但这种情况后来被我父亲给避免了。
徐家寨的愧疚可能是与生俱来的。它像一种隐疾,藏在身体里,到他们晚年才爆发出来。我们一家,特别是我父亲,对那头牛的愧疚,就发作得比较早。这并不意味着,我们一家就有资格指责他们。相反,我理解他们,如果愧疚是病的话,那么,谁不希望无病一身轻呢?
他们甚至觉得对不起我父亲。
这更加不必要。
他们借助猫、狗、牛而取笑我们一家,羞辱我父亲,这由不得他们。如果身体里藏着疾病,总会间歇性发作呀。况且,我父亲也做不到随时随地捍卫自己的尊严,徐家寨根本没有这种人,只要他自己不在乎,受到的伤害就可以忽略不计。
但这种不必要的愧疚,还是让我信赖徐家寨。这里毕竟从未发生过暴力流血事件,而这种地方,镇里并不多见。有人到了晚年,还会觉得自己曾经对不起小动物,对不起大牲口,对不起别人。
当然也有必要的愧疚。
这种愧疚还发生在我父亲身上。
一年夏秋之交,地里玉米棒子刚出穗,挂着缨子,猴子就来掰食。往年也被掰食,但这年还是早了些。猴子掰下玉米棒子,撕开玉米壳,见不到一粒饱满的玉米粒,扔了,接着掰下一个……这块地里的玉米糟蹋完了,接着糟蹋下一块地里的玉米。徐家寨人极为愤怒,布下罗网、陷阱,众人出动,竟然捉来七只猴子,一只老猴子,六只小猴子。猴子被带回徐家寨公房场院里,它们都哭了。见此情景,软善者提议释放所有猴子,它们哭起来太像人了。凶残者提议打死这些猴子,它们和徐家寨结下了仇恨。作为生产队长,我父亲非常后悔安排捕捉猴子,试图以杀鸡儆猴处置此事。他的想法,真就是宰杀了一只大公鸡,猴子见过了鸡血,放归山林后不敢再来糟蹋玉米就行了。然而,徐家寨人吃过鸡肉,觉得少吃一次也无所谓,但没吃过猴子肉,就是想吃一次。况且,一只猴子哪里是一只鸡可以比的,肉多,够吃。于是,一个主意成型了:杀死一只老猴子,释放六只小猴子。如何杀死这只老猴子?一个办法想出来了:教会这只老猴子扒臼窝,但扒臼窝方法故意弄错,让它一只手、上半身和脑袋都处于臼窝之上,这样,舂椎忽然砸下去,定能砸死它。这只老猴子的聪明不亚于徐家寨人,而且它也好学,立即就掌握动作要领了。舂椎准确砸中了它的脑袋。我父亲看到老猴子脑袋被砸中的瞬间,它恰好在向人们做鬼脸,它一只手在脑袋下面,另一只手忽然抓住臼窝边沿,但脑袋、上半身还是被舂进臼窝,两条腿不由得腾空而起,不着边际地蹬了几下。这只老猴子惨叫一声,也只是一声,没叫出第二声。六只小猴子哭得稀里哗啦,绳索解开之后,它们还想朝臼窝包围过来,但还是被徐家寨人驱赶着离开了。待这只老猴子死定之后,徐家寨人抬起舂椎,将它从臼窝里弄出来。臼窝里只有少许高粱垫底。徐家寨人还算诚实,为了欺骗这只老猴子,还真在臼窝里放上一层高粱。血液的鲜红抢占了高粱的淡红,红得让徐家寨人害怕,谁也不敢真吃猴子肉。这只老猴子被埋在一座山冈上。
外界进入徐家寨的路并不多,其中一条横穿一处山坡。这处山坡坡度在30°至40°之间,中间一条山沟,山沟里雨季会有流水,山沟里长满荨麻。这条路上边下边叠满悬崖,悬崖被灌木覆盖。这里地名叫猴子湾。当初掰玉米棒子被捕获的七只猴子,就是从猴子湾出去的。现在,猴子湾这个地名还保留着,猴子却不知流落到哪里去了。
除了愧疚,徐家寨也会怜悯。
一位外出打工者,很多年没有回来,徐家寨固执、偏执己见,他流落他乡了。一年冬天,他忽然回到徐家寨。但回来的不是活生生的他本人,而是一个红布包,里面装着嘎吱作响的骨殖(骨灰被焚尸炉烟囱扬到天上去了)。到了这个地步,他当然无法单独回来,只能由他妻子带他回来。而过去,总是他单独回来,妻子不回来,孩子也不回来。这一回,为了显得不那么孤单,两个孩子也一起回来了。男孩七岁,女孩四岁。到了徐家寨,由于地势、坡度的原因,两个孩子一次又一次摔倒,大男孩会哭,小女孩反而不哭。他父亲张罗,他哥哥和他弟弟给他操办,请来道士先生敲锣打鼓念经跳神超度亡魂,最终,他的骨殖被分摊在一件青布寿衣(他父亲的)上,用一副杉木棺材(也是他父亲的)收敛,仿佛是空的,抬到一座山冈上安葬。丧事上,徐家寨帮忙的人都用心、卖力。看到两个孩子披麻戴孝,跪在棺材前烧纸,火光照亮兄妹俩脏兮兮的脸,能依稀回忆起他的面目来,不少人落泪了。他不是死于事故,而是死于疾病。可能因为这种死亡还算温和,而且过于漫长,送回徐家寨又是遵照他的遗嘱,这几天里,他妻子没有表现出多么悲伤。也有人猜测,他曾经挣到不少钱,还置下家产,但治病用完了那些钱,他妻子还背负了债务。丧事办结,他父亲拿出他哥哥和他弟弟开列的清单,计算了一下,礼金抵销开支之后,他妻子弥补兄弟俩七百元,账就平了。他父亲希望他哥哥和他弟弟养育这两个孩子,而他们两家也是在外打工,不敢应承下来,他妻子也不同意,带孩子走了。
在此之前,他三四年没回来。现在看来,没有别的原因,就是生病了。徐家寨以为他忘恩负义,不会再回来。而他究竟忘的什么恩负的什么义,谁也说不上来,仿佛一个人的出生地就该是他的恩典、道义。实际上,他还真做过一件事:他去请求当上村委会主任的小学同学拉通自来水未果,就花三万多块钱买来水管和水泥、砂石,让徐家寨人自己去弄。我哥哥还感叹,如果徐家寨今天不通自来水的话,丧事上这么多人饮食,赶马驮水来用真是苦差事啊。就凭这一点,徐家寨人也念他的好。不过也有人抱怨,拉通徐家寨自来水,他怎么不支付工钱呢?他不让生病消息传到徐家寨,就连他父亲和他哥哥、他弟弟都不告诉,可能还是因为,他不太相信故乡和亲人吧?
他死前不奢求亲人去见最后一面,却交代死后要埋回故乡。
难道他也有流落之感?
这让我联想到美国作家威廉·福克纳长篇小说《我弥留之际》,女主人公艾迪·本德仑苦熬了一生,“活着的理由就是为永久的死亡做好准备”,她丈夫和儿子们承诺在她死后,送她回娘家的墓地安葬。我印象非常深刻的是名为《卡什》诸章中的一章,只有两句话:“那东西没有放稳。我早就告诉他们了如果他们要平稳地搬它运它,他们必须得”。严格说来还算不上两句话,因为第一句话是完整的,而第二句并不完整,“他们必须得”怎么样,留下太多空白。“那东西”是什么呢?是艾迪·本德仑的遗体,收敛遗体的棺材,还是她这个人,活着的时间和死去的鬼魂。活人的故事,也在讲述死人的故事。一定是这样的。
而他,仅仅是将骨殖送回徐家寨埋掉。
流落的人,就这样埋在了故乡,他能安息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