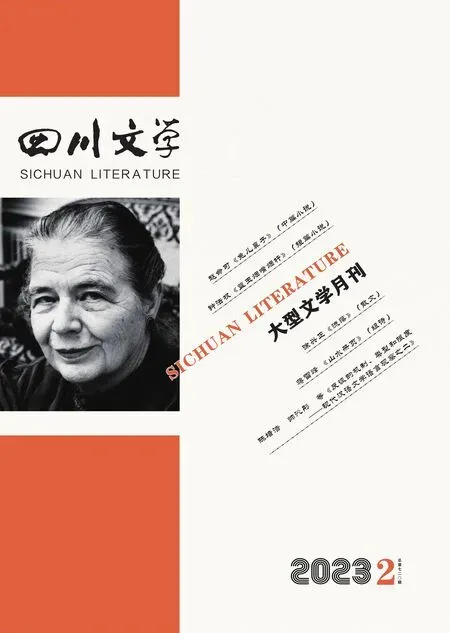我们总是绕啊绕
2023-09-01孟祥鹏
□文/孟祥鹏
一
苹果刚啃了两口,王莽忽然大彻大悟,世间男女,离合悲欢,结婚不过是徒增烦恼,他说以后不相亲了,孤身至死,再不行,出家当和尚。李逵啐了一口,当和尚,你也配,没有本科文凭,你去看看哪个庙要你。王莽白他一眼,别胡说八道,这跟文凭有什么关系。
行啦,李逵安慰他,不就是个杨彩虹嘛,天涯何处无芳草呢?王莽听着烦,捶他一拳说滚滚滚,然后眼神空洞起来。他最怕别人提这个,大伙儿明知他心里还惦记着杨彩虹,偏要时不时地往他伤口上撒点盐。李逵把苹果核丢进垃圾桶,劝道,闲着没事就去泡泡温泉喝点小酒儿,好日子还是一样过。王莽懂他意思,可自己就是下贱,澡可以泡,酒也可以喝,但少了杨彩虹,干什么都寡淡无味。
杨彩虹去香港已经第三年了。她刚走的那段时间,王莽还没觉得多难过,只是她不辞而别,让他脸上有点难堪,艺术团里的八婆们私底下都在传王莽工夫不够硬,留不住欲壑难填的杨彩虹。他听了气得牙痒痒,恨不能脱了裤子自证清白。后来他逐渐想开了,集中精力,认真相亲,珍爱网,百合网,世纪佳缘,大大小小的相亲网站会员充了几千块,想赶快找个人双宿双栖,好让大家知道,是她杨彩虹有眼无珠,与年富力强的王莽毫无关系,他硬得很。
第一个相亲对象约王莽去喝咖啡,开口就问他读没读过张爱玲,王莽说我在艺术团里踩高跷,读张爱玲做什么。女的一脸鄙夷,连张爱玲都不读,往后日子怎么过。第二个是短发齐刘海,戴黑框眼镜的公务员,两人吃了五百八十块钱的菜,相谈甚欢,王莽结完账,女的才想起什么似的问他,艺术团的工作是铁饭碗吧?王莽犹豫了一下,理论上是,但我没编制。对方愣了,你早说啊,白了他一眼转身就走。第三个是家里给介绍的,见面一看是初中同学,读书那会儿姑娘肤白貌美,清水出芙蓉,王莽迷恋过一段时间,如今再相逢,本应欢喜,却怎么也没那种感觉了。两人约着吃了几回饭、逛了几趟街,然后就牵手拥抱接吻,该干的事儿一样没落下,几个月下来,王莽觉得少了点什么,女同学也不冷不热,好像没多大意思。王莽演出忙的时候,经常忘了联系,她也从来没主动找过他。半年后王莽想起来要去看她,结果她挽着另一个男的出来,拍着脑袋说真对不起,我都订婚了。王莽说没事,我也是恰巧路过。寒暄了几句,他匆匆跑出那幢公寓楼,跳上一辆公交车,大街小巷转了整整一下午。
一个人的时候,王莽经常会怀念杨彩虹,饭后发呆,午夜梦醒,忽然就伤感起来,觉得一片赤诚被她辜负,心里总是遗憾难舍,尽管她身材样貌都普普通通,人也很难相处,但就是让他格外着迷,喜欢她哪一点,王莽自己也说不清。杨彩虹不合群,团里人不太待见她,李逵嘴巴最毒,说她整天板着脸像家里死了人。王莽劝他积点口德,李逵摇着手说我都搞不定的女人,你也不用痴心妄想了。李逵倒是没吹牛,他在这方面确实天赋异禀,会和女生们聊兰蔻、雅诗兰黛、雪花秀的不同功效,讨论娱乐圈男明星的绯闻八卦与私生活,刚认识两天就能挽着胳膊去逛街买衣服,彼此还以姐妹相称,偏偏就杨彩虹不吃他这套,一身正气,刀枪不入。李逵经常暗地里翻她白眼,说她不识抬举。除了李逵,厨房的翠翠也对杨彩虹咬牙切齿。临时工们住在一个狭窄的仓库,一边堆放演出用的杂物,另一边供大家打地铺,杨彩虹在角落里铺了张凉席,衣食住行都远离集体。她每天练完功独自缩在墙脚读书,别人跟她搭话,她也不愿搭理,通常微笑一下,敷衍了事。翠翠爱管闲事,好奇她整天看的什么书,趁着杨彩虹到外面洗漱,蹑手蹑脚地跑过去翻看,然后阴阳怪气地给大家展示那本《声乐基础》,啊哟哟,可了不得,我们这里出了个歌唱家。杨彩虹端着盆回来,翠翠猛地一转身,两人迎面相撞,书里的笔记和卡片散落一地,杨彩虹冷着脸让她滚开,翠翠恼羞成怒,从此见了面就骂骂咧咧,冷嘲热讽。
几门亲事相继告吹后,家中二老坐不住了,整日倚杖叹息,泣涕涟涟。王莽好不容易回趟家,他们带他到处相亲。人家问王莽做什么工作,父亲抢着回答说在市艺术团搞演出,人家点点头,工作还不错,王莽红着脸解释,其实就是踩高跷,母亲咬着牙拧他大腿,连忙补充说工作很稳定,衣食无忧。王莽对那些姑娘不满意,嫌她们长得不行,母亲语重心长地开导他,不能只论外表,好看的女人大多凉薄,找个八字旺的,下半辈子升官发财。王莽说,升官发财不指望,能寿终正寝就行,找不到合适的我就打光棍。没料想母亲认真起来,听完这话,嘴唇哆嗦几下就开始掉眼泪。王莽目瞪口呆,不知怎么应对,说妈你别哭,我尽力。母亲悲壮地点头,你最好尽力,不然我和你爸就没脸活了。
折腾了大半年,这一瞬间他忽然意识到,结婚没那么简单,结婚并不是一种可以自由选择的仪式,而是某种程度上的社会性事件,一种关系到家族颜面和声望的人类法则,或许,他要为此作出很多牺牲。李逵说你这种想法不对,而且大错特错,他一边搽护手霜一边告诫王莽,千万不要妥协,人,生来独立且自由,凭什么被婚姻绑架。王莽说道理没错,可那些叫嚣着要单身到底的人,最后不还是都结了婚。李逵瞥他一眼,他们是他们,你是你。王莽愁眉苦脸,不知道该怎么说,本来他以为相亲比谈情说爱更容易,条件讲清楚,一拍即合,两个人住到一起就算是合法夫妻,哪儿料到有这么多坎坷波折。李逵想了想,说你要是真急着结婚,我这儿有个亿万富婆,可以介绍给你。富婆?嗯,前两年死了老公,名下有巨额遗产。
二
路上下了场大雨,王莽赶到的时候,苏梅自己先开始了,桌子上摆着瓶烧酒,已经干掉大半。王莽有点怀疑她的身世,亿万富婆怎么会来路边摊撸串,而且还撸得这么尽兴。不好意思苏阿姨,来晚了,王莽放下雨伞,手足无措地给她鞠躬。苏梅没吭声,瞪了他一眼。他意识到称呼不合适,立马改口,对不起苏女士。你坐吧,苏梅面无表情,给他添了杯酒。王莽摇手推辞,我不会喝酒。苏梅也没勉强,端过来一盘烤串,使劲吃,不够再点。王莽拘谨地笑笑,拾起一串小红腰,细嚼慢咽。今年多大了?苏梅问他。二十五,王莽彬彬有礼地回答。你呢?他反问道。他本来想说“您”,但想到自己是来相亲的,就用了“你”字,并且挺了挺腰板,希望不因贫穷而低她一等。四十五,苏梅字正腔圆,重音落在四上,生怕王莽听不清。
晚上李逵问他今天相亲怎么样。王莽说不怎么样,场面她在掌控,我像只温顺的小绵羊。李逵恨铁不成钢地推他一把,人家又不是情窦初开的少女,你妄想着给她当家做主吗。王莽没反驳,好像有什么难言之隐被李逵说中了。苏梅确实让他很没有成就感。其实她的外表不算老,身材保持得也很妙,如果忽略脖子上的细纹和下垂的苹果肌,四舍五入也相当于一个少女。王莽问她现在做什么工作,苏梅说近几年在专心写书,王莽又问她出过什么书,她说出过两部长篇小说,还有一本散文集。她拿起旁边马扎上的一个皮包,在里面扒拉了几下,抽出一本递给王莽。王莽两只手接过来,虔诚地看了眼书名,三个字,两个不认识,他觉得尴尬,偷偷瞄了下苏梅,她正一口烤肉一口酒,嘴角还沾了几粒芝麻和孜然,根本没在意他的反应。王莽松了口气,莫名地联想到张爱玲,张爱玲应该也会这样大快朵颐地吃烧烤。
之后苏梅来过几次电话,约王莽去游泳,王莽说练功崴了脚,下次吧,然后又请他去参加party,王莽说感冒了不能出门。李逵看不过去,说你要实在不愿意,我帮你回了她,欲拒还迎算什么意思。王莽扶着脑袋想了想,说再给我几天时间考虑一下吧。扪心自问,他还是挺喜欢苏梅的,虽然年纪大了点,但没写在脸上,那天见面的时候她画着淡妆,穿了条碎花长裙,眼神生动,肉体丰盈,看起来也会让人心动,可不知道为什么,他感觉和苏梅在一起畏首畏尾的,明明苏梅也还算温柔,但在她跟前就是拘谨,举手投足都要留心她的脸色,这让王莽大受其挫,好像辱没了与生俱来的男性尊严,他连杨彩虹都无法驯服,何况是腰缠万贯的苏梅阿姨。
本来杨彩虹接纳他的那一刻,他心里还暗暗窃喜,以为两个人会一直这样走下去,携手并肩踩高跷,踩它个海枯石烂地久天长,后来他发现事情并非想象的那么简单,杨彩虹心里揣着宏图大志,他王莽根本就不在计划之内。她早晨天不亮就起床,抱着那本《声乐基础》,爬到屋顶上去唱歌,从前团里的人还要定闹钟,杨彩虹来了以后,连闹钟都用不上,她必定要比闹钟提前一小时,把队友们都吵醒,为此女生们和她吵了好几回。起先她们不好意思翻脸,只凑在一起抱怨,李逵也位列其中,他们捂着耳朵小声咒骂,齐心协力祈祷老天爷把杨彩虹变成个哑巴,变不成哑巴,从房顶上摔下来也行。王莽说你们这样未免恶毒了点,毕竟唱得还不错。他们朝他翻白眼,你能听懂吗?王莽说,能啊,不就是首英文歌嘛。李逵说不对,好像是广东话,粤语歌。旁边女生笑道,你们两个乡巴佬,这分明是意大利歌剧。一番讨论下来,大家目瞪口呆,对杨彩虹的怨恨里多了几分敬意。慢慢地,队友们习惯了她每天早晨吊嗓子,比公鸡打鸣还准时,有时候实在觉得吵,就用被子蒙住脑袋,忍一忍就过去了,谁也不想贸然招惹一个会唱多国语言的杨彩虹。但翠翠不高兴,她眼见着众怒平息,越来越着急,为此事日夜忧心,到处煽风点火,讲杨彩虹坏话,你们知道吗,她在外面和老头儿约会!不会吧,你别瞎说。骗你干啥,我亲眼看见的。王莽听见他们嚼舌根,心里不是滋味,便制止道,说这种话可要负责任的。翠翠撅着嘴,侧眼剜他,王莽你可别胳膊肘往外拐。王莽冷笑,什么叫往外拐,你不会以为咱俩一伙儿的吧。翠翠问他你什么意思,王莽说好好炒你的菜,其他事别操心。她被戳了痛处,立马变脸,掐着腰嚷嚷道,我炒菜怎么了,你们也不过踩个高跷,都是下三滥,谁比谁高贵了。王莽懒得理她,转而去安慰杨彩虹,杨彩虹正在看《声乐基础》,书页泛黄,边角卷翘,一字一句读得认真,时不时地张开嘴巴,按照书里的方法寻找共鸣。王莽拍拍她肩膀,说你别往心里去,杨彩虹不领情,反问道,关你什么事。
三
第二次见面,苏梅似乎有点不同,她从里到外都变得柔软起来,挽着王莽胳膊,时不时倒在他怀里,说几句柔情蜜意的悄悄话,或嬉笑,或嗔怒,万种风情。相比之前的苏梅,王莽很喜欢她这样,不过或多或少,觉得她有点刻意,可能李逵在中间说了什么,所以她调整了姿态,好让王莽在她跟前顶天立地。
那是一场慈善拍卖,王莽本来不想去,李逵生拉硬拽,把他塞进一辆加长版的林肯。一个西装革履的老头儿坐在后排,两根手指夹着雪茄烟,颤颤巍巍一大截烟灰,李逵上了车,依偎过去,细着嗓子嗔怒,趁我不在又抽上了。然后他拿起一只绛红色的玛瑙烟灰缸,麻利地把烟掐灭。王莽坐在旁边,看着他们情意绵绵,不知道怎么摆放自己。李逵拉过他的手介绍说,这是王莽,然后指着老头儿说这是我干爹秦老板。秦老板笑意盈盈地点头,从头到脚把王莽打量了一遍,尤其下半身,额外多瞅了几眼,然后咂巴着嘴夸赞说,看着生龙活虎的,苏梅真有福气。王莽听出他的意思,笑了笑不知道怎么接。李逵在秦老板胸口打了一下,拖腔拉调地骂他没正经,声音娇俏,软绵绵地拐好几个弯儿。秦老板很受用,两人揽着腰亲热起来。
苏梅和几个太太聚在桌边聊着什么,手里晃着小半杯酒,脸色微红,时不时地往门厅方向瞥一眼。王莽刚进门,她便放下酒杯迎了上来。李逵老远与她寒暄,几天没见,苏老板又漂亮了。苏梅笑着在他脑门儿上戳了一下,就你嘴甜。接着她和秦老板点头示意,然后径直走到王莽身边,挽起胳膊,头靠到肩上,说我还以为你不来了。大厅里灯光浓烈,苏梅穿了件墨绿色的直襟旗袍,腰口处绣了一朵蒲公英,轻盈却不轻佻,比上次见面更多了几分风韵。王莽没想到她这么热情,整个人僵在那里。刚才那几个太太也跟过来,停在两步之外,对着王莽交头接耳,掩面窃笑。苏梅把王莽介绍给她们,其中一个披着丝巾的感叹说,老天爷啊,竟然是这么标致的小帅哥。摇白色绒扇的那个害羞道,王莽,这名字也好,听了就让人胡思乱想。另外几个小声起哄,推搡着说她下流。苏梅噘嘴笑着,不理睬众人,带王莽到一间包厢里坐下来,王莽只顾着紧张,一句话还没讲,他从没见过这么多有钱人,总觉得自己格格不入。苏梅伸出两个手指,在他胸膛上撩拨了几下,问他怎么心跳得这么厉害,说完还咬咬嘴唇。王莽心里招架不住,说天气热,穿得有点多。那就把外套脱掉吧,她顺手去扒他的衣服。衣服是李逵租来的,标签在里边还没拆,王莽怕弄坏了要赔钱,推阻她说,不用了,穿着也挺好。苏梅又招呼服务生拿酒,王莽劝她别再喝了,苏梅笑笑,如弱柳扶风,瘫在沙发上盯着他,你难道不希望我喝醉吗?王莽知道她话里有别的意思,磕巴了半天,不知道怎么回答才合适。她侧身斜卧,一条腿微微蜷缩,另外一条搭在王莽大腿上,旗袍的扣子蹭开了几个,从小腿到胸口都若隐若现,肌肤白皙,宛如莹莹月光,王莽忍不住偷偷看了好几眼。她比其他几位太太更加风姿绰约,更能挑弄人心,可说到底,他们两人之间相隔将近二十年,或许恍然间听起来也不算遥远,但二十年沧海桑田,光的速度足够在地球与太阳之间穿梭130万次。王莽思绪缥缈,心事重重,这种原本应该意乱情迷的时刻,却又想到了杨彩虹。
某个清晨,他毫无征兆地醒来,队友们还在睡着,鼾声参差错落,整晚的呼吸作用把气味变得极其糟糕。他看到外面天光漫漫,杨彩虹已经出去练嗓了,歌声在耳边时断时续,于是他胡乱套了件衣服,鼓足勇气爬上房顶。杨彩虹看见他上来,没有在意,继续对着天空唱歌剧,几颗还未熄灭的星,惨淡地亮在她头顶。王莽不敢靠近,怕招她厌烦,在距离很远的地方伸胳膊伸腿,假装锻炼。若杨彩虹红开口,他也准备好了说辞,不会让场面太难堪,可杨彩虹一首接一首地唱,始终没有理他的意思。
翠翠端着盆到井边打水,旁边是一捆待洗的阔叶青菜,她抬头打了个哈欠,看见他们二人在屋顶,气不打一处来,捏着嗓子刻薄他们,哟,爬那么高去谈情说爱,吵了老天爷,当心被雷劈。杨彩虹没搭腔,背过身去继续唱,不过声音小了一些。王莽听着她的话刺耳,没好气地说,洗你的菜去吧。翠翠脸色更难看了,她最讨厌别人这么讲,总觉得这种话是在侮辱她。她其实不想在厨房里打杂,老早就申请和其他人一起踩高跷、演杂技,团长不同意,嫌她瘦小,也不够漂亮,为此她哭闹过十回八回,甚至弃团出走了好几天,那段时间大家都以为她不会回来了,没想到有天吃午饭的时候,她又在窗口里拎着勺子打菜,戴着口罩,肿着眼泡,人家讲话她也不理。翠翠去哪儿啦?以为你发财去了。怎么回来了,是想我们吗?她低着头,满腔怨气。大家发牢骚说菜太少,再多给一点,她把勺子一摔,去你妈的,爱吃不吃。杨彩虹来团里以后,她就把所有怒火都发泄到杨彩虹那里,给别人一勺菜,给她就半勺,还要哆嗦好几下,最后到她盘子里所剩无几,两人打照面,她总要哼一声,翻个白眼,像有什么不能化解的深仇大恨。杨彩虹在屋顶上练嗓,她明里暗里地讽刺挖苦,说她要是能当歌唱家,野鸡就能变凤凰,做梦。王莽看不惯,顶了她好几回,她就连王莽一起骂。她对着屋顶大声说王莽捡破鞋,捡人家老头儿玩剩下的。王莽想下去和她理论,杨彩虹伸手阻拦,说算了,随她去吧。翠翠呸了一声,端着盆扭身进了厨房。
翠翠一走,只剩下他们两个在屋顶,晨光四起,世界开始喧嚣躁动,远处城市里的灯火渐次熄灭。难得的好机会,王莽心里有千言万语,却堵在嘴边不知道该说哪句。杨彩虹倒是没有扭捏,掏出一台随身听,拨弄了一会儿,一只耳机塞进耳朵,另一只给他递过来,王莽受宠若惊,赶忙伸手接住,内心波澜万丈,外表风平浪静。他戴上耳机,里面是一首声音很大的外国歌。好听吗?杨彩虹问他。他点点头说,好听。太阳彻底跳出地平线,光亮在人间蔓延,王莽看着她的侧脸,微风吹动发梢,她目光望向天空,像一条长满了刺的鲸鱼,始终发出与别人不同的频率,此时此刻,她忽然放松了戒备,他小心翼翼地游到她身边,呼吸脉搏全都近在咫尺,两颗灵魂无限重合。
四
拍卖的时候,苏梅花了很大一笔钱,拍下一支毛笔,说是曹雪芹用来写《红楼梦》的小狼毫,价值巨大,让王莽瞠目结舌。回去路上,他小心翼翼地问苏梅这笔有什么用,苏梅说没什么用,送给你吧。王莽不敢接,慌忙摆手,说太贵重了,我怕折寿。苏梅笑笑,转过头去,路灯的光影透过车窗,在她脸上匆匆掠过,旗袍的缎面在霓虹映照下,夜色如水般荡漾。她醒了酒,话变少了,刚才的浓情蜜意好像一场梦。他们分坐在两端,各自望向窗外,中间还隔着很大一段空白,司机从后视镜里观望两人,奇怪的气氛在狭小的空间里氲散。王莽心里酝酿了几个话题,想与她聊点什么,可似乎都没什么值得聊的,他们之间的交集太少,层次差异的壁垒很难打破,他不知道她怎么打理巨额财富,她也不会感兴趣他如何踩高跷。
车子转了几个弯,进入一条沿海公路,视野逐渐开阔起来,王莽打破沉寂,说要不聊聊你写的书吧。苏梅眼睛里闪烁了一下,问他,那本书你看过了?嗯,王莽回答说,看过了。怎么样?她盯着他,好像在期待什么。王莽点点头,说挺好的,我很喜欢。哦,苏梅听了,眼神黯淡下去,显然这种认可不足以打动她。王莽很失落,呼吸都不敢太大声,他想多说点溢美之词,可话题仓促,自己言语又匮乏,或许,她根本不是想要赞美,只是想找一个懂她的人而已。
车子停在一间别墅门前,司机从驾驶室出来到后排开门,他穿着正装,戴着白手套,站在车门边,上半身倾斜45度,恭恭敬敬地等他们下车,王莽心里百感交集,从没想过可以被这么体面的人服侍。苏梅把手包挎在腕上,款款道,家里就我自己,进去喝杯茶吧。王莽犹豫了一会儿,推辞说不早了,改天再喝吧。他明白除了喝茶,还有别的事要做,可心里还是胆怯,某种气节和正义感在作祟,使他不想太早跨过这一步,他也知道有些事做了会很快乐,可这么仓促就能得来的快乐,难免让人担忧。苏梅有点失望,但也没有强留,那我让司机送你回去,想来的时候随时可以再来,说完便下了车。王莽忽然想起她的那本书,有一篇是关于她去世的丈夫,他探出脑袋问她,你还会留恋以前的人吗?苏梅回过头来,愣了两秒钟,笑了笑说,不会。她笑得很有耐心,像是大人安慰小孩子的那种笑。王莽点头答应,心里却感到惭愧,觉得很对不起她,她努力要拉近两个人的距离,而他一个问题便让她前功尽弃了。
晚上睡觉的时候,王莽睡得不安稳,而且做了一个很长的梦。父母带他去了一个闹哄哄的地方,人来人往,吵闹无比,王莽不耐烦,问他们来这里做什么,母亲食指堵在嘴上,示意他小点声,我们是来相亲的。他心想,相亲就相亲,怎么还偷偷摸摸?而后他感觉口渴,在一望无际的荒漠里寻找水源,发现远处有个熟悉的身影,仔细分辨,竟然是苏梅,她转过头来对他微笑,温柔静默,眉目含情。王莽高兴地跑过去,说你怎么在这儿。仔细一看,她身穿校服,扎了两根马尾辫,腮脸细滑,大概只有十几岁的样子。没等苏梅回答,有一列火车呼啸驶来,停在他们身边,乘务员冲他们招手,说本次列车开往西伯利亚,已经为你们预留了两个座位,他和苏梅相视一笑,牵手跨上了车。
汽笛声嗡嗡作响,火车开始穿山越岭,外面云雾弥漫,虽然没有太阳却到处流光溢彩,穿过很长的隧道后,世界变成广袤无垠的湖,金色的诗句如流星般从天上坠落,掉在湖面上燃起熊熊烈火,而后变成一朵朵绽放的花。光影变幻间,苏梅不知所踪,王莽走进一个空旷的村子,独自穿行在五彩斑斓的瓦墙之中,急切地呼喊她的姓名。飞檐下撑着巨大的伞,一群人在那里举行盛宴,门口有位身着长袍的白胡子老人。王莽问他是谁,他说他是这场宴席的司仪,名叫曹雪芹。王莽又问他有没有见过苏梅,他说朱颜辞镜花辞树,太阳只是一个巨大的表盘。而后丝竹管弦响起,宴会即将开始,王莽心里着急,苏梅丢了,你让我进去找找。他摇头晃脑地朗诵道,蝴蝶路过人间,琉璃是南方的翅膀,满船清梦压星河,时光将要打开罪恶之门。最后他俯下身,把一支毛笔系在王莽腰间,说哪儿来的就回哪儿去吧。
清晨,王莽翻身时被什么东西硌醒,抓过来一看是拍卖会上的那支小狼毫,装在镂金的黄花梨木盒里。他搓着眼睛回忆了半天,不记得苏梅什么时候塞过来的。他用被子蒙住头,想继续睡,但想到夜里那个梦,辗转反侧,难凉热血,心里多了很多渴望与幻想。很多话苏梅没有说清楚,他也不敢过分揣测,他很想接受她的示好,以及一些肉体上的暗示,可似乎总有些看不清的屏障横亘在中间,他不想为了一时之快而委屈了谁,这对两个人都不公平。当初杨彩虹说香港是大城市,她要去那里唱歌,王莽以为只是赌气的话,他没想到有人会这么不服输,不认命。他们坐在屋顶上,远处山顶的信号灯忽明忽灭,王莽正暗暗盘算着两个人日后的生活,心里充满无限美好。杨彩虹问,你会跟我一起走吗?她脸上满是忧郁,话也轻飘飘的,给谁听都是随便说说的语气。王莽没太在意,抓过她的一只手,揣在怀里,慰藉道,慢慢来,一切都会好的。她点点头,没再说话,跟着耳机里的旋律哼了起来。几天后,一个平凡的早晨,杨彩虹走了。那天艺术团要下乡去演出,为一个大户人家的葬礼助兴,但杨彩虹没有起来练嗓,害队友们睡过了头,大家一边匆匆忙忙地穿衣服,收拾演出行头,一边埋怨杨彩虹天天鬼哭狼嚎,关键时刻掉链子,长久以来积攒的不满,全在这天早晨爆发出来。他们说杨彩虹故意的,就是想让大家迟到,并扬言如果因此丢了饭碗,绝对要让杨彩虹好看。等大家收拾完毕准备出发的时候,有人发现杨彩虹还没起床,他们以为杨彩虹在耍脾气,骂得更狠了,说真不要脸,以为会唱几首外国歌,就成大腕儿了,就是就是,野鸡还想变凤凰,不知道自己几斤几两。他们骂了半天仍旧不见动静,不知道谁,跑到墙脚掀开被子一看,杨彩虹没了。仓库里的吵闹突然平息,外面阳光照进来,灰尘在半空中飘摇。王莽心里有一种不好的预感,他撂下手里的东西,忙不迭地跑过去,掀开她的枕头,到处摸索。人家问他找什么,他也不吭声,把凉席掀起来抖了半天,什么都没有。随身听和《声乐基础》,她全拿走了。
五
外面阴云密布,今天没有演出,不知道谁的闹钟突然响了,声音急促,把队友们全都吵醒,屋子里一片怨声载道,王莽也吓了一跳。自从杨彩虹走后,团里的作息被打乱,少了她的歌声,大家都觉得缺点什么。
王莽起身,随便披了件衣服,想爬到屋顶上去透透气。外面下着丝丝细雨,翠翠起得比他还早,正在院子里练习踩高跷。两个人的目光撞到一起,王莽想与她说点什么,以便缓和僵硬的关系,她却一身傲骨,撇过头去不肯看他。杨彩虹走后,因为找不到其他人顶替,翠翠终于得到了表演机会,可她身形弱小,每次表现得都不出色,有几回还从高跷上摔下来,直接影响了演出效果。团长严词厉色地警告她,如果再出现这种问题,别说踩高跷,菜也不用炒了,直接滚蛋。她流着泪说不会的不会的,一定好好努力。于是她每天比别人早起一个多小时,梳妆打扮,然后去院子里练习各种动作,王莽睡觉很轻,有时候睡梦中会听见外面沉闷的响声,就知道她又摔跤了。翠翠身上经常青一块紫一块的,人家问她这是怎么了,她说关你什么事,人家问她是摔的吗,她说放屁,然后大家笑话她,个子虽矮,心比天高,她不服,歪着头反驳,气急了就朝人家吐口水。下过雨的院子湿滑,王莽提醒她要小心一点。她回过头来,瞪了他一眼,说知道了。语气还是那么硬,但态度柔和了不少。王莽发现自己不再像从前那样讨厌她了,甚至某些瞬间,她吃力的身影会让他想起杨彩虹。
下午王莽叫了辆出租,他想去把那支昂贵的小狼毫还给苏梅。刚坐上车,有一辆加长版的林肯开过来,停在旁边没有熄火,王莽觉得眼熟,想了想,应该是秦老板的车,果然没多久,李逵急匆匆地从屋里跑出来,穿着一身花花绿绿的衣裳,肘上还挎着一个名牌包。王莽摇下车窗问他去哪儿,他说要和干爹去打高尔夫,你呢,你去哪儿?王莽说我要去找苏梅,李逵坏笑着给他鼓掌,加油,尽快拿下。王莽懒得接茬,提醒他脸上护肤品没抹匀,他惊声尖叫,谢天谢地,幸亏你提醒我。
出租车行驶了近一个钟头,抵达苏梅的别墅时,天已薄暮。王莽按了几下门铃,没人开门,雨骤风急,他又没有带伞,只好抱着双臂,蜷在门廊下等她。他今天一定要把那支笔还给她,因为它实在是价值连城,他对他们的未来抱有期许,所以想有一个干净纯粹的开始,有些事他可以将就苏梅,也希望有些事苏梅可以将就他,最好的爱情是在彼此容忍和将就中产生的,她比他大了二十岁,肯定明白这个道理。他把苏梅写她丈夫的那篇文章读过好几遍,不认识的字都查了新华字典,隐约间,他好像明白了要如何放下那些已经失去的东西,无用的思念如同对着深渊呐喊,一叠一叠,一浪一浪,再怎么大声也不会有回响,他也是时候斩断情丝忘记杨彩虹了。
苏梅回来时,天已经完全黑了,凉风的侵袭让王莽止不住地发抖。车子停在门前,司机从驾驶室出来给她开门,苏梅缓缓下车,身上披了一件鹅黄色的织锦披肩,里面换了一件白色的连衣裙,点缀着几朵浅淡的梅花。她见到王莽,愣了一下,你怎么来了?王莽忘记事先给她打招呼,自己也觉得鲁莽,说实在抱歉,打扰你了吗?她无奈地摇摇头,脸上很复杂。随后车里下来一个年轻男子,慌忙跑过来,给苏梅撑伞,苏梅看了男子一眼,又眼神悲悯地看看王莽。王莽见他和自己差不多年纪,面目清俊,唇红齿白,大概明白了什么意思。
男子穿了身整齐的休闲装,戴着一副无框的眼镜,风度翩翩,温文尔雅,笔直地站在苏梅身后,身体与她轻轻贴在一起,看起来很是般配。王莽觉得自己多余,往后退了两步,心想他应该是个读书人,如果苏梅也问他对那本书的看法,他肯定有很多中肯的意见可以发表,不像自己,只会说些冠冕堂皇的废话。苏梅说外面雨大,咱们进去说吧。王莽说不了,我还要赶着回去,他从内侧的衣兜里掏出那个黄花梨木盒,递给苏梅,我来把这个还给你。苏梅看了看,没有伸手接。王莽低着头,脚边的水滴溅起来,又落下去。雨下得越来越密,敲在伞上的声音让人意乱如麻。王莽沮丧地解释,我后半辈子可能一直踩高跷了,不配拥有这支笔。他虽然言辞不卑不亢,心里却有点悲凉,本以为将来还有很多戏,结果自己不是主角。苏梅还是没有应答,王莽不知道她脸上什么表情,他也不打算去看了,希望就以这种怯懦的姿态,尽快结束这尴尬的碰面。沉默了很久,苏梅说,你留着吧,做个纪念。王莽说不需要纪念了,谢谢。然后把盒子塞进她手里,转身走进了茫茫大雨之中。
他没有带返程的路费,只能徒步往回走,走着走着,开始疯狂地奔跑起来。汽车堵在城市中央,行人来去匆匆,夜色茫茫,无边无际,王莽感觉两条腿似乎在一瞬间失去了知觉。某个拐角,他失足跌倒在路边,磕破了膝盖上的一层皮,鲜红色的血倏地渗透出来。路灯的光被雨水打碎,疼痛从里到外撕扯着他,孤独如同野兽,从四面八方侵袭,原来两个人的频率不会因为时空距离的远近而变化,无论靠得多近,有一些细小的声音还是只有自己听到。意大利歌剧的旋律不断在他脑海跳跃盘旋,他忽然想起那个平凡的早晨,杨彩虹离开之前,曾经在他耳边悄悄告别,我要走了,去香港,我们永远不会再见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