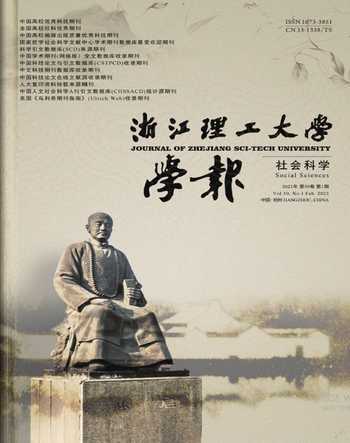诉源治理视域下法院角色定位的进与退
2023-08-31吴静尚润泽
吴静 尚润泽
摘 要: 作为“枫桥经验”在新时代的创新发展,诉源治理能有效缓解人民群众与日俱增的解纷需求同人民法院日益紧张的司法资源之间的矛盾,使纠纷消解于萌芽状态。囿于当前司法实践及学理上对法院的诉源治理角色定位不明,有的法院在推进诉源治理过程中出现“过度退缩”或“过度冒进”的异化现象,有悖于诉源治理设计的初衷,难以发挥其制度上的效用。鉴于此,有必要从理论层面厘清法院在诉源治理中的应然角色定位,防止出现角色反差及功能失调。回归法院参与诉源治理的正当性基础,以及基于对现实与理论逻辑的双重考量,法院应积极投身于诉源治理实践并承担参与者角色,在“源头预防”“诉前调解”“司法裁决”三个不同阶段发挥递进式作用。
关键词: 诉源治理;基层治理;枫桥经验;法院角色;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
中图分类号: D926.2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673-3851(2023) 02-0119-06
Advance and retreat of the role of court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governance of litigation source
WU Jing1, SHANG Runze2
(1.Zhejiang Hangzhou Intermediate People′s Court, Hangzhou 310008, China; 2.Anhui Hefei Luyang Primary People′s Court, Hefei 230001, China)
Abstract: As the innovative development of Fengqiao Experience in the new era, the governance of litigation source emphasizes source governance of conflicts and disputes, which can relieve tension and strain effectively between people′s increasing needs for dispute resolution and decreasing judicial resources of people′s courts and curb the increase in conflicts and disputes from the source and in the bud. However, subject to restrictions on the vague role of governance of litigation source of courts in judicial practice and in theory, there appear alienation phenomena of excessive retreat or advance of courts in process of practicing governance of litigation source, which is contradictory to the original design intention and is difficult to maximize value of system of governance of litigation source. Therefore, it is necessary to clarify the ought-to-be role of courts in governance of litigation source so as to prevent malposition and dysfunction. Returning to the legitimacy basis of participation of people′s courts in governance of litigation source, and considering both the reality and theoretical logics, courts should devote actively to the practice of governance of litigation source, take on the role of participant, and then play a progressive role in three different stages, namely "source prevention, pre-litigation mediation and judicial decision".
Key words: governance of litigation source; grassroots governance; Fengqiao Experience; role of courts; diversified dispute resolution mechanism
在訴源治理视域下,法院所扮演的角色应当与审判权在国家、社会中的权利、义务和行为模式相一致。若法院在诉源治理中出现角色不清等情形,便会产生应然角色与实然角色的反差,从而造成法院的功能失调[1]。关于法院在诉源治理中的角色定位问题,理论界存在较大争议。有学者认为,诉源治理实质上是法院运用非诉化的手段辅助政府及其职能部门的行政性治理[2];也有学者认为,法院在诉源治理中处于司法断后而非前置主导的角色,不宜在司法治理之外主动广泛地挖掘矛盾纠纷[3]。实践中,不乏有法院基于司法能动主义的错误认识和政绩追求,在诉源治理中出现角色反差及功能失调。总的来看,各界仍未将法院在矛盾纠纷的“源头预防”“诉前调解”“司法裁决”三个阶段中扮演何种角色进行精细化、精准化定位。
以法院为代表的司法机关参与诉源治理何以正当?法院系诉源治理的参与者还是主导者?法院在诉源治理中的三个不同维度分别发挥何种作用?为了回答上述问题,本文首先分析法院参与诉源治理过程中的异化现象。其次,立足本土化思维审视现代型法院与基层社会治理间的关系及界限,厘清政治机关与审判机关双重属性,指出法院动态调整司法理念主动参与诉源治理的正当性基础。最后,以卢曼系统论为指引,提出法院在不同阶段的递进式角色定位,克服“法院中心主义”倾向产生的“去界分化”风险。
一、困局:法院在诉源治理中的进退失据
改革开放以来,伴随着内生型权威的日渐式微,宗族长老等传统精英作为化解基层矛盾纠纷的主力地位逐渐丧失,加之法治理念的不断普及深入,权利意识和规则意识逐渐在基层民众心中“生根发芽”。人们也逐渐抛弃了内部柔性化解纠纷的理念,转而寻求国家审判机关等外生型权威解决纠纷。近年来,“诉讼爆炸”的现象深刻反映了人民法院逐步取代基层社会内生型权威的地位,成为基层纠纷化解主力军的现实境地。但这种主要仰赖诉讼解决社会纠纷的模式开始显露不少弊端,引起了实务界及学界的高度关注。
“治政之要在于安民。”评价任何解纷路径的优劣,均要以纠纷化解效果为导向,此外,是否促进了社会和谐稳定亦是一项重要的衡量标尺。相较于单一的诉讼解纷模式而言,以诉源治理为目标的非诉讼纠纷解决机制在破解基层社会矛盾和社会冲突方面具有无可比拟的优势,这也在全社会尤其是司法实务界形成了普遍共识。诉源治理作为“枫桥经验”在新时代的创新发展,强调对矛盾纠纷的源头治理。其通过在不同层次采取有针对性的纠纷预防和化解措施[4],密植递进式分层过滤矛盾纠纷体系,促使矛盾纠纷解决在基层、化解在萌芽,实现了矛盾纠纷化解从“治已病”到“治未病”的重大转变。诉源治理的提出和有效推进,回应了人民群众与日俱增的解纷需求同有限的司法资源之间的结构性矛盾,是符合中国情境、彰显“东方智慧”、顺应司法规律、具有本土特色的矛盾纠纷化解“新时代路径”。
当前,诉源治理正在全国各级法院如火如荼开展。尽管不少法院的诉源治理工作取得显著成效,但不可忽视的是,实践中同样存在部分法院参与不当的异化现象,主要体现为“能动”与“克制”的认识模糊,“前进”和“后退”的角色混乱,以及“治理”与“裁判”的逻辑混淆:一方面,有的法院对诉源治理仍心存顾虑,认为这会将法院从化解社会矛盾纠纷的“最后防线”推至“第一线”,有突破司法被动性之嫌,因而不愿主动参与;另一方面,有的法院对诉源治理的认识存在偏差,认为其应处于诉源治理的主导地位,对社会矛盾纠纷不分情况地大包大揽,过度介入尚未成讼的社会纠纷。究其根源,主要是由于实践中的探索不足与理论上的众说纷纭,由此引发了法院在诉源治理中角色定位模糊的问题[3]。此外,囿于法院长期以来承担纠纷化解“主力军”的固有路径,部分地方党委、行政机关等承担社会治理职能的机构尚未破除“单线作战”的机制藩篱和“有纠纷找法院”的思维定式,陷入矛盾纠纷源头化解功能弱化和主动性式微的桎梏之中。对于“法院主导型”的诉源治理模式,依然存在“让子弹飞一会儿”的观望态度。
二、回归:法院参与诉源治理的正当性基础
法院作为裁判机构,其权威来源之一便是客观中立。实践中,不少法院或是心存顾虑而止步不前,或是随意而为、以政绩为先。有学者对某市中级法院及其下辖基层法院诉源治理活动进行实证分析后指出,既有实践存在有损法官“中立”角色、超出能动司法界限的伦理风险、架空立案登记制、模糊诉中调解与和解的界限、冲击国家机关职能分工的法治风险,以及诱发纠纷非实质性化解、人案矛盾非有效缓解的技术风险[5]。鉴于此,有必要从理论上对法院参与诉源治理的正当性基础予以证成,引导其主动投身于诉源治理的实践。
(一)破除审判权良性运转障碍的现实需求
在当代中国社会变迁与国家转型的现实语境下,纠纷数量激增、种类日趋复杂,“诉讼爆炸”现象在民事司法领域早已稀松平常[6],“案多人少”及“案结事不了”的矛盾由此愈发激化。“案多人少”凸显的是汇聚于法院的大量诉讼案件与法院有限审判资源之间存在巨大鸿沟,“案结事不了”折射的是纠纷经过法院的裁判处理后仍然无法得到真正化解的尷尬境地。前者表现了审判机关在面对司法需求过载时的无能为力与无可奈何,后者则反映了司法裁判权威性与有效性的不断消减与日渐式微。可以说,这两大障碍极大地制约了审判权的良性运转,不利于司法公正与司法效率的实现。
面对审判权在超负荷运转之下出现的功能失灵困境,作为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的重要举措之一——诉源治理由此应运而生。有别于传统型纠纷解决机制,诉源治理不仅着眼于“治标”,即缓解当下的人案矛盾,更注重“治本”,即强调从纠纷源头上治理,从长远上减少诉讼增量。具体而言,在诉源治理视阈下,矛盾纠纷的治理过程可进一步划分为前端解纷、诉前解纷与诉讼解纷三个阶段。通过全面构建递进式的矛盾纠纷分层过滤体系,前移解纷端口,下沉解纷力量,从“事后救济”转为“事前预防”,让大量矛盾纠纷于生发之处得到关照,于萌芽之际得到调和,于诉至法院之前得到解决,在诉讼之端得到处理,有效避免大量纠纷进入审判程序,尽可能减少衍生案件的产生,进而达到“人案平衡”和“案结事了”的目标,破除审判权良性运转的障碍。
(二)满足人民群众多元解纷需求的应有之义
随着社会主要矛盾的转化,人民群众对公平正义的理解日渐具化,对实质正义的追求日渐强烈,对多元解纷程序的需求日渐突出[7]。人民法院具有的化解矛盾、定分止争、救济权利的司法功能,理应在多元解纷中有所作为。然而,从法院发挥司法功效的传统路径观之,法院往往是以事后的生效裁判对业已成讼的纠纷作出最终定论,难以从根源上起到预防和化解矛盾的效用。更何况,对于合法权益已然受损的当事人来说,选择诉讼方式来解决纠纷,还需经历漫长的等待以及承受高昂的诉讼成本,无疑是雪上加霜。简言之,法院凭借以往单一的司法裁判功能已无法满足当今纷繁复杂的社会需求,且裁判的局限性也昭示了向法院提起诉讼并非是最佳、最有效的解纷方式。
相较司法裁判在回应社会需求上表现出的“力不从心”,诉源治理能有效弥补传统诉讼解纷方式之不足。通过聚焦诉源治理这一基层社会治理现代化目标,在纠纷解决机制的建构与完善进路上发力,实现从单一司法诉讼“独木桥”到多部门齐抓共管解纷“立交桥”的转变,构建符合规律、高效便民、共同发力的多元解纷路径,让当事人以低成本、低诉累方式解决纠纷,将矛盾纠纷置于基层和萌芽状态化解。申言之,诉源治理为处于冲突之中的当事人增设了除诉讼以外的更多自由选择,提供了多层级、多门类、多主体纠纷解决方式的机会,实现纠纷化解中的“帕累托最优”[8]。
(三)促进基层社会治理法治化的必由之路
与行政权天然具有的主动性与扩张性不同,司法权的运行表现出被动性与中立性的特征。有鉴于此,长期以来司法权始终以消极司法的姿态游离于社会治理体系之外,以审判为首要职能的人民法院也并未被认作是传统意义上的社会治理主体。然而,伴随社会主要矛盾的转变,司法资源分配的不平衡、发展的不充分与人民群众日益多元的解纷需求之间的矛盾愈加明显,消极司法对于解决社会纠纷、修复社会关系、创新社会治理的能力日益弱化。相反,积极司法强调司法活动是社会治理的关键面向和有力抓手,法院应以积极、主动的姿态践行司法为民理念,提升社会治理法治化水平[7]。
诚然,法院的基本角色定位是裁决纠纷,但并不意味着这是法院唯一的工作职能。现代型法院往往在发挥上述基本功能的前提下,行使着其他功能[9]。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提出了党委领导下的多元共治社会治理体系,其中强调了司法权的合理运用在完善社会治理格局的法治保障功能。实际上,行使审判权的人民法院,在法律领域具有的专业性和权威性的优势,能够为社会治理法治化和基层治理现代化提供专业的法律指导及方向引领,从而促进基层社会治理的自我完善与自我发展,这与积极司法的理念不谋而合。因此,法院主动参与诉源治理,并非是对司法权基本特征和固有司法规律的突破,而是为适应时代需求和完善社会治理对司法理念作出的动态调整。从消极司法到积极司法的转变,能够有效克服消极司法在社会治理中的参与不足,充分发挥基层社会治理过程中的法治保障作用。
三、澄清:法院系诉源治理的参与者而非主导者
当前,学界及实务界关于法院在诉源治理中应承担主导者还是参与者角色的问题存在较大争议。有观点认为,考虑到司法解纷的专业化,以及实现基层治理法治化乃诉源治理的制度目的,诉源治理应采法院主推下的多元共治机制[7];有观点则认为,诉源治理强调于源头处消弭纠纷,其很大程度上依赖多元社会力量的共同参与,特别是党委于其中发挥的领导作用,故法院不可能成为诉源治理的主导者[10]。相较而言,后者更值得肯定,主要是基于对现实及理论逻辑之双重考量。
(一)现实逻辑:法院无法成为诉源治理主导者的现实因素
诉源治理是一项多方共同参与的系统工程,法院不具有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统筹能力。正如《法治中国建设规划(2020—2025)》提出的“整合基层矛盾纠纷化解资源和力量”之构想,诉源治理通过搭建全社会共同参与的社会矛盾纠纷解决平台,实现行政部门、审判机关、仲裁机构、调解组织、公证机关等主体的协调联动,引导各类解纷机制积极参与、多元共治、各取所長、各尽其能。就社会治理的中国语境而言,党的领导是诉源治理工作取得实质性成效的根本保证。坚持党的集中统一领导和全面领导制度,充分调动社会各方力量共同参与,汇聚起强大的基层社会治理合力,从而推动形成人员联动、力量联动、资源共享的诉源治理工作格局。相较于党委强大的统领能力,法院显然无法以一己之力汇聚诉源治理过程中多元主体的思想共识,也无力统筹协调社会各界共同有序参与诉源治理大局。有相当一部分基层法官坦言:“在社会矛盾化解中,人民法院的力量仅仅是其中很小的一部分,在社会综合治理这台高速运转的大机器面前,人民法院扮演的角色仅是修理维护的作用。”[11]
诉源治理是对矛盾纠纷积极主动地进行源头治理,而法院以审判为主的职能决定其不宜成为诉源治理的主导者。一方面,法院主导诉源治理将造成本职工作的本末倒置。法院是国家的审判机关,通过审判维护权益、解决纠纷、捍卫公平乃法院天职所在。法院的首要职责会是、仍然是且将始终是司法审判[8]。一旦法院成为诉源治理的主导者,就意味着其将原本花费在审判工作的大部分精力转投至社会治理领域,俨然从司法裁判者倒置为社会治理者。另一方面,即便是在司法能动主义的语境下,司法审判职能并非可以无限度延伸。特别是在尚未成讼纠纷的解决初期,法院更应努力避免司法审判职能触角的过度扩张与蔓延。一旦司法权过度延伸,将产生法院主导下的诉源治理异化风险[3]。将法院置于诉源治理主导者角色,无疑是过分强调司法能动主义与过度延伸法院司法审判服务的体现。
(二)理论逻辑:法院主导下的诉源治理模式将引发系统风险
将诉源治理纳入系统论视阈下进行理论分析,可以发现法院主导下的诉源治理模式将会引发相应的系统风险。依据卢曼(Luhmann)的系统论,社会是由不同的功能子系统构成,各个子系统以“结构耦合”的形式相互影响,并通过沟通媒介和特有的二元符码,解决子系统与环境之间的复杂关系[12]。法律系统是社会的一个功能子系统,具有自我观察、自我反思的能力以及“自我指涉”和“外部指涉”的特性,亦即通过系统的“运作封闭性”与“认知的开放性”来保证自身的独立性和自主性[13]。
一方面,系统的正常运行要求各子系统之间严守彼此界限,实现各自功能的特定化。功能的特定化限定了系统操作的具体界限,且能够通过对规范运作的取向而被承认。丧失了功能特定化,系统也就失去了存在的必要性与可能性[14]。因此,审判系统作为法律系统的子系统,也应在法律的特定功能范围内活动。令人遗憾的是,在诉源治理这一基层社会治理子板块推进的过程中,边界思维并没有在地方内部树立,部分地方将大量社会治理事务导流至审判机关。即便是审判机关都没有对自身功能的理解保持理性克制,常常以能动司法之名承担起社会治理“排头兵”角色,肇致审判系统与其他系统间的界限愈发模糊不明,引发审判系统在诉源治理的“去界分化”风险。
另一方面,系统的正常运行要求各子系统严守其内在的自主性,且不得越界对其他子系统的功能造成倾轧。由于没有任何子系统能够在功能上相互代替对方,故而每一个子系统相应地具有一项独特的功能。可见,子系统的自主性是关乎全系统协调运转不可或缺的关键属性[13]。反观现实,某些法院通过“法官进网格”的形式,安排干警定期前往街道、社区驻点,甚至对诉前阶段的家事纠纷提前介入,先行启动程序调查事实,指导当事人起诉、收集证据、申请人身保护令等,俨然充当起当事人“法律顾问”的角色。这种现象反映出部分法院还未在诉源治理工作中找准自身的定位。倘若法院没有对“自我差异性”的固守,越俎代庖将属于其他组织的职能揽入怀中,这势必将扭曲审判系统自身的运行轨道。当审判系统放弃与其他系统及外部环境的沟通,主动将其置于诉源治理的主位之上,担负起纠纷化解综合性平台的主导责任时,便脱离了自身系统赖以存在的“运作上的封闭”,难免会陷入“开放系统”回归的窠臼中。
四、重构:法院在诉源治理中的应然定位
针对目前部分法院在诉源治理中出现的“过度退缩”及“过度冒进”两类不当实践,应在理论上厘正其应然角色定位并作出相应调整。如前所述,正因法院参与诉源治理有其正当性,故其应投身于诉源治理实践并发挥作用,即要适度地“进”;同时,立足于现实与理论两大逻辑,法院亦不能在诉源治理中占据主导或过度参与,即要适当地“退”。放眼诉源治理的三个层次,法院在这三个阶段发挥的作用应有所不同、有所侧重,呈现出明显的递进态势。
(一)源头预防为先:前端解纷中有限参与
在“源头预防为先”的第一阶段,法院在前端解纷环节需要从“以我为主”转为“有限参与”,坚持在党委领导的诉源治理格局中发挥法治保障作用,不过于主动介入矛盾纠纷,避免突破司法权固有属性。
一方面,要坚持党委领导下的诉源治理机制。各级法院应以更加积极的态度参与党委领导下的社会治理体系,在统筹协作中适时发挥审判机关的系统性功能,助力矛盾纠纷源头治理,让大量矛盾纠纷预防、排查、化解在萌芽,解决在当地。以浙江的改革实践为例,可以发现当前法院已由最初的“引领者”转变为如今的“参与者”角色,诉源治理工作机制不再如以往一般紧紧依附法院运作,而是过渡为多方共同参与的一站式解纷平台[3]。具体而言,依据各地实际情况,浙江法院将诉讼服务中心的整体或者部分(成建制)入驻党委政法委牵头设立的社会治理综合服务中心(信访超市),以信访超市为诉源治理的中枢平台与指挥纽带,由其统一受理矛盾纠纷、划分类别、并分流至不同调解主体进行化解等工作。法院则依托该中心有序参与到诉前矛盾纠纷调解工作,纠正了以往仅依靠法院“单打独斗”的诉前矛盾纠纷化解模式。
另一方面,要发挥法治保障作用但不僭越固有司法职权。诉源治理是对矛盾纠纷的综合治理与协同治理,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的诉源治理新格局需要各治理主体的分工合作和有序配合[15]。在党委领导的社会治理体系中,法院应立足本职,着重发挥司法在完善基层社会治理中的保障作用。基于法院在纠纷解决方面的高度专业性与法律权威性,法院可通过法律咨询、业务培训、实地指导等方式,加强对各类调解组织的业务指导,助推矛盾纠纷多元化解机制的向上发展[16]。同时,法院也要牢固树立“司法并非是社会矛盾纠纷化解的第一道防线”底线思维,避免过度挖掘、介入社会矛盾,防止自身沦为化解社会矛盾纠纷的“第一责任人”。
(二)非诉机制挺前:诉前解纷中积极引流
在“非诉机制挺前”的第二阶段,法院在诉前解纷环节需要坚持把非诉讼纠纷解决机制挺在前面,在不违背当事人意思自治原则下,引导鼓励其优选和解、调解等诉外纠纷解决方式化解矛盾,积极促使诉前纠纷向诉讼外其他解纷方式引流。
一方面,要加强诉前多元解纷机制的联动。诉前多元解纷联动工作的开展离不开多方参与和共同合作。法院要积极转变以往独自化解矛盾纠纷的工作思路,着重加强纠纷化解的社会化、专业化、类型化运作体系构建,推动更多法治力量向引导端和疏导端发力,打造各方有序参与诉前矛盾化解的全新格局。其中,针对当地收案量较大的类型化行业纠纷,可通过设置相关行业协会诉前调解程序,如由银行业协会负责对金融借款合同纠纷的先行调解,以此发挥行业调解组织的专业化优势,大幅降低进入诉讼程序的类型化纠纷数量,最大程度实现“行业纠纷由行业解决”的良好治理效果。
另一方面,要强化对司法确认程序的适用。司法确认程序通过赋予调解协议强制执行力,将人民调解委员会的调解成果在法律层面予以固定,使大批经过调解程序的矛盾纠纷化于未发、止于未诉。这对于支持和保障人民调解组织发展、提升纠纷解决效率、明确法律规则、稳定法律关系发挥了积极作用。为解决当前司法确认程序在实践中适用比例不足的问题,法院应主动向前来立案的当事人告知司法确认程序的内容及优势,提高当事人对司法确认程序的认知程度与可接受度,鼓励引导其选择司法确认程序高效化解纠纷;同时,将司法确认案件的承办数量和办案质效等情况纳入法院日常工作考核,进一步强化办案人员办理司法确认案件的内生动力,切实提高矛盾纠纷的诉前化解率。
(三)法院裁判终局:诉讼解纷中主动作为
在“法院裁判终局”的第三阶段,法院在诉讼解纷环节需要立足自身审判职能主动作为,努力提升诉讼案件审判质量,及时进行判后答疑消除当事人疑惑,增强人民群众对司法裁判的信服感和满意度,实现息诉服判和案结事了。
一方面,要精准推进案件繁简分流。在当前司法资源愈发紧张的现实语境下,推进案件繁简分流、轻重分离、快慢分道,能够有效破除资源配置不平衡、解纷力量不均勻、解纷规则不健全的藩篱,推动诉源治理实质化进程。在分流环节,通过加强“人工智能+繁简分流”的深度融合,由机器进行自然语言识别,将抽取的案件关键要素与事先建立的繁简分流标准进行比对,从而实现对繁简类别的科学精准分流。在审理环节,一是推进简案快审,通过建立速裁快审团队,促进诉调对接实质化,诉讼程序简捷化,做到应调尽调、当判则判,从简从快办理简单案件,切实减轻当事人诉累,避免诉讼延迟带来的不正义;二是推进繁案精审,使承办法官得以集中精力办理疑难复杂要案,通过类案推送、智能检索、专业法官会议等举措,降低其在认定事实、适用法律的出错几率,减少上诉、改判及发回重审案件数量。
另一方面,要规范完善判后答疑程序。判后答疑既是审判工作的重要“后半场”,也是强化诉源治理效果的最后关键举措。通过出台规范性文件来完善判后答疑程序,依法向不服法院生效裁判的案件当事人进行释法说理,有助于促进当事人对生效裁判的息诉服判,从源头上减少一审案件衍生出的二审、再审、执行、信访等案件。具体可借鉴浙江高院有关判后答疑的程序性规定,明确判后答疑的适用情形、工作原则、责任主体、答疑流程、后续处理等内容。例如,参照《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关于判后答疑的若干规定》第2条、第6条及第7条的相关规定,法院在收到当事人提出的判后答疑申请后,由原承办法官对案件审理及制判过程中的程序适用、证据采纳、事实认定、裁判理由等向当事人进行解答,全程做好答疑记录,并根据当事人申诉有理与无理两种情况分别作出不同的处理。
五、结 语
作为一项系统性、全局性工程,诉源治理涉及多个社会治理角色的相互配合,这一过程需要打破诸多壁垒、建构多项机制、统筹多方利益,依靠法院在地方政治生态中的力量,显然难以为之。因此,地方党委能否转变思路,切实承担起“中军帐”的职责,进而使成员单位之间打通隔膜、共享资源、合作共谋,决定了诉源治理的最终成效。人民法院唯有在党委领导下,遵循“到位但不越位”的原则,把准进与退之间方寸,方能发挥其在诉源治理中的正向功效,在完善基层社会治理、维护社会稳定发展中贡献司法力量、彰显司法担当。
参考文献:
[1]施新州. 人民法院在国家治理中的功能定位分析[J]. 治理现代化研究, 2019(1): 44-52.
[2]曹建军. 诉源治理的本体探究与法治策略[J]. 深圳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2021, 38(5): 92-101.
[3]吴明军, 王梦瑶. 诉源治理机制下法院的功能定位[J]. 行政与法, 2020(7): 87-95.
[4]郭彦. 共建共赢 内外并举 全面深入推进诉源治理[N]. 人民法院报, 2016-12-28(08).
[5]周苏湘. 法院诉源治理的异化风险与预防:基于功能主义的研究视域[J]. 华中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0, 34(1): 28-37.
[6]左卫民. 通过诉前调解控制“诉讼爆炸”:区域经验的实证研究[J]. 清华法学, 2020, 14(4): 89-106.
[7]侯国跃, 刘玖林. 乡村振兴视阈下诉源治理的正当基础及实践路径[J]. 河南社会科学, 2021, 29(2): 18-27.
[8]苏力. 关于能动司法与大调解[J]. 中国法学, 2010(1): 5-16.
[9]左卫民. 司法审判职能之分化: 傳统型与现代型法院制度的比较研究[J]. 学术研究, 2001(12): 124-130.
[10]周苏湘. 法院诉源治理的异化风险与预防:基于功能主义的研究视域[J]. 华中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0, 34(1): 28-37.
[11]张素敏. 美丽乡村建设背景下人民法庭参与诉源治理的进路[J]. 沈阳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1, 14(4): 1-6.
[12]泮伟江. 探寻法律的界限:论卢曼晚期系统论法学思想[J].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1, 34(1): 22-30.
[13]卢曼, 韩旭译. 法律的自我复制及其限制[J]. 北大法律评论, 1999(2): 446-469.
[14]杜健荣. 卢曼法社会学理论研究:以法律与社会的关系问题为中心[M]. 北京: 法律出版社, 2012: 198.
[15]钟明亮. 法院在诉源治理中的角色定位及完善[N]. 人民法院报, 2020-01-09(08).
[16]李少平. 传承“枫桥经验”创新司法改革[J]. 法律适用, 2018(17): 2-10.
(责任编辑:秦红嫚)
收稿日期:2022-02-20网络出版日期:2022-11-14
作者简介:吴 静(1993-),女,海南东方人,法官助理,硕士,主要从事民事诉讼法学方面的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