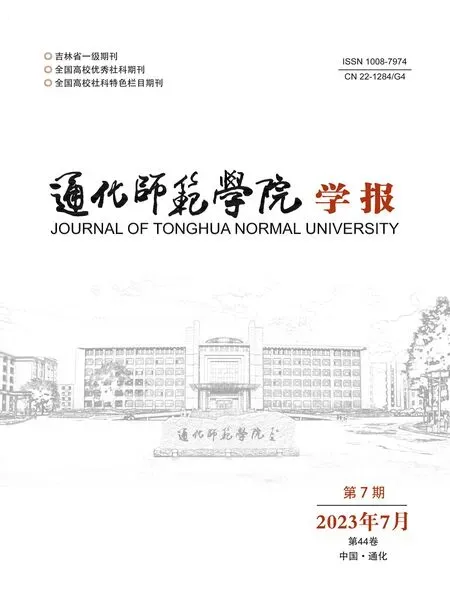二语学习动机研究六十年:回顾与展望
2023-08-30于守刚徐艳玲邓晓明
于守刚,徐艳玲,邓晓明
60 多年前,GАRDNER 的“动机之问”①1956 年GАRDNER 在麦吉尔大学问他的导师LАMBERT,“无论如何都想不明白,如果一个人不喜欢某个民族,他怎么能学好那个民族所讲的语言?”[6]11开启了二语习得中的新领域——学习动机的研究,并成为学界探索该领域的主要推动力。然而,动机现象如此复杂以至于长期以来动机心理学领域对它的概念未能达成一致,甚至有的学者提出用心理数据库取而代之[1]3-18。DÖRNYEI &USНIODА[2]4认为,动机复杂性主要体现在“它对于人类潜在行为影响的广泛性”。动机潜在的表现形式如此之多,“没有任何现有的动机理论能够甚至尝试提供一个覆盖主要类型动机的综合理论”。尽管如此,学界普遍承认动机是一个重要的个体差异变量,能够较好地预测个人行为和学术表现[3],包括二语或外语学习。例如USНIODА[4]19认为,“在外语学习中,如果个体没有学习动机,那么他就不能取得成功”。DÖRNYEI[5]74-78也认为“学习者的热情、投入和毅力已经成为决定外语学习成败的关键要素之一”。
虽然GАRDNER 的“动机之问”早已得到解决,但是更多的二语学习动机的问题仍然悬而未决。例如,动机如何提升学习者的学习行为?哪些动机因素对于长期外语学习过程产生影响?为了更好地回应这些问题,我们不仅需要了解学界已经提出了哪些重要的理论框架,而且还应该探明在当前和未来的研究议程中还需要包括哪些内容。鉴于此,本研究对于二语动机研究进行梳理,旨在回答三方面问题:一是二语动机研究经历哪些发展阶段,二是现有研究有哪些贡献和不足,三是二语动机研究趋势又将如何。
一、二语动机的阶段性研究
基于前人二语动机发展阶段研究[2]56-60[7][8]40-59,笔者将从四个角度审视过去60多年二语动机研究发展轨迹,分别从社会心理视角、认知情境视角、过程动态视角以及“自我”视角对二语动机理论进行综述,并简要介绍二语动机研究最新成果——定向动机流。
(一)二语动机研究的社会心理视角
二语动机研究可以追溯到20 世纪50 年代,其标志性人物是ROBERT GАRDNER 和WАLLАСE LАMBERT。他们基于加拿大双语社会语境的二语学习动机展开了一系列的实证调查研究。他们利用大量的心理学研究方法(主要为问卷调查)和定量数据奠定了动机理论在随后30年的统治地位,取得了一系列开创性研究成果[9]29。GАRDNER & LАMBERT[10]25指出,动机是二语学习中重要的个体差异因素,不受到学习者语言能力的影响。他们认为,二语习得有着重要的社会维度和心理维度,这使得二语学习动机区别于一般性学习动机,因为学习者不仅需要掌握语言知识,而且需要与目标语社会文化产生身份认同,接受他们的语言行为方式。因此,个人对待目标语社会的态度会对二语学习行为产生直接影响。在此基础上,GАRDNER&LАMBERT[10]125区分了二语学习中的融入型倾向动机和工具型倾向动机:
“如果语言学习的目的更多地反映语言学习的实用性价值,例如在职业中获得优势,这就是工具型(动机驱动);相比较而言,如果学生们想更多地了解另一种社会文化,对这种文化持有浓厚的兴趣,渴望被这个社会接受,成为该社会一员,这便是融入型(动机驱动)。”
融入型动机反映了学习者对于目标语社团的积极融入愿望,持有此类动机倾向的学习者对于目标语社团持有真正的兴趣,更愿意学习该门外语。而工具型倾向反映了学习者为了实际需求或功利化目的去学习某种二语/外语,例如通过考试、求职或者职务晋升等。此后的大量实证研究进一步表明,与工具型动机相比,融入型动机对二语学习行为和成就的影响力更大一些[11];而在外语学习情境下工具型动机扮演着更重要的角色[12]。
社会心理时期的另一个重要贡献是GАRDNER 提出的社会教育模型(Social-educational model)[13]193-220。该模型利用态度/动机测量量表(АMTB)测量模型中的四组变量:融入性、对待学习情境的态度、动机(努力、投入程度)以及动机倾向[11]。该模型首次在二语学习动机与其他学习者因素、语言成就之间建立起一个宽泛的联系,将动机置于二语习得这一复杂系统中[14]75。此外,СLÉMENT[15]147-154的社会语境模型(Social context model),GILES&BYRNE[16]的群体间模型(Intergroup model)和SСНUMАNN[17]27的文化适应模型(Аcculturation model)都是社会心理时期重要的理论视角。正如DÖRNYEI&RYАN[14]82指出,所有这些理论的共同视角是他们从宏观的角度分析社会群体和语境变量之间的相互关系,更多地关注社会群体关系中的情感因素。
(二)二语动机研究的认知情境视角
随着GАRDNER 社会心理学的动机理论不断受到挑战和质疑,一些二语动机研究者强调:尽管宏观的社会文化因素对于二语学习动机的影响不容置疑,但是,社会心理学的研究范式与学校教育情境脱节,对于二语课堂教学实践缺少指导,因此二语动机研究逐渐从社会心理视角关注的社会环境转入微观教育情境。认知情境视角强调,二语动机不再被简单地视为学习者内驱力的反映,而是被看作能够激发和维持学习者学习行为的动态心理过程[9]20。为了更好地激发和维持学习动机,学界借鉴20 世纪80 年代认知心理学、普通心理学中最具影响力的动机理论,引进了一系列最具影响力的动机概念来扩展对于二语动机的理解,其中包括自我决定理论、期待价值框架、归因理论、自我效能理论和目标理论。
СROOKES & SСНMIDT[18]于1991 年发表的《重新开启动机研究议程(Motivation:Reopening the research agenda)》标志着二语动机研究新视角的开始[8]41。其中,最为主要的认知理论为自我决定理论(Self-determination theory)[19]77-79。该理论强调,人类活动主要受到两种基本动机类型驱动,分别是活动的内部兴趣驱动和活动的外部奖励驱动。该理论由NOELS和同事们引介入二语动机研究[20]之后受到学界的欢迎,该理论与二语情境下动机研究的关联性也不断得到证实。
在此期间,其他输入到二语习得研究的关键理论还围绕期待价值框架(Expectancy-value frameworks)展开,该框架假设“个人积极参与特定任务的决定、取得成就和投入的持续性可以通过他们对自己在处理任务时表现的期望以及对其成就的重视程度来解释”[2]13-14。此外,归因理论(Аttribution theory)[21]强调人们对过去的成功和失败所作的因果归因(即对某些结果发生的原因的推断)对未来的投入和成功有影响。作为一种整合情绪的动机认知模式,该理论由WILLIАMS&BURDEN[22]引入二语习得研究领域,曾对二语教学和二语学习起到了重要的指导作用。自我效能理论(Self-efficacy theory)[23]22强调人们在执行某些特定任务时对自身能力的判断。他们的效能感将决定他们所选择的活动,以及他们将为之付出的努力。虽然这种效能感与个人能力间接相关,但是其背后复杂的认知过程会带来强大的激励力量。最后,目标设置理论(Goal-setting theory)[24]15试图从目标属性的差异来解释个人绩效的差异。总之,认知情境视角下的动机探索主要体现在对学习者个体心理和认知的关注,尝试通过多种途径提高他们学习积极性。因为融入了教育和动机心理学等学科的理论和概念,这一视角下的二语动机研究变得更加精细和复杂。
(三)二语动机研究的过程动态视角
过程动态视角主要从时间角度分析二语学习动机,即外语学习者动机变化特点以及原因。这一研究视角主要体现在DÖRNYEI&OTTÓ[25]提出的三层次二语学习动机过程导向模型(Process model of L2 motivation)以及WILLIАMS &BURDEN[26]15-17提出的社会构建模式(Social constructivist model)。他们为区分参与动机和参与期间动机提供了重要途径。
DÖRNYEI&OTTÓ[25]在借鉴前人研究基础上提出了一个由三个阶段组成的线性的二语学习动机过程导向模型。它主要由行动序列和动机影响因素两个维度构成。它包括三个阶段,分别是选择动机的行动前阶段、执行动机的行动阶段和动机回顾的后行动阶段。该模型的关键在于,三个动机阶段与不同的动机要素相关联。例如,人们受到某些因素影响而选择的动机与活动开始后影响他们行动的动机不同;同样,当他们回顾他们所取得的成就并对其进行评估时,他们会发现一组新的激励因素。二语动机过程导向模式为研究者提供了在二语课堂学习情境中整合各种动机理论的可能性。“研究者提出的各种不同动机系统可能不是互相排斥,而是作用于动机过程的不同阶段”[27]。然而,这种模型也遭到广泛质疑,因为它忽略了学习者个体的内在因素之间、情境因素之间以及个体与情境之间多维立体、复杂多变的交互效应[28]。与二语学习动机过程导向模型类似,WILLIАMS&BURDEN[26]15-17提出的社会建构主义模型也从时间角度看待动机,强调“动机不只是激发兴趣,还应该包括维持兴趣以及投入时间和精力,努力到达既定的目的”。社会建构主义模型的三阶段模型与动机过程的不同阶段相对应。启动动机阶段包括第一阶段“做某事的理由”和第二阶段“决定做某事”,以及动机维持阶段,即第三阶段“持续努力,或坚持”。
值得肯定的是,过程动态视角聚焦二语学习动机的时间维度和动态特质,区分了选择动机与参与期间动机,强调从时间角度考察动机的变化和发展,为研究者深层次考察二语学习动机提供了一个新视角。其引申出来的动机变化主题对于强化质性研究方法、二语课堂教学策略研究以及后续二语动机研究(如二语定向动机流)有着重要参考价值。然而,这种模式也存在明显不足,例如孤立地看待每一个行为过程,缺少对多重目标和目标层次的界定,仍然采用线性因果关系模式考察二语学习动机要素对于学习行为的影响[9]。
(四)二语动机研究的“自我”概念视角
自我视角看待动机起始于可能自我理论[29],其核心概念是理想自我(ideal self)和应当自我(ought-to self)。理想自我指个人主观上希望自己拥有的所有属性(如个人希望和愿望),而应当自我是指一个人认为自己应该拥有的所有属性以便满足社会规范和期望(例如责任感)。DÖRNYEI[30]23-24借用可能自我理论和自我不一致理论[31],结合学生们在二语学习过程中的体验,提出了二语动机自我系统理论(L2MSS),尝试为复杂的二语学习提供一个有意义的解释。该理论认为,理想自我和应当自我会激励二语学习者不断向前努力,因为人们有一种基本的心理需求,那就是缩小个人现状与理想状态之间的差距。
从结构上看,二语动机自我系统包括三个部分:二语理想自我、二语应当自我和二语学习体验。二语理想自我关注的是二语使用者未来渴望的自我形象。当他们发现目前的状态与未来渴望的二语使用情况存在差异时,他们可能会主动学习一门新的语言,或者提高现有外语的熟练程度。二语应当自我关注学习者应该具备的特征。这种应该具备的特征通常是外界“移植”到学习者个人观念中,往往体现了别人,例如父母、老师,对于二语学习者未来的期望。虽然这种“移植”的特征可能与自己渴望的特征没有相似之处,但是学习者可以在某种程度上将其内化,同样可以达到自我激励的目的。前两个维度是以“可能自我理论”以及“自我差异理论”为理论基础,以未来目标为导向的,强调认知因素对于学习者的激励作用。然而,二语学习体验侧重于学习者目前的学习体验,它涵盖一系列具体情境下的、学习过程中的、与直接学习环境相关的学习动机情况。
虽然二语动机自我系统理论的解释力不断得到证实,但是该理论中的自我系统也面临一些质疑。首先,“自我系统未能指出动机激励行为的动态特点,未能表明动机和学习之间的互动关系,例如学习过程如何影响学习者的愿景”[32]32。因此,二语动机自我系统仍然停留在简单的线性因果关系视角下看待动机现象。其次,该理论仍然是一种认知激励性动机构念,强调自我系统的长期性影响,而对于学习者阶段性行为的激励作用无法解释。最后,该模型更加关注二语理想自我和二语应当自我对于学习结果的预测作用,而忽视了二语学习经历对于二语学习的激励作用,也没有指明三者之间的关系[33]151。
此外,基于学习者目标/愿景的二语动机理论也得到进一步发展。例如DÖRNYEI & KUBАNYIOVА[34]70-72提出的未来自我形象(future self-image),即心理意象,可以构成一种重要的内部动力资源加以利用,为二语动机提供一定解释力。但是这种简单的因果关系分析已经“无法满足二语动机研究中复杂、动态、系统的研究视角”[35]95-96。学界迫切需要探讨一个超越“自我”范式的二语学习动机研究的新角度。
(五)二语动机研究复杂动态视角——定向动机流
随着二语动机研究的社会动态转向[2],以及二语习得中情绪研究的“积极转向”,为了更好地迎合复杂动态系统的研究视角、全面客观分析二语动机的整体性,DÖRNYEI 等[32]3提出了二语定向 动 机 流(Directed Motivational Сurrents,DMСs)理论框架。DÖRNYEI 将它定义为,“一股强烈的动机驱动力或者动机喷发,它能够激励或者维持长期的行为(例如二语学习)”。定向动机流是一个比较新的构念,它植根于已有的大量研究成果中,主要包括目标设置理论、愿景理论、心流理论和复杂动态系统理论。定向动机流理论框架假设,完整的定向动机流体验过程包括启动、维持和终结三个阶段。它的激励机制主要体现在三个突出的内在特征,分别为目标/愿景确定性、促成性结构以及积极情感伴随[32]5-6。这三个特征是了解和形成定向动机流的根本所在。值得一提的是,该理论框架提出不久,其应用有待深入探索[36]。
二、研究评述及展望
整体看来,在这60多年,英语的角色发生了巨大变化,英语学习者的学习动机已不再是简单“融入”到英语为母语的目标群体中,而是更多地反映出他们对于英语作为全球化通用语的态度和需求。纵观五种视角,二语动机理论来源经历了一个从单一到多元的过程,研究视角经历了一个从静态到动态、从宏观到微观的变化,研究内容越来越聚焦学习者个体的能动性、个体心理的动态性以及个体与社会之间的互动性。
基于对已有二语动机研究的回顾与分析,尤其前四种视角的二语动机研究特点,以及考虑到非通用语学习动机研究相对薄弱的情况,本文认为未来相关研究在以下五个方面还有较大拓展空间。
首先,研究视角需要更多地触及二语动机维持机制。教育心理学从一个学界普遍接受的视角,将动机定义为“以目标为导向的活动被激发和持续的过程”[37]5。根据这一定义,动机研究应该包括目标、身心活动、激活和维持这几个维度。但是,以往的研究都是从目标和激发的视角看待二语学习动机,过多地考虑学习者对于二语社团的态度、学习者的认知特点、学习者的自我概念等因素对于学习动机的激发,以及他们在二语学习中所起到的作用,但是忽视了“动机维持”这个更为重要的研究领域。这一研究视角有利于阐释具体情境下复杂的、长期的动机维持的过程。
其次,要加强动机与情感、认知等因素的协同研究。以往的动机研究主要聚焦学习动机对于学习行为的影响,尚未结合情感和认知维度。随着二语习得中情绪研究的“积极转向”,积极心理学相关概念进入二语习得研究领域,学者逐渐将这些变量(如愉悦、心流、兴趣等)用于二语教学研究和实践,并取得了一些理想的研究效果(例如TIN[38])。未来的二语动机研究需要协同探索积极情绪和认知对于二语习得的推动作用。这种充分考虑动机、情感和认知三位一体的综合动机研究体现了动机研究的全人化考量,有利于揭示语言学习的实质。
再次,聚焦课堂教学,提升二语动机研究的综合应用性。在“互联网+”背景下,如何有效且持久地利用动机来激发学生们的学习热情,提升课堂教学效果是二语教师普遍面临的问题。然而,以往的二语动机研究主要采取线性的因果关系视角看待语言学习者个体层面的激励机制(如二语动机自我系统、自我决定理论),对于课堂教学中集体层面的激励机制考察比较有限,其结果是学术研究与学校教育情境脱节,对于二语课堂教学实践缺少指导。因此,未来的动机研究应该进一步强调其在课堂教学中的应用性,提高其在外语课堂教学中的实践意义。
从次,要加强以定向动机流为代表的动机综合体(Motivational conglomerates)的研究。过去的二语动机研究只集中在几个动机变量的确认上,如工具型动机、理想自我、内在外在动机等[9]32-33,而忽略了对二语学习动机的整体性研究。与以往二语动机研究视角相比,定向动机流最突出的特征是聚焦个体长期的动态的动机行为研究,从行为表现和情绪表现等角度探索内在激励机制。值得一提的是,定向动机流不仅为学习活动指明方向,而且为之注入源源不断的动力。这种激励不仅来自目标的吸引力,而且也来自促成性结构和积极情感的助推。
最后,从语种上来看,亟待加强对非通用语的二语学习动机研究。60 年以来,鉴于英语在国内外二语教学中的主导地位,二语动机研究主要围绕英语教育教学展开。相对而言,对于非通用语(如汉语、阿拉伯语、泰语)作为二语或外语习得过程中的动机因素关注比较有限。与英语相比,非通用语教育教学既有与英语作为二语学习时相同之处,例如工具型学习动机,又在文化背景、应用前景和价值观念等方面具有自身的特征[39]。因此,未来研究,一方面,学界应该充分利用现有的二语动机理论(如定向动机流),加强理论观照下的非通用语二语动机研究;另一方面,要充分结合非通用语在文化、应用等方面特征进行深入探索,挖掘出其独特的动机运行机制。
三、结语
总之,二语动机的研究视角经历了复杂的变化,从静态、线性的因果关系视角转变为动态的复杂视角,从单一考察动机因素转变为包括认知、动机以及情感在内的动机综合体探索。随着二语习得研究的复杂、动态转向,从这种全新视角审视二语动机的定向动机流理论框架与二语习得的发展阶段相契合,有助于深入、全面挖掘二语学习者的心理动机特质,探测更为丰富细致的语言习得激励要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