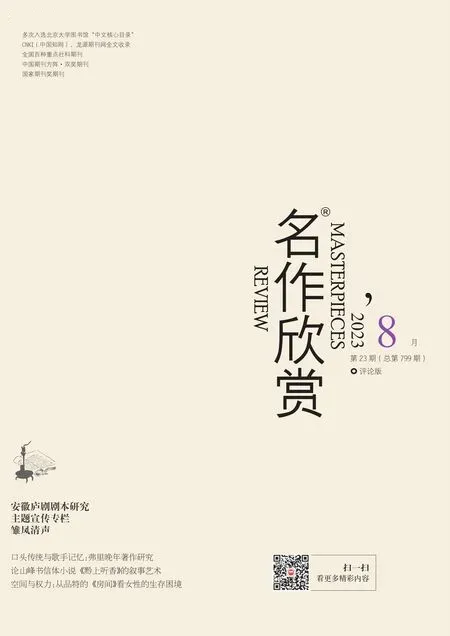废名小说《浣衣母》的美学探究
——飘逸脱俗的生命哲学
2023-08-25舒艺娉中南民族大学武汉430074
⊙舒艺娉[中南民族大学,武汉 430074]
一、废名式美学:生命哲学
探究废名小说《浣衣母》中的美学,首先应该明晰何谓“美学”,尤其是何谓“文学的美学”。美学之概念由德国哲学家亚历山大·戈特利布·鲍姆嘉通在18 世纪50 年代首次提出,亚历山大又称其为“感性学”。古往今来,人们对“美”之概念的看法各式各样,当今学界对美学定义的观点亦是各持己见,可谓见仁见智。亚历山大则认为美学是一种以美的方式去思维的艺术,是美的艺术的理论,且美学与众多学科均有着密切的联系。①
艺术并不受美的限制与框定,在对《浣衣母》的美学进行研究时,实质上则是在文学视域下进行美的探索,其研究分析中应包括美学意义上的美。所谓文学中的“美学”,主要指对文学艺术进行的哲学思考,其思辨性最强,观照范围最广。②本文将基于此研究范围,从人物角色反映的乡民人性与文章表现的审美方式两个纬度阐释《浣衣母》的美学体现,同时通过分析《浣衣母》一文进一步了解废名式美学:飘逸脱俗的生命哲学——超越痛苦与冲淡悲痕的理想。
二、乡民人性:泛爱达观、真诚善良、自然淳朴
(一)达观大度与泛爱人间的“神圣静美”
《浣衣母》中的主人公李妈是一名十分慈爱的母亲,她为孩子们开辟了一片任意欢乐的自由天地,也就是她的茅草屋前的区域。在这片区域里,孩子们欢乐地玩耍,如同鸟儿般自由地翱翔,也吸引了城里的少年少女在夕阳西沉时来到此处,卖柴的乡人在树下乘凉,休闲而惬意,“姑娘们回家去便是晚了一点,说声李妈也就抵当得许多责备了”③,甚至连嚣张跋扈的一些人也被她的“慈爱”所感化。
对于孩子们,李妈慈悲而仁爱,细致而入微。当太太们从家来带来米和菜食以表谢意时,李妈“顾不得承受,只是抚摸着孩子:‘不要哭,明天再来’”;当人们在她的茅草屋前的河流边、沙滩上欢乐闲适地过着自己的生活时,李妈“坐在门口,很慈悲地张视他们”;对于孩子们的吃食,李妈秉持着“专门为着这班小天使,加以善于鉴别糖果的可吃与不可吃”的细腻态度,让自己的口袋“从未空过”;甚至连守城的兵士也被这份慈爱的温暖所融化,“有两个很带着孩子气的,简直用了妈妈的称呼”。
废名虽对“母爱”一词只字未提,但这份伟大的慈爱却化身整篇小说的核心,贯穿始终。正如文中所言,她成了他们“公共的母亲”,李妈平等地爱护着每一个人,她将自己的慈爱撒向人间,不论是孩子们、兵士们,还是城里的太太、乡里的邻朋们都为这份特别的情所感染,信任甚至依赖着李妈,文中这份独特的“母爱”造就了李妈母性的“神圣”,体现着泛爱人间的道家哲学。
同时,面对生活重创的达观大度,又进一步展现出李妈这一角色的“神圣静美”的人性境界。
面对一位儿子的去世与另一儿子的杳无音讯,李妈对此感到十分空虚,她有过悲伤怅惘与难过悔恨,愤恨之余甚至会对着驼背姑娘痛骂“前世的冤孽!”但很快李妈的空虚便被别人的恐怖所填补——别人遭受劫掠与骚扰,而自己却仍然能够好好地进出茅草房。
面对驼背姑娘的死,李妈虽号哭不止,但也“并不十分艰苦一年一年地过下去了”。
生活的重创并未使李妈显露颓丧,反而成为李妈冶炼达观大度之人性境界的精神养料,在思想陷入怅惘时,李妈善于看到自身所长,满足并感恩自身所遇,不仅体现了她豁达乐观的人生态度,同时给我们带来了关于生命的积极思考——死亡给生命带来巨大悲哀的同时,也使得生命更加坚韧。
当其“达观大度”之人性境界与“泛爱人间”的人性情怀交织融合时,便造就了李妈这一位“神圣静美”的角色,废名也曾评价李妈是“形式虽孤单,其精神则最为热闹”。李妈的伟大之处不仅在于她无私的爱与慈悲的胸怀,更在于她精神的坚韧与灵魂的厚度。废名通过刻画李妈这一神圣静美的形象向读者表达面对生活重创时的积极态度与对生命的积极思考,向读者展示了一位拥有超然的勇气并慈悲为怀的母亲形象,满含飘逸脱俗的生命蕴意。
(二)真诚善良的少女之美
纵览全篇,文中着墨最多的少女无疑是李妈的女儿——驼背姑娘。
废名用温柔的笔触描绘出驼背姑娘的灵动可爱与真诚善良,她会低声唱歌,模仿妇人啼哭,俏皮之气跃然纸上:“倘若有一个生人从城门经过,不知道她身上的缺点,一定感着温柔的可爱——同她认识久了,她也着实可爱。”驼背姑娘是否驼背似乎已经不再影响她的灵动可爱。“驼背姑娘的爱孩子,至少也不比孩子的母亲差……”少女细致地照顾着孩子们,善良而真诚地付出自己的爱。她用心服侍自己的母亲,即便得到责罚也只是“呜呜咽咽地哭着”;她好奇世界,会发出“鬼火”的惊奇疑问;她真诚可爱,面对守城的兵士,因着少女的羞怯,她“起初躲避他们的亲近”,慢慢地,“……也同伴耍小孩一样,真诚而更加同情了”。不同于同时期的鸳鸯蝴蝶派小说对于少女肉体的俗态描写,废名以极简的笔触勾勒出的是少女的精神美和诗意美,是少女如同月光般的纯洁自然与真诚善良。
在废名笔下,少女的真诚、善良、友爱、灵动、活泼之美只几句便充分展现,而这份属于少女的真诚善良与活泼乐观,事实上也暗示着废名对于生活生命的积极态度:关心并热爱,真诚而自然,乐观而积极。展示了废名对于朴素真诚之社会风气的向往,他希望生活乃至生命都是和谐而质朴的,充满着人道主义的情怀,体现了飘逸脱俗的废名式美学。
(三)自然淳朴的乡民
除了李妈与驼背姑娘,在《浣衣母》中还有着其他众多角色,多表现出乡民人性的自然与质朴,充满着田园牧歌式的闲适淳朴色彩,如:
傍晚,河的对岸以及宽阔的桥石上,可以看出三五成群的少年,有刚从教师的羁绊下逃脱的,有赶早做完了工作修饰得胜过一切念书相公的。桥下满是偷闲出来洗衣的妇人,有带孩子的,让他们坐在沙滩上;有的还很年轻。一呼一笑,忽上忽下,仿佛是夕阳快要不见了,林鸟更是歌啭得热闹。
少年是天真而烂漫的,妇人是欢乐而慈祥的,林鸟甚至也高兴地婉转歌唱,一展歌喉。废名以轻巧的笔力,写出了田园的丰富情趣,将乡村田园的生活画卷直观地展现在读者眼前。从城墙旁的茅草屋,到河流上的小桥,从稚气未脱的少年,到劳动且欢乐的妇人,原本彼此独立的景色与人物被废名用简单的词句自然顺畅地串联在一起,不仅没有失去其原本的韵味,更是从头至尾贯穿着宁静闲适、和谐自然的牧歌节奏美感,形成了一幅澄净清澈的田园画面,而生活在这样一幅画面中的乡民则自然地透露着古朴与淳厚,给人一种闲淡清净之感,仿佛超然世俗,独立桃源,这也是废名式美学的重要体现。
三、审美方式:超然飘逸、悲痕淡显
“五四”小说家中,对社会的感受之深,莫过于鲁迅;对自然美的感受之细,除郁达夫外,莫过于废名。④
废名作为现代抒情乡土小说家中极具代表性的人物,他爱写隐于小城旁的宁静乡村之景色,爱写流水淌过松软的泥土、钻过小桥的潺潺之音,写水上小桥静然聆听流水,写人们在此环境下平静而闲适的田园生活,其环境皆是诗意清雅,景色秀丽。而这宁静闲适的一切,实际上是废名在乡土社会物质匮乏、贫困单调与衰败凄苦状态下对痛苦的超度,对悲伤的淡隐,总体上呈现出超然飘逸、悲痕淡显的审美方式。
(一)悲剧性、人情美与童稚美的自然融合
在《浣衣母》中,废名对单调衰败、受旧传统道德束缚的乡土社会所显露出来的悲剧色彩进行了冲淡,具体表现在增加了对人物人情美和童稚天真美的着墨,其中最典型的便是废名对人物形象的塑造。
李妈这一角色在文章中可谓充满了悲剧色彩:丈夫早亡,两个儿子一个去世一个杳无音讯,唯一陪伴自己的女儿也与世长辞,最后自己甚至悲哀地淹没于封建传统的流言蜚语中。但废名并没有扩大这些悲情,而是选择着力渲染李妈的慈悲为怀与达观大度,用人情之美冲淡了身世之悲。
值得一提的是,冲淡悲痕之风格在废名小说中的体现除了李妈和驼背姑娘人情美和悲剧性的交融,还有他对孩子们的童真质朴的刻画。废名写孩子们的天真活泼,饶有活力与生气,面对母亲的横视而不自知,仍旧维持着天真的行为,“孩子们也一伙伙团在墙角做他们的游戏;厌倦了或是同伴失和了,跑去抓住妈妈的衣裙,无意的得到妈妈眼睛的横视;倘若还不知退避,头上便是一凿。”写土坡上孩子们玩乐时不同的状态,“……有时候跑到沙滩、赤脚的,头上梳着牛角的,身上穿着彩衣的许许多多的小孩,围着口里不住唱歌,手里编出种种玩具,两条腿好像支不住身体而坐在石头上的小姑娘。”废名笔调自然,揭示并赞美童稚的纯真与自由。
在小说的结尾,李妈因流言蜚语从“神坛”跌落至“沼泽”,许是未经雕琢的童心使然,此时仍有部分孩子愿意来到李妈家旁的沙滩,无视旧式的伦理道德而追求内心纯洁的快乐,这正是废名对孩童所展现出的童稚美的赞扬。这份不谙世俗伦理的童稚美是脱离于乡土世俗的超凡存在,是另一种“乐观”与“神圣”的体现。而这份童稚美构成了废名式美学中有关悲痕淡显风格的独特之处,是废名式美学的重要色彩。
(二)自我理想世界的构建与社会现实的讽刺
1.理想世界的勾勒:着力渲染乡土闲适宁静的特点
废名的作品在精神上蕴含着对陶潜传统的承继,他曾回忆自己原来是对政治很热心的人,然而终于是逃避现实,对历史上屈原、杜甫的传统都看不见了,最后躲起来写小说乃与古代陶潜、李商隐写诗相似。废名的作品多是在对乡野生活的细致描写中表达超然洒脱的自我追求与安逸闲适的生活态度,勾勒和谐纯真、充满诗意的自我理想世界。
废名在《浣衣母》中对自我理想世界的描写并非平铺直叙,而是将其对幻想中的古朴和谐诗意世界的追求磨成粉末,洒在字里行间,他写李妈的居所时只用寥寥几笔:
这茅草房建筑在沙滩的一个小土坡上,背后是城墙,左是沙滩,右是通到城门的一条大路,前面流着包围县城的小河,河的两岸连着一座石桥。
空间位置的转换介绍简单却自然,不仅直观地将景物展现在读者面前,而且轻而易举地描绘出田园乡野居住环境的诗情画意,气质是质朴而优雅,后文勾勒的简单而快乐的生活亦以此为背景,奠定了和谐牧歌的自然基调。
废名大甩笔墨于渲染乡土的宁静与闲适,用乡土社会的诗意和古朴抹淡物质匮乏带来的单调衰败,又如后文通过写李妈与卖柴的乡人之间的友好互动,展现出乡土社会的人情和谐:
卖柴的乡人歇下担子在桥头一棵柳树下乘凉,时常意外的得到李妈的一大杯凉茶,他们渐渐也带点自己田地里产出的豌豆。
废名展示给读者的理想世界和谐而美好,在宁静闲适的牧歌基调下冲淡了封建乡土社会暗藏的悲哀,从侧面表达出废名对闲适纯真生活的向往与追求。
杨义先生曾在文章中提到,废名的小说承继了陶潜之气,不同于李白从天上俯视人间,也不同于杜甫从深处剖析人间,废名小说中字里行间的田园之气有一种安逸闲适的情调,正是陶渊明一般的浩然,其诗趣有余,而入世不足。废名将宗法制的乡村罩上了诗情画意与闲适宁静,正所谓“入世不足”,体现了废名对理想世界的勾勒与向往。
总而言之,废名在《浣衣母》中所展现出的田园美是值得称道的,它能引起读者对于作品别样的欣赏兴致与审美感受,宁静温馨的情调如同绕梁的余音,回荡在读者的脑海久久不散。正如杨义先生所言:“它不是战斗中的文艺,也不是象牙塔里的文艺,而是树荫下闲坐者的文艺。”⑤这份对和谐理想世界的追求,是废名式美学的重要体现。
2.《浣衣母》的现实讽刺意义
废名式美学处处体现着超然飘逸、悲痕淡显的特点,但文学作品的研究必然离不开时代背景,探究废名式美学在《浣衣母》中的体现,其现实讽刺意义不可或缺。
《浣衣母》中所蕴藏的现实讽刺意义事实上是基于宗法制社会而产生的,而文中深受宗法制社会迫害的无疑是主人公李妈。从最初李妈被人们“供上神坛”,成为神圣的“公共的母亲”,到结尾因为可畏的流言蜚语而跌落泥沼可以看出,这是废名对旧式伦理道德的痛恨与批判,他的笔力虽不若鲁迅讽刺现实时那般强劲,愤懑之气如排山倒海一般倾涌而来,却仍可窥见他对自己笔下人物李妈的叹惋:传统道德成为束缚李妈的枷锁,让这位慈悲的母亲暮气沉沉,满是心酸。
四、结语
《浣衣母》一文充分展示了废名的行文特点。废名的笔触是平淡的、质朴的,是轻灵而澄澈、优雅而富有诗意的。他的作品中因悲痕淡显而极具超然飘逸之气,人物刻画与审美方式也表达出一种积极的生命态度与豁达的生命境界。可以肯定地说,废名在《浣衣母》中所展示出的废名式美学对我们思考生命哲学、探索生命意义是大有裨益的。
①胡家祥:《审美学》,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2—7页。
② 朱刚:《二十世纪西方文论》,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引论第6页。
③废名:《废名短篇小说》,陈建军编订,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2019年版,第40—49页。(本文有关该书引文均出自此版本,不再另注)
④⑤ 杨义:《废名小说的田园风味》,《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1982年第1期,第1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