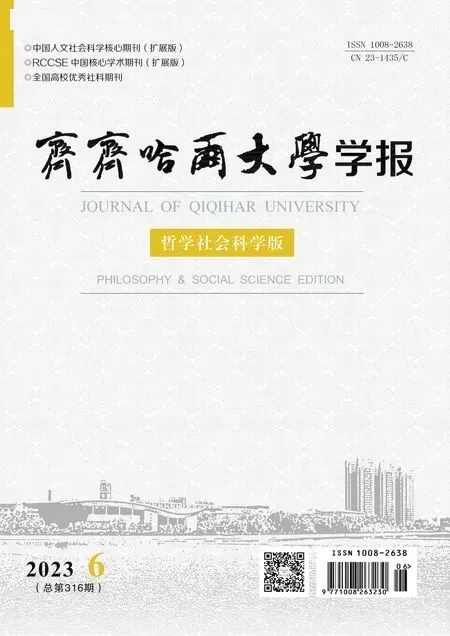梭罗《瓦尔登湖》中的物本体书写研究
2023-08-22吴美群
方 耀,吴美群
(1.安徽农业大学 外国语学院,安徽 合肥 230036;2.长沙大学 外国语学院,湖南 长沙 410000)
文学是人学,也是物学。中国文学家历来热衷于物的书写,关注物和人的关系。从《诗经》《山海经》《博物志》《搜神记》等古代作品,到近代名著《聊斋志异》《镜花缘》《红楼梦》,再到现代作家鲁迅、沈从文、张爱玲的经典作品中,都有着丰富多彩的物书写和物性叙事。中国文论中也有着历史悠久的物叙事理论传统。例如,以南朝文论家刘勰为代表的“心物感应”,另有北宋理学家邵雍提出的“以物观物”等。西方对物的探索始于古希腊时期,哲学家们把物质性本原当作万物之本,肯定物的本体地位。物随后经过了苏格拉底“灵魂说”和柏拉图“理念说”的贬低,又经基督教神学的轻视,在17世纪重获本体地位。英国哲学家霍布斯在《论物体》(1655)中提出了物的“主体”性[1]424。18、19世纪以来,黑格尔、康德、马克思等纷纷对物是第一位还是人的主体是第一位进行了阐释。
20世纪以来,随着量子力学和混沌论等对牛顿二元论的挑战,建立在二元论基础上的传统物质观显露出弊端,海德格尔呼吁重新思考“物”以及“物人关系”。西方学界在后人文主义和新物质主义等“后理论”的影响下掀起了一股“去人类中心主义”的思潮,而文学批评领域在以新批评(New Criticism)为代表的“语言学转向”和以新历史主义(New Historicism)为代表的“文化转向”之后,出现了一种明显的“物转向”(Material Turn)。“物转向”带领我们重新回归“物”自身,去探索人类之外“物”的本体性和能动性。简言之,西方思想中的“物”在大体经历了中世纪的“附魅”和现代性的“祛魅”之后,开启了后理论时代的“复魅”之旅。在物转向理论中比较典型的有以简·本尼特(Jane Bennett)、布鲁诺·拉图尔(Bruno Latour)及凯伦·芭拉德(Karen Barad)对物质活力和物质能动性的强调;有格兰厄姆·哈曼(Graham Harman)对物质本体性的肯定;也有比尔·布朗(Bill Brown)对物质无意识的关注。物转向理论整体主张物具有独立于人的生命和活力,物在本体论上具有与人同等的地位,不以人的理性和意志而转移,而人类可以超越理性对物进行美学想象和艺术想象。
亨利·大卫·梭罗(Henry David Thoreau)是美国超验主义文学家和自然主义者,他深受爱默生超验主义自然思想影响,热爱自然、亲近自然并书写自然。他在代表作《瓦尔登湖》中书写了一个远离尘嚣、充满活力而又无比神圣的自然物质世界。他也是一个博物学家,在《瓦尔登湖》中观察、研究并记录了上百种动植物,包含各类花、草、虫、鱼及树木等。他还是一个超验主义实践家,对测量有着精准而独特的敏感,他把对自然的观察记录和哲学思考紧密相连,深入探索了现代工业文明背景下的新型物人关系。《瓦尔登湖》中虽然有大量关于自然测量和博物的记录,但并不是一部有关自然的科学文献,而是一部关于人与自然关系的艺术性和哲学性作品。那么,梭罗在《瓦尔登湖》中具体提出了什么样的物与人的关系?作品中随处可见的自然物又是以什么样的文学方式呈现?它们蕴含了什么样的审美价值和文化内涵?梭罗借助这些物性叙事表达了何种自然思想?本文将围绕这些问题深入探讨《瓦尔登湖》中物性叙事的呈现方式和审美视角以及文化内涵。
物在文学文本中的呈现方式各不相同,既有新历史主义式的“文化之物”,也有思辨实在论式(Speculative Realism)的“本体之物”和“活力之物”。文化之物旨在揭示作为文化符号的物背后所隐含的文化历史内涵。本体之物重点探索物独立于人的“物性”(thingness)。活力之物考察叙事如何再现物的力量、凸显物的施事能力,该维度下的物善于讲述自己的历史或故事,尤其强调物在叙事中扮演的积极作用。唐伟胜在此基础之上提出物性叙事的四种方式:无限隐退之物、平等之物、没有我们的世界、活力之物。《瓦尔登湖》中的物叙事既有无限隐退之物,也有活力之物,但其中最显著的物性叙事方式是平等之物,主要体现在以下四个方面:物的罗列(listing)、谨慎的拟人化(cautious anthropomorphism)、人的物化(reification of persons)以及心物感应。
一、物的罗列
博古斯特(Bogost)受格兰厄姆·哈曼为代表的物导向本体论(Object- Oriented Ontology)影响,强调本体之物具有无限隐退(withdrawn)的特征且互不相关。他认为,物本体书写虽然可以揭示物与物之间的关系,但并不需要提供详细描写或因果解释。他在哈曼的作品中发现了大量无逻辑式的物质罗列,并将这些罗列称为“拉图尔经文”(Latour Litany),博古斯特随后将这种罗列式的书写拓展成物本体书写的方式,而且在他看来,罗列(listing)是物本体书写的最佳方式。博古斯特认为,罗列事物而不对其关系进行任何形式的解释不仅切断了“语言的连接能力”,也切断了物本体之间的连接能力,让我们发现“系统虽然在运作,但系统中的个体却完全是孤立的”[2]40。但神奇的是,被罗列而切断了联系的物本体恰恰摆脱了人类中心主义式的“再现的牢笼”(prison of representation),显示出它的勃勃生机,将我们的关注点从一个纬度转移到多个纬度,从而“让我们更加强烈地关注到物自身”[2]45。
梭罗是一个博物学家,在植物学和鱼类学方面颇有研究。他在《瓦尔登湖》中花了大量的笔墨描写不同动物和植物的种类和习性,因而该作也曾被同时代人误以为是博物类科普作品,但结合博古斯特的“罗列”叙事便不难发现,看似毫无联系的事物罗列背后实际上蕴含着一个万物彼此独立又互相影响的有机整体,表达了梭罗对物物关系和物人关系的新物质主义式哲学思考。《瓦尔登湖》中的物质罗列既有列表式的生活日常用品罗列,也有大自然的生物罗列。一方面,梭罗以记账的形式罗列了在康科德生活期间的生活用品及买卖物品,每个物品都标注了详细价格。机械的记账形式看似缺乏文学性和美感,容易让人误解甚至费解。但如果结合梭罗对工业文明和自然的不同态度便不难发现,这些标注了价格的物品都是工业文明和商业文明的产物,无需语言的叙事性描述。物本身便叙说了自身的故事,展现了建立在“人类中心主义”基础上的美国现代工业文明中以“实用”和“利益”为根本的价值观。
然而,《瓦尔登湖》中更重要的物罗列体现在自然物的罗列上。首先,书中罗列了大量的飞禽走兽,当然最多的当属鱼类,如银鱼、鳕鱼、鲈鱼、鲑鱼、梭鱼、鲷鱼、鲦鱼、鳗鱼、鳟鱼、鳅鱼、鳊鱼、大头鱼、齐文鱼、大泥鱼、胭脂鱼、七鳃鳗、黑斑鳕等等。其次,梭罗还罗列了种类繁多的花草树木,如松树、漆树、桤木、杨木、榉木、椴树、朴树、白桦、菖蒲、黑莓、树莓、长生草、狗尾草、落花生、核桃树、鹅耳枥树、山毛榉、黑桦木、黄桦木、灯尾草、百合花、北美油松等等。没有因果关系也没有被赋予文化含义的动植物罗列,让物本体摆脱了作为符号或者叙事工具的地位,它们并不是食物,也不是日用品,更不是故事的背景或者参照物,却展现出物本体的生机与活力,吸引“我们更加强烈地关注到物自身”[2]45。罗列中的每个物个体,看似互不相关,但每一个都焕发着勃勃生机,它们共同组成了一个有机整体。作者并没有通过生动的语言逻辑带给我们一个画面或者故事,而是通过物的自我呈现向我们展现了一个意气盎然的有机自然,与被罗列出来标注了价格的商品所呈现的“文明”世界形成对话。
在这个自然物的世界中,梭罗忘记了人类的特殊存在,人也成了这个自然物质世界的一部分,没有任何等级差异。因此,我们不难理解,梭罗能够发现梭鱼“极其炫目的超凡的美”,在他看来,梭鱼不是“市井的常客”,更不是人们餐桌上的食物,是“珍珠,是瓦尔登湖水的动物化了的核心和结晶”[3]227。而漆树富生命力和情感,是“愉快”、“任性”、又“脆弱的”[3]91。无论是梭鱼还是漆树,它们不是别的什么,而是它们自己,拥有与人类平等的本体地位。通过物的罗列叙事,梭罗摆脱了用语言逻辑再现出物的叙事模式,从叙事上实现了对人类中心主义的颠覆,书写了一个物人合一的有机自然共同体,与康科德(Concord)外部文明世界形成对话。
二、谨慎的拟人化
除了物的罗列,《瓦尔登湖》中的物性叙事方式还体现在谨慎的拟人化(cautious anthropomorphism)。思辨哲学家史蒂芬·夏维罗(Steven Shaviro)在“万物宇宙论”一文中从三个角度阐释了万物平等论,即“拟人化”(anthropomorphism)、“物质活力论”(vitalism)、“泛灵论”(panpsychism)[4]60。谨慎的拟人化可以有效避免人类中心主义,因为人类中心主义的二元论认为,只有人类有感觉/感情(feelings),我们可以通过把感觉归于花草树木或者岩石、焦油等来避免二元论的陷阱。正如简·本尼特所说,“拟人化可以培养我们对物质力的敏感性,“使我们与物质产生共鸣”,“我们不再处于非人的‘环境’之上或之外。”[5]119-20。简而言之,拟人化能够帮助人类摆脱自我中心主义的自负,拟人化的物不再是作为“环境”或者非人的存在,而是和人类同样拥有感情的物本体。
值得注意的是,夏维罗提倡的是谨慎的拟人化,其核心不是要消除人类,而是谨慎地给万物赋予“情感”,这样便能在很大程度上消除人和万物在本体上的差异,实现“去人类中心”的效果。这和梭罗的自然观非常契合,他并不是一个反人类者,也不是一个反社会者,哪怕在康科德隐居期间,他也常有访客。《瓦尔登湖》的散文集里,收录了一篇“访客”、一篇“村落”,专门记录作者在康科德的访客以及附近的村落生活,他始终关注人类自身的完善。康科德的万事万物都有情感、有智慧,甚至还有荣誉感、集体感和历史感。梭罗通过谨慎的拟人化,向人类中心主义式的外部文明世界发出挑战,但又始终关注人类本身,强调人类在自然生态中的持续责任。
首先,梭罗拟人化地描述了动物的智慧。湖区动物大多拥有智慧,有的甚至超越了人类的智慧。如小鹧鸪的眼神“令人一见难忘。一切智慧似乎都在那眼睛里得到反映。”[3]180土拨鼠总能狡黠地和我玩游戏,当然,梭罗最为欣赏和赞美的是潜水鸟的智慧。秋天潜水鸟一出现,当地的猎人们全部出动,“有的坐马车而来,有的步行而来,三五成群,带上猎枪、子弹和望远镜......一只潜水鸟至少被十个猎人盯上。”[3]185猎人们兴师动众、装备精良、分工合作,尽管猎人们大费周折一番,大多还是“空手而归”,足以说明对手(潜水鸟)的智慧和强劲,这引起了梭罗的强烈好奇心,于是他计划通过自己的方式和潜水鸟来一次短兵相接的博弈。
梭罗曾担任康科德地区的土地测量员,因为他对测量有着非常精准、独特或者接近本能的技巧,比如,他能用脚步精准丈量林子的面积,也能目测水的深度。梭罗凭借职业本能敏锐地判断出潜水鸟的出水距离,划船跟上,然而,潜水鸟在距他50杆之遥的水面冒出,“它大声狂笑了一番”,梭罗也承认“它笑得合情合理。”[3]186浅水鸟充满智慧,一会“冷静地考察”,一会“运筹决策”,一会诱敌深入,把梭罗“诱入最宽广的水域”,就这样给他布下了“一个美丽的棋局”,一个人鸟对弈的棋局,而且它始终占据上风,梭罗无法揣摩它的用意。它“用笑声来嘲笑[梭罗的]白费力气,并且相信它自己是足智多谋的。”[3]186-7就这样博弈把玩了一个多小时之后,梭罗终究还是甘拜下风,心服口服地离开了它。诚然,潜水鸟只不过是康科德智慧动物的代表而已,野鸭、水獭、松树无一不聪明狡猾且充满着智慧。相比较而言,人类在这里显得笨手笨脚,四处碰壁。通过对动物智慧的拟人化书写,梭罗再一次把我们的注意力拉到物本体身上,进一步讽刺了人类中心主义式的自负。
其次,梭罗还拟人化地书写了自然的声音。《瓦尔登湖》中收录了一篇散文“声音”,专门记录康科德的各种声音。对于梭罗来说,自然界的回声是“林中仙女日常谈话和吟唱的曲调”,“哞哞的牛叫声,声音甜美而富有旋律”,像“游吟诗人”的吟唱声。猫头鹰发出“古老的呜——噜——噜的叫声,就像哀嚎的妇女”,或者说是“智慧的夜半女巫”,“那是最为肃穆的墓地哀歌......它们夜行于大地,干着黑暗的勾当......以哀号或挽歌来为自己赎罪。”[3]98-9有的鸟儿在叹息,猫头鹰在唱着小夜曲,青蛙们则在井然有序地喊着绕口令“头儿龙哥”[3]100,康科德似乎在举行一场热闹非凡的音乐会和酒会。而猫头鹰每次看到有“文明人”闯入湖区,便会发出“沙哑而发抖的声音”,甚至说着康科德的方言,侮辱那些来自赫德森湾的闯入者,‘胡,胡’地要把它们逐出康科德的领空。”[3]217在梭罗的笔下,动物的声音和人类的声音一样,有的饱含情感,有的传递信息,有的表达艺术,还有的维持秩序,有的甚至是维护家园的武器。拟人化的声音描述,让我们再次感受到康科德地区的勃勃生机,而这生机与活力来自物,有着生命力和能动性的物。
再者,梭罗还拟人化地描述了一场惊心动魄的蚂蚁战争。那是他“亲眼目击的一场蚂蚁战争,曾经亲临前线的唯一的激战犹酣的战争;自相残杀的战争。”[3]182梭罗用了两千多字的篇幅详细描述了这场红蚂蚁和黑蚂蚁之间的恶战,它们有着战争的口号“不战胜、毋宁死”,也有着“各自的军乐队”,“吹奏着各自的国歌”,“一只孤独的红蚂蚁眼睁睁看着同伴失去了一条腿,犹如“阿基里斯一样的英雄,独自在一旁光火着”。梭罗把蚂蚁之间的这场撕战一会描述成为了权力之争的英国内战,一会描述成塑造英雄的特洛伊之战,或是一场“奥斯特利茨之战,或一场德累斯顿之战”,又或者像“邦克山之战。”[3]182-3观战让梭罗“相当激动”,“觉得它们和人类并没有不同”,他认为在康科德的历史中,“没有一场大战可以跟这一场战争相比的,无论是战斗人员的数量来说,还是从它们所表达的爱国主义和英雄主义来说。”[3]82
梭罗把黑蚂蚁描述成保皇派、黑武士、波特利克;红蚂蚁描述成共和派、红武士、阿基里斯。它们身上体现出强烈的英雄主义、爱国主义,而且有着集体荣誉感和坚定的信仰。梭罗通过拟人化的书写,将蚂蚁描述成了拥有历史和文化的民族和国家。读者的注意力被紧紧吸引到蚂蚁身上,其情感也随着梭罗的激动观战而波动起伏,蚂蚁不再是微不足道、无关紧要的他者,而是有着自己历史文化记忆的生命群体,和人类没有任何区别。梭罗对自然的拟人化书写激发和培养了“我们对物质力的敏感性”,“使我们与物质产生共鸣。”[5]119-20在梭罗看来,自然的故事不是任由人类书写,人类只不过是大自然的抄写员,灵感的过滤器、诗歌产生的物质场域,而故事的叙事者是自然本身,是物本体。
三、人的物化
对于新物质主义而言,物的拟人化和人的拟物化(reification of persons)是打破物人界线的两个维度。大卫·爱布拉姆(David Abram)的著作《成为动物》(Becoming Animal, 2011)专门探讨了人的拟物化。“物的拟人化”和“人的拟物化”可以使“主体和客体出现一定程度的合并或重叠,进而消抹了有生命与无生命之间的界限。”[6]371对于梭罗来说,物具有情感、智慧、能动力等原本只属于人类的品质,人也随时可以进入物的状态,呈现物的特征,人与物在“内在互动”中相互影响、“相互纠缠”,并“在纠缠中相互生成。”[7]33梭罗在《瓦尔登湖》中以第一人称叙事视角记录了自己不同形式的物化状态,进一步模糊了人和物之间的界限,打破了人类中心主义的藩篱。
首先,梭罗“意识到自己身上存在一种动物性。”[3]175当他走在打猎回家的路上,遇到一只土拨鼠,内心突然“产生一种野性的喜悦,萌生了一个念头:‘一定要抓住它,然后生吞掉。’不是因为他饿了,而是“野性使然”[3]167。在梭罗看来,人具有双重本能,基于精神追求的高级本能和基于野性的原始本能,后者往往会处于沉睡的状态,但在荒野与土拨鼠的突然相遇激发了梭罗的动物野性。他与土拨鼠无异,也是动物世界中的捕食者。动物性的显露恰恰削弱了人类主体的优越感,进一步消弭了人与动物之间界限。
其次,梭罗在他的日记里详细记录了凸显自身植物性的经历。那是一个夏日午后,因为天气炎热,梭罗自称感受到了大气的重量和压力,他夸张性地利用了自己在测量方面的天赋,声称感觉到了周围的压力是“每平方英寸一十五磅”,这种压力使人不由自主屏住呼吸、停止思考,“只能像棵麦穗似的在微风里点头”[8]76。对于梭罗来说,自然的神秘力量促使人类思维脱离正轨。他停止了思考行为,进入一种自发的植物状态,模仿植物的行为,像麦穗似的点头。如果说土拨鼠的突然出现唤醒了梭罗体内沉睡的动物性,那么炎热午后的空气压迫诱发了梭罗体内植物性的苏醒,促使他成功地从人的状态过渡到植物的状态。
除动物性和植物性之外,梭罗还随时可以呈现其他不同的物质状态。当他安静地站在瓦尔登湖旁,他感觉自己“就是多石的湖岸”[3]153,当他站在拱桥上观赏瓦尔登湖湖水,顷刻间他觉得自己就“像一头海豚生活在其中”[3]160。“湖岸”和“海豚”都是梭罗在自然神秘力量影响之下的自我物化行为。最有意思的莫过于将人物化为泥土的描述,梭罗在散文“春天”中发问,“人不就是一团溶解的泥土吗?”[3]124接着他进一步形象生动地将人体器官加以物化,将手指和脚趾描述成“凝结的水滴”,手掌则是“舒展的棕榈叶”,耳朵是“苔藓”,鼻子则是“凝聚的水滴或钟乳石”,脸颊是“斜坡”,人的生物主体性随着这种物质性拆解逐渐消弭。生物体的人变成了一个物质体的人,人与物之间的界线进一步被消解,人和自然已经浑然一体。
四、心物感应
如果说“与禽兽为邻”中的物本体呈现主要通过“谨慎的拟人化”,“更高法则”中的物本体书写主要通过“人的物化”,那么散文“寂寞”则主要通过“心物感应”或者说“跨物种同情”来进行物本体书写。散文一开始梭罗便感觉自己“好像成为了一个整体,每个毛孔都钻进了欢乐的小精灵。在大自然中我任意翱翔,融进它的身体里。”[3]102森林里“每一枝小松针都富有同情心地胀大起来,成了我(梭罗)的朋友。我明显地感到这里存在着我的同类。”[3]104松针的同情说明梭罗和松针之间存在着情感互动,人和物的界限完全消除,人和自然最终融为了一体,实现了物我为一、相互影响、相互纠缠的状态。
从新物质主义的视角来看,松针和我之间的同情是一种“跨物种同情”(Cross-Species Sympathy),表达了人和物之间的互动与纠缠。简·本尼特认为同情并不专属于人类,也不具备一方对另一方的优越感,而是“一个更古老的同情形象,它是一种从外部作用于身体的生命力,一种脱离了人类中心主义的大气力量。”[5]27它与“自然和神奇的传统保持着重要的联系。”[5]29同情不是人类专属情感,而是一种在空气中循坏的“感情流”,它脱离了人类中心主义的藩篱,把不同类型、不同物种的事物联系在一起,把自然和人类联系在一起,弱化了人类主体的物种优越性,也弱化了人和物之间的界线。梭罗感觉自己和自然融为了一体,“婀娜多姿的赤杨树,微微晃动的白杨”[3]102异常让他心动,“心动”也恰恰说明了人和物之间的跨物种同情和情感上的互动。
梭罗笔下的跨物种同情,让人不禁想起中国传统自然观中的“心物感应”说。在爱默生的影响和带领下,梭罗在超验主义俱乐部期间大量阅读了中国典籍,深受中国传统自然观的影响。他在《瓦尔登湖》中大量引用中国典籍《中庸》《礼记》等的原文,这为我们从中国传统“心物感应”说反观梭罗的自然思想提供了依据。无论是人与松针的“同情”,还是人对树木的怦然“心动”,都体现了中国传统文论中关于“心物感应”、“物我两依”的感物观。中国古代对心物关系的探索形成了源远流长、影响深远的“感物”传统。“感物”说强调外物对人的刺激以及人对外物的感应,在心物感应中形成天人合一的亲密关系。中国“感物说”最重要的理论来源来自《礼记·乐记》:“凡音之起,由人心生也。人心之动,物使之然也。感于物而动,故形于声”[9]525。南宋刘勰在《文心雕龙》中提出了“心物感应”之论,“构成物之心会、心之物会的双向同构、相互交感的‘感物’说”[10]164。
“感物”说的一个重要代表是北宋邵雍所提出的“以物观物”。他继承了道家的“以道观物”说,强调遵从天地之道,即客观世界自然而然的运行规律,不以个人情感和视角观天地之道。他认为,“夫所以谓之观物者,非以目观之也。非观之以目,而观之以心也。非观之以心也,而观之以理也”[11]49。邵雍反对以目观物”和“以心观物”,提出“以理观物”,进一步发展成“以物观物”。用“心物感应”和“以物观物”说来反观梭罗的自然观会有不一样的发现,他在“寂寞”一文中提出,人类“只是一个思想和情感的舞台”,而“一切事物,无论好坏,都像一股急流从我们身边流过”[3]106。对于梭罗而言,人只是一个思想和情感的物质载体,人只有遵从自然的崇高法则。他认为,“神鬼之为德,其盛矣乎!视之而弗见,听之而弗闻,体物而不可遗。使天下之人,斋明盛服,以承祭祀,洋洋乎,如在其上,如在其左右”[3]106。这段话的原文出自中华典籍《中庸》,意指鬼神的德行强大无比,虽看不见也摸不着,但它却隐形于万物之中使人无法脱离其存在的影响。
梭罗怀着“以物观物”之心,最大限度地弱化自我,甚至“以物观我”,使自己进入物化的状态,最终实现“心物感应”、“物我两依”的和谐状态,因此他“感觉到和大自然作伴是如此甜蜜、如此受惠。”[3]104。他能感受到大自然对人类的跨物种同情,也能感觉到自己“和大地灵性相通”,感觉自己是“绿叶和植物的土壤的一部分”[3]109。“以物观物”的方式,让梭罗看到了自然的神圣和物化自然的“无限撤退”(withdrawal)本质,“任何试图通过直接或字面的语言来把握的努力都不免要失败”[12]20,因此梭罗批评人类文明的“洋洋得意”,也批评人类“自以为聪慧,自以为在大地上建立秩序”[3]264的自负。
对梭罗来说,地球是一个生机勃勃的星球,“万物都是有生命的”[3]245。自然是一个有机整体,每个个体都独立地感知并相互作用。瓦尔登湖具有强大的吸引力,因为“它高悬在我的思想之上”[3]153,展现出一种它在宁静中与世隔绝、使人难以接近却又渴望接近的巨大力量。但是“它的神奇不可测量”[3]229。这种近在眼前却让人无法操纵、无法理解的状态,让梭罗产生敬畏之心和不可思议之感,让他觉得瓦尔登湖是“接近上帝和天堂”的地方。梭罗深知很多“看似矛盾、实际却交相呼应的法则,它们产生的和谐却有更惊人的力量”[3]231。
总之,梭罗通过物的“罗列”、谨慎的拟人化、人的物化以及“以物观物”的物性叙事,不仅大大丰富了西方文学中的物本体书写,与当今畅行于西方文论界的新物质主义“物转向”形成跨时代共鸣,也从侧面客观发展了中国文学中的“感物”传统,与中国“心物感应”、“以物观物”说形成跨时空对话。通过物本体书写,梭罗在《瓦尔登湖》中表达了“去人类中心主义”的哲学观和尊重自然万物生命价值的环境伦理观,与19世纪美国工业文明话语进行对话与对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