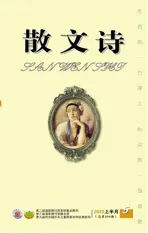灵魂的出口
2023-08-22毛歆炜
◎毛歆炜
帽 子
经过不懈努力, 终于获得了一个令人羡慕的职位, 我却怎么也高兴不起来, 因为上司奖励给我一顶帽子。
帽子上站着一只小鸟, 远胜过单独一片羽毛的优雅。 它啄帽子的时候, 我便点头哈腰; 它拍翅膀的时候, 我便拼命鼓掌; 它欢呼雀跃的时候, 我便鞍前马后, 为上司臃肿的妻子打开车门,撑开遮阳伞。 它让我的工作无比顺利, 即使困倦到打瞌睡, 也能瞬间焕发出神采。 当然, 我是从同事的帽子上看出这些蹊跷的。
这天, 我突发奇想, 回家后径直走到梳妆台前, 假装整理领带, 突然举手驱赶它。 它比我机敏多了, 低头、 旋转、 跳跃, 轻松化解了我一连串的袭击, 我气得团团乱转, 却连它的一片羽毛都没摸到。 它始终在帽子的正上方, 举手就能够得到的高度。
剧 本
“我要下班了。” 他看着我, 没有收起打字机, 桌上还有几张白纸。
其实, 他是在问我, 想好了没有? 究竟要怎样的剧本, 过怎样的人生? 那么多人都拿着剧本走了, 唯独我还坐在这里。 桌上的几张白纸足够写完我平淡的过去, 若不出意外, 也够写完我平淡的未来。
“明天见。” 我从桌子上下来, 在金色的落日里, 沿着沙滩和潮汐走向公路。
“你知道这里边的秘密。” 他站起来, 海边的猎犬跑到跟前。
“我一直都知道。” 我摘下帽子朝他挥了挥, 没有停下来。
正是这个秘密, 让我犹豫不决。 想要改变剧本的人很多, 但没有一个人提出来, 所以, 拿到的剧本都是重演。
他们怀抱着剧作家有一天拿错剧本的希望, 像排着队买彩票的人。 我想要的剧本, 断不是几张白纸就能写完的, 只是现在还没想好。
大 鱼
我拎着手提箱来到湖边的商店, 租一条船度过难得的假期。老板是一条青色的大鱼, 它的声音醇厚, 像沉入深海的绿酒。
它对我说: 你来晚了, 船都租出去了, 如果你不介意, 可以骑在我的背上遨游。
虽说是条大鱼, 但也没大到可以让我骑上去, 小时候, 我曾从一头小猪的背上颠簸下来过, 现在, 这可是一片大湖。
见我有些犹疑, 它说, 你不要不知好歹, 能骑在我背上可是多少人梦寐以求的事。
湖面风和日丽, 难得的好天气, 我答应下来。
它走到浅水区, 趴下来, 咕噜咕噜喝了几大口湖水, 身体瞬间变大了好几倍。
我好不容易爬上它丝绸般柔滑的脊背, 刚抓住背鳍坐下, 它便开足了马力, 一路乘风破浪, 向湛蓝的大湖深处驶去。
白 鹳
天空昏暗下来, 洪水从江边漫了上来, 屋后的茭白地里灌满了水, 人们卷起裤管在水里摸鱼。 他脱掉鞋袜, 加入到人群中,抱起卡在茭白丛中的一条大鱼, 大鱼蹦了一下, 变成了一只小猪, 从他手上逃脱, 飞快地跑到了岸上。 光线真暗啊, 他们是怎么摸到鱼的呢? 难道是手掌的皲裂消除了鱼鳞的光滑?
他看到了一条蛇或黄鳝, 在水面上立起身子, 他迅速出手,扼住了它的咽喉, 它窒息般地坚硬起来。 他抬起头, 白鹳醒来,轻抬翅羽, 露出长长的喙, 疑惑地看向他。 他感到十分抱歉, 连忙松开手。 一大群白鹳越过茭白地, 振翅飞向山林。 人群停下手中的活计, 哄笑起来。
他悻悻地上岸。 或许一开始就应该明白, 他这种人不适合在水里捕鱼。 他可以在岸上捕鱼, 在天上捕鱼, 就是不能在水里。他们看起来站在水里, 但桶里的鱼, 是不是在岸上捉到的小猪或天上捉到的白鹳呢?
雪 象
下雪了。
他披上大衣, 戴上帽子, 牵着狗来到雪地里。 朋友打着伞,胳膊下夹着报纸包裹的面包。
他们站在雪地里攀谈, 狗靠着一根乌黑的柱子, 几个孩子在门口堆雪人。
“有人看到雪象, 向小镇走来。”
“雪象总是在下雪天穿过小镇。”
他们满怀期待, 四下打量, 渐渐不安起来。
“雪象是不是早就过去了?”
突然, 狗叫了几声, 一个孩子从屋里跑了出来, 兴奋地追向什么, 而他们什么也没看到。
湖
人人都说这片湖很美, 湖也知道自己很美。
它的平静与波浪, 蔚蓝与洁白; 它身上披着的清爽的风, 头上戴着的湛蓝的天; 它呼出的云朵和飞过的鸟群, 无一不是美的。
一个画家从它身边经过, 由衷感慨道, “真美啊!” 随后摇摇头, “可惜太过单调, 要是有一座岛就好了。”
几年后, 湖上冒出一座天然形成的小岛, 岛上有一棵盛开的合欢树。
画家在岛上支起画架, 摊开颜料, 他的小船拴在合欢树上,帽子搁在船头。
他画下了湖边的遮阳伞、 桌椅、 棕榈树、 酒店和群山, 画下了椅子上度假的人和桌上的椰子, 唯独没有画这片湖。
跑 步
跑步的时候想什么不重要, 身体的忽闪明灭不是由思维放电造成的, 其本身就是一种断断续续的不为肉眼所捕捉的影像进程。
譬如绘画《下楼梯的女人》, 譬如一条狗从栅栏的一端走到另一端后身体不断拉长, 栅栏的静止填补了它流动时身体虚幻的部分。 静止的形态即是斑马黑白相间的条纹, 钢琴黑白相间的琴键。
脚踩在地面的一刻, 是存在的; 双脚脱离地面的瞬间, 是虚无的。 持续流动造成的连贯影像不过是一种幻觉, 连环画是真实的速写, 而一幅画到下一幅画之间, 不过是子虚乌有。
阿波利奈尔
长途汽车司机激烈地与自己交谈, 或许是车速太快, 前言老是搭不上后语。
我完全听不懂他在说什么, 其他的乘客听得懂吗? 有时候,语言表达的内容比语言的种类本身更捉摸不透。
由于司机的头颅里有一场自我的唇枪舌剑的对决, 原本包扎脑袋的纱布开始渗透出微红的血迹来。 他是一个顽强的斗士, 像战场上头部负伤的阿波利奈尔, 又像大江健三郎那出生时即患有脑疝的儿子光。
外面是一场大雪, 弯曲的竹枝上蹦跳的麻雀踏落下蓬松的雪块, 凛冽的空气中传来桉树折断的声音。 阿波利奈尔双手拢在衣袖里, 独自向风雪中的医院走去。 我们安静地坐在车里, 等待下一趟车的到来。
蓝孔雀
气温骤降。 你黑色的连衣裙过于单薄, 我脱下薄外套裹住你颤抖的肩膀, 我们都被南方连日的艳阳天欺骗了。 路灯锃亮的圆脸庞, 剥出一粒粒细碎的光。 商店已打烊, 变幻的天气让橱窗里的模特不知道穿什么好, 便索性什么都不穿。
我们往南走。 街道的尽头, 一只巨大的蓝孔雀, 身体隐藏在大厦后面, 敞开的尾羽, 像一束寒冷的光线指向夜空中寥落的星斗。 无论怎么走, 蓝色的尾羽始终若即若离。
“不能再往南了, 再往南就是大海。”
你周身萦绕起阵阵寒凉的晨雾, 裸露的脚踝, 像一块蓝色的冰。 此刻, 海上传来蓝孔雀摄人心魄的鸣叫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