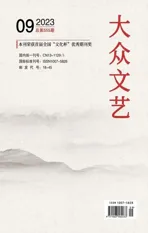黑暗灵魂的舞蹈
——评残雪《黄泥街》的荒诞叙事
2023-08-21邱怡
邱怡
(湘潭大学,湖南湘潭 411105)
20世纪80年代中期,在世界文艺思潮涌入国内的背景下,西方现当代作品的主题思潮和艺术形式成为中国新时期文学的重要借鉴。依据《美国当代荒诞小说》(Contemporary American Novelist of the Absurd,Harris Charles B)查理·哈里斯在书中给出的精确定义,荒诞派小说即“运用荒诞的写作手法处理荒诞主题,用荒诞的创作方法处理故事、塑造人物和经营语言,借此反映荒诞世界的视域”①[1]。八十年代中期中国先锋派的代表人物之一残雪,其作品《黄泥街》的内容和形式均明显受到荒诞派的影响。而八十年代中国文学的生长语境,又使先锋文学具有中国特色的文化面纱。小说《黄泥街》在厚重的历史文化基础上展开奇特的想象,体现出强烈的个性化和本土化特征,是为荒诞派叙事在中国土壤上蔓生的枝丫。
在《残雪文学观》中,残雪曾表示通过写《黄泥街》,她明白了她文学创作的目的是要写具有最大普遍意义的文学,也即“纯文学”。她所谓的“纯文学”,是一种对人生存在问题的超意识形态化书写,借助于非理性、反逻辑和潜意识的荒诞写作,残雪将读者推向自我的心理世界。在文本细读的基础之上,本文通过对小说荒诞化的语言、人物、情节进行分析,以期探寻残雪故事冰山下的生命真谛。
一、诗性而梦呓般的语言
梦呓,指人进入睡眠状态之后发出的某种语音,醒后也不能回忆。《黄泥街》的序文,便铺叙了一个似真又幻的场景。第一人称视角的“我”,在黄泥喧天、破败不堪的一条街上遇上人就问“这是不是黄泥街?”而没有任何人回答“我”的问题。街边房子全塌了,门框上结着蛛网,空气中弥漫死尸的臭气,街上的人“瞪着死鱼的眼睛”,乞丐的头发里可以掉出“金龟子那么大的绿头苍蝇”。场面的描述已然奠定了全文的怪诞,进而笔触伸展:“有一个梦,那梦是一条青蛇,温柔而冰凉地从我肩头挂下来”。小说中的“我”是谁?从何而来?为什么要找寻黄泥街?那条街为何又如此令人犯怵?正如日本学者近藤直子曾提到的,残雪的小说里总带给读者那种熟悉的不可思议、熟悉的陌生感、暗示读者的无知的谜,有关黄泥街的梦也让读者陷入扑朔迷离的境地。
梦呓般的语言在以第三人称视角进行叙述的小说主体部分得到鲜明地呈现。恰似人在梦中的所想所见常有不合逻辑以及让人感到怪诞、恐惧的特征,梦呓般的语言也就指向了《黄泥街》小说语言的非理性组织与意象不知所由的冒出。首先是语言形式上的混乱,如小说中人物之间的对话交流虽看似在你一句我一句地进行着,而对话实则鲜少达到真正沟通的效果,人物交流达到的效果并不是形成一个联络起来的空间,而是向每一个人物隐秘的深处开凿。话语的排列并不构成逻辑。如宋婆说自己家有一只猫被老鼠咬死了,转瞬紧接着说关于街上王子光的事件的备案工作应该停止了,再一折回来,又莫名其妙地让人思考老鼠为何能咬死猫。故事中无论是人物的言语还是场面的描绘,都存在着蒙太奇式的跳跃之感。适应了寻常语言逻辑的读者会发现想要在《黄泥街》中找出清晰连续的片段只是一种徒劳的努力。其次是语言内容上的超乎寻常,小说在意象的选择上其实为读者形成了较大的阅读障碍。残雪走向了审美的反面——审丑,她尽其所能地描绘烂果蔬、烂鱼肉、苍蝇、蟑螂、蚂蟥、白色小蛆、垃圾、粪便、流脓的伤口等。又写宋婆拌着饭吃苍蝇,吃过的蝙蝠的骨头也填满了一座墙;胡三老头为了证明自己能吃蜈蚣,连吃几十条蜈蚣;老郁将他老婆的手用钉子钉在床沿上,只是想试验,来看看血从钉子眼里流出来,如同一根细带子等等。这些令人发怵的场景,只有在梦里才具有可能性与合理性,梦呓般的语言映照出荒诞的特性。
但《黄泥街》的语言却又是存在着诗性的特质的。一方面,残雪并非写不出寻常的具有美感与韵律的语言,小说的结尾部分再次回到“我”的视角,回应着序言“温柔而冰凉”的梦,她以优美的语言吟唱:梦的碎片落在我的脚边——那梦已经死去很久了,夕阳照耀,这世界亲切又温柔。②[2]小说在文章两端(即序文与结尾)实现了诗歌所要求的律动、审美的特征,在流淌、绵延、鲜明的语言中透露出孩子般的纯真。而另一方面,《黄泥街》的诗性内蕴于“拒斥”读者的荒诞描写。残雪在访谈录中曾提及,自己的创作应该算是一种“小说诗”。所谓诗性,是将普遍性、本质性的真理蕴藏于言语之中的文学性质。或许浮华美丽的外表常常让人忘记诗的本性,所以残雪神经质地干脆丢掉近乎所有的矫饰,用极丑极恶把读者推向思考的深渊。残雪在《黄泥街》中的语言让人的精神在经历痛创与恶心之后得到疏泄,而小说两端文字绵长的质感则又让人感到虚空,恰如西方荒诞派的作品让读者们感到人生的状态即存在于意义与虚无的挣扎之间。
二、具有夸张怪癖而符号化的人物
在荒诞小说中,人物常常被作为符号和象征来设计。为了表现小说荒诞的荒诞主题,人物的个性特质得到了充分的强调和夸大,作为符号或象征的人物也就指代了人物形象中独有的性质和冲动。一览《黄泥街》的人物命名,会发现人物名称构成其实都极为简单,宋婆、齐婆、王四麻子、齐二狗、胡三老头、老郁、袁四老娘、王厂长……故事中从未交代过他们有什么样的过去,读者在捕捉这些人物时只能获得一种可替代性,也就是说,每一形象的身份其实都暧昧不清,不过是一个个的符号而已。这种符号化表现在黄泥街中反复出现的“王子光”上尤为明显,“王子光”三个字成为“黄泥街人的理想”,而“王子光”究竟是不是一个真实存在的人?究竟是谁?从来没有得到过确认。符号化的处理模式还让残雪得以抛弃现实世界视为极重要的常理。她隐去小说中的社会关系、抛却人情伦理,如胡三老头因为年纪大,被儿女嫌恶、驱赶,女儿总是盼着他死去;宋婆的父亲死后,夫妻两个人将马路上的尸体塞进大纸箱里,捆好,抬至河边,直接扔进河里,温情荡然无存。人物的变形如弗朗西斯·培根的画,他的每一幅画中有一个独立、痛苦的情绪化人物,残雪的每一个符号中就有一个乖张、荒蛮的灵魂世界。但残雪的小说并非要通过人物的描写鞭挞人的丑恶,而是要捅开一个人们选择视而不见或不愿承认的真相:自私、虚荣、嫉妒、残忍、狂妄,这些人性弱点从来都无可避免。
黄泥街人另外一个普遍特质是对他人隐私的窥探,因而在黄泥街上,也就构成了一个窥探与被窥探纵横交织的网络。也正是因为无处不在的窥伺,人物形象的怪癖如同在放大镜下被夸张地凸显。宋婆不停地吃蝇子和蝙蝠,老郁喜欢看血细带,江水英的丈夫爱将活物关在笼子里……有些怪癖甚至是普遍性的,如黄泥街上的人,无论四季,为了防止风寒都要穿着棉袄,他们宁可沤出蛆来。整个黄泥街就处在居民们的彼此监视之中,种种怪异被视为常态,他们相互之间充满厌恶、排斥,但也相互接受,矛盾之中,相互的窥探也就构成了相互的暴露。由此观之,故事的叙述者残雪,她对于作品的每一笔刻画,仿佛是在书写与“窥探”他人,实则也是对潜意识的自我内心世界的书写呈现。
符号化而具有夸张怪癖的个体就这样被置于黄泥街迷雾般的空间里,人物所处的社会空间、所具有的社会身份被予以淡化。残雪笔下怪癖的人物形象究竟影射着何种现实,读者无法确切得知。但可以肯定的是,在残雪构筑的“对立的世界”中,现实面具的不复存在,人物真实的本性被无所顾忌地暴露出来,从而展现出人性中不加掩盖的阴暗面。在书写符号式的人物的过程中,残雪正是通过抛却现实中人的附属之物,让社会集体中的“人”得以回归至个体的“我”,触摸人性中最深层的世界。恰如残雪所持之观念,所谓的善与恶并不存在于她的文学作品之中,因为她的故事并不完全反映现实世界,而却映照着人的真实自我。古老的欲望与现实的理性挣裂出一番天地,诡诞的生活中人心自在地漫游。这正是荒诞的旨归,即冲破传统的牢笼,歇斯底里地舞动,最终投向人的内心世界。
三、错乱而无果式的情节
在常规的小说世界中,依据时间顺序对于故事情节进行交代是符合读者的阅读期待的。如果作家因效果呈现的需要,也会较为审慎地选择其他如插叙、倒叙、回叙的方法,不致以让读者反复回读前文。而残雪的小说却予以读者一种挑战,如学者金蕾蕾所说:“愈用逻辑线来疏导,愈产生一种‘云深不知处’的感觉”③[3]。在《黄泥街》中,顺时的情节倒是成了小说中的稀缺品。残雪善于在她的文本中运用顺叙、倒叙、插叙、补叙、回叙,而将最后重组情节的工作交给读者来完成。《黄泥街》中这样的例子随处可撷,如记录宋婆父亲死亡的过程,小说的情节交代是:1.一天夜里下了场没完没了的怪雨,雨水又黑又臭。2.第二天早上,宋婆在厨房发现她父亲躺在水里。3.宋婆把丈夫和儿子们叫来。4.死尸的喉咙被宋婆和丈夫用叉叉住,抵到马路上。5.在三个月前,父亲说他要住在厨房里。6.宋婆在前一天夜里用铁铲向父亲躺的地方铲去。7.早上,夫妻两人又一起将马路上的尸体塞进一只大纸箱,扔进了河里。首先,在对这七个情节进行记录时,本身也夹杂着各种各样其他无关事物的描述与无关人物的对话,让读者常常记了前边就忘了后边,顾此失彼。其次,将宋婆父亲死亡相关情节单拎出来,也会发现顺序的错乱,残雪留给读者的仁慈是她较为鲜明地将时间词语放置在情节片段之中,读者才得以稍有脉络。错乱的情节呈现出浓烈的陌生化效果,每一次对于记忆中连续情节的呼唤又夹带着无关情节的渲染,迷离殊异、恍若隔世,《黄泥街》所有的叙述就像一场被打碎的梦魇。
《黄泥街》在情节上还呈现出无果式的特征。正如故事开头的“我”询问这条街是否是黄泥街,每个人都对我报以死鱼般的眼光却没有最终的答案一样,全文不断出现的“王子光”和“王四麻”事件也从来没有得到最终的结果。在故事的第二节,残雪将标题命名为“改变生活态度的大事件”,这一节中,王子光的到来与存在似乎是让“黄泥街新生了”,而这种“新生”,并非什么人物在行动上实质性的改变,而是让街上的居民们有了一种对“王子光”的猜度臆想,这让原本就足够疯狂的黄泥街搅动了更多的烂泥污水,黄泥街人无端地生出那些没有边界的幻想,又长长地浸于苦恼和兴奋的轮替之中,不得解脱。围绕着“王子光”,小说第四节进而写“王子光进入黄泥街”,为了查明被认作为人的“王子光”的真实身份,朱干事和区长开展调查,居民善于窥探,街上流言四起,人人说起自己印象中的或看到的“王子光”。事件未被查清,有的居民却莫名其妙地失踪与离世,王四麻、老孙头、老郁、杨三癫子……继而他们就一个接一个地被指认为“王子光”,哪怕最后宋婆认真地宣布,王子光其实是一个普通人,是跳楼身亡的,人们也不愿相信。黄泥街上的人总在虚无缥缈地状态下煞有介事地谈论,但直到最后“王子光”究竟是人是谁还是其他事物都不能确定。于是在每个人自说自话的空间里,“王子光”成了一个“戈多”般的期盼。故事情节最终的无果,让读者同小说中认为“王子光”必然存在的居民一样,居民滞留在对“王子光”执拗、永恒的想象之上,读者因无法获得故事情节的结果,则就滞留在了对居民们想象的观察之上。
正是因为情节的错乱与无果,读者的目光就难以聚焦在“王子光”“王四麻”事件的脉络之中,转而思考黄泥街的人们为何总愿意沉迷于无端的臆想,于是我们就会发现黄泥街人其实饱含着一种生命的活力:污浊的环境之中,他们喝着阴沟水,吃着泥巴、蝇子、蝙蝠……住在朽烂的茅草屋里,到处都是垃圾粪便;相互之间充满了窥探与怨恨,家庭成员间毫无温情可言,而每一个卑小怯懦、愚昧昏聩甚至穷凶极恶的黄泥街人哪怕在极为破败的境地之下仍然关注着意识形态和审美的问题,“以一种可笑、可怜、可鄙然而毕竟令人感动的方式表达着他们不敢沉沦的人性闪光和生命的韧力”④[4]。万劫不复的地狱里,残雪所做的正是在为他们唱着温柔的歌,用孩童般自在的节奏与曲调,慰藉着这每一个舞蹈着的黑暗魂灵。
结语
黄泥街是残雪凭借着一种“野蛮的力”构造出她所认为的与现实世界对立的世界,而关于这个世界的书写,并非在走中国传统的“讽上化下”“兴观群怨”和批判现实主义文学的道路,读者也无法通过“国民性批判”对此加以解读。正如至今很多人认为卡夫卡所做的是一种对资本主义制度的批判,残雪认为这种解读是完全不够的。残雪的作品已无法用“文学反映现实”再去平庸地理解,她从卡夫卡那承延的实为一种人性的反思,归根结底是关于自我世界的发现和再发现,黑暗灵魂的舞蹈最终指向于万劫不复的地狱生活中人的生存意志的不可遏制的盲目冲动。
《黄泥街》作为一部先锋文学作品,对于传统的文体理论有着颠覆性的挑战,它既非文体变异也非文体嬗变,而是实打实的一次文体解构。作者笔下晦涩的故事堆砌起了无数关于内容与形式的疑问,语言、人物与情节的突破式处理逼近读者弃读的阈值,而故事又就此戛然而止,独留读者霎时间突然落空的想象。于是,小说被不甘心的读者再次翻开,千回万转地勾连起蛛丝马迹,却如何也仍走不出故事的迷障。而停下脚步、闭眼,向自我深处探寻,便会遇见此番景致——荒诞至极的叙述将遮蔽着人性世界的光滑外壳敲碎、剥落,本我的欲望与真实的冲动赤裸地呈现出来,这是残雪的心灵世界,或许也是现代意义上每个人心中的深藏的世界。
注释:
①徐明,刘伟萍.西方荒诞叙事对中国新时期荒诞派小说表现手法的影响及反思[J].东北师大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8(03):111.
②残雪.黄泥街[M].广州:花城出版社,2013:153.
③金蕾蕾.生命的梦魇——论残雪小说《黄泥街》的叙事策略[J].名作欣赏,2008(02):93.
④残雪.黄泥街[M].广州:花城出版社,2013:2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