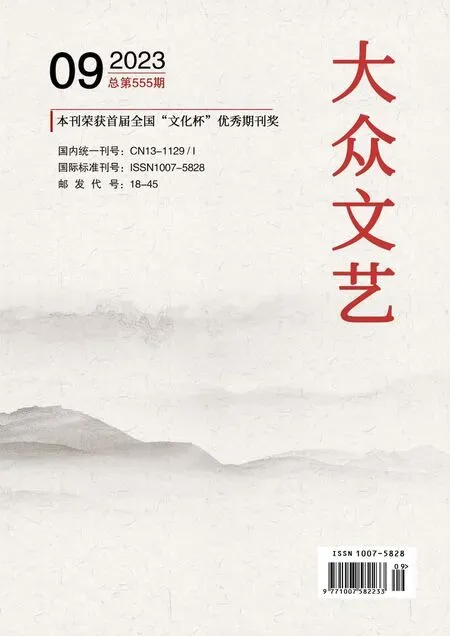T.S.艾略特与卞之琳三十年代创作中对古典诗传统的回望
2023-08-21孙思宇
孙思宇
(郑州大学 文学院,河南郑州 450001)
卞之琳是现代中国著名诗人和翻译家,他在漫长的文学生涯中不仅留有许多脍炙人口的诗篇,而且还撰写了数量可观的文字以集中阐释他对新诗写作的理论认识,极大推动了中国新诗的发展。在1979年出版的《雕虫纪历》所写自序中,卞之琳将其诗歌创作分为三个阶段。其中的战前诗作集中体现了卞之琳诗歌的独特风格。这一时期他开始接受现代西方诗学理论,创作日益走向成熟,从波德莱尔、魏尔伦、马拉美到瓦雷里、里尔克和艾略特,卞之琳不断汲取外来养分并结合既有经验,逐渐形成自己的诗歌气象。而在诸多西方诗人中,卞之琳对艾略特较为推崇,并多次论及艾略特与其诗歌创作的关系。首先,卞之琳在译介艾略特的诗文方面做出了突出贡献:艾略特的著名论文《传统与个人才能》正是在卞之琳的翻译下才得以首次为中国民众所知,而且《卞之琳译文集》中也收录了他对艾略特的评价:“艾略特……最初一起干的是所谓‘拆台’工作……他们在精神上无出路当中产生的消极作品里,也多少可以起揭露现时的积极作用。”①[1]从中可以看到卞之琳对艾略特创作的肯定态度。此外,他还回忆到:“对于西方文学……从1932年翻译魏尔伦和象征主义的文章转到1934年译T.S.艾略特论传统的文章,也可见其中的变化。”②[2]更提及“写《荒原》以及其前短作的托·斯·艾略特对于我前期中间阶段的写法不无关系。”③[3]不难发现,艾略特对卞之琳来说具有相当重要意义。
1934年5月1日出版的《学文》杂志上刊登了卞之琳受老师叶公超嘱托翻译的《传统与个人才能》,这也是它在中国刊物上的首次发表。卞之琳自称此文“大致对三四十年代一部分较能经得起时间考验的新诗篇的产生起过一定作用。”④[4]艾略特这篇论文主要由两方面组成:首先,艾略特介绍了自己对于历史意识、历史现存性等问题的看法:“传统的意义实在要广大得多……要理解过去的过去性,而且还要理解过去的存在性……现存的艺术经典本身就构成一个理想的秩序,这个秩序由于新的(真正新的)作品被介绍进来而发生变化。这个已成的秩序在新作品出现以前本是完整的,加入新花样以后要继续保持完整,整个的秩序就必须改变一下。”⑤因此作家和作品始终都处于历史和传统之中,他们被传统制约的同时最终也会加入传统并推动现存的体系发生变化,正是在这一过程中,传统的价值和意义得以进一步丰富。其次,艾略特具体论述了诗人心灵在具体创作中的催化功能,进而旗帜鲜明地指出诗歌价值主要体现在其艺术过程上而非创作主体本身情感的强烈波动。虽然《传统与个人才能》没有能用于实际参考的创作方法,但它肯定了诗人与传统的密切联系,并在此基础上主张诗人要不断放弃当前的自己,归附更有价值的东西。这些理论无疑对卞之琳产生了影响,促使他在1930年代的创作中更自觉地检视和利用中国古典诗歌的丰富资源。
作为贯学中西的诗人和翻译家,卞之琳在20世纪30年代初就走上一条既现代又传统的创作路径,而《传统与个人才能》亦加深了他对“传统”的理解。发表于抗战胜利前夕的《新文学与西洋文学》一文中卞之琳系统表达了有关“传统”的体会:“那并不是对旧东西的模仿……我们只有以新的眼光来看旧东西,才会使旧的还能是活的。”⑥[5]可见卞之琳眼中的传统并非静止的实体性概念,它与现代超越了狭隘的二元对立,在时代和历史中不断变迁并显示出强大的整合能力和生命力。这就使置身现代西方诗歌场域中的卞之琳更强烈地意识到自身传统的力量,他在1930年代创作的一些作品就从多个方面对这种“传统”观念进行实践。
一、有意识使用中国古典诗歌成规
卞之琳在诗歌中曾大量运用“水”“梦”“春草”等古典意象,此前学者对此做过专门分析。古典意象的运用固然对诗歌风格定型起到重要作用,然而仅凭这些词汇只能在表面上渲染典雅气氛,隐藏于意象背后的结构因素才是关键。中国古体诗词的中心意象群都与诗歌主题有所关联,而所谓古典诗歌成规的运用就是这些元素在现代语境中的重现,表现之一便是对“典故”的使用。众所周知,新文学运动的先驱胡适先生旗帜鲜明地提出“务去滥调套语”“不用典”两条戒律,但卞之琳却在多首诗中大量用典,还自加注释阐明其含义。虽然这些并非都是古代诗人常用的典故,可仍在很大程度上显示出卞之琳的诗歌与古诗的联系,同时也和胡适提倡的“白话”诗分道扬镳。例如《春城》:
北京城:垃圾堆上放风筝
……
真悲哉,小孩子也学老头子
别看他人小,垃圾堆上放风筝
他也会“想起了当年事……”
悲哉,听满城的古木
徒然的大呼
呼啊,呼啊,呼啊
归去也,归去也
故都故都奈若何
我是一只断线的风筝
……
北京城:垃圾堆上放风筝
诗题中“春城”意象源于韩翃《寒食》首句“春城无处不飞花”,一直以来,这首诗常被用以讽刺君王独宠专权的宦官和外戚的昏庸之举。由此可见,诗句背后隐含的典故无形中扩大了诗歌的表现范围,而卞之琳将自己的《春城》视为“讽刺诗”就是将其作为古典诗歌的成规加以使用。除此之外还有以下几处:“归去也,归去也”化用《诗经·邶风·式微》蕴含的国家衰败之意;“故都故都奈若何”则改写了项羽的《垓下歌》;“想起了当年事……”似乎只是一般引语,但由于卞之琳熟知戏词,此处可能截取了《四郎探母》中杨四郎在辽营英雄无用武之地的喟叹。在一系列化用和典故中卞之琳表现出“直接对兵临城下的故都(包括身在其中的自己)所作的冷嘲热讽”这种只有具备现代民族国家意识的人才会产生的情感。不仅如此,我们还能看到艾略特《荒原》的影子。首先,《春城》一定程度上借鉴了诗中酒馆对话那部分所表现出的戏剧性表演的抒情方式。作家在该段诗歌中将抒情主体隐藏,单从对话的戏剧情境中表现批判意味。《春城》第四段的表现方式则与“酒馆对话”如出一辙,作者不对交谈双方做出说明,也没有让抒情主体表达观点,仅凭对话传达出讽刺意图。另外,作者还像旁观者一般观察着其他的戏剧性场景:如“他也会‘想起了当年事……’”好似稚童唱着沧桑的戏词,苍凉感呼之欲出。另一个技巧则是对古典成规的运用,该手法在《荒原》中也大量出现,艾略特甚至为此加以注解。《春城》中出现的诸多短句正如《荒原》中“请快些,时间到了”“晚安”的不断循环,象征着卞之琳对艾略特传统观的实践。
从卞之琳的《无题》诗中同样能体现出他对古典诗歌成规的运用。学者们大多将这种以男女情爱作为主要内容并有所寄托的“无题诗”体式看作李商隐的首创⑦[6]。卞之琳的《无题》共五首,也有关于爱情的表达,这是对李商隐的无题诗最明显的借用。不过更重要的区别在于它们体式上的差异。卞之琳五首《无题》的格式皆为“每首八行,四行一段”;可正如张采田所说“此体只能施之七律,方可宛转动情”,⑧[7]从古至今李商隐《无题》中最为人称道的却还是六首七律诗。对比卞诗的“每首八行,四行一段”,它自然与近体律诗有相似之处,但实则两者并不相同。众所周知,律诗的每一联都需要承担固定功能,而且非常注重韵律和节奏上的起承转合,即使李商隐诗歌具有较强的跳跃性和隐晦性,我们仍然能较为清晰地看到其中的七律章法。而卞之琳《无题五》中“襟眼是有用的,因为是空的”和“世界是空的,因为是有用的”两段在语法上呈现出重复中变化的样式,并通过“簪花”“散步”等意象的转变在同样的逻辑结构中得出相似的意味。可以说第二段是在第一段基础上推衍出来的,其中的同构逻辑又凭借意象的变化凝聚诗意,这与律诗乃至所有古典诗歌的组织方式都有所不同。再如卞之琳的《无题三》。此处明显化用了李商隐“梦为远别啼难唤,书被催成墨未浓”一句。通过对比我们不难发现,李诗主题上所突出的“思远”与《无题三》着力表现的相见和分离确有相似之处。但细读后我们便会发现此诗布局上的巧思:第一段中“我”“你”“门荐”“渗墨纸”“尘土”“字泪”“踩”“掩”之间存在高度对应,是逻辑同构关系;第二段第一句接续上文,而“珊瑚”又理应是“海水洗尽人间烟火”后的结晶,所以第二句显然与后两句承接更为密切。全诗虽传递出惆怅情绪,但诗人并未直接陈说短暂相逢后又要分离的悲哀,而通过见面时“我”的慎重到想象对方的书信再到最后“月台送别”等一系列具体场景折射出一丝缠绵的哀伤,这与李商隐《无题》诗中的寄托和寓言手法有所不同。
二、诗歌中自由联想的结构方式
当深入到结构层面时,卞之琳的诗呈现出另外的特点,废名称之为“自由表现”和“观念跳得厉害”,⑨[8]这与卞之琳奉行的“注重暗示性”和“着重含蓄”⑩[9]艺术追求共同为其诗歌创作赋予类似于李商隐、姜白石诗词的形迹。造成此形迹的原因除了对古典诗歌成规的运用,还有就是废名所说的与古典诗相近的新风格。废名曾将这一特征与温庭筠的《菩萨蛮》相比较。这首词从开篇中静态的绣鸟联想到真实水鸟激起的波纹,再进一步推至池上的花,思绪呈现出跳跃性。下片四句的跳跃更加明显,废名说“他描写了好几样事情,读者读之而不觉”,(11)但看似不觉实则整首词中都暗含对应关系:“绣衫”句对应“翠翘金缕”,“烟草”句则与“水纹”句的“春池碧”契合。朦胧的烟草正是“池塘生春草”所致,而“青琐”句的“芳菲”恰是“池上”句的“海棠梨”,进一步触发“玉关”一句女子对心上人的思念。即便全篇没有逻辑连接词,表面看只是意象的堆放,其内在的逻辑结构却严丝合缝,使之看似跳跃却又让人读之不觉。由此可见,观念的跳跃并不随意,貌似混乱的表面下贯穿内在的情感和逻辑线索。
类似的对位结构在卞之琳诗中也有体现。例如《寂寞》。这首诗结构简单,但颇似温庭筠词中的意义对位模式。作者首先通过声音的相似性将蝈蝈与夜明表联系起来,夜明表像鸣叫的蝈蝈在枕边滴答作响,帮助孩子排遣苦闷。第二段再次提到蝈蝈,不仅字面上呼应第一段,而且鸣叫的“动”还与荒墓的“静”形成对照;诗的最后说“他死了三小时夜明表还不曾休止”,可见虽然表还在发声但人已归于沉寂,此时夜明表和死去的孩子之间同样存在对照,使夜明表与蝈蝈在“寂寞”的意义上再次产生联系。从语言上也能发现诗中鲜有表示逻辑关系及表达情绪的词汇,意义层次间都只做客观呈现而没有进行说明和抒情,体现出异于温庭筠的客观化特征。
另一种经常出现在诗歌中的跳跃结构线索是情感,但由于情感的急遽跳跃往往令读者难以捉摸,也就造成它们不易用释义的方法进行解读。因此,情感线索如若真的存在于诗歌中并发挥功能,对其解读也必定要立足文本中的形式功能。如卞之琳的《车站》。这首诗中有多个“梦”字以及与之相关的意象,但主题又是现实。在梦与非梦的意象之间出现钢丝床、小地震、火车的怔忡几个跳跃性强同时又是对心跳的喻指。从语义上看,被弹响的钢丝床多出现在辗转反侧或梦醒时分;“小地震”指的是惊心动魄的梦境;接着以火车的怔忡隐喻火车与铁轨的撞击和心率的共振,又象征火车将到来时主人公内心的激动,暗示“我”对火车到来已渴望许久,却唯恐如今的现实只是一场梦的心路历程。
三、跳跃及非演绎倾向的语言
此外,卞之琳的诗歌还呈现出一种并不常见的技巧,即语言上跳跃和非演绎倾向的特征。前文中通过自由联想构成的观念跳跃从语言上就能找到线索,进而使读者产生别样的审美效果。比如温庭筠“惊塞雁,起城乌,画屏金鹧鸪”一句,塞雁、城乌、鹧鸪虽都是鸟类意象,但却是不同的动物,而随着字面线索的跳跃,读者的观念和视野也随之变化。再看卞之琳的《候鸟问题》。这首诗的跳跃从白鸽铃到骆驼铃开始,再从骆驼到陀螺,它们共同营造的语境由“远了”和“挽”形成重合。接着通过“鸟”进行的隐喻则构成全诗的核心。被风筝羁绊的“纸鹰、纸燕、纸雄鸡”不仅与归雁形成对比,而且和后文的《候鸟问题》一书共同暗示“我”像风筝和陀螺一样不自由的尴尬处境。整首诗的语境彼此断裂又共同指向对“我”的隐喻,将“我”被封锁在城市中的困境淋漓尽致地表现出来。
由此可见,结构和语言的跳跃是两个密切相关的问题。叶维廉把它作为中国旧诗语言的重要特征与白话诗的说理性和演绎性相对比,将之命名为非演绎性表达,并进一步概括出:“极少或没有人称代词;极少或没有时态或表示时间变化的词;极少使用表示逻辑的连接性、分析性的词”。(12)[10]等特点。而我们在温李一派的创作中往往能看到这些要素:他们在诗词中使用最多的就是名词和实词,其次是动词,而很少使用表示逻辑关系、时态、心理状态以及突显感情色彩的名词,这就使句子间的转换鲜有情感上的说明。由此,温李诗歌注重自由表现、跳跃等结构要素实则都可以视为语言的特点。进一步分析卞之琳的诗歌也能发现这种特征。卞之琳的诗中也多有副词和虚词,但它们的使用一般是为了达到让句子通顺的目的,而在句与句、段与段之间的空白处这些需要逻辑线索的地方却往往省去连接词。例如《半岛》:
半岛是大陆的纤手
遥指海上的三神山
小楼已有了三面水
可看而不可饮的
一脉泉乃涌到庭心
人迹仍描到门前
昨夜里一点宝石
你望见的就是这里
用窗帘藏却大海吧
怕来客又遥望出帆
全诗没有表示状态或时态的副词,只在“昨夜里一点宝石/你望见的就是这里”中出现了人称和时间状语。那么与其说是强调时间,不如说是在突出暗夜与发光宝石的对比。所以此时的“昨夜”就代表了回忆和对过去的怅惘,像李商隐《无题》中的“昨夜星辰昨夜风”一样不单单发挥其表示时间的作用。而且诗中没有表明分析和逻辑性的关联词,比如作者并未说明“三神山”“三面水”和“一脉泉”之间的关系,还有最后两句也明显省略了表示因果的连接词等等。这种非演绎性语言给卞之琳的诗歌带来古典风韵的同时也加深了其中的晦涩之感。
四、客观性表达
艾略特认为维护传统离不开个性的牺牲,这是他对浪漫主义、表现主义等理论的反驳,并且在《玄学派诗人》《哈姆雷特》等文中进一步提出“客观对应物”“思想与感性的结合”等创作原则。比如“客观对应物”原则是指:“用一系列实物、场景,一连串事件来表现某种特定的情感,要做到最终形式必然是感觉经验的外部事实一旦出现,便能立刻唤醒那种情感。”(13)[11]而中国古代的咏物词中似乎也有这种创作倾向。例如姜夔《暗香疏影》中《暗香》一篇:“旧时月色,算几番照我,梅边吹笛。唤起玉人,不管清寒与攀摘。何逊而今渐老,都忘却春风词笔。但怪得竹外疏花,香冷入瑶席。江国,正寂寂。叹寄与路遥,夜雪初积。翠尊易泣,红萼无言耿相忆。长记曾携手处,千树压西湖寒碧。又片片、吹尽也,几时见得。”姜夔并没有直接抒情,而是将开篇的梅花作为激发思绪的关键线索,作者以“梅花”展开联想,不仅完成了回忆与现实的场景切换,还表现出追忆往昔的感慨。这就使“自我”消隐在这类咏物词的结构中,进而让以对物进行观察的主体视角结构全章的方式替代了既往主体情感占据中心地位的抒情方式。
卞之琳在诗歌创作中同样运用了类似的技巧。比如代表性的咏物诗《圆宝盒》。卞之琳在结构中将自我抒情主体隐藏,开篇点出“幻想”并将圆宝盒作为对想象力容器的象征,串联各种颜色结构全章。关于这一点卞之琳曾在《雕虫纪历》中依据“让时间作水吧,睡榻作舟/仰卧舱中随白云变幻/不知两岸桃花已远”这几句已经作废的诗做出了一些解释。他认为这两段具有相似性。对比来看,它们都存在视点变换,注释中的诗句在结尾处隐去“让时间作水,睡榻作舟”的主体,淡化人的视角;正文将圆宝盒作为观察视点同样隐藏了“人”,使圆宝盒成为融合不同时空和视角的色相的载体,呈现出客观化效果。再如收录于《鱼目集》中的《归》。诗开篇中“闻自己的足音”“自己圈子外的圈子外”都可看作是客观化表达,而作者也通过天文家、足音等客观对应物将抽象的情感外化为具体形象,同样带来了含蓄的审美效果。此外,这首诗中还有卞之琳对艾略特诗歌的化用和吸收。除了此前论者“只不过中国诗人写得更简练,更紧凑,而这是传统的绝句律诗多年熏陶的结果”(14)[12]这句对卞之琳化用艾略特《普鲁弗洛克的情歌》以道路比喻心理状态的评价,诗中的客观对应物同样是对艾略特诗学原则的实践。此外,卞之琳将《归》收入《雕虫纪历》时对它做出了一些改动,修改后的《归》似乎就像通俗的说理性表达一般,并且强调了“脱出轨道”,对“圈子之外”也不再提及:每句字数不再整齐,将“闻”改为“听见了”,第三句也变为“莫非在外层而且脱出了轨道?”[13]这或许出于作者对一些可能引发歧义的词的担忧,不过句中依旧保持着“在外层”的说法,可见作者客观的态度并未改变,整首诗的风格也没有较大出入。
结语
综上所述,卞之琳在1934-1937年间的创作中大量选取古典诗词的典故、意象入诗,而且还融合古典诗词的结构和语言特征,体现出他这一时期对传统的回归。同时,尽管卞之琳诗歌中存在许多古典诗词元素,但其诗学理论基础和审美视野是现代的,而且毫不掩饰对西方诗学技巧的运用,表达的也是现代人所具备的情感。就像他所说的那样:“由于对西方诗‘深一层’的认识……进一步了解旧诗、旧词对于新诗应具的继承价值,一般新诗写作有了他所谓‘惊人的发展……’”(15)因此卞之琳对中国古典诗歌传统的回望并非简单地用“旧材料”进行拼凑,所以没有造成林庚那样被嘲笑为“没有格律的古诗”的结果。他以现代人的眼光站在现代诗学的审美立场上去发现意象、典故等传统资源在现代语境中的适配性与合理性,这不仅使其创作在新与旧的碰撞中激发更多可能,而且也推动我国古代诗歌传统在“历史现存性”的开掘中焕发生机与活力。
注释:
①周伊慧.T.S.艾略特对卞之琳的影响[J].湖南医科大学学报(哲社版),2006(04):151.
②卞之琳.卞之琳译文集(上卷)[M].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0:5.
③卞之琳.雕虫纪历[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16.
④卞之琳.卞之琳集[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9:339.
⑤卞之琳.卞之琳译文集(中卷)[M].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0:277.
⑥解志熙.灵气雄心开新面——卞之琳诗论、小说与散文漫论[J].现代中文学刊,2011(1):78.
⑦刘学锴.李商隐传论[M].合肥:安徽大学出版社,2002:630-633.
⑧刘学锴.李商隐诗歌集解(增订重排本)[M].北京:中华书局,2004:1647.
⑨(11)废名、朱英诞.新诗讲稿[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16,23,332页.
⑩卞之琳.人与诗:忆旧说新(增订本)[M].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7年版第295,31页.
(12)叶维廉.中国诗学[M].上海: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2:246-252.
(13)王恩衷编译.艾略特诗学论集[M].北京: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89:13.
(14)王佐良.中国现代诗中的现代主义——一个回顾[M].文艺研究,1983(04):30.
(15)卞之琳.人与诗:忆旧说新(增订本)[M].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7年版第295,3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