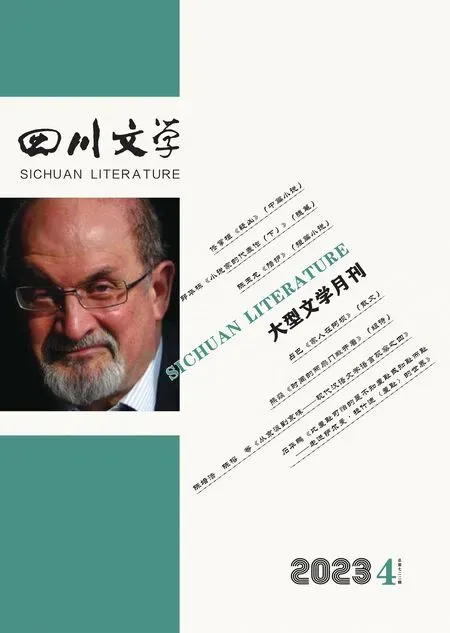从京派到京味
——现代汉语文学语言观察之四
2023-08-21陈培浩陈榕
□文/陈培浩 陈榕 等
导语:京派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有着独特创作个性和美学风格的文学流派,小说方面以废名、沈从文、凌叔华、萧乾、芦焚、林徽因、汪曾祺为代表。京派作家以从容宽厚的文化心态追求艺术的纯美与人性的健康纯正,作品充满东方古典式和谐圆融的情致。京派小说的独特魅力集中体现在语言上,京派文学语言因含蓄精致的古典气息、圆熟流转的声腔韵律、别具一格的现代品质,而携有高辨识度、高可诵性与高审美性的文学基因。从“京派”到“京味”的嬗变,更是证明“京”作为别具魅力的风格标识,在时光长河中薪火相传、变化出新。
摘录一:化古出新与文白之美
1.水桶歇下畦径,荷锄沿畦走,眼睛看一个一个的茄子。(废名《菱荡》,《废名小说》,浙江文艺出版社,2003年,第72页)
2.小林站着那个台阶,为一棵松荫所遮,回面认山门上石刻“鸡鸣寺”三字,刹时间,伽蓝之名,为他出脱空华,“花冠闲上午墙啼”,于是一个意境中的动静,大概是以山林为明镜,羽毛自见了。(废名《桥》,《废名小说》,浙江文艺出版社,2003年,第221页)
3.祠堂位置在山坳上,地点较高,向对河望去,但见千山黄草,起野火处有白烟如云。村落中乡下人为耕牛过冬预备的稻草,傍附树根堆积,无不如塔如坟。银杏白杨树成行高矗,大小叶片在微阳下翻飞,黄绿杂彩相间,如旗纛,如羽葆。又如有所招邀,有所期待。沿河橘子园尤呈奇观,绿叶浓翠,绵延小河两岸,缀系在枝头的果实,丹朱明黄,繁密如天上星子,远望但见一片光明幻异,不可形容。(沈从文《长河》,当代世界出版社,2019年,第19页)
4.两个女儿,长得跟她娘像一个模子托出来的。眼睛长得尤其像,白眼珠鸭蛋青,黑眼珠棋子黑,定神时如清水,闪动时像星星。浑身上下,头是头,脚是脚。头发滑滴滴的,衣服格挣挣的。(汪曾祺《受戒》,文汇出版社,2020年,第50页)
5.一日,天色薄暮,满天霞光,四野荒烟,前面横着一条茫茫大水,沙滩上留宿着鹄和雁。浅渚,芦苇,水面雾着轻霭,一江载满着霞彩,正浩荡东去,这人立近渡口。高声喊道:
“船家来呀!”
那船家缓缓抄着棹,唱的是——
大江的水
岸上的柳……
(师陀《一片土》,《海上文学百家文库:师陀卷》上海文艺出版社,2010年,第198页)
陈培浩:首先要澄清一个问题,有人在论京派语言时,喜用“古典化”,事实上京派的创造不在“古典化”,而在“化古典”。古典化乃是以古为典,以古为模本和规范,其规则是往古里走,这在根本上与现代文学的精神是格格不入的。化古典则不然,不妨以古为师的同时与古为新。古典不妨作为资源,但立场则在现代和当代。依我之见,古典化对于现代作家不是赞美,实在近于骂人,等于泥古不化。实在说,“化”是所有作家一辈子的大命题。不仅化古,化洋化欧化民间,食而不化,则为僵尸,一个道理。大家可留心摘录中,京派作家是如何“化”的。
陈榕:京派作家从辉煌灿烂的中国古典诗歌中汲取营养,其所求在于“化古典”,而非“古典化”。通过文言与白话、古典与现代的融汇,京派作家将古典语的“接穗”嫁接到现代汉语的“砧木”上,提供了对古典资源进行现代转化的绝佳范例。
文段一,“水桶歇下畦径,荷锄沿畦走”一句并非严格的对仗,前后句字数也并不相同,却使人联想起五言诗,盖因作家化用了古典文言的句法规则。印欧语系的句法形态讲究成分完整,主谓宾齐全。汉语作为非形态语言,其优势在于“不以某个动词为核心,而是用句读段散点展开”。(申小龙《汉语与中国文化》)“水桶歇下畦径,荷锄沿畦走”一句暗含的主语是“提桶”“荷锄”的人,施动者在句中隐身,营造主谓宾模糊的独特语感。本句与“苔痕上阶绿,草色入帘青”共享一套语法规范,是典型的诗歌韵律风格。第三句“眼睛看一个一个的茄子”却散发着浓郁的现代白话气息,“一个一个”的重复打破了传统诗歌句中重复的禁忌。三句并列的联动式结构摆脱了古典诗词的平行句式与僵化的形式规定,达到“化古典”而非“古典化”的和谐效果。
文段二,小林由“鸡鸣寺”的“鸡鸣”二字望文生“形”,乃至耳听——耳边响起鸡鸣之声;目视——山林中浮现羽毛之状。由实入虚,由真入幻,思维跳跃,语言灵动。作家引用五代词“花冠闲上午墙啼”(孙光宪《浣溪沙·轻打银筝坠燕泥》),原作借鸡鸣抒发独守空闺的寂寞之感,废名取“静中之动”,走出封闭仄狭的闺房,将鸡鸣声置于空旷的山林,诠释古典诗词原有意境的同时建构起全新的想象。废名曾言“用写绝句的方法写小说”(《废名小说选·序》),他将绝句的炼字、写意等手法移植到小说中,配合禅宗的思维方式,在冥想中突破物象界限、语言束缚,带来小说语言的诗化——句与句之间跳跃、生长,在跳脱、断裂、含混、空白处制造语言的弹性张力。
文段三是对古典诗词技法的现代化改造。“千山黄草”“白眼如云”“成行高矗”等四字词语的大量使用增添了语言的古典韵致,“如旗纛,如羽葆”“有所招邀,有所期待”对偶句整齐匀整,近似魏晋南北朝时期的骈文。“沿河橘子园尤呈奇观,绿叶浓翠,绵延小河两岸,缀系在枝头的果实,丹朱明黄,繁密如天上星子”前三句字数分别为九、四、六,后三句为八、四、七,各自采用“长—短—长”的语流节奏,且前后两部分字数总和同为十九。前半部分的尾字“岸”为仄声,后半部分尾字“子”为轻声,符合古典诗词“仄起平收”的语音规律。前三句与后三句构成“弹性对偶句”,句子长短相济,内部整齐而富于变化。作家示范了如何不使用文言字词,而将古典诗词的血液融入现代白话语言。长短句的巧妙搭配、奇偶句式的交叉变换显示,作家对古典诗词技法的使用已然臻于化境。
文段四,首句“长得跟他娘像一个模子托出来的”营造口语化的语境,“白眼珠鸭蛋青,黑眼珠棋子黑”省略谓语,将两对色彩相近的意象并置,于空白处传神;“定神时如清水,闪动时像星星。”是充满古典韵味的文人化表达;“头是头,脚是脚”则有一种语意重复的民歌语调;“格挣挣”则是作家的家乡方言。作家融汇多种语言资源的优长,方言口语的声腔韵调与古典汉语的形神韵致在句子中参差错落。小说语言既有白话口语的松弛,又富古典文言的精致,尽显“文白”之美。
文段五的景物描写从古典诗词意境中脱化而来,“薄暮”“霞光”“荒烟”等意象都能在古典诗词中找到影子。景物的刻画上采用了白描手法,所取只在其意境和神韵,小说语言贯彻了东方美学和谐、节制的审美原则,宛如中国古典水墨丹青,于留白处营造出苍茫辽阔的境界。京派作家将古典诗词、水墨画等中国传统元素引入现代小说,将母语文化的唯美与诗意推向极致。
五四以来,文学语言经历着“欧化”的语言危机,很多新作家对传统文言弃之如敝屣,争相通过繁密的修饰语、长句与欧化语接轨,京派作家则以渗透着古味、平淡雅洁的语言风格向含蓄蕴藉的中国美学传统致敬。京派文学的价值在于帮助语言摆脱欧化语的束缚,重建文学语言的“汉语性”。现代汉语在现代语境中生成,是多种语言资源的杂糅,古典文言、欧化语言、民间口语皆为其有机组成部分。京派作家深入泛黄的语言褶皱,将携有古典美学基因与民族文化符码的语言移植到现代白话语言的土壤,并适当施以欧化语言的肥料,借此创造出了具有“汉语性”的文学语言。
帅沁彤:京派文学的“纯文学”追求表现在对母语“新传统”的构建上,对传统的语言资源的激活进行了有意识的探索,路径不尽相同。沈从文《长河》、汪曾祺《受戒》两个文段,更多采用白话语言的语法,在句式上穿插古典散文。首先是词,文段二中“但见”“有所”等双音节词是古典汉语的特征;其次是句,“如旗纛,如羽葆。又如有所招邀,有所期待。”“眼睛长得尤其像,白眼珠鸭蛋青,黑眼珠棋子黑,定神时如清水,闪动时像星星”,字数相近,前后对仗。文段五的句式,与古典散文更为相近,对比《醉翁亭记》,文段中去掉“也”“乎”等字,词语之义更偏白话,句式也更显灵活。对比张承志《北方的河》“他看见在那巨大的峡谷之底,一条微微闪着白亮的浩浩荡荡的大河正从天尽头蜿蜒而来。”又多了古典散文的凝练和节制。“一日,天色薄暮,满天霞光,四野荒烟,前面横着一条茫茫大水,沙滩上留宿着鹄和雁”就比“天色薄暮,漫天霞光,四野荒烟,茫茫大水,沙滩鹄雁”更显悠长,最后两个长句不仅将句式调节得更丰富,且“横”“留宿”等细节在古典的意境中增添了现代的生命力。可见折叠与舒展的艺术,长短搭配,音律和谐。好似插花,花枝一般高低,略显呆板,高低相间,留白恰当,便生机勃勃,美感油然而生。总的来说,京派文人对于传统语言资源的运用,一是身形的“干练”——语言的简洁、凝练;二是善用词的多义性,来营造多维意境感;三是固化的“语码”在新的语境压力下变形,或在古典意境中加入现代词语,从而激发出新的力量;四是节奏韵律,利用声音的节奏进行句式的调节。这几点往往同时进行,或在古典散文的句式中调配白话之义,或在白话语法中向传统思想致敬。
摘录二:节奏与声情
1.多少年了,三合祥是永远那么官样大气:金匾黑字,绿装修,黑柜蓝布围子,大杌凳包着蓝呢子套,茶几上永远放着鲜花。多少年了,三合祥除了在灯节才挂上四只宫灯,垂着大红穗子,没有任何不合规矩的胡闹八光。多少年了,三合祥没打过价钱,抹过零儿,或是贴张广告,或者减价半月;三合祥卖的是字号。多少年了,柜上没有吸烟卷的,没有大声说话的;有点响声只是老掌柜的咕噜水烟与咳嗽。(老舍《老字号》,《老舍小说全集:第10卷》舒济、舒乙编。长江文艺出版社,1993年,第328页)
2.体面的,要强的,好梦想的,利己的,个人的,健壮的,伟大的,祥子,不知陪着人家送了多少回殡;不知道何时何地会埋起他自己来,埋起这堕落的,自私的,不幸的,社会病胎里的产儿,个人主义的末路鬼!(老舍《骆驼祥子》,四川人民出版社,2017年,第243-244页)
3.芦花才吐新穗。紫灰色的芦穗,发着银光,软软的,滑溜溜的,像一串丝线。有的地方结了蒲棒,通红的,像一枝一枝小蜡烛。青浮萍,紫浮萍。长脚蚊子,水蜘蛛。野菱角开着四瓣的小白花。惊起一只青桩(一种水鸟),擦着芦穗,扑鲁鲁鲁飞远了……(汪曾祺《受戒》文汇出版社,2020年,第59页)
4.打鱼的有几种。
一种用两只三桅大船,乘着大西北风,张了满帆,在大湖的激浪中并排前进,船行如飞,两船之间挂了极大的拖网,一网上来,能打上千斤鱼。而且都是大鱼。一条大铜头鱼(这种鱼头部尖锐,颜色如新擦的黄铜,肉细味美,有的地方叫做黄段),一条大青鱼,往往长达七八尺。较小的,也都在五斤以上。起网的时候,如果觉得分量太沉,会把鱼放掉一些,否则有把船拽翻了的危险。这种豪迈壮观的打鱼,只能在严寒的冬天进行,一年只能打几次,渔船的船主都是个小财主,虽然他们也随船下湖,驾船拉网,勇敢麻利处不比雇来的水性极好的伙计差到哪里去。
……
还有一种打鱼的:两个人,都穿了牛皮缝制的连鞋子、裤子带上衣的罩衣,颜色黄白黄白的,站在齐腰的水里。一个张着一面八尺来宽的兜网;另一个按着一个下宽上窄的梯形的竹架,从一个距离之外,对面走来,一边一步一步地走,一边把竹架在水底一戳一戳地戳着,把鱼赶进网里。……(汪曾祺《汪曾祺全集》第二卷,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8年,第163页)
陈培浩:所谓节奏,就是时间的调节,就是急缓快慢的有效安排。节奏几乎是所有艺术中的重要问题,尤其是对于能够呈现时间性的艺术形式。对于文学、电影来说,节奏极其重要,就是对雕塑等时间性不突出的艺术来说,也不能说完全不存在节奏问题,只能说节奏在这种形式中是相对隐匿的。事实上,不仅艺术有节奏,生命也有节奏。我们看一个人走路,有人踩着散文的节奏,有人则踩着韵文的节奏,有人则根本没有节奏。一个人若踏在自己内心的节奏上,或稳稳或款款,就自在从容,就怡然自得。一个人走路若失去节奏,必是慌了阵脚,方寸大乱。叙事作品,若一直是高潮,等于没有高潮,读者反而疲劳。叙事高潮其实是通过节奏对照出来的。有经验的作者必懂得铺垫,懂得张弛有度,这是整体结构上的节奏。我们这里谈的节奏其实是语言上的节奏,句子内部及句群中的节奏。摘录句段,大家好生揣摩。
陈榕:节奏是音响运动中有规律地交替的长短和强弱现象。古典诗词借助规范的字数、规律的停顿、声调的平仄以及交替出现的韵脚营造诗的节奏。文学的节奏不仅存在于诗词中,也存在于小说中。小说语言的节奏表现在长短句的剪裁、声腔韵调的安排等。京派作家深谙听觉与文字艺术的结合之道,追求声音的美感效果。
所谓“声情”,具有声中含情,依情定声之意,老舍善于根据情感表达需要选取恰切的声音节奏。他曾言,“短句足以表现迅速的动作,长句则善表现缠绵的情调。”创作中,裁剪得当的长句与短句对情感表达具有突出效果。文段一采用排比句形式,从外观装饰之精致、生意礼仪之规矩、店内氛围之和谐诸方面凸显“老字号”三合祥的传统之悠久。四个“多少年了”连缀使用不仅在形式上带来整齐匀称的美感,而且在声音上带来回环往复的效果。由并列组合结构形成长句,增强了语言表达气势,提升了情感浓度,且富于节段律动之美。文段二则采用形容词性的并列组合结构,中心词“祥子”前设七个并列的形容词,七个词独立成句,一字一音,一句一顿,形成强烈的节奏感。“不知……不知……”的长句舒缓了语气,随后又出现形容词构成的短句。“堕落的,自私的,不幸的”具有贬义色彩,与此前“体面的,要强的,好梦想的”等具褒义色彩的形容词形成对比。前后构成对称式并列组合结构,突出祥子堕落前后的巨大反差。老舍曾言“音乐和诗词是时间的艺术……音乐是完全以音的调和与时间的间隔为主。诗词是以文字的平仄长短来调配”(《文学概论讲义》)。老舍将音乐时间间隔的艺术挪用到小说中,以时间间隔之短长铸就文字抑扬顿挫的效果。文段一句与句之间停顿间隔长,节奏舒缓,宛如一曲动人的抒情曲;文段二停顿间隔短,节奏急促,像戏剧高潮的变奏曲。停顿频繁的短句传达捶胸顿足、愤懑不平的情感。语音形式的选择透露出作家情感倾向的差异。可见,节奏给作品带来的深层意蕴价值超过语言形式本身。
文段三使用“软软”“滑溜溜”“一枝一枝”等叠音词以及拟声词“扑鲁鲁鲁”增强语音的节奏与韵律。对芦穗的描写采用了定语后置,将长句短句化。并列成分的安排也大有讲究,“青浮萍,紫浮萍。长脚蚊子,水蜘蛛。”一句,若为求形式的规整改成“长脚蚊”,则四短句皆为上扬的声调,缺乏重音;若改成“青浮萍,紫浮萍。水蜘蛛,长脚蚊子。”“平平平轻”的音韵一平到底,相比之下,原句“平平轻平”的音韵有所起伏,读来有种民间歌谣的节奏韵致。可见,在“单音词+双音词”的结构中穿插两个音步的双音词是作家的精心营构,使节奏活泛,富于变化。
钱穆先生曾言“中国文学重情,故能和合进音乐,而融会为一体。”[《略论中国音乐(一)》]京派语言充分发挥汉字作为有声调的语言的优势,语言的高低起伏、轻重缓急、长短变化不仅带来听觉上的美感效果,而且发挥了中国文学声情融会的特性。
欧阳师哲:从节奏与声律的角度观察语言,能很好地体会作者依托语言所试图传递的情感态度,甚至于更深的文化心理。《骆驼祥子》之中,从开头对“一身清凉劲儿”祥子的偏爱、同情,慢慢转向厌恶,并最终在结尾处以十分短快的语句斥责他堕落成为“社会病态的产儿、个人主义的末路鬼”这样的奥勃洛摩夫形象,我们显然感受到老舍对祥子这个人物的感情多变。这样多变的情感之下,蕴含的并非老舍自我矛盾、难以自洽的写作逻辑,反而是老舍的一种继承与尝试。即通过在结尾处以短句叠加的手段,对“个人主义”进行颇富气势的斥责,从而将祥子从新民主主义革命论中剥离,放入了五四以来以鲁迅为中心“改造国民性”的元叙事话语,在文化角度更为深入广阔地批判了国民的劣根性。
当然,语言的节奏除了能使情感与文化观念生动化,也往往能增强语言的画面具象和视觉冲突。除京派语言具有鲜明的节奏感,海派语言,尤其是二十世纪30年代新感觉派小说也富于鲜明的节奏气质。穆时英在《上海的狐步舞》中曾描述舞厅那“当中那片光滑的地板上,飘动的裙子,飘动的袍角,精致的鞋跟,鞋跟,鞋跟,鞋跟,鞋跟。”这一语句并非简单的修辞反复,除有力加强了语言的声律感,我们也在作者这种非线性时间的回旋叙述模式中,对舞厅的场景有了更逼真的感受。时间似乎缺位了,取而代之的都是空间的变化。这种描述既有类似于“摇镜头”的电影拍摄的一面,同时也符合老上海舞厅那种特殊的地板构造:特质弹簧的应用。在弹簧之上跳国标舞,恰有轻盈旋转的跃动之感,“鞋跟,鞋跟”的反复也反映了小说叙事模式与十里洋场生活范式之间的某种内在对称。
许再佳:京派小说的语言节奏与声情是一个很有意味的问题。“节奏”作为一种语言形式的分析维度,它描述的实际上是语言的运动轨迹。汪曾祺的笔记体小说《故乡人·打鱼的》,正是通过语言节奏的调整和编排营造出一种“静穆”“澄明”之美。
汪曾祺笔下,西北风是“大西北风”,帆是“满帆”,这些词语的重音都在定语。定语作为修饰成分,体现了情感倾向。开头整体上语调昂扬(从重音的语调看整体的语调),例如“船行如飞”,“飞”的语调就是高昂的,尤其与“行”搭配,一种流畅的速度感呼之欲出。在语段内部,其语音总体保持一致,没有太大波动。叙述节奏的背后是叙述者的声音和心境,一种平稳、平静的情绪流。尽管这两组有“对比”,但语义重点却不尽相同。起始语段弱化了打鱼过程,叙述重点在描述打上来的鱼,“大铜头鱼”“大青鱼”颜色鲜艳,数量颇多,有时为了避免翻船还得放掉一些。结束语段重点却在描写打鱼过程,语调大多比较低沉,“一步一步地走”“一戳一戳地戳”,语义和音节的重复,创造了拖沓、低沉、舒缓的氛围。语言节奏具有丰富的审美功能。卢卡契曾说:“第一,节奏的职能是使相互结合的内容上异质的东西同质化。第二,节奏的意义在于选择重要的东西而排除次要的细节。第三,节奏能为整个具体作品创造一个统一的审美氛围。”(卢卡契:《审美特性》)汪曾祺小说正是通过微观的节奏调节,将富人的富足、轻快、向上与穷人的匮乏、木讷和呆滞对照,差异化的本事化合为一个有机整体,从而呈现出“静穆”“澄明”的美学特征。
摘录三:“京味儿”语言
1.“告诉你,祥子,搁在兜儿里,一个子永远是一个子!放出去呢,钱就会下钱!没错儿,咱们的眼睛是干什么的?瞧准了再放手钱,不能放秃尾巴鹰。当巡警的到时候不给利,或是不归本,找他的巡官去!一句话,他的差事得搁下,敢!打听明白他们放饷的日子,堵窝掏;不还钱,新新!将一比十,放给谁,咱都得有个老底;好,放出去,海里摸锅,那还行吗?你听我的,准保没错!”[老舍《骆驼祥子》(八),《宇宙风》第32期,1937年1月1日]
2.9 号的门脸儿也不漂亮,甭说石狮子,连块上马石也没有。院儿呢,倒是咱们京华宝地的“自豪”——地道的四合院儿。四合院儿您见过吗?据一位建筑学家考证:天坛,是拟天的;悉尼歌剧院,是拟海的;“科威特”之塔,是拟月的;芝加哥西尔斯大楼,是拟山的。四合院儿呢?据说从布局上模拟了人们牵儿携女的家庭序列。嘿,这解释多有人情味儿,叫我们这些“四合院儿”的草民们顿觉欣欣然。(陈建功《辘轳把胡同9号》,《鬈毛》,北京燕山出版社,1997年,第13页)
3.要提起这“会鸟儿”来么,敢情那些个退了休,又迷上养鸟儿的老头儿们,还是分帮论伙的呢。比方说这北半城吧:会“百灵”的,常去青年湖;会“红子”的,爱上东直门里头老俄国坟地;要是会“画眉”的呢,奔这地坛根儿来的就多了。可为什么必得分个“楚河汉界”呢?皆因是怕“串音儿”,更怕“脏口”。听说,老辈子人养百灵,只它学上一嗓子喊“老家贼”——就是如今常说的“麻雀”——口脏了!就仿佛在街面上为人处事,张嘴就带脏字死似的,那品格儿,登时就得矮下一截子去。(韩少华《点红颏儿》,《遛弯儿》,北京燕山出版社,1997年,第1-2页)
4.三贝子、二额附、索中堂的少爷、袁宝宫的嫡孙。年纪相仿,门户相当。你夸我家的厨子好,我称你府上的裁缝强。斗鸡走狗,听戏看花。还有比他们老子胜一筹的,是学会些摩登派的新奇玩意儿。溜冰、跳舞、在王府井大街卖呆看女人,上“来今雨轩”饮茶泡招待。[邓友梅《那五》,《邓友梅小说精选(上)》,太白文艺出版社,2001年,第2页]
5.“你说你是什么鸟变的?人家有酒瘾棋瘾大烟瘾,什么瘾都说得过去,没听说像你这样有‘砍’瘾的,往哪儿一坐就屁股发沉眼儿发光,抽水马桶似的一拉就哗哗喷水,也不管认识不认识识听过没听过,早知道有这特长,中苏谈判请你去得了。”(王朔《顽主》江苏文艺出版社,2005年,第5页)
6.“……您日理万机千辛万苦积重难返积劳成疾积习成癖肩挑重担腾云驾雾天马行空扶危济贫匡扶正义去恶除邪祛风湿祛虚寒壮阳补肾补脑补肝调胃解痛镇咳通大便,百忙却还亲身亲自亲临莅临降临光临视察观察纠察检查巡察探察侦查查访访问询问慰问我们胡同,这是对我们胡同的巨大关怀巨大鼓舞巨大鞭策巨大安慰巨大信任巨大体贴巨大荣光巨大抬举。我们这些小民昌民黎民贱民儿子孙子小草小狗小猫群氓愚众大众百姓感到十分幸福十分激动十分不安十分惭愧十分快活十分雀跃十分受宠若惊十分感恩不尽十分热泪盈眶十分心潮澎湃十分不知道说什么好……”[王朔《千万别把我当人》,云南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150页]
陈培浩:京派和京味是两个不同的概念。京派是文学流派概念,京味则是审美风格概念。一般来说,一群作家必得有统一的艺术主张或追求,有几个代表性作家方可称派。这方面京派当然是不缺的。某种意义上,京味儿恰是京派的艺术结果。可是,京味儿又超越了京派,京味儿的艺术特别是语言并不能被京派代表作家所垄断。在艺术特别是语言上讨论“京味儿”,实质是讨论区域性的文化资源如何转化为文学语言的创造。人们会问,既有京味儿,那么海味儿、川味儿、闽味儿、粤味儿、桂味儿又是什么样的?可见,并非所有的区域文化都已在语言层面上产生文学结晶。由此我们想问:京味儿的语言给我们的启示何在?
陈榕:京味小说以纯熟的京白描摹北京的风土习俗与人情世态,是有着地域风味的文学艺术。“京派”并不等于“京味”,但北京宽厚、雄浑、舒展的地域文化造就了京派语言独特的韵味,京味一定程度上已然内化为京派的文化基因。这种隐性的基因依托北京地域文化,在京派没落之后仍然得到传承。追踪“京派”到“京味”的嬗变轨迹,可见语言的传承与变异。
“京味”最直接的来源是北京的白话口语。老舍从北京白话口语中挖掘语言资源,将朴实无华的北京土语白话调动得鲜活自然、生动悦耳。文段一,高妈教给祥子放印子钱的方法,人物语言用通俗浅近的北京话写就,具有浓厚的京味。北京话多轻音,“里”“呢”“儿”“的”等一系列轻声词尾轻巧爽利,搭配重音的使用,形成有规律的间隔轻化。语流圆熟流转,曲折跃动。声调的高低轻重,快慢的协调配合,辅以“放秃尾巴鹰”“堵窝掏”“海里摸锅”等北京俗语,形成北京话独有的声腔韵调。经此描写,热心、精明、强悍的人物性格跃然纸上。
新时期,在文学启蒙思潮向寻根思潮转化之际,北京强大的地域文化魅力得到重新挖掘。陈建功、邓友梅、韩少华等第二代京味小说家延续了老舍京味语言的行腔韵调以及化俗为雅、精致圆熟的风格特征。他们将北京的民俗文化揉进小说,小说在地理、市井风情、人文、语言等诸多方面都显示出浓重的京味色彩。文段二、三、四的叙述语言中存在诸多京味语言的风格标识,主要体现在儿化音与人称代词的使用上。词尾使用儿化音是北京话语言的一大特点,文段二“门脸儿”“院儿”“四合院儿”“人情味儿”儿化音和和软软,传达亲切可爱的情感。文段三,轻音“儿”“么”“呢”“吧”搭配重音“鸟”“伙”“头”,调值先升后降,语气由强到弱,具有跌宕起伏的节奏美。儿化音的频繁出现造成声腔上的圆润轻巧,语调节奏的悠游舒缓,充分展现了北京人闲散、精致的生活哲学。此外,北京方言中常出现第二人称“您”与第一人称“咱们”,人称代词的使用模拟出“说书人”的语调,营造“我说你听”的语境,显得亲切热闹。“甭说”“敢情”等惯用字眼及自由散漫的语气、自问自答的语境共同形成京味语言独特的风格标识。京味文学语言不仅具有通俗性与生动性,而且常在口语中夹杂文言语词,形成独特的风格韵味。“草民”“顿觉欣欣然”“登时”都是具有“古味”的语言表达。文段四,邓友梅从古典词赋中汲取营养,化用汉赋的“排偶式铺陈”,语段中出现八个句式结构一致,字数弹性变化的对偶句,规整而又富于变化。长短相间的句子形成排偶,音调铿锵,富于节奏美。文言词汇、句法的使用显示出北京方言古老、高雅的文化身份。
二十世纪90年代,随着文化景观的变更,第三代京味小说应运而生。由于老北京的胡同、四合院被中央的机关、企业单位的大院取代,语言的京味也发生改变。不同于传统京味小说化俗为雅的审美取向,王朔化雅为俗,甚至以俗讽雅。文段五,少妇不满丈夫的整日乱侃,对扮演其丈夫的马青破口大骂,言语间取“侃”的谐音“砍”,仅此一字便起到化雅为俗的效果。中苏谈判是严肃的政治事件,将其降格为抽水马桶的流水声,构成对知识分子话语的嘲讽、对宏大话语的颠覆与消解。文段六是对流行的颂歌体的戏仿、解构与嘲讽。元豹妈代表坛子胡同向恩人大胖子敬献颂词,文段援引了赞颂体的基本架构,如“您日理万机……百忙却还亲身……这是对我们的……大众百姓感到……”,但无关词语置于其间,带来语无伦次的荒诞效果。比如,将“去恶除邪”这一严肃的政治话语与“祛风湿祛虚寒壮阳补肾补脑补肝调胃解痛镇咳通大便”这类医学术语、生活俗语并置,打破严肃的语言与卑俗的语言的壁垒,且暗示了颂歌体的语言构成方式,即以近音、同语素组词的方式进行繁殖,最终产出言之无物、冠冕堂皇的语言废料。此外,形态上,词藻堆叠重复、语言华丽铺陈构成对古代汉赋传统的戏拟。以王朔为代表的第三代京味小说家整体呈现出作家消解宏大话语、背离传统的先锋姿态。戏谑、轻浮、狂欢化的语言与典雅稳重的传统京味语言形成较大悖反。这与八九十年代知识分子非道德、非理想的精神危机息息相关。
从“京派”到“京味”乃至“新京味”的嬗变轨迹表明,所谓京味,是随时代而变的游动的气味因子,而非陈旧凝定的存在。“京”作为一种独具魅力的风格标识,已然实现由地域文化资源向独特审美风格的创造性转化。
许再佳:北京人说话爱在词尾用儿化韵,小小的“儿”内有乾坤,成为京味小说活泛起来的重要语言媒介。词根后缀以“儿”并不仅仅是简单的构词法,它不仅使北京话读起来朗朗上口、悦耳动听,也传达出丰富的情感色彩。除了《骆驼祥子》,老舍其他作品也大量使用儿化词。“两杯水酒,一碟炒蚕豆,然后羊肉酸菜热汤儿面,有味儿没味儿,吃个热乎劲儿。”(老舍《正红旗下》)福海二哥这一连串的“热汤儿”“味儿”“热乎劲儿”,亲切热情、和和软软,即使吃着没味儿,也让人觉得心里热乎乎的,喝着水酒就着炒蚕豆吃个面,也让北京人说出体恤热闹的感情来。叶广芩笔下的人物虽然都操着一口“官话”,但儿化语的使用是没有地位阶级差异的,如“咱这位大姐马上是要出门子的人了,还使小性儿,就这样到了婆家,只有吃亏受气的份儿。”(叶广芩《谁翻乐府凄凉曲》)金家兄弟对即将出阁的大姐的这段评价,“使小性儿”显出了他们对大姐脾气性格的不满却因着亲情的参与使读者觉得他们并不厌恶。相反,倒是大姐一副小女儿的娇憨之态跃然纸上;“份儿”这一说法已广泛流传得到认可并普遍使用,用在这里则表现出了弟弟们对大姐前途的担忧、叹息与无奈。
陈银清:何谓“京味”?孔庆东认为“京味”有两层含义:“一是题材的京味,即传神地描绘北京地区的文化风俗。二是语言的京味,即使用纯正地道的北京口语”。(孔庆东《北京文学的贵族气》)“京味儿”语言与“京派”作家作品的语言有所区别,使用“京味儿”语言的作品不局限于“京派”作品之中。“京味儿”语言给人一种光滑感与响亮感,有明快的节奏,鲁迅就曾以“响亮的京腔”与“绵软的苏白”对举。同时,文学作品中的“京味儿”语言也是一种方言化的文学语言,具有地缘文化的特点,承载着的是一种文化认同,表现的是一种文化心理。林海音的《城南旧事》里充满了“京味”语言,如“这时大门里疯子的妈妈出来了,皱着眉头怪着急地说:‘秀贞,可别把人家小姑娘吓着呀!’”(林海音《城南旧事·惠安馆》);“三个人?还有一个是谁?”“您猜。”“左不是你爸爸!”(《城南旧事·兰姨娘》);“我的头发又黄又短,很难梳,每天早上总是跳脚催着宋妈,她就要骂我:‘催惯了,赶明儿要上花轿也这么催,多寒碜!’”(《城南旧事·驴打滚儿》)林海音在《城南旧事》中运用了大量通俗易懂的北京口语词以及儿化词,其中的“怪着急”“左不是”“赶明儿”都是典型的北京方言词汇,让语言有了浓浓的“京味儿”。“京味儿”语言的背后,是浓郁的地域乡情,是明丽的风俗与风景,是作者儿时生活的美好记忆。通过“京味儿”语言,我们能够抵达充满“京味儿”的北平,抵达作者的童年记忆。当代表着京味的胡同与四合院慢慢消失,作家自觉使用富有“京味儿”的语言,既是对自我身份的文化认同,也是不断丰富现代汉语资源的努力。
摘录四:京派语言的现代性
1.城垛子,一直排;立刻可以伸起来,故意缩着那么矮,而又使劲的白,是衙门的墙;簇簇的瓦,成了乌云,黑不了青天……(废名《桃园》,《废名小说》,浙江文艺出版社,2003年,第64页)
2.一个远了淡了的影子,清馨静穆的夜空里,一声鹅黄色的叹息呵。(萧乾《梦之谷》,广东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117页)
3.老太太颤巍巍地喘息着,继续维持着她的寿命。杂乱模糊的回忆在脑子里浮沉。兰兰七岁的那年……送阿旭到上海医病的那年真热……生四宝的时候在湖南,于是生育,病痛,兵乱,行旅,婚娶,没秩序,没规则地纷纷在她记忆下掀动。
“我给老太太拜寿,您给回一声吧。”
这又是谁的声音?这样大!老太太睁开打瞌睡的眼,看一个浓妆的妇人对她鞠躬问好。刘太太——谁又是刘太太,真是的!今天客人太多了,好吃劲。老太太扶着赵妈站起来还礼。(林徽因《九十九度中》,青岛出版社,2020年,第45页)
4.太阳晒着港口,把盐味敷到坞边杨树叶片上。海是绿的,腥的。
一只不知名大果子,有头颅那样大,正在腐烂。
贝壳在沙里逐渐变成石灰。
浪花的白沫上飞着一只鸟,仅仅一只,太阳落下去了。
黄昏的光映在多少人额头上,在他们的额头上涂了一半金。
多少人逼向三角洲的尖端。又转身,分散。
人看远处如烟。
自在烟里,看帆篷远去。
来了一船瓜,一船颜色和欲望。
一船是石头,比赛着棱角。也许——
一船鸟,一船百合花。
深巷卖杏花。骆驼。
骆驼的铃声在柳烟中摇。鸭子叫,一只通红的蜻蜓。
惨绿的雨前的磷火。
一城灯!
(汪曾祺《复仇》,《受戒》,文汇出版社,2020年,第7页)
陈培浩:开篇我们就说到京派在文学上应是“化古典”而不是“古典化”。前面是在具体的语言使用上讨论,这里我们还需从思想意识上再深挖,则不能不谈到现代性。所谓一时代有一时代的文学,我们学习古典,却并非要完全回到古典那里去。《红楼梦》再好,却已经无法从我们时代土壤中长出来。今天的写作,必须有对自身问题、资源和可能的洞察,并在此基础上选择、发展和锤炼艺术形式。现代性、当代性说一千道一万,实质就是基于时代迫切性的艺术意识。须知,语言问题还包含着复杂的文化和审美信息。不是说文白结合就有现代性,现代性需在现代的文化和价值立场上弥散出来。
陈榕:京派以坚持传统为特色,似乎与现代主义相距甚远,实际上,京派作家大多具有开阔的眼光与丰富的外国文学学养。京派小说在叙述技巧、叙事视角、叙事结构等层面体现出迥异于传统小说的现代性。
文段三中叙述视角的聚焦、融汇与转化充满着现代性意味。语段开头是老太太的回忆,“兰兰七岁的那年……送阿旭到上海医病的那年真热……生四宝的时候在湖南,于是生育,病痛,兵乱,行旅,婚娶,没秩序”句子主干缺失,不符合语法规范,宛如一个个细小的“线头”被捻起,形象地展露出记忆碎片化的特点。沉浸在回忆中的老太被忽然传来的画外音所惊。“这又是谁的声音?这样大!”此为老太太的心理活动,随后是叙述者的声音,“老太太睁开瞌睡的眼,看一个浓妆的妇人对她鞠躬问好”;“刘太太——谁又是刘太太……”又复归老太太的心理语言;文段最后以叙述者声音收束“老太太扶着赵妈站起来还礼”。人物意识在心理与现实穿梭,叙述语言与人物内心语言彼此缠结,且不加标点符号。这种叙述方式为“自由间接引语”,打破叙述语与转述语的壁垒,直陈人物心理活动。中国古典小说所用的中文不带标点符号,为区分叙述语和转述语只能频繁使用“他说”“她想”等引导语,此类直接引语暗含着叙述者对行为主体的控制与距离,自由直接引语则将叙述者的声音降至最低,突出行为主体的心理感觉。叙述技巧的选择体现着传统小说与现代小说的差异,前者采用“说书人”语调与全知全能的视角讲述故事,后者关注现实的复杂构成,挖掘人物隐秘的内心景观。
为进一步还原人物的内宇宙,京派作家借鉴了西方现代小说的心理描写方法,并对其进行了东方化改造。文段一,“伸起来”“缩着”将衙门的墙拟人化,化静为动,形象地写出了城垛子的高低起伏的景致。随后采取“先感后思”的写法,先看到“白”再意识到那是“衙门的墙”,突出思绪的迟滞。由瓦的黑联想到乌云,乌云这一意象又引出青天,作家以意象联结思绪的流动,与西方“意识流”语体异曲同工。然而,不似西方意识流的非逻辑,废名的小说语言虽充满跳跃和省略,但仍保有意识的完整性。这种“东方意识流”更接近中国古典诗词,高度写意,只为凸显事物独有的神韵及主体的感受和意趣。
类似的,文段四描写为父报仇的青年的心理活动。由太阳、盐味联想到海,海的绿引出果子,果子的圆关联头颅,头颅的腐烂引出贝壳的腐蚀……相关的意象相互繁殖,构成恍惚迷离的意识流。随后,“瓜、船、鸟、百合花、杏花”等意象陆续涌现,意象的跨度进一步增大,好似主人公记忆片段的快速闪回,又似梦中之境的随意拼贴。中国古典诗词中有着用意象叙事的传统,作家以渗透着古味的意象描绘背剑的旅行人一生中“各色的夜”,使画面氤氲着浪迹天涯的漂泊感;与此同时,借鉴西方象征手法,无论是“通红的蜻蜓”“惨绿的磷火”,还是文段二静穆的夜空下那声“鹅黄色的叹息”,都现代感十足。京派作家取古典山水诗之“神”与西方现代主义诗歌之“形”,创造既有中国传统文学审美风范,又充分体现时代特点的文学意象。京派作家融合中国古典文学借助意象表现情感的“间接”以及西方意识流小说通过语言模拟意识流动的“直接”,拓宽了人物心灵的表现空间。为进一步把握人物意念与情感,京派作家以心理结构小说,沈从文称之为“情绪的体操”。京派小说的心理情绪模式淡化了传统小说以情节为中心的结构,促进小说与诗歌、散文的融合,体现结构上的现代性。
总之,京派小说在叙事视角、结构、技法等多方面显现出鲜明的现代品格,京派作家的探索在传统与现代的辩证统一中展开,因而在现代化浪潮中充分保有民族文化资源的特殊性。
帅沁彤:京派文学对于传统语言资源的运用,并非“返回”,而是“激活”。艾略特在1917年的《传统与个人才能》一文中阐述其对“传统”的认识。艾略特不是将“传统”视为一成不变的前一代方法或过去存在体,而认为传统“不是继承得到的”,他对“传统”的认识无疑已跳脱出一般的线性继承视野,在他看来,面对传统不仅应理解“过去的过去性”,还需理解“过去的现存性”。所谓“过去的过去性”是指“过去”之人对于“过去”的认识,由此形成过去传统的秩序与面貌;而“过去的现存性”则指现世之人对于过去传统的新认识,构成传统的新面貌与新秩序。传统正是将“过去的过去性”和“过去的现存性”结合而得以建构其完整体系。文段一“城垛子,一直排;立刻可以伸起来,故意缩着那么矮……”,颇似童谣,押韵但不对仗。“使劲的白,是衙门的墙”,改变了现代汉语“衙门的墙是白的”的语法,采用类似“使劲的白,墙也”的句式。但其中的生命力早已按捺不住,“白”通常作为颜色的形容词,在此当了主角,有了“故意”的意识、“使劲”的动作。“簇簇的瓦,成了乌云,黑不了青天”,“瓦片”“青天”“云”都是常见的古典意象,瓦“簇簇”,成了乌云,“黑”活用为动词,形成了现代的诗意。一些常见的古代汉语活用、倒装等现象,用在这里,无意返古,而是要显现一种新的生命力,“借”力“创”力。由此可见,“传统”的秩序和面貌并非固定不变,处在不同历史时代的人会从中发现其不同质素,“传统”会在“新与旧的适应”中进行调整和修改,京派文学也非一味使用“传统”的语言,“传统”永远处于被不断改造和重新发明的状态。
郑慧芳:前面谈到京派语言通常在现代汉语中激活古典资源,讲究文白之美,追求内在节奏。所谓京派语言的现代性,是指京派语言如何在保持上述特殊性的同时实现对现代性的追求。废名深受魏晋诗歌和唐诗的影响,又身处全面西化的文学创作背景中,他回到了中国古典诗歌传统中去寻找语言的现代因子,打破“传统”与“现代”非此即彼的割裂关系,表现出鲜活的创造力。“城垛子,一直排;立刻可以伸起来,故意缩着那么矮,而又使劲的白……”充满了古典诗词跳跃、省略的特点,追求音律美,用字节俭,行文简洁,将诗歌的表达方式用到小说创作中,充满了古典文学的古朴典雅气息。与此同时,“立刻可以伸起来,故意缩着那么矮,而又使劲的白,是衙门的墙”却冲破了传统汉语语法的束缚,采用英法俄的语法特点组织句子,是一个典型的欧化倒装句式(……is……)。主语后置,凸显出细致、复杂的修饰语。虽是白描,却有古味;虽有古味,却有欧化,集传统与现代于一体,达到一种新颖的审美意趣。
相比于句式上的欧化,意识流手法的引入与运用使京派语言的现代性更加明显。物理时间不再作为单一向度,在物理时间的裂缝中,小说填补记录着心理时空中的变化过程。文段三中老太太喘息和妇人问好的外部现实描写之间,插入了一段老太太回忆过去的意识流动过程。但语言基本西化,追求现代性的同时语言的特殊性反而有所丢失。
文段四既保持了京派语言的美感,又有着极其鲜明的现代性特征。“海是绿的,腥的”、像头颅一般腐烂的果子,与波德莱尔《恶之花》相似:“天空对着这壮丽的尸体凝望,好像一朵开放的花苞,臭气是那样强烈……”突破了中国传统审美意蕴,使用了西方现代小说中习用的沉重、暗黑、轻颓的灰色意象,这些“丑”的意象是隐喻式的,与主人公此刻的内心活动具有一致性。一大段散文式的环境描写,细看却是化用了意识流手法,将客观景物与主观情绪结合,将环境描写与心理描写结合,使景物流露出意识,使意识流露出诗意。一般的景物描写透过人的眼睛,而该段描写穿透的是人的意识,主人公在看到瞬间的画面时想象到了长时间的动态过程。果子“正在腐烂”、贝壳“逐渐变成石灰”、太阳“落下去了”、人“逼向……又转身,分散”都是长时间的动态变化过程。随着意识的流动,主人公又由景物联想到了诗句,便有了“人看远处如烟。自在烟里,看帆篷远去”的感慨。由帆篷引出对船中物品的猜测,“一船瓜”“一船石头”可能是现实,也可能是幻想。而鸟、百合花则由“也许”一词点明这是主人公的意识流动。意识由“百合花”吟咏出“伸向明朝卖杏花”,又在现实中看到了骆驼……客观现实与心里流动交相呼应,不分彼此,语言呈现出本土化、个人化的现代性特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