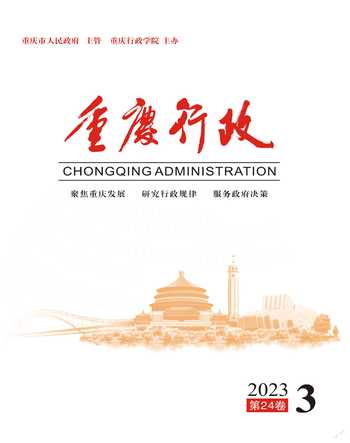发展型社会政策理论视角下渝东南民族地区乡村发展问题及对策探讨
2023-08-14赵雪映余一波
赵雪映 余一波
渝东南民族地区位于重庆东南部,幅员1.98万平方公里,占全市总面积的24%,[1]是国内规模较大的以土家族和苗族为代表的少数民族聚居区。渝东南具备独特的发展优势,然而,当前渝东南民族地区发展过程中,始终呈现不同的发展弊端和困境,发展结果不尽如人意。渝东南民族地区存在经济发展水平低、城乡发展不均衡、社会发展与经济发展不同步等现象。共同富裕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其核心在于“共同”。“共同”的本质是一个社会如何实现团结发展的问题。
因而要推动渝东南民族地区走向共同富裕,核心在于振兴乡村,实现渝东南民族地区乡村的发展。本文根据渝东南的发展现状和已有的研究成果,总结了渝东南在推动民族地区乡村发展中的典型问题,并结合发展型社会政策相关理论,对渝东南民族地区乡村发展问题进行诠释,并对相关问题提出对策,供有关部门参考。
一、渝东南民族地区乡村发展存在的问题
渝东南民族地区是指包括黔江、石柱、秀山、酉阳、彭水和武隆在内的区县,渝东南民族地区在改革开放后特别是借助于重庆直辖的效应实现了经济的跨越式发展,经济总量在增加,年均递增率在提高。[2]但作为重庆唯一的少数民族聚居区和唯一的集中连片特困地区,[3]渝东南地区的贫困问题仍然突出,具有典型性和复杂性。根据重庆市最新统计年鉴数据显示,2021年,重庆全市GDP总量为27894亿元,渝东南GDP总量为约为1543亿元,仅占全市GDP总量的5.53%,全市农村农业总产值约为2935亿元,其中渝东南约为352亿元,仅占全市的12%。从数据可以看出,渝东南民族地区经济发展总体水平较落后,其农村地区的发展水平仍有巨大的提升空间。渝东南民族地区乡村的发展具有西部民族地区发展问题的共性与自身的特性,主要面临四大方面发展问题。
(一)经济发展水平落后
渝东南民族地区乡村由于多方面原因造成了生产力的低,经济发展水平落后。渝东南地区地处山区,地势起伏。由于地形限制,渝东南民族地区城镇化率不高,无法形成城镇带动乡村发展的连锁发展效应,乡村人均可支配收入远远落后于重庆其他地区。根据2021年重庆市统计年鉴,截至2021年底,重庆全市城镇化率为70.96%,而渝东南民族地区城镇化率仅为51.68%。渝东南民族地区城镇居民年人均生产总值为53875元,仅占重庆市人均生产总值的62.0%。在社会原因方面,渝东南民族地区,尤其是乡村地区土家族、苗族等少数民族同胞聚居,宗教信仰、民族习俗各异,在发展经济的同时要尊重民族同胞的文化习惯。民族文化是一把双刃剑,既可以是经济发展的动力,也可以变成掣肘,如何把握好这两者之间的“度”,是一个值得权衡的问题。根据2022年重庆市统计年鉴,在渝东南民族地区乡村中,第一产业的经济生产总值为2115400万元,第二产业的生产总值为5170100万元,第三产业产值为8146400万元,分别占渝东南民族地区生产总值的13.71%、33.50%和52.79%。在三种产业布局中,渝东南民族地区乡村地区的生产方式以第三产业为主,其中旅游服务业是主要发展生产方式,其次第二产业占比较大,以工业发展为主要生产方式。可以看出,渝东南民族地区乡村的经济发展过于依赖第三产业,但第三产业的发展受多方面因素影响,具有不稳定性。此外,三种产业布局的整体发展水平十分有限。
(二)农村地区缺乏发展的必要社會条件
除了经济整体发展水平较低外,渝东南民族地区的环境、基础设施、科技发展水平和教育水平等也欠发达。其中环境包括自然环境和人居环境。从自然环境看,渝东南地区背靠大山大水,地势起伏较大,为典型的喀斯特地貌,只能依赖比较低级的农业生产方式。这些较初级的生产方式对土地资源的利用率较低,并且由于生产方式粗放,对生态环境带来了一定程度的破坏。据重庆市2022年统计年鉴,渝东南农村农业生产过程中,对于农药、化肥和电力使用均大幅度低于其他地区农村,最终的农业产出效率低下。地理条件的劣势也限制了人居环境变迁,具体表现为限制了基础设施的发展。根据重庆市2022年统计年鉴,渝东南地区目前仅拥有高速公路609条,占重庆市的22.48%。较薄弱的交通基础也成为渝东南民族地区发展的障碍。
(三)劳动力外流明显且素质较低
人是发展的核心。在全国城镇化背景下,农村劳动力向城市流动是不可避免的一种趋势。渝东南民族地区乡村的优质劳动力也大量的流向了城市,除了城郊的一些村社,乡镇各行政村内青壮年劳动力占比不到10%。[4]这里的“优质”不但指年龄和体力上占优势,同时特指受教育程度高。渝东南地区少数民族分布集中,是重庆市少数民族人数分布最多的片区,其中土家族和苗族人口占比最大。这些民族有属于本民族的语言甚至文字,在多民族杂居与本民族小聚居的生活环境下,汉语的普及促进了民族地区同胞与汉族人民的交流与融合,年轻一代的少数民族汉化程度较高。在这样的背景下,少数民族中的青壮年劳动力出于谋生的本能,开始离开乡村往城市迁移,由于城市具备乡村所不具备的区位优势,他们中的大多数选择定居城镇,成为了城镇居民。根据重庆市2022年统计年鉴,渝东南地区城市人口从2011年的90.05万人增长到2009年的130.54万人,呈现连年递增的大幅增长态势。但渝东南地区仍有300多万总人口,城镇人口只占约三分之一,约有超过60%的人口仍旧定居在乡村,这部分人出于各种原因选择留在农村,是渝东南民族地区乡村发展的主力军。乡村地区除了劳动力的流失,劳动力素质较低也是值得重视的现象。根据重庆市2023年人口普查年鉴,以渝东南地区的彭水县、酉阳县为例,彭水县农村地区13047人中教育程度为初中及以下的人口为11511人,占比为88.22%;酉阳县12379名农村人口中初中及以下的人口为11158人,占比为90.13%。这部分人群构成了渝东南民族地区乡村发展的主体,但是由于受教育水平低下,只能选择从事方式单一的经验行业或体力行业。
(四)政府主导的发展方式形式单一
渝东南民族地区乡村受困于各种制约因素,发展效果欠佳。在区位劣势下,当地的发展现状对社会组织没有太大的吸引力,导致农村地区的发展始终只能由政府引领。政府主导的发展具备一定的优势,但与此同时,一个地区的发展不能光靠政府扶持,在政策优势以外,民族地区乡村还应遵循发展规律,找到最契合自身的发展路径。
二、发展型社会政策视角下渝东南民族地区乡村发展问题的原因分析
(一)经济发展方式可持续性差,产业布局单一
渝东南地区的发展以旅游业为代表的第三产业为主。特殊的自然地理是渝东南地区的优势,但同时也是劣势。旅游业受到多种因素的制约,在发展前景上的可持续性较差。例如,过去三年,由于“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的影响,当地旅游业受到严重打击,经济发展受到重创,直接影响了渝东南整体片区的发展。可见,过于单一的产业布局抗风险能力差,缺乏应对危机的能力。
(二)社会发展落后于经济发展,两者不同步
尽管发展型社会政策理论认为社会政策应与经济政策融合发展,经济发展应该放在一切发展之首。经济发展是社会整体发展的内在动力,对提高人们的生活质量具有重要的推动作用,渝东南民族地区乡村经济发展落后,经济发展低效,在发展过程中选择了不可持续的发展方式,导致乡村地区陷入了脱贫—返贫—扶贫的恶性循环。这种不可持续的经济发展方式阻碍了渝东南民族地区乡村发展的步伐。
发展型理论认为,如果只注重经济发展,而将社会发展置于经济发展的附属地位,那么这个地区的发展是“扭曲”的发展。如果单纯着眼于振兴民族地区乡村的经济,导致社会发展不同步,那么在社会发展的过程中会将这二者的关系割裂,最终社会发展会产生严重的问题。
(三)人力资源的素质培养欠缺,社会发展受阻
社会发展需要人的参与。发展型社会政策理论认为,人力资本影响着劳动力的素质,渝东南民族地区乡村的人力资本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最终导致青壮年受教育程度低,劳动力群体素质较低;职业培训方面力度不够、人力资本投资不足,最终导致民族地区乡村产业发展受限、乡村振兴受阻,在社会层面上还造成了事实性的社会隔离。
(四)社会发展的力量参与不均衡,思路转变难
社会发展需要国家、社会和个人等多元力量的共同参与。在渝东南民族地区乡村发展过程中,一直以政府各部门的力量为主导,有少量社工机构、志愿服务团体和社会爱心企业参与。政策适用的对象也要转变思想观念,应从传统的被动接受到主动适应和参与。
三、发展型社会政策理论视角下渝东南民族地区发展问题的对策
发展型社会政策是社会政策的代表性理论之一,主要包括几个方面:强调社会福利的普遍性,实现发展成果由所有人共享;在发展经济的基础之上,社会发展与经济发展同等重要,二者应该融合、协调、相互促进;可持续发展,关注社会政策的经济产出,重视对人力资本的投资;促进社会发展需要政府主导、各种力量共同努力。目前,发展型社会政策的理论运用范围较广,在乡村振兴领域的研究成果也较为丰富,民族地区乡村是发展中重要的版块,运用该理论探讨其发展困境及对策,对当地的发展具有现实意义。
(一)调整产业布局:促进经济可持续发展
发展意味着可持续。发展型社会政策强调“投资”“可持续”,在民族地区乡村社会的发展中,面对脆弱的生态环境,政策制定者应用“可持续”的眼光来制定发展政策。在渝东南民族地区乡村发展过程中,要充分利用好优越的旅游资源,在此基础上打造一系列的第三产业发展链条,促进旅游与民族文化的融合;与此同时,也要注重对第二产业的投入;最后,响应最新的保卫粮食安全政策,适当增加第一产业的比重,引入小型机械,科学、高效地推动第一产业发展,最终形成以第一产业为基础、第二产业做支撑、第三产业做补充的产业发展格局,增强经济发展的抗风险能力。
(二)推动经济与社会融合发展:经济与社会发展并重
社会发展应该与经济发展置于同等重要的位置。传统的以蒂特马斯为代表的认为“经济发展靠市场,社会福利靠政府”[5]的理论并不适用于当下的中国社会。实际上,按照发展型社会政策的观点,经济发展与社会发展之间呈现交叉的关系。在促进经济发展中有政府的身影,而社会福利也不能单纯地依靠政府。在渝东南民族地区乡村的发展问题上,不能只注重经济的发展,同时也要兼顾社会福利的落实,注重社会和经济的双重效应。社会发展的根本目标就是社会和经济的协调发展,确保发展的成果由整个社会所共享,惠及各个社会阶层。[6]良好的社会政策有利于促进各民族平等,增进民族间的团结,增强凝聚力,促进社会和谐,从而实现社会良性运行和协调发展。这要求我们要将民族地区乡村的经济发展和社会发展放到同样的高度上,科学制定社会发展政策,兼顾政策在经济方面的产出;同时也要注意经济政策的社会效应,尽量规避其负面社会效应,最终形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融合发展局面,促进双方共同进步。面对渝东南民族地区乡村落后的社会发展状态,政府应围绕着社会公共福利制定相应社会政策,加大基础设施建设,增加居民的福利保障等。
(三)加强人力资本投资:提升职业培训力度
人力资本投资最直接的影响就是劳动力素质的提升。人力资本的提升可以从两方面入手:一是针对学龄群体普及专业教育,这直接影响着未来劳动力的素质,并会形成如下的良性效应——投资民族地区乡村的人力资本,促使劳动力素质得到整体提升,进而提升劳动者的竞争力,开拓劳动者的就业渠道,甚至吸引或者创建更高水平的产业到民族地区乡村;二是针对已就业的群体开展实用的职业技能培训,包括耕种技能、机械操作步骤、职业技能,等等。
(四)建设多元格局:以成政府主导、社會带动、个人参与
社会发展不能单纯地依靠某种单一的力量。民族地区乡村的发展格局多元复杂,民族、宗教、文化等力量相互交错。从区域来看,由于受到民族、风俗习惯等的多重影响,渝东南民族地区还有着较为丰富复杂的民族生态习惯法,[7]仅凭政府的力量不能实现社会的良好发展。在发展问题面前,政府应站在宏观角度,引入社会资本力量共同参与发展;个人也应化被动为主动,在政府和相关机构领下提高自身素质,选择最适合自己发展的路径,最终实现政府—企业—个人共赢的发展局面。
参考文献:
[1]陈真.渝东南民族地区加快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路径研究.[J].商业经济.2020(01):143-144.
[2]范远江.渝东南民族地区发展性贫困的原因及对策探析.[J].黑龙江民族丛刊.2009(05):71-75.
[3]孙晗霖.连片特困地区财政扶贫绩效评价及影响因素研究.[D].西南大学.2016.
[4]田富.乡村振兴背景下渝东南民族地区人才振兴问题研究.[J].广西城镇建设.2021:44-46.
[5]方巍.发展型社会政策: 理论、渊源、实践及启示.[J].广东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3(01).
[6]吴炜.发展型社会政策及其对我国社会政策发展的启示.[J].内蒙古社会科学.2014(06).
[7]阳盼盼.新发展理念下渝东南民族地区高质量发展路径探析.[J].南方农业.2020,14(04):54-56.
作者单位:赵雪映,重庆工商大学法学与社会学学院
余一波,重庆市垫江县民政局
责任编辑:粟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