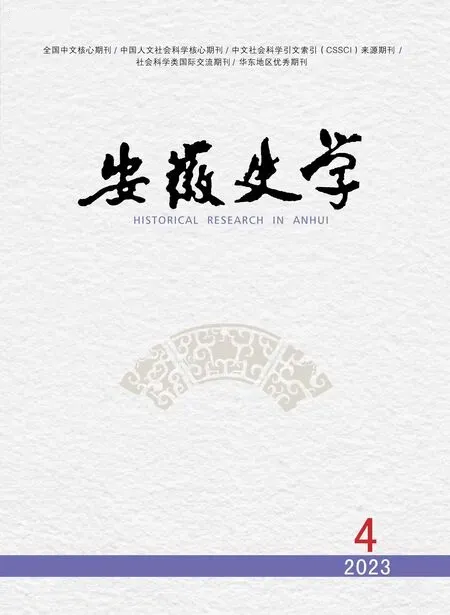《官商快览》与近代日用出版
2023-08-09肖文远
肖文远
(中山大学 历史学系,广东 广州 510275)
近代城市生活的变迁使得明清时期畅销的日用书籍已无法指导人们的日常实践。一个新的日用书市场在清末应运而生,成为上海出版商竞逐的新战场。但是在近代出版史的一般叙事中,对“学”的关注将研究者的目光局限在科举用书、教科书和中西学书籍上,却遮蔽了日用书籍在近代出版业的崛起中所扮演的角色。(1)相关研究有[美]芮哲非著、张志强等译:《谷腾堡在上海:中国印刷资本业的发展(1876—1937)》,商务印书馆2014年版;许静波:《石头记:上海近代石印书业研究1843—1956》,苏州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杨丽莹:《清末民初的石印术与石印本研究:以上海地区为中心》,上海古籍出版社2018年版;曹南屏:《阅读变迁与知识转型:晚清科举考试用书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8年版。一些学者分别从知识传播、社会生活的变迁、文本编辑策略等角度对个别日用书籍展开了探讨。(2)叶凯蒂通过《日用百科全书》展现了现代化的追求在日常生活层面的渗透,Catherine Vance Yeh,“Helping Our People ‘to Jointly Hurry Along the Path to Civilization.’ The Everyday Cyclopedia,Riyong baike quanshu日用百科全书”,Milena Doleželová-Velingerová,Rudolf G.Wagner(eds.),Changing Ways of Thought:Chinese Encyclopaedias of New Global Knowledge (1870-1930),Berlin:Springer,2014.季家珍探讨了《万宝全书》在近代的出版及其受众的变化。Joan Judge,“Science for the Chinese Common Reader? Myriad Treasures and New Knowledge at the Turn of the Twentieth Century”,Science in Context,Vol.30,No.3(2017),pp.359-383.关于城市指南的研究较多,最新研究成果有巫仁恕编:《城市指南与近代中国城市史研究》,(香港)开源书局出版有限公司、(台湾)民国历史文化学社2019年版。但是出版史研究的缺失导致近代日用文本演变脉络隐晦不明,限制了个案研究的价值。如叶凯蒂将《万宝全书》和商务印书馆的《日用百科全书》分别视作清末和民国时期日常生活经验的表征,进而断言:清末到民国日常生活经验出现了断裂。(3)Catherine Vance Yeh,“Helping Our People ‘to Jointly Hurry Along the Path to Civilization.’ The Everyday Cyclopedia,Riyong baike quanshu日用百科全书.”pp.367-398.这种错误的判断源于对当时的日用书市场缺乏清晰的认知。
相比于《万宝全书》《日用百科全书》,《官商快览》更能代表口岸城市的日常经验。(4)许静波在研究书业公所时,简略述及书业公所出版《官商快览》的活动。许静波:《成本最简模式下的近代化——上海近代石印书业研究(1878—1956)》,复旦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2年,第178—179页。小浜正子从文献学的角度初步介绍了该书的内容及变化。[日]小浜正子:《〈官商快覧〉から〈国民快覧〉へ―中国近代のマニュアルブック》,《言語·文化·社会》2018年第 16 号。《官商快览》自1897年问世,到1930年被查禁,风行三十余年。本文将以《官商快览》的出版为线索,围绕日用出版领域参与主体、出版秩序、市场竞争,展现这一市场在20世纪前三十年的扩张趋势。这不仅有助于把握近代出版业的多重面向,也可为知识史的下沉提供坚实基础。
一、从石印业的利薮到书业公所的禁脔
19世纪末,口岸城市的日常生活发生了深刻的变迁。明清时期流行的日用文本已经难以满足人们的日常需求。1897年,天津绛雪斋编辑出版了第一份《官商快览》(以下或简称快览),标志着一个新兴的出版领域浮现。(5)绛雪斋1905年在《大公报》刊载的广告中,有“自丙申创办以来,已阅九载”等语,可知其始创于光绪二十二年末。见《大公报》1905年2月12日,第3版。绛雪斋的创办者甘厚慈,又称甘眠羊,是一个从官场隐退、转而从事出版的书商。(6)杨凤藻说,甘厚慈曾“由军功以知县指分直隶,竟未入仕途一步。”《杨凤藻题辞》,甘眠羊编:《新天津指南》,天津绛雪斋1927年版。因此,他在清末十余年间所编辑出版的书籍都与官场有着千丝万缕的关联。(7)甘厚慈在清末先后出版了《时务策》(出版年份不详,惟据杨凤藻言,此书最早出版。见《杨凤藻题辞》,甘眠羊编:《新天津指南》)、《李傅相壮游日记》(1896)、《官商快览》(1897)、《皇朝经世文新编续集》(1902)、《北洋公牍类纂》(1907)。相比于其它书籍强烈的经世色彩,《官商快览》十分特殊。从内容来看,它继承了通书的时日宜忌,并囊括铁路、轮船、邮政、度量衡、币制、关税、官制、捐官章程等信息,是一部以官员、商人为目标受众的日用文本。从出版周期来看,它与历书一样逐年刊行,故可称之为日用年刊。
《官商快览》问世后迅速风靡口岸城市。这一点可从同行的反应中得到印证。甘眠羊在戊戌本(1898)序言中写道:“本斋石印《戊戌官商快览八十种》尚未出书,而市间忽有发售明年《官商快览》《华英通书》名目。亟购阅之,盖取丁酉敝斋旧本删去一半,照样缩印,贱价发售,希图利益。”(8)《本斋琐言》,《戊戌官商快览八十种》,天津绛雪斋1898年石印版,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学院图书馆藏。快览问世的第二年,天津就出现了翻刻本。绛雪斋所说的《华英通书》即《华洋通书大成》,该书现有庚子本(1900)存世。书中刊登的楹联以及津榆、津卢铁路价位表和时刻表均翻刻自绛雪斋《官商快览》,惟书中没有出版者的信息。(9)《庚子岁华洋通书大成》,1900年石印版,国家图书馆藏。同年,绛雪斋呈请天津县颁布示谕:禁止天津居民、书局、铺户翻刻《官商快览》,也禁止代售外埠翻刻本。(10)《天津县示》,《辛丑官商快览二百四十种》,天津绛雪斋1901年石印版,南京图书馆藏。示谕中所说的“外埠”就是上海。1899年1月,《申报》就刊登了一则文富斋《官商快览》的广告:“是书为京都文富斋所印,首华洋通书,附以诹吉便览,次通商约章,次洋关税则,次振(赈)捐新例,次中西年月日表、各省府州厅县指掌、官阶品级俸禄表、电报新编、电报价目表,而以沪游便览异名录、姓氏郡名录、经验良方诸书附其后,诚可谓集群籍之大成,为枕中之秘笈。……昨日承虞山鲍君叔衡见贻……”(11)《申报》1899年1月10日,第3版。京都文富斋已不可考,但赠书之人鲍叔衡即抱芳阁的老板鲍廷爵。考虑到此种赠书的广告色彩,鲍廷爵应当就是幕后出版商。
自1898年至1907年的十年间,快览在上海石印业中引发了效仿和翻刻的热潮,成为清末最炙手可热的出版物。据笔者不完全统计,在这十年间,出版快览类书籍的堂号分别有绛雪斋、鸿雪斋、映雪斋、印雪斋、扫雪斋、赏雪斋、晴雪斋、萃雪斋、瑞雪斋、咏雪斋、快雪斋、广雪斋、文宝斋、文富斋、快睹轩、惜阴别墅等16家。其中多以“X雪斋”为名,书名也多以“官商快览”“官商便览”为名。只有惜阴别墅将自己的出版物命名为《酬世全书》,其实相当于快览的缩略版。以相近的堂号和书名来影射原本、鱼目混珠,是传统出版业的惯用伎俩。但此处的堂号还有另一层用处,即隐藏实际的出版者。这也使得沪上书局在其中扮演的角色扑朔迷离。不过,书籍和广告提供了一些蛛丝马迹。简言之,广告中的发行者往往就是真正的出版者。据此判断,鸿雪斋的背后是点石斋,文宝斋的背后是文宝书局,快睹轩的背后是申昌书局,惜阴别墅的背后是《新闻报》馆。(12)鸿雪斋与点石斋的关系可见诸《鸿雪斋官商便览五百种》,上海点石斋1905年版,上海图书馆藏。其余诸家见《申报》1902年12月7日,第4版;1904年11月27日,第4版;1906年10月26日,第18版。
1907年,书业公所经费竭蹶,由叶九如提议,将各家《官商快览》《酬世全书》书底上交,归书业公所统一发行。上交者多达19家,每家1股,共计19股。(13)叶九如:《书业公所创立经过略记》,汪耀华编著:《上海书业同业公会史料与研究》,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19—20页。书业公所档案中保留了一份民国时期的花户名单,共30户19股(见表1)。户名远超19户,是因为很多书局将股份进一步析分到了个人名下,或转让他人。股份流转的情况下,现户名后会注明原户名。从中可大致了解清末快览的出版格局。共和新记是民国以后成立的书局,至于原户主文新不知何人。席子佩有1.5股,应当包括了点石斋和申昌书局的股份。叶心安其人不可考,但是“澄衷”当是指澄衷蒙学堂印书处,后者曾是映雪斋《官商便览》的承印者。汪汉溪来自《新闻报》馆,该馆是惜阴别墅《酬世全书》的出版者。刘松山和乌仁甫均来自鸿宝斋书局,二人各占0.5股。成燮春是燮记书局的老板。其余户名,或不可考,或因工作流动难以确定原先所代表的书局。综上所述,可以确定清末出版过快览的书局有扫叶山房、文瑞楼、广益书局、铸记书庄、商务印书馆、章福记、晏文盛堂、鸿文书局、点石斋、《新闻报》馆、澄衷蒙学堂印书处、鸿宝斋书局、燮记书局、申昌书局、文宝书局、顺成书局(绛雪斋的代印书局)等共计16家。

表1 书业公所《国民快览》的股权分配
书业公所1907年开始垄断快览的发行,民国建立后改名为《国民快览》。直至1930年,因为附载阴历和宜忌,被力推国历的南京国民政府查禁。(14)《江苏省政府公报》1930年第344期,第12页。根据书业公所档案,在1917—1928年间,《国民快览》的年销售量在3.4万—5万份之间波动(见表2)。需要强调的是,这是其生存空间受到竞争对手严重挤压下的销售量(详见下文)。因此清末一枝独秀时期,快览的市场规模可能高于这个数字。依据表2中的销售量和销售额可以推算出,起初快览的批发价为每本1角5分,1919年升至1角8分,此后十年一直保持不变。但是快览的售价从清末到民国经历了明显的下调,批发价应当也不例外。若清末批发价为2角,销售量在5万份左右,则清末快览的市场规模可达到1万元。每年1万元的市场规模固然不能弥补科举停废的损失,但是对亟需拓展出版业务的石印书局而言,其重要性不言而喻。

表2 书业公所1917—1928年《国民快览》出版数据
二、版权之争与石印业的出版秩序
石印书局先于铅印书局进入日用出版领域,但是二者的态势却在民国时期发生倒转。(15)虽然下文所讨论的商务印书馆是个兼具铅印和石印业务的综合性书局,但是它的日用书籍皆通过铅印出版,故而在本文中将其视为铅印书局。产生这种转变的主要原因不是技术差异,而是二者不同的经营模式和出版秩序。
石印书局参与快览出版的方式可分为三种。一种是与编书机构开展合作,一方提供内容,一方负责印刷。绛雪斋是独立的发行方,没有印刷能力,它选择将印刷业务委托给上海的顺成书局。因此,绛雪斋的《官商快览》中,更突出“绛雪斋”和编者“甘眠羊”,而不是代印书局。类似的还有映雪斋,其《官商便览》中刻意凸显编者王作霖。(16)其版心处皆有“映雪斋作霖王氏真本”字样,见《映雪斋分类官商便览七百种》,映雪斋1905年石印版,上海图书馆藏。据此推断,映雪斋与负责印刷的澄衷蒙学堂印书处也是委托关系。文宝书局和点石斋代表了另一种出版模式,即石印书局雇佣编者,一手操办编辑、印刷等环节。在这种模式下,书中往往忽略编者而凸显出版商。
第三种模式是翻印。如印雪斋丙午版(1906)《官商便览》就翻刻了绛雪斋辛丑版(1901)、壬寅版(1902)的内容。该书第一页以丙午年正月月历遮人耳目,后面的月历翻刻了壬寅版,其余内容则翻刻了辛丑版,甚至连版心“天津绛雪斋庚子冬在沪印”的字样都未抹去。(17)《印雪斋官商便览八百四十种》,1906年石印版,南京图书馆藏。“印雪斋”同时也是商务印书馆的股东印有模的别名,是否只是巧合已难以追索。《新闻报》馆的手法更为隐秘,它从绛雪斋旧本中抄录信息,打乱次序,重新誊写落石,以《酬世全书》之名发行。翻印最大的问题在于滞后性,翻印的对象多是往年版本,较为陈旧。但是一些书局甚至能够及时翻印最新版本的快览,使得真本和翻印本更加难以区分。如咏雪斋和瑞雪斋两家丁未版(1907)的内容完全相同,显然是其中一家原样翻刻了另一家。(18)《咏雪斋官商便览九百四十种》,1907年石印版,安徽省图书馆藏;《瑞雪斋官商便览》,1907年石印版,安徽省图书馆藏。由于咏雪斋版留下了编者的姓名,瑞雪斋翻印咏雪斋的可能性更高。
绛雪斋在《官商快览》遭到翻刻时,曾试图借助官府的力量来保护自己的利益。继光绪二十四年天津县颁布示谕后,光绪二十六年(1900),绛雪斋又呈请苏松太道和英法租界当局颁布了类似的示谕。这种寄希望于地方政府介入,来保障自身权益的做法,常见于雕版印刷业。但是私人权益即便具有合理性,也很难得到地方政府的支持。于是,出版商往往诉诸于一套公益话语。在呈文中,绛雪斋不仅指出自己是《官商快览》的原创者,翻刻行为损害了其利益,更强调其它竞争者“将该斋隔年之书更换私印,朦混出售,而于本年应增应减之端未能细心考察,以致官商购览,皆受其欺”。(19)《苏松太兵备道示》,《辛丑官商快览二百四十种》。因此,禁止其它出版商出版该书,不仅是捍卫绛雪斋的正当权益,也是为了保护公众利益。
这些禁令未能阻止上海书业的翻刻热潮,参与的书局越来越多,到1907年已经不少于19家。石印书商们只是将自己的出版物改名为《官商便览》《酬世全书》,以规避禁令。不过,地方政府的示谕提供了令人信服的依据,有助于绛雪斋塑造自家“真本”与一般翻刻本的对立。在广告中,它也努力和竞争者划清界限:“各种翻本荒谬绝伦,依然照录历年敝本,竟无分毫进境,欺己害人,良堪痛恨。”(20)《申报》1905年1月30日,第4版。
1907年书业公所决议由公所垄断《官商快览》的出版,以所得盈余之四成为公所经费,六成归各书局所有。公所只负责快览的编辑工作,誊写、印刷、装订、销售等环节均由各书局承担。(21)许静波:《鸿宝斋书局与上海近代石印书籍出版》,《新闻大学》2012年第3期。同年,书业公所在《申报》刊登告白,措辞相当强硬,要求各书局及时交出书底:“《官商快览》书底,现诸公议定并归公所印售。如同业向有书底者,限至本月廿六日止送到公所,当给收据。倘有今年新抄未成之底,亦限三日内交到公所,照给抄价,以遵定章。过期不收,幸勿自误。”(22)《申报》1907年9月1日,第1版。次年,书业公所又禀请上海县和苏松太道分别颁布告示。(23)《光绪三十四年三月十九日上海县出示谕禁事》,《庚戌年官商快览》,上海书业公所1910年石印版,广东省中山图书馆藏;《光绪三十四年三月初三日苏松太兵备道给示谕禁事》,《壬子年官商快览》,上海书业公所1912年石印版,广东省中山图书馆藏。
所谓书底,即可供复制的印刷媒介,如雕版印刷中的刻版,石印中已经落石的石版。(24)Fei-Hsien Wang,“The ‘Copyright’ Regime of Chessboard Street”,Pirates and Publishers:A Social History of Copyright in Modern China,Princeton and Oxford: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2019,p.171.以编书为业的绛雪斋自然无法提供书底,也就被排除在外。绛雪斋无法继续在上海立足,被迫迁回天津。映雪斋的王作霖也被排除在外,反而是负责印刷映雪斋《官商便览》的澄衷蒙学堂印书处获得了股份。1910年《大清著作权律》的颁布一度让绛雪斋看到了希望(25)甘厚慈在《辛亥官商快览》中隔空喊话:“本斋现已遵照奏定新章禀请版权,同业本勿再蹈前辙”,似有重新争夺版权的行动。见《辛亥官商快览》,绛雪斋1911年石印版,南京图书馆藏。,但是清廷很快覆灭,而书业公所在民国之初便向新政权申请了版权保护。(26)《书业公所广告》,《申报》1912年1月13日,第1版。绛雪斋夺回版权的努力最终落空了。
书业公所的垄断也不时受到挑战。辛亥革命爆发后,书业公所未能及时更替《官商快览》的内容,仍然刊载了大清龙旗、帝后重臣肖像、清廷政治改革等内容。有书局闻风而动,欲私自出版快览。但是书业公所很快向民国政府申请版权保护,并登报谴责该出版商“实属有意破坏公益,殊于公所经济大有妨碍”。(27)《书业公所广告》,《申报》1912年1月13日,第1版。此事最后以该书局缴纳罚款、销毁书底而告终。(28)《书业公所通告》,《申报》1912年2月3日,第1版。在书业公所的陈述中,书局私自发行快览不被容忍,不是因为书业公所拥有快览的版权,而是因为私自发行影响了公所的经费来源,进而对整个行业秩序产生不好的影响。虽相隔十余年,书业公所与绛雪斋维护自身利益的措辞如出一辙,私利必须包裹在“公益”的外衣下,才能获得合法性。
绛雪斋作为快览这一文本类型的创造者,其版权诉求在清末遭遇的尴尬处境,意味着石印行业的出版秩序很大程度上是传统出版业的延续。王飞仙指出,中国传统的版权观念认为出版权益不属于作者,而属于投入资金、刊刻出版的出版商。(29)Fei-Hsien Wang,“The Curious Journey of ‘Copyright’ in East Asia”, Pirates and Publishers:A Social History of Copyright in Modern China,p.23.与其说这是一种版权观念,毋宁说是一种地域性出版秩序。包筠雅曾提到,四堡书商会通过协商来确定来年的出版计划,避免同业之间的恶性竞争。(30)[美]包筠雅著,刘永华、饶佳荣等译:《文化贸易:清代至民国时期四堡的书籍交易》,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125页。这种行业秩序本质上是同一地域内出版商的相互制约和妥协。超出熟人社群,这种约束就无法成立。知识既不属于作者,也不属于出版者,而是一种任人取用、刊刻的公共资源。(31)从李仁渊的研究中,我们可以看到,《幼学琼林》等蒙学书籍在全国各地的翻刻情形。Li Ren-Yuan,“Necessary Knowledge for Young Students and Commercial Publishing in 17th-to Early-20th-Century China”,Asia Major,Volume 35 part 2(2022).石印行业的翻刻热潮不过是雕版时代的遗风。上海石印书局虽然采用了新的印刷技术、提高了出版效率,但是依旧将复制作为主要营利手段。
正因如此,石印业和铅印业对于版权的界定存在根本差异。王飞仙认为,书业公所和书业商会的成立是近代出版业版权实践的标志性事件。二者在国家法律缺位的情形下,通过纠集出版商、规范行业秩序来实现对版权的保护。(32)Fei-Hsien Wang,“The ‘Copyright’ Regime of Chessboard Street”,Pirates and Publishers:A Social History of Copyright in Modern China,pp.158-210,pp.171-177.同时他也意识到,书业公所和书业商会对于版权的界定存在些微差异:书业公所将文本的物质形态视为版权依据,而书业商会则将文本的内容视为版权依据。(33)Fei-Hsien Wang,“The ‘Copyright’ Regime of Chessboard Street”,Pirates and Publishers:A Social History of Copyright in Modern China,pp.158-210,pp.171-177.在笔者看来,版权判定依据的差异意味着石印业和铅印业所欲建立的出版秩序截然不同。书业公所将书底这一复制的母体作为版权裁决的标准,与传统出版业对雕版的重视如出一辙。因此,书业公所缔造的出版秩序,依然是石印行业内部相互妥协和制约的结果。作为内容创造者的绛雪斋在其中没有立足之地。而书业商会缔造的版权秩序以知识为核心,这反映了铅印书局对内容创作的重视。出版商不再是知识掮客,而是知识的生产者。这种自我定位的差异决定了石印书局与铅印书局在日用出版领域的消长。
三、商务印书馆与日用出版领域的竞争态势
商务印书馆和快览诞生于同一年,注册资本仅4000元,1901年得到张元济、印有模的注资,才达到5万元的规模。从后见之明来看,1904—1911年借助在教科书市场独占鳌头,商务印书馆迅速崛起。但是后见之明往往具有夸大的成分,它忽视了商务出版业务的多样性。站在1904年的关口,教科书市场尚未兑现,尽可能拓展业务范围可有效降低经营风险。参与快览的投机热潮让它深刻认识到日用出版的巨大市场前景。
1904年商务印书馆出版《袖珍日记》,为进军日用出版之嚆矢。作为日记簿,它还刊载了时间、邮政、电报、轮船、火车、上海租界等信息,与快览有很大的重叠。(34)《申报》1904年2月15日,第4版。此后,商务印书馆(以下或简称商务)陆续推出《学堂日记》《官商通用日记》《便用日记》《月月日记》等多种日记簿。(35)《申报》1909年1月25日,第29版。在时人看来,商务的日记簿与《官商快览》属同一类书。黄炎培曾言:“今之《官商快览》以及坊间印售之日记册,附载各种,实包有无数适于应用之好资料”。(36)黄炎培:《学校教育采用实用主义之商榷》,《民国经世文编(教育)》,《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第496辑,台湾文海出版社1989年版,第4190页。商务印书馆代售书业公所《官商快览》的信息也是在《袖珍日记》的广告中简略提及,亦可见二者的微妙关系。(37)《申报》1907年11月10日,第20版。
日记之外,商务印书馆推出的另一种日用书是城市指南。1909年,商务出版了《上海指南》,并在一年时间内连续出版四次,共印2万册。(38)《申报》1909年7月16日,第1版;1909年9月12日,第1版;1909年10月30日,第1版;1910年5月9日,第1版。到1930年,共出版二十三版。《上海指南》虽然以上海的地方信息为主,但是也试图兼顾全国性:“附件二种:各省旅行须知凡三十余处,备载舟车、旅馆、钱币、风俗……”(39)《申报》1909年7月16日,第1版。1912年,为了弥补全国性信息的不足,商务又推出了《中国旅行指南》,每年更新,涵盖了全国主要城市的交通、通讯、食宿、游览、娱乐等信息。商务的日用书还不止于此。1913年版《国民快览》中刊登了商务的书籍广告,专列“日用必携”一栏,列有《中外度量衡比较表》《百八十年阴阳历对照表》《明码密码电报书》《中国旅行指南》《交通必携》《增订七版上海指南》《国民日记》《学校日记》《袖珍日记》等九种日用书,尺牍类书籍单列一栏。1914年商务又推出新的日用年刊——《日用须知》,它的内容更为全面,是针对快览的替代品。1921年《日用须知》中也刊载了商务自家的书籍广告,“居家旅行必备”一栏有十七种书籍,尚不包括日记簿。(40)《日用须知》,商务印书馆,1921年第5版。
商务印书馆在日用领域的诸多出版活动都具有开拓色彩,成为其它出版商效仿的对象。如点石斋、亚洲公司新书局在清末便效仿商务出版日记簿。(41)《申报》1906年12月12日,第1版;1906年12月21日,第5版。而在商务的《上海指南》出版后,中华书局、世界书局、文明书局纷纷编辑其它城市的城市指南。
简单勾勒商务印书馆在日用领域的出版地图,可以看出,它对于城市生活变迁的因应策略与石印书商截然不同。《官商快览》试图以无所不包的姿态,兼顾不同受众的需求,从而获得最广阔的市场。商务则对日用领域进行细致分解。拆分的标准多样,如知识种类、使用场合和受众等。以知识种类为依据进行拆分,如度量衡、历书、交通、城市信息等皆以专书的形式出版。以用途为依据者,如日记中包括了袖珍、便用、月月三种。在广告词中,商务特意指出:“《袖珍日记》可存怀中而纸幅较小,《通用日记》版本又大,不便于携带。本馆特印《月月日记》,每日一页,每册三十页,足供一月之用,既便取携又足应用。”(42)《申报》1908年12月8日,第5版。三种日记分别满足人们对便携、书写空间两个维度的不同需求。而《学堂日记》则是专为学堂学生而编制,“除日记用纸外,搜辑普通各科学中最切要之表式百余种,既便检查又可窥各科学之门径”。(43)《申报》1909年1月25日,第29版。对受众需求的精确把握增强了日用书籍的粘性,成为日用出版市场持续扩张的关键所在。
产品种类日渐多样、参与者越来越多,使得日用出版领域的竞争越来越激烈,这直观反映在价格的变动上。清末快览的定价稳定在6—7角。而商务印书馆出版的一系列日用书,包括各种日记本、《上海指南》《中国旅行指南》《日用须知》皆定价5角。(44)分别见《申报》1907年12月20日,第5版;1915年8月12日,第15版。商务的袖珍本在价格上更具竞争力,如《袖珍日记》1角6分,《上海指南》袖珍本2角。(45)《中华民国二年岁次癸丑国民快览》,书业公所1913年石印版,广东中山图书馆藏。这种价格优势迫使书业公所在1915年将《国民快览》的价格降至4角。(46)《申报》1915年11月30日,第1版。
在商务印书馆等后起之秀的猛烈冲击下,快览的市场份额在民初应当经历了明显的萎缩。这直接导致书业公所辞退了快览的编辑田慰农,改聘毕公天。1918年《国民快览》序文中有“民国五年,上海书业公所同人以本年份《国民快览》销行不畅,故六年份特请先生改纂”等语。(47)《序文》,《民国七年国民快览》,书业公所1918年石印版,广东中山图书馆藏。毕氏接手后,面临的问题是如何在乱花迷眼的出版市场保持《国民快览》的不可替代性。快览本是实用信息的汇编,以无所不包的丰富内容吸引读者。随着竞争对手的增多,这种优势已经被大大削弱。毕公天采取的策略是提升快览的可读性,使其成为兼顾实用性和可读性的期刊。他在扉页中刊登了沪上文人所题的序文或诗词,以自高身价。编入汪精卫、吴稚晖、蔡元培等革命巨子的文章,吸引读者兴趣。又充分利用石印在制图方面的优势,增加了大量的插画。(48)《申报》1918年11月8日,第14版。这种改变收到了一定的成效,1917—1924年间,《国民快览》的销量呈现缓慢却相对稳定的增长态势,毕氏也得以长期担任编辑一职。
石印书局比铅印书局更早进入日用出版领域,但是由于石印书局对于内容创造的漠视,最终失去先机。清末石印业满足于同质化的单一文本——快览的制造,而未能有效开拓市场。商务印书馆则恰恰相反,通过对需求的敏锐捕捉和强大的内容创造能力,推出大量日用书籍,有效拓展了日用出版市场。在新建立的版权秩序中,无法创造内容的石印书局再无与铅印书局颉颃的可能。
四、广告媒介:印刷资本与工商业资本的合流
近代日用出版的扩张中,日用年刊的崛起是一个不可忽略的现象。从《官商快览》到商务印书馆的日记簿、《中国旅行指南》《日用须知》等都是日用年刊。《上海指南》的更新虽不够规律,但是更新频率比起年刊有过之而无不及。周期性出版物带来了出版活动、读者群体的可预期性。
以快览为例,每年数万份的发行量意味着它拥有一个相对稳定、且规模不逊于任何报纸、期刊的读者群体。不仅如此,快览与日常生活的紧密联系,也是报刊媒介所难以比肩的。这些特性使得日用年刊成为对商家颇具诱惑力的广告媒介。书业公所垄断之初,就积极为《官商快览》招徕广告,强调该书不仅销量大,而且读者将会使用一年半之久,广告性价比极高:“书前告白:封面后半页洋五十元;全页洋八十五元,半页洋四十五元,全页四份之一洋廿五元,全页六份之一洋十八元。书后告白:全页洋七十五元,半页洋四十元,全页四份之一洋廿二元,全页六份之一洋十六元。倘有代制铜板画等,小照自备,外加一成半代制费”。(49)《申报》1908年9月14日,第2版。
清末快览出版的乱象严重削弱了它作为广告媒介的价值。只有绛雪斋、点石斋有过刊登广告的尝试。书业公所垄断后,快览的媒介价值便凸显出来。首先吸引了扫叶山房、文瑞楼、商务印书馆等一众公所成员刊登书籍广告。民初又逐渐出现了药品、文具制造、金店、保险公司等广告。起初广告多为书后页,随着广告需求的增加,广告空间不断拓展,书前页和书中页都插入了广告,地脚的空白也成为承接广告的“摊位”。书业公所档案中收藏了一份广告合同:杭州乾厚金号购买1919年版《国民快览》全书1/3页面的地脚广告,成交价50元。(50)《(民国六年至十八年)经办(第十届至二十二届)快览帐略》,上海市档案馆藏,档号:S313-2-28。
商务印书馆同样精通此道,在其出版的日用年刊中,大多刊载了广告。1917年版《上海指南》中所刊广告多达14页,其中商务自身的书籍广告约占一半,其余则包括药房、医生、铁路、饭店、面粉厂、保险公司等。(51)《增订九版上海指南》,商务印书馆1917年版,日本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图书室藏。其种类之丰、数量之多远超《国民快览》。
《官商快览》与《上海指南》在文本、受众方面的差异,决定了二者的广告也具有明显的差异。快览的内容具有全国性,受众主要是口岸城市的官员、商人等具有较高知识水平和购买能力的群体,因此它的广告从书籍到药品、文具等,以个人消费品为主。而《上海指南》的受众与快览有一定的重合,因此其广告中也包括个人消费品。但是它鲜明的地域性,也吸引了一些地域性的广告,如医生、饭店、沪宁铁路局等以提供服务为主的个体和机构,难以像个人消费品那样突破空间的限制,因而选择以城市指南为载体。同时,《上海指南》作为地方商业信息的汇编,也是工商业者的查询手册,故而还吸引了一些机器厂的广告。
工商业资本和印刷资本的结合方式从20世纪20年代开始也逐渐多样化。日用便览编辑社所出版的《日用便览》也是一份日用年刊,1935年版共印2.7万册,部分在各口岸销售,部分由各企业承购。当年承购五百本以上的企业共八家,共计购买11500册。(52)《日用便览社启事》,《民国二十四年日用便览》,日用便览编辑社1935年版,上海图书馆藏。也就是说,该书近一半的销售量由企业贡献。出版商会在封面和扉页增印承购企业的信息。承购企业再将其作为赠品送给顾客,达到巩固市场和宣传自身的目的。一些工商业企业甚至亲自编制日用文本,委托印刷机构代印,作为赠品向顾客散发。这类文本是日用信息与广告信息的结合体,但是二者的主次关系已经发生倒转。如浙江地方银行从1930年开始每年赠送《日用便览》,该书既是一本日用书籍,也是银行的宣传手册,大量篇幅用于介绍该银行的概况、章程、债券、相关法规等。(53)《日用便览》,浙江地方银行1931年版,上海图书馆藏。
日用年刊独特的媒介价值吸引着工商业资本的流入。在日用属性之外,日用年刊作为广告媒介的属性也日益突出。借助日用年刊,工商业资本主义得以渗透到更广泛的群体和日常生活空间中去。而广告收入也降低了日用年刊的生产成本,推动着日用出版的进一步扩张。
结 论
快览风行中国三十余年,见证了近代日用书市场的繁荣,也在这一领域打下了自己的烙印。在《官商快览》之前,未见以“快览”命名的书籍。相反,“便览”一词更为常用。清末《官商快览》风行之时,很多出版商则以《官商便览》之名影射。《官商快览》《国民快览》的流行,也使得“快览”一词在出版领域风行。民初城市指南中就有不少以“快览”命名,如世界书局出版的《天津快览》《苏州快览》等。20年代以后还出现了很多名为“日用快览”“生活快览”的历书衍生物,国民党控制的中央图书局更是直接采用了“新国民快览”之名,取而代之的意图流露无遗。
快览自清末至民国的流行,表明日常经验的断裂并未发生在政权鼎革之际。石印行业的广泛参与,意味着由近代城市生活变迁所孕育出的新的出版市场已经成熟。从《官商快览》到《国民快览》,贯穿了日用出版崛起的全过程。这个过程可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的市场竞争尚处于石印行业和快览内部,即石印书商通过出版同质化的文本来瓜分一个相对恒定的市场。第二阶段的竞争主体是书业公所、商务印书馆和一众其他书局。这一阶段,快览依旧保持相当可观的销售规模,但是增长陷入停滞,而商务印书馆通过对日用知识、受众和使用场合的精细划分,推出种类繁多的日用书籍,持续开拓新市场。在这一时期,工商业资本的注入为日用出版的扩张增添了另一重助力。
限于相关研究的缺失,我们暂时无法断言日用出版在近代出版业的崛起中所扮演的角色。但是这一市场的迅速扩张和众多出版商的激烈争夺,至少说明日用出版构成了近代出版业不可忽视的重要面向。而这一面向是以往研究所忽略的。石印与铅印在日用出版领域的此消彼长,正是近代出版业实力变迁的一个缩影。石印书局的出版活动具有保守性,它们倾向于翻刻、出版已经被市场验证的出版物。(54)许静波:《石头记:上海近代石印书业研究(1843—1956)》,第57—58页。这固然和资本规模有关,但是应当指出,1902年商务成立编译所时,其资本规模尚不如几个石印巨头。更主要的原因是,石印书业的经营模式依旧在传统书业的轨道上滑行。石印行业的出版秩序压制了知识创新的尝试,也让石印书局失去了与铅印书局互争雄长的机会。随着版权制度的建立,拙于创新的石印书局日益举步维艰,只能退守没有版权限制的古籍出版领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