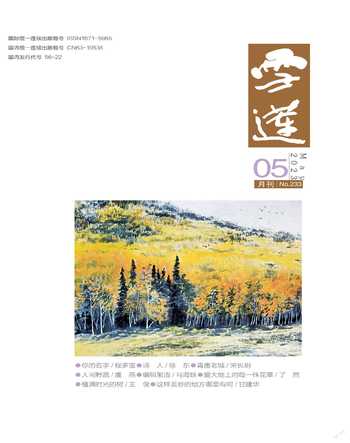青唐老城
2023-08-06宋长玥
僻隅西北,在西宁城已经三十年了,万般世相皆为幻象,其间寥落甚于荒野。心无归处时便无归处。漂游之地,或为故乡,所念在远,或为异乡,唯以妥协飨魂,感恩天赐。
西宁卫城,古湟中地。西汉为金城郡西平亭。魏晋为西平郡。元魏、隋为鄯州,大业中,复为西平。唐为鄯州西平郡、都督府,没吐蕃,号青唐城。宋复建鄯州,崇宁中改为西宁州,元因之。在明洪武十九年,命长兴侯耿秉文率陕西诸卫军士筑之。基割元西宁州故城之半,周围九里一百八十步三尺。
——《西宁卫志》
场景1.尕寺巷口的鞋攤
巷子五六百米深,南头是条窄街,老名儿叫莫家路。如今,街上住的不是莫家后人,杂姓人家把老街挤得很窄了。平常车多,来来往往,剩余不多的古旧气息就越发清淡。
巷口东北角,一块不规则的方形空地,裸出黄土,有些凸凹;东面建了间泥砌的黄砖墙水房,屋顶斜斜的,从远处看,有些耳朵的样子。中午或黄昏,二三居民挑着水桶来买水。一个蓄着花白胡子的白帽子老人收钱,放水,叨几句家常。墙根里放着几盆臭绣球和倒挂金钟,懒懒地晒着太阳,生出些温吞吞的生气。
紧靠水房西墙,摆着一个鞋摊。钉鞋匠年纪三十六七,家在互助农村,腿有点瘸,脸瘦且黑红,戴副眼镜,印象中常叼着根烟,话不多,笑容更少。鞋摊斜对角,是个茶艺,门口也有一大片空地,阳光很好。但鞋匠一年四季决不去那里。他的摊,中午以前,大部分时间被墙影子遮着,夏天凉快,冬天说不出的冷,天天罩在尕寺巷的穿堂风中。
他没有搬到对面的意思。有活的时候,右手戴着一只五指被割去少半截的手套低头忙着。闲下来,偶尔斜着眼,双手抄在袖筒里望着对面的茶艺。茶艺叫古道,名字有老当年的味儿,散发出陈旧和沧桑,很让人心生倦意。这个名字大约在鞋匠的心中是一条越走越远的路,爷爷走过,父亲走过,他走过,儿孙们还要走。路当然开在家乡的地上,庄稼一年黄一回,土房三年五年上一次房泥;月圆的日子,吃几十杯青稞酒,对着月亮想几遍尕妹妹,说不完的快活。
鞋匠身下的一小片黄土和它连着的老家,演绎的生活也许远不是这些。
在尕寺巷口,鞋匠的心事埋在心里,脸上看不见过去和未来,只挂着现在。遇客人有事,催着快点儿,他仍抽他的烟,手下并不加快,多催几次,他不抬头,吐口烟说,你们城里人孽障,日子跑不掉,急啥哩?
有几次中午回家,鞋摊孤零零的摆在墙根,不见鞋匠。去巷子的梁记杂粮小吃店买卤肉,发现他在里面吃饭,一碟泡菜,一瓶啤酒,从从容容,不理会是否有人来修鞋。我笑他娇惯自己,鞋匠说,出门人苦着哩,不能亏待了自己呀。笑一笑,继续吃喝。
前几天,吃过晚饭到煤场对面的一家理发店理发,正理着,鞋匠进来了,看样子和店主很熟,对店主说,理个发,明早儿回趟家。语气里听不出啥,大概鞋匠想媳妇孩子了。
场景2.爆米花的男人
尕寺巷穿过三座楼房,拐两个弯,伸向鸡鸭岭。三个门洞下面各有营生的人。第一个临街,常年摆着水果摊;第二个靠西,是梁记杂粮小吃店,吃客有时排队;第三个门洞在第一个拐弯的地方,东面放着几个空货架,西面,前几天一个男人摇着长方形的小火炉,爆米花。
我在摊儿上买过几次东西,和摊主说过几次话。这个男子中等个儿,体瘦,头发有些乱;话不多,问一句,答一句,一看就是才离开庄稼活儿不长时间的人。他说话的时候稍低着头,很腼腆,不像四十多岁的男人,令我不忍心再问。
摊主从河南来,说家里地少,不少乡亲到外面挣钱,他也出来试试。他说,钱挣得费劲。
爆米花,只是他的一个活儿,还有爆大豆蚕豆瓜子,随着一声响,满门洞清香,庄稼的味儿让人心醉。这时候,他起身,把新爆的一点一点收拾好,行动中透着一些满足。
来爆米花的人不是很多,男人也不心急,依旧一炉一炉地爆,有股庄稼不成年年种的劲儿。
有几次,看见他靠着楼墙,端着洋瓷缸子吃饭,大约是方便面,不像巷口的鞋匠,爆米花的男人从不去小吃店,吃饭时候都守着摊子。饭吃得有滋有味,偶尔出神望着对面的空货架,大概想起了老家。在别人的城市,他的享受不多。
天冷的这几天,门洞里的穿堂风很厉害,我回家时没见着他,以为天晚收工了。有天早回,也没见他,才明白男人挪摊儿了。不知道这个冬天他在西宁的什么地方过,也许回家了吧。
场景3.尕寺巷的夜晚
巷口,细圆的几根长钢筋竖起来,围几大块有些发黑的白布,十来个平米的烤羊肉摊子就搭好了。烤炉的烟向巷子周围飘散,从隐隐袭来的羊肉香味中,尕寺巷的夜晚已经走在地上。
水果摊还摆着,由于暗,第一个楼门洞下,几个摊主从小商店引来电线,挂上了电灯,稍暗的光四周散开,远处亮得吃力。赶着回家的人,脚步多少有些匆匆,巷子里响着凌乱的步子声,人在渐浓的夜色很快模糊了影子。
夜深些,水果摊撤了,烤羊肉摊便现出几点生气,肉香味儿酽得很;摊子上五六食客,忙得女人擀面,男人烤肉,调料滴在烟火中滋滋响。楼上,亮着几盏灯,不知里面内容。
子夜,尕寺巷不怎么安静。常有醉汉的喊叫或少男少女的大声喧哗;有几次,我被破锣似的歌声从浅睡中弄醒,盯着天花板,一腔愤怒,对闹市越生厌恶。
因为贪玩,常夜深回家。有时,并不急着进门,沿着巷子向里走。巷子北头,是座清真寺,年头不短;夜里,只能看个大概,但一轮弯月依然可辨,虽说是金属做的,我仍感觉到那一层薄薄的银粉,铺在地上,映照着我。
后来,听说巷子外边几个晚归的人遭了抢,一个还被伤了身子,再也不敢独自在夜深时闲逛。尕寺巷的夜晚,我少了一份很美的享受。
场景4.深夜候客的人
夜很深了,莫家路上的车比白天少了许多。偶尔驶过几辆,窄窄的街道嘈杂一下又恢复了清净。
看惯了阳光下的街道,觉着夜晚有好处——至少,我在尕寺巷没见心烦的事情,就是巷子东面摆的扭七歪八的货架,隐隐绰绰的影子,也让人嗅到生活的味儿,很亲切。
尕寺巷南口,夜晚常有两三辆出租车候客,司机大约就住在附近,有时候一人坐在车里,抽烟,听广播,并不开车内的灯。昏暗的街灯照在车上,司机的脸明明暗暗,看不见他的表情。有时两三个人凑在一起,说说笑笑,直到客来,才散开,各忙各的。
他们的日子,夜晚滋生的滋味我不知道,这种神秘和好奇,使我经常注意他们。平常,我以为到夜里一两点,会收车回家,实际上,這时候正是他们精神的时候,不时看着零零散散来往的人,准备拉客人。如果有人对他们的期望不置一顾,这些守候在深夜的男人也不失望,继续耐心等。
深夜候客的出租车司机,一年四季重复着这样的日子。没聊过天,也就不清楚他们有没有抱怨。养家是一方面,另外的原因,我想,他们喜欢夜里的生活,夜里的纯粹。在我看来,白天,这条小巷过于琐碎和忙碌,夜晚显得松散和闲适,水泥与钢筋的禁锢淡了,正好补了一些心里的缺憾。
好几次下夜班凌晨回家,还发现有辆车停在巷口,车窗紧闭,司机躺在座上睡着了,我加重脚步走过车旁,也没惊醒他。这个疲劳的男人,在他的梦中出现了什么呢?
场景5.外面的声音跳进六楼
身在高处,听的最多的是风声。尤其秋冬风紧的时候,坐在六楼上,忽忽驰过的风,很容易让我心回草原,随自由的鬃毛在草尖上飞。
可是,我栖身的地方,离真正的马有几百里。而西宁被草原扔在湟水边,疯长水泥和钢筋,六楼就在它们的上面。
有的周六周日,我也去六楼,干活或不干,随心所欲。静坐着,就有声音从窗户钻进来,觉得很有趣,它像个小人儿,绵绵的小手挠着我的心。现在,我听见一男一女走在街上,两人高声相互抱怨;一会儿,声音远了,但我知道,他们的故事还在延续,结局肯定不坏。一男一女,在偌大的人间相遇,不是奇迹,却是缘,有缘,本身就好。
除了风声,也有救护车的尖叫冲过楼前的长江路,心情随之暗下来,为不认识的那个人祈祷;间或消防车一路警笛,瞬时消失在远处。我知道,在这个城市的某个角落,火毁坏了很多人的情绪。夏秋季节,也有警笛呼啸着驰过街道,“让道”的喊叫声不绝,我于是心生厌恶,并鄙视这种破坏常人生活的行为,继而怀疑:谁坏了规矩?
外面的声音跳进六楼,在我的身边环绕,这一群孩子,让我心有所属。
场景6.穿过三角花园
长江路和七一路见面的地方,形成一个上千平米大的三角,种些树和花草,散发着园林味道。大家叫它三角花园。
我觉得它是一处园林,里面铺了方砖小道,砌几个带着花圃的三四人座水泥椅子,四五十棵树。在西宁,有绿色且幽静的空地少,虽有人工制作的痕迹,又缺自然的苍莽,但在原野消失的城市,我喜欢它。
只是花园里的青草越来越少了,在人的脚底下,成片死去。原来的草地上,陈着几条扎眼的小道,如今,我已习惯它的存在,却从不走。这条路,大约是世界上最短的,不过两步,就是人行道,匆匆或悠闲的脚步把这个边塞小城踩得有些乱。
我每天都要穿过三角花园。一早,四五十个老人在花园里练剑舞棍或扭秧歌打太极,大多衣着鲜艳,红衣,白发,把早晨燃烧起来;看东边楼顶的太阳,也想要烧一样。
夏秋的花园要生动许多,几顶塑料桌椅,几顶遮阳伞,一个小茶园就开张了,茶客也多。原先有个老太太摆棋摊,后来,老太太不见了,但棋摊还在,下棋的人围了一大圈,两个人下,十几个看客七嘴八舌支招。经常有个湟中来的小伙子卖酸奶,不贵,一块一碗,吃的人或站或坐,很有趣。你走过去,有股生气围着,让你留恋。
这两天冷,来花园的人少。冬天走在三角花园,自己都有点清冷。昨天晚上下班,经过花园,看见一个小男孩趴在水泥椅上写作业,不时呵呵手,心里便生出酸楚,整个晚上也不快活。
场景7.老木桥上的黄昏
老木桥原名好像叫莫家路儿桥,这是民间的叫法。现在,木桥已被水泥桥代替,人们仍习惯说,那是木桥。
今天,木桥的作用不单是过河,还供人们休息和摆摊度日。落日以前,在桥上闲坐的多是老人,偶有一两对情侣低声细语,更见风景。黄昏,这里有七八个人摆摊,针头线脑,水果蔬菜都有。
摆摊的中间,有个白发老太太,紧靠一排水泥栏杆,一块两平米见方的红布上,摆着鞋垫、鞋绳、钥匙链、袜子、指甲刀等。老太太身子不高,头上裹着大花头巾,慈眉善目。她站在那里,也不吆喝,偶有人从前走过,就殷勤问要什么;对方不搭理,她一点儿不生气,继续站着,似乎不知道累。
我中午回家的时候,老太太早就摆好了摊儿;身边并没有饭盒之类装饭的东西,我疑心她中午是不吃饭的。一九九五年,我离开西宁去兰州谋生;一九九七年母亲去世。办完丧事,哥哥告诉我,他几次中午回家看母亲,发现母亲不吃饭,或吃几块馍馍凑合。回兰州后,心里难受,在朋友父母的空房子里喝了三天三夜酒;朋友以为出事了,进了门,见我醉在沙发上,枕边湿了一大块。
以后,在木桥见老太太,就努力控制自己,加快脚步,向前。
晚上下班,我仍走木桥。此时,木桥已被黄昏没在一条河上,人们走过桥,消逝在兴海路市场更多的人群中。有几次,我看见那个老太太守着摊儿,望着来来往往的人,眼里没有什么内容。我不忍,买了个钥匙链,付了钱,低头快快走了。
场景8.走在莫家路上
老西宁人习惯把兴海路叫莫家路儿。
这是西宁的一条窄街,东西走向,长三四千米,宽不过三十米;东头连着黄河路和一个市场。街窄,来往的车却多,有点儿闹市的雏意。
家在莫家路儿里面,每天穿过它。
刚开始,心有好奇,东张西望,街面的小店和陈设都留在心里;时间久了,有的景象便模糊起来,仿佛不曾存在过。印象中,街道南面有个垃圾回收站,大多时间垃圾堆在外面,很像莫家路儿的一块恶疮,见了几次,就不想再见;脑子里渐渐没了它。前两天路过,发现这里已改造成了一个加工皮鞋的小店。问老板,说有一年多了。出来,回头望,无法把垃圾和皮鞋拉到一块儿。
莫家路儿街两旁,多是店铺,卖肉,卖药,卖日用生活品,像个综合贸易市场,但没有乱哄哄的场景。每日上班,我走北面的人行道,发觉早晨的街坊们步履匆匆,少有像我那样吊儿郎当走路的;也许,曾有人注意过我,但我却不知晓。他或她奇怪:这人走路怎么像赏风景?
快到莫家路儿东头,是一大片待搞基建的空地,围了一人多高的围墙。围墙下面,七八个站大脚的农民蹲着,有的年纪上五十了;身边放着布袋子,装的大概是晌午饭馍馍。早晨八点多,想来不会有人雇,这一点似乎并不影响他们的心情,抄着双手,跺着脚,站在冬天的莫家路儿十字路口。有时,中午我回家,见他们还站着,看着行人,眼里满含期望。
莫家路儿每天都在变,不变的是坑坑洼洼的人行道,挖了填,填了又挖,下面的管道好了,上面人却难行,街坊多有怨气,但无可奈何,依旧高低不平走路;娃娃们摔了,哭两声,不见大人来,抹抹眼泪,继续走。街两边的店铺过不几月就有换主的,储蓄所改成了火锅店,娱乐厅变成了温州姐妹美发屋,如此等等。有的彻头换内容,有的换汤不换药,半死不活的撑着。
从莫家路儿,南可到胜利路,北能抵鸡鸭岭,进而长江路和七一路,东接黄河路,西通高架桥,直达西平高速公路。有时候,走着,我突生怪念头:从莫家路大约会走到非洲去。
现在,任何一个地方,都是生活的十字路口。
场景9.卖大煤的男人
十多年前,入了冬,西宁街头卖大煤的马车慢慢多了起来。嘚嘚嘚的马蹄声,从马路上漫开,撞在街两旁的高楼上,又反弹回来。声音虽弱了些,但回声仍很好听,不过,一会儿就散了。
赶马车的全是男人,装束几乎一样:头戴黄色或黑色鹰翅帽,帽耳忽闪着;上身着一件羊皮袄,腰里勒着一根麻绳或草绳;下身无一例外穿大裤裆棉裤,颜色都深。许是捡煤的缘故,他们的脸上,盖着薄薄一层煤灰,只有两个眼睛,明啾啾的,生活的内容全在里面。
卖大煤的男人们,大部分时间走在小街小巷;嘴肯定不闲着,不时“卖大煤——”“卖大煤——”地喊几声。有买主,讨价还价,讲好了,帮买主把大煤送过去。卖掉一马车大煤,要耗掉一天或几天。
我在小饭馆门前和居民区经常看见他们,脸上不见高兴或失望,一家一家的推销大煤。如果运气好,店家把一车煤全要了,男人们便喜滋滋的往店里搬煤,好像做了一笔大买卖。记忆中,这样的场景不多,从这家出来,进那家门,倒常见;他们有足够的耐心,让一车大煤变成几张钞票。
往往在清晨,这些卖大煤的男人们就开始了一天的功课,而在晚上,有时我还看见他们行走在街上。车里或多或少拉着剩余的煤塊,越走越远的身影,看上去特别孤单。
记不清哪年冬天,走宁张公路去甘肃,大约是早上五点,快到大通的时候,见好几个男人在公路上往马车里装大煤。后来,和几个卖大煤的男子聊过几次,说天没亮出门,那是常事;晚了,赶到西宁,会耽误生意,有时还进不了城。男人们感叹城里烧锅炉取暖的多,大煤不好卖。可能是这样,有一次,我确实看见一个卖大煤的男子拿煤换中午饭吃,幸好,饭馆老板没拒绝。那男子的晌午,也就是一碗面,两个饼。而我见的另一个卖大煤的男子,却未了心愿:他想用煤块换几根红头绳,对方没答应。
现在,西宁的街道已不允许马车走了。敞开的城市,有些人永远进不来。
场景10.流汗者
一条条道路通向西宁。路上,走满了怀揣掘金梦的农民。
在他们的眼里,敞开的城市是一片庄稼味儿被深埋在心底的田野,是另一个版本的村庄。但这些粗手大脚的男人和女人们,很快在街头发现,脚下的土地散发着陌生,钢筋和水泥构筑的魔块以及异样的目光正在粉碎他们进城的自信。
接受农耕文明的心灵被工业文明巨大的创造力和破坏力撞痛了。茫然和隐忍在城市的角角落落随处可见。在遭遇了冷漠与有限的接纳后,街头的盼望者明白,他们在城市,这个走得太远以致有些迷失方向的地方,生存的手段仅剩出卖苦力。这是绝大部分农民赚得第一桶金必须迈出的一步。
在早晨或黄昏经常看见他们,或蹲在地上,或抽着纸烟,或在一处工地挥汗,他们的行动就是他们的身份证。他们以等待希望和承受疲劳的姿势,认真过着每一天,远处村庄的炊烟和用黄土夯实的庄廓,是支撑这些劳动者挺进城市源源不断的信心。
我的眼光随着他们游动的身影穿行在这个城市的大街小巷;在一个寒冷的早晨,冬天隐隐渗骨,零零落落的雪花落在西宁,几个人蠕动在一幢大楼的废墟上。他们挥着镢头,刨着砖头,原先矗立的大楼成了废砖的小山;还没拆完的一面墙,悬孤孤的立着,上面是一孔孔拆去框子的窗户,那种张望有现代派的味道。但是,它显然不能回答要拆除它的农民们在城市的困惑。
记不起去年夏天的哪一天,在长江路的一处工地上,暮色四合,一家人忙着拾捡白天拆下来的废砖。男子四十多岁,不断地把砖头从埋得深的地方挖出来,一双手套已烂了十指;女子盖着绿头巾,坐在废墟上,用砍刀使劲砍掉废砖上面的水泥。车道上,静静的停着手扶拖拉机;偶尔有水泥里遗留的钢筋,男人满心欢喜,费劲地剥。这些砖头和钢筋过不了几天,在他们的手里变成了或多或少的钞票。
拆楼的农民们用双手清掉了废墟,不久,新的建筑在他们苦过的地方站起来了,他们的劳动,换来的不仅仅是钱;这些人流了汗,流了血,有的甚至把命留在了那里,这使我对他们心怀尊重——走出了从农村到城市的一步,这条路他们也许一辈子也走不完。
【作者简介】宋长玥,青海人,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在《诗刊》《人民文学》《星星诗刊》等国内100多家报刊发表诗歌、散文等文学作品,部分诗歌入选数十部选本。出版诗集、散文集9部(其中一部合著)。获20多项文学奖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