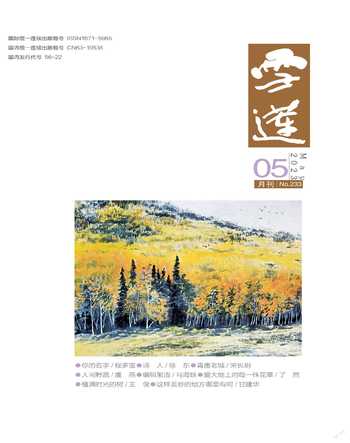海棠依旧
2023-08-06程相崧
1
在病人和家属争吵时,我们这些保姆是不该插嘴的。不仅不该插嘴,听都不应该听。这是行业规则。俗话说“久病床前无孝子”,吃药打针,做各种检查治疗,都需要不小的花费,儿女之间难免争争吵吵。这种事儿,都司空见惯了。这家人还好,从我伺候老太太,晚辈们遇到事儿都商商量量,相安无事。我这样的看法,也许跟对这家人的第一印象有关。这家人給我的好印象,首先来自于他们的外貌。在晚辈里面,男人几乎都帅,女人几乎都漂亮。儿女不用说了,媳妇和女婿也是一表人才。尤其是那个叫小亮的孙子,身材高挑模样好看,简直是从画上下来的。模样好,嘴儿又甜,总是王老师王老师地叫我。我们这行当看人,当然不只凭外貌、只凭言谈举止。这是我个人的毛病。我年轻时就这样,还因此吃了不少亏。当然,他们除了长得好,还都有体面的工作,都是些有身份的人。
我刚照顾老人时,她还住在呼吸科,是当作普通肺病办的入院手续。她的真实病情,大家都没有告诉。现在,当然转进了肿瘤科。这地方条件不错,是一处独立院落,安静优雅,适合疗养。在老太太病室的窗外,正巧有一棵海棠树,开了满树的花,引了不少的蜂蝶。我第一天就注意到了那棵树,因为我家也种了一棵海棠,就在农村院儿里,但比这棵大。老太太身材高挑,满头银发,皮肤松弛得厉害,但还蛮白皙。可以看出,年轻时肯定也是一个美人。我刚照顾她时,老人情绪还好,跟我和大夫护士说说笑笑。她自己只当是胃里出了毛病,住几天院,打几天针,好了就可以回家。在转入肿瘤科时,老人的儿子找了关系,让医生和护士都对她保密。
老太太是国营变压器厂一名退休干部,有些性格。在呼吸科,因为按照规定没法给她使用麻醉药物,抑制不了疼痛,她曾朝大夫和护士们发过脾气。到了这里,疼痛控制住了,她情绪才慢慢好起来。她有时跟我聊一些过去的事情,或者让我给她打开床头的电视,看一会儿新闻。老人关心国家大事,惦念着非洲和美国人民的生活。我总觉得,老太太未必不知道自己的病情,只是不愿挑破,跟大家心照不宣。老人儿媳也已退休,却不怎么过来。据说,年轻时跟婆婆有过一场矛盾。她来了,我也不让她伺候,老太太倔强地说。不几天,她家的情况我就摸熟了。老太太儿子在县人事局工作,女婿是教育局副局长,女儿从前在统计局,现在已经内退。孙子小亮刚刚大学毕业,临时在爸爸的单位,连着考了好几年的公务员,都没考上。今年又参加了考试,结果还没有下来。
他们一家人都很信任我,白天一般都不过来,只是到了晚上,偶尔才过来跟我一起伺候老太太。那天是个周末,本应该女儿和女婿在这里陪着老人。但是,儿子的同事打电话说要探望一下,他们一家便开车匆匆赶过来了。在探望的人离开之后,晚辈们少有地聚在了一起。尽管女儿和女婿催促着他们一家回去休息,可儿子一家仿佛觉得既然来了,马上走总有些不太好。儿子便在母亲床头的小马扎上坐下来,抓着她的手,又望了望大家,笑着说:我就是愿意跟妈在一起。那边儿媳妇跟孙子看着这样的情景,也都感慨地说:人别管多大岁数,在老人面前总还是个孩子!
在这其乐融融的气氛中,我也附和着笑起来。但是,老太太的眉头却紧皱着,显得一点儿也高兴不起来。儿子也看出这一点,关切地问:妈,我看你心里有些不高兴。你还有什么未了的心愿,想给我们安排吗?在此之前,为了不给老太太压力,大家几乎忌讳提到“病”这个字眼。此时,儿子突然问出这话,让大家感到既意外又紧张。儿媳妇本来是要去刷碗的,忽然站住,拿眼睛挖了丈夫一眼,仿佛是说:哪根筋搭错了?怎么扯到了未了的心愿?然后又转过身来紧张地盯着床上的老太太。女儿和女婿也从陪人床和陪人椅上站起,凑了过来。
老太太叹了两口气,才努力睁开了微闭着的眼睛,无力地望望儿子,又扫了大家一眼,叹口气嘟囔道:不说了,说了也没用。这时,大家才轻轻舒了一口气。孙子也趁机走过来扯扯爸爸的衣角,催他快走。但是,做儿子的却不为所动,坚持问道:您老人家有啥心愿,就说一说吧。这时,老太太仿佛才下定决心,一字一顿地说:我还是那句话,我死后不想去张庄。这时,先是儿媳妇变了脸色,不耐烦地拉了丈夫一把。接着,女儿在那边也插嘴说,这都已经说定了的事儿了,怎么又讨论起来?小亮也按捺不住,走过来给老太太掖了掖被角,说奶奶你累了一天,也困了,赶紧睡吧。然后,他转身按照惯例叮嘱了我几句话,就拉起他的爸爸,把他推搡着,推出了病室的门。
他们出了门,却并没马上走。我给老人伺候小便的时候,还听到他们在外面走廊上小声争吵着什么。老太太耳朵一点儿不聋,肯定能听到他们的声音,却也并不吭声。她让我伺候着解了小便,就躺在床上,紧紧把眼睛闭上了。她明显情绪有些烦躁,但十几分钟过之后,还是睡着了。我知道,这是吗啡发挥了药力。我出去给老人倒便盆时,看到老太太的女儿和儿媳还在走廊上说着话。据老人说,她们两个平时是最不和睦的,这时不知为何,竟然站到了同一战壕里。
你说他问那干啥?他就是闲着多事儿!从儿媳的话里,我听出她正在埋怨丈夫。她们看我出来,声音变得更小了,叽叽咕咕。我从洗手间出来,她们还在斗着头儿小声地议论着什么。女儿说,事已至此,也没别的办法,只有瞒着了。女儿性格爽朗干脆,说话的声音平常也就高些。儿媳妇听后却摇了摇头,用手捅了捅大姑姐的腰,小声地说:瞒着她怎么能行?说是总得说的。要不然,她到了那边一看不是自己想去的地方,回来缠着我们怎么办?
我是后来才知道,张庄就是老太太农村的婆家。她作为张家的儿媳妇,去世之后自然应该被送到那里,埋到张家的林地。但是,老太太却固执地不愿回去。这件事儿在她生病住院之前一家人就曾经商量过,最终老太太妥协了。晚辈们的理由是,因为老太太的丈夫在很多年前就已去世,埋在了老家。老太太这时下葬并不能算作是新坟。按照礼数,如果老太太不愿回张庄,唯一的办法就是把他丈夫的坟也同时迁出,再另买墓地安葬。用他的话说,多花些钱也不要紧,多费些周折也不要紧。关键是这样做不合礼数,会让张庄那些族里人笑掉大牙。
2
如果在大城市,我这样的人应该被叫做护工。但是,在我们这小地方还不兴,大家都叫我们保姆。保姆听起来仿佛没护工显得专业。当然,我们干着护工的工作,却并没有受过正式的训练。就拿我来说吧,只是伺候过几位老人,也送走过几位老人,便有了些这方面的经验。尤其是在病人重症晚期,需要做啥检查,大致吃啥药物,各种药的用法用量,我们虽不敢跟大夫护士比,却至少比家属更了解一些。我听说在大城市医院,常年离不开这样的人。我们这里小地方,护工也十分紧俏。因为一般人不愿干这样的活儿,又脏又累,还担着责任。
我之所以乐意干,主要是收入可观,来钱也快。我有过一个男人,年轻时长得帅,相亲时我就是看上了他这一点。我后来才知道,帅不能当饭吃。我前面说过了,我年轻时看人迷恋外表,吃过亏,指的就是这事儿。我男人仗着一副好皮囊,好吃懒做,跟镇上的剧团四处浪荡,慢慢染上了吃喝赌的恶习。后来,在外面还有了女人。在村里,他臭名昭著,走到哪里,大家都会像躲瘟疫一样躲开。村里没有一个人不恨他,不讨厌他;没有一个人不同情我,可怜我。
在孩子三岁那年,他最后一次回来,跟我吵了一架,还动手打了我,比以前更狠。现在我脸上还有那次他用腰带扣留下的疤痕。他是回来跟我离婚的,但是我死活不肯!我并不是缠着他,我是打心眼里真心爱他。这多么怪!他那么坏,可我还是爱他。我们吵了一架,他离家出走了。他说再也不会回来见我了。我不知他后来去了哪儿,却可以断定,他没跟原来胡搞的那个女人待在一起。因为,几个月之后,那个女人挺着大肚子来找过。这真是活该,现世报!
我没有再嫁人,而是一门心思养育儿子。现在,他也大学毕业了,学的师范专业,在一所农村中学任教。为了娶媳妇,在城里我给他买了一套三室一厅的房子,拉了一屁股的账。那时,儿媳妇在城里开衣服店,说俩人两地分居,没有车不方便,又贷款买了车。现在很多人问我盼不盼着抱孙子,说实话盼,但不敢让他们要。我的想法,是让他们好好干上两年,还还贷款,经济压力没有那么大了再要。那样的话,我也能腾出空来喘口气儿,再帮帮他们。现在,农村种田不挣钱,我便把几亩地租了出去。家里原来还养着几只鹅的,后来也卖了,整个院子里唯一的活物就是院子中央的那棵大海棠树。
我出来在医院干了几年保姆,为的就是多挣些钱,补贴一下他们。两个人结了婚,不要孩子总是不行的。等他们有了孩子,我就等于被捆住了手脚,出不来了,也啥都干不成了。
这个行当除了挣钱多挣钱快,还有一个好处,就是可以结识一些有本事的人,积攒一些人脉。我去年伺候过的那个老太太的家人,后来就帮了我们的大忙。那老太太的儿子是市联通公司的副总,平时工作忙,只在周末才开着奔驰来看母亲。他出手大方,为人也豪爽。那时,我儿媳妇在步行街开小店,不挣钱,还得一天到头辛苦伺候着。我觉得这是一个机会,便在伺候老人时,做得格外用心。开始我上白班,晚上老人的女儿照顾。他们安排我早晨从食堂给老人和陪人买饭,但我每天早晨都是去菜市买来黄颡鱼、或者牛尾之类的,给老人炖汤。
这样伺候了一段,老人就离不开了。在走之前,她对我十分依恋,如果我不在,她每次小便都会尿湿床垫。说实话,我对待自己的亲妈都没有这么尽心过。有一次,老人的痰涌上来,憋得直瞪眼,值班护士又忘了带吸痰器,一时手忙脚乱。我二话没说,就口对口给她吸上了。这事儿说起来还有些反胃,可当老人起死回生,又喘过气来之后,在场老人的女儿和儿子都哭了。他们紧紧抓着我的手,一个劲儿地说:王老师,您是娘的救命恩人!在老人走后,她的女儿抱着我痛哭,喊我王妈妈。她说王妈妈,就算我们这些做儿女的,对母亲都没有这么尽心。母亲摊上你这样一个保姆,这辈子值了!
说实话,跟老人相处这么长时间,也处出了感情。我想,要不干脆再送老人一程?现在的年轻人,虽说有文化,懂得多,可一摊上家里有老人倒头,就忙了手脚。我帮着给老人净面,穿衣,又帮着入殓下葬,一条龙服务。在埋葬了老人之后,他们一家请我们一家人吃了一顿饭。不是请我自己,还有我的儿子和儿媳妇。这不就处成朋友了吗?吃完了饭,结完了工钱,还特意给了两千块钱的小费。分手的时候,大家都有些恋恋不舍。
那老太太的儿子抓着我的手说:王妈妈,今后家里有什么事儿需要帮忙,尽管开口。我犹豫了一下,有些不好意思地提出了儿媳的工作。那老总是个爽快人,三天之后就给我们打来电话,说已经给县里联通公司说好了,给安排了一个话务员的工作。具体干啥?你们经常收到的一些推销业务的骚扰电话,就是她们打的。工资虽然不高,却整天对着电脑,有闲工夫。她原来的小店不干了,货却没少卖,她把生意都搬到了网上。
据我观察,现在这一家人如果利用好了,说不定会对我儿子的前途有很大帮助。
老人的儿子在政府部门,女婿是教育局领导,那可是我儿子的直接上司。这样的资源不用实在可惜了。我在这老太太身上花费的心思,绝对不亚于去年那个老太太。当然,跟去年不同的是,除了讨得老太太欢心,还得让老太太的儿女们满意。现在,他们之间有了冲突,有了意见分歧,我一定得抓住这次机会。站好队,解决他们的燃眉之急。
那天晚上冲突后,我能明显感到老人的精神有些垮。她似乎有了什么不祥的预感,又似乎还在为自己的安置问题忧心不已。那天,虽然服用了安定药物,可一晚上还是没有睡好。在平常,我给她喂药时,她都能够积极配合,表现出极强的求生愿望。但是第二天早晨却一反常态。她说王老师,你每天给我喂这么多药,你给我念念说明书,我想知道这药能不能治好我的病。幸好,准备药时,胶囊已经从板上抠下来,瓶装药也从瓶里倒了出来。我告诉她,这些药是处方药,护士按粒儿发的,没有说明书。在我的连哄带骗下,药她还是很顺利地吃下去了。然后,闭上眼睛休息了一会儿,又睁开眼睛喃喃地说:王老师,我知道日子不会太长了。
我不是專业医师,但也知道这时应该多给她些鼓励,少给她些烦恼。我原本应该给她些安慰,甚至善意的欺骗。因为,病人就算猜出了一切,也宁愿从谎言中得到些慰藉。但我没有,我没有主动提到“死”,但也没有岔开话题。我甚至盼望她能谈到这个,并准备寻找机会说服她听从儿女们的安排,不要迁坟。如果我能够成功,无异于立了大功一件。在护士打上点滴之后,我跟老人唠起了年轻时的事儿。我说:您都这岁数了,身材面貌还是这么好,年轻时肯定有不少人追。老人笑笑,叹口气说,从前家里成分不好,三十来岁才找到一个对象,还是个农村人。
她说,他一米八的个头儿,长得帅,对她也挺好。但是,婆婆却有些嫌弃她。婆婆在乡村算个能人,针线和饭食,样样拿得起来。那时,她男人在村里当小队长,跟其他男人一起打场,割麦子。活做得辛苦,女人们便想让他们回家吃口好的。她们都在一起摊煎饼,蒸窝窝,她却笨得连火也烧不着,呛得婆婆直流眼泪。人家蒸的窝窝翻过来像一个小泥碗儿,里面可以装上炖菜,她里面却是实心的。有女人戏弄她,说做窝窝得用蒜臼锤子。将面用手团成小球,再用蒜臼锤子使劲一按,便是一个小窝落。她回家找蒜臼锤子,让婆婆一顿好骂,说她是中看不中用的花瓶儿。
她为张家生了两个娃儿,一男一女。女儿出生那年秋天,婆婆提出让儿子跟她离婚。理由是嫌她连孩子的小衣裳也不会做,连孩子也不会搂,连尿布也不会洗。你男人当时啥想法?我问。他还不是跟他娘一气?老太太说。他们赶我走,可城里的房子都充公了,一处成了大药房,一处成了棉厂的仓库。我连个家也没,往哪儿去?我说离可以,离了婚我哪儿也不去,就死在这里。
他听了这话也哭了。我们虽是经人介绍认识,却一见钟情,感情比现在自己谈的还好。那时跟现在不一样,现在婆婆都听儿媳妇的。那时农村婆婆,可是说一不二。我们商量好了儿女一人一个,春天天气暖和了就去离婚。——我们选择春天,是因我娘家没有个像样的住处,气温上来了,在哪里都能将就。那年春节,好多东西他都不舍得吃,给我留着,让我带回去。什么菜丸子、焦叶儿、蜜饯儿,还有白菜和萝卜。
我们的婚没有离成,因为有一天他进地瓜窖里扒地瓜时出了事儿。你知道,那时没有冷库,农村里储存地瓜都是挖一个深窖。他进去扒地瓜,就没爬上来。那年挖的又是井窖,入口小,窖底深,难往上爬。地瓜窖封了好几个月,里面早没有了氧。我不懂,他也不懂。我带着两个娃儿,给他送了终。婆婆哭着求我留下,至少留下一个娃儿,可我给他烧了五七纸,便带着两个孩子回了县城。
我死缠硬磨,把被棉厂当做仓库的那处院落要了回来。那地方我们现在还住着,后来盖了五间楼房,还有一个很大的院落。在老太太断断续续说这些时,我已经走到窗前。我装作看窗外的那棵海棠,悄悄擦干了流到眼角的泪水。我想起我的男人离家出走后我母亲说过的一句话。她说,在这个世界上,女人的命到啥时候都是最苦的。从言谈间,我能感觉到老太太的尊严和执拗。那天,我没有开口劝她,因为我能感觉到让她改变主意并非易事。
3
第二天傍晚,老人一家又来了。儿子、女儿、儿媳、女婿,还有孙子。这一次,他们说是专门来陪老人的。他们从食堂打来了饭菜,凑在老人的床头,吃了一顿团圆饭。老人胃里不舒服,吃得不多,但跟孩子们在一起还是很高兴。收拾了碗筷,把床上吃饭用的小桌子撤去,老人说让人在她身后塞一个枕头,她要倚着看一会儿电视。电视打开了,孙子拿着遥控器找她平常爱看的法律频道,却不知为什么没有找到,只得看了一会儿戏曲频道。上面演的是一台什么戏曲选秀节目,咿咿呀呀地唱一段,评委们点评一段。老太太看着看着,便有些没精神。我们都说,将枕头撤了,将床头摇下来,让她休息休息。
这时,老太太却使劲摆了摆手。说你们今天晚上来的意思,我心里明白。别白费心思了。我这辈子就有这一个心愿,就当是我求你们行吗?
这时,儿子脸上显出尴尬神色,说妈,这个不是求不求,这个不合规矩。这话让老人有些生气,说你懂什么?我带着你们姐弟俩回到城里,连个落脚的地方也没有,有谁帮我?是我从公家死乞白赖地要来老院子,也就是你们住的那处。要是合规矩,你不知道在哪个旮沓喝西北风呢。老人因为情绪激动,咳嗽起来。我赶紧凑过去帮她拍背,扶她躺下。这时,女儿又凑过来想要说什么,老人情绪更加激动了,拍着床说:王老师,你把他们给我赶出去!黄鼠狼给鸡拜年——没安什么好心。
在我的劝说下,他们几个终于离开了。我把老人哄睡,打算在陪人床上躺下来休息一会儿。刚铺好垫子,就听见有人敲门。我以为是护士,转过脸看,却发现门外站着的是老人的儿子。他说王老师,我们想请你到医生办公室里聊一聊。
这时,一名护士进来代替了我的工作。我便跟着他去了医生办公室。办公室里没有医生,也没有护士,在亮若白昼的日光灯下,我有些惴惴不安。他们却很热情,女婿甚至还特意给我搬来一把椅子。我坐下之后,儿媳笑着说:王老师,不怕你笑话,这件事儿你也看到了,应该也了解了个八九不离十。
我说:老太太既然有这个心愿,如果能,就尽量满足她吧。
王老师,你不知道其中的原因,小亮插嘴说,事情比较复杂,还有隐情。
我听了他们的讲述才知道,原来,年轻人坚持不给老人迁坟,执意让老太太走后埋在老家,除了不合礼数,还另有原因。前些日子,小亮考完公务员,去观过一次香。所谓的“观香”,其实是一种占卜方式。请有道行的人通过观察香燃烧发出的火焰、烟雾和燃后留下的形状,判断命运的吉凶,预测某事的结果。那次观香,原本是想要问一问公务员考试的结果,也不知怎么就说到了奶奶的病,说到了将来的安葬。据那位有道行的高人讲,祖坟是绝对不能够迁的,不然就会对小亮这一代孙子辈儿的人不吉利。
王老师,您这个年龄的人见多识广。您给我们拿个主意,这事儿应该怎么办?老太太的女婿凑上来诚恳地问。
我心里有些诧异,没想到他们都有文化,尤其小亮又年纪轻轻,竟然对这个深信不疑。从理性考虑,我其实更赞成老太太的选择。她跟婆婆有矛盾,丈夫又走得早,一个人在城里生活,长期守寡。在死后不愿意去一个陌生的地方實在是合情合理。但是,从年轻人这边考虑,常言说“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都想图个吉利。小亮参加了公务员考试,就算考上,也只是刚刚踏上仕途。老太太的外孙女也是刚刚提了副科级,算是当上了单位的一个小中层。以后的日子,还要一步步地往上走呢。
这事儿草率不得,我们才都想起了你。老太太的儿媳妇望着我很诚恳地说,现在,老太太跟我们是完全地对立起来了。她目前信赖的人只有你,也只有你的话,她还能听得进去些。我们刚才就想着,能不能请你凑机会跟老太太说一声,劝一劝她。
如果能成,我们可以加钱。老人的孙子小亮顿了顿说。
如果能成,以后王老师需要什么帮助,尽管找我们。老太太的女婿也笑着温和地说。
我站在那里,像是掂量着他们的话,权衡着该如何选择。其实,我早已让他们的话打动了,尤其是女婿的话。我儿子在一所乡镇中学代课,每天早晚来回四五十多里,尤其到了阴雨天,很不方便。这位局长要能想想办法,把孩子调到县城,安排在某所学校,那就再好不过了。
他是教育局副局长,我儿子就在他手底下当差。我犹豫了半天,最后还是不好意思地把儿子的事儿说了。我的话还没有说完,那位女婿就摆了摆手,笑着说,你儿子可以正常参加明年的教师编制考试,我相信他,好好做做准备,一定能行。
我琢磨不出他的意思,到底是帮,还是不帮。但说了总比不说好,说不定明年真能帮上呢。
4
我受命之后,便一直在找机会说服老太太。有天晚上,老人睡不着,我便陪她聊了起来。开始说儿子,说女儿,说小亮,还有在北京某机关工作的那个外孙女。她说,从男人走后,她就一个人扛着这个家,从来不敢怠慢。现在,她终于可以放下担子了。我正犹豫着是否该跟她扯一扯墓地的事儿,没想到她却先开了口。她说王老师,我是说不动那些年轻人了。你能不能帮我去劝一劝他们,我实在不想回去,让他们随便给我找个窝儿,让我和早死的男人安安静静地待着去。
我朝着她无奈地笑笑,说这个想法我完全能够理解。可是常言道“叶落归根”,对于一个女人来说,丈夫那里就是你的归属啊。我准备着老人会反驳,但她没有。老太太沉默了一会儿,最后喃喃地说:我就是不想回去。
在以前,我们对于老人是连“病”这个字眼儿都不愿提起。现在,却不得不直白地谈论安葬,每当此时,我都感觉有些别扭。接下来的几天,在年轻人的电话催促下,我又做了幾次老太太的工作,最终也没有成功。我有些沮丧,心想请老太太女婿帮忙的事儿,恐怕只能放弃了。有一天晚上,我看老人睡不着,又忍不住提起了老人墓地的事儿。老人听着,忽然慢慢地睁大了眼睛。她仿佛使尽了浑身力气,一字一顿地说:
王老师,张庄,我是坚决不会回去的!
她说完这句,又轻轻喘了几口气,才继续慢慢说话。
她说:我那天告诉过你,婆婆嫌弃我,让我男人跟我离婚。我还告诉过你,男人是下窖扒地瓜,因为里面没有氧憋死的。但是,我没有告诉你,那些地瓜,他是扒了想让我离婚后带走的。他给我准备了两大口袋东西,丸子、窝窝、大米、小米、白菜、萝卜。那天,我们说好了第二天就去离婚,他忽然想起来,我跟孩子都喜欢吃地瓜。他要去给我们扒几个地瓜。
他出门去了,我就在床沿上坐着哭。那窖是用一块磨盘盖着的。我听到了他挪动磨盘的声音。然后,他衣服“刷拉刷拉”蹭着窖壁下去了,最后是跳下去发出的“咕咚”声。我知道他下去了,却也没想很多。过了一会儿,我听到他在里面“哎呦”了一声。我上过学,知道狭小封闭的地方没有氧。但是,我当时心里乱得很,没有想到及时地去救他。我觉得他不会出事,而且就算出事我也不怕!我豁出去了,心想大不了一块儿死!我那时没有想到一对儿女,我把他们彻底忘了。
我在外面等他出来,等了一个钟头,他也没出来。我坐在那里,泪干了,浑身冰凉。我感觉到死亡在逼近他,也在逼近我。我蹒跚着跑到窖口边,低头朝里喊了两声。我的声音“嗡嗡”的,下面没有一点儿动静。
那时,我一点儿也不害怕死。我只是想,他死了就好了。他前脚死,后脚我就跟上。我坐在地上,盘算着自己不久后的死,想着各种各样的死法儿。那会儿,我只有一个死的心思。我没有赶紧找人去救他。我甚至想,就算他爬了出来,我也要用砖头往脑袋上给他一下子。
我后来喊来人时,他已经不行了。我给他披麻戴孝,给他送了殡,下了葬。那时,我才看到了我跟他的一对儿女。我不能把他们留给婆婆,留给张家。我好悔恨,悔恨自己只想着死,竟然忘了一对儿女。开始,婆婆想把两个孩子留下,将我扫地出门。我哪里肯?
后来,她又想留下其中的一个,为张家延续香火。我当然也不同意,做梦去吧!我把两个孩子都带在身边,牢牢带在身边。我把他们一个个养大,养得水葱样。这些年,我扫过街,掏过粪,后来终于在变压器厂找了个正儿八经的工作,从缠线圈做起,做到质检,又到车间经理。
我不后悔没有救他,救了他,他也要跟我离婚。他迟早是人家的。现在,他是我的丈夫,唯一的,一辈子的。我只有一个遗憾,就是当年把他留在张庄,没带他出来。当然,回城之后,也有人给我介绍过对象,可我见都不见。我有丈夫,我这辈子只属于他!我老早就有个心愿:我死了,要带他离开张庄,到一个新的地方去。
那天,老太太的话让我的心禁不住微微战栗。这样的场景我太熟悉了,深得像井一样的地瓜窖,上面长年盖着沉重的磨盘,里面的地瓜有的已经腐烂,有的生长出病态的黄色嫩芽。这充满腐烂和生命气息的地方,总让人感到藏着什么秘密。
我并没胜利完成任务。没过几天,儿女又来了。他们态度很坚决,轮番上阵,跟老人商量。仿佛说服不了她,就不善罢甘休。开始,老人闭着眼睛,脸上显出痛苦的神色。儿子抓着她的手,她却有些厌烦地慢慢将手缩了回来。最后,像是实在没有办法,她看了我一眼,跟年轻人们说:我们都是局内人,只有王老师一个外人。要不,我们就让王老师给评评理,拿个主意?
我看看老太太,又看看他们的亲人。我从来没有感觉到自己像现在这样重要。我感到喉咙干涩,吐不出字,说不出话。我转过脸来,尴尬地望了一眼那位在教育局任副局长的女婿,最终还是开了口。我说:这是……这是老人的最后一个心愿了,孩子们应该答应她!
我的声音很低,嗫嚅着。
我的话结束了那场战争,也结束了我的保姆生涯。第二天,他们给我结清工资,将我辞退了。我收拾行李离开时,老人服了吗啡,正在沉睡。
这是我的最后一单生意。
我有时会想起那位老太太,想起她那不近人情的临终遗愿。我想,在我将要离开人世的那天,也许我的要求会让家里的年轻人们感觉更不近人情。我要让他们把我埋在院子中间的那棵海棠树下。那棵海棠树,是我男人离家出走之后种下的。种树的地方,原来也是一个储存地瓜的井窖。
那时候,这样的井窖很多,几乎家家都有一个。
我男人离家出走后的第二天,那地瓜窖就突然坍塌了。我便用土将它填平了,然后在上面种了一棵海棠树。如果在我将来死后,能埋在海棠树下该多好啊。那样,春天一来,我头顶上就会有满树的花,满树的蜜蜂和蝴蝶。
【作者简介】程相崧,1980年生于山东金乡。中国作家协会会员、第八届全国青创会代表、第五批齐鲁文化之星,山东省作协小说创作委员会委员、山东省作协第六批签约作家。发表小说、散文100余万字。作品散见《十月》《作家》《山花》等,部分作品被《小说选刊》 《中华文学选刊》等推介。小说集《金鱼》入选中国作协“21世纪文学之星丛书2018年卷”,并荣获第五届叶圣陶教师文学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