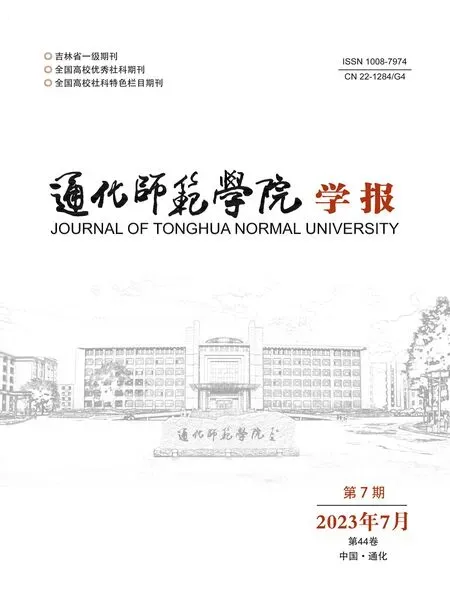明代小九卿身份考析
2023-08-03孙圳
孙 圳
九卿之称,古已有之。自秦汉以来,历朝多以不同的官职衙门充“九卿”,至明代仍沿袭不辍。随着时间推移,明代的九卿又变化为大小九卿。虽然九卿一词源远流长,且明代自皇帝至大臣均常以此指代部分官员或衙门,但是大小九卿究竟是指哪些人、哪些衙门,终明一代却并无明文规定。一般来讲,明代的大九卿指六部尚书以及都御史、通政使、大理寺卿,亦可指上述九个衙门(大九卿衙门),这基本已经形成了共识。而小九卿所指则众说纷纭,莫衷一是。直至当今,学界不少专著仍只引诸多说法中的一种,不作辨析。①目前笔者见到有学者专文考证了清代的九卿,见王道瑞:《清代九卿小考》,《故宫博物院院刊》,1983年第2期。但是,小九卿显然在明代政治生活中有极大价值,理清小九卿的指代是对明代政治制度史的诸多细节的有益补充。因此,本文拟对明代文献中关于小九卿的疑问及解释作梳理,辨析各说的正误,并探究小九卿身份争议背后所反映出的问题。文中所言,难免有不妥之处,敬请方家指正。
一、小九卿身份问题的提出及解释
在明代的文献记载中,小九卿的概念较早见于吕柟《朱子抄释》中的释义:“释:后世内而大小九卿,皆设司务典簿等官,外而省府州县,皆设经历簿史等官,其意深矣”[1]369。吕柟自序该书刊于嘉靖十五年,则该说法在嘉靖十五年之前已经出现。不过在嘉靖之前的文献之中,笔者却并未找到提及小九卿者,因此初步推断该概念出现于嘉靖时期。由于小九卿概念出现较晚,因此嘉靖之前的明人并不能关注到明代小九卿的身份问题。较早发现这一问题的,是万历时期的沈德符。《万历野获编》载:
本朝以六部都通大为大九卿,不必言矣,但小九卿其说不一,或云太常、京尹、光禄、太仆、詹事、国子、翰林,而益以左右春坊,是为小九列衙门。或云詹事、春坊为东宫官属,不宜班之大廷,当以尚宝、鸿胪、钦天足之。或云鸿胪仅司传宣,非复汉晋大鸿胪之职,钦天仅掌占候,亦非秦汉太史令之职,且皆杂流世业所窟穴,只可与太医院、上林苑等耳。众说纷纷,莫有定论,即有公事会议,奉旨有“大小九卿公同”之谕,亦竟不知何属也。近闻之侍从诸公,则以太常、詹事、京尹、光禄、太仆、鸿胪、国子、翰林、尚宝定为小九卿,不知始自何时。[2]435
这段材料表达的信息很多。沈德符在文中不仅提到了小九卿身份的问题,还指出了时人对小九卿的不同解释。其一,小九卿为太常、京尹、光禄、太仆、詹事、国子、翰林及左右春坊。其二,去掉詹事和左右春坊,加入尚宝司、鸿胪寺、钦天监。其三,去掉鸿胪、钦天,加入太医院、上林苑监。各说均有一定的理由辩驳。最后,沈德符又通过“侍从诸公”之口,得出小九卿的最新解释为太常、詹事、京尹、光禄、太仆、鸿胪、国子、翰林、尚宝。因此,在沈德符所在时期,关于小九卿的身份已存在着许多不同的说法,且各说均不能使人信服。
除了沈德符以外,清人阮葵生亦提出该问题,不过他对小九卿的解释与沈德符基本相同。[3]74此外,明代文献中对于小九卿仍有其余解释,为方便比较,笔者将包括《万历野获编》在内的不同解释列为表格(表1)。①除《万历野获编》外,其余分别引自张岱:《夜航船》,卷6,《续修四库全书》子部1 135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 年,第589 页;张岱文中只有8 个,并无尚宝,但是其文中言“太常太仆光禄鸿胪上林苑等卿”,京官之中,除上述衙门外,其余称卿者,只有大理寺、尚宝司,显然此处应指尚宝司卿。但是张岱文中的上林苑正官并非称卿,而是称监,此又是矛盾之处;璩昆玉:《新刊古今类书纂要》,卷5《仕宦部·九卿》,转引自龚延明:《简明中国历代职官别名词典》,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16年,第63页。

表1 明代文献对小九卿的不同解释
可以看到,诸多解释中,对太常、光禄、太仆列为小九卿均无任何异议。其余诸说的异议主要在于六部都通大佐贰官、春坊、京尹、翰林、詹事、鸿胪、国子、尚宝、钦天、太医、上林各衙门。
这里需要注意的是,解释四“侍从诸公”所提及的小九卿。“侍从诸公”将这九个衙门定为小九卿的依据或与推升京堂的资格有关。据嘉靖《吏部职掌·文选清吏司·开设科》记载,有资格被推举的京堂官有通大衙门四五品官以及太常、京尹、光禄、太仆、詹事、国子、鸿胪、翰林、尚宝这九个衙门的主要堂官,通大作为大九卿衙门,剩余的九个衙门恰好与“侍从诸公”的解释相同。因此,“侍从诸公”的解释,有吏部条例作为依据,很有可能是最为官方的解释。不过该条解释的依据虽然权威,但其余的衙门同样有一定的证据支撑,且小九卿的身份并未像大九卿一样曾被官方广泛提及,几成制度。因此,我们不妨将沈德符所言的“侍从诸公”的解释暂定为官方解释,其余解释则定为私人解释。
以上观之,沈德符所言“众说纷纷,莫有定论”诚然道明了小九卿解释纷杂的情况,诸书对小九卿的解释均不尽相同。表1中的六种解释,或许并未穷尽所有文献,不过其中所包含的衙门,已经涵盖除大九卿外绝大部分独立的文职京官衙门。该范围同明人对九卿(大九卿)的定义范围一致,应该是可信的。
二、小九卿衙门诸说正误考
上文已述,明代文献关于小九卿的诸多解释中,对于太常、太仆、光禄三者均无异议,故而对这三个衙门暂不作辨析,仅考证其余诸说涉及的衙门是否为小九卿衙门。
(一)非小九卿衙门
可以证明并非小九卿者共有三个,分别为六部都通大佐贰官及左右春坊。
首先是六部都通大佐贰官。六部都通大的正官为大九卿已无异议。明代的大九卿,存在广义与狭义两种说法,所谓狭义,自然只包括六部都通大衙门正官,如尚书、都御史、通政使、大理卿。而广义者,则又指六部都通大衙门堂上官,包括侍郎、副都御史、大理少卿、左右通政等。因此,如果将六部都通大佐贰官定为小九卿,则势必会和大九卿衙门堂官的身份冲突,显然是不合理的。
其次是左右春坊。按明朝制度,左右春坊各设大学士、庶子等官。沈德符文中以“詹事春坊为东宫官属,不宜班之大廷”一句认为詹事春坊官是辅导太子之官,不当列为小九卿,显然未抓住症结所在。詹事后续再作讨论,此处专讲春坊官。春坊官虽为太子属官,但是其本身属于清秩,后又多为翰林官员迁转之用,无论其地位还是品级,列为小九卿都是无妨的。而其之所以不能列为小九卿,真正原因便在于它不是一个完全独立的衙门。《明史·职官志》记载:
詹事府。詹事一人,正三品,少詹事二人,正四品,府丞二人,正六品……左春坊,大学士,正五品,左庶子,正五品,左谕德,从五品,各一人……詹事掌统府、坊、局之政事,以辅导太子。[4]1783
即左右春坊虽然有着自己的独立名称,但是并不是完全独立的衙门,从隶属关系来看,应归属于詹事府管理。既然可以证明春坊官并非完全独立,而是隶属于詹事府,即使真列为小九卿衙门,詹事府也可囊括左右春坊,而不必将詹事与春坊官并列。春坊官非小九卿,此亦确证。
(二)小九卿衙门
上文已对非小九卿的诸衙门作辨析。本节则对有明确证据佐证为小九卿的衙门进行考证,这些衙门是国子、尚宝、京尹、鸿胪、钦天、太医。
关于国子、尚宝、京尹为小九卿的证据,朱国祯《涌幢小品》言:
六部不相统摄,小九卿体杀各部,而事与之关。如光禄则关礼部,先年光禄卿崔志端、陈俊,南光禄卿牛凤以厨役事屡与礼部争,言本寺非礼部之属,文移往来不应自大,封还劄付,下部详议至参奏受屈。由此观之,要见小九卿如太仆则属兵部,国子监、鸿胪、尚宝俱属礼部,京兆无所不属矣。近年郭明龙为南祭酒,李九我为南少宗伯署事,郭还其劄付俱用咨文,二公同年而郭强甚,李不能抗,亦一变也。[5]302
这段材料的本意并非专门解释小九卿身份,而是在于其与大九卿衙门移文往来。朱国祯其人万历时中进士为官,天启时官至大学士,从他所处时代及仕宦经历看,所言的内容应属可信。文中朱国祯先以光禄寺与礼部争执为由,进而指出部分小九卿与各部的关系,其中便提到了尚宝司、国子监及京尹。后朱国祯特举郭正域任南京国子祭酒时与任南京礼部右侍郎的李廷机往来一例,以辩各部与小九卿衙门移文规矩。此亦可佐证国子监为小九卿之一。
此外,朱国祯在同书中又举一条有关大小九卿相遇礼节,“南小九卿除国学外,凡遇大九卿,皆先下轿,俟之至亦下轿,街次对揖,俟大九卿上轿,乃上。大周既转南光禄少卿,相遇不下,对举手而已,至今独光禄用此例,余则否。”[5]504此处国学,即指国子祭酒。不独是朱国祯,明末清初的史玄在《旧京遗事》中同样有着类似礼节记载:“京朝三品大臣乘轿,自四品卿寺、翰林、六科以至御史、部属乘马。然四品京堂乘马,而祭酒班小九卿之列,自顺城街乾石桥以南造朝堂乘马,以北进国学乘轿。”[6]323-324这则材料虽然意在指出国子祭酒的特殊地位,却也提到了国子监是小九卿衙门。
尚宝司可列为小九卿的证据同样充分。沈德符在谈及尚宝司丞一职时便言:“尚宝司丞虽六品,然小九卿之佐,若非首辅任子初授,而以时望自他曹迁者,为清华之选。”[2]241尚宝司为正五品衙门,堂上官有卿、少卿、丞。既然沈德符言尚宝司丞为小九卿之佐,那么尚宝司便应是小九卿衙门。万历时,大学士叶向高在辞免考满恩荫时也提到尚宝司丞一职乃是小九卿官,自己不敢冒领此荫,“委无尺寸功劳可以堪此……至于尚宝司丞,乃清华之秩,列于小九卿,臣子何功何能,而可冒此?”[7]345不仅如此,晚明时期朝廷给予尚宝司堂上官的制诰中同样有类似提法,李光元在尚宝司少卿黄龙光的制诰中便有“尔方与九卿,或迭出以忧国,或更进而用事。”[8]473此处虽未直接提尚宝司为小九卿,然而尚宝司显然不是大九卿衙门,如此只能解释为小九卿衙门最为合适。
京尹,原指的是京兆尹。明代的京师分为两京,所谓京尹则具体指北京顺天府尹和南京应天府尹,两京府尹皆正三品。朱国祯文中在谈大小九卿统属之时,便提“京兆无所不属矣”,可见其同属小九卿一员。万历时大学士王锡爵与当时顺天府尹来往书信时,提到“北京兆在九卿中”。[9]609此处的北京兆,指的便是北京顺天府尹,九卿亦如同上文尚宝司少卿黄龙光制诰称九卿一般,实际指小九卿。
最后论证鸿胪、太医、钦天三衙门是小九卿的说法。上文朱国祯所言大小九卿衙门移文规矩时,已经提到鸿胪寺,徐学谟《世庙识余录》中谈及小九卿衙门与大九卿争礼时言:
既正九卿职掌以来,于小九卿各有专属。文移往还,谁敢陵越?即如太常、光禄、太仆、钦天监、太医院解到各处钱粮,必由部投牒发批,太常等衙门不过司其收放而已。盖朝廷体统,大小相维,自是如此。万历间礼部奏正纳言职掌为鸿胪所侵,当复其旧,已得俞旨矣,而鸿胪官故出中官门下,胪卿贾名儒阴有所恃,复强辨抗奏,竟旨从内降如旧,礼卿不能争也。[10]203
该材料在谈及小九卿衙门移文往来时所举之例,明确指出钦天监、太医院、鸿胪寺三者均为小九卿衙门。徐学谟历经嘉隆万三朝,曾官至礼部尚书,想来对朝中衙门颇为熟悉,所言应有依据。
除徐学谟外,同时期的潘季驯在南京兵部尚书任上给神宗的官方奏疏中,所言及南京大小九卿衙门时,亦提及鸿胪寺和钦天监。潘季驯奉圣旨“遵照钦依事理,行准南京大小九卿各该衙门,查自正统六年历嘉隆以来,节次裁革并见今奉圣旨革过官员逐一拟议”,随后潘季驯即开列官员名单,“查得先今裁过官员吏部右侍郎一员,司官六员,户部司官一十一员,礼部右侍郎一员,司官八员……太常寺少卿一员,光禄寺少卿一员,鸿胪寺寺丞一员,钦天监监副一员。”[11]45虽然该疏因为内容限制并未将南京大小九卿逐一列出,但是恰好鸿胪寺和钦天监有裁减过的官员在内,如此则可证鸿胪寺和钦天监为小九卿衙门。
(三)特殊衙门:翰林、詹事
上文所辨析之各衙门,都有明确的证据证明其是或者不是小九卿。然而还有部分衙门,如翰林和詹事,存在着矛盾的情况,即既有支撑的证据,又有排除的证据,较之其余衙门情况相对复杂,特辨析如下。
首先是支撑翰林、詹事为小九卿的证据。何良俊《四友斋丛说》中记载:
两京小九卿衙门首领官皆有印,惟翰林院独无印,见南京翰林院掌院先生自佥名回各司手本,于事体颇觉有碍。或以为翰林院原隶于礼部,然太常寺、詹事府、国子监皆隶礼部,亦只是首领官行,不应翰林院独是堂上官与各司对行。[12]367
朱国祯《涌幢小品》亦言:
余署南翰院,院之体貌原与大九卿亚。叶台山署宗伯事,移箚付撰皇太孙贺表,叶以书先之,谓旧规如此,亦惧余之抗也。夫居官各有体,岂以此争强弱哉。九卿以大小分,文移间宜有低昂,且一切总于大。[5]302-303
何良俊本人曾有在南京翰林院任职的经历,而朱国祯更是曾经署南京翰林院事,本衙门人言本衙门事,自然较为可信。何良俊此言虽然主要针对翰林院首领官没有印信一事而发,然而根据其“两京小九卿衙门首领官皆有印,惟翰林院独无印”一句,已足以证明翰林院的身份,后列举诸小九卿衙门时又提及了詹事府。朱国祯虽然没有出现直接点明的话语,不过结合其“院之体貌原与大九卿亚”以及“九卿以大小分”两句,同样可以推出翰林院的身份。
詹事也有直接证据可证。《南京都察院志》中记载御史移文的仪注时,在小九卿衙门中,除了上文无异议以及经辨析后确为小九卿的衙门外,还提到了翰林与詹事:
本院经历司行五军都督府经历司、六部各清吏司、通政司经历司、大理寺左右二寺、六科十三道,太常寺、光禄寺、鸿胪寺、太仆寺、钦天监、国子监、詹事府各典簿厅,太医院、翰林院各首领衙门,或本院劄付该道令小九卿衙门吏典抄案。[13]271
上述诸衙门中,五府是武官衙门,六部、通、大明确为大九卿,六科十三道是言官,文末所言的小九卿衙门吏典,便只能是指文中自太常至翰林诸衙门了。
认为翰林詹事不是小九卿衙门者,同样是朱国祯。其在《皇明史概》中直言:“翰林原三品,改五品,优遇仍三品礼。故詹翰系文学侍从之臣,不在大小九卿之列。间出为祭酒,称小九卿。然以从四品廷推,太常诸卿莫敢望焉。”[14]107他认为翰林与詹事不在大小九卿之列,而国子祭酒虽然是小九卿,却能以从四品廷推,也非太常等卿可比。朱国祯此言显然是凸显翰林詹事的特殊地位,然而同一个人为什么会出现自相矛盾的言论?笔者认为,这或与各则材料所处的语境有关。认为翰林詹事为小九卿者,所指的均为南京翰林院詹事府。何良俊、朱国祯两则支撑材料的背景其实是南京翰林院,《南京都察院志》是关于南京都察院的志书,而非北京,文移往来亦指的是南京衙门。朱国祯后来则在北京任职并官至大学士,在《皇明史概》中评论性质的语言,并未单指南京,自然是北京翰林詹事。明代南北二京官员虽然在名义上是平等的,但事实上,南京官员的地位权势一般低于北京官员。且据万历《明会典》所记,南京翰林院与詹事府皆不设正官,[15]16,18北京翰林院与詹事府却多以大九卿衙门堂官充任掌事者。[4]1785、1787因此南北二京的翰林、詹事,无论在地位上,还是掌事者的身份上,均不可同日而语。清人阮葵生言,“大小九卿,说者不一,明中叶时尤紊乱,无一定之制,每以势力为轻重。”[3]74所指或在于此。翰林与詹事在品级上确为小九卿衙门,只是因为南北二京的衙门地位产生较大的悬殊,所以在北京引起了不同的看法。
最后,仍需要稍作解释的是诸多异议衙门中仅剩的上林苑监。由于笔者目前尚未寻得上林苑监是小九卿衙门的直接证据,故而此处暂且存疑。①上林苑监是正五品衙门,从品级上看似可列为小九卿。不过其所负责的内容过于特殊,且自洪熙时,便已经不设正官,仅设监丞掌事,夹杂以宦官,会典中南京更无上林苑衙门,似又不可列为小九卿。
三、小九卿争议与九卿概念
在对诸多解释中有异议的衙门进行逐一辨析以后,鸿胪、尚宝、京尹、詹事、翰林、国子、钦天、太医均有可作为小九卿的支撑证据。在诸衙门中,由于北京翰林、詹事的高规格地位,明人又有不将北京翰林与詹事视为一般的小九卿衙门者。对于诸多解释中均无异议的太常、太仆、光禄三衙门,虽未具体辨析,但在考证时许多史料中均已提及了其作为小九卿的身份。
上述已对明代小九卿衙门诸说辨析完毕。若依据上文六种解释来看,则官方解释与私人解释均有正确者。
但是有一个问题非常值得注意,即上文的六种解释虽各有不同,其总数均为九个,而经过笔者考证,明人眼中的小九卿却并不止九个。若从晚明时期奉圣旨大小九卿会议的参与情况看,上文的小九卿中,参与较多的是太常、太仆、光禄、国子、尚宝、翰林、詹事诸衙门,至于京尹、钦天、太医三衙门,目前笔者尚未见到他们曾参与九卿会议的记录,则可参与会议的小九卿似又不满九个。钦天和太医尚可理解,但是依据京尹的品级及其京官的性质,很难说它并非小九卿。如此,上文虽考证了诸衙门是否为小九卿,却并未解决小九卿指代争议的问题。其实,无论是官方还是私人,在没有明文规定或是渐成惯例时,都仅是一家之言,很难完全适用,一家之言所造成的争议,根源在于明人对九卿概念的误解。
从大小九卿概念的来源看,无论是大九卿还是小九卿,均源于九卿一词。九卿一词虽然自先秦时期便已有之,然而其本质是对三代官制的想象,即所谓“古者天子三公,每一公三卿佐之”,故有九卿之称。而从秦汉开始的九卿,显然便是对三代官制的一种附会。此后历朝仍多有以九个官署附和九卿者。明代亦如是。
九卿虽然有着深厚的基础,但是明廷显然不是依据九卿的概念来安排具体的官制的,则所谓的九卿,同样是附会。九卿(大九卿)的附会有着九卿会议作为基础依据,历时悠久且根基深厚,因此朝野均达成共识,而小九卿则不然。近人徐一士在其书中便引用晚清李慈铭同治三年甲子十月二十五日日记:
按明以六部拟周六官之制,六部尚书曰六卿(吏部尚书号为六卿之长,视冢宰也),皆为正卿(大理太常等寺之卿,俗亦称正卿,对少卿而言,非此之比),侍郎为卿贰,言为正卿之贰官也。六部尚书之外,益之以都察院都御史,曰七卿。更益之以通政司使大理寺卿,曰九卿。六部都通大称九卿衙门。九卿会议,贰官率亦与焉,以同为九卿衙门之堂官也。清九卿因之。至所谓小九卿,则为九卿外京卿之泛称。曰小者,示别于九卿,因更称九卿为大九卿焉。所谓大小九卿者盖如此。大九卿(即九卿)之九为实指之数,小九卿之九则为泛称之词,汪中《释三九》所谓“实数可稽,虚数不可执”是也。小九卿云者,犹众官之言百官耳。若斤斤按九数列举,其于或数或不数,则煞费推敲,而每难自圆其说云。[16]275
李慈铭是晚清时期著名的文史大家,他的观点非常有参考价值。明之九卿本就是先六卿、再七卿、后九卿,方才凑满,所谓六卿(六部尚书)是仿周礼天地春夏秋冬六官,后续的七卿、九卿均是在此基础之上的演变,明中叶以后又有大九卿、小九卿的差别。大九卿的几番拼凑成型,实际有九卿会议制度作为依托。而小九卿虽然同大九卿一样,都是长期形成的指代性概念,却并没有一定的保障作为依据。因此,明人乃至清人多简单地以大九卿衙门的数量作为依据,附会小九卿衙门,此或是明清文献中诸多解释均恪守九个衙门的原因。但是从小九卿概念出现的目的来看,显然是为了区分大九卿的。不过明代的官制除大九卿衙门外,其余可称“卿”的京官衙门的数量却不大可能正好符合九个的要求。如果非要强行拼凑满足九个衙门,又没有足以服众的依据,自然会造成诸多争议,“每难自圆其说”。因此,笔者认为,认识明代的小九卿,应抛弃“九卿为九”的执念,而关注不同场合下的具体所指。大小九卿会议时的情况上文已有所述,曾任副都御史协理院事的许弘纲在万历辛亥京察时言“京察旧规,大小九卿各开所属贤否于部院”[17]268,这里的大小九卿普遍指一般京官衙门,小九卿即是大九卿之外的列卿;而曾任吏部尚书的张瀚在《松窗梦语·铨部纪》中又有大小九卿并翰林科道的说法[18]152,则他笔下的小九卿又不包含翰林。笔者上文所考证的结果,便是诸多具体所指的汇集。
其实,“九卿非九”并非李慈铭凭空而生的想法。杜晓便提及,西汉时期九卿已经成为泛称,九是虚数而非实指。[19]九卿早在汉代便已经可以泛指,只是后世各朝多有以九个官署附和九卿者,于是才形成了九卿之九为实数的说法。延至明清,该观念早已深入人心,难以打破。由此亦可见传统九卿概念对时人的影响。
四、结语
本文的主要目的就在于揭示明代小九卿身份争议的实质,其中小九卿之九并非实指而是虚指是本文所要表达的核心观点。笔者推断,因为小九卿的界定无据可依,官方主要依据推举京堂的资格来界定,私人则多以品级来界定,然而他们的标准均被数字“九”限制。事实上,明人口中的小九卿有泛指、有特指,并非固定为九个。
通过本文对明代小九卿概念的辨析,有利于加强对明代官场称谓乃至官僚制度、官场文化的认识。诸如小九卿的概念,虽然明代官方制度中并未明确规定,在解释时也多有矛盾之处,然而该称谓却广泛地使用于官方私人的各类文书中。这些在官场长期形成的概念显然是明代官僚制度的“活的”部分,同官方的正式制度一并构成了明代官僚体系的日常运作,其作用不可忽视。
此外,明代类似小九卿的官场指代性称谓仍有许多,学者在使用,尤其在解释定义时,对于有争议或是指代不明确的称谓,似应慎重落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