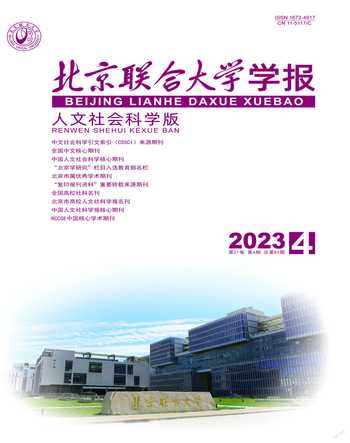网络游戏规则著作权保护:路径选择与侵权判定
2023-08-01孙玉荣李贤
孙玉荣 李贤
[摘 要] 在网络游戏“换皮”抄袭猖獗、游戏产品同质化现象严重的当下,网络游戏规则能否得到有效保护事关网络游戏版权产业的良性循环。司法实践中以游戏画面为载体的间接保护模式虽有一定的合理性,但局限性也很明显,只是《著作权法》修订之前的权宜之计。论述网络游戏规则的可版权性,并不意味着所有的网络游戏规则都能成为著作权保护的客体,但只有承认网络游戏规则具有可版权性,才能将其纳入著作权法的分析框架加以保护,而不是用反不正当竞争法的一般条款来解决问题。探究网络游戏规则著作权法保护模式和具体路径,在此基础上,结合司法裁判现状,对“换皮”纠纷著作权侵权判定中关键的“实质性相似”认定方法提出完善建议,以期实现游戏从业者利益保护与创作自由的平衡,从而促进网络游戏版权产业健康有序发展。
[关键词] 网络游戏规则;著作权;视听作品;实质性相似
[中图分类号] 中图分类号D923.41 [文献标志码]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672-4917(2023)04-0058-09
一、引言
“网络游戏规则”并非著作权领域专业术语,目前我国理论界及实务界尚未对“网络游戏规则”形成统一认知,给游戏规则下定义并非易事,通过传统文义对游戏规则进行解释难以体现其本质,应将其还原至网络游戏设计开发中进行理解。游戏业内认为“游戏规则规定了游戏能够参与的玩家、玩家行为、游戏目标、胜利条件与失败条件、冲突方式、奖励惩罚机制及资源”[1],有时也被称为“游戏机制”(game mechanics)。通俗来说,于玩家而言,游戏规则是游戏设计者创造的用于指引玩家进行游戏的一套指令,起到划定游戏行为边界的作用。尽管游戏规则并不直接描述玩家操作游戏的过程,但游戏规则的设计决定了玩家与游戏的交互过程及效果,进而直接影响玩家的游戏体验。以玩家感知程度为标准,游戏规则可分为基础规则、具体规则和隐性规则三种。网络游戏规则因自身法律属性存在争议,游离于著作权保护的边缘,游戏规则的抄袭也处于著作权侵权的灰色地带。因此,对网络游戏规则的可版权性进行探讨,在此基础上,探究网络游戏规则著作权保护模式与路径选择,紧密结合司法实践,对网络游戏规则著作权侵权判定方法的优化提出完善建议,以促进网络游戏版权产业健康有序发展,就显得尤为必要。虽然在我国司法实践中,不乏通过反不正当竞争法路径对网络游戏规则进行司法保护的裁判案例,但是本文认为,应该慎用反不正当竞争法一般条款对此进行兜底保护。对于那些无法认定为著作权侵权的行为,不宜随意适用反不正当竞争法模式的规制路径。
二、网络游戏规则可版权性探讨
在著作权法视域下,認定网络游戏规则的法律属性实际上就是探讨其是否具有可版权性,能否构成著作权保护客体。
(一)区分网络游戏规则中的思想与表达
游戏规则的思想与表达之辨往往是网络游戏“换皮”侵权纠纷争议的焦点,网络游戏规则究竟属于思想还是表达不能一概而论,思想表达二分法对划分公有领域与私权保护有重要指导价值,网络游戏规则的法律属性认定仍需回到思想表达二分法及其例外情形这一起点。
1.正确适用思想表达二分法
思想表达二分法是著作权法的一项基本制度,意为著作权法不保护思想,只保护表达,功能在于确定著作权保护的边界。这一原则的形成源自判例,美国Baker v. Selden案被公认为现代思想表达二分法原则的发端,现国际条约及各国版权法中亦有成文规定,如美国版权法第102条 17 U.S.C.§ 102( b).“对独创作品的著作权保护无论如何不及于思想、程序、步骤、系统、使用方法、概念、原则和发现,不论其以何种形式在作品中描述、说明、展示或体现。”与《Trips协议》第9条 《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定》第九条,第二款,“版权保护仅延伸至表达,而不延及思想、程序、操作方法或数学概念本身”。。著作权法之所以不保护思想,一是因为表达是传递思想的必经途径,作者的个性及内在情感只有借助于表达才能外显于人;二是为了维护他人就普遍性思想进行表达的权利,体现机会平等的精神[2]。
第21卷第4期孙玉荣等:网络游戏规则著作权保护:路径选择与侵权判定北京联合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23年7月
在网络游戏发展初期,囿于对网络游戏产品本身的不了解以及对行业认识的不充分,学界传统观点以及司法裁判均认为游戏规则属于抽象思想而非具体表达,不能受到著作权法的保护。在美国Atari, Inc. v. Amusement World案中,法院认为被告显然是在借鉴原告游戏的基础上完成了自己游戏的设计,即被告盗用了原告的创意,但由于版权法只保护思想的表达而非其本身,故此种行为并不被法律所禁止Atari, Inc. v. Amusement World, Inc., 547 F. Supp. 222 (D. Md. 1981).。同样,在Capcom U.S.A, Inc. v. Data E. Corp案中,法院认为正是因为原告游戏作品中有相当部分元素并不受版权法保护,才为竞争对手留下了模仿空间Capcom U.S.A., Inc. v. Data E. Corp.No. C 93-3259 WHO, 1994 WL 1751482 (N.D. Cal. Mar. 16, 1994).。在国内,最早涉及“换皮”抄袭的网络游戏侵权案件是《泡泡堂》诉《QQ堂》案,在判决中,法院将两款游戏的登录、等待、实战、道具界面分别拆分为美术作品、文字作品进行相似度比对认定,尽管也采用了思想表达二分法剔除其中属于通用表达的内容,却忽略了贯穿网络游戏整体的游戏规则的存在,未能意识到此种抄袭的本质 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2006)一中民初字第8564号判决书。。在《炉石传说》案中,原告认为具有高超的竞技平衡性的游戏卡牌和套牌组合的游戏规则应受到著作权法的保护,法院虽以游戏规则属于思想、无法成为著作权法调整的对象为由驳回了该诉讼请求,却又在判决书中指出此种抄袭行为显然具有不正当性。可以看出,法院虽认同应当给予游戏规则一定的保护,但未能跳出思想表达二分法的限制,因而转向反不正当竞争法寻求保护依据。
近年来,随着网络游戏著作权侵权纠纷的激增,司法裁判经验日益丰富,人们逐渐意识到笼统地将游戏规则排除在著作权保护范围外带来的弊端,观念由完全否定其保护可能性转变为部分肯定。“《太极熊猫》案”作为首次明确游戏规则可受到著作权保护的典型案例,明确提出应对游戏规则中的思想与表达进行区分。法院认为在游戏整体系统设计中,概括、一般性描述的玩法规则落入思想范畴,而具体到足以使玩家感知到其来源于特定作品并提供玩赏体验的玩法规则就可能构成表达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2018)苏民终1054号判决书。。不少学者认为给网络游戏规则提供著作权保护可能会造成游戏规则设计的垄断,从而阻碍行业创新,这种观点事实上是对思想表达二分法的教条化理解,刻板地将游戏规则置于“思想”与“表达”非此即彼的境地。在作品中,从具体表达到抽象思想呈现为“金字塔”结构,在塔底和塔顶之间总是存在着一条从“量变”到“质变”的临界线,界线以上的部分属于思想不受保护,界线以下的部分则因足够具体而构成受保护的表达[3]。同样,凝聚了游戏设计师精巧构思与平衡智慧的网络游戏规则中也存在这样一条分界线,游戏规则中既有属于公共领域的思想,也有应受著作权保护的独创性表达。只是对于不同的游戏而言,界线的具体位置亦不同,有赖于法官在个案中结合游戏类型、新颖程度、玩家可感知性等情况进行具体判断、自由裁量。思想表达二分法本属于价值法则,关乎成本收益的利益衡量及取舍,无法在事实层面为法官提供统一普适的裁判标准 [4]。
限于文义解释的局限性,“思想”一词语义模糊,内涵难以明确,寻找“思想”与“表达”的界限相当困难,这与思想和表达之间界限模糊难分的特点有关,即思想经由表达而被感知、传播,表达必然体现和承载思想。不是所有脱离思想范畴的表达都能受到保护,在对网络游戏规则中的“表达”进行提炼和分析时,还应结合混同原则、场景原则综合判断是否存在例外情形。
2.谨慎适用混同原则与场景原则
“混同原则”又称为合并原则,此处的“混同”意为思想与表达的混沌不清,是指在特殊情况下,某种思想只能经由极其有限的表达被感知,致使思想与表达界限模糊,难以分割。此时,不论该表达是否具有独创性,都被纳入不受法律保护的思想范畴[5]。“场景原则”是指在设立某种特定的风格、主题、场景时,所必须使用的基本或常见的表达,这些表达同样不能受到著作权法的保护,此时在其后作品中使用相同或类似的表达不构成侵权。与混同原则、场景原则密切相关的是“抽象-过滤-对比三步检验法”(简称AFC检测法),它最早起源于美国Atari案,是著作权侵权案件中用以区分思想与表达及判定作品实质性相似的经典方法。其中“抽象”是指抽离涉案游戏规则中的思想部分,确定保护对象;“过滤”是指通过适用合并原则和场景原则进一步剔除表达中的有限表达及标准场景部分,细化保护范围;“对比”即指判断被诉侵权游戏是否使用了他人已构成独创性表达的游戏规则,其中,“抽象”和“过滤”正是划定网络游戏规则著作权保护范围的关键步骤。司法实践中,法院适用混同原则与场景原则将游戏基础规则排除在著作权保护范围之外的同时,往往过度缩限了具体规则的保护范围。过去,网络游戏的玩法简单、操作简便,在游戏规则方面没有太多发挥的空间,随着游戏引擎的广泛应用以及制作技术的提升,游戏的外在表达层面有了更多想象和选择的空间。一些游戏规则设计不应再被认定为通用表达,若继续采用过往的判断标准,可能导致排除范围过宽[6]。
在游戏版权保护领域,美国法院对思想表达二分法及其例外原则的适用进行了探索及突破,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在Triple Town案中,法院排除了场景原则在该案中的适用,认为场景原则只适用于网络游戏设计普遍会采用的一些元素,比如猜拳或掷骰子等基本游戏机制 Spry Fox LLC v. LOLApps Inc., Not Reported in F.Supp.2d (2012).。纸牌类游戏通常一直囿于其有限的表达方式而受到较为薄弱的版权保护,在Da Vinci案中,法院摒弃了传统纸牌游戏所遵循的判例,对混同原则与场景原则的适用采取了更加克制的态度 DaVinci Editrice S.R.L. v. ZiKo Games, LLC, Not Reported in F.Supp.3d (2014).。上述判例显示,裁判观点在如何区分游戏作品中的思想与表达方面发生了转变,即在网络游戏领域适用混同原则和场景原则时应更加谨慎,防止滥用,并且这一转变涉及多种游戏类型。尽管法院的这些分析和判决是基于游戏的整体表现形式而不是“游戏规则”本身作出的,但当中体现出打击网络游戏版权侵权、鼓励网络游戏行业创新的价值取向值得我们思考与借鉴[7]。
(二)网络游戏规则满足作品的构成要件
“作品”是著作权的起始概念,在判断网络游戏规则是否具有作品属性时,仍应从作品的构成要件入手分析。
1.属于文学、艺术和科学领域内的智力成果
網络游戏的研发制作涉及程序编写、美术设计、游戏策划、技术维护等工作,需要工作人员投入大量智力劳动,无疑汇聚了无数智慧结晶。游戏规则作为游戏的“灵魂”,不同于大自然中客观存在的现象、法则、定律,它由开发者设计产生,创作本身就是游戏开发者创意、理念、知识与技能的积聚过程,显然是脑力劳动结成的果实,毋庸置疑蕴含智力要素。早在2011年,美国就正式宣布“电子游戏是一种艺术形式”,赋予其“第九艺术”的称谓,可以说,作为电子游戏分支的网络游戏,自诞生之日起就承载着技术、媒体、审美艺术、社会经济的发展,是融多元素于一体的产物[8]。网络游戏规则自然是属于文学、艺术和科学领域内的智力成果。
2.具有独创性
具备独创性是网络游戏规则具有可版权性的实质性条件。我国著作权法未对“独创性”的含义以及判断标准进行解释说明,长久以来,理论界未能就此达成共识,审判中也存在着一定的盲目性和任意性[9]。不同作品类型所适用的独创性判断标准不同,不能一概而论。在面对网络游戏规则这样突破传统作品类型的新型创作物时,除了容易陷入创作性高度认定分歧的困境,还面临着如何取舍独创性标准的问题,即所谓的“独创性”指向的究竟是创作的过程还是结果[10]。
早期受技术水平的限制,游戏内容相对单调,独创性较低。随着行业发展的日渐成熟,网络游戏开发呈现模块化趋势,设计师先选择一款现有的基本规则以确定游戏的基本类型,再对玩法系统或模块进行选择、排列和组合,并在此基础上设计操作流程、对战模式、角色属性、技能体系、数值平衡等具体内容,以此实现游戏逻辑的自洽。那么这种在成熟游戏模式的基础上进行开发的创作方式能否保证游戏作品具有足够的原创性呢?应当注意的是,游戏基本规则的相似并不意味着游戏整体或游戏规则整体的相似,单个游戏规则或许简单易懂,多个规则组成一个整体后,游戏运行机制就变得更加复杂而精妙。实际上,基础规则在组合、展开、细化成具体规则的过程中离不开设计人员的想象、思考和判断,耗费了开发者的劳动心血,凝聚了智慧结晶,能够达到一定的创造高度。创作者经历背景的不同以及对游戏机制可玩性、平衡性等内容理解的不同,也会造成游戏规则设计方面的差异。鉴于创新性是一种定性概念而非定量概念,可以认为,只要游戏规则能够区别于其他现有设计,不论区别大小,就具有原创性[11]。
3.以一定形式表现
2020年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以下简称《著作权法》)将作品构成要件之一的“能以某种有形形式复制”修改为“能以一定形式表现”。在此之前,《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实施条例》“能以某种有形形式复制”的表述不甚明确,在理论和司法实践中存在不同的解读,引发不少争议。它究竟是指“再创作性”“可复制性”“固定性”还是“可感知性”,至今没能达成统一意见,甚至在许多判决中,法官并不对该要件进行具体论证,一定程度上造成这一构成要件被空置。曾有观点批评作品的“可复制性”要件不具有现实意义,因为除了那些仅能停留在脑海中的想法,几乎不存在无法被复制的表达[12]。亦有学者指出,应将著作权法规定的“有形形式”理解为一般公众可以感知的方式,不论究竟是通过物理方式还是非物理方式[13],在这一层面上,不论是通过图片、文字,还是连续动态画面等视听因素的形式,或是通过实际操作被玩家感知得以表现,网络游戏规则都是符合“能以一定形式表现”这一要件的。
综上所述,本文认为,满足作品构成要件的网络游戏规则可以获得著作权保护,但并不是所有的网络游戏规则都能成为著作权保护的客体。
有观点认为,构成作品除了需满足“独创性表达”的实质条件外,还应当具备一定的形式条件。所谓的形式条件,即指讨论对象的表现形式应当属于我国法定作品类型之一,而网络游戏规则正因无法归类于我国现有的作品类型而不具有可版权性 [14],笔者认为上述观点不可取。
首先,有必要厘清作品客体与作品类型的关系。作品的客观存在是第一性的问题,如何通过著作权法对作品进行类型化并赋予相应的保护是第二性的问题,先确定作品类型、后判断作品属性的做法颠倒了第一性“客观存在”与第二性“制度选择”的顺序[15]。其次,应正确理解作品定义条款与作品类型条款的功能区别。作品的定义条款具有规范功能,用于统一作品的概念及内涵;而作品类型条款则承担示例功能,具有减轻法律解释负担的作用[16]。正如有学者所言,法律列举的意义在于方便公众了解法律权利以及在司法活动中查找依据。设立作品类型条款,在法条中列举具体的作品类型是为了对那些已明确纳入著作权保护范围的作品进行常规化、类型化的梳理[17],统一规定不同类型作品的权利归属、权利限制及权利保护期等利益分配问题,而不是以法定作品类型框定著作权法的保护范围。随着社会科学技术的发展,新型创作物层出不穷,其表现形式完全有可能突破原有限定,但这不妨碍著作权法赋予其相应的保护,将作品类型条款作为可版权要件无异于削足适履。
作品类型依据不同的表现形态而划分,从著作权法的发展历程来看,作品表现形态的种类是随着技术变迁而不断扩张的。自著作权制度由“印刷版权时代”进入“网络版权时代”,突破传统作品分类的新型创作物不断涌现,如网络游戏、直播节目等。总体而言,作品类型范围呈现不断扩大的趋势。法律具有一定滞后性,对于新型创作物而言,在法律未明确禁止给予保护的前提下,若无视时代发展需求,仅因未获得立法关注、未被类型化的缘故否认其作品属性,阻碍其获得及时有效的法律保护,不仅在逻辑上难以自洽,更是与促进文化繁荣、鼓励创作与传播的立法宗旨背道而驰[18]。2020年新修订的《著作权法》已将过去规定的“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其他作品”修改为“符合作品特征的其他智力成果”,改变以往的作品类型封闭状态,能够为实践中的作品类型扩张提供合法依据,有助于保护目前已经存在或未来可能出现的新型智力成果,而在该模式下,对新型创作物法律属性的认定更应回归到“作品”定义本身,不宜以作品类型法定之局限因噎废食。
三、网络游戏规则著作权保护模式路径选择
网络游戏构成复杂、内容多元,在游戏“换皮”侵权纠纷中,法院遵循碎片化保护原则,曾尝试将拆分出的游戏规则纳入文字作品、计算机软件的范围,亦有观点主张为网络游戏规则设立独立的作品类型。网络游戏规则作为游戏设计的核心内容,如同“骨架”一般贯穿了游戏运行的方方面面,采取拆分保护模式对网络游戏规则适用直接保护的做法忽略了游戏内部的完整性,其局限性日益凸显。司法实践中逐渐摸索出以游戏画面为载体的间接保护模式。
(一)为网络游戏规则提供间接保护的司法实践
近些年,认定网络游戏画面构成类电作品的整体保护模式在司法实践中逐渐兴起并受到各地法院的青睐,同时也获得了学界主流观点的認可。广东省高院也发布了相关《审判指引》,就游戏连续动态画面构成类电作品的具体认定给出了较为清晰的指引。网络游戏画面之所以能够为网络游戏规则提供间接保护,是因为玩家只有在操作游戏时才能感知到网络游戏规则,这与游戏规则的特性有关,而网络游戏运行所呈现的最终表达形式正是游戏画面,游戏画面经此成为游戏规则设计被感知的依托。
在《奇迹MU》案中,法院通过认定游戏整体画面构成类电作品,从而间接地为网络游戏规则提供了保护上海知识产权法院(2016)沪73民终字第529号判决书。。《花千骨》案中,法院就游戏规则的“表达性”进行了论证,“依托游戏界面呈现的详尽的游戏玩法规则,类似于详细的电影剧情情节,游戏开发过程中通过绘制、设计游戏界面落实游戏规则的表达,与电影创作过程中依据文字剧本绘制分镜头剧本摄制、传达剧情具有一定相似性”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5)苏中知民初字第00201号判决书。。与拆分为美术作品、文字作品相比,类电作品的认定标准不局限于表达的外部可见部分,也考量了内在的不可见部分,符合游戏规则需依附于其他作品得以展现的特点,无疑能够实现对游戏核心部分——游戏规则的适当保护。有部分学者认为,网络游戏规则并不具备类电作品应有的表现形式[19]。在此需要澄清的是,司法实践中将网络游戏画面认定为类电作品只是为网络游戏规则提供间接保护,并不是说直接把网络游戏规则认定为类电作品。
(二)视听作品的配套制度有待完善
尽管如此,对于网络游戏规则而言,司法实践的间接保护模式也并非完美无缺。由于我国立法及相关司法解释中涉及类电作品的内容较少,实践中的认定标准并未统一、比较模糊,不同法院产生了不同的认定思路和结论。相关裁判观点在“连续动态画面”及“摄制”创作手段等方面基本达成共识,然而在认定“剧情或故事情节”“交互性”等方面,各法院裁判不一、争论不断。上海浦东法院以风光片或纪录片作品为例,认为没有预先设定的故事情节并不构成否定网络游戏画面构成类电影作品的理由上海市浦东新区法院(2017)沪0115民初77945号判决书。。与此相反的是,上海知识产权法院在判决书中指出,在认定是否构成类电作品时,除了要判断是否满足“具有连续动态图像”的条件,还应注意网络游戏整体画面是否具备相应的故事情节或剧情上海知识产权法院(2020)沪73民终33号判决书。;广州互联网法院亦从作品内容的角度强调在游戏整体画面中,“游戏人物在游戏场景中不断展开游戏剧情……类似电影的复合表达” 广州互联网法院(2018)粤0192民初1号判决书。。这种认定标准将导致许多故事情节要素较弱的特定类型游戏画面无法顺利落入类电作品的范围,如卡牌类、射击类、沙盒类游戏。角色扮演类游戏的剧情架构相对完整、丰富,能够满足以上标准,但此类游戏仅占我国游戏类型数量的1/4。可见,游戏规则虽不等同于游戏故事情节,类电作品认定标准的不明确却直接影响了网络游戏规则的著作权保护效果。
司法实践中以游戏画面为载体的间接保护模式虽有一定的合理性,但其局限性也很明显,只是《著作权法》修订之前的权宜之计。过去,受限于著作权法中类电作品必须“摄制在一定介质上”的规定,游戏画面的作品类型认定涉及对“类电作品”概念的扩大解释、类推适用,还需结合《伯尔尼公约》对相关含义进行澄清,这在实践中引发了不少争议,将网络游戏画面“强行”纳入类电作品的保护范围实属不得已而为之。2020年修订《著作权法》后,“类电作品”的概念被“视听作品”所取代,这一修改顺应了科技社会发展的时代要求,是著作权法律制度与时俱进的必然产物,可为网络游戏规则提供更为名正言顺的保护路径。然而在现阶段,与之相关的配套制度尚未更新或建立,视听作品的定义、认定标准及权属规则等内容仍有待司法解释或相关立法进行阐明,仍需理论界及实务界共同努力继续进一步地探讨及完善,否则关于视听作品理解及适用的争议会继续进行,无益于网络游戏规则作品认定问题的解决,亦阻碍网络游戏规则著作权保护模式的落实与进一步完善。
四、网络游戏规则著作权侵权判定方法的优化建议
在著作权侵权纠纷中,判断被诉侵权作品是否使用了他人作品,实践中普遍适用“接触+实质性相似”原则。相比于满足“接触”要件,作品“实质性相似”的认定更加复杂、关键,通常是双方争论的核心焦点。多年的司法实践逐渐形成了一些裁判共识,即无论以何种作品形式为网络游戏规则提供保护,在侵权对比环节都应根据游戏作品的外在表现形式进行整体把握,而非机械地分解元素并逐一比对,实际上这也与通过认定游戏画面构成类电作品或视听作品的间接保护模式保持了一致。关于如何进行实质性相似判定,司法实践发展出了多种测试方式,常见的包括“抽象分离法”和“整体观感法”两种路径。
(一)以抽象分离法为主
抽象分离法是指将作品中的思想、事实或通用元素等不受著作权保护的部分抽象剥离,仅留下作品中明确受著作权保护的部分进行相似度比对。本质上它仍属于思想表达二分法的适用,其优点在于几乎可适用于所有类型作品,法院在网络游戏相关侵权案件中也多采用这一方法。抽象分离法的实施效果取决于法官如何合理地拆分游戏内容并解释游戏规则与其他游戏要素之间的关系,如何对游戏规则的表达边界、独创性程度、相似程度进行详细分析,考验着法官对游戏行業及产品知识的认知水平。在标准的“换皮”式抄袭中,除了视听元素有差异,被诉侵权游戏的其他要素都与原游戏有明显的对应关系,在此情形下,法官无须进行过多分析和解构即可得到双方作品实质性相似的结论。尽管“抽象分离法”的路径很清晰,但随着抄袭手段的升级,其局限性已经显现。在当前游戏行业,越来越常见的是对游戏部分要素的使用或借鉴。在此种情况下,进行实质性相似判定的前提是更加准确、精细地对游戏的内容和要素进行分解并确定思想表达分界线,提高“抽象分层”的操作要求。
在以往的判决中,法院通过拆分、对比游戏画面所包含的各类元素对游戏整体画面做相似认定。在近期的游戏规则侵权案件中,法院尝试从游戏设计、研发制作等不同视角对游戏整体进行从抽象到具体的界分,将游戏作品划分为多个层次并明确其著作权保护范围。在《蓝月传奇》案中,法院从游戏设计的角度将游戏分为五层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2019)浙民终709号判决书。。其中,游戏基础玩法和基本系统架构是此类游戏常见的设计模式,因自身具有高度抽象性而落入思想范畴,但若游戏的创作元素、属性与数值的取舍、安排之间形成了特定对应关系,使得各系统之间组合而成的特定玩法规则和情节达到了区别于现有游戏的创作性高度,并能够通过游戏画面对外呈现,那么不论它是以直白的文字形式还是以连续动态的画面方式呈现,这些具体表达都属于著作权保护的客体。换言之,法院认为第四层和第五层的内容可以落入表达范畴。在《守望先锋》案中,法院根据游戏研发阶段的先后顺序将游戏分为五层:第一层是游戏的类型定位;第二层是围绕游戏类型定位的规则设计;第三层为游戏资源的核心部分制作,包括地图线路设计、人物数值策划和用户界面的整体布局;第四层是资源串联和功能调试,以提升游戏规则与游戏资源的契合度;第五层是以视听元素为主的游戏资源的细化制作,最终形成游戏整体画面。法院认为第三层的设计要素在第四层的游戏资源里与游戏规则融合共同构成了表达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2017)沪0115民初77945号判决书。。在最新的《穿越火线》案中,法院更进一步将抽象分离法的适用范围从游戏作品整体缩小到游戏部分内容,即将“场景地图”设计分为七个阶段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2017)粤03民初559号判决书。。
根据作品抽象层次理论,作品可以划分为“内在表达”与“外在表达”,外在表达体现为作品中较低抽象层次的独立元素,内在表达则是作品整体在较高抽象层次内的各独立元素结合成的整体[20]。内在表达更加隐蔽,更容易与思想相混淆,在对网络游戏进行实质性相似认定时,应格外注意被诉侵权游戏是否存在对内在表达的模仿。如上所述,游戏规则设计系统庞大而复杂,由许多单个的玩法规则系统经选择、安排、组合而成。在对比游戏规则时,不仅要对相似的单个玩法系统单独进行比对,而且应从游戏整体的系统安排、选择、组合上判断是否相似,同时还要综合考虑相似部分的重要性及所占比例。
(二)以整体观感法为辅
所谓“整体观感法”,也被称为“整体概念和感觉分析法”,指根据“普通观察者”(ordinary observer)对作品整体的主观感受来判断两部作品是否构成实质性相似的方法[21]。该方法强调对作品进行整体认定与综合判定,不再对作品细节加以分析,也不要求观察者具有较高的专业知识水平,带有较强的个人主观色彩。在美国Castle Rock v. Carol Publishing案中,法院以作品类型及传播方式的不同会造成感觉的相异为由,拒绝在进行实质性相似判定时适用整体观感法 Castle Rock v. Carol Publishing, 150 F.3d 132 (2nd Cir. 1998).。不过,网络游戏规则侵权案件并不存在这种困扰,因为“换皮”游戏所保留的相同游戏规则恰恰决定了涉案游戏的类型必然一致。
在我国司法实践中运用这一方法的典型案例是“庄羽诉郭敬明”案,法院认为,分别独立对比一些相似程度不高或来源于生活中的素材,难有准确结论,若进行整体对比就会发现具体情节和语句的近似是整体抄袭的体现,二者可互相印证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2005)高民终字第00539号判决书。。在“琼瑶诉于正《梅花烙》”案中,法院亦就采用整体观感法的合理性进行了详细阐述,认为作品中确实存在不受著作权保护的内容,但这并不意味多个部分的有机联合整体也不具有独创性,部分内容不相似无法排除整体不构成实质性相似的可能,同时,“受众对于前后两作品之间的相似性感知及欣赏体验也是侵权认定的重要考量因素”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2014)三中民初字第07916号判决书。。在网络游戏著作权纠纷中,机械拆分游戏元素的保护方式逐渐被整体保护所取代,在认定游戏画面构成视听作品的趋势下,网络游戏内在完整性和连贯性得到重视,整体观感法成了认定游戏画面相似度的重要手段。在《奇迹MU》案中,法院也明确提出网络游戏整体画面的比对重点在于关注其整体性。
在网络游戏抄袭纠纷中,“普通观察者”并非指那些对游戏一窍不通的“路人”,一般是指涉案游戏的玩家或资深玩家,他们不一定具备游戏设计制作的专业知识,但对游戏产品本身比较熟悉。对于大型复杂的网络游戏而言,如果没有经过实际操作,很难对它产生具体认知,遑论进行感知对比。在实践中,通常当事人会向法院提交有关受众感觉调查方面的证据,以证明实质性相似的存在,在《奇迹MU》案、《太极熊猫》案以及《守望先锋》案中,原告均列举了各平台上有关抄袭的用户留言及评论。对此,部分法院持积极认可态度,在《奇迹MU》案中,法院明确将受众及玩家的感受作为判断是否构成实质性相似的考量因素,将网友对《奇迹神话》的评测及评论留言作为支持原告诉求的证据。部分法院虽未直接就受众留言进行评价,但同时强调了玩家对游戏整体感知的重要性。如前所述,“换皮”游戏侵权案中,收集有关“玩家感受”作为实质性相似的证据呈现给法庭是常见的诉讼策略,但从实践来看,无论当事人是否提供普通测试者结论,法官都会对涉案游戏进行抽象分离的比对。可见,玩家感受如何并非判定网络游戏构成实质性相似与否的关键因素,原因在于:一方面,在论坛、贴吧等场所收集到的言论通常具有零散、片面、情绪化的特点,缺乏论证的科学性和系统性,而测评文章因普遍具有宣传推广作用,其中立性、公正性易受到质疑[22]。另一方面,由于整体观感法系从作品整体出发,并不单独区分网络游戏中不同游戏元素的著作权属性,难免导致对比范围的不当扩大 [23]。
综上,运用整体观感法判断两款游戏之间的相似程度,可以作为“抽象分离法”的补充,但是不能过度依赖,更不能省略在实质性相似中对游戏要素及内容的梳理、分析,并判断构成著作权保护客体与否的步骤。对网络游戏规则适用整体保护不代表一味对游戏作品整体进行笼统的相似观察,在个案裁判中依然需要对具体内容层层剥离,注意剔除当中无法受著作权保护的部分。正如学者所言,“权利整体化并不意味着侵权判定笼统化”,应时刻注意避免网络游戏整体保护变成“囫囵保护”[24]。
五、结语
著作权法需要平衡著作权人与社会公众之间的利益[25],网络游戏行业“换皮”抄袭乱象扰乱了市场竞争秩序,阻碍游戏行业整体创新能力的提升与进步。由于我国尚未建立明确的法律指引,此类抄袭所涉网络游戏规则本身应如何定性、能否受到著作权保护及采取何种保护路径等问题依然模糊不清,莫衷一是。过去囿于游戏规则具有的抽象性、功能性等特点,网络游戏规则未能及时获得应有的著作权保护,在区分网络游戏规则中的思想与表达的基础上,作为游戏设计核心的游戏规则可构成著作权法意义上的“作品”,作品类型条款不应构成可版权障碍。著作权的设计致力于为创新提供必要激励[26],本文探究网络游戏规则著作权法保护模式和具体路径,在此基础上结合司法裁判现状对“换皮”纠纷著作权侵权判定中关键的“实质性相似”认定方法提出完善建议,以期实现游戏从业者利益保护与创作自由的平衡,从而促进网络游戏版权产业健康有序发展。在著作权侵权认定标准方面,建议应当以抽象分离法为主、整体观感法为辅,先抽象出游戏规则中受著作权法保护的表达,再结合普通观察者视角对实质性相似与否作出综合判定。
[参考文献]
[1] 张帆:《游戏策划与设计》,清華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57—70页。
[2] 李雨峰:《为什么著作权法不保护思想》,《电子知识产权》2007年第5期,第57—58页。
[3] 王迁:《知识产权法教程》,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21年版,第87页。
[4] 熊文聪:《被误读的“思想/表达二分法”——以法律修辞学为视角的考察》,《现代法学》2012年第6期,第168—179页。
[5] 王凤娟、刘振:《著作权法中思想与表达二分法之合并原则及其适用》,《知识产权》2017年第1期,第87—92页。
[6] 何培育、李源信:《“换皮游戏”司法规制的困境及对策探析》,《电子知识产权》2020年第9期,第17—28页。
[7] 熊良:《美国电子游戏版权保护历史演进及其启示》,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学位论文,2017年。
[8] 关萍萍:《互动媒介论——电子游戏多重互动与叙事模式》,浙江大学学位论文,2010年。
[9] 李伟文:《论著作权客体之独创性》,《法学评论》2000年第1期,第84—90页。
[10] 卢纯昕:《法定作品类型外新型创作物的著作权认定研究》,《政治与法律》2021年第5期,第150—160页。
[11] 卢海君:《网络游戏规则的著作权法地位》,《经贸法律评论》2020年第1期,第134—143页。
[12] 王洪友:《版权制度异化研究》,知识产权出版社2018年版,第142—143页。
[13] 刘春田:《知识产权法》,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22年版,第14页。
[14][19] 李忠诚:《论网络游戏规则不具有可版权性》,《苏州大学学报(法学版)》2020年第7期,第98—105页。
[15] 卢海君:《短视频的〈著作权法〉地位》,《中国出版》2019年第5期,第9—12页。
[16] 李琛:《论作品类型化的法律意义》,《知识产权》2018年第8期,第3—7页。
[17] 刘佳欣:《网络游戏设计的可版权性》,《山东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9年第5期,第37—44页。
[18] 张书青:《类推适用:网络游戏著作权保护的应然路径》,《中国版权》2020年第4期,第44—47页。
[20] 宋戈:《作品“实质性相似+接触”规则研究》,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学位论文,2019年。
[21] 梁志文:《版权法上实质性相似的判断》,《法学家》2015年第6期,第37—50页。
[22] 胡岩:《换皮游戏像不像,谁说了算——感觉测试法在实质性相似认定中的适用》,https://mp.weixin.qq.com/2021-11/12/s/0wdLDZW7G.htm。
[23] 许波:《著作权保护范围的确定及实质性相似的判断——以历史剧本类文字作品为视角》,《知识产权》2012年第2期,第28—34页。
[24] 张伟君:《呈现于视听作品中的游戏规则依然是思想而并非表达——对若干游戏著作权侵权纠纷案判决的评述》,《电子知识产权》2021年第5期,第66—76页。
[25] 赵丽莉、张子璇:《“市场因素”在网络游戏直播合理使用认定中的适用性分析》,《重庆邮电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2年第4期,第37—44页。
[26] 朱双庆、张艺:《论二次创作短视频引发的权利冲突与救济》,《重庆邮电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1年第2期,第37—46页。
Research on Copyright Protection of Online Game Rules:
Mode & Identification Method
SUN Yurong, LI Xian
(Faculty of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Beijing Intellectual Property Research Institute,Beijing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Beijing 100124,China)
Abstract: In the current era of rampant plagiarism in online games and serious homogenization of game products, whether the online game rules can be effectively protected is related to the virtuous circle of the online game industry. In judicial practice, the indirect protection mode with game pictures as the carrier has certain rationality, but its limitations are also obvious. It is only a temporary measure before the revision of the Copyright Law. Discussing the copyrightability of online game rules does not mean that all online game rules can become the object of copyright protection, but only by recognizing the copyrightability of online game rules can they be included in the analysis framework of copyright law protection rather than using the general provisions of anti-unfair competition law to solve the problem.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copyright protection mode and specific path of online game rules. It puts forward suggestions for improving the identification method of “substantial similarity” in the determination of copyright infringement in “skin changing” disputes in combination with the current situation of judicial adjudication, In order to achieve a balance between the protection of the interests of game practitioners and the freedom of creation, and encourage the healthy and orderly development of the online game industry.
Key words:online game rules; copyright; audiovisual works; substantial similarity
(責任编辑 编辑刘永俊;责任校对 编辑孙俊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