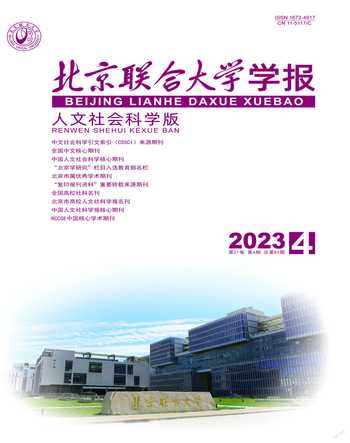北京红色设计发展脉络及特征价值研究
2023-08-01张彬张晓新黄超
张彬 张晓新 黄超
[摘 要] 红色设计是以革命精神为核心的、有目的的艺术创作,它将红色文化通过视觉形态表现出来,成为中国共产党发展历程中呈现的红色印记。红色设计融合了马克思主义理论、政治学、新闻传播学、美术学、设计学等学科特征,从多元化的角度阐释中共党史、中国设计史。以中国共产党在北京地区的发展历史为主线,通过对1915—1949年北京红色设计的发展脉络、特征和价值进行梳理和阐述,有助于推动对红色设计的深入研究,深化对中国化时代化马克思主义的理解,增强文化自信自强。
[关键词] 北京;红色设计;红色文化;革命精神
[中图分类号] 中图分类号K291 [文献标志码]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672-4917(2023)04-0035-09
在中国共产党波澜壮阔的发展历程中产生了许多举足轻重的设计,这些设计生动形象地记录了中国革命、建设、改革的历史进程,也是现代中国艺术设计的重要代表。如中国共产党的形象——党旗党徽、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象征和标志——国旗国徽。红色设计是以革命精神为核心、以实现革命目标为目的的艺术设计。从形态上,红色设计可以概括为“平面”“立体”和“空间”三大类。物质是标志客观实在的哲学范畴,这种客观实在是人通过感觉感知的,它不依赖于我们的感觉而存在,为我们的感觉所复写、摄影、反映。红色设计作为革命意志的形象反映,记录了中国共产党革命活动的历史,传达出中国共产党人的革命理想和信念。本文以1915年到1949年中国共产党领导北京革命发展的历史为主线和时空维度。“中国当代文化,源自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熔铸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在革命、建设、改革中创造的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到当代,本质上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如果以颜色作为象征,总体上说是一种以红色为基调的文化;而中国共产党培育、形成和展现的文化,则是一种比较完全意义上的红色文化。”[1]红色设计作为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革命、建设和改革中的思想感知的物化体现,自然是红色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其突出特征表现为革命性、传承性、创新性和先进性。
红色设计载体包括书刊、报纸、插图、标志、徽章、宣传画、票证、用具、建筑、景观等,它们对马克思主义传播、革命道路选择、群众宣传鼓舞、进步力量团结、统一战线壮大、革命助推和引领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见证了中国共产党从酝酿到诞生、从启航到发展、从弱小到强盛的发展历程,生动、具体、形象地展现了中国共产党的伟大革命精神。
红色设计融合了马克思主义理论、政治学、新闻传播学、美术学、设计学等学科特征,从多元化的角度阐释中共党史、中国设计史。中共党史专家李忠杰认为:“红色设计在党史研究中是个创举。”[2]本文通过对1915—1949年北京红色设计的发展脉络、特征和价值的梳理和阐述,加强对红色设计的深入研究,增进对中国化时代化马克思主义的理解和认同。
一、北京红色设计的发展脉络
事物的发展过程是循序渐进、螺旋式上升的。北京红色设计是对中国共产党领导北京人民进行革命斗争的历史形象印证,它随着中国共产党北京历史的漫漫画卷展开呈现,沿着中国共产党北京发展路线逐步前行,脉络清晰、节奏鲜明。按照中国共产党北京历史的阶段划分,北京红色设计发展可以概括为六个时间阶段。
(一)北京红色设计的初生时期(1915—1923年)
北京是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初期的研究和传播发散中心,中国共产党在北京酝酿成立。俄国十月革命爆发后,李大钊在《言治》季刊第三期发表《法俄革命之比较》,翻开马克思主义进入中国的篇章。1918年11月,李大钊发表《庶民的胜利》《Bolshevism的胜利》,向民眾宣传俄国十月革命的伟大意义。1919年5月,李大钊在其主编的《新青年》上发表了《我的马克思主义观》《马克思主义学说》等多篇宣传介绍马克思主义的文章。建党准备时期,办报办刊成为北京乃至全中国先进分子挽救国家危亡、争取民族独立、宣扬传播马克思主义的重要手段。一批报刊、图书以全新的面貌出现,它们设计思想新潮、表现形式新颖,北京红色设计应运而生。
《言治》《新青年》是这一时期红色设计的突出代表。从辛亥革命胜利至五四运动前夕,西方文化思想和先进印刷技术被不断引进,国内印刷业的快速发展带动了期刊业的发展。这个时期的期刊设计呈现出新的气象,许多期刊都采用“中西合璧”的装帧形式。1913年4月1日出版的《言治》第1期为32开本,封面为草绿色。封面主体是实地凸版印刷草绿色色块,色块四周有同色圆角装饰边框围合;封面中文全部为竖排,中间是很大的露白书法体刊名“言治”。《言治》月刊封面采用了双色印制,总体看上去显得简陋。封面没有图形,只由刊名、期号等中外文字组合构成,文字围合的样式像西式拱门状,竖排的汉字显现出其受到中国传统书籍装帧的影响,而外文的排列完全是西式风格。封面构图平稳,在草绿色的底色的衬托下,刊名“言治”二字显得非常突出,形成中国碑文拓印的视觉效果。《言治》的版式设计沿用了中国传统书籍版式,正文是上下阅读方式,标题和正文都是宋体字,标题的字号要比正文大一些。正文没有标点符号,以黑点标注断句。正文版心较小,四周留白较大,阅读起来比较清爽。《言治》作为民国初期的政论杂志,主要价值在于从其创办到内容均呈现李大钊早期的思想变化,反映了李大钊从一个具有国家民族危亡忧患意识的知觉者成长为拯救国家民族自觉者的过程,也印证了中国共产党成立的必然性。《言治》的设计也反映出当时中国传统文化在西方先进文化的冲击下开始蜕变,寻求设计和文化上的自我重塑,这个过程是深刻的、革命的。
《新青年》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早期传播的重要阵地,陈独秀、李大钊等作为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都曾是《新青年》的主要编辑。《新青年》从创刊号开始就颠覆了传统杂志封面的设计样式,如“万树江边杏,新开一夜风”,让人耳目一新。《新青年》设计最突出的是刊名——“新青年”,红色的三个字,“新青年”为手写设计体,整体为黑体字形态,但夹含隶书韵味,厚重而不失灵动。“新青年”三个字呈上窄下宽梯形状,在视觉上表现出挺拔向上的力量感,置于封面最上端,引人注目,给人以冲破旧世界的感觉。《新青年》的设计秉承该刊办刊同人的激情与理想,尽可能以简明的形式来强调一种力量感和速度感,设计上充满对现代文明的憧憬以及对民族崛起的理想。从某个角度而言,《新青年》的设计开启了近代中国平面设计的现代意识,展现了设计的时代力量。
这一时期还出现了主张公理、反对强权的《每周评论》、唤醒民族觉悟的《国民》《新潮》《晨报副刊》《京报副刊》、为劳工呐喊的《劳动音》《工人周刊》、孕育青年无限希望的《先驱》、少年强则中国强的《少年中国》,以及饱含青春热血的五四运动纪念章、劳工神圣的长辛店工人俱乐部证章等,这些都是红色设计初生的扛鼎之作,每一个设计都独具特色,它们发出拯救民族危亡的呼喊、充满了寻求中华出路的急切渴望。
(二)大革命风暴中的北京红色设计(1924—1927年)
第一次大革命时期,北京的群众运动此起彼伏。“这一时期,北京处于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政府的统治之下。扩大党的组织、建立革命的统一战线,发动群众运动,配合和支援南方的国民革命军北伐,成为中共北京组织的主要工作和活动。”[3]中共北京区委在李大钊的直接领导下,积极发展北方革命力量,广泛宣传马克思列宁主义,提高党员团员的理论水平。此时,北京红色设计以书报刊和印刷宣传品为主,在设计风格上呈现出朴素、简约等特点。
《政治生活》于1924年4月27日在北京创刊,1925年秋成为中国共产党北京区委机关刊物,是中国共产党地方组织中最早创办的刊物,也是这一时期北京红色设计的代表。《政治生活》的发刊词旗帜鲜明地表明立场:本刊的使命,便是要领导全国的国民,向奋斗反抗的政治生活走![4]李大钊非常重视《政治生活》的编辑、出版、发行等工作,并为该刊撰写了许多文章,使之成为党在大革命时期战斗性极强的刊物,风行全国。从第62期开始,《政治生活》的设计由“报纸形态”改为“刊物形态”。这表明,红色刊物在办刊理念和设计思想上较以往都有了新的变化,更趋于现代期刊的概念。刊头设计是《政治生活》的最大亮点,“政治生活”四个字笔画粗壮,字体棱角分明、方正有力,充满强烈视觉张力的字体设计如音乐中的强音拨动人的心弦,给人以振奋的力量。刊名后面有象征共产主义的圆形图案衬托,图案由镰刀、锤子、五角星和车轮构成。刊名和背景图案均有斜向留白线条画过,营造出一种疾风劲草般的视觉效果;使人产生革命者在艰难处境中义无反顾、坚定前行的联想。
这一时期,北京还产生了《语丝》《莽原》《蒙古农民》《猛进》等一批宣传革命和进步思想的刊物。鲁迅主编的《莽原》是一本文艺期刊,提倡“撕毁旧社会的假面”,注重文明批评和社会批评。鲁迅在《华盖集·题记》中阐明了办刊宗旨:“我早就希望中国的青年站出来,对于中国社会、文明,都毫无忌惮地加以批评,因此曾编印《莽原》周刊,作为发言之地,可惜来说话的竟很少。”大革命时期,鲁迅在北京创作出版了一系列红色进步书刊,鲁迅的书籍装帧设计体现出他追求民族与现代相结合、简约与装饰相结合的设计美学观,“鲁迅对封面设计观点,是希望能够体现我国自己的面貌,而不同于别国的风格,这个见解是十分重要的”[5]。鲁迅亲自设计了《呐喊》《桃色的云》《热风》《中国小说史略》《华盖集》《坟》等书刊的封面,他还指导并影响了陶元庆、钱君匋、孙福熙、司徒乔、陈之佛等人从事书籍装帧设计,对近现代中国书籍装帧设计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
(三)土地革命时期的北京红色设计(1927—1937年)
第一次大革命失败后,中国革命转入低潮,中国共产党人继续坚持斗争,在挫折中艰苦探索革命道路。北京(平)的中共地方组织受到严重破坏,虽然党组织及其活动处于极端艰难困苦的境地,但中共北京(平)地方组织领导广大人民群众同新旧军阀进行了不屈不挠的斗争。这一时期的北京红色设计仍然以书报刊和印刷宣传品为主,呈现出材质粗糙、外包伪装、隐蔽性强等特点,体现出共产党人冲破白色恐怖、勇于牺牲、一往无前的大无畏精神和价值追求。这一时期红色设计的代表作品有:推动顺直党组织改造的《出路》、作为广大工农群众喉舌的《北方红旗》、冲破黑暗洪流激荡的《火线》等。
《出路》是继《顺直通讯》后中共顺直省委的第二个机关刊物,《北方红旗》《火线》是中共顺直省委的秘密刊物。顺直省的干部和党员在这些刊物上发表关于党的建设、工农运动、反帝斗争、互济工作、对敌斗争策略等方面的指示和文章,指导和推动顺直省的革命工作。刘少奇为《出路》创刊撰写序言,他还以肇启、KV为笔名,在《出路》《火线》上发表《怎样改造顺直的党》《客观环境很好,但是党没有出路吗?》《把一般的原则与现实生活中的具体问题联结起来》《怎样进行群众工作》等一系列文章。周恩来也曾在《出路》上发表文章。由于北京处于军阀白色恐怖统治之下,革命环境异常艰苦,党的工作在地下秘密进行。为了保护革命,共产党人发明了伪装隐蔽设计,刊物封面多采用图画的设计方式,以达到伪装隐蔽效果。如《出路》第7期封面画的是“春江水暖鸭先知”情景,喻示革命情况好转。第6期、第9期的封面都是情景式的淑女图画,画面表现与中国传统小说中的绣像非常相似。《火线》第3期封面设计放大突出镰刀锤头形象,这在同时期的革命刊物中很少见。《火线》第4期封面最引人注目的就是在封面中央的列宁图像和刊名“火线”两个字,列宁图像是木板刻印、“火线”二字是设计字体,两字既统一又给人突破感,显现出很高的专业水平。
革命环境是艰难的,但革命斗志是昂扬的。此时还涌现出《顺直通讯》《直之生活》《长城》《暗流》《东方暨白》《北方青年》《北平文化》等许多进步刊物。1930年9月18日,北方左联成立,它的成立推动了北方左翼文化运动的开展,北方左联曾先后创办《前哨》《北方文艺》等30余种刊物。这些刊物大都是蜡板油印本,设计简单、印刷工艺简陋,这也反映出当时中共顺直党组织的工作条件是非常艰苦的。许多刊物采取伪装隐蔽的设计手法,显示了革命者对敌斗争的智慧和策略。虽然这些刊物印制工艺不是很好,但它们为宣传党的政策方针、为革命工作在敌后开展发挥了很大作用。
(四)抗日战争时期的北京红色设计(1931—1945年)
1931年九一八事变拉开了中国长达14年抗战的序幕。北平作为全民族抗戰的始发地,平郊抗日根据地作为晋察冀抗日根据地的前哨,涌现出众多富有革命特色的红色设计。一手文、一手武,红色设计既有书刊报纸、插图宣传画,也有兵器徽章、地道等,设计体现出抗击日本侵略者的不屈精神和顽强斗志。代表性作品有《文艺月报》(北平)、《挺进报》、抗战木刻、抗战宣传画、抗战徽章、晋察冀日报社印刷机设计、焦庄户地道设计等。
《挺进报》于1939年9月1日在平西抗日根据地创办,是中共冀热察区党委机关报。《挺进报》为4开4版,“报纸除了刊登新华社的新闻稿外,主要还刊登本地区的新闻和评论文章”[6]。《挺进报》在平西时采用石印,转移到平北后由于条件限制,只能采用油印。抗战时期,版画成为宣传记录抗战、鼓舞人心的重要艺术形式。1933年4月16日至19日,北平木刻研究会首次举办展览(在北平西长安街艺文中学),展出北平及上海木刻家作品约百幅。《北京晨报》《北辰报》等报纸对展览做了报道。如4月19日《北辰报》第3版《木刻展览会》一文指出:“这次展览在‘荒漠的北平……恐怕是破天荒的出现吧!而会场中‘那令人兴奋的静的动人的空气,是叫你肃然起敬,顿时觉得你的周遭尽都是黑暗和恶魔,你的前途呈现着希望和光辉!多数作品‘都能抓住时代的精神,‘不失为新兴的一种运动。”[7] 1935年元旦,“全国木刻联合展览会”在北平太庙开幕,第一天参观者达到五千多人,震动了平津舆论界。
焦庄户地道位于北京顺义焦庄户村。抗日战争时期,这里的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利用地道与日本侵略者展开英勇斗争,用不屈的精神和超人的智慧,筑就了坚固的“人民第一堡垒”,谱写出一曲人民战争的壮丽诗篇。焦庄户地道的设计让人拍案叫绝,地道内设计和安装了掩体、会议室、水缸存放处、陷阱、翻板、碾盘射击孔、地道射击孔、猪圈射击孔等生活设施和战斗设施。地道在实战中不断被改造和扩展,最后形成户户相连、村村相通、四通八达、上下呼应,能藏、能走、能防、能打的“四能”地道网。
抗日战争时期的北京红色设计映射出伟大的抗战精神,这些设计体现了“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爱国情怀、宁死不屈的民族气节、不畏强暴血战到底的英雄气概和坚韧不拔的必胜信念。
(五)解放战争时期的北京红色设计(1945—1948年)
抗战胜利后,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为建立一个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新民主主义国家而斗争。这一时期北京红色设计作品以宣传中国共产党的主张、揭露国民党阴谋、争取广大人民群众为主要目标,具有广泛性、大众性、通俗性等特征。这一时期红色设计的代表作品有:第一套人民币、《论人民民主专政》、北平《解放》报、《人民日报》(北平版)、《进步日报》《光明日报》,以及为民主发声的《民主周刊》(北平版)、“六八斗”斗争相关设计和双清别墅相关设计等。
1947年10月24日,中共中央批准华北财经会议决议,华北、西北和华东三大解放区首先进行货币统一工作。1948年12月1日,中国人民银行成立,并宣布从即日起发行中国人民银行钞票“人民币”。“人民币”在新中国成立前夕的炮火硝烟中诞生,成为新中国的统一货币。第一批发行的人民币有三种:50元水车矿车票券、20元运肥火车票券和10元灌田矿井票券。第一套人民币从1948年12月1日开始发行到1955年5月10日停止流通,共12种面额62种版别。
近代中国钱币主要依靠外国人设计印制,没有中国人自己的设计思想和文化风格。第一套人民币的出现打破了近代中国钱币设计“洋化”的窠臼,第一次展现了中国人民自己货币的风范。第一套人民币上的图案有劳动人民、解放区劳动场景、交通运输工具、优秀传统建筑等;除了必要的阿拉伯数字外,钱币上的文字全部使用中文;董必武为第一套人民币票版题写了“中国人民银行”行名、面额大写数字和纪年等文字。
第一套人民币的设计生动展现了中国解放事业及新中国成立初期人们的劳动、生活、文化和社会活动场景,其设计理念体现了以人民为中心、人民当家作主的政治主张,反映出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全国各族人民自力更生、艰苦奋斗、齐心协力、埋头苦干建设新中国、新社会的激情和豪迈。正如毛泽东所说:“人民有了自己的武装,有了自己的政权,有了自己的土地,现在又有了自己的银行货币,这才真正是人民当家做主的共和国哩!”[8]第一套人民币的设计思想影响了后来各套人民币的设计,为人民币的设计与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
《论人民民主专政》、北平《解放》报、《人民日报》(北平版)、《进步日报》等的设计在北京红色设计历史上也都具有里程碑意义,记载了新中国建立大的节点事件。解放战争时期的北京红色设计有力地配合了人民解放战争的胜利,对于推翻国民党反动统治、解放全中国起到了重要作用,见证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革命从农村走向城市,从胜利走向胜利的伟大转折,取得新民主主义革命伟大胜利的光荣历程。
(六)构建新中国形象的北京红色设计(1949年)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庄严成立,饱受蹂躏和屈辱的中华民族以独立自强的新姿态屹立东方。新中国需要新形象,这是集中体现国家主权、人民尊严和民族精神的视觉宣言。新中国的形象设计作为北京红色设计实践的重要内容,选择与既往符号有所区别,又恰当代表新中国性质与特征的视觉元素,构建具有影响力的国家形象系统,成为这一时期北京红色设计的主题。代表作品有:中国人民解放军军旗、八一军徽、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徽、中国人民政治協商会议会徽以及人民英雄纪念碑等。这些设计既代表国家形象和气度,又体现了北京在参与新中国成立时对红色设计组织工作所起到的重要作用。
中国人民解放军军旗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武装力量的标志,是中国人民解放军荣誉的象征。早在秋收起义时期,何长工、陈树华、杨立三等人设计了中国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军旗,这面旗帜成为中国革命军队军旗的基本样式。此后,人民军队的军旗样式经历多次修改,但组成军旗的基础图案(五角星、镰刀、斧头或锤子)和鲜红的旗色没有改变。1947年,中国人民解放军进入战略反攻阶段,但全军仍未有统一的军旗和徽标。1948年2月21日,中央军委发出指示电报,向各中央局、各军区、各野战军前委及中央工委、中央后委,征求设计全军统一军旗、军徽、帽徽和臂章的意见。征集工作持续近一年时间,各机关单位踊跃报送设计方案。毛泽东对军旗设计作出重要指示:军旗上要有“八一”二字,象征1927年8月1日南昌起义打响中国革命第一枪,是建军之日;要有五角星,象征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周恩来指出,军旗要以具有革命性的红色作为底色。因此,“八一”字样、五角星与红色旗底,成为中国军旗设计的重要提示。1949年6月15日,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委员会在北京开幕,会议以“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名义颁布命令,正式规定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军旗样式:旗幅为红色,制式横竖比例为5∶4的长方形,靠旗杆上方缀金黄色五角星与“八一”二字。因而也简称为“八一”军旗。
1949年7月14日至8月15日,《人民日报》《解放日报》《新华日报》等重要报刊先后刊登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在全国范围内征集国旗图案的通知,呼吁人民群众为新中国国旗的设计创意贡献想法。短短一个月的时间,组委会便收到1920件应征稿件,共有2992幅国旗图案作品。筹备会委员与专家们从近三千幅应征图案中遴选出38幅。最终,32号方案“红地五星旗”获得筹委会及领导专家们的一致认可,确定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方案,并改名为“五星红旗”。1949年9月28日,《人民日报》各大报纸刊登了国旗的最终确定方案,公布《国旗制法说明》。曾联松设计的五星红旗图案经过修改与定稿,被选中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图案。
1949年7月16日,《人民日报》刊登启事,公开征求国旗国徽图案及国歌词谱。1950年9月20日,毛泽东主席签署《中央人民政府命令》,公布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徽图案及说明,国徽设计方案最终确定。该说明对国徽的色彩与图案作出明确规定:国徽之涂色为金红二色:麦稻穗、五星、天安门、齿轮为红色,圆环内之底色及垂绶为红色;红为正红(同于国旗),金为大赤金(淡色而有光泽之金)。
新中国成立时的红色设计任务繁重、意义重大。每一件红色设计物都振奋人心,饱含着设计者的心血与激情,经历了传奇般的设计过程。新中国的形象设计既是对中国革命历程的回望与总结,也是中国共产党人对未来发展新征程的开拓与探索,具有民族性、凝聚性、独特性、开拓性等特点。诞生于北京的国旗国徽、军旗军徽、人民政协会徽、人民英雄纪念碑等设计物,既代表了国家的形象与气度,又体现了北京为新中国成立在红色设计组织工作中所做的重要贡献。
二、北京红色设计的特征
红色设计是革命精神、革命意志、革命目标相结合的产物。北京红色设计伴随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中国共产党成立、大革命风暴、抗战烽火、解放战争硝烟、新中国成立的革命历程一路走来,形成了自己独特的发展历史和精神气质,概括起来主要有以下特征:
(一)革命性
革命是历史的火车头,是历史向前发展的重要推动力量。对实践的唯物主义者即共产主义者来说,全部问题都在于使现存世界革命化,彻底的革命性是马克思主义政党的内在规定。革命性也是红色设计的天然属性,其天然性由三个因素决定:一是红色设计的动机是革命的。红色设计从开始的设计动机和意识就是为了革命需要,需要是多元化的,可能是宣传、展现,也可能是群众活动或武装斗争。不论是一张传单设计,还是一个封面设计,从设计开始就明白设计需要,明白设计为谁而用,明白如何设计。如:土地革命时期的书刊是传播革命思想、传达党的指示的重要载体。艰难的革命环境决定了革命方式必须以地下隐蔽的方式进行。因此,红色书刊在外观上被设计成普通书刊的样式,但里面却藏有革命的内容。二是红色设计的目的是革命的。红色设计的目的就是为了打倒敌人、强大自己,创建新中国,建设伟大的社会主义中国,复兴中华民族。在这样的目的感召下,红色设计充满激情和力量。三是红色设计的表现是革命的。任何事物或现象总有内容与形式两个方面,总是内容与形式的矛盾统一体,内容决定形式,形式反作用于内容。红色设计的外在表现形式源于其设计的目的和要表现的内容,红色设计表现的内容是进步的、革命的,所以,红色设计所呈现的形式必然是进步和革命的,而这也逐步形成了红色设计特有的设计观和美学观。
(二)时代性
红色设计伴随着中国共产党的诞生与发展,具有强烈的时代性特征。中国共产党在不同阶段有着不同的目标和任务。例如,在中国共产党初创时期,党的主要任务就是广泛传播马克思主义,成立中国共产党。围绕这一任务和目标,革命者不断演讲、出版书报刊、发表革命文章。因而这一时期的红色设计主要体现在书报刊方面。解放战争时期,党的主要任务是解放全中国,迎接新中国的诞生。新中国第一套人民币设计、《论人民民主专政》书籍设计等突出地反映了这一时期的党的工作目标,并为实现目标发挥了重要作用。红色设计不仅是一种设计类型或样式,它更印证了中国共产党的漫漫发展历程,丰富了中华民族五千多年的灿烂文化,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人和中国人民的文化图腾和精神皈依。红色设计是红色文化的突出代表,从文化角度看,红色设计既具有文化的认知性特点,也具有文化的改造性特点。文化的认知性表现为精神层面,文化的改造性体现在物质载体方面。所以,红色设计凝聚着革命精神,以精神感召、锻造马克思主义信仰者,同时它也以具体物化的形态被人民认识和感知。中国共产党是百年大党,正向着第二个一百年进发。在一百年的发展历程中,红色设计在不同阶段呈现出不同的时代性,在今后的前进道路上依然会呈现出阶段特点,但是中国共产党的本色不会变、精神不会变、为人民服务的宗旨不会变,这个全过程的时代性特征是永恒的。
(三)传承性
源浚者流长,根深者叶茂。传承意为传授与继承,传承代表了事物的发展。事物的产生和发展必然有其本源,就像浩浩荡荡的大江大河是由無数条支流小溪汇聚而成,但源头却是冰雪融化的水滴。红色设计的源流就如同江河,它的发端也有源头,中国共产党成立是红色设计的源头,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和使命是推动红色设计不断发展的魂魄和动力。中国共产党党徽的演变过程是红色设计传承性的最好写照。党旗党徽是中国共产党的象征和标志,党徽的图案是由镰刀和锤头组成的。镰刀象征着农民,锤头象征着工人,镰刀与锤头的组合象征着以工农为主体的无产阶级。1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宣告成立。建党初期所使用的旗帜样式均是模仿俄共(布)的旗帜,红色旗面上有镰刀和斧头或镰和犁的图案。1927年9月9日,毛泽东领导秋收起义,起义部队打出工农革命军的旗帜,红色旗面中央是白色五角星,五角星里面是黑色的镰刀和锤头。同年10月15日,《中共广东省委通告(第14号)》指出:“一律废除青天白日旗,改用红旗以斧、镰为标志,与国际旗同。”中国共产党第一次正式规定以“镰刀斧头”作为党的标志。在此之后,镰刀锤头标志被广泛使用。新中国成立后,党徽的形象多次变化。1982年9月召开的中共十二大会场首次悬挂了党徽。1996年9月21日,《中国共产党党旗党徽制作和使用的若干规定》对党徽、党旗作出规定。2021年6月26日,《中国共产党党徽党旗条例》规范了党徽党旗的样式。从党徽的演变可以看到一代代中国共产党人不断守护、传承党的根脉,虽然党徽图案一直在变化,但镰刀锤头形象始终没有改变,党的初心始终没有改变。
(四)创新性
创新是突破、创造,是打破旧的思维,开拓新的思想,不断创造新成果的过程。一切创新成果都是人类智慧的物化,都是思维的结晶。红色设计的基本属性是设计,创新必然是其特征之一,也是推动红色设计不断向前发展的不竭动力和设计者始终不渝的追求。红色设计的创新性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设计思想创新,二是设计形式创新。红色设计作为人类智慧的创造性活动,设计者在设计过程中始终保持创新性思维,其成果都是创造性智慧的凝聚。与一般设计不同,红色设计不只是设计者个体思想的表现和表达,更主要是党的意志主张与目标诉求的体现。例如,北京天安门广场的人民英雄纪念碑设计。人民英雄纪念碑是近代以来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争取民族独立解放、人民自由幸福和国家繁荣富强精神的象征,是国家和人民纪念、缅怀英雄烈士的永久性纪念设施。人民英雄纪念碑作为中国历史上单体规模最大的纪念碑,是新中國成立后首个国家级艺术设计工程。1952年5月10日,首都人民英雄纪念碑兴建委员会成立。委员会由全国政协、全国总工会等17个单位组成,彭真担任委员会主任。建设团队汇聚了魏长青、郑振铎、吴作人、梁思成、刘开渠、彦涵等一大批当代中国最优秀的文史专家、建筑学家、艺术家、工程师与能工巧匠。设计方案几经设计、审核、修改,最终确定纪念碑外观为碑塔形建筑,“突出碑文”。这一设计思路既体现了中央的要求,也与梁思成的主张密切相关。1958年4月,人民英雄纪念碑落成。它造型沉稳大气、庄严肃穆、极具民族气度,同时蕴含着深厚的中华文化和深切的怀念之情,不论从历史文化维度还是从现实空间维度都给人以极大的心灵震撼。
(五)先进性
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社会意识是社会存在的反映。任何文化的生成、生存和发展都离不开特定的社会历史条件。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和发展是中国近现代历史发展的必然选择,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必然结果,更是中国共产党先进性的集中体现。红色设计是中国共产党的理想目标与思想意志的形象体现。红色设计的先进性源于中国共产党的先进性,党的先进性铸就了红色设计的先进性。红色设计的先进性除了体现在其代表的主体先进外,还体现在其传达的思想内容和表现形式也是先进的。红色设计的表现内容具有正确的价值观,符合广大人民群众利益,代表中华优秀文化。红色设计的表现形式与内容相辅相成,往往呈现出最好的效果,代表一个阶段或时代的最好水平。例如,鲁迅的小说《呐喊》的封面是腐血一般的暗红色,在暗红色中间嵌着一块黑,黑块上以中国印章的方式镌刻着“呐喊”和“鲁迅”四个字,犹如被压迫的人挣扎着、发出大声的呼喊。《呐喊》封面在设计上以大面积的留白与小块黑色的对比造成视觉上的不平衡,而黑色块又给人以坚硬、坚强的感受,让人过目难忘。封面设计借用了中国古代线装书的表现手法,但更具有现代主义色彩,可称得上是中国近代书籍设计史上的佳作。
三、北京红色设计的价值贡献
北京红色设计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北京人民进行新民主主义革命的重要艺术设计见证,也是北京红色文化与红色革命精神的凝聚物,具有独特的艺术价值和重要的历史贡献。
(一)见证革命斗争历程
北京红色设计通过设计语言的成熟、视觉图形的提炼、物品功能与技术改进等方面,生动地呈现了红色设计对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参与及贡献,鲜活地体现出革命者在艺术设计领域的创作实践及独特贡献。中国共产党成立前后时期,北京红色设计在全国具有引领性与示范性,在设计物形态与面貌上,北京红色设计呈现出极大的丰富性。陈独秀、李大钊等人编撰的宣传马克思主义思想的进步书刊,以及以鲁迅为首的革命家创作的文学革命书刊,其编撰与设计都是北京红色设计的重要组成部分,其标识、插图和刊题设计,都具有鲜明的革命特征。大革命时期和土地革命时期,中共北京(平)地下党领导人民,积极开展反帝爱国学生运动和工人罢工斗争。虽然北京(平)政治环境更加严酷,但红色设计继续肩负传播马克思主义、宣传中国共产党政策主张、反抗国民党残暴镇压、鼓舞人民革命斗志的使命任务,不过形式上更加隐蔽。无论革命刊物还是革命组织标识,不得不以灰色的伪装面目出现,但其属性依然是进步的、革命的,也就是红色的,因此成为白色恐怖下反动当局封杀“围剿”的目标,遗存至今的红色设计物可谓弥足珍贵。1937年七七事变之后,中国进入全民族抗战阶段。北平成为日伪当局统治华北地区的中心城市,平郊抗日根据地逐步发展成为晋察冀抗日根据地的前哨,大到报刊武器小到徽章皮包,出现了许多富有抗战意义和时代特色的红色设计,不仅在物质上对抗战起到了推动作用,在文化层面上也起到了鼓舞激励人民抗战斗志的作用,体现了中国人民伟大的抗战精神。随着解放战争的不断胜利,新中国的国家形象设计提上了重要的议事日程。这一时期,北京(平)红色设计成为中国红色文化历程的集中显现。包括美术设计、建筑工程与文史在内的各界专家学者,组建高效设计团队,发挥高超的专业能力,完成了代表中国人民解放军形象的八一军旗、军徽,以及代表新中国形象的五星红旗、国徽创作设计任务。北京意象符号与国家形象符号生动叠合,形成人民军队、人民共和国的视觉表征。新中国的形象设计,是这一时期北京红色设计的集中体现。北京红色设计见证了中国共产党伟大非凡的革命历程。
(二)促进视觉语言革新
北京是近现代中国北方的政治中心、文化中心,作为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发祥地之一,也是最早创立共产党组织的城市之一。北京的城市环境和文化氛围,对马克思主义的宣传、中国共产党的孕育起到了重要作用。20世纪初期,在新文化运动影响下,北京涌现出《新青年》《每周评论》《新潮》《国民》等一批进步刊物和社团,有力扩大了新思想、新文化、新文学的社会影响。北京大学成为宣传马克思主义的主阵地,以《新青年》《每周评论》为代表的进步期刊,积极宣传马克思主义。李大钊以开拓者的无畏姿态,旗帜鲜明地指出马克思主义是时代的真理,是“拯救中国的导星”。正是李大钊等一批革命家的救国救民理想抱负,使得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得到广泛传播。为了传播新思想、新文化,宣传马克思主义,在极其危险恶劣的办刊环境下,进步刊物以地下出版物、伪装本等形式出现,出版行为与设计行为呈现出不屈不挠的革命性、开拓性。仅以此为例,足以说明北京红色设计丰富了革命斗争的形式,促进了革命斗争的开展。北京红色设计以思想的革命性为先导并自觉体现,而红色设计为革命宣传提供了新的图形及样式,在思想革命的同时,也进行着视觉与造型上的革命。思想的革命性与视觉语言的革命性同时发生。正如毛泽东 “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的著名论断,北京红色设计正是红色设计星火中的重要火种,从井冈山革命的第一面军队旗帜到中国人民解放军的旗帜,从红军帽徽的设计到国徽的设计,它将现代设计的创新性与中国革命的斗争性生动地结合起来,以其独特的方式参与了中国革命历程。北京红色设计具有重要的影响力,它促进了视觉语言革新和革命斗争的开展,在北京及整个中国革命斗争中发挥了独特作用。
(三)体现传统现代融合
北京红色设计的革命性及其所反映出来的现代性,二者相互关联、密不可分。20世纪初的北京红色设计,具有生动的现代性的反思,在书籍形态设计上,展现出对于传统书籍装订、印刷、排版、构图等方面的反叛与实验;在内容筹划与编辑上,对于西方现代设计语言的借鉴与吸收,体现出北京红色设计的现代性。现代设计元素影响了红色文化的传播路径与效果,新艺术运动与装饰艺术运动中的图形与装饰元素,在《新青年》等杂志的封面与版式设计中屡有体现;俄国构成主义、荷兰风格派和达达主义的艺术创作手法,在海报、图形、徽标等北京红色设计中有生动呈现,西方现代设计元素被美术工作者自觉或不自觉地应用到红色文化的设计实践之中。鲁迅的《狂人日记》《孔乙己》《药》等代表作以及《呐喊》《彷徨》等作品集,在文学创作与书籍装帧上,均呈现出从传统向现代转型的探索,并引领了一批有志从事书籍装帧、插图与版画创作的进步青年。北京红色设计,充分联结与展示了传统文化与红色文化。参与中国革命的美术工作者们,在创造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革命视觉符号时,自觉地将中国传统文化与艺术因素融到现代审美与现代设计的探索中。因此,北京红色设计是传统性、现代性与革命性为一体的视觉呈现,是古为今用、洋为中用、推陈出新的设计艺术的成功实践。
(四)传承红色设计之魂
红色是革命的色彩,也是中国共产党的底色;是中国近现代革命历史的背景色,也是新中国继往开来的未来色。每一件北京红色设计物,都承载了革命艺术设计者的生命热情与专业智慧,聚焦着一个个中国革命的生动故事。北京红色设计无论在视觉上、造型上还是功能上,都集中呈现红色文化的精神气质,具有深远的历史影响。现代设计的发展,受社会经济、政治、文化、制度等因素的深刻影响,北京红色设计发展历程有力地说明了这个道理。北京红色设计通过独特的艺术设计路径,呈现出红色历史的视觉印象、红色文化的精神脉动、红色革命的精神之魂,从现代设计实践的角度参与了中国红色文化的构建。敢为人先的创作精神、勇于斗争的革命精神、服务大众的艺术精神,是北京红色设计之魂。在推进全国文化中心建设、构建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之都、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的征程中,红色设计必将继续以独特的方式参与其中,必须传承弘扬红色设计之魂。
[参考文献]
[1][2] 张彬:《北京红色设计》,北京出版集团、北京出版社2020年版,第1—2、8—9页。
[3] 中共北京市委党史研究室编:《中国共产党北京历史大事记1919—1949》,北京出版社2001年版,第42页。
[4] 欧阳淞、章育良主编:《红藏:进步期刊总汇(1915—1949) 政治生活》,湘潭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1页。
[5] 上海鲁迅纪念馆、中国美术家协会上海分会、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鲁迅与书籍装帧》,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1981年版,第3页。
[6] 何光:《驰骋敌后的一支新闻轻骑——忆平北抗日根据地的〈挺进报〉》,《北京党史研究》1989年第4期,第45—50页。
[7] 李允经:《北平木刻研究会和北方木刻运动》,《新文學史料》1984年第2期,第139—143页。
[8] 邓加荣:《开国第一任央行行长:南汉宸》,中国金融出版社2006年版,第277—278页。
Study on the Development Context and Characteristic
Value of Beijing Red Design
ZHANG Bin1, ZHANG Xiaoxin2, HUANG Chao3
(1.School of Design Arts, Beijing Institute of Graphic Communication,Beijing 102600,China;
2.Library, Beijing Institute of Graphic Communication, Beijing 102600, China;
3.Capital Museum, Beijing 100038, China)
Abstract: Red design is a purposeful artistic creation with a revolutionary spirit as the core, which expresses red culture through visual forms and becomes a red mark presented by the Chinese people led by CPC in the historical process of revolution, construction, and reform. Red Design integrates Marxist theory, political science, journalism and communication, fine arts, design, etc., to explain the history of CPC and Chinese design from a new perspective. Taking the development history of CPC in Beijing as the main line, this paper focused on sorting out and elaborating the development context, characteristics, and values of red design in Beijing from 1915 to 1949, so as to promote in-depth research on red design, deepen the understanding of Marxism in the Chinese era, and enhance cultural self-confidence and self-improvement.
Key words:Beijing; red design; red culture; revolutionary spirit
(责任编辑 编辑孙俊青;责任校对 编辑刘永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