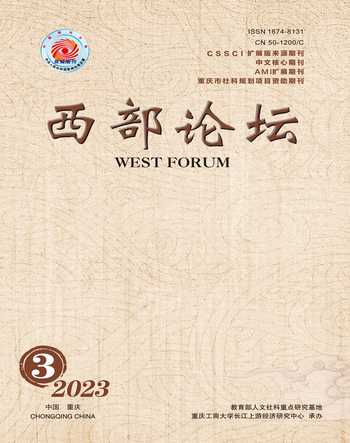劳动智能化改善了劳动者就业质量吗?
2023-07-29明娟鲍翔宇张艺
明娟 鲍翔宇 张艺



摘 要:劳动智能化不仅提高了劳动效率和生产质量,而且对劳动者的就业状态产生了深远影响。采用中国劳动力动态调查(CLDS)2018年个体问卷数据的分析发现:相比劳动还未智能化的劳动者,劳动智能化的劳动者具有较高的就业质量,经过内生性处理和稳健性检验后该结论依然成立;劳动智能化有利于劳动者的工资增长,但对劳动者工作条件的影响不显著,表明劳动智能化主要是通过提高劳动报酬来提升样本个体的就业质量;劳动智能化对不同类型劳动者就业质量的影响存在显著差异,表现为对男性劳动者、35岁及以下劳动者、高技能劳动者的就业质量改善作用较强;劳动智能化对就业质量的改善受到劳动者非认知能力的调节,即劳动者非认知能力的提高会强化劳动智能化的就业质量改善效应。因此,在积极推进劳动智能化的同时,要不断提升劳动者技能水平和非认知能力以增强劳动者的智能化适应能力,还应特别重视劳动者工作条件的改善以充分发挥劳动智能化改善工作条件的潜在功效。
关键词:劳动智能化;就业质量;货币收入;工作条件;劳动技能;非认知能力;智能化劳动
中图分类号:F062.4;F24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674-8131()0-0001-14
引用格式:明娟,鲍翔宇,张艺.劳动智能化改善了劳动者就业质量吗?[J].西部论坛,2023,33(3):1-14.
MING Juan, BAO Xiang-yu, ZHANG Yi. Does labor intelligence improve the quality of laborer employment?[J]. West Forum, 2023, 33(3):1-14.
一、引言
中国式现代化要持续增进民生福祉,不断提高人民生活品质。劳动者的就业质量是民生福祉的重要内容,在实现社会财富快速增长的同时,切实提高全体劳动者的就业质量是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本质要求。技术进步不仅会改变经济发展形态,也会革新劳动方式,劳动智能化成为数字经济下劳动方式演变的必然趋势。劳动智能化,是指在劳动过程中利用先进的智能技术和设备,实现劳动过程自动化、智能化和数字化,以提高生产效率、降低成本的劳动模式转变。从理论上讲,得益于技术进步的劳动智能化改变了传统的生产模式,提升了生产效率,增强了生产的可持续性和竞争力,并可以改善劳动者的劳动条件,减少人工操作,降低工伤事故率。那么,在经济实践中,劳动智能化能否带来劳动者就业质量的显著改善?虽然越来越多的经验证据表明劳动智能化对生产力发展具有积极的影响,但关于劳动智能化对劳动者的影响,相关文献的实证分析主要聚焦于就业机会和收入水平等,而就业质量是对劳动者工作状况的综合评价,包含多维特征(侯俊军 等,2020)[1]。因此,劳动智能化对劳动者就业质量的影响及其机制还有待更加全面深入的研究。
劳动智能化是智能技术及机器人等智能应用于生产过程的结果,会对劳动力市场和就业质量产生深远影响。现有研究主要探讨了人工智能、工业机器人等对就业质量的影响,并形成两种观点:一是抑制论,认为人工智能等会对劳动者就业质量的提升产生不利影响。比如,智能化产生的替代效应会降低劳动者工作的稳定性和社会保障水平,从而影响劳动者就业质量(齐乐 等,2022)[2]。二是提升论,认为人工智能等会提高劳动者的就业质量。比如,智能技术可以通过提高生产效率、缩短劳动者工作时间、优化人力资本结构、促进劳动要素自由流动等途径提升劳动者就业质量(王军 等,2018)[3];人工智能能够通过“人机融合”提高劳动效率、优化产业结构、提升人力資本水平等促进就业质量改善(陈志 等,2022)[4];“机器换人”可以提高在岗职工的收入,并改善工作环境,进而促进就业质量提升(侯俊军,等,2020)[1]。总体来说,关于智能技术应用对劳动者就业质量的影响,还未得到一致性结论,且缺乏从劳动智能化角度进行的深入研究。
本文旨在探讨劳动智能化对就业质量的影响,并采用“中国劳动力动态调查”(China Labor-force Dynamics Survey,CLDS)2018年的数据进行实证检验。本文的边际贡献主要在于:一是有别于现有文献多从宏观层面分析智能化对劳动者就业和工资等的影响,采用CLDS个体问卷数据从微观层面分析劳动智能化对劳动者个体就业质量的影响;二是已有文献多基于工资收入、工作环境、工作强度等单维度指标分析智能化对劳动者就业的影响,本文基于劳动者的货币收入和工作条件构建多维度的就业质量综合指标,分析了劳动智能化对劳动者综合就业质量的影响;三是进一步分析了非认知能力在劳动智能化影响劳动者就业质量中的调节作用,并从性别、年龄、技能等方面探究了劳动智能化影响劳动者就业质量的异质性,为劳动智能化的就业质量改善效应及其作用机制提供了经验证据。
二、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说
1. 劳动智能化对劳动者就业质量的改善
劳动者的就业质量通常包括劳动报酬和劳动环境(条件)两个方面。根据现有研究,劳动智能化可以产生补偿效应,促进整体就业增长,并通过收入提升效应、工作条件改善效应等来改善劳动者的就业质量。从补偿效应来看,智能技术应用带来的效率提升和技术扩散使得相关产业规模扩大,增加总体就业需求(惠炜,2022)[5],从而弥补劳动被智能技术替代产生的失业;还可以创造出新的就业岗位,稳定和增加劳动力就业(Mcguinness et al,2019;蔡跃洲 等,2019)[6-7]。
一方面,劳动智能化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不仅会降低生产成本,而且能提高劳动者收入,从而产生收入增长效应(王军 等,2018)[3]。生产过程中使用智能技术可以通过“价格-生产率效应”和“规模-生产率效应”两种互补方式提高劳动者的收入(Acemoglu et al,2018)[8],且智能技术对劳动者收入的正向影响具有较强的持续性(闫雪凌 等,2021)[9]。
另一方面,劳动智能化可以优化劳动者工作环境,减轻劳动者工作强度,提高劳动者工作自主性,从而产生工作条件改善效应。首先,人工智能等智能设备可以替代工作中一些不安全或不适合人力完成的任务(周卓华,2020)[10],降低或消除劳动者工作的危险性;同时,智能技术的发展让居家办公、远程协作和人機协作成为可能,劳动者的工作空间跨度加大、劳动效率提升,从而改善了劳动者的工作环境。其次,企业在重复性、简单生产环节引入智能设备,使复杂的体力劳动自动化,可以减少劳动者的工作强度并增加劳动者的闲暇时间,进而提高劳动者的心理舒适度(王军 等,2018)[3]。最后,劳动智能化通过改变工作内容和任务分配方式引起组织管理的变化,可以提高劳动者工作的灵活性和自主性。劳动智能化减少了劳动者的通勤时间,降低了工作场所限制,劳动者可以更好地控制工作节奏;同时,劳动者通过自主学习和互助交流,在专业技能、自我管理、时间管理、信息处理等方面也会得到较大提升,工作自主性将进一步增强。
基于此,本文提出假说1:劳动智能化可以促进劳动者就业质量的改善。
2. 劳动智能化影响就业质量的异质性
不同类型的劳动者受智能化的影响可能有所不同,因而劳动智能化对其就业质量的影响也存在差异。对此,本文从性别、年龄和技能3个方面进行探讨。
(1)劳动者性别的异质性。在当前的就业结构中,男性劳动者在较高层级的职业以及STEM(科学、技术、工程、数学)职业中的占比较高,因而可以通过劳动智能化的补偿效应和收入效应中获得更多收益(Brussevich et al,2018;Aksoy et al,2021)[11-12]。而女性劳动者往往会承担更多的家庭责任,辅导孩子学习、做家务等各项家庭无偿劳动的时长明显高于男性劳动者,导致其在工作中获得和享受的智能化红利相对较少(汪前元 等,2022)[13]。同时,在任务分配上,男性通常被认为在思维能力、机器设备的学习能力和逻辑推理能力等方面存在优势,女性则往往被认为在沟通设计能力、细心等方面存在优势,企业通常会优先对男性员工进行智能技术培训,导致男性在劳动智能化中获得更多的机会和收益。此外,现阶段劳动智能化对工作任务的改变主要是替代体力劳动,而这类工作更多由男性担任。因此,相对于男性劳动者,劳动智能化对女性劳动者就业质量的改善效应较弱。
(2)劳动者年龄的异质性。相比于中老年劳动者,青年劳动者更具开拓、创新、冒险精神,在体力和精力方面也具有优势,更能适应就业形式的变化,且被智能技术和设备替代的风险较小。 一方面,智能技术的应用需要劳动者学习和掌握新技能,年轻人的知识水平和学习能力均较高;另一方面,劳动者在就业选择上往往会受到环境、家庭、教育背景等因素的约束,并存在路径依赖和职业惯性,随年龄增长劳动者更加偏好稳定的职业,而不愿意接受工作改变的挑战。同时,智能技术的应用对创造思维和学习能力的要求提高,青年劳动者比老年劳动者对机械操作的学习和动手能力更强。此外,目前智能技术更多的是用于替代环境差、强度高的工作,而这部分工作大多由中青年劳动力完成。因此,劳动智能化会为青年劳动者创造更多机会,从而对青年劳动者就业质量的改善更为明显。
(3)劳动者技能的异质性。劳动智能化对不同技能劳动者的影响具有明显差异,导致劳动力市场呈现两极极化(高技能劳动力和低技能劳动力就业相对增加,而中等技能劳动力就业相对减少)或单极极化(高技能劳动力就业增加而中低技能劳动力就业减少)的趋势(明娟 等,2022)[14]。劳动智能化不仅通过替代非技能劳动岗位和创造技能劳动岗位的非对称方式扩大劳动技能溢价(胡晟明 等,2021)[15],还可以通过提高技能劳动者相对非技能劳动者的劳动生产率造成技能溢价(Acemoglu,1998)[16]。劳动智能化与高技能劳动之间更多的是互补关系,人机合作等提高了高技能劳动者的生产率,从而增加高技能劳动者的收入;劳动智能化与低技能劳动之间则更多的是替代关系,智能技术的应用替代了低技能劳动者的劳动,从而减少低技能劳动者的收入(何勤,2021)[17]。因此,与低技能劳动者相比,高技能劳动者更容易获取劳动智能化的红利,工作报酬更易得到增长,工作环境更易得到优化,工作自主性更易得到提高,从而产生更为显著的就业质量改善效应。
基于此,本文提出假说2:与女性、老年、低技能劳动者相比,劳动智能化对男性、青年、高技能劳动者就业质量的改善更为显著。
3.非认知能力的调节效应
新人力资本理论认为能力是人力资本的核心,包括认知能力与非认知能力。认知能力主要指人脑加工、储存和提取信息的能力;非认知能力主要指性格、情感、意志等,包含人际交往能力、适应能力、对事物的好奇心等内容。相比认知能力,非认知能力在劳动智能化促进就业质量改善中发挥的作用更为明显。一方面,与认知能力相比,人工智能技术与非认知能力会形成较强的互补性。非认知能力较强的劳动者可以更好地与人工智能技术环境融合,从而更有利于在工作中产生能力溢价,并实现较快的收入增长(王林辉 等,2022)[18]。另一方面,相比于认知能力,非认知能力的提升空间更大,可以产生更显著的边际效应(李阳 等,2023)[19]。因此,本文主要分析非认知能力对劳动智能化影响劳动者就业质量的调节作用。
劳动智能化对劳动者就业质量的影响会因劳动者非认知能力的提高而发生变化。一方面,非认知能力的提高有助于劳动者在智能化背景下获得更好的就业机会,从而改善其就业质量。随着技术的进步,一些重复性、通过反复练习获得的操作技能(“硬技能”)很容易被智能技术和设备所替代,而创造力、创新、社会化、领导能力等非认知能力(“软技能”)很难被智能技术替代和模仿。此外,劳动者的非认知能力越强,越有利于人机协调和互补(尤其是情绪稳定、社交、信任等在人机协同中发挥着重要作用),越能促进劳动生产率的提升和劳动者收入的增长(胡晟明 等,2021)[20]。另一方面,非认知能力的提高有助于劳动者更好地面对由劳动智能化带来的工作变化和工作压力,提升劳动者的心理舒适度。智能技术的应用会对工作流程进行重组,对工作任务进行标准化,技术和算法成为重要的管理手段,导致短时工作压力骤增,加大了劳动者的负担和心理压力;同时,劳动智能化会拓宽劳动者的工作地点,一定程度上模糊工作与家庭的界限,客观上增加工作时间,造成情绪消耗。而劳动者的非认知能力提高,可以使劳动者更好地调整工作方式、调节心理状态,以更好地应对智能化冲击中带来的工作压力(李阳 等,2023)[19]。
基于此,本文提出假说3:非认知能力对劳动智能化改善劳动者就业质量具有正向调节作用。
三、实证研究设计
1. 模型设定与变量测度
为检验劳动智能化对劳动者就业质量的影响,参考Mcguinness等(2019)的实证策略构建如下基准模型[6]:
其中,i表示劳动者个体,i为随机误差项。
被解释变量(Qualityi)为“就业质量”。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劳动者就业质量的内涵不断拓展,如工作生活质量、体面劳动、工作满意度、高质量就业等。Eurofound(2012)认为,就业质量的综合评价应兼顾货币方面的劳动收入和非货币方面的工作条件[21]。本文借鉴Antón等(2021)的测量方法[22],从货币收入和工作条件两个方面来评价样本的“就业质量”。货币收入即“工资水平”,数据直接取自CLDS问卷,用扣税后的年工资性收入总额来衡量;“工作条件”的测度指标包括工作强度、工作环境、自主权、培训情况等维度,采用主成分分析法计算得到综合指标( 工作强度和工作环境根据问题“请您对工作时间进行评价”和“请您对工作环境进行评价”进行赋值,非常不满意、不太满意、一般、比较满意、非常满意依次赋值1、2、3、4、5;自主权根据问题“在您的工作中工作进度多大程度上由自己来决定”和“在您的工作中工作量/工作强度在多大程度上由自己来决定”进行赋值,完全由他人决定赋值为1,部分由自己决定赋值为2,完全由自己決定赋值为3;培训情况根据问题“2017年7月以来您是否有参加过至少5天的专业技术培训”进行赋值,是和否分别赋值1和0。对上述变量标准化处理后进行可行性检验,通过KMO检验和Bartlett检验(KMO=0.517,Bartlett检验P值为0),按照累计贡献率超过50%、特征值大于1的原则提取出2个主成分(主成分1包含工作强度、自主权、培训情况,主成分2包含工作环境),根据2个主成分的方差贡献率进行加权拟合,得到“工作条件”综合指标。);在此基础上,采用主成分分析法构建“就业质量”综合指标( 所有变量标准化处理后进行可行性检验,通过KMO检验和Bartlett检验(KMO=0.5281,Bartlett检验P值为0),适合使用主成分分析进行降维;根据特征值和因子贡献率,提取出3个主成分(累积方差贡献率达到73.44%),主成分1包含工作进度的决定程度、工作量/工作强度的决定程度、工作环境,主成分2包含工作时间,主成分3包含培训情况和工资收入;进一步根据3个主成分的方差贡献率进行加权拟合,得到“就业质量”综合指标。)。
核心解释变量(SDTi)为“劳动智能化”。参考Mcguinness等(2019)的方法[6],采用劳动是否智能化的虚拟变量来衡量,若样本所在单位的劳动过程实现了或正在进行智能化,且样本认为自己的技能(工作)发生了变化,则赋值为1,否则赋值为0。本文基于CLDS问卷的数据可得性,选取两个问题来测量“劳动智能化”:问题1“是否经历智能化:您所在的工作单位是否正在使用高度智能化、机器人、人工智能(如无人驾驶、机器翻译、工业机器人等)等技术”,问题2“技能是否发生变化:您的工作有没有因高度智能化、机器人、人工智能等新的技术而改变”。如果对这两个问题的回答均为肯定,则认为该样本在劳动过程中经历了智能化并认为自己的技能(工作)发生了变化,即“劳动智能化”变量赋值为1。
参考Mcguinness等(2019)和侯俊军等(2020)的做法[6][1],控制变量包括个体特征(Individuali)、工作特征(Jobi)、行业特征(Occupationi)和地区特征(Districti)。个体特征变量包括“性别”“年龄”“受教育程度”;工作特征变量包括“单位类型”“合同类型”“公司规模”“就业年限”;行业特征变量,参考毛宇飞和胡文馨(2020)的分类方法[23],其他行业取值为0,新经济行业取值为1,传统行业取值为2( 将问卷中16个行业划分为传统行业、新经济行业和其他行业三类,其中新经济行业包括信息传输、金融业、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教育、卫生/体育、社会服务;传统行业包含农林牧渔、采掘业、制造业、电力煤气及水的生产和供给业、建筑业、批发和零售、房地产、水利。);地区特征变量,西部地区取值为0,东部地区取值为1,中部地区取值为2( 参考国家统计局的划分标准,将问卷中的28个省份划分为东部地区、中部地区和西部地区,其中西部地区包括内蒙古、重庆、四川、广西、贵州、云南、陕西、甘肃、青海、宁夏,东部地区包括北京、天津、上海、江苏、浙江、福建、山东、广东、河北、辽宁,其他省份为中部地区。)。
2. 样本选择与数据处理
本文数据来源于中山大学社会科学调查中心主持的中国劳动力动态调查(CLDS)2018年的个体问卷数据。2018年CLDS数据覆盖了除港澳台地区、新疆、西藏和海南之外的28个省区市,并在个体、家庭和社区三个层面上收集数据。其中,CLDS个体问卷收集了家庭中年满15周岁且仍在工作的劳动力信息,包括劳动者的工作收入、工作环境、工作压力等,并询问了机器人、人工智能、自动化等对其工作和技能的影响,可以较好地反映劳动智能化对就业质量的影响,基本满足研究的数据要求。本文剔除了工作单位为党政机关、人民团体、军队的样本,只保留了就业单位为国有、集体及私营企业的样本,进一步剔除数据缺失和异常的样本后,最终纳入分析的样本量为1 997个,主要变量的描述性统计见表1。
四、实证检验结果分析
1. 基准模型回归结果
考虑到采用的样本数据为横截面数据、被解释变量“就业质量”的连续性以及问卷回答的序数设定,线性模型的回归结果能更直观地呈现边际效应,并参考Mcguinness等(2019)的做法[6],采用最小二乘估计(OLS)来检验劳动智能化对就业质量的影响。基准模型回归结果见表2,其中(1)~(4)列依次纳入个体特征、工作特征、行业特征、地区特征变量,“劳动智能化”对“就业质量”的估计系数均显著为正,表明劳动智能化促使劳动者的就业质量得以提升,假说1得到验证。进一步分别以“工资水平”和“工作条件”为被解释变量进行模型检验,回归结果见表2的(5)(6)列。“劳动智能化”对“工资水平”的估计系数显著为正,对“工作条件”的估计系数为正但不显著( 现阶段,智能技术的应用主要是通过提高劳动者就业能力和拓宽劳动者就业机会等来增加劳动者的工资收入,短期内对劳动者工作条件的改善有限。劳动智能化改变了劳动者工作的内容和形式,提供了更好地控制工作节奏和组织形式的可能性,但也可能模糊工作与生活界限,增加劳动者的工作时间,降低劳动者自主权(Mazmanian et al,2013)[24]。同时,智能技术的精确性、可预测性和标准化还可能导致劳动者工作强度增加。因此,短期内劳动智能化对劳动者工作条件的改善不明显。),表明劳动智能化主要是通过提升劳动者的劳动收入来提高其就业质量。
2. 内生性处理
(1)IV-2SLS估计。本文的模型可能存在内生性问题:一方面,劳动者心理状态、过往经历遭遇等不可观测因素都可能影响劳动者就业质量,从而产生遗漏变量问题;另一方面,劳动者就业质量越好,说明企业效益和规模越大,越有可能引进人工智能等新技术,形成反向因果关系。为克服反向因果关系和遗漏变量导致的内生性问题,本文运用工具变量两阶段最小二乘法进行检验。借鉴齐乐和陶建平(2021)的思路[2],选用“智能科技成果”作为“劳动智能化”的工具变量,具体来讲,通过对《中国科技项目创新成果鉴定意见数据库》的关键词搜索获得各省份2018年的智能科技成果数量。智能科技成果是劳动智能化的技术体现,能够直接推动劳动智能化的发展;同时,智能技术成果与劳动者的就业质量没有直接关系,只有通过产业化等实际运用才能转变为生产力。因此,工具变量的选择符合相关性和外生性要求。IV-2SLS的估计结果见表3的(1)(2)列:第一阶段回归的F统计值为12.237,表明不存在弱工具变量问题;“智能科技成果”的估计系数在1%的水平上显著,表明工具变量与内生变量具有显著正相关关系。第二阶段回归中,拟合的“劳动智能化”对“就业质量”的估计系数在1%的水平显著为正,表明在缓解内生性问题后,基准模型的分析结果仍然成立。
(2)PSM估计。基准模型的估计还可能存在样本自选择问题,并非新技术应用带来的劳动智能化提高了就业质量,而由于是广泛应用智能技术的企业本身吸纳的员工技能或教育水平较高(即其就业质量原本就较高)。为克服样本选择偏差,本文采用倾向得分匹配(PSM)方法进行样本处理,即选择具有相同特征的实验组和对照组样本来进行检验。借鉴Mcguinness 等(2019)的做法[6],采用Logit模型获得倾向得分,然后运用核匹配法将实验组与对照组个体的倾向得分值进行匹配,从而使得两组样本之间的特征变量均值没有显著差异。回归结果见表3的(3)列,“劳动智能化”对“就业质量”的估计系数显著为正,表明在排除样本的自选择后,本文的分析结论仍然成立。
3. 稳健性检验
为进一步验证基准模型分析结果的可靠性,进行以下稳健性检验:一是改变被解释变量测算方法。参考王阳(2019)的做法[25],采用熵值法测算“就业质量”,重新进行模型检验,回归结果见表4的(1)列。二是剔除特殊样本。直辖市具有明显的区位优势和经济政治优势,有一定的特殊性,因此剔除北京、天津、上海、重庆4个直辖市的样本后重新进行回归,结果见表4的(2)列。三是数据缩尾处理。为避免极端值和异常值对回归结果的影响,对样本数据进行1%和5%缩尾处理,重新进行回归,结果见表4的(3)(4)列。上述稳健性检验结果显示,“劳动智能化”对“就业质量”的估计系数均显著为正,表明劳动智能化有助于改善劳动者就业质量的结论具有较好的稳健性。
4.异质性分析
分别对男性和女性样本的分析结果见表5。劳动智能化对男性劳动者的就业质量以及工资水平和工作条件均有显著的改善作用,而对女性劳动者的就业质量及工作条件具有负向影响。参考张世伟和张君凯(2022)的方法[26],将35岁作为年龄异质性分析的样本划分标准( 一般来讲,35岁是个人职业发展的一个分水岭,35岁之前和35岁以后个体面临的职业发展和择业机会有明显差异,因此本文将样本根据其年龄划分为35岁及以下和35岁以上两组。),分别进行回归的结果见表6。劳动智能化对35岁及以下劳动者的就业质量有显著正向影响,且主要通过优化工作条件来改善其就业质量;劳动智能化对35岁以上劳动者的工资水平有正向影响,但对就业质量的影响不显著。参考侯俊军等(2020)的方法[1],用受教育水平衡量劳动者的技能水平,初中以下学历为低技能劳动者,初中和高中学历为中技能劳动者,大专及以上学历为高技能劳动者,分别回归的结果见表7。劳动智能化对高技能劳动者就业质量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对中、低技能劳动者就业质量的影响不显著;此外,劳动智能化对高技能劳动者和低技能劳动者的工资水平也有正向影响。综上所述,总体上看,劳动智能化对男性、35岁及以下、高技能劳动者的就业质量改善效应更为显著,假说2基本得到验证。
5.调节效应检验
根据前文的理论分析,借鉴孙雪等(2022)的研究[27],选取“非认知能力”作为调节变量。参考王林辉等(2022)、孙雪等(2022)的方法[18][27],基于大五人格模型,从严谨性、外向性、顺从性、情绪稳定性、开放性五个方面选取指标( 严谨性根据问题“努力完成该做的事情”进行赋值,非常不同意、不同意、同意、非常同意,依次赋值1、2、3、4;外向性根据问题有“生活幸福感”进行赋值,从非常不幸福到非常幸福依次赋值1、2、3、4、5;顺从性根据问题“被访者合作程度”进行赋值,很不合作、不合作、合作、很合作依次赋值1、2、3、4;情绪稳定性根据问题“感到身心疲惫频率”进行赋值,每天、一周数次、一月数次、一年数次或更少、从不依次赋值1、2、3、4、5;开放性根据问题“在工作中表达意见的机会”和“工作有趣度”进行赋值,非常不满意、不太满意、一般、比较满意、非常满意依次赋值1、2、3、4、5。),并運用主成分分析法测度“非认知能力”( 变量标准化处理后进行可行性检验,通过KMO检验和Bartlett检验(KMO=0.645,Bartlett检验P值为0),提取出2个主成分(主成分1包含生活幸福感、在工作中表达意见机会、工作有趣度、感觉身心疲惫频率,主成分2包含努力完成该做的事情、被访者的合作态度),根据2个主成分的方差贡献率进行加权拟合得到“非认知能力”综合指标。),进而构建“非认知能力”与“劳动智能化”的交互项,纳入基准模型进行回归,结果见表8。“劳动智能化×非认知能力”对“就业质量”和“工资水平”的估计系数显著为正,表明劳动者非认知能力提高会强化劳动智能化对就业质量的改善效应,假说3得到验证。此外,“非认知能力”的估计系数均显著为正,表明劳动者认知能力的提升可以显著改善其就业质量。
五、结论与启示
数字经济的快速发展以及智能技术的广泛应用不但提高了劳动生产率,而且改变了劳动者的劳动方式。劳动智能化对劳动者工作方式、工作环境以及劳动收入都会产生显著影响,然而,现有文献关于劳动智能化对劳动者就业质量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研究不足。本文采用中国劳动力动态调查(CLDS)2018年个体问卷数据的分析发现:第一,相比劳动还未智能化的劳动者,劳动智能化的劳动者有更高的就业质量,该结论在经过内生性处理和稳健性检验后依然成立;第二,劳动智能化对劳动者的工资增长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但对劳动者的工作条件改善没有显著影响,即劳动智能化主要是通过提高劳动报酬来提升劳动者的就业质量;第三,劳动智能化对劳动者就业质量的影响具有异质性,表现为更能促进男性劳动者、35岁及以下劳动者、高技能劳动者的就业质量改善;第四,劳动者的非认知能力对劳动智能化改善其就业质量具有正向调节作用,即非认知能力的提高会强化劳动智能化改善就业质量的作用。
基于上述结论,本文得到以下启示:第一,大力鼓励和支持智能技术的发展和应用,加大对智能技术创新的政策扶持和资金投入,加快推进各领域的劳动智能化,让广大普通劳动者充分享受智能化带来的技术红利。第二,不断提升劳动者技能水平,降低劳动智能化带来的负面冲击。要鼓励企业加强岗前和转岗技能培训,提升员工的“技能—岗位”匹配度;要强化针对性的技能培训社会服务,优化人才层次结构,提高整体劳动力技能水平,以适应智能化对人才的需求。第三,重视劳动者工作条件的改善,发挥劳动智能化改善工作条件的潜在功效。在本文的样本中,劳动智能化未能产生显著的劳动者工作条件改善效应,但这并不意味着劳动智能化不能改善劳动者的工作条件,而是可能存在某些因素阻碍了劳动智能化改善工作条件的功效发挥。因此,在劳动智能化进程中,要特别注意劳动者工作条件的改善问题,促进劳动者就业质量的全面提升。第四,注重劳动者非认知能力的培养,强化劳动智能化的就业质量改善效应。企业要加强对员工责任心、执行力、创新力的培养,培育和拓展良好的企业文化,帮助员工更好更快地适应智能化技术。劳动者自身也要不断提高非认知能力,积极参加各类社会活动,保持灵活性与适应性,以更好地应对劳动智能化带来的各种变化。
本文探讨了劳动智能化对就业质量的影响,为劳动智能化的就业质量改善效应提供了经验证据,但也存在拓展和深化的空间,比如:对劳动智能化和就业质量的测度有待进一步优化,限于数据的可得性,本文对两者的测评均不全面,且仅采用了1年的数据,在未来有更多数据支撑的情况下,可使用追踪数据,对劳动智能化和就业质量进行更为科学全面的测度,进一步深入分析劳动智能化对就业质量的影响;劳动智能化影响劳动者就业质量的路径和异质性表现是多样化的,还有其他机制和异质性值得深入探讨。
参考文献:
[1]侯俊军,张莉,窦钱斌.“机器换人”对劳动者工作质量的影响——基于广东省制造企业与员工的匹配调查[J].中国人口科学,2020(4):113-125+128.
[2] 齐乐,陶建平.产业智能化与农民工就业质量的影响机理及提升路径[J].华中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3(1):34-46.
[3] 王军,詹韵秋.技术进步带来了就业质量的提升吗?——基于中国2000—2016年省级动态面板数据分析[J].云南财经大学学报,2018,34(8):29-39.
[4] 陈志,程承坪,陈安琪.人工智能促进中国高质量就业研究[J].经济问题,2022(9):41-51.
[5] 惠炜.人工智能与劳动收入份额——来自中国城市数据的经验证据[J].北京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2,22(6):99-112.
[6] MCGUINNESS S,POULIAKAS K,RESMOND P. Skills-displacing technological change and its impact on jobs: challenging technological alarmism?[R]. IZA Discussion Papers,2019.
[7] 蔡跃洲,陈楠.新技术革命下人工智能与高质量增长、高质量就业[J].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2019,36(5):3-22.
[8] ACEMOGLU D,RESTREPO P.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automation and work[M]//The economics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An agenda. Chicago: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2018:197-236.
[9] 闫雪凌,李雯欣,高然.人工智能技术对我国劳动力市场的冲击和影响[J].产业经济评论,2021(2):65-77.
[10]周卓华.人工智能技术发展对就业的影响及应对[J].重庆社会科学,2020 (10):44-54.
[11]BRUSSEVICH M,DABLA-NORRIS E,KAMUNGE C,et al. Gender,technology,and the future of work [M]. 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2018.
[12]AKSOY C G,ZCAN B,PHILIPP J. Robots and the gender pay gap in Europe [J]. European Economic Review,2021,134(1).
[13]汪前元,魏守道,金山等.工業智能化的就业效应研究——基于劳动者技能和性别的空间计量分析[J].管理世界,2022,38(10):110-126.
[14]明娟,胡嘉琪.工業机器人应用、劳动保护与异质性技能劳动力就业[J].人口与经济,2022(4):106-121.
[15]胡晟明,王林辉,董直庆.工业机器人应用与劳动技能溢价——理论假说与行业证据[J].产业经济研究,2021(4):69-84.
[16]ACEMOGLU D. Why do new technologies complement skills?Directed technical change and wage inequality[J]. The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1998,113(4):1055-1089.
[17]何勤.人工智能创新投入能提升企业员工的收入吗?——基于技能结构错配视角的研究[J].北京工商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1,36(5):24-36.
[18]王林辉,钱圆圆,赵贺.人工智能技术、个体能力与劳动工资:来自认知和非认知能力视角的经验证据[J].东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2,24(4): 58-69+149+147.
[19]李阳,张文宏.从自驱力到胜任力:非认知能力对新业态灵活就业人员作用机制研究[J].学习与探索,2023(2):31-38.
[20]胡晟明,王林辉,赵贺.人工智能应用、人机协作与劳动生产率[J].中国人口科学,2021(5):48-62+127.
[21]EUROFOUND. Trends in job quality in Europe[M]. Publications Office of the European Union,2012.
[22]ANTN J I,FERNNDEZ-MACAS E,WINTER-EBMER R. Does robotization affect job quality?Evidence from European regional labour markets[R]. JRC Working Papers on Labour,Education and Technology,2021.
[23]毛宇飞,胡文馨.人工智能应用对人力资源从业者就业质量的影响[J].经济管理,2020,42(11):92-108.
[24]MAZMANIAN,MELISSA,ORLIKOWSKI,et al. The autonomy paradox:the implications of mobile email devices for knowledge professionals[J].Organization Science,2013,24(5):1337-1357.
[25]王阳.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中就业质量的突出问题和提高路径[J].中国人力资源开发,2019,36(9):48-62.
[26]张世伟,张君凯.技能培训、工作转换与就业质量[J].劳动经济研究,2022,10(1):3-29.
[27]孙雪,宋宇,赵培雅.人工智能如何影响劳动收入——基于个人能力的微观解析与实证检验[J].山西财经大学学报,2022,44(8):17-29.
Does Labor Intelligence Improve the Quality of Laborer Employment?
MING Juana, b, BAO Xiang-yua, ZHANG Yia
(a. School of Economics; b. Key Laboratory of Digital Economy and Data Governance, Guangdong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Guangzhou 510520, Guangdong, China)
Abstract: Intelligent technology is an important force in labor production and is conducive to improving employment quality. However, the existing literature on the impact of labor intelligence on employment quality and its mechanism is insufficient. This paper argues that labor intelligence can improve employment quality by improving workers non-cognitive ability, and it presents heterogeneity depending on workers age, gender, and skill level. This paper uses the China Labor Force Dynamics Survey (CLDS) data to conduct an empirical study, and the results show that (1) labor intelligence has a significant positive impact on employment quality. Labor intelligence improves the employment quality of workers, and the conclusion remains robust after endogenous processing and robustness tests; (2) labor intelligence has a heterogeneous effect on employment quality. Compared with female workers, labor intelligence has a more obvious effect on improving the employment quality of male workers. In different age groups, labor intelligence has a greater effect on the improvement of the employment quality of workers aged 35 and below. In different skill groups, labor intelligence plays a greater role in improving the employment quality of highly skilled workers; (3) further analysis of the moderating effect shows that non-cognitive ability plays a positive moderating role i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labor intelligence and employment quality, indicating that the improvement of non-cognitive ability strengthens the role of labor intelligence in improving employment quality.
Compared with the existing literature, this paper discusses the influence of labor intelligence on employment quality, and provides empirical evidence for the mechanism and heterogeneity of labor intelligence in improving employment quality. The possible innovations of this paper are as follows: firstly, unlike existing literature, which mainly analyzes the impact of intelligence on employment and wages from the macro level, this paper uses CLDS individual questionnaire data to analyze the impact of labor intelligence on individual employment quality from the micro level. Secondly, unlike different pieces of literature which mostly explore the impact of intelligence on single indicators such as income, work environment, and work intensity, this paper intends to construct comprehensive indicators of employment quality from monetary income and working conditions to analyze the impact of labor intelligence on employment quality. Thirdly, it analyzes the moderating effect of non-cognitive ability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labor intelligence and employment quality, and pays attention to the heterogeneous influence of labor intelligence on employment quality.
This study shows that the development of labor intelligence is helpful to improve the employment quality of workers and improve the employment quality by improving the non-cognitive ability of workers. Therefore, it is important to encourage the development of new technologies such as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increase policy support and financial investment in intelligent technologies, and continuously deepen technological reforms so that ordinary workers can enjoy the “technological dividend” brought by intelligent technologies. Moreover, it is necessary to develop targeted skills training services, encourage enterprises to increase pre-employment and transfer skills training, improve workers skills level and enhance skills-job matching. Finally, it is necessary to focus on the cultivation of workers non-cognitive abilities, improve their quality, and help them actively adapt to labor intelligence to achieve a steady improvement in employment quality.
Key words: labor intelligence; employment quality; monetary income; working conditions; labor skills; non-cognitive ability; intelligent labor
CLC number:F062.4;F24 Document code:A Article ID:1674-8131()0-0001-14
(編辑:黄依洁)
收稿日期:2023-02-06;修回日期:2023-04-28
基金项目:广东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2022年一般项目(GD22CYJ23);国家社会科学基金后期资助一般项目(22FJYB045);广东省哲学社会科学创新工程2022年度特别委托项目(GD22TWCXGC11)
作者简介:明娟(1980),女,湖北黄石人;教授,经济学博士,主要从事人工智能与就业研究;E-mail:mingjuan520888@gdut.edu.cn。
鲍翔宇(1999),女,河南驻马店人;硕士研究生,主要从事人工智能研究。
张艺(1986),通信作者,男,江西赣州人;讲师,经济学博士,主要从事数字经济研究;E-mail:yizhang17@gdut.edu.c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