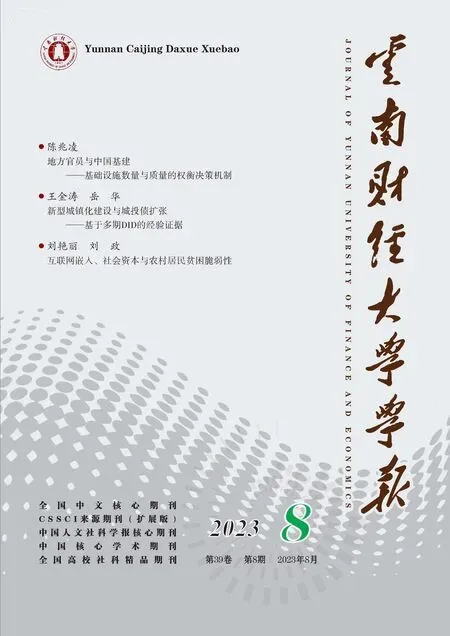互联网嵌入、社会资本与农村居民贫困脆弱性
2023-07-27刘艳丽
刘艳丽, 刘 政
(1.中共昆明市委党校 市情研究中心与决策咨询研究所,昆明 650504;2.江西师范大学 管理科学与工程研究中心,南昌 330022)
一、引言
党的十八大以来,在“精准扶贫”政策指引下,中国如期完成了脱贫任务。期间,中国减贫人口占到全球减贫总数的70%以上,提前10年完成了《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规划的全球减贫目标。脱贫攻坚消除了绝对贫困,但没有完全解决相对贫困,“脱贫摘帽不是终点,而是新生活新奋斗的起点”。
2020年以来,削减相对贫困与实现共同富裕成为中国减贫事业的重心(周云波和杨家奇,2022)[1]。相对贫困与绝对贫困不同,其范围广且周期长(Decerf,2017)[2]。相对贫困与物质充裕程度无直接关系,专指与他人相比,部分人群在物质和生活条件上相对匮乏的状态。相对贫困不仅包括物质收入差距,还表现为主观剥夺感和发展机会及选择权利的丧失(姜安印和陈卫强,2021)[3]。
就中国实践看,农村初步脱离绝对贫困的人群和数量庞大的低收入者,都是中国相对贫困的主要群体(张楠等,2021)[4]。受外部性冲击,相对贫困人群更易返贫,其个人或家庭的贫困脆弱性更高,缺乏抵御贫困的能力韧性,且摆脱贫困脆弱性的恢复力也更小(贺立龙和吴伟,2022)[5]。因此,如何降低低收入农村居民的贫困脆弱性,巩固易返贫群体的脱贫成果,建立预防返贫的长效机制,仍是亟待破解的现实难题。
另一方面,随着国家数字乡村战略的实施,中国农村互联网获得普及。2020 年《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显示,中国农村网民数已经达到2.55亿人,占全国网民总数的28.2%。互联网嵌入为中国农村经济发展注入了生机与活力。互联网信息技术与中国破解贫困脆弱性存在何种联系,能否借助互联网来助力中国农村居民预防返贫呢?
学理层面,许多研究发现,互联网作为信息交流平台,能够拓宽农产品销路,推动农村居民创业兴业(赵羚雅和向运华,2019)[6];互联网技术能够嵌入农户人力资本提升(周洋和华语音,2017)[7],促进农机设备采纳(陈昕等,2022)[8],并增强社会资本积累(张思阳等,2020)[9]。显然,借助互联网的“去中心化”“去中介化”功能,那些自然资源少、交通条件差、经济基础薄弱的农村返贫家庭,也能够拥抱数字技术而走出脆弱贫困陷阱。
综上所述,本文立足2018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实证检验互联网嵌入对农村居民贫困脆弱性的影响,并验证了微观机制。本文研究发现,使用移动互联网的农户比不用移动互联网的农户,更易摆脱贫困脆弱性;社会资本是互联网嵌入促进农村居民跳出贫困脆弱陷阱的主要中介渠道;借助互联网社交工具,农村居民在就业、创业以及农机设备使用上都更有优势,因此,助力农户跨越脆弱贫困陷阱。
与既有研究相比,本文可能的贡献体现在:一是采用微观调查数据识别了互联网嵌入影响农村居民贫困脆弱性的因果关系,为借助现代数字信息技术攻克相对贫困、实现共同富裕提供了新的经验证据。二是通过机制分析,本文解析了“互联网+”助力农村居民摆脱相对贫困的理论“黑箱”,为中国治理相对贫困提供了学理支持。
二、文献综述与研究假设
沿着阿玛蒂亚·森的观点,贫困是指缺乏创造收入的能力和机会的状态。贫困具有动态性(Chaudhuri et al.,2002)[10],即使当期富裕的家庭和个人,在未来也可能陷入贫困,即出现返贫。脆弱性是贫困的重要特征,也是反贫困领域的研究重点。世界银行定义的贫困脆弱性(vulnerability to poverty),专指特定人群易受风险冲击而返贫致贫的倾向和概率。
贫困脆弱性加剧了返贫致贫的风险(贺立龙和吴伟,2022)[5],也是理解脱贫攻坚和预防返贫两阶段目标的衔接桥梁。学界对于贫困脆弱性展开了系统研究,归纳起来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如何测度贫困脆弱性?二是怎样解释贫困脆弱性。关于贫困脆弱性的测度,主要有三种思路:分别是期望效用决定的贫困脆弱性(VEU)、风险暴露影响的贫困脆弱性(VER)以及基于预期收入的贫困脆弱性(VEP)(吴雪婧等,2022)[11]。其中,VEU 从消费者效用水平入手测度贫困脆弱性特征,VER重视风险冲击与家庭事后应对的贫困脆弱性,VEP则采用收入函数法,在选取标准贫困线的基础上推断贫困发生率。相比之下,基于预期收入的贫困脆弱性方法(VEP)获得广泛采用(吴雪婧等,2022)[11]。当然,VEP方法离不开如何定义贫困线标准(张栋浩和尹志超,2018;郭露和刘梨进,2022)[12~13],以及怎样设置贫困脆弱性阈值(斯丽娟,2019)[14]。
许多研究进一步解释了贫困脆弱性的诱发原因,且结论也很丰富。其一,从风险入手,解释自然灾害对贫困脆弱性的影响(吴雪婧等,2022)[11],这涉及到热带天气冲击与农作物减产(Harshan,2021;Trinh et al., 2021)[15~16]、地震与家庭收入锐减(Llorente-Marrón and Díaz-Fernández,2020)[17]、地质灾害与收入下降(Xu and Peng, 2017)[18]等。其二,从金融发展视角,检验普惠金融对贫困脆弱性的积极作用(张栋浩和尹志超,2018;尹志超和张栋浩,2020)[12][19]。其三,从健康医保角度讨论贫困脆弱性(张栋和刘文璋,2022)[20]。其四,从社会合作、社会资本变迁视角分析贫困脆弱性(郭露和刘梨进,2022;谢家智和姚领,2021)[13][21]。近期,随着数字经济深度嵌入到社会经济活动,互联网技术也成为解释贫困脆弱性的重要视角,少许研究初步考察了互联网金融、互联网使用对于农户减贫、巩固脱贫攻坚以及家庭贫困恢复力的影响(周云波和杨家奇,2022)[1]。
归纳起来,国内外学者关于贫困脆弱性的研究经历了现象描述、概念提炼和测度分析的过程,系统解释了贫困脆弱性的决定因素,少许研究将“互联网+”与贫困脆弱性结合,但对其作用机制的解析还有待深入揭示。尽管直接研究互联网信息技术与脱贫攻坚和预防返贫的文献不多,但将互联网与三农问题结合的其他研究则比较广泛,这些研究为进一步解释互联网如何影响贫困脆弱性和预防返贫提供了理论解释。
第一,互联网是现代社会的沟通桥梁,是社会资本的重要载体(张思阳等,2020)[9]。互联网嵌入直接促进农村居民社会资本积累,降低了居民返贫风险。基于社会资本理论,社会网络可以促进信息共享、改进群体决策而缩小贫富差距(Grootaert,1999)[22]。互联网作为社会网络的重要载体(见图1),互联网接入增强了社会沟通,促进了社会信任,并有助于建立数字信息时代的社会规范。互联网推动了多元社交,帮助农户突破地域限制、扩大社交半径、拓展人脉资源(周广肃和梁琪,2018)[23]。互联网也通过增加交流和信息传递提升社会资本,助力农户应对外部风险冲击。借助互联网的社会网络效应,农户易于吸收新知识和新技能,强化自身克服贫困的能力韧性(唐红涛和陈薇,2020)[24]。总之,互联网嵌入能够打破传统农户中的社会“孤岛”,降低交易成本、促进分工合作、提升社会信任,最终推动农村社会的开放性,降低相对贫困的发生率(谢沁怡,2017)[25]。

图1 互联网嵌入与农村居民贫困脆弱性的逻辑关系
第二,借助互联网嵌入,农村居民能够基于社会联系获得并巩固就业机会,最终插上就业腾飞和经济创收的翅膀。一方面,互联网劳务平台丰富了就业信息,扩展了个人社交渠道,增加了就业机会(胡雅淇和林海,2020)[26];互联网普及也增加了农村劳动力需求,创造了更多非农就业岗位(毛宇飞等,2019)[27]。另一方面,互联网通过降低市场搜寻成本,促进劳动力市场的供需匹配,提高农户创业而带动就业(周洋和华语音,2017)[7]。此外,互联网使用不仅提高农村劳动力的非农就业,还有效拓宽了农村弱势群体的非农就业渠道(潘明明等,2021)[28]。互联网尤其显著促进了女性就业(毛宇飞和曾湘泉,2017)[29]和劳动者多重就业(陈瑛等,2021)[30]。
第三,互联网能够赋能农民职业选择,促进农民创业兴业,进而预防返贫。部分文献发现,缺乏社会资本阻碍了农村居民创业,而借助数字信息技术、互联网、移动支付和电子商务等互联网运用显著推动了农业资源交易,带动了农村居民创业兴业(尹志超等,2019)[31]。一方面,互联网帮助农户获得创业的启动资金,克服信息不对称、捕捉创业机会、缓解创业压力(胡雅淇和林海,2020)[26]、降低创业风险(蔡跃洲,2016;何慧等,2021)[32~33]。另一方面,许多定量研究指出,选择上网的农村家庭比不上互联网的农村家庭,其创业率高3.83%(周洋和华语音,2017)[7],且互联网促进居民创业的结论对于波兰、加拿大以及德国的海外经验数据也成立(Janson and Wrycza,1999;Cumming and Johan,2010;Audretsch et al.,2015)[34~36]。
第四,互联网促进农业机械使用,增强农业社会资本与生产资本的有效结合,提升农业生产率并助力农村居民摆脱脆弱贫困陷阱。众多文献表明互联网促进了农业机械推广,提升了农业生产率(李欠男和李谷成,2020)[37]。一方面,互联网使用降低了农机作业的信息成本和监督成本,增加了农机作业的服务需求,提高了农机服务的采纳率(郭海红,2019)[38]。陈昕等(2022)[8]定量研究指出,农户家庭互联网使用率每提高1%,农机服务采纳率则增加6.8%。另一方面,互联网使用通过替代农业就业而间接促进农业机械化,李忠旭和庄健(2021)[39]发现互联网信息技术增加了农业劳动成本,诱使更多的农机换人,但互联网使用并不是促进农户购买农业机械,而是促进农村居民外包和共享农机服务。综上考虑,提出以下研究假设:
假设1:其他条件不变时,互联网嵌入有助于农村居民降低贫困脆弱性。
假设2:社会资本是互联网嵌入降低农村居民贫困脆弱性的重要中介渠道;互联网嵌入也通过社会资本的中介渠道,促进农村居民就业、推动农村居民创业以及激励农村居民使用农业机械。
三、实证设计
(一)数据来源
基础数据来自北京大学中国社会科学调查中心2018年发布的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该调查采用内隐分层与按人口比例的随机抽样方法,对全国城乡居民家庭收入、消费以及生产经营活动进行访谈。本文以家庭库为主,按家庭户主特征合并了部分成人库信息,保留了农村户籍,最终获得3207户农村居民家庭样本。
(二)变量构建
农村居民贫困脆弱性(vul)是被解释变量。就文献看,基于期望的贫困脆弱性测度(Vulnerabilityas Expected Poverty,简称VEP方法)是评估居民贫困的重要方法(吴雪婧等,2022;斯丽娟,2019)[11][14],其核心思路是,先估计居民收支,再给定不同档次的贫困线,测算居民收支落入贫困线的概率,然后定义居民贫困脆弱性指数(Chaudhuri et al.,2002)[10]。VEP方法也适用于横截面数据,因此获得学界广泛支持(樊丽明和解垩,2014)[40]。

显然,实际的贫困标准线lnZi不同,导致农村居民的贫困脆弱性也不一样。本文从三个视角来选择贫困脆弱线,以此测度农村居民的贫困脆弱性。其一,借鉴世界银行针对中高收入经济体的贫困线标准,选取人均每天消费5.5美元(折合人民币为人均年消费8133元)作为第一类高标准贫困线,据此测度中国农村居民预期的贫困脆弱性(vulwmh)。其二,考虑到中国城乡发展差距,重新选取世界银行针对中低收入经济体划分的贫困标准,将人均每天消费3.2美元(折合人民币为人均年消费4584元)作为第二类中标准贫困线,重新测度农村居民预期的贫困脆弱性(vulwmd)。其三,出于稳健性考虑,进一步选择2018年中国划定农村居民的低标准贫困线(人均年消费3535元)测算中国农村居民预期的贫困脆弱性(vulcpl)。
互联网嵌入是核心解释变量。结合2018年的CFPS调查,其在个体问卷中汇报了“是否电脑上网”和“是否手机上网”两类特征。统计显示,样本中农村居民采用电脑上网的比例偏低(9.83%),采用手机上网比例较高(37.22%),且手机上网比例高度接近2018年中国农村互联网普及率(38.4%)。因此,选择农村居民“是否手机上网”作为互联网嵌入的代理变量。在稳健性检验部分,将农户至少选择“电脑上网”或“手机上网”定义为1,将不上网定义为0,构建农村居民互联网嵌入的替换变量。
借鉴斯丽娟(2019)[14]、吴雪婧等(2022)[11]的做法,本文选取政府补助(govsub)、拆迁(remove)、家庭总房产(lnhouse)、土地资产(lnland)、现金和存款(lnsaving)、银行贷款(bankloan)、老人个数(oldnum)、是否慢性病患者(sick)、最高学历(edu)、医疗保险(medsure)、是否男性(male)、是否已婚(spouse)、智力水平(IQ)等作为控制变量。
变量的描述性统计如表1所示。

表1 变量描述性统计
(三)研究模型
选用农村居民贫困脆弱性(vul)作为被解释变量,建立如下计量模型:
vuli=α0+β0interneti+γ0Wi+αd+εi
(1)
其中,internet为家庭农户是否使用互联网特征,W为系列控制因素,αd为省份固定效应,ε为随机扰动项。方程(1)为本文基准计量模型,鉴于该方程因遗漏变量问题而可能存在内生性,采用工具变量方法进行检验。考虑到大量农村居民没有使用手机网络(高达63%),导致方程也面临样本选择性。对此,采用处理效应模型,事先控制农村居民是否选取互联网的样本选择性偏误:
(2)
vuli=α0+β0interneti+γ0Wi+γ1λi+αd+εi
(3)

四、实证结果与计量分析
(一)基准回归
表2报告了基准回归结果。表2的(1)~(3)列,立足中高收入经济体对应贫困线来测算中国农村居民的贫困脆弱性(vulwmh),采用最小二乘法(OLS)检验互联网嵌入对农村居民贫困脆弱性的影响。采用逐步增加控制变量的思路,表2的(1)列仅控制家庭类特征变量,表2的(2)列仅控制户主层面的影响因素,表2的(3)列将家庭组特征和户主特征都控制。综合显示,互联网嵌入在前三列估计系数均始终为负,高度显著(1%显著性),说明中国使用互联网的农村居民比未使用互联网的农村居民跌入脆弱贫困陷阱的概率更低,这支持了互联网嵌入助力农村居民摆脱脆弱贫困的结论,证实了假设1。表2的(4)~(6)列,采用世界银行针对中低收入经济体确立的贫困线,构建略低标准的农村居民贫困脆弱性指标(vulwmd),检验显示,互联网嵌入系数均始终高度显著为负(1%显著性),这再次证实理论假设1,说明借助互联网工具,中国农村居民更易摆脱脆弱贫困陷阱。

表2 互联网嵌入影响农村居民贫困脆弱性的基准回归
就表2的(3)、(6)两列的回归结果展开比较,解释互联网嵌入影响农村居民贫困脆弱性的经济含义。以表2的(3)、(6)两列互联网嵌入的边际系数而言,其分别为-0.082和-0.032,说明与未使用互联网的农户相比,使用互联网的农户陷入贫困脆弱性的概率分别下降了8.2%和3.2%,可见互联网嵌入对中国农村居民巩固脱贫攻坚成果和预防返贫具有实践意义。鉴于表2的(3)列的贫困脆弱性采用了比表2的(6)列更高的贫困线标准,上述结论进一步表明,中国农村的中高收入群体更依赖互联网工具来摆脱贫困脆弱性。进一步简单解释主要控制变量的回归结果。就家庭层面看,获得拆迁的农户,以及家庭总房产、土地资产、现金和存款、银行贷款越多的农户,其陷入贫困脆弱性的可能性越低,获得政府补助的农户反而贫困脆弱性更高;就户主特征看,慢性病患者易于陷入脆弱贫困,户主的最高学历越高、智力水平越高,越易摆脱脆弱贫困,此外,医疗保险、是否已婚以及户主性别等对贫困脆弱性的影响十分有限。
(二)模型内生性与工具变量检验
遗漏变量问题很可能加剧计量方程(1)的模型内生性,并导致实证结论出现偏倚。借鉴张景娜和朱俊丰(2020)[41]、张要要(2022)[42]的研究,选取家庭每月邮电通讯费支出作为互联网嵌入的工具变量。主要原因如下:其一,就相关性条件而言,邮电通讯费支出是农户使用移动网络的主要资费来源,邮电通讯费支出越多,农户嵌入移动互联网络的程度越深,因此,其易于满足工具变量的相关性条件。其二,就外生性看,邮电通讯费支出包括邮件快递支出和电话费用支出,对于农村居民而言,邮件快递支出占比较低,而电话费支出是主体,结合中国电话费支出存在年费绑定、月租流量套餐等预付模式,致使家庭每月邮电通讯费支出属于前定变量,其相对外生。因此,本文选用“家庭每月邮电费支出的对数”作为互联网嵌入的工具变量。
表3汇报了采用工具变量方法控制模型内生性的回归结果。首先,表3的(1)~(3)列报告了两阶段最小二乘法(2SLS)工具变量检验。表3的(1)列检验了工具变量影响核心解释变量的第一阶段回归结果,显示家庭邮电通讯费支出越多,农村居民嵌入互联网的概率越大,这与理论预期相符。表3的(2)~(3)列依次检验了互联网嵌入影响农村居民两类贫困脆弱性的第二阶段工具变量回归结果,针对贫困脆弱性的工具变量排他性检验报告了第一阶段的F统计值(71.90),其高度显著为正,说明家庭每月邮电费支出通过了工具变量的相关性假设。此外,工具变量伪识别和弱识别检验值也很高,高度显著,说明本文选取家庭每月邮电费支出作为互联网嵌入的工具变量,也满足工具变量所需的外生性假设和弱工具假设,体现了工具变量的合理性和有效性。其次,在表3的(2)~(3)列发现互联网嵌入始终高度显著为负(1%显著性),这说明控制内生性之后,互联网嵌入仍然显著降低了中国农村居民的贫困脆弱性,促进了农村居民摆脱相对贫困陷阱。此外,出于稳健性考虑,采用有条件或无条件的内生分位数回归方法展开稳健性检验。具体地,分别考察了0.2、0.5、0.8三个贫困脆弱分位点,互联网嵌入影响农村居民贫困脆弱性的稳健性。其中,仍然选取家庭每月邮电通讯费支出作为互联网嵌入的工具变量。表3的(4)~(5)列报告了有条件内生分位数回归的工具变量检验结果,表3的(6)~(7)列报告了无条件内生分位数回归的工具变量检验结果(1)受篇幅限制,表3报告了0.5分位的回归结果,其他分位如0.2和0.8分位的结论一致,未报告。,发现互联网嵌入均仍然高度显著为负,这说明在考虑模型内生性和被解释变量位于不同分位点时,互联网嵌入降低农村居民贫困脆弱性的结论稳健显著。

表3 互联网嵌入影响农村居民贫困脆弱性的工具变量检验
(三)排除样本选择性偏误
鉴于样本中超过60%的农户没有使用移动互联网,说明农户的互联网嵌入特征具有样本选择性,这可能导致方程(1)存在样本选择性偏误。采用方程(2)、方程(3)的处理效应模型进行检验,实证结果见表4。在第一阶段,估计农村居民选择是否采用移动互联网的解释原因,即在主方程选择已有控制变量的基础上,新增控制了家庭收入水平、户主年龄、学历、农机价值、社会网络等,计算衡量样本选择性偏差的逆米尔斯比率;将其引入方程(3)检验互联网嵌入对农村居民贫困脆弱性的影响。
具体而言,在表4的(1)~(2)列采用两步法进行估计,表4的(3)~(4)列采用极大似然法进行检验。最终结果显示,逆米尔斯比率(Lambda hazard)和衡量两阶段方程独立性的检验都高度显著,说明回归模型确实存在样本选择性,应该对其控制。在第二阶段的回归结果显示,互联网嵌入系数在表4的(1)~(4)列高度显著为负,说明在控制样本选择性偏误之后,仍然得出互联网嵌入降低农村居民贫困脆弱性的一致结论。考虑到逆向概率加权方法(IPW)、逆向概率加权回归调整方法(IPWRA),都有助于进一步纠正样本的选择性偏误(Linden et al.,2016)[43]。因此,表4的(5)~(8)列进一步采用上述加权方法控制样本选择性,结果显示,互联网嵌入系数均仍然高度显著为负,这再次支持了互联网嵌入助力农村居民摆脱脆弱贫困的结论。
(四)排除核心变量测度偏误
核心变量的测度偏误也可能影响实证结论。结合问卷,构建新的贫困脆弱性指标。其一,选择2018年中国划定的居民贫困线(人均年消费3535元)作为更低标准,来测度农村居民的贫困脆弱性(vulcpl)。其二,根据恩格尔定律,将家庭食品支出除以总支出比重,构建农村居民家庭的恩格尔系数,将该恩格尔系数是否小于59%设置虚拟变量(vulengel),作为农村居民贫困脆弱性代理指标。其三,借鉴斯丽娟(2019)[14]的研究,在构建贫困脆弱性指标的基础上,进一步将该指标是否超过某个阈值(29%),构建农村居民是否面临贫困脆弱的二值虚拟指标(vepwmh和vepwmd),作为农村居民贫困脆弱性的代理变量。
表5的(1)~(4)列汇报了主要实证结果,显示无论采用何种新的贫困脆弱性指标,以及采用不同的实证计量方法,互联网嵌入系数均始终显著为负,说明排除被解释变量的测度偏误后,主要结论仍然成立。同时在构建新的贫困脆弱性指标基础上,进一步选取新的互联网嵌入指标。将农户至少使用手机上网和电脑上网都赋值为1,将不使用手机和电脑上网赋值为0,重新构建新的互联网嵌入变量,仍然选择前四列新的贫困脆弱性代理变量。表5的(5)~(8)列检验显示,在替换被解释变量以及更换核心解释变量之后,互联网嵌入系数均始终显著为负,这依然证实本文主要结论的稳健性。

表5 排除核心变量测度偏误的稳健性检验
(五)采用倾向值匹配方法检验稳健性
采用倾向值匹配得分方法,就互联网嵌入对农村居民贫困脆弱性的影响展开稳健性检验。具体而言,将样本分为有互联网嵌入的“激励组”和无互联网嵌入的“控制组”,采用倾向值匹配方法(PSM)先估计农村居民是否使用互联网的倾向值得分p(xi),然后测量“激励组”和“控制组”的样本匹配性,检验不同测度模型的平均处理效应ATT(Average treatment treated),验证有互联网嵌入的“激励组”是否比无互联网嵌入的“控制组”对应更低的贫困脆弱性。
ATT=E[(vul1i-vul0i)|interneti=1]
(4)
其中,当样本为“激励组”(有互联网嵌入)时取值为1,当样本为“控制组”(无互联网嵌入)时取值为0。vul1i和vul0i分别代表“激励组”和“控制组”并对应潜在的农户家庭贫困脆弱性,ATT为“激励组”和“控制组”对应的农户家庭贫困脆弱性差异。具体实证结果如表6所示,采用近邻匹配法,针对农村居民贫困脆弱性值指标,依次选取1∶2、1∶3或1∶4的匹配比例,倾向值匹配方法检验显示,“激励组”样本比“控制组”样本始终对应更低的贫困脆弱性,且该差值高度显著(5%显著性水平),可见互联网嵌入的确有助于农村居民摆脱脆弱的贫困陷阱。

表6 采用倾向值匹配方法的稳健性检验
(六)家庭收入异质性检验
以下考察互联网嵌入影响农村居民贫困脆弱性的异质性特征。结合家庭人均收入的划分标准,将样本分为高低四个分位,表7检验了不同收入分位的农村居民借助互联网嵌入而影响贫困脆弱性的异质特征。结论显示,互联网嵌入对不同收入层次家庭贫困脆弱性的影响不同,互联网嵌入对于表7 的(1)、(5)两列最高25%收入分位家庭的贫困脆弱性影响不显著,但互联网嵌入对于其他分位收入家庭的贫困脆弱性都有显著的抑制作用,且对于最低25%分位低收入家庭贫困脆弱性的削减效应最突出。进一步就中高收入群体或中低收入群体内部展开比较,不难发现,互联网嵌入在表7 的(2)、(4)、(6)、(8)列系数绝对值均始终分别大于表7 的(1)、(3)、(5)、(7)列系数绝对值,这说明互联网嵌入对于农村居民的高收入群体(50%分位以上)和低收入群体(50%分位以下)各自内部的相对低收入人群(中上25%收入分位家庭和最低25%收入分位家庭)降低贫困脆弱性最明显。可见互联网嵌入的确有助于缓解农村居民高低收入人群内部的收入阶层固化,有利于农村居民群体缩小内部相对收入差距。
五、机制检验
互联网嵌入为何助力农村居民降低贫困脆弱性?结合理论假设2,进一步从社会资本渠道,建立中介效应模型展开验证。具体而言,将问卷中“家庭过去12个月的人情礼支出”取对数,作为农村家庭社会资本强度的代理变量;借鉴Baron 和 Kenny(1986)[44]、温忠麟和叶宝娟(2014)[45]的研究,建立如下因果中介效应计量模型:
mediatori=α1+β1interneti+γ1Wi+αd+ξi
(5)
vuli=α0+β2interneti+β3mediationi+γ2Wi+αd+ζi
(6)
其中,第一步检验立足方程(1),重点验证β0的显著性,判断是否存在中介效应(2)表2已经检验了互联网嵌入对贫困脆弱性的显著影响,表明存在中介效应,不再赘述。。若β0显著,第二步则检验方程(5),即将社会资本刻画的中介变量(mediator)作为被解释变量,检验互联网嵌入如何影响农村居民的社会资本强度,观察β1是否显著,判断是否存在间接效应。若间接效应成立,第三步将中介变量引入计量方程(6),检验互联网嵌入和社会资本对贫困脆弱性的综合影响,考察β2和β3的显著性,判断是否存在直接效应。若直接效应也成立,第四步比较β1×β3与β2符号是否一致,判断是否存在部分中介效应,根据(β1×β3)/β0计算中介效应占比。
借鉴Imai等(2010)[46]、Frölich和Huber(2017)[47]的因果中介分析法(CMA),表8报告了基于上述因果中介效应模型的实证结果。鉴于表2已经充分证实了方程(1)中互联网嵌入系数β0的显著性,说明中介效应成立,在此不再赘述。在表8的(1)列,检验方程(5),发现互联网嵌入系数β1高度显著为正,说明互联网嵌入的确提升了农村居民社会资本强度。表8的(2)~(3)列检验方程(6),显示中介变量系数β3显著为负,说明社会资本也促使农村居民贫困脆弱性下降,证实模型存在间接效应。通过观察,发现方程(5)互联网嵌入变量与方程(6)社会资本中介变量的乘积项(β1×β3)符号为负,其与方程(6)中互联网嵌入的系数β2符号一致,证实存在部分中介效应。通过Sobel检验,发现表8的(2)~(3)列各模型的Sobel检验值较高、p值较低,证实社会资本是互联网嵌入助力农村居民降低贫困脆弱性的主要中介渠道。计算中介效应占比,发现互联网嵌入通过社会资本而抑制农村居民贫困脆弱性的中介效应占总效应的比例位于24.92%~44.47%之间。
图2的(a)、(b)部分分别报告了社会资本作为中介变量(互联网嵌入影响两类贫困脆弱性)的敏感性检验,显示当且仅当方程(5)和方程(6)的误差项相关系数分别等于-0.422和-0.415时,互联网嵌入通过社会资本抑制农村居民贫困脆弱性的中介效应才可能为0,由此可见,整体而言,社会资本作为互联网嵌入来降低农村居民贫困脆弱性的中介效应具有显著性。此外,进一步选取家庭每月邮电通讯费支出作为互联网嵌入的工具变量,采用引入工具变量的中介效应模型展开稳健性检验。具体实证结果见表8的(4)~(5)列,发现在采用工具变量方法控制模型内生性之后,社会资本仍然是互联网嵌入助力农村居民降低贫困脆弱性的主要中介渠道,且此时互联网嵌入通过社会资本来抑制农村居民贫困脆弱性的中介效应占总效应之比大幅提高,甚至分别达到了84.79%和94.34%。

图2 社会资本作为中介变量(互联网嵌入影响两类贫困脆弱性)的敏感性检验
进一步借助因果中介效应分析法(CMA)检验思路,将可能影响农村居民贫困脆弱性的具体因素细化,作为农村居民贫困脆弱性的代理指标,剖析互联网嵌入影响农村居民贫困脆弱性的中介“黑箱”。其一,就业是农村居民创收的重要来源,是降低贫困脆弱性的基础要件。选取问卷汇报的农户是否“外出务工”,作为农村居民获得非农工作机会的关键就业指标。将就业作为因变量,检验互联网嵌入是否通过社会资本中介渠道影响农村居民就业。表8的(6)列采用因果关系的中介效应模型检验显示,互联网嵌入通过社会资本来促进农村居民获得非农就业的中介效应占比达到了8.44%。可见,互联网嵌入通过社会资本的中介渠道,助力农村居民获得非农工作机会,助力农户摆脱脆弱贫困陷阱。其二,创业也是农村居民预防返贫的重要手段。结合问卷,将家庭层面是否“从事个体私营活动”进行赋值,构建农村家庭居民是否创业的虚拟指标。表8的(7)列将是否创业作为被解释变量,检验了互联网嵌入通过社会资本影响农村居民是否创业的因果中介效应。结果显示,互联网嵌入通过社会资本来促进农村居民创业的中介效应占比为8.38%。其三,从农村居民使用先进农业机械入手解析可能的中介渠道。将问卷中户主“是否支付农机租赁费用”,作为农村家庭是否外包应用农业机械的代理指标。表8的(8)列检验显示,互联网嵌入也通过社会资本的中介渠道来促进农村居民采纳农机设备,其中介效应占比为8.05%。综合而言,社会资本是互联网嵌入抑制农村居民贫困脆弱性的主要中介渠道,借助互联网嵌入下的社会资本推力,农村居民在就业、创业以及农业机械使用上都更具优势,因此,助力农户摆脱脆弱贫困陷阱。此外,图3的(a)、(b)、(c)三部分分别报告了社会资本作为中介变量(互联网嵌入影响就业、创业和农机设备使用)的敏感性检验,发现当且仅当方程(5)和方程(6)的误差项相关系数分别等于0.1或0时,互联网嵌入通过社会资本促进农村居民就业、创业以及使用农机设备的中介效应才可能为0,由此可见,社会资本作为互联网嵌入影响农村居民就业、创业等的中介效应也稳健显著。

图3 社会资本作为中介变量(互联网嵌入影响就业、创业和农机设备使用)的敏感性检验
六、结论与建议
削减相对贫困与实现共同富裕成为新时代中国减贫事业的重心。贫困脆弱性是相对贫困的典型特征,也是理解脱贫攻坚和预防返贫两阶段目标的衔接桥梁。本文立足2018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在测度贫困脆弱性的基础上,考察了互联网工具如何影响农村居民的贫困脆弱性。研究发现,与没有互联网接入的农户相比,使用互联网的农村居民陷入贫困脆弱性的概率更低,其预防返贫的能力韧性更强。这说明互联网是中国后脱贫时代巩固脱贫成果和预防农村居民返贫的必要工具。就机理而言,发现社会资本是互联网嵌入助力农村居民降低贫困脆弱性的主要中介渠道,借助互联网社交工具,农村居民在就业、创业以及利用农业机械方面都更有优势,最终推动了农村居民摆脱脆弱贫困陷阱。
为了更好地巩固脱贫攻坚成果,推动农村低收入群体预防返贫,本文从加强农村数字基础设施建设、促进农村数字普惠金融发展以及推动农业数字人才积累三个方面,提出以下政策建议:
第一,统筹数字乡村建设,为互联网更好赋能农村居民生产生活创造基础条件。探索数字乡村的发展规律,统筹农村5G网络、人工智能、互联网、物联网建设,扩大农村偏远地区、落后地区、人口稀疏地区的光纤网络、移动通信网络、数字电视的覆盖面,提高农村居民互联网实际应用率,缩小乡村内部的“数字鸿沟”,减少“数字排斥”。促进数字引领驱动农业现代化,全面推动智慧农业,提升农业生产的智能化、网络化,在生产决策、产品质控等领域加强数字创新,实现“数字兴村”和“数字兴农”。
第二,加强农村数字普惠金融发展,保障农村居民参与数字交易的最后一公里。充分挖掘数字普惠金融对农业的赋能,扩大农村数字普惠金融信贷业务,夯实乡村数字金融发展的基础设施条件。组织开展农村数字金融培训,引导农民提升数字操作能力,加大农村数字金融服务平台建设,针对农村偏远地区、低教育人群以及易返贫群体,量身定制数字普惠金融服务。运用数字普惠金融手段,深度嵌入农村土地流转、农业补贴、农民保险等涉农业务,优化农村金融风险管控。
第三,重视农村数字人才培养,提升农业数字人才积累。积极推广“农业数字技术员”,探索新型职业农民数字人才培训体系。大力培养熟悉信息化、懂数字技术的高素质农民,重点提升乡村经营性人才利用数字化工具的能力。加大农村数字人才培育力度,创新数字人才培养模式,开展数字人才实训交流,培养兼具文化内涵、技术水准和创新思维的乡村数字人才队伍。充分结合乡村人才振兴战略,加大数字乡村复合人才培养,支持数字乡村创新创业,推动数字乡村发展。广泛调动农村干部、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以及广大农民培训掌握数字技能和互联网知识的积极性。加强电子商务应用对农村居民的人才辐射功能,切实采取可行措施鼓励数字人才下乡,多渠道、多形式地推动数字乡村人才建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