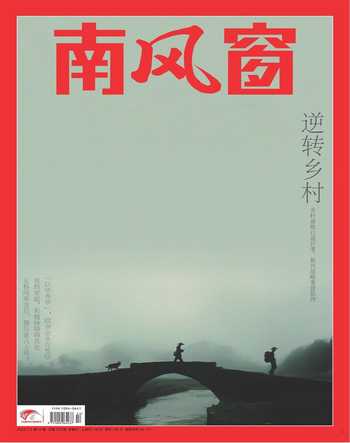我的家庭,和精神障碍共处
2023-07-26端霓
端霓

时隔6个月之后,我再度陷入低潮。
身为记者的我,在又一个无法按时交稿的晚上,向妈妈求助,表示自己需要正式的治疗。
“我可以带你去精神病院看一看。”妈妈说。那是她熟悉的、往返20余年诊疗取药的地方。作为一名资深双相情感障碍患者,听筒里妈妈的声音很平静,她说可以带我去看看,以打消我的焦虑,“但那儿,并没有你希望的那样有用”。
关于交稿,我的上一次失败尝试,在半年前的除夕。
彼时,两年没有回过家的我,接到主编的约稿—过年返乡,回望家庭。虽然这是媒体每年新春的惯例动作,但我的为难显而易见。前年除夕,爸爸跟他的新妻子和未满一岁的新小孩在一起,妈妈住在老家的精神病院,而我留守在1800公里之外的广州,我们一家像天南地北的三座孤岛。而除夕,也是我的生日。
这一次返乡约稿,我本来是抵触的,但是又没有拒绝。因为我心里存有一丝希望,想借着“记者”这份工作的名义回家,探索我这样的家庭里成长的小孩,应该怎样去看待自己的父母,怎样看待家庭,怎样回归常态、获得幸福。
遗憾的是,我失败了,而且“交稿失败”所带来的沮丧在半年后又席卷了我。
当下,我想将自己从工作秩序的全面崩塌中解救出来,最快捷的方式也许就是回到半年前,让我从那个悬而未决的议题中降落。我不知道这样的诉说是否正当,但我相信,这不止是我一个人的困顿,困在其中的还有我的爸爸妈妈,更多在公共场域失声的精神障碍患者,以及他们身边有相似境遇、需要支持的人。
这是一个讲述普通家庭里每个人如何同精神障碍共处的故事,我们身在其中,相互逃离又彼此羁绊。
回 家
下定回家的決心,不是件容易的事。
我虽然答应了编辑的约稿,但仍旧改签了两次机票,直到正月初二,才悄悄登上回家的航班。
放假前,妈妈说她非常非常想我,但老家还有阳性病例,嘱咐我不必冒险勉强返乡,我顺势答应。对于爸爸,之前我因为一次争吵拉黑了他的所有联系方式,已达一年之久,更没人敦促我回家。说实话,我也不知道该怎么面对他们,索性向他们默认,今年也跟去年一样不回家。
直到我拖着虚浮的双脚,恍恍惚惚地过了安检,才忙不迭掏出要写稿的借口,瞒着爸妈,只告诉了姑姑:我马上回来,拜托晚上家里分给我一张床睡。
我们一家的疏离,某种程度上是因为妈妈的病。
这场精神疾患从我1996年出生的除夕暴发,或许是因为当年的生育观念相对守旧,条件有限、照料不周,妈妈和奶奶一家产生龃龉,她很快入院并确诊双相情感障碍,开始了在躁狂和抑郁的波峰波谷间载沉载浮的斗争史。
躁狂像滔天的潮水,将人卷起抛向高空。一个小小的偶发念头,对常人而言,只是颗种子,但在躁狂发作时会迅疾地生根破土发芽,抽枝后开出一朵朵花,果实结出又落地,不一会儿一片茂密的森林已然拔地而起。每分每秒的想法都像大爆炸的宇宙,人会妄想自己是天选之子得了神谕,不眠不休地追随自己的直觉乃至幻觉,做出任何事情,直至意志和体能都被燃尽,在一片废墟上陷入虚脱。
而抑郁则像漫无边际的沼泽,人的能动性衰减,感到舒适和安全的活动半径急剧坍缩,出门困难,不能跟人会面,不愿听见声音,躺在床上起不来,会用一种言语和词汇之外的东西混沌地进行思考,读写和表达能力消失,最终对自己身体的感觉也模糊了。在极其严重的自杀尝试的瞬间,人生就已结束了一次,再次主动或被动地回返现实后,会遭遇一种能把人封印住的认知失调的陌生感。
妈妈就是在这样的精神困境中挣扎的,而我的描述,仅仅是冰山一角。
我想向你讲述故事的另一个版本。它是平静的、幸福过的,和许多人的家庭都一样。
因为这一切的时间原点是我的出生,所以每年除夕,我们的小家都会经历一个旧账被掀开的痛苦时刻。直到2018年尾爸爸和妈妈离婚,它才宣告结束。因为从此往后,除夕夜家里只有我和妈妈两个人。
但在我不得不讲述了这些极端的家庭情况之后,我想向你讲述故事的另一个版本。
它是平静的、幸福过的,和许多人的家庭都一样。
在介绍妈妈时,我极少提到她是一名双相情感障碍患者,我更愿意告诉别人,她是位有30多年教龄的老师,她在师专读的专业是历史,但她教过生物、也教过数学,还在职业生涯中期,从小学调到初中,克服了种种困难,工作一丝不苟,拿了五花八门的教学奖项。
她也是个称职的母亲。她的独生女儿安稳地长到27岁,一路都是“别人家的孩子”,考上了一所好学校,也在一线城市谋得了一份喜欢的工作。
疾病折磨着我的妈妈,但是没有摧毁她。
在我读幼儿园前,她便病情好转出院,在爸爸的持续监测下,通过咨询、服药,在十几年间把自己的生活管理得井井有条。
妈妈住院时,我也被奶奶和姑姑照顾得很好。她出院后,我们一家三口一起生活,我在和睦宽松的家庭氛围里从幼儿园一直读到大学。
那是一个什么样的家呢?我的家里,沙发和床上总是堆满了闲书和时新刊物,我的爸爸拥有十里八乡的第一台胶卷相机,后面又升级成了数码相机。
他是一位语文老师,很文艺,思想开明,爱看小说和电影。2010年我恰好升入他所任教的高中,我们“狼狈为奸”,遇到无聊的阅读题和作文他会帮我去网上找答案,在我压力大时,他甚至去骗我的班主任,说他的女儿生病了,牵着我的手大摇大摆穿过门卫,回家吃零食追剧睡大觉。
我们一家有过很多幸福的时刻,因为小县城里的老师和学生的作息时间高度一致,所以我几乎每顿饭都可以和爸爸妈妈一起吃。我们在客厅里端着碗一边看电视一边谈天说地,再分头去学校。我们也会一起放假,所以有许多一起出游的机会,妈妈也像所有女孩一样爱美爱拍照,他俩改完作业我写完作业,就一起去附近的郊野玩耍。
“我是因为工作太忙了,才初二回家。”想着过去的事情,我这么跟在机场接到我的网约车司机师傅解释。
因为师傅很健谈,而我想掩盖无人问候的窘境,我对司机说:“我爸妈他俩在家做着饭等我回去呢!”在言语的一来一往中,我甚至不得不,把这顿想象中的饭描绘得越来越具体。
实际上,爸爸再婚后,再也没有来机场接过我了。刚刚唯一知道我航班落地的姑姑,正在上班。没有人在家里等我。
窘 迫
我和师傅在车里的谈笑风生被一个陌生来电打破。“请问您是?”我接起电话。
“我听你姑说你回来了。”右边听筒里传来的,是一年多没听到过的我爸的声音,左边,网约车师傅投来目光。我瞬间因为谎言被拆穿窘迫到失语,向爸爸解释自己怎么回来的声音,越来越小。
但,比我更窘迫的是我爸。
沉默地行驶了半小时后,我被放在姑姑家门口,我打电话问还在上夜班的姑姑钥匙在哪里,不一会儿就有人从楼道里探出身子—是我爸。
他头发白了许多,看起来还比原来矮了一点儿,我意识到我们已有整两年没见过面了。
他想要像往常那样接过箱子,但我把背包塞给他,假装目不转睛地提着箱子上楼,箱子太重了。
到了姑姑家的客厅,不知是因为太久没见的难为情,还是北方室外的天寒地冻,他放下行李,讪讪地搓着手。
断联的一年多时间里,我和我的爸爸,唯一的交集发生在我的视频软件上。
两年前,我把一个我不常用的视频平台的会员账号给了我爸,给过就忘了。直到去年的十一假期,我为了一期人物采访,登录上去连续几天看一档冷门节目,无意打开了历史记录,才发现,那一个账号里另一个人的密密麻麻的观看痕迹。
无疑是我的爸爸。他在看电视剧,时间非常规律,几乎每一天都看到凌晨4时甚至清早5时。
在公司加班的我,把他的視频观看记录投屏到大荧幕上,一条条往下翻。
我仿佛看到,他在白天,陀螺一样地为了学生和重组的家庭劳神费力,也许只有夜深人静才有自己一点点清净的时间,侧躺着,把亮度调到最低,在小小的播放器里逃离日常。
他还会上火的时候生点口腔溃疡一类的小毛病吗?十一长假,他还会像以前带着我一样,带着他的新家人回奶奶家摘石榴和柿子、烧柴火炖土豆排骨吗?
公司空无旁人。我大哭一场。
终于再见了。我有机会当面问问他过得怎么样,但就在旁边,他的新小孩 (原谅我不知道怎么称呼这个陌生的孩子)刚满一岁、蹒跚学步、牙牙学语,正是需要大人每时每刻关注的时候。
爸爸一边照料小朋友,一边和我就这样面对面地坐在姑姑的客厅里。
望着万家灯火,他也哭,我也哭,哭到晚8时,他牵着我回家了。
我们有一搭没一搭地讲着话,话头常跟着小孩的积木一起,落在地上,摔出脆响。
2020年也是在十一假期,我回老家放松过节,和爸爸一起在妈妈家和奶奶家之间往返,上山下河好不快活。彼时爸爸和妈妈已离婚近两年,但我和妈妈都觉得除了分居,日子跟以往没有太大差别。家里有东西坏了或者有大件需要采买,爸爸会第一时间上门来办得利利索索,得了好吃好喝的会给妈妈送来一份,需要按时去医院复诊取药他也会开车陪同。
而分居,也没什么不可理解的。妈妈的病情从2014年开始有反扑的迹象,如果一定要归纳出一个诱因,也是不可理喻:那年夏天我上大二,进医院拔了两颗蛀牙,这种性质的入院没有人会在意,但精神障碍这桩事似乎就是这么没有道理可讲,妈妈为此开始偶尔情绪失控。
我还记得2014年的那一年除夕,妈妈突然开始无厘头地回溯往昔的创伤,暖水瓶、陶瓷杯被摔了一地。我和爸爸无力劝解,又觉得妈妈这样子,我们作为家人是有些许责任在身上的,崩溃极了。
晚上7时多,我和爸爸,我们两个逃出门去,漫无目的地在空荡荡的大街上乱晃,望着万家灯火,他也哭,我也哭,哭到晚8时,他牵着我回家了。
我们三个打开电视,热了晚饭,伴着春晚的背景音,端出了我的生日蛋糕,像刚刚几个小时什么都没有发生一样。
在我后来常年在外求学工作的日子里,我相信,爸爸曾独自一人无数次地面对过类似那晚一地鸡毛的场景。
和精神障碍共生,像一场旷日持久的战争,我知道妈妈尽力了,她已经努力地好好维持了那么多年,平日跟我的交流里从未流露出异样;
我更知道爸爸尽力了,他知道那些只是病理性的表征,他长久以来努力累积经验,一次次把冲突平息过去。
但人的意志是会日复一日地被消磨的。所以,当我在考研结束的那一天,被他们轻描淡写地告知,他们已经离婚,我豁达得很,甚至安慰他们:拉开一点距离,反倒让彼此都轻松。
但这种天真的豁达和我与爸爸的“革命情谊”,在2020年的十一假期产生了裂隙。爸爸让我跟他去参加一个饭局,我很乐意地跟他一起出发。因为妈妈精力有限,陪他吃饭是我从小到大常做的事,而且不管席上有谁、我长到多大,爸爸总会给我夹鸡腿、剔鱼刺。
那一天,上完菜我们一桌人刚开始吃,一位看起来很腼腆的孕妇阿姨缓缓挪步进来,她坐得离我不远,我举手之劳帮她布菜,还搀扶她去洗手间。
饭局结束后,我和爸爸回了奶奶家。
在我们漫不经心地在天井的石榴树下吹风谈天的时候,奶奶提起那个阿姨,爸爸连忙讲她们相处得很好。我也卖乖说:“是噢,我还扶她去洗手间。”话一说出口,一个我从未料想过的事实攫住了我—爸爸再婚的时候我在出差,忙得不可开交,对此并没有实感,而那位孕妇阿姨的身份不言而喻。
奶奶应该没想到,爸爸从头到尾没跟我提起过任何事情。爸爸眼神躲闪,露出窘迫的神色,我本能地转移了话题。
而此刻,我的余光又捕捉到那有过之而无不及的窘迫神情浮现在爸爸脸上—那个小朋友从姑姑家的客厅,憨态可掬地朝我扑了过来。
我朝他张开了双臂。我不知道我应该作何反应,我的脸上甚至还保留着我那亲和的“孩子王”式的招牌笑容。
相见时难
我在姑姑家,像鸵鸟把脑袋埋在沙子里一样从初二躲到初五,什么事也没做成,什么深度的交谈也无法展开。
但我逐渐意识到一件事,在这许多年里,不管是地理上千山万水的阻隔,还是亲人们心照不宣的保护,我都被保护地太好,而有意无意地回避掉了许多事情。
我一刹那明白了,妈妈为什么会在上个除夕重新住回了精神病院。
他们离婚后,爸爸仍对妈妈照顾有加。我们都以为,一切理所应当会在原有的轨道上运行,所有情感和关系都有转圜的余地。
但那样的愿望悄无声息地落空了。
要怪谁吗,可在这个过程里谁不需要依靠,谁又是容易的呢?怪病症本身吗,病又怎么可能像一个实体一样出來跟你复盘对证,向被搅和得支离破碎的生活开出赔偿的价码?
姑姑家离我的家只有500米,妈妈就在家里。直到初五,她还不知道我已经返家。
爸爸和姑姑问过我几次要不要回去,但我的确不知道该怎么面对我的家庭、我家里唯一的妈妈。我绝不可以也绝不会认为妈妈是当下家庭混乱的“始作俑者”,但我也担心面对她的痛苦,不愿意回到自己的家。那里曾经美好过,但也是物是人非的“第一现场”。
挨到初五的下午,我以我残存的理智计算发现,如果我再不回去,可能就要再等一年了。
我终究还是决定从床上爬起来,回到那个我居住了20多年的房子。
家里就像龙门石窟那样错落地摆放着各种神龛和佛像,我之前的衣服和书本都不知被丢到了哪里去。
这个过程太过艰难,我连一句额外的话语都无法说出,我没有发微信也没有打电话,直接走出门去。
到了,我开始敲门。
没有人开,妈妈果然是又在里面的卧室休息。我敲得更大声,我听到有脚步声由远及近,她开门了。
她先是愣住,缓缓地推了推眼镜,然后高兴得不得了,她唯一的日思夜想的女儿、她“无私”地让踏实待在广州别费力回来过年的女儿,不声不响地,就这么回来了站在门口,她反复确认这是否又是她千万次幻觉中的一次。
我进到屋里,发现整个家,比我上次走时更混乱了。妈妈的病让她偶有幻听幻视,她会误以为有人藏在角落昼夜不息地监控她,或是指挥她做这做那。她在绝大多数情况下保持清醒,但在理性、智识和现代医疗手段解决不了问题的时刻,她不得不求助于玄学和一些意味不明的复杂仪式。
夸张点说,家里就像龙门石窟那样错落地摆放着各种神龛和佛像,我之前的衣服和书本都不知被丢到了哪里去。那种熟悉的无奈和烦躁,又可耻地涌上我的心头。
妈妈问我是怎么回来,又准备怎么走,我已经没有任何心力去撒谎和圆谎,如实讲完,她也如我所料地暴怒了。
这个女儿,甚至是她在已经绝望地站上楼顶的风口,迫使她走回人间的最大动力。但这个女儿,回到老家不但不第一时间告诉自己,还要去“投敌”?
我实在难以向她解释清楚我为什么会这样做,但我自觉理亏。
我在妈妈的泪水中,环视熟悉又陌生的四周,只想马上逃跑。
但当她发现我们只剩一个晚上可以待在一起时,竟很快消了气:“妈妈不对,本来说好你就不回来了,你回来了我就已经是赚了,不得好好珍惜吗?”
这是很多场景下她惯常的“精神胜利法”,她开开心心地下厨去了。
疾患给妈妈带来了转换更快速的情绪,也意味着她比常人需要更多的休息,那天晚上吃完饭,我们很早就并肩躺在了床上。
大概是因为两年没见到的我终于回来,安心得过了头,本想好好夜聊的她竟很快睡熟了过去。我在一旁怎么也睡不着,竟然想起了很多类似于今晚的“熟睡”这种—疾病给她带来美好特质的场景。
她的情绪总是很充沛的,也是因为疾病,我们全家对彼此的容忍度都很高,我在她眼中仿佛无所不能的完美小孩。她常常在微信和电话里,毫无预兆地“发疯”一样天花乱坠地夸奖我,反复用文字和声音来强调我自己都已经忘记做成的某件小事。她发自内心地相信就算我不回家,也能在外面把自己照顾得很好,让她骄傲。因为她的病,我有时觉得自己得到了远超平常容量的父母之爱。她是那么那么爱我。
她也格外敏锐地关心别人的感受,有一次我因为繁琐的审批流程错过了期待已久的出行,悻悻地坐在打算去大吃一顿的公交车上向她吐槽时,她先是变着花样地把刻板的制度大骂一通,突然又郑重地跟我说:“我觉得你很棒,因为你知道难过的时候出去吃好吃的买喜欢的东西让自己开心,比闷在家里强太多啦!做得特别好!”
她是跟精神障碍很好地相处着的妈妈,也是因为莫名的神经质而天马行空的可爱妈妈,她跟别人的妈妈都不一样。
别亦难
第二天天亮了,我也该如期返程了。
爸爸开车来接我,我们三个人像之前每次我要离家去学校或者上班之前一样,煮一锅打卤面分着吃。
面条到了嘴里,妈妈像是才从漫长的睡眠中清醒,她之前设想的要带我吃的带我玩的都还没去呢,就已经要走了?她端着碗的手马上开始颤抖,眼泪又无声地滚了下来。
我其实是可以请假在家多留几天的,但是截稿日接踵而至,我自忖没有办法在这种过山车式的环境中写出任何东西,但还没等我出声,妈妈就又开始她一套严丝合缝的自我劝慰:“你从小就写不完作业睡不着觉,现在留你在家玩你肯定不踏实,还是走吧,忙完再回来。”
她一边碎碎念叨着,一边努力眨着眼睛喝面汤。
理智告诉我,为了工作应该走了。爸爸载我去到奶奶那里,很快就因为要照顾孩子先行离开。我跟奶奶吃了饭,奶奶也很不舍得,但也张罗着给我叫车去机场了。
我很少进行如此极限的出行,我原本计划搭乘的航班起飞时间是下午四时半,车子一点钟出发,预计两点多抵达机场。
但直到上了出租车,我还没有买机票。因为我盘算着,去济南要走跨城高速,理论上上高速之前,我可以随时叫停、下车。
我不想走,我想回家找妈妈。
她是跟精神障碍很好地相处着的妈妈,也是因为莫名的神经质而天马行空的可爱妈妈,她跟别人的妈妈都不一样。
我盯着导航上移动的定位,反复准备大喊一声让司机停车,但“想要写完作业”的好学生习性还拉扯着我,一路开到机场,我都没有开口。
拖着箱子走进机场,我感觉从没有一趟车坐得我这么累过。我瘫坐在入口的椅子上给妈妈打电话,说“我到了机场,但不想走了,我想回去”。
妈妈马上哭了:“你就坐在那里不要动,妈妈现在就打车去济南接你回来!”
我仿佛已经听到她手舞足蹈从床上跳起来被单摩擦的声音,又想哭又想笑:“你是不是傻,我自己打车回来就好了嘛,钱跟时间都省了一半。”
她又开始赞美我,觉得我很聪明。“是噢!你叫车,我在家等你。”
但她的理智好像也一并从卧室天花板落回到了体内:“跟你编辑说一声、请个假,应该就行吧?”她这么一说,我的头脑也冷却下来:“不然我还是走吧,会赶不上出刊的。”
正在我纠结之际,情绪大幅波动后的妈妈又暴怒起来。我发觉因为疾病的影响,她再次难以自抑地陷入了前一天下午未竟的愤怒里,她开始语无伦次地發脾气,把之前所有受伤的事情一件一件摊开讲。
我知道这不是她真实的反应,但还是听不下去,用最后的力气买了那张计划中的机票,上气不接下气地大哭:“好了妈妈,我买好票了,我要走了。”
她又一下子平静下来,边哭边坚定地说:“想回来就把票退了回来吧,别疼钱,妈给你报销。当然你觉得必须得完成工作,就先走,下回清明就能回来了吧……”又在微信上敲字:“着急的话元宵节咱就回来!”
尽管这么说,我还是没有下定决心,时钟已过三点,我想先安检好了,先登机再说,直到飞机已经在跑道上向前推进,我还在搜索“滑行时能否要求下机”。
但还没看到答案,已经起飞了。
我关掉手机,一路哭到白云机场,刚一落地就给她打电话:“妈妈我现在就重新买票飞回家去好不好?”
我听到她在那头哭了又笑了:“你赶路一天太累了,先坐地铁回去休息吧,睡个好觉起来写稿,不然你哪有心思玩?”她又顿了顿,跟我商量说:“等你以后有空,也给你老爸打个电话。”
这一刻,我突然感觉到,她已经完完全全地原谅了我这次回家的所有荒唐。我同时也意识到,她其实早在上个春天出院联系我的时候,就又一次以她的方式,从疾病手里逐渐夺回对生活的掌控,我的崩溃反倒是一种被亲情蒙在鼓里的滞后。
我不再哭了,开始往地铁站走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