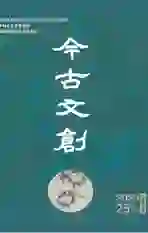论《卡彭塔利亚湾》中的混杂性
2023-07-20陈家会
【摘要】本文借用后殖民理论中的混杂性理论,分析了亚历克西斯·赖特笔下的《卡彭塔利亚湾》中的澳大利亚白人与土著居民之间的矛盾关系。从语言和文本叙述混杂到关系混杂,在一定程度上重现了土著真实历史。白人与土著混杂性一定程度上消解了澳大利亚白人的殖民话语,为土著的历史以及文化身份的重构赢得一片空间。
【关键词】亚历克西斯·赖特;《卡彭塔利亚湾》;混杂性;解构
【中图分类号】I61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6-8264(2023)25-0004-03
【DOI】10.20024/j.cnki.CN42-1911/I.2023.25.001
《卡彭塔利亚湾》于2007年获迈尔斯·富兰克林文学奖,其作者亚历克西斯·赖特成为首位独享该奖的土著作家。该书把澳大利亚土著的神话传说以及时代信仰和现实历史混杂起来,描述了一幅虚实相间的画卷。在描述时所使用的混杂语言以及混杂的叙述策略皆从内部挑战了殖民权威。
国内外学者从不同角度对该书进行研究。Ben Holgate(2015年)重新定义了《卡彭塔利亚湾》中作为后殖民话语的魔幻现实主义。Sefton Rowston和Adelle L(2016年)认为亚历克西斯·赖特挑战主流的希望哲学范式,从反乌托邦的本土视角重新创造“未来”。詹春娟(2015年)讨论了该书土著性的混杂构建,认为赖特通过混杂的表述结构和叙述方式意在复原历史本真,抵制强加于被殖民的权威意识,逐步构建土著人本身的话语权利。吴迪(2016年)次年分析了澳大利亚白人与土著之间相互混杂,互相依赖的矛盾关系,认为《卡彭塔利亚湾》解构了边缘与中心的界限,在一定程度上恢复土著的地位与话语权。张智荣(2018年)从叙事策略,土著对宗教信仰的坚守以及精神故土的捍卫三方面探讨了土著如何重塑自己的民族文化身份。冷慧和宫红英(2018年)从土著梦幻的世界观中阐释了主体的意义反叛力。
本文援用当今跨文化研究和后殖民研究中的混杂性概念来重新探讨小说的主题含义和艺术价值,因为后殖民社会中混杂性意味着消除各种等级制严格的界限与桎梏,也意味着多力抗衡空间的生成。在巴巴看来,混杂性是一个相互混合的过程,是一种解构霸权的策略。混杂性使权威话语问题化,逆转了殖民者的权威,于是殖民话语逐步失去权威性。[1]114
本文以混杂理论出发,通过分析《卡彭塔利亚湾》中混杂的关系、语言和文本叙述,揭示殖民权威的可瓦解性,肯定土著文化以及话语权的基础上。本文认为,通过混杂的模糊手法,可以看到了土著和非土著和解的可能性,这对双方来说都是一个新的开端。基于此,本文从混杂的白人与土著关系解构了白人身份的优越性;从混杂的文本和叙述技巧上证明了土著的话语权。在解构的基础上,本文认为混杂性为土著与白人的和解带来了可能,对于彼此来说都是一个新的开端。
一、白人与土著关系的混杂
后殖民主义学家霍米·巴巴对身份有其见解。他认为身份是不断变化的,是一个过程,无法和个人,社会分隔开来看待。它是个人通过语言、社会和无意识的演练形成的。[2]67对于文化身份来说,文化总是不完全相异。尤其在多元文化蓬勃的今天,不同文化相互交流与碰撞。这自然形成了混杂的文化身份。在巴巴看来,殖民者看到被殖民者被同化之后,会产生一种混杂的情感。既对自己文化的优越性认同,又害怕被同化的土著摧毁其优越性。殖民者在自我的认同定位上,会产生一种危机。[3]203殖民者对被殖民者既贬低又好奇的矛盾状态指向“那种‘他者性,既是欲望的目标也是嘲笑的目标。”[1]67对于被殖民者也是如此,殖民者的文化优越性使得被殖民产生自身文化的卑劣感。但与此同时被殖民者也能看到殖民者的劣势,从而使得被殖民者觉得自己不再处于低劣地位。殖民者与被殖民者在优势与劣势中起起伏伏,形成一种混杂的矛盾关系。他花时间学着如何讨城里那些家庭主妇们的开心。[4]153但楚斯福尔也发现了自身身份的缺失,于是强烈渴望找到一个低下的他者,重新建构自己身份的优越性。于是后来,楚斯福尔在凡特姆家胡作非为,对格里亚心怀不轨,他认为自己是凡特姆家里的男人,并且可以保护格里亚和凡特姆一家。这位小镇白人警察对于土著的矛盾混杂态度,贯穿其一生,导致了最后的毁灭。这也就是说无论被殖民者反抗与否,殖民关系都在悄无声息的运作,最终被破坏。巴巴认为,殖民关系总是暧昧的,因为如果被殖民者变的与殖民者一模一样,那殖民的权威性,优越性将不复存在。[3]205土著对于白人亦具有混杂的态度,他们不自觉的认同和模仿白人价值观念,但是在发现白人问题时,又自觉抵抗白人文化。安吉尔·戴是模仿白人价值观的代表,她被称之为垃圾女王,她认为土著和白人的区别在于白人信奉基督教。白人富裕,是因为他们供奉着圣人的雕像。但与此同时,安吉尔·戴也抵抗白人文化,她对于澳大利亚白人的品性与行为了如指掌。她把那些写“官方文件”的人称作“胡说八道的伪君子”。[4]80莫吉·费希曼认为,天主教的教义像格洛格酒一样,毒化了土著人的思想。[4]258土著对于白人的混杂态度也暗示了,土著不完全的处在劣势,在这种模模糊糊的混杂关系中,总会产生一定的抵抗。认同和抵抗存在于殖民者与被殖民者摇摆不定的混杂关系中,使得殖民话语变得不纯,从而进一步解构、颠覆殖民话语。
二、“混杂”的语言与文本叙述
在《黑皮肤,白面具》中,法农认为用一种语言与接受一种文化无异。殖民过程中,压制被殖民语言,推崇殖民语言成为帝国主义统治的有效手段。[5]237澳大利亞地理文章估计,在殖民化之前使用的250种土著语言中,今天只有50种仍在使用。因为使被殖民者使用殖民者的官方语言是殖民统治最有效的方法,被殖民者一旦使用官方语言便会踏入失语状态。正如《卡彭塔利亚湾》所说的,在德斯伯伦斯说话要留神,万一被传到某些人的耳朵里,就会带来一些不可知的麻烦。被压迫的不只是语言,还有被殖民者。但不可否认,用英语写作可以收获更多的读者。语言是多层次的,不确定的。在语言上吸收同化或以模仿求颠覆是使得英语扭曲变形的常用方法。在任何情况下,语言的纯粹性在一个文化多元里都不可能实现。阿尔瓦雷斯在《作家的声音》一文中说过,作家在写作时可能会听到一些不喜欢但确实来自内心深处的声音。对于作家们来说,既然英语受众更广,那就应该掌握好英语为自己的创作服务,从而打倒英语的权威。如果英语含有殖民者的思想,那就挖去其思想。[6]34正如混杂英语(englishes)一样,作家们可以使用当地特色改造英语。赖特坦言在写作中,在叙述原住民故事时尽量使用的土著语言和本土化措辞方式。《卡彭塔利亚湾》中,赖特很明显地将土著语言的特色和创造力铭刻在英文字母中。这种混杂性语言强调的是语言的开放性、延宕性和协商性,它使语言摆脱了僵化的本质,成为积极的、能动的社会符号。[7]101书中描写了姆赤用结巴的英语劝说诺姆,却被诺姆讽刺道,说的哪门子外语。姆赤的英语带有土著特点,是一种混杂语言,这从内部瓦解了英语的权威性。通过挪用和重构帝国中心语言,使之脱离殖民优势地位。混杂使得殖民语言带有杂质,最终令其从内部崩溃,对殖民的反叛与颠覆也由此实现。
文本叙述层面上,土著作家也不是单纯地用土著文本形式和内容推翻白人权威。而是强调杂交:“运用所谓‘白人的形式(如小说)来写本土故事;跨越既定的记载,去掉固定的观点;用土著所谓的‘胡说八道或‘屁话,将幻想同幽默结合。”[8]264各个故事之间存在联系但又相对独立。文本中的时间线是水塘式存在的——非线性永恒。[2]46这一时间线体现了土著的叙述风格,在他们的认知中,远古和现在融为一体。叙事时间在《卡彭塔利亚湾》中弹性伸缩,就像主人公诺姆,谁也不知道他活了多少年。水塘式时间观叙述手法解构了传统小说线性时间观。在内容上,小说开篇从远古时代开始,带读者走入古老的历史传说,接着笔锋转向被污染的德斯伯伦斯小镇现状。神话与现实的跳跃,展现了土著悠久的历史与现实的凄切。四千多年的土著文明被撕裂,被肢解,被驱赶到边缘的世界。[8]64赖特再现了土著神话的恢宏与历史的悠久,土著的历史以口口相传的形式存在于土著人心中,永生不朽。虽然没有文字记载,但岩洞里,洞壁上留下了老祖宗画的关于人类历史的壁画。然而,澳大利亚白人的历史却是从“骆驼被赶走”开始的。澳大利亚白人将这一微不足道的小事记录在史册,恰也证实了白人历史的不堪一击。历史的叙述,于被殖民者来说是一种对自我的把控。把握了历史与历史的叙述,就意味着看到了时间的入口。赖特对于土著历史的真实再现,揭示了殖民霸权,引起了土著对历史的反思。混杂的语言以及文本形式与内容,使土著的历史、神话和艺术传统为更多人所知。使长期患有“失语”症的土著民族恢复了应有的声音。[8]66
三、“混杂”的解构策略
亚历克西斯·赖特试图通过写作来向世界展示澳大利亚是谁、在做什么以及如何思考;并让所有人看到,土著并不是一个封闭的民族,他们一直都在关注外面的世界。澳大利亚土著属于这个世界,是世界的一部分。《卡彭塔利亚湾》就讲述了一个从未被听过的澳大利亚历史。赖特通过混杂的叙事再现澳大利亚历史,展示了土著人民真实生活状态以及土著对于殖民权利的反抗,从而在一定程度上瓦解了殖民权威。她通过还原土著历史,解构殖民权威,为土著重获历史与话语权。然而赖特深知历史不能重来,因此《卡彭塔利亚湾》再现历史的同时也面向了土著的未来发展。赖特在《卡彭塔利亚湾》中通过混杂的语言与文本消解了殖民的话语权威,通过土著与白人的混杂关系瓦解了殖民与被殖民的二元对立。在面向土著真实历史的基础上,为土著未来的发展赢得一片可能性空间。这种混杂性不止体现在语言和文本上,还体现在土著与白人的文化关系上。小说揭示了土著在澳大利亚生存的困境,但同时也为土著赢得了一定的话语权。长期以来,殖民者通过民族暴力,文化控制在经济与政治上对被殖民者进行非人道的压制。澳大利亚土著被视为劣等民族,“不那么像人,不怎么开化,是小孩子,是原始人,是野人,是野兽,或者是乌合之众”。这种把被殖民者看做劣等民族的种族暴力使被殖民者逐步丧失话语权。德斯伯伦斯中,土著作生活在小镇的边缘,作为澳大利亚边缘人存在。而城里白人住在镇中间。白人对土著进行杀戮,如安吉尔·戴所说:“你们杀死了我们多少人。早在我们出生之前,这个家族许多人被你们杀害。”[4]108土著被笼罩在白人犯下的罪行里。然而白人并没有自己构建的那么高级,土著也不并没有自身的劣根性。土著威尔勇敢坚韧,抵抗白人价值观,最终炸毁矿山,为土著赢得自己的生存空间。反观白人对海水很惧怕,反映了白人无知状态。这一对比有力的消解了殖民者与被殖民者的二元对立,解构了殖民所谓的优势,被殖民者所谓的劣势。赖特在书中也消解了白人的宗教的教化作用,神父丹尼在过去的几十年里,通过拳击、唱歌、谩骂传授基督教义。通过多次拳击比赛,造就出一大批天主教徒。[4]326而诺姆对于大海的信仰始终带领诺姆前进,寻找到生命的方向。
混杂的语言和文本以及混杂的身份关系,超越了二元对立,构建了一个阈限性地带。在这一地带里充满了歧义,产生了一种表述的间隙能动性。赖特在《卡彭塔利亚湾》中运用的混杂性语言,摆脱了英语语言的束缚,使土著声音被大范围听到。她通过混杂的文本形式与内容,展现了土著真实历史,反讽了白人历史的荒唐。赖特对土著历史的再现无疑唤醒了土著的自我意识。然而赖特也深知,在殖民之下土著无法回归本真性。土著与白人的混杂文化关系,使得澳大利大土著与白人都生活在第三空间中。叙述中,赖特通过对比土著与白人,直接解构了白人的优越性。她通过混杂、破坏和重构来实现社会转型。殖民与被殖民混杂碰撞的第三空间印证了和解存在的可能性。如果在多元混杂的现代语境中,社会不愿意重新开始,进入另一个陌生、陌生和未知的世界,那么新的世界秩序很难建立。土著与白人在协商中文化共谋是必然选择。对于白人来说,可通过和解进入另一个想象世界来看到和感受这些意识形态差异并探索土著世界的形而上学,同时也将白人读者从无家可归的心理中解放出来。对于土著澳大利亚人来说,因为文化和精神生存远比物质或经济财富重要,和解为土著的发展带来了希望。正如蛇这一古老的形象贯穿文与小说的希望主题紧密相连。埃利亚斯·史密斯就是协商的产物,他处在白人与土著的接触点上,不断协商自己的身份。这也是巴巴所说的那个既非这个也非那个,而是之外的事物——第三空间。[1](28)第三空间的存在消解了白人话语权威,使得土著得以从边缘走向中心。赖特为所有土著发声,作为澳大利亚不可或缺的一分子,土著在多元文化共存的当代社会中必须拥有自身的生存权利与发展空间。
四、结论
赖特不止用写作为澳大利亚土著民发声,还为澳大利亚土著人的土地权、为改革宪法获得土著自治权、为保护土著自身的利益,奔走呼号,做了多年斗争。《卡彭塔利亚湾》揭示了历史的真相,为土著民发声。赖特在书中运用混杂的语言以及混杂的文化身份动摇了殖民语言以及其文化的优越性。试图通过混杂性颠覆殖民话语权威,从内部挑战了殖民话语。殖民者不再是中心,被殖民者也不再是边缘。殖民者和被殖民者不再是一种二元对立,而是一中相互依存的关系。小说的最后也隐含了赖特的美好期许,矿山和小镇被摧毁,土著从边缘人到中心人,不再“失语”,古老的声音和神话传递者希望。虽然飓风将该镇夷为平地,但并不是所有白人都死亡——只有违法者一人死亡。这个结果无论对于土著还是白人来说都是一个新的开端。赖特以恢宏的叙述为土著发音,通过诸多“混杂”,消解了白人与土著的二元对立,一定程度上恢复了土著的话语权。真正的民族和解可能还实现不了,但是对民族历史的再现是唤醒民族意识到开端,对殖民权威的消解是多元文化发展的关键。在殖民话语和语言形式中可能找不到土著和非土著主题的希望,但在混杂的棱镜中可能会出现。威尔(Will)和霍普(Hoe)名字所寓意的正是如此。
参考文献:
[1]Bill Ashcoft、Gareth Griffiths and Helen Tiffin. The Emire Writes Back[M].New York:outledge,2002.
[2]艾勒克·博埃默.殖民与后殖民文学[M].盛宁,韩敏中译.辽宁:辽宁教育出版社,1998.
[3]彭青龙.后殖民语境下的当代澳大利亚文学[J].外国语,2006,(3):59-67.
[4]吴迪.《卡彭塔利亚湾》中混杂性的演现探析[J].山东社会科学,2016,(4):100-105.
[5]Homi Bhabha.The Location of Culture[M].New York:outledge,1994.
[6]Ben Holgate Unsetting narratives:Re-evaluating Magical Realism as ostcolonial Discourse Through Alexis Wrights Carentaria and The Swan Book[J].Journal of ostcolonial Writing,2015:634-647.
[7]王福祿.神话、反种族主义与创伤—— 《卡彭塔利亚湾》的书写策略[J].复旦外国语言文学论丛,2019,(01):82-87.
[8]冷慧,宫红英.《卡彭塔利亚湾》远古“梦幻”世界观的当代叙述[J].英语研究,2018,01):42-52.
[9]亚历克西斯·赖特.卡彭塔利亚湾[M].李尧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2.
作者简介:
陈家会,女,安徽亳州人,助教,安徽大学外语学院在读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英美文学及澳大利亚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