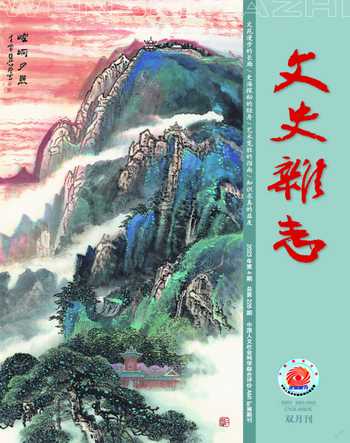任乃强先生对“成都”得名研究的贡献
2023-07-06田小彬
田小彬
摘 要:任乃强先生在上世纪80年代初连续发表了《成都》《赞同〈试为“成都”得名进一解〉》两文。他是继北宋史家以后第二个解释成都名义的,引发了关于“成都”来源和涵义的研究,有益于成都的发展。在这方面,任先生是引导者,贡献极大。之后,在有关成都历史的介绍中,无论是官方还是民间,多采用了任先生的说法。任先生学识非常渊博,却决不故步自封,在关于“成都”得名的研究中,堪称“活到老,学到老”的典范。不过,任先生撰写、发表两文时,年已耄耋,记忆力已经大不如前,所以他在《成都》一文的文末特别注明“未暇翻检书史,详作考证”。可叹的是,许多对任先生文字的引用者“懒”得去翻检书史,核对古籍原文,以致沿袭了任先生文字的某些舛误。
关键词:任乃强;“成都”得名研究;引导与贡献;引用误导
任乃强(1894—1989)先生是著名的历史学家。他一生的学术贡献主要体现在藏学、民族史和西南地方史三个方面。研究四川地方史,任先生的《华阳国志校补图注》是不可或缺的权威典籍。该书提出了大量新颖独到的见解。在关于“成都”之名的来源和涵义的研究中,任先生是引导者;因该研究有益于成都的发展,故贡献极大。
一、任先生引发“成都”得名研究
成都城和“成都”这个名称,可以肯定都是先秦时代就已經存在的。成都城的修建已有定论,是在“秦文王二十七年”即公元前311年由当时的蜀郡郡守张仪、张若连续九年的修建而成的。至于“成都”这个名称,从古到今,只有宋代的几个历史学家对它的来源和涵义进行过释义。
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学术繁荣,郭沫若先生将之称为“科学的春天”。[1]任乃强先生虽然年已耄耋,却以超人的精力,相继完成了《羌族源流探索》《川藏边历史资料汇编》等七部专著及《四川地名考释》等数十篇论文,其中就有引发“成都”得名研究的《成都》一文。
《社会科学研究》1980年第2期发表《成都》,为《四川地名考释》之首篇,也是引发在宋代对“成都”研究之后的第二波对其来源和涵义研究热潮的第一篇论文。任先生在该文中说:
鱼凫之后又曾出过一个名王叫作“杜宇”,他是耕种能手,也善于教人耕种。蜀国农业由他大兴,从而富强起来了,于是建成了国家,蜀人把他称为“杜主”。杜主的子孙,以杜宇为氏。传了若干世才到望帝杜宇,政权为开明氏所夺。……
成都城,则是蜀人已经向平原冲积土发展耕地时候才营造的。大概在蜀望帝杜宇任用鳖灵治水的时候。所谓鳖灵治水,不过把成都平原的沼泽积水排除,造成沟洫,使平原农田逐步增加起来,并不如昔人传说他凿开了那匹山把水放走。蜀民得到平原农田的生产丰收,大大富足起来,所以人人爱戴鳖灵,望帝也把政权交付与他,自己逃避到西山老林去死了。蜀民虽爱戴开明氏鳖灵,也仍不忘历世杜宇发展农业的功劳,怜念这位亡国之君,把催耕的布谷鸟称为杜宇,说他是蜀王杜宇的魂。
望帝杜宇新营造这座都城,所以取名“成都”,是取成功、成就、完成的意义。[2]
不久之后,任先生又撰写了《赞同〈试为“成都”得名进一解〉》,发表于《社会科学研究》1981年第1期。他说:
从公元前316年秦灭蜀,置成都县起,迄今二千二百九十六年来,只北宋初年乐史撰的《太平寰宇记》解释过成都二字的取义。他说:“成都县,汉旧县也。以周太王从梁山止岐下,一年成邑,二年成都。因名之成都。”
任先生连发关于“成都”之名来历和涵义的两文,意义非常重要。因为,作为一定地域标志的地名,虽然是特定地理实体的指称,却也是人们为某一特定地域位置上的自然或人文地理实体所赋予的专有名称。任何地名都有意义,它不仅代表该对象的空间位置、类型,还常常反映当地的自然地理或人文地理特征,保留着较多的历史信息以及深厚的文化积淀。
成都是著名的历史文化名城,也是发展迅速的现代大都市。遗憾的是,关于“成都”这个地名的由来及含义,却一直没有一个准确的解释。这对成都迈向国际大都会的发展是非常不利的。
任先生的两文,首提北宋乐史在《太平寰宇记》中解释过“成都”二字的取义。他用一“只”字表示这是有关“成都”之名的最早出典、唯一解释。这让学者对成都的来历有了可以寻源的方向。之后,在有关成都历史的介绍中,无论是官方还是民间,多采用了乐史的说法。
只是,任先生在引用乐史说法的同时,还有往往被人们忽略了的——就是他指出了乐史在《太平寰宇记》解释“成都”二字的取义,“这一推断,显然有三重错误”,即:
(一)蜀族与周族都是唐虞以后,分别从梁州与雍州发展起来的。在周族迁歧以前,这两族没有发生过政治、军事的交涉和经济文化的联系。这就不能说蜀国的成都,得名于周族迁歧的成就。
(二)周太王去幽迁岐,是举国迁徙,所至即成为都邑;并不似匹夫崛起,需要经过一年两年的经营才得成为国家,才得建成都邑。《大雅·緜》这篇诗,是周人歌咏太王迁到岐下时,开辟周原建造新都邑之诗。它说:“古公亶父,来朝走马,率西水浒,至于岐下,爰及姜女,聿来胥宇”。(第二章选地立国)“曰止曰时,筑室于兹”。(三章。卜定宅地)“乃召司空,乃召司徒,俾立室家。……作庙冀翼”。(五章。建成官寺和宗庙了)“百堵皆兴鼛鼓弗胜”。(六章。民众齐心,应鼓声合力建筑)。“乃立皋门”“乃立应门”“乃立冢土,戎丑攸行”。(七章。国都建成了)。足知:他是初至周原,立即建立国都,哪能有“一年成邑,二年成都”的旧说可据。
(三)“一年成聚,二年成邑,三年成都”是《史记·五帝本记》称道舜由匹夫崛起,群众向往,积年发展过程的话,也是“成都”二字最早的出典,不合误加到周太王的身上来。就引据典实来说,也根本错误了。
其实,乐史在《太平寰宇记》解释“成都”二字的取义时,还有一重错误,即成都不是“汉旧县”;因为早在秦灭古蜀后,成都就与郫、临邛一并成为秦所设立蜀郡时的最早三县。成都应该是秦旧县。
不管怎么说,任先生在上世纪80年代连发两文,因为指出了乐史关于“成都”二字的解释是错误的,所以在其后就引发了一波又一波关于“成都”得名研究的热潮。据不完全统计,有:李金彝、王家祐《成都考》,温少峰《试为“成都”得名进一解》,徐中舒《成都是古代自由都市说》,刘冠群《“蜀”与“三都”得名管见》,沈仲常、黄家祥《从出土的战国漆器文字看“成都”名字的由来》,西禾《蜀族的演进与成都聚落的形成》,谭继和《自然经济对古代成都城市发展的历史影响》,孙华《成都得名考》,钱玉趾《青川战国墓出土漆器文字符号考辨——古蜀文字“成都”的发现与试析》,贾雯鹤《圣山:成都的神话溯源——《山海经》与神话研究之二》,徐学书《“成都”释名——天堂·圣山·乐园》,周宏伟《从湖泊名称到聚落名称——“成都”的由来与含义探索》等等。这些文章,对探讨“成都”之名的来源和涵义都有积极的作用,而引发这一研究热潮的任先生,更是功不可没。
二、任先生治学的大家风范
任先生是著名历史学家。他学识非常渊博,却决不故步自封,持有传统文化人特有的风度、气派,堪称“活到老,学到老”的典范。
关于“成都”之名的来源,任先生在《成都》一文中是这样说的:
望帝杜宇新营造这座都城,所以取名“成都”,是取成功、成就、完成的意义。当时他是满意于得到鳖灵为相,把屡世希望垦辟这个冲积洳湿平原成为农田的愿望实现了。他选择成都城的地点,位于黄土冈陵与冲积大平原之间,既便于管理旧的农田,也便于开发新的农田,既不受潮湿水灾之害,又能收交通便利之效。他已踌躇满志,认为建国功成,可垂久远,这个都城可以一成不变了,所以命名为成都。这与舜的“一年成聚,二年成邑,三年成都”的成都含义是有所不同的。
《成都》之文发表后,受任先生“成都”之名研究的引导,比任先生小36岁,精通古文字学与音韵学而又富于深湛之思的温少峰先生主动向任先生请教并作学术交流。曾任中共成都市委党校副校长、研究员,四川大学客座教授的温少峰,长期从事国学尤其是先秦史研究,著有《殷墟卜辞研究——科学技术篇》《周易八卦释象》等书。据任、温后来一并发表的两文所述,他们两人在学术上的交谈使之一下子就成为了忘年交。温先生认为:成字以丁为声,与顶、颠、天等音同部,是羌族支派的本称,不当用华文字义作解释,并由“成熟”连称,涉想到蜀字音义来。任先生说,与温先生的交流,“使我受到很大启发。我们洽谈两次,互相补充,逐步提高,完全统一了认识”。任先生不因温先生是小辈,学术观点又与自己完全不同而固执己见。他认为温先生的说法有道理,主动放弃了自己的观点。
更难能可贵的是,当温先生完成《试为“成都”得名进一解》初稿时,任先生不仅帮助文稿的修改,还为其补充史料,使文章的阐说更加完善。他不仅将温先生的文章推荐给《社会科学研究》刊发,还专门为该文另写了《赞同〈试为“成都”得名进一解〉》,与温先生的文章同期发表。
在《赞同〈试为“成都”得名进一解〉》文中,任先生展现出的是在治学问题上的大家风范。他首先检讨自己在《成都》一文中的失误:
我前写《四川地名考释》合当是二千三百年来第二个解释成都名义的。论据只在《华阳国志·蜀志》广汉郡、新都县有“蜀以成都、广都、新都为三都,号名城”这一句话。把这句话结合蜀族从汶水蜀山逐步移进入成都平原,多次迁徙都邑的历史发展过程作出推断,以为他因为最后定都在此,遂未再迁,故曰成都。这一推断,是只用新、广、成和都字的华文含义造意,别无其他依据。不过比乐史之说较能符合于古代典籍和地理实际,还不敢自信是绝对正确的。
当时曾自疑的,是:蜀族并无文字;其人语言是否就与中原语言相同;用中原文字含义来解释蜀人自己制定的地名,是否适当?从前,我撰写《华阳国志图注》,对这问题就曾考虑了很久。去年作《四川地名考释》,又曾考虑过一次,总觉:蜀山氏曾与中原的黄帝轩辕氏结成儿女亲家;蜀地生长的颛顼、帝喾、大禹,都到中原作了皇帝;彭祖与苌弘也都是蜀人到中原作了殷周的大夫,从而相信蜀族与华族的语言是互通的,便再一次把成都名义肯定了。
学术交流,就是一个相互启发,共同提高的过程。任先生说,当他们初次接谈时,只谈到“成”字的问题。任先生回忆当时的感受,是不但新颖,而且十分正确。“成”,就是“高原来人”之义,是古羌族分支进入河谷盆地经营农业者的自称。所以陇西留下了“成纪”这样的古地名,四川也留下了“成都”这样的古地名。这些地名,都是周代以前就已有了的,不是秦汉才有的。所以用秦汉年代的文义来解释“成都”的取义,与用“三年成都”来作解释,是“以五十步笑百步”的错误。任先生说他当时就作了检讨。这就是大家的治学风范啊!
任先生在《赞同〈试为“成都”得名进一解〉》的文末说:
我虽两次都热烈拥护这样的新解,仍未免还小有所疑,疑在……这三种解释,只是我为了拥护温氏新说而作出否定自己旧说的检讨性自解,希得附于温氏之末,备研讨此问题者参考。
窃谓,学问之道,最忌“管窥”“株守”“固步自封”“毁所不见”。那样时代学术就会永远落后,终被淘汰。治学所贵,在能“集思广益”“擇善从之”“广纳众流”“盈科而进”。这样才能逐步提高,发展为登峰造极。
这确实是做学问的金玉良言啊!也是任先生学无止境的楷模引导,更是引发“成都”得名研究热潮的学术贡献。
三、任先生在“成都”得名研究中的误导
任先生研究“成都”之名的两文,引发了对“成都”之名来历和涵义的研究热潮,这不仅是对学术研究的贡献,更是对成都未来发展的贡献。至今,在有关“成都”的介绍和研究中,任先生研究“成都”之名的两文仍被不时提及、引用。
但是,当任先生撰写、发表这两文时,已近九十高龄,记忆力已经大不如前,这是人生的自然规律,没有人可以幸免。作为学术大家的任先生,显然是认识到自己的身体状况的,所以,他在《成都》一文的文末特别注明:
关于成都城的发展历史,此仅凭记忆所及考订一些有关地名的取义,供修史者参考。未暇翻检书史,详作考证。愿得抛砖引玉,征求不同意见,更作分别讨论,期于折衷允当。非敢自限于此也。
这是一位学术大家对自己所写文章的负责态度,值得肯定。可叹的是,许多对任先生文字的引用者,却“懒”得去翻检书史,核对古籍原文,造成引用任先生“仅凭记忆”写出的可能存在问题的文字,造成对读者的误导。这不是任先生的错误,错在使用者。
(一)乐史不是最早也不是唯一解释“成都”之名者
任先生在《赞同〈试为“成都”得名进一解〉》文中说:“只北宋初年乐史撰的《太平寰宇记》解释过成都二字的取义。他说:‘成都县,汉旧县也。以周太王从梁山止岐下,一年成邑,二年成都。因名之成都。”
其实,在历史上“解释过成都二字的取义”的不只是任先生所提到的《太平寰宇记》,还有差不多同时期的《太平御览》和稍晚一些的《方舆胜览》;进一步说,《太平寰宇记》也不是历史上最早对“成都”二字进行解释的典籍,而是稍早于《太平寰宇记》的《太平御览》。
《太平御览》虽然是宋代由李昉、李穆、徐铉等学者奉敕编纂的类书,但是,该书因为保存了宋代以前的大量文献资料,遂使它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宝贵遗产。在《太平御览》卷一百六十六《益州》条下有:“《史记》曰:‘周太王逾梁山,之岐山,一年成邑,二年成都,故有成都之名。”
《太平寰宇记》是古代中国地理总志,由北宋历史地理学家、文学家乐史编撰。它记载了宋初的疆域政区以及唐末、五代十国和宋初行政区划的变化。《太平寰宇记》卷七十二《益州》条下有:“成都县,汉旧县也,以周太王从梁山止岐下,一年成邑,二年成都,因名之成都。”
在与李昉、乐史同时代的许多书籍中,都记载有《太平御览》《太平寰宇记》两书编纂的起始时间:《太平御览》撰始于北宋太平兴国二年(公元977年)三月,成书于太平兴国八年(公元983年)十二月;《太平寰宇记》则成书于雍熙(公元984—987年)末至端拱(公元988—989年)初。这说明,《太平御览》至少比《太平寰宇记》早四年或者更多。[3]
南宋人祝穆是李昉、乐史两百多年以后的学者。他在《方舆胜览》的“成都府路”条中,又有“成都”得名“盖取《史记》所谓三年成都之义”的记载。
诚如任先生所说,乐史以及李昉、祝穆等宋人关于“成都”二字的“取义”推断,是有错误的,是靠不住的。
(二)《战国策》中没有“西控成都,沃野千里”之说
任先生在《赞同〈试为“成都”得名进一解〉》文中说:
成都这个地名,最先出现在《战国策·秦策》。原文为“西控成都,沃野千里”。后世因为蜀国都城就叫成都,便分别把苏秦所说这个“沃野千里”定为蜀国之地,而把“成都”二字定死为蜀国都城的专称了。……还使我回忆到苏秦说的“西控成都沃野千里”的“成都”,不是指的蜀国都城,而是指的蜀國的地面。
《战国策》是一部记载了战国初年至秦灭六国约240年间事的国别体史学著作,是研究战国历史的重要典籍。《战国策》中与成都或古蜀有关的,只有《秦策一》中的《苏秦始将连横说秦》《司马错与张仪争论于秦惠王前》两文。在这两文中,确实谈到了古蜀之地对欲统一天下的秦国的重要性,并且在《苏秦始将连横说秦》中也确实出现了“沃野千里”这四个字,但是,其中并没有“成都”二字,当然也就谈不上“西控成都”了。也就是说,在西汉司马迁撰写《史记》之前,古代典籍中没有出现过明确指“成都”的文献资料。
据考查,在《战国策》千年之后的明代典籍中,才出现有“西控成都”这几个字。例如《大明太祖高皇帝实录》卷之二十一就有:“己亥,夏主明昇遣使来聘。上因与语,使者辄自言:其国东有瞿塘三峡之阻,北有剑阁栈道之险,古人谓‘一夫守之,百人莫过,而西控成都,沃壤千里,财利富饶,实天府之国。”在《明太祖宝训》卷六、《明史纪事本末》卷十一“太祖平夏”中也有“西控成都”这样的字。[4]
(三)从古至今未发生过地名变更的不只是成都
任先生在《成都》文中说:
我国地名,从古至今没有发生过一次变更的只有一个,那就是成都。成都之所以独得具此特点,自必有它独特的原因。
地名研究源远流长。在中国古代典籍中,许多典籍都记载有大量地名,如班固的《汉书》,仅《地理志》就载有各类地名4000多处。对古代典籍所载地名和命名原由、名称演变进行说明,且从文化学与历史学的意义上予以分析,以及对典籍所载地名的读音、含义、位置、沿革给予阐述和研究,可以帮助后人了解该地名所存在时期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方面的信息。这是无须多言的。
中国有许多历史文化古城,著名者亦不少,成都是其中之一,被列入“中国十大古都”。不过,成都并不是唯一的“从古至今没有发生过一次变更”地名的城市。
《汉书·食货志下》有载:“遂于长安及五都立五均官,更名长安东西市令及洛阳、邯郸、临淄、宛、成都市长皆为五均司市师。”[5]即是说,早在汉代,成都就已经是当时全国在政治、经济、文化方面最有影响的“五都”之一了。值得研究的是,仅就这“五都”而言,洛阳、邯郸在先秦典籍中出现的频率就远远高于成都,它们也一直延至今天仍然“城名不变”,据此就可以证明成都并非“唯一”!此外,咸阳、长沙、广州、福州、荆州、扬州、益阳、即墨等地名,亦是“从古至今没有发生过一次变更”地名的城市。
(四)成都、广都、新都不是古蜀之“三都”
任先生在《赞同〈试为“成都”得名进一解〉》文中说:
《华阳国志·蜀志》广汉郡、新都县有“蜀以成都、广都、新都为三都,号名城”这一句话。把这句话结合蜀族从汶水蜀山逐步移进入成都平原,多次迁徙都邑的历史发展过程作出推断,以为他因为最后定都在此,遂未再迁,故曰成都。
《华阳国志》卷三是《蜀志》,其中的“广汉郡”属下有“新都县”,确实有这样的记载:“蜀以成都、新都、广都为三都,号名城。”但是,这条资料所说的“蜀”,是不是就一定是先秦时代的古蜀国呢?
必须明确,在《华阳国志》中,以“蜀”字作为区域或国家名称的,不仅有古蜀国,还有三国时期刘备的蜀汉国,以及秦汉时期的蜀郡。
在记载“三都,号名城”的“新都县”之后是“广汉县”,又记载有:“蜀时,彭羕有俊才。”彭羕,《三国志》有传,他是被刘备重用过的蜀汉官吏。那么,这里的“蜀”,可以肯定指的是三国时刘备的蜀汉国。
查《华阳国志》原文:“新都县。蜀以成都、广都、新都为三都,号名城。有金堂山。水通于巴。汉时五仓,名万安仓。有枣,鱼梁。多名士,有杨厚、董扶。又有四姓马、史、汝、郑者也。”[6]设于新都县的“万安仓”,是汉代最大的粮仓,足证该地的重要性。新都(今为成都市新都区)的“杨厚、董扶”以及“马、史、汝、郑”四姓,均为三国时期的文化名人。他们选择于此居住,说明新都在蜀汉国时期的重要地位。
所以,徐中舒教授明确指出:“《华阳国志》又说:‘蜀以成都广都新都为三都,号名城。此三都为名城,完全是秦汉以后的事。”[7]
任先生研究成都得名的两文,意义很重大,尤其是对成都未来的发展更是有突出贡献。只是这两文中确实存在错误,而这些错误,至今还在流传。例如,2017年,蒲江考古发现了一把战国时期的青铜矛,上面刻有“成都”二字。一时间,所有的新闻媒体都被这条新闻消息轰动了:
据中新社成都(2017年)2月17日电:(记者徐杨祎安源)记者17日从成都市蒲江县文体旅局获悉,该县盐井沟船棺墓群M32号墓近日出土一柄附着淤泥的青铜矛。经过清理,该柄青铜矛上刻有“成都”二字,……西汉時,刘向《战国策·秦策》云:“西控成都,沃野千里”,这是“成都”两字在文献中较早出现,……[2]
必须指出的是,中新社是中国非常权威的新闻媒体,而这条由权威媒体发布再传播于全国乃至世界的新闻,其中所说的“西汉时,刘向《战国策·秦策》云:‘西控成都,沃野千里,这是‘成都两字在文献中较早出现”云云,完全是失实的,因为《战国策》中并没有“西控成都,沃野千里”这样的字词!
这些错误的出现,源头虽然是任先生研究成都得名的两文,但我们不应该苛责老人。责任在于发表该文的编辑,没有尽到编辑的责任去认真核对就轻率发表;后来的读者尤其是引用者,自是相信老专家,相信编辑部和杂志,以致以讹传讹,造成今天的严重误读。
注释:
[1]郭沫若:《科学的春天——1978年在全国科学大会闭幕式上的讲话》,《人民日报》1978年4月1日。
[2]任乃强:《成都》,《社会科学研究》1980年第2期;《赞同〈试为“成都”得名进一解〉》,《社会科学研究》1981年第1期。以下引任先生文,均来源于此二文。
[3]参见李殿元:《论“成都”得名研究中的资料误导》,《文史杂志》2021年第4期。
[4]参见李殿元:《论蒲江“成都矛”解读中的几个问题》,《文史杂志》2017年第3期。
[5](汉)班固:《汉书》卷二十四《食货志下》,中华书局1999年版,第986页。
[6]任乃强:《华阳国志校补图注》卷三《蜀志》,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第166页。
[7]徐中舒:《成都市古代自由都市说》,载《成都文物》1983年第1期。
作者:四川师范大学巴蜀文化研究中心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