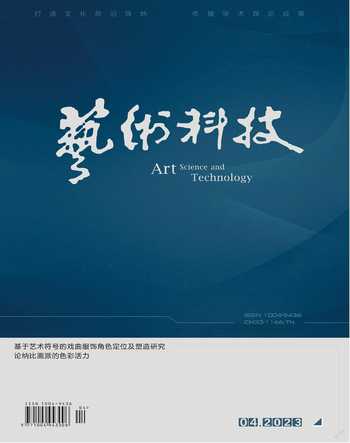大运河文化视域下扬州评话的当代价值与传承研究
2023-06-22何勰何卿澜
何勰 何卿澜
摘要:扬州自古是重要交通枢纽、商业城市,也是运河城市、南北文化传播的必经之地,三教九流混杂,方言、文学、艺术交融演变,塑造了扬州文化宽容野逸、推陈出新的特征。当地的文学艺术彰显出雅俗文野、因袭独创的底色,说唱文学的发展可谓如鱼得水,以扬州评话为代表的通俗文艺至今不衰。扬州评话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受盐业盐商、漕运漕帮影响,在享乐风气、江湖武侠风气中发展,与大运河文化相伴而生。基于此,文章在大运河文化视域下研究扬州评话的当代价值。扬州评话中蕴含极为丰富的当代价值,通过展现扬州的地域风情,得以弘扬民风民俗,发挥了优秀传统文化凝聚人心、教化群众、淳化民风的作用。在扬州评话作品中,多样的艺术性与深刻的社会性得到统一,传奇色彩与写实精神结合,为当代大众提供了一种雅俗共赏的审美趣味,并以生生不息的适应力和创造力,丰富充盈了大众的精神世界。它与大运河文化的深度融合形成共赢模式,以文化遗产推动“非遗”的保护与传承,赓续了运河文脉。当下,面对传承困境,可在文本上讲究多类并举,为传统书目注入新的内容元素,在表演上设法创新,重视书场建设,改进曲艺语言;还可借助新媒体为传统赋能,丰富其传播方式,推动受众群体年轻化;同时依托大运河文化打造“非遗”产业亮点,将扬州评话打造成具有民族特色的国家品牌,展现其经久不衰的文化魅力。
关键词:扬州评话;大运河文化;“非遗”;传承
中圖分类号:J82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9436(2023)04-00-03
历史文化名城扬州受到大运河的滋养,在漫长的岁月中积淀出独特又丰润的文化品格,孕育了极具地域特色的文学艺术,成为运河文脉中的重要分支。其中,扬州评话又是扬州文化宝库中一颗璀璨夺目的明珠。扬州评话作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蕴含着丰富的思想内涵和人文精神,价值与意义历久弥新,对其进行传承与创新势在必行。
1 文化氛围
1.1 盐业盐商与享乐风气
扬州自古以盐业发达、盐商豪奢著称。不同于京师的官员文化与苏锡的文人文化,扬州文化在盐业繁荣时期更偏向于商人文化,这是因为淮扬盐商阶层所引领的商业文化精神对扬州的生活风气与文化底色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为说书、唱戏等娱乐活动提供了坚实的经济社会基础。
盐业税收不仅是扬州经济的命脉,对国家财政的稳定也有举足轻重的意义。盐商的富有程度、社会地位、交往关系不容小觑,大盐商受到封赏并不鲜见,他们的顶戴、头衔乃至黄马褂,虽是虚衔,但级别甚至高于地方官员。不同于寻常商人在思想学问方面的短板,扬州盐商的文化素养很高,并有意接受文化熏陶。据嘉庆《两淮盐法志》记载,淮扬盐商子弟中进士和举人者二百人以上,商仕集于一身成为淮扬特色。一方面,他们迎合官府和文人阶层,并兴办书院,例如盐商创办的扬州安定书院和梅花书院走出了段玉裁、王念孙、姚鼐、汪中、赵翼等著名文人;另一方面,他们展现出个人的文化选择和审美情趣,推崇通俗文艺,促进了通俗文学的发展,如著名盐商江春蓄养花部、雅部两个戏曲班子,这对戏曲种类的相互交流显然有直接影响[1]22-24。
1.2 漕运漕帮与江湖武侠
江淮自古多盐枭武装贩私,剽悍勇猛,善于械斗。晚清周伯义纪实笔记《扬州梦》中提到官府招安某些骁勇的盐枭,封赏官职,重用并使之缉捕同类,酿出武林正邪之争,漕帮与盐枭合流趋势不断加强。而由大运河漕运而起的漕帮强调内部团结,一致对外,强调忠孝、侠义,严禁奸佞邪恶,这无疑影响了江湖武侠小说在运河沿线一带的繁荣。
清代乾隆以后,扬州评话形成“武说”派别,如邓光斗“跳打《水浒》”以武打动作描绘见长,甚至模仿武技表演,引起听众的兴味。同时,《三侠五义》等武侠题材书目在扬州也找到了适宜的土壤,王少堂先生在青年时期就曾想放弃家传《水浒传》而改说《三侠五义》,可见江湖武侠在运河流域的流行[1]258-259。武侠小说之所以有如此强的生命力,与它同说唱艺术血肉相连、相依相承的联系是分不开的。在说唱艺术中,口头演说的评话粗犷明快,擅长大书、短打故事,是侠义题材最合适的载体。可以说,江湖武侠的盛行推动了说唱文学的发展,对于说唱艺术新格局的形成功不可没[1]262。
2 当代价值
2.1 展现地域风情,弘扬民风民俗
真实的市井生活、市井语言,尤其是下层市民的生活环境、日用起居、邻里关系,在扬州评话中得到全面展示。评话《皮五辣子》十分逼真地描绘了东城脚贫民区各行各业的生活状态,如卖菜小贩倪四一家三口的每日开支都被详尽描述。丰富的民俗文化反映了中华民族独特的精神内涵和人文传统,是中华民族文化之本。因此,发掘、传承扬州评话中民俗文化的积极因素,对弘扬中华传统文化的优秀精神内涵有重要作用。例如《皮五辣子》中某寺庙施粥放赈,但粥分三等,多借以敛财,层层克剥,施放到贫民手中的已是稀粥汤,表达了对下层贫民血泪的同情、不平,以及对腊八施粥所代表的本原精神——慈悲喜舍、广种善根的呼唤[2]。在今天,扬州的大明寺、文峰寺在腊八节免费向群众施粥已成为传统,民风民俗持久、广泛地滋养着一方人民。
2.2 提升大众审美,满足精神需求
扬州评话以现实精神为审美选择,其主要倾向表现为:疏离神怪妖异,贴近现实生活,诠释市井风情,玩味人间百态,冷淡脂粉情愁,倾向粗豪阳刚,嘲讽酸腐儒弱,推崇尚武之风[1]236。在扬州评话作品中,多样的艺术性与深刻的社会性得到统一,传奇色彩与写实精神有机结合,为当代大众提供了一种雅俗共赏的审美趣味。
以扬州评话的重要篇目《武松》为例,它在原作的基础上增加了新人物、新情节,这种增加大有深意,使人物性格的复杂性更为突出,将渲染世态人情、分析做人处世之得失放在首位。其中,武松与鲁智深的关系被改为师徒关系,在智取二龙山的情节中有意营造二人的误会与冲突,作者甚至详细描绘二人打斗的场面:“鲁大师把棍子摆在他刀上,‘嘻嘻嘻嘻,那个笑法子,不气了。笑着,棍头在刀上揉着,两下子一揉,武二爷周身汗被他揉出来了。”说书人不断变换角度,在评议中着重强调为人的道理,即绝不可骄傲自大,须保持谦逊。这一个英雄传奇故事将对社会人生哲理的思考融入真实可信的故事中,而说书人结合情节展开了生动的议论,让听众在娱乐当中获得了人生经验。这种方式不令人厌烦,反而极有说服力,富有教益,耐人寻味[1]239-240。因此,发掘大运河文化视域下扬州评话的审美价值,既能探究其在具体时期的特定功用,又可将其与当代价值观相结合,充分发挥其现世作用,教化人心,匡正风气。
2.3 保护“非遗”,赓续运河文脉
2006年,扬州评话被批准为首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2014年,中国大运河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浪潮下,扬州评话与大运河文化的深度融合将形成共赢模式,以文化遗产推动“非遗”的保护与传承,这有利于对大运河文化进行更活态、更全面、更必要、更有针对性的保护,使运河文脉璀璨闪耀、流淌不息。
大运河文化既指包括物质文化、非物质文化、制度文化在内的运河的本体文化,又指受运河影响在运河区域产生的文化现象,如哲学、史学、文学等上层文化和民间文学、风俗等市井文化。扬州评话是大运河沿线地区形成、发展的表演艺术,毫无疑问与大运河文化有所合流。立足于当下文化市场的需求,研究扬州评话中的文化符号与现代社会的文明价值观之间的内在联系,能够搭建起传统与现代在精神层面的关联,拓宽当代大运河文化研究的范围和思路,用运河边成长起来的说唱文学去创作新的运河文学艺术,重新编演新时期的运河故事。利用中国大运河这一世界级的文化遗产,活化运河历史文化,以扬州评话为代表的表演艺术最容易架起与当下观众的桥梁,输出文化产品,潜移默化地传播运河优秀文化,增强国民的文化自信。
3 传承发展
3.1 换“脑子”:在书房里和书台上创新
扬州评话在泛娱乐化、信息化浪潮中虽然不可避免地受到了一定的冲击,且面临着缺少人才、受众面窄、行业不景气等困境,但并不是不見出路,相反,只要走可持续的传承与发展之路,扬州评话的未来必定有永葆青春的活力与博大广阔的空间。
在文本上,要讲究多类并举,并为传统书目注入新的内容元素。首先,应逐步恢复说书人对书目的多样化选择。扬州评话原有数十种书目,如《西汉》《三国》《隋唐》《水浒》等,但目前常说的只有固定的几种,剥夺了观众接触多元题材的机会。其次,应建立多层次的书目系统,突破书目创作的瓶颈。保持长篇书目统领书台的传统,同时创作与时代脉搏、现实生活贴近的新书目,有意识地从当代人熟悉的生活素材中汲取灵感素材,创造以传统曲艺为形式、以当代人喜闻乐见的生活内容为核心的新曲目,以流行文化的外观阐述传统文化精髓,与受众同频共振[3]。
在表演上,要求重视书场建设,改进曲艺语言。一方面,扬州评话是看得见、摸得着的口头艺术,书场是其阵地,也是最合适的表演舞台。必须加强实体书场建设是,社区书场、校园书场的建设是赢得听众的良好举措,这样既传播了传统艺术,又培养了新一代听众,解决了听众断层的问题。同时,还应新建几处有规模、有层次的专业书场,将其打造成扬州的文旅名片,使扬州评话有安身之处[4]。另一方面,应保持扬州评话“接地气”的传统,坚持曲艺语言来自民间[5]。扬州评话语言以通俗易懂、鲜明生动为本色,面对新时期的观众,说书艺人不应局限于“套路”“程式”,而应讲求艺术的控制力,语言简练而深刻,力避传统评话中的冗长、不必要的铺陈,积极借鉴其他艺术门类的表现手法[6]。
3.2 借“梯子”:新媒体为传统赋能
随着新媒体的大力发展,曲艺传承活动与新媒体技术的深度融合能够为传统曲艺创新传承赋能。扬州评话利用互联网丰富其传播方式,能够有效促进自身的传承与创新,推动受众群体向年轻化方向拓展。
除却实体书场的拓展,创建新型“书场”也是培养新式听众的良方。通过电台电视、平台直播、短视频APP等途径,以耳目一新的内容、生动活泼的手段,吸引更多人的兴趣,让更多人从认识扬州评话,到感受到扬州评话的魅力,再到自觉自发传播弘扬传统曲艺文化。另外,借力现代传播渠道与高新技术,网络直播还可以使曲艺艺人与观众进行直接互动,在线为观众答疑,也能清扫年轻群体对传统曲艺的盲区,以提高大众对曲艺文化的关注度,扩大其生活影响力,突破形式拘囿,拓宽戏曲表演的变现营收途径。著名扬州评话艺人马伟在此领域已有所突破,他的抖音账号“小马抖趣”反响热烈,他认为,“观众在哪里,演员就要在哪里,或者说扬州曲艺的年轻观众在哪里,就要去哪里寻找他们”。
3.3 创牌子:打造民族特色国家品牌
扬州评话作为本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存在一定的地域限制性及空间狭窄性,要焕发活力就必须打造具有民族特色的国家品牌。只有通过对传统文化的汲取、融合、创新,将商业元素与文化元素有机融合,才能更好地实现真正意义上的保护传承条件下的文化复兴。
充分利用好各级文化馆及“非遗”基地,有利于扩大扬州评话的展示空间。应推进建立活态体验区、大师工作室、博物馆等区域,发挥扬州评话传承人和扬州市曲艺研究所的带头效应,建设人才孵育基地,进一步实施“师带徒”等政策。同时,应与高校、科研院所等单位合作,政府则应予以财力和人力的支持,扶持、鼓励新的人才、新的艺术流派出现。
此外,还应依托大运河文化打造“非遗”产业亮点,激发产业创新变革。抢抓大运河文化带建设机遇,大力开发运河“非遗”资源,在旅游景区中融入扬州评话等具有运河特色的“非遗”元素,使扬州评话成为中国大运河“非遗”保护传承的新名片。同时,应联动大运河沿线城市,策划举办中国大运河曲艺交流展演,形成集聚效应,使扬州评话走向全国、走向世界,实现“运河戏曲重镇”的复兴繁荣[7]。
4 结语
传统曲艺的传承与发展,与每一个中华儿女息息相关。扬州评话拥有不可估量的宝贵价值,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也是民族未来发展不可缺失的文化财富。新时期,在国家与党的号召下,必须活化与振兴传统曲艺,使这项古老的艺术品种有更长足的发展,以展现其经久不衰的艺术生命。
参考文献:
[1] 董国炎.扬州评话发展史[M].南京: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2019:22-24,236,239-240,258-259,262.
[2] 陈午楼.扬州评话与民俗学:兼谈民族审美心理[J].扬州师院学报(社会科学版),1985(4):95-102.
[3] 殷健.新时代传统曲艺传承创新路径研究:以扬州评话为例[J].文化创新比较研究,2020(21):107-109.
[4] 肖淑芬,杨肖.扬州评话发展史及海外影响[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6:428.
[5] 姜庆玲.扬州曲艺的传统资源与现代发展[J].曲艺,2011(3):19-21.
[6] 徐德明,季培均.怎样传承,如何创新?:扬州评话的前世今生[J].曲艺,2014,(12):40-43.
[7] 姜师立.中国大运河文化[M].北京:中国建材工业出版社,2019:295-297.
作者简介:何勰(2002—),女,江苏无锡人,本科在读,研究方向:汉语言文学(师范)。
何卿澜(2001—),女,江苏苏州人,本科在读,研究方向:汉语言文学(师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