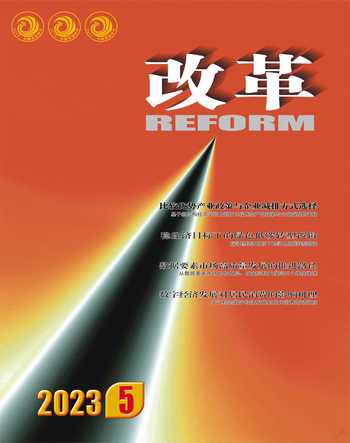比较优势产业政策与企业减排:基于新结构经济学视角
2023-06-13林毅夫蔡嘉瑶夏俊杰
林毅夫 蔡嘉瑶 夏俊杰
摘 要:加强产业政策与环保规制政策的协同,有助于实现经济社会发展与生态环境保护目标共赢。在面临环保规制压力时,企业有两类减排方式选择,一类减排方式会导致牺牲经济绩效的冲突性困境,另一类减排方式则可实现环保与经济绩效的共赢。后一类减排方式是高质量发展的有效实现路径,但激励企业选择此类减排方式的条件尚缺乏研究。产业发展方式是一个重要因素,在符合比较优势的产业发展战略下,产业中的企业环保绩效显著提升,企业污染物排放强度降低,且通过环保与经济绩效共赢的减排方式实现。内在机制在于,符合比较优势产业中的企业更具有自生能力,通过清洁生产实现减排的能力和意愿更强,具体包括改进绿色技术、增加环保设备设施投入等措施,此类减排机制有助于实现环保与经济绩效共赢,而并非以牺牲经济绩效为代价。深入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除直接运用环保政策工具对污染企业进行约束外,还可协同使用产业政策工具,采用遵循比较优势的产业政策,提升企业满足环保合规性的能力、意愿和环保绩效表现,实现经济社会发展与生态环境保护协同目标的达成。
关键词:比较优势;产业政策;环保绩效;企业减排
中图分类号:F12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7543(2023)05-0001-17
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我国发展面临的内外部环境深刻变化,能源资源约束趋紧,应对气候变化任务艰巨,努力实现经济社会发展与生态环境保护协同共进是当前的紧迫任务。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内涵之一,对新时代中国生态文明建设的战略任务作出战略部署,强调要统筹产业结构调整、污染治理、生态保护、应对气候变化,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西方传统工业化在创造巨大物质财富的同时,也造成了自然资源的过度攫取和较为严重的环境污染,经济发展和环境保护常被认为无法兼顾[1]。在我国早期工业化进程中,由于对环保重视力度不够,采取了高耗能、高污染的粗放型经济增长模式,以牺牲环境为代价换取经济发展。新时代新征程下,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这组矛盾呈现如下新特征:
第一,环保问题得到充分重视,生态环境质量持续改善。党的十八大以来,党和国家以前所未有的力度抓生态文明建设,生态文明建设被摆在“五位一体”总体布局的高度来论述,党的二十大报告更是将“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纳入“中国式现代化”的内涵之一。在具体举措上,环境保护税、排污权交易试点、节能减排补贴等市场激励型环境规制工具[2-3],以及减排总量控制、排放许可证、环保技术标准等命令控制型环境规制工具的广泛应用[4-6],对企业高排污高能耗行为形成有效约束。近十年,我国生态环境保护取得历史性成就,以年均3%的能源消费增速支撑了年均6%以上的经济增长,二氧化碳排放强度下降了35%,同时也成为全球大气质量改善速度最快的国家。我国生态文明建设取得的成就表明,生态环境保护和经济发展是能够辩证统一、相辅相成的。
第二,面临日益趋严的环保目标,执行中出现牺牲经济发展的冲突性困境。作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全球第一制造业大国、全球第一大货物贸易出口国,我国长期承接了发达国家等商品消费国的排污压力,承担了减污降碳的巨大责任,并面向世界作出“双碳”目标的庄严承诺。然而,环保目标执行中的经济成本也是巨大的。政府支出方面,2012—2021年,全国财政节能环保支出从2 963.46亿元增长到6 305.37亿元,年均增长8.8%,以支持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系列举措的实施。近年来,一系列环保政策措施相继出台,思路愈发清晰,目标愈发明确,要求愈发具体。研究发现,部分企业为满足环保合规性,其应对环保规制中会出现牺牲经济效益的窘境,如为减少污染产生而采用低生产率技术或减产的做法,造成工业产值损失[5]。与此同时,“拉闸限电”“碳冲锋”等事件对国民经济健康发展造成的波动不容忽视。
在中国式现代化目标实现进程中,要协调产业结构调整与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寻求环保与经济绩效的双赢结果,就要从微观企业层面了解制造业主体在面临环保压力下的减排行为选择逻辑。企业选择不同减排方式所传导的经济绩效截然不同:第一类指向环保与经济绩效共赢的策略,如绿色技术创新(环境友好型技术、节能技术、可再生能源技术等)和环保设施投入等减排方式。根据“波特假说”[7],企业竞争优势源于低成本和差異化,尽管绿色技术创新和环保投入在短期内会增加企业生产成本负担,但在长期可倒逼企业提升产品质量和绿色全要素生产率[8-9],会随着居民对环保支付意愿的提升而更具市场竞争力,有利于企业维持优势市场地位[10]。中国经验方面,关于排污权交易试点、环保目标责任制、环境保护税等研究都支持“波特效应”的存在[6,11]。而另一类减排方式则导向牺牲经济绩效的冲突性困境,一是企业通过减产停工以减少污染产生来达到环保合规性,但同时会造成产值缩减、就业恶化等经济代价,甚至退出市场[4-5]。二是企业搬迁至环境规制更为宽松的地区[12-14],以重新布局生产,这是环保压力下一种策略性的、牺牲资源配置效率的企业选址变化。研究发现,尤其当我国地区间环境规制强度差异不断扩大时,污染企业的搬迁发生概率越大[13]。
综上可见,若要构筑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之间的共赢关系,就要在微观层面了解企业在何种情形下采取第一类清洁生产的减排方式,而非第二类以牺牲经济发展为代价来满足环保合规性。第一类方式也是当前政策导向大力支持的减排方式。2021年10月,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等部门联合发布了《“十四五”全国清洁生产推行方案》,要求充分发挥清洁生产在深入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和推动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目标中的重要作用。现有文献对于企业不同减排方式选择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对这种差异性的现象描述,如环境规制政策工具类型与强度[15]、地区发达程度、企业性质与规模等异质性[11],其背后原因尚待进一步挖掘。
本文从产业发展战略的视角出发,尝试打开企业在环保压力下减排行为选择差异的“黑箱”。新结构经济学的大量研究表明,一个地区的产业发展是否符合比较优势,与这个地区企业的自生能力①紧密相关[16],这直接影响到企业满足环保合规性的意愿和能力,从而能够为企业为何作出差异化的减排选择提供一种解释。具体来说,若企业所在产业的要素结构与其所在地区的要素禀赋结构越匹配,该行业发展越具有比较优势,行业中的企业在当地生产时越能够有效降低要素投入成本,越有能力选择清洁生产的减排方式,进行清洁技术创新或进行环保设施投入。而违背比较优势产业中的企业往往缺乏自生能力,依靠政府的保护补贴维持生存,没有多余财力更新设备和技术,若要满足环保合规性,往往只能采用减产停产等策略应对,这种方式不仅会损害企业经济绩效,而且实现的减排是可逆的,未能从本质上实现清洁化生产,反而导致经济发展和环境保护目标出现冲突。
一、制度背景与理论机制
这里结合相关制度背景,阐明为何产业发展应该遵循比较优势的原则,以及为何现实中一些地方仍存在不少偏离比较优势的产业。在此基础上,再将发展遵循比较优势的产业政策与企业减排之间的联系机制搭建起来。
(一)比较优势与产业发展
支撑国家宏观经济增长的微观基础是技术进步、要素积累和产业升级。推动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要将劳动力、资本等生产要素配置到附加值更高的技术和产业中,这样才能不断提高经济发展水平和居民人均收入[17]。西方话语体系下的国家现代化,往往把西方发达国家的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作为现代化标尺,把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间的差异视为应当消除的扭曲。这一底层逻辑忽视了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的内生结构差异,这种差异既包括禀赋结构的差异性,又包括禀赋结构所内生的产业、技术、硬的基础设施和软的制度安排的结构差异性。新结构经济学认为,经济发展是一个资源随着要素积累、比较优势动态变化,不断从现有技术和产业配置到效率更高的技术和附加值更高的产业结构变迁过程[18]。如果一个国家的产业在结构变迁中遵循自身的比较优势,那么它就可以最低的生产要素成本生产具有比较优势的产品和提供服务,并有机会形成竞争优势,出口至国际市场,这个经济体将达到最有竞争力的状态,可以创造最大的剩余,投资会有最大的回报,资本要素会以最快的速度积累,经济体的禀赋结构和产业结构将以可能的最快速度升级。反之,如果违反比较优势,企业在开放竞争的市场中就没有自生能力,只能依靠政府长期保护补贴才能生存,产业升级就会面临失败[19-21]。
(二)有为政府与发展比较优势产业
纵观人类历史,只有韩国等少数经济体跨越中等收入陷阱成为高收入经济体,其产业发展均按照比较优势规律进行产业升级和要素积累[22]。韩国20世纪60年代开始出口服装、假发等劳动力密集型产品。当资本逐渐积累后,便向汽车、电子等资本更为密集的产业升级,主要产业部门时刻与该国比较优势保持一致。中国改革开放后的经济增长奇迹,同样也遵循按照比较优势发展产业这一原则。然而,这个过程若单纯依靠市场,有时很难自发演化,需要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的共同作用,有为政府可通过产业政策帮助企业进入具有比较优势的产业[23]。
第一,地区发展特定产业时,尽管要素生产成本低,但若软硬基础设施差、交易费用高,这些产业的潜在比较优势也无法转化为真正的比较优势,获得在国内外市场的竞争优势。这就需要有为政府来改善和支持硬的基础设施(如能源、交通道路等)和软的制度安排(如金融服务、法制环境等),这些单纯依靠企业自身难以克服[24]。第二,经济体的要素禀赋是随着积累动态变化的,相应的比较优势产业也会不断转型升级,在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的过程中,必须要有“第一个吃螃蟹的企业家”,敢于投入效率更高的技术和附加值更大的产业中,并且先行者的成败会给后来者提供有用的信息。这就需要有为政府支持新的、能动员更多资本、有效分散风险的金融制度安排和硬基础设施与其匹配,对先行者提供外部性补偿[25]。第三,需要有为政府协调基础科研公共品的投入。美国世界领先的航天、信息、医药等产业,大量创新成果都建立在政府资助的相关基础科研成果之上[26-27]。16—17世纪英国追赶荷兰,19世纪中叶以后美国、德国、法国追赶英国,到“二战”后的“东亚奇迹”,这些经济体在追赶过程中都曾采用关税保护、补贴等产业政策来扶持国内幼稚产业的发展,才实现产业升级和经济增长[28]。
(三)地方仍存在偏离比较优势产业的现象
就我国区域经济发展的状况而言,仍存在着一些地方产业发展偏离比较优势的现象[29-30]。理论上经济发展中存在三类产业:具有潜在比较优势的产业、远离比较优势的产业和失去比较优势的产业。对于第一类,如有为政府能够提供基础设施投资、降低交易费用、激励先驱者,潜在比较优势就会变成真正的比较优势,企业就会自发进入这类产业中。对于后两类,理论上自发的市场企业不会进入这些偏离比较优势、没有自生能力的产业中,但现实中仍存在不少此类情形,主要有如下原因:第一,有的产业发展虽然违背比较优势,但关乎国防安全和国家发展战略需要,如战略性新兴产业和国防安全产业,以及对其他产业产生正的外部性影响的上游行业。第二,随着要素的积累和产业变迁的动态调整,企业投资试错的结果还没有调整至新的具有比较优势的行业。过去符合比较优势的行业,也可能会随着要素积累而失掉比较优势。第三,地方政府的赶超冲动[31]。以发达国家新产业新技术作为参照系,发展中国家地方政府很容易忽略自身稟赋而纷纷投资于这类产业,这个过程中就很容易产生对比较优势的偏离。第四,历史原因导致的路径依赖。比如我国在重工业赶超时期,利用行政手段配置资源,一些重工业产业在落地过程中违背了当地比较优势[32-33]。后几类原因造成的偏离比较优势产业发展结果,都可通过政府有为之手的作用予以解决。
(四)比较优势产业和企业减排
在面临外部环保规制压力时,企业可采用各种不同的减排方式(如绿色创新、优化能耗、停产减产、企业搬迁等)予以应对。从环保绩效来看,这些方式都能实现减排目标。但若将经济绩效纳入考量则大相径庭。一类指向环保与经济绩效共赢的策略,如绿色技术创新、环保设施投入等减排方式;另一类减排方式则导向牺牲经济绩效的冲突性困境,如企业减产停工、搬迁,甚至退出市场。然而,现有文献对于企业不同减排方式选择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对这种差异性的现象描述,尚未对背后原因作进一步挖掘。如从环保政策类型角度出发,研究者认为市场型环境规制赏罚分明,可能更容易诱发企业绿色创新的决策,而命令型环境规制下更容易产生激励不足[15]。企业异质性方面,研究者认为非国有企业、发达地区企业、大型企业以及高工业化水平城市企业中“波特效应”更容易产生[11]。从企业能力的角度出发,研究者观察到环境管制可能导致企业在保持原有生产规模条件下增加技术创新投资的正向效应、与缩减生产规模的负向影响,前者正向效应往往在高能力企业中成立,低能力企业往往选择后者,缩减生产规模甚至退出市场。然而,学者们尚未对企业能力差异的来源作进一步的分析[34]。
企业所在产业是否符合当地要素禀赋决定的比较优势,与其自生能力密切相关。当企业所在产业的资本密集度与其所在地区的要素禀赋结构越接近,企业的劳动生产率、利润水平、全要素生产率均显著更高[35]。因为该产业在当地发展越具有比较优势,要素投入成本越低,就越有能力进行技术创新。反之,如果目标产业的要素密集度偏离经济体禀赋结构,就要过多使用稀缺要素,导致生产成本过高,使企业缺乏自生能力[36]、研发创新激励也更低[18]。现有研究大量探讨了比较优势产业发展战略与一系列经济绩效表现之间的因果关联,如经济增长[37]、产业升级、技术进步[18]、国企改革[38]、收入分配[39]等。然而,关于比较优势产业发展战略与环境污染之间关系的研究相对较少,且集中在宏观层面。总的来说,现有研究发现了违背比较优势发展对环境治理的负面效果,但尚未对微观机制进行详细讨论。跨国经验上,研究者发现若一国采用违背比较优势的重工业优先发展的赶超战略,会导致经济体内的微观企业缺乏自生能力,需要更多政府补贴扶持企业,这会扭曲市场的最优资源配置并造成能源使用效率降低[40]。省级层面上,研究者发现一个地区的企业缺乏自生能力的比例越大,该地区环境污染将越严重。机制在于,企业缺乏自生能力,容易引发该地区环境治理投入水平不足、环境约束软化并抑制技术进步[41]。
本文深入微观企业层面,研究产业发展战略如何影响环保绩效,以及企业减排方式的选择问题。关于比较优势产业发展战略,现有文献的研究集中于经济绩效,本文在环保绩效上作出有益补充,不仅在微观层面探讨了企业的不同减排应对方式选择,而且考虑了不同减排策略与经济绩效之间的关联。在环境经济学这支文献上,已有研究从环境规制政策出发,研究不同政策工具的减排效应是否有效,得到的结论不尽相同,且不同的减排方式下达成的环保绩效强弱、对生产行为的影响程度呈现差异。大多数文献停留在对这种差异性的现象描述,尚未对不同减排方式选择的内在原因作进一步挖掘。本文考量到环境规制工具和产业政策工具之间的协同关系,环境规制政策对企业形成外在减排目标约束,而产业发展战略则影响企业满足环保合规性的内在意愿和能力。遵循或违背比较优势产业发展战略下的企业,其减排方式选择会呈现显著不同,能够为我国日益趋严的环保政策下生产活动中企业面临的经济与环保目标冲突性困境提供一种解释,进而在宏观层面从产业发展政策和环境规制政策协同的角度,为实现环境保护和经济发展共赢提供思路。
二、数据来源、基础模型与变量说明
(一)数据来源
研究开展主要涉及三个数据集: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中国工业企业污染数据库、中国城市统计年鉴数据。中国工业企业污染数据库提供各种污染物的企业级排放信息,内容包括企业生产、污染排放、污染治理等信息,目前该数据在环境经济研究方面得到了广泛应用[5]。依据企业身份信息所形成的唯一识别码,本文将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与中国工业企业污染数据库匹配,形成满足本文实证研究所需要的面板数据。最终将研究年份确定为1998—2012年,研究年份的选择主要基于以下考虑:一方面,该时期我国的环境污染问题逐渐得到关注与重视,如“科学发展观”的提出就在这一时期。另一方面,这一时期内我国的工业化发展迅速,尤其加入WTO之后,我国逐渐融入全球产业链分工,作为重要污染来源的第二产业比重迅速增长并达到峰值。此外,本文将工业企业与工业企业污染数据匹配,以重污染工业企业作为样本的合理性在于:我国工业污染源占比较大。根据2020年生态环境部、国家统计局、农业农村部共同发布的《第二次全国污染源普查公报》,2017年底全国各类污染源总量中69%左右来源于工业污染源。最终,匹配后合计551 521个观测样本,样本的行业分布排在前五位的是非金属矿物制品业、化学原料及化学制品制造业、纺织业、造纸及纸制品业、农副食品加工业。
(二)基础模型
本文核心问题是考察产业发展是否遵循比较优势对企业环保绩效的影响。在实证分析上,构建城市—产业层面的产业发展与比较优势是否一致的指标Congruence,基于企业所在行业要素投入结构与所在城市要素禀赋结构的匹配程度构建,该指标越大,则该产业越符合比较优势。实证部分回归模型中的被解释变量是企业单位产值的污染物排放,核心解释变量是产业发展与比较优势是否一致的指标。基础模型设定如公式(1)所示:
Pollutionisct=α·Congruencesct+βXisct+γct+ηst+εisct(1)
其中,i代表企业,s代表行业,c代表企业所在城市,t代表年份。被解释变量Pollutionisct表示企业i在t年的单位产值污染物排放强度。Congruencesct代表企业所在产业符合所在城市禀赋比较优势的程度。Pollutionisct具體分为水污染和大气污染两个方面的指标:企业单位产值的化学需氧量(COD)排放,是水污染方面的代表性排放指标;企业单位产值的二氧化硫(SO2)排放,是大气污染方面的代表性排放指标。Xisct代表企业层面控制变量,包括企业年龄、所有者属性;γct和ηst分别代表城市时间固定效应与产业时间固定效应;εisct为残差项。
(三)核心指标构造
1.产业发展的比较优势一致性
Congruencesct=-|ln(■/■)-ln(■/■)|(2)
本文构建关于产业发展的比较优势一致性指标Congruencesct,如公式(2)所示[35]。Congruencesct越大,代表企业所在行业要素投入结构与所在城市要素禀赋结构越接近,企业所在产业越符合当地的要素禀赋对应的比较优势。其中,s代表企业所在行业,t代表年份,c代表企业所在城市。■是当地的固定资本存量,■是当地的总就业人数,■代表当地的要素禀赋结构,即当地的资本的相对丰裕程度,■是全国的资本相对丰裕程度。■是s行业当年在全国的平均资本密集度,代表这个行业的要素投入技术特性。此外,为便于解读回归结果,对产业发展的比较优势一致性指标Congruencesct进行了标准化处理。
关于本文构建的产业发展的比较优势一致性指标,有两方面需要说明:一是相较于过往研究基于国别层面构建的该指标[35],本文拓展到了“城市—行业—年份”维度。我国不同城市的要素禀赋、产业结构呈现较大差异,地方政府在引导地区产业升级中也面临不同的策略,因而关于地区层面的产业发展与比较优势是否一致的研究不可或缺。二是指标中对于企业所在行业资本密集度和对于地区资本丰裕程度的衡量都采用的是在全国的相对水平,这能更好地刻画地方产业发展特征。如广东省佛山市既有家电产业集群又有纺织产业集群,家电产业本身属于资本密集度较高的产业,而纺织产业本身虽然资本密集度不高,但在佛山市生产的纺织产品或生产环节相对于纺织产业在全国的平均水平而言是更加资本密集的,这二者可能都是与当地要素禀赋结构相匹配、符合比较优势发展的产业,能够在本文构造的比较优势指标中得以体现。
2.主要被解释变量
主要被解释变量包括:企业单位产值的COD排放,是水污染方面的代表性排放指标;企业单位产值的SO2排放,是大气污染方面的代表性排放指标。这两项指标是水污染和大气污染中最主要的标志性污染物,数值越大表示污染排放越严重,数值越小表示环保绩效越好。这两项指标也是“十一五”规划后被明确与地方政府考核问责绑定的量化减排指标,通过层层分解下达至各省市级地方政府,一直沿用至今。以这两项指标对企业减排绩效进行测度,具有合理性与代表性。
(四)变量说明及描述性统计
指标说明和描述性统计见表1,样本企业成立年限平均约为14年,企业单位产值的COD排放量平均值为30.03千克/万元,SO2排放量平均值为48.95千克/万元。样本中约13.10%的企业为国有企业,9.52%的企业为外资企业。约82.68%的企业拥有废水或废气治理设施。本文的核心解释变量Congruence经标准化处理后的数值位于-3.59至1.20之间。
三、实证结果分析
(一)基础回归结果
基础模型回归结果见表2(下頁)。其中,列(1)与列(4)中未添加任何控制变量,列(2)与列(5)添加了包括企业年龄以及是否国有企业、港澳台企业、外资企业的一系列控制变量,控制城市×年份的固定效应,以及行业×年份的固定效应,同时将标准误聚类在城市×行业层级。列(3)和列(6)对核心解释变量Congruence作了滞后一期处理,以缓解要素流动与企业行为相互影响的内生性问题。表2结果显示,核心解释变量比较优势产业发展战略指标的系数始终为负且显著。由此可知,企业所在产业发展越符合当地要素禀赋对应的比较优势,单位产值污染物排放量越低,减排绩效越好,这一结论非常稳健,无论在水污染还是大气污染物的测度下都能够保持成立。平均而言,企业所在行业符合所在地比较优势程度提高1个标准差,企业单位产值的COD排放量下降5.2%,企业单位产值的SO2排放量下降2.1%。可见,产业发展越符合比较优势,企业减排的效果越好。
控制变量中,企业年龄的回归系数正向显著,说明成立时间越短的企业单位产值的污染物排放量越低。企业性质的回归系数显示,与民营企业相比,国有企业排放量相对较大,外资企业和港澳台企业的单位产值的污染物排放量相对更低。为保障研究结果的可靠性与一致性,下文所有回归模型的固定效应和聚类层级均与表2列(2)和列(4)相同,即控制最严格的固定效应与聚类层级① 。
(二)稳健性检验
为保证基础回归结果的可靠性,这里进行了四类稳健性检验:一是添加更多控制变量以缓解遗漏变量偏误;二是采用1998—2009年样本区间,避免规模以上企业筛选标准变化的干扰;三是采用不同的固定效应,以保证回归结果的稳健性;四是基于测量偏误的考虑,采用不同的污染物指标。
第一类稳健性回归是加入更多控制变量,尽可能地控制影响企业排污行为的其他因素。具体地,在保留基础回归中控制变量的基础上,新增其他可能影响企业排污行为的控制变量:一是企业资产负债率,即总负债除以总资产,表征企业的外部融资能力,这也是衡量企业债务水平及风险程度的重要标志。二是固定资产占总资产比重,反映企业的经营灵活度和盈利能力。三是企业经营规模,以从业人数是否大于50人的虚拟变量构建。表3(下页)列(1)和列(5)展示了加入更多控制变量后的结果,可以看到,核心回归系数的绝对值略有增大,符号和显著性均未发生变化,回归结果依然十分稳健。新增控制变量反映出如下信息:企业资产负债率与单位产值污染物排放强度正向相关,企业规模与单位产值的污染物排放强度负向相关。资产结构方面,固定资产占比越高,企业单位产值的污染物排放强度也更高。
在第二类稳健性检验中,调整回归年份区间至1998—2009年。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对规模以上企业的筛选标准自2010年起发生了变化②,这可能导致纳入样本库的企业发生较大变化,影响估计结果的可靠性。因此,表3的列(2)和列(6)中单独采用1998—2009年作为回归样本区间,以排除样本库筛选标准变化带来的干扰,结果显示,比较优势产业发展战略系数的符号与显著性均没有发生变化,回归结果依然十分稳健。
在第三类稳健性检验中,控制企业层面的固定效应,克服企业层面不随时间变化的影响因素干扰,进一步缓解可能存在的遗漏变量问题,表3的列(3)和列(7)显示结果仍十分稳健。此外,此前基础回归中,关于行业固定效应控制采用的是二位码行业分类,我们也尝试了更细致的四位碼行业分类,核心结论在更细致的行业分类控制下仍然成立①。
在第四类稳健性检验中,基于测量偏误的考虑,采用了不同的污染物指标。水污染物指标方面,除了前文基础回归中我们使用到的COD外,另一项指标氨氮(NH)也是测度水体含氮有机物污染的关键指标,并且NH在“十二五”规划后被纳入水污染方面的重点约束性减排指标。类似地,大气污染方面,除了前文基础回归中我们使用到的SO2,另一项指标氮氧化物(NOX)也是造成我国大气污染的关键污染物,同样也被纳入“十二五”规划的约束性减排指标中。因此,表3的列(4)和列(8)中采用企业单位产值的NH和NOX排放量作为不同污染物指标进行稳健性检验②。结果显示,比较优势产业发展战略系数仍保持显著为负,印证了结论的稳健性,即换用其他的污染物的度量指标不会对文章的核心结论产生质的影响。
(三)考虑环境规制的影响
环境规制强度是影响企业减排行为的外部重要因素,这里验证比较优势产业发展战略对企业环保绩效的正向作用,以及这一基础结论是否因环境规制强度变化的影响而改变。在本文研究区间1998—2012年内,宏观层面的环境规制强度的确发生了较大变化,并且存在明显的地区层面差异。“十一五”规划中明确了包括COD和SO2在内的污染物定量减排目标,同时将减排目标完成情况纳入官员考核问责硬约束的体系,作为地方政绩考核评价的重要依据,之后又在“十二五”“十三五”规划中添加NH和NOX等新增的减排约束性指标,形成了地方官员考核问责硬约束的体系并沿用至今。因此,“十一五”规划是宏观层面环境规制趋向严格的标志性政策冲击[6]。
表4对“十一五”规划前后的研究区间进行子样本回归,以验证核心结论是否受宏观层面环境规制政策趋严而改变。表4回归结果显示,无论环境规制是宽松还是严格,“十一五”规划前后的子样本回归中比较优势产业发展战略显著降低企业单位产值的污染物排放这一核心结论均成立。此外,2006年以后外部环境规制普遍趋于严格,减排目标硬约束下全国各地企业单位产值的污染物排放普遍均已下降至较低水平。但是,根据表4列(3)和列(4),地区的产业发展战略越符合当地要素禀赋所对应的比较优势,产业中的企业单位产值污染排放显著减少、减排绩效表现更优。这充分说明了在企业减排影响因素研究中产业发展战略研究视角的重要性。
企业面临的外部环境规制强度除了宏观时序上的波动,还有地区间的差异,目标污染物的减排任务往往是从中央直接下达至省(区、市),再由省(区、市)分解到市县具体执行。尽管在基础回归中,已严格控制城市×年份的固定效应,这意味着城市层面随时间变化的环境规制因素已被包含其中,但为使回归结果更加稳健和可靠,这里进一步控制了省份层面的环境规制强度差异。省份环境规制强度的指标通过计算各省份政府工作报告中与环境相关的词汇出现频次占全文词频的比重来构建①,比重越高表明各省级地方政府越重视环境保护。表5(下页)的回归结果显示,控制省份层面环境规制强度差异后,无论是水污染还是大气污染,核心解释变量产业发展的比较优势一致性系数均显著为负,即越符合比较优势的产业中企业单位产值污染物排放强度越低,环保绩效表现越好,该结论在考虑地区层面的环境规制水平异质性影响后仍然成立。
四、机制分析
上文通过基础回归与一系列稳健性分析回答了比较优势产业发展战略是否影响企业污染排放的问题。在此基础上,进一步考察具体传导机制,即回答比较优势产业发展战略为何能够提升企业环保绩效的问题。要了解企业最终减排绩效表现更好的原因,就要追溯到高能耗高污染企业为满足环保合规性的三种可能的表现行为:改进更清洁的生产技术;加大环保设备设施投入;减产停工控制污染产生①。以上三种机制中,前两种减排机制更有利于高质量发展和“经济—环境”共赢目标实现,而第三种方式以牺牲经济绩效为代价来满足环保合规性,会形成“经济—环境”目标冲突。本文认为,比较优势产业发展战略是决定企业满足环保合规性的能力和意愿的重要因素。企业所在产业越符合当地要素禀赋结构对应的比较优势,其所在产业的资本密集度与所在城市的要素结构越匹配,在生产中就能以较低的成本进行要素投入,更有能力和意愿选择前两项机制实现减排——改进清洁生产技术和增加环保投入。而当企业所在产业发展偏离当地比较优势时,企业生产中要素投入成本相对较高,企业往往缺乏自生能力,需要依靠补贴才能生存。此时若要满足环保合规性,往往缺乏能力实现购买设备和改进技术,更可能采用短期减产停工的方式减少污染产生。这种方式会损害企业经济绩效,且实现的减排是可逆的,没有从本质上实现可持续发展。接下来逐一实证验证比较优势产业发展战略如何影响企业的这三类行为表现,究竟其中哪几项机制是比较优势产业发展战略提升企业环保绩效的真实原因。
(一)改进清洁生产技术
验证比较优势产业发展战略是否通过改进清洁生产技术这一机制促进企业减排,最直接的方式是将企业清洁生产技术作为被解释变量进行回归分析。由于数据可得性限制,无法直接测度企业清洁生产技术,这里采用间接方式验证,通过区分污染物“产生”和“处理”两方面打开比较优势产业发展战略显著降低企业污染排放的“黑箱”。具体地,最终的污染物排放量等于污染物产生量减去污染物处理量,如果企业采用更加清洁的生产技术是比较优势产业发展战略引致企业环保表现更好的原因,实证结果中将看到污染物的“源头产生量”更少,而不是污染物产生后的“末端处理量”增加。
表6(下页)列(1)—(2)和列(3)—(4)分别以水污染物和大气污染物的“产生量”作为被解释变量进行回归,其中列(1)和列(3)未添加任何控制变量,列(2)和列(4)添加了与基础回归一致的控制变量。结果符合预期,无论添加控制变量与否,表6中核心变量系数估计值均显著为负且通过了1%的显著性检验,在水污染和大气污染方面均呈现一致结论,即比较优势符合程度越高的企业单位产值的污染物产生量显著更低,意味着企业环保绩效的改善效益主要源自污染物“源头产生量”更少,即采用了更加清洁的生产技术和方式。原因在于,企业所在产业越符合当地要素禀赋结构对应的比较优势,其所在产业的资本密集度与所在城市的要素结构越匹配,在生产中就能以较低的成本进行要素投入,企业也往往更有能力和意愿改进清洁生产技术。
(二)环保设备设施投入
第二项机制考察产业发展的比较优势一致性如何影响企业对环保设备设施的投入情况,进而传导至环保绩效。表7展示了将企业环保设施购置和运行能力作为被解释变量时产业发展的比较优势一致性对其回归的实证结果。选取三类度量企业环保设施情况的指标:是否购置有废水(气)处理设施;单套废水(气)治理设施处理能力(吨/日);年度企业废水(气)治理设施处理能力合计(套数×能力×天数)。
表7列(1)显示,产业发展的比较优势一致性的估计系数为正,且通过了1%的显著性检验,说明比较优势产业发展战略显著提升了企业购置环保设备的概率。由表7列(2)与列(3)可知,企业所在产业符合比较优势程度提高1个标准差,企业的废水处理设施的单套每日处理能力上限平均约高出6.2%,废气处理设施的单套每日处理能力上限平均约高出9.7%。即企业所在行业越符合所在地比较优势,企业越倾向于购买运行能力更强的废水或废气治理设备。在表7列(4)和列(5)中,被解释变量是年度企业废水(气)治理设施处理能力合计,基于假设企业购买的所有套数环保设施全年运行能处理的污染物总量构建,代表企业潜在污染处理能力上限。结果显示,越符合比较优势的企业,废水和废气处理总能力越强。这再次印证了预期机制,当企业所在产业的资本密集度与当地的资本丰裕程度更为匹配时,更加具备符合当地要素禀赋对应的比较优势,生产中要素投入成本越低,企业自生能力越强,这些企业可能更加具备投入环保设施设备的意愿和能力,从而实现改善企业环保绩效。
(三)排除其他可能的机制:通过减产停产控制污染排放
越符合比较优势产业中的企业最终排污更少,可能还存在另一项减排机制,即这些企业环保绩效的提升是由减产停工的经济代价带来的[7]。那么有没有可能,本研究中越符合比较优势产业中的企业越倾向于满足减排的合规性,以损失经济绩效的方式达到环保绩效目标呢?如果本文研究的遵循比较优势的产业发展对企业环保绩效的提升背后也是经济绩效代价损失带来的,那么引导产业发展与地方要素结构更匹配对于地区发展的意义将会大打折扣。通过实证检验发现这一机制并不存在。表8详细验证了比较优势产业发展战略对企业经济绩效的影响,我们选取了反映企业经济规模的四个指标:工业总产值、主营业务收入、营业利润、从业人员。表8回归结果显示,企业所在产业符合比较优势程度提高1个标准差,企业的工业总产值约提高11.2%,主营业务收入约增加11.6%,营业利润约上升15.3%,从业人员约增加7.0%。结合基础回归中要素结构匹配度对企业环保绩效的改善效应,说明引导行业发展与地区要素禀赋匹配,是实现经济绩效与环保“双赢”的重要路径。这里的分析不仅排除了遵循比较优势的产业发展提升企业环保绩效是通过减产停工的牺牲经济代价机制,而且强化了前文分析中的两项机制的合理性。表8列(3)显示,产业发展的比较优势一致性显著提升了企业利润,进一步佐证了前文中提到的,越符合比较优势产业中的企业越有能力和意愿改进清洁生产技术,并增加环保设施投入。
五、结论与政策启示
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努力实现经济社会发展与生态环境保护协同共进是当前的紧迫任务。在中国式现代化目标实现进程中,促进产业结构调整与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寻求环保与经济绩效的双赢结果,要深入微观企业层面,研究制造业排污主体在面临环保压力下的减排行为选择逻辑。企业选择不同减排方式所传导的经济绩效截然不同,一类减排方式(如减产停工)导向牺牲经济绩效的冲突性困境,另一类减排方式(如清洁生产)则指向环保与经济绩效双赢的策略。后者也是当前政策如《“十四五”全国清洁生产推行方案》等大力支持的减排方式。然而,现有文献对于企业不同减排方式选择的研究,主要集中于对这种差异性的现象描述,而对于其背后的原因尚缺乏讨论。本文从比较优势产业发展战略的视角出发,以城市—产业层面的要素结构匹配程度指标,刻画企业所在产业与所在城市的要素禀赋比较优势的符合程度,为企业在环保压力下减排行为的选择差异提供一种解释。
研究发现,遵循比较优势的产业发展能显著提升企业环保绩效,降低企业单位产值的污染物排放,在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该结论仍然成立。平均而言,企业所在产业符合其所在城市比较优势程度提高1个标准差,企业单位产值的COD排放量下降5.2%,SO2排放量下降2.1%。原因在于,符合比较优势的产业发展能够有效降低企业要素投入成本、提高企业的自生能力,从而促使企业有足够的能力和意愿改进更加清洁的生产技术,增加环保设备设施的投入,以清洁生产的减排方式实现环保绩效提升。
此外,本文的研究也排除了符合比较优势的企业为减排而减产停工的牺牲经济绩效机制,实证结果发现,遵循比较优势的产业发展在推动企业环保绩效上升的同时,产能、利润等经济绩效均未下降。这意味着,企业作为减排主体,满足环保合规性的内生能力十分重要,通过遵循比较优势来发展产业,可提升企业所在城市与产业的要素结构匹配程度,企业能以较低的要素投入成本进行生产,提升企业选择清洁生产减排模式的能力和意愿,从而实现经济绩效与环保双赢的目标。
本文为当前深入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提供了新思路,即除直接运用环保政策工具对污染企业进行约束外,政府還可配合使用产业政策工具,采用遵循比较优势的产业政策,引导产业发展与地方要素结构相匹配的方式提升企业满足环保合规性的能力、意愿和环保绩效表现,实现经济社会发展与生态环境保护协同目标的达成。地方政府在招商引资和制定产业政策时,可更多基于当地要素禀赋结构,根据资本丰裕程度考虑选择具有比较优势的行业发展,而非盲目追求资本、技术密集的高新技术产业。中央政府在为特定行业发展寻找合适的区域时,也可优先考虑资本丰裕程度与该行业更匹配的地区,这样的产业发展战略下的企业更具有自生能力,而非高度依赖政府补贴才能生存,经济和环保双重绩效都会表现更优。实现产业政策和环保政策的协同,可从如下方面着手:
第一,把握好整体和局部、短期和长期的关系,统筹协调好产业发展与节能减排目标。一是增强全国“一盘棋”的意识,把握好地区资源禀赋、比较优势、产业分工的客观实际,研究确定各地产业转型和环保方案,不搞“齐步走”和“一刀切”。二是坚持系统观念,把“双碳”工作纳入生态文明建设整体布局和经济社会发展全局,构建降碳、减污、扩绿、增长协同推进的产业与环保制度安排和统筹协调机制,在多重目标中寻求动态平衡。三是积极参与应对气候变化全球治理。积极参与全球气候谈判议程和国际规则制定,推动构建公平合理、合作共赢的全球气候治理体系,在全球产业竞争中把握战略主动。
第二,在环保政策实施中,要兼顾产业发展与安全。一是减污降碳要确保能源安全、产业链供应链安全,避免对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造成冲击。二是着眼长远,把握好降碳的节奏和力度,依据我国产业发展阶段,实事求是、循序渐进、持续发力。三是以绿色低碳技术创新带动产业转型升级,立足我国国情和“双碳”目标任务推进时间表,紧跟国际能源技术革命新趋势,以绿色低碳为方向,分类推动技术创新、产业创新,把绿色低碳技术及其关联产业培育成带动我国产业升级的新增长点。四是减污降碳中要坚持两手发力,推动有为政府和有效市场更好地结合。坚持环境规制行政和市场化手段并用互补,在政府设定总量管理目标和科学分配初始配额的基础上,健全资源环境要素市场化交易制度。
第三,以产业政策为抓手,助力产业发展与环保目标双赢。一是通过发展遵循比较优势的产业,不断积累要素资源,推动技术进步和产业结构优化升级。从长期来看,经济体产业升级本身就是绿色化、低碳化的过程,高耗能产业占比会逐渐下降,而低耗能产业占比会逐步上升。从短期来看,面临在既定的环保规制约束下,遵循比较优势产业中的企业更具自生能力,满足环保合规性的能力、意愿更强,而非高度依赖政府补贴才能生存,经济和环保双重绩效都会表现更优。二是推行支持绿色低碳发展的重点产业政策。绿色低碳转型是当今时代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方向,我国风电、光伏等绿色产业形成的低成本优势正在重塑我国竞争优势,带动相关行业发展,孕育经济增长新优势新动能。同时,我国巨大的传统产业绿色升级改造需求和绿色消费需求正在催生世界上规模最大的绿色市场,形成经济增长新空间。三是针对绿色发展的产业政策,要筛选合适的技术和赛道。若违背比较优势,长期补贴缺乏自生能力的企业,反而会带来不利的后果。对于重点绿色产业的支持政策,要根据地区的产业基础、资源禀赋来选择合适的地区推进。■
参考文献
[1]GREENSTONE M. The impacts of environmental regulations on industrial activity: Evidence from the 1970 and 1977 clean air act amendments and the census of manufactures[J].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2002, 110(6): 1175-1219.
[2]齊绍洲,林屾,崔静波.环境权益交易市场能否诱发绿色创新?——基于我国上市公司绿色专利数据的证据[J].经济研究,2018(12):129-143.
[3]刘金科,肖翊阳.中国环境保护税与绿色创新:杠杆效应还是挤出效应?[J].经济研究,2022(1):72-88.
[4]LIU M, SHADBEGIAN R, ZHANG B. Does environmental regulation affect labor demand in China? Evidence from the textile printing and dyeing industry[J]. Journal of Environmental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 2017, 86:277-294.
[5]HE G, WANG S, ZHANG B. Watering down environmental regulation in China[J]. The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2020, 135(4): 2135-2185.
[6]陶锋,赵锦瑜,周浩.环境规制实现了绿色技术创新的“增量提质”吗——来自环保目标责任制的证据[J].中国工业经济,2021(2):136-154.
[7]PORTER M E, VAN DER LINDE C. Toward a new conception of the environment-competitiveness relationship[J]. Journal of Economic Perspectives, 1995, 9(4): 97-118.
[8]OBERNDORFER U, SCHMIDT P, WAGNER M, et al. Does the stock market value the inclusion in a sustainability stock index? An event study analysis for German firms[J]. Journal of Environmental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 2013, 66(3): 497-509.
[9]原毅军,谢荣辉. FDI、环境规制与中国工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增长——基于Luenberger指数的实证研究[J].国际贸易问题,2015(8):84-93.
[10]POPP D. Induced innovation and energy prices[J].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2002, 92: 160-180.
[11]余泳泽,林彬彬.偏向性减排目标约束与技术创新——“中国式波特假说”的检验[J].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2022(11):113-135.
[12]LEONARD J. Pollution and the struggle for the world product[M].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8.
[13]金刚,沈坤荣.以邻为壑还是以邻为伴?——环境规制执行互动与城市生产率增长[J].管理世界,2018(12):43-55.
[14]林伯强,邹楚沅.发展阶段变迁与中国环境政策选择[J].中国社会科学,2014(5):81-95.
[15]ANOULIèS L. Heterogeneous firms and the environment:a cap-and-trade program[J].Journal of Environmental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 2017, 84: 84-101.
[16]林毅夫.新结构经济学、自生能力与新的理论见解[J].武汉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7(6):5-15.
[17]林毅夫,付才辉.中国式现代化:蓝图、内涵与首要任务——新结构经济学视角的阐释[J].经济评论,2022(6):3-17.
[18]王勇,樊仲琛,李欣泽.禀赋结构、研发创新和产业升级[J].中国工业经济,2022(9):5-23.
[19]LIN J Y, TAN G. Policy burdens, accountability, and the soft budget constraint[J].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1999, 89(2): 426-431.
[20]林毅夫,付才辉.比较优势与竞争优势:新结构经济学的视角[J].经济研究,2022(5):23-33.
[21]林毅夫.经济发展与转型:思潮、战略与自生能力[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
[22]林毅夫,蔡昉,李周.比较优势与发展战略——对“东亚奇迹”的再解释[J].中国社会科学,1999(5): 4-20.
[23]LIN J Y. Industrial policies for avoiding the middle-income trap: A new structural economics perspective[J]. Journal of Chinese Economic and Business Studies, 2017, 15(1): 5-18.
[24]LIN J Y. Industrial policy revisited: A new structural economics perspective[J]. China Economic Journal, 2014, 7(3): 382-396.
[25]龔强,张一林,林毅夫.产业结构、风险特性与最优金融结构[J].经济研究,2014(4):4-16.
[26]周建军.美国产业政策的政治经济学:从产业技术政策到产业组织政策[J].经济社会体制比较,2017(1):80-94.
[27]MAZZUCATO M. The entrepreneurial state: Debunking public vs. private sector myths[M]. New York: Public Affairs, 2015.
[28]张夏准.富国陷阱:发达国家为何踢开梯子[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7.
[29]阮建青,石琦,张晓波.产业集群动态演化规律与地方政府政策[J].管理世界,2014(12):79-91.
[30]林毅夫,张军,王勇,等.产业政策:总结、反思与展望[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8.
[31]林毅夫,巫和懋,邢亦青.“潮涌现象”与产能过剩的形成机制[J].经济研究,2010(10):4-19.
[32]邓宏图, 徐宝亮, 邹洋.中国工业化的经济逻辑:从重工业优先到比较优势战略[J].经济研究,2018(11):19-33.
[33]林毅夫.解读中国经济[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8.
[34]QIU L D, ZHOU M, WEI X. Regulation, innovation and firm selection: The Porter hypothesis under monopolistic competition[J]. Journal of Environmental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 2018, 92: 638-658.
[35]LIN J Y, WANG F, XIA J, et al. What determines the success of industrial policy: Evidence from China's special economic zones[Z]. Working Paper, Peking University, 2021.
[36]申广军.比较优势与僵尸企业:基于新结构经济学视角的研究[J].管理世界,2016(12):13-24.
[37]林毅夫,张鹏飞.适宜技术、技术选择和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增长[J].经济学(季刊),2006(3):985-1006.
[38]林毅夫,刘培林.自生能力和国企改革[J].经济研究,2001(9):60-70.
[39]陈斌开,林毅夫.发展战略、城市化与中国城乡收入差距[J].中国社会科学,2013(4):81-102.
[40]王坤宇.国家发展战略与能源效率[J].经济评论,2017(5):3-13.
[41]郑洁,付才辉.企业自生能力与环境污染:新结构经济学视角[J].经济评论,2020(1):49-70.